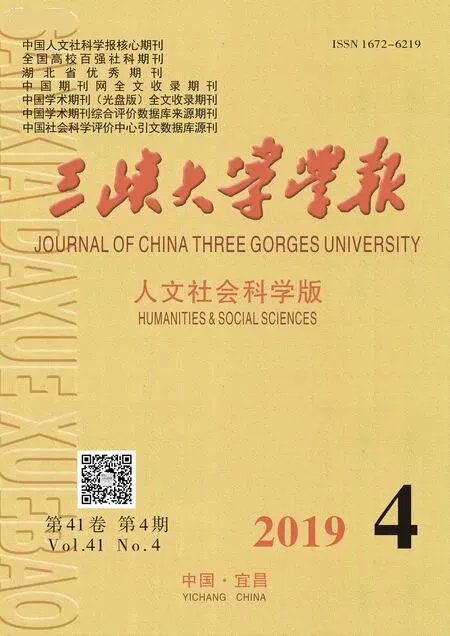“溪州铜柱”所隐含的争论性问题评议
龙仕平
(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吉首 416200)
溪州铜柱是研究河南地方史、民族史的重要史料。溪州铜柱高4米,入地2米,直径0.4米,呈八边形,每一面宽0.15米,重达5000斤。原有铜盖子,相传毁于清中叶[1]。这种规制和形式,乃是模仿东汉马援征服南越交趾所立铜柱,因为马希范自称是马援之后,有完成祖先征服湘西并立下铜柱为证的愿望。目前交趾铜柱早已毁灭,只有这一根溪州铜柱仍然傲立于世,实在是非常珍贵的[2]。
土司制度源于秦汉时期的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所实行的羁縻政策。这种羁縻政策,秉承“修教齐政、因俗而治”的传统理念而与地方少数民族谋求利益平衡及共同发展,从而实现大一统国家稳定与文化多样性传承的民族生存和社会管理的政治智慧,因而对土司历史的全面性研究,有利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政治智慧,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及未来多民族共同繁荣、文化多样性的有效维护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近20余年来,通过“溪州铜柱”这一史料来研究溪州土司历史与文化的论文主要有:龙海清《湘西溪州铜柱与盘瓠文化》(1991年);彭武一《湘西溪州铜柱与土家族历史源流》(1989年);李文君、彭路《溪州铜柱不是图腾柱——与龙海清先生商榷》(1994年);彭勃《溪州铜柱不是“盘瓠图腾柱”》(1991年);黄纯艳《论溪州铜柱的设立及其文化内涵——与<湘西溪州铜柱与盘瓠文化>一文作者商榷》(1991年);彭武文《溪州铜柱及其铭文考辨》(1994);雷家森《溪州铜柱树立与迁徙考论》(2014年)等①。这些研究非常地接地气、通人文,从溪州铜柱的产生、迁移、历史价值、社会地位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为全面了解溪州土司的真实历史与文化打开了一扇扇“亮窗”。然而,对于溪州土司之研究,一直还有几个争论性问题,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为消除这些争论,笔者拟从如下五个方面进行评议。若有疏漏,敬请方家赐正。
一、溪州治所究竟在何处?
古溪州位于武陵山区的西北部,处于云贵高原东侧,介于鄂西山地和江南丘陵的过渡地段,在湖南的西北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府吉首的东北部。古溪州大部分今属永顺县所辖。唐宋时期的溪州分上中下三州,上溪州在龙山,中溪州在永顺西部,下溪州在永顺南部和古丈北部。三溪州都有建治所的说法。
首先,治所建在上溪州说。如果治所建在上溪州,那么,龙山理应成为溪州的统治中心。但从唐置“溪州”,彭士愁以“溪州刺史”标名铜柱,开创了彭氏土司政权八百年的基业。元明以后,封建王朝实行“修教齐政、因俗而治”的少数民族治理政策,彭氏以“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的身份继续管辖这片区域,政治中心就设在永顺老司城。清雍正六年(1728年),永顺宣慰司改土归流,设永顺府,辖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四县原土司管辖地区。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永顺仍为专署所在地。故溪州治所建在龙山境内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其次,治所建在中溪州说。也就是说治所建在永顺西部地区。但中溪州是老司城所在地,老司城是溪州的中心位置,并不是建治所之地。
第三,治所建在下溪州说。笔者认为自土司王朝建都于老司城之后,彭氏土司为巩固疆界而修建了会溪流坪治所,它其实是一个土司王朝边界哨卡,而不是整个土司王朝的治所(即土司王朝政府所在地)。其理由如下:一是彭士愁授封的官衔。据《历代稽勋录》载:“彭士愁在公元908年朝廷议为溪州刺史,公元910年朝廷正式授封彭士愁为溪州刺史,建都老司城,彭士愁于公元912至923建造土司王朝皇城等,都得到当时天朝皇帝的认可。尔后又授封南北江(南边沅水,北边酉水)靖边都誓主。”从此建都中溪州老司城,统辖二十州,从没有建都下溪州统辖二十州的记载。二是当时的管辖区。彭士愁建都于中溪州老司城,辖上溪州龙山、下溪州会溪坪、施溶州、罗依溪和南渭州等。中溪州老司城是溪州的中心位置,而下溪州是边界,不可能将都城建在边界上。三是民间流传。据老司城内和郊区田家湾谢氏历代流传:彭士愁管辖达南江沅水支流的洪江流域,当时洪江流域遭受特大水灾,谢姓祖先原定居洪江与沅江汇合处的江口,遭受水灾那年,随彭士愁迁至老司城和田家湾定居。四是议和期间商议的四件大事:第一,向宗彦愿代替溪州五大姓的向姓在铜柱文中任职签名;第二,向协助彭士愁做好了原吴著冲手下的大将田尔庚归顺工作,彭士愁当即封田尔庚为统兵大将;第三,请旨马希范要向宗彦代管辰州、沅陵、桃源、澧州等南江即铜柱以南疆界;第四,请旨马王上谕朝廷,彭氏从下一代承袭起,其职名要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授封,适当之时在会溪坪铜柱边建于治所。其意是对楚王和朝廷明示彭氏溪州南疆永固在会溪坪。
诚然,自彭士愁建都老司城起,世袭二十八代、八百余年都城从未变动过,会溪坪治所是土司王朝的边界治所、哨卡,对朝廷、对南江各地和楚国起到明示疆界、抗衡、鼎立的作用。只能说明彭氏土司对于下溪州,自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宋,直到公元1279年止,只是彭氏土司自治而已。因此,溪州治所究竟建在何处至今还是一个谜。
二、如何正确客观地评价“溪州之战”?
根据新旧《五代史》《九图志》《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载,大体经过是这样的:后晋天福四年(939年)九月,楚王马希范派军五千人向溪州进攻,当时身为溪州刺史的彭士愁统领溪兵奋力抵抗。由于“溪兵困斗”,溪州刺史彭士愁临危不惧,但溪州一方被打败了。对彭士愁失败后的情况,史书有两种说法,一是《新五代史·楚世家》所说,彭士愁“遣其子师暠率诸蛮酋降于勍,希范乃立铜柱为表,命学士李(弘)皋铭之”;一是宋《方舆胜览》所说,“铜柱在会溪城,晋天福五年溪州刺史彭士愁纳土求盟,楚王马希范请于朝以立之”,而宋《太平治迹统类》则进一步说“晋天福五年马希范与彭士愁约和,而五州酋豪既来盟,乃立铜柱为之界”。请注意,立铜柱为界,而铜柱最初立在会溪坪,那么,彭士愁的统治范围大大缩小,沅江也就是史称的南江,损失殆尽[3]。
这场战争起因如何?到底是谁挑起的?根据铜柱铭文中楚国的说法,是由于溪州“剽掠耕桑,侵暴辰澧”,似乎罪责完全在溪州这一方。辰州是今天的沅陵,在溪州的东南。澧州是今天的澧县,在溪州的东北。如果说,溪州土司能大规模侵凌这两个比较发达的地方,那么,土司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当时溪州刺史所管辖的地方,多达二十多州,包括今天地理上大湘西,即湘西州全部、张家界、怀化一部分和常德少数县份等。但是,其面积既宽,战线又长,力量反弱。所以,溪州土司实际管辖主要在湘西北。铭文说:“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恩知劝,故能历三四代,长千万夫。非德教之所知,岂简书而可畏,亦无辜于大国,亦不虐于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处。”按此说法,彭士愁及其祖父辈,既不欺凌小民,又不得罪大国,上下左右各类关系处理是妥当的。既然如此,溪州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与楚国动起干戈来的呢?铭文说:“无何忽承间隙,俄至动摇。……非萌作孽之心,偶味戢兵之法……”彭武一曾说:“忽、俄、偶几个字都表示了彭士愁出兵不是经常的,只是一时性的;而且这种出兵且非蓄谋(作孽之心),只是‘忽承间隙’,突然钻了一个大空子。”[4]82-83这个空子在马希范这一方面可能只是意谓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而从溪州这一方面来看,却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不能不对楚兵来个迎头痛击。所以楚国指责溪州是战争的挑起者,是强词夺理。但另一个学者叶德宝则认为挑起战争的是溪州一方。因为溪州一方不甘心作楚国的附庸[5]29。
再看战争究竟谁取得胜利?铜柱铭文乃是楚国一方的李弘皋奉命起草,实际体现的是楚王的意志。一个重要特点是,大力宣扬祖宗马援征蛮的赫赫武功,大力宣扬溪州之战楚兵精锐无比,溪兵则降服于天降神兵,不堪一击,只有归顺王化,由此看来楚方打赢了。这次大战之后,溪州作为一个整体并未受到任何损害,反而更加紧密、团结[6]。当然,马希范在和平谈判中做出重大让步,除了溪州一方的强悍,还在于当时楚国内忧外患。马希范继位于932年,死于947年。这十五年马希范都是在内争中度过的。马殷多内宠,诸子嫡庶无别,临终遗命王位要兄终弟继。马希范是等哥哥马希声死后才继承王位的,在位期间害死兄弟马希旺和马希杲,其他兄弟必各怀异志。正是在这种情势下,马希范不得不撤军谈判,签订和平协议,树铜柱为界。
笔者以为,只要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地方政权采取的是羁縻政策,不触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归顺封建王朝是顺应历史趋势的,对形成历史上各民族和睦友好局面是有利的,对于保证中华民族大团结,保证国家的领土完整和长治久安都有好处。马希范也是增进民族团结与和解的重要人物。
三、溪州铜柱移动的原因
溪州铜柱始立地,当在五代时的溪州古城内,即“乃迁州城,下于平岸”前得高山之城。铜柱的移动直接影响溪州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同时也影响溪州自治安宁、和平的环境。溪州铜柱自五代至清代共移动4次,但每次移动的原因不同[2]225。现评议如下:(一)溪州铜柱第一次移动。在五代十国后期,各国争霸,相互兼并,开疆辟土,战争不断,溪州刺史彭允林把溪州治所迁于溪州古老六峒之首的福石峒下游的龙潭城。这次辰州移动铜柱应在五代溪州古城附近,没有超出原溪州古城之内,可能是溪州古城西侧的岩柱湾一带。(二)溪州铜柱第二次移动。太平兴国年间,是彭师杲长子彭允林(彭士愁之孙)袭职间,对其父辈所立铜柱没有征得溪峒同意,被辰州边戌随意移动了。这次铜柱迁移地点应在明滩,即明溪。由此证明溪州铜柱第二次从岩柱湾一带迁于明溪。(三)溪州铜柱第三次移动。据《宋史》载:“至和二年(1055年),知辰州宋守信再次攻下溪州及俘铜柱”。这次征战是铜柱迁出辰州“部内”之后,立在溪州属地内的界标,从此铜柱就变成了争疆之战胜利与失败的标志。(四)溪州铜柱第四次移动。据《苗防备览》转《张沈周总戎事嘞》载:“周一德,金乡人,雍正三年署彝陵镇事,将征容美司,田昱如驻自崖洞,传桑植司为前导,行赴永保等处,永之土人犹顽抗,时驻营鬼滩,谋知有伏波祠,遣记今年、月、日,应我倒铜柱,令尔等为中国民,永人疑,皆蚁山悬崖持抡弩以观,公从容焚香拜庙毕,示诣柱前,举臂撼柱,柱应手倒,永人惊隍,即匍匐曰:谨乞命遵约束,于是风声所布,迎周历三日,而桑、保、永三州所领茅岗、旅溶等十七司尽入版图。田酋为所逼自缢死。”这次倒柱是那么神秘,可见铜柱已无莲花石台坚固之基,周一德很容易在基脚暗做了手脚,一借土人对铜柱的尊崇:二借伏波平蛮之神威,以小计骗土人服,溪州诸司蛮地尽入版图。这次倒铜柱,标志刺史制和后来的世袭士司制政治作用的结束,溪州铜柱只是以民族历史文物而竖立在溪州,它的界标作用亦不复存在了。解放后铜柱还有几次移动,这里不再赘述。
溪州之战后,溪州铜柱成为溪州彭氏集团与楚王结为政治同盟的标志,成为了溪州彭氏地方政权建立的基础。铜柱每一次移动,标志溪州土司疆域或扩大,或缩小,这充分见证了彭氏地方政权发展的真实历史轨迹。
四、溪州土司历史上是否有“槃瓠遗风”?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而伏羲即虙戲的含义,跟土家族崇拜虎相同,且与土家族自称毕兹是一致的。因为“伏羲”一词,在《管子·封禅篇》、《淮南子·览冥训》及《郑氏诗谱·陈》等古籍中都写作“虙戲”。此二字从虍,其义为虎。伏羲时期的虎部落共有两大支,白虎支和黑虎支。从地望上讲,伏羲出生在西戎或西戎地区,即今甘肃天水西北之邽山,邽山得名,亦因伏羲曾在此山画卦,据《山海经·西山经》说,邽山多白虎,伏羲与白虎也似不应没有联系。李巡注《尔雅·释地》“六戎”,其中有“鼻息”。这里的鼻息当是虙戲的误写。《战国策·赵策》有“老臣贱息舒祺”之句,贱息即贱子,息可读子、自,故鼻息可读毕子,毕自,或“毕兹”,则虙戲(伏羲)可读作“毕息”或“毕兹”了。而“伏”与“白”音相近,“呜呼”与“乌虖”的感叹词古亦作“于戏”,则“戏”又与“虎”音同,故伏羲之名又近于“白虎”。照传说,伏羲与巴人是祖孙关系,属于虎图腾,乃西方白虎,由于被汉族接受为古帝王的正统带头地位后,变为与龙蛇特别有关,乃至专与龙蛇(女娲氏)系统联系在一起。“毕兹卡”的“卡”,是族或部落之意。所以,这个“毕兹卡”的本意并不是“本地人”,而是被强制使用的虎氏族称呼,它贯穿着从有巴人到现今土家族之始终。值得注意的是,虎部落的两大支,白虎支(巴人为例)显然是父系制度,黑虎支(巫蛮为例)则是母系制度,这从侧面反映了远古族内群婚制。后来,虎部落发生分裂,黑虎支南移,白虎支东移。东移的白虎支,一度隶属于以鸟为图腾的东夷少昊集团,因而又有白虎夷之称。少昊即白帝天王,以鸟为图腾,故白虎部本图腾上又曾被冠以鸟图腾。白虎部落由于不适应东夷集团的生活,而且一定是跟东夷集团产生矛盾,因而又不得不向西迁移,《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路史·后记·太昊伏羲氏》亦载:“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炤;后炤生顾相夆处于巴,是生巴人。”《郑氏诗谱·陈》也有“大神虑戲”的记载。这说明虎伏羲确是巴人的祖先,“巴人”即是“白(虎)人”的转音,即今白虎土家族。
关于(白)虎神的传说,还散见于其它典籍。晋代干宝《搜神记》载:“汉江之间有貙人,其先,廪君之苗裔也,能化虎。长沙所属蛮县东高居民作槛捕虎。咋忽被召,夜僻雨,遂误入此中,急出我!曰:‘君见召,不当有文书耶?’即出怀中召文书,于是出之。寻视,乃化为虎上山走。或云:貙虎化为人,好著紫葛衣,其足无踵。虎有五指者皆是貙。”江汉指的是长江汉水流域,即东汉时江夏地区,有史书所载之江夏蛮,即被迫迁去的巴人后裔住此。晋代张华《博物志》卷二:“江陵有猛人,能化为虎,俗又曰貙”。江陵即汉代南郡郡治所在地,《后汉书》所说的作为巴人后裔的南郡蛮就活动在这一带地区的长江两岸。左思《蜀都赋》也说“皛貙氓于萋草”。貙,本是虎的一种,所以,能化虎的人称貙,这里的貙人,亦应是广义巴人一支。清代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曾多次提到贵州的人化虎和虎化人之事,如“江都俞生说:曾蜀定番州(今贵州惠水县)事,一但随群虎入山,形体尤人,……久之,渐变虎形,不复至。”等等。虽是村野之言,但亦有白虎图腾崇拜的影子,这类传说在鄂西还很多。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云:“虎在巴人生活里的中心地位发展到一个程度,终于与巴人合二为一,巴人就是一种虎人。”到后来,白虎神形象逐渐脱离了群体,成为单一的、超然的白帝天王,白虎图腾崇拜达到了顶峰。
但是到了唐宋年间,土家族历史可谓承上启下,要研究好这段历史,溪州铜柱铭文史料无疑是最好的读本。铜柱上呈现“槃瓠遗风”四个字,于是个别学者将土家族也当成槃瓠之后,甚至说溪州铜柱说成槃瓠图腾柱。所谓“槃瓠”,乃是一条五彩斑斓的神犬。将盘瓠神话故事记入书的,首先是东汉时代应劭的《风俗通义》。三国时的《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妇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茧。夫人盛瓠中,覆之以盘,俄顷化为犬,其文五色,故名盘瓠。”晋《荆州记》云:“沅陵县居酉口,有上就、武阳二乡,唯此是盘瓠子孙。……二乡在武溪之北。”干宝《晋记》曰:“武陵、长沙、庐江郡夷,盘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盘瓠凭山阻险,每常为害。糅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俗称赤髀横裙,即其子孙。”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云:“时帝(昔高辛氏)有畜狗,其毛五色,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自相夫妻。……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服斑斓,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以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央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水经注·沅水》条有云:“武陵有五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五溪蛮也。水又经沅陵县西,有武溪,源出武山,于酉阳分山。水源石上有盘瓠迹犹存矣。”宋《溪蛮丛笑·序》云:“五溪蛮皆盘瓠种也。聚落区分,名亦随异。沅其故壤,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瑶、曰僚、曰僮、曰仡佬。风俗气息,大略相似。”[7]20
一条五彩斑斓的狗,传说它与高辛氏的公主婚配之后生下六男六女,这六男六女又自相结合,繁衍而成为槃瓠种。这是一种狗图腾崇拜。实际上,可能因为远古时期,狗帮助过苗瑶等族的祖先,于是尊狗爱狗,以狗为族徽,为图腾。这在苗族和瑶族的风俗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瑶族有一种作为家谱的《过山榜》,其中就有像这样的祖源记载。瑶族应为槃瓠之后,《过山榜》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图腾崇拜常转为宗教信仰,有些宗教仪式,也常常显示出图腾特征。晋《搜神记》就说槃瓠子孙“用糁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这些祭仪对狗行为的模拟一直流传到后世。《皇清职贡图》卷四:“(兴安县)平地瑶……岁首祀盘瓠,杂置鱼肉酒饭于木槽,扣槽群号以为礼。”《岭表纪蛮》就说得更具体:“狗王,惟狗瑶祀之。每值正朔,家人负狗环行炉灶之匝,然后举家男女,向狗王膜拜。是日就餐,必叩槽蹲地而食,以为尽礼。”清乾隆《辰州府志》和《泸溪县志》载:“辛女岩在邑南三十里,危峰高耸,有石屹立如人,相传高辛氏之女于此化为石。”《大清一统志》亦载:“辛女岩在泸溪县南三十里,奇峰绝壁,高峻插天,壁立水中,有石屹立如人,相传高辛氏之女化石于此,傍有石林。”民国时期传教士陈心传亲到实地考察后说:“……一石如人立,苗人传其为辛女飞异之化石,名辛女岩,帝女岩。”[8]45-51
然而,土家族地区找不到上述传闻和仪式,也就是说没有“槃瓠遗风”。土家族乃是以白虎为图腾,即白虎崇拜。湘西有的地方确曾保留有“槃瓠遗风”,但都在苗族地区。清代《苗防备览》卷二十就曾指出镇溪军民千户所,即今吉首“俗多祖槃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注所说的与槃瓠有关的石窟和武山本来就在泸溪一带。由于传说的纷扰,资料的缺乏,以偏概全,很容易将湘西各个少数民族都当作槃瓠种。沅水在沅陵以上有五条支流,分布的绝大部分是蛮族。就笼统称为“五溪蛮”,并简单地与槃瓠种联系。铜柱正文是楚王马希范手下文臣李弘皋(《旧五代史》写为李皋)写的,他沿袭某些旧说,写下了“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族聚”这样的话。李弘皋这样写,并没有错。因为槃瓠传说区域很宽,沅水流域多个地方多个民族都有这个传说,都有这个认同感,而土家族只是湘西一族,居住靠北的酉水澧水一带,没有这个传说和认同。但是,铜柱所立地方就有苗族同胞聚居。彭武一和彭南均等先生对于铜柱上的说法和某些学者的类似观点持不同意见。但只要明确土家族不是槃瓠之后就可以,只要明白溪州铜柱是溪州土家族土司和楚国汉王马希范签的和平条约就可以,其他是非,存而不论。彭士愁代表溪州,当时没提出异议,大约也因为无关紧要。事实上早在唐宋年间《通典》、《太平寰宇记》等书是将溪州这一带定为板楯蛮的,没有归在槃瓠种之内[9]246。至于土家族族源问题,至今聚讼纷纭,没有公认的结论。建国之后,以潘光旦先生为代表的专家团到湘西进行调查研究,经过六年探索,出版《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这是土家族得以确认单一民族的重要依据,也为确认或者说探讨土家族族源有很大的帮助。1957年国务院正式下文确认土家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之后湘西成立土家族苗族联合的自治州。
五、溪州彭氏土司究竟来自何方?
最早提出彭氏土司来自江西的观点,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谢华先生《湘西土司辑略》一书,当时影响甚大。溪州地区唐以前不见有彭姓的记载,加上铜柱上刻有“历三四代,长千万夫”这样的字眼,于是作为溪州大姓的彭姓,就被称为不是土著,是从外地迁进来的。根据是家谱都说彭士愁是江西吉安府人氏。而且,湘西北土家族强宗大姓,都有口碑传说,说祖上来自江西。但是,土家学界对此还是争论不休,至今没有定论。民族学家也是彭氏后人的彭武一先生,原来主张江西迁来说,后来彻底改变看法,力主土生土长说。理由有两点:一是明朝人都说永顺蛮人不识字;二是家谱漏洞多,靠不住[4]132。明英宗天顺五年《大明一统志》六十六说永顺“土民……不晓文字”,万历《广志绎》卷四说永顺保靖“不识文字”,等等。永顺司家谱修缮也有一个过程,民国《永顺县志》所辑录的资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卷三十二说明代正德年间宣慰使彭世麒撰有《宣慰司志》,“大约纪其世职山川景物之类”。将该司志扩大为《永顺司宗谱》,该书是乾隆初年写的,作者是改土归流时被迁到江西吉水末代土司彭肇槐的后代彭声振。这本《宗谱》与后来的家谱显然不同之处就在于“详(彭)玕略(彭)瑊”。《宗谱》本来写有“后晋溪州刺史彭士愁墓在辰州(沅陵)彭家湾”。彭肇槐之后儿代在修家谱时却将彭士愁墓写成是在江西永新县寮山(很可能是衣冠冢)。这样一来彭士愁就彻底变成江西人了。
关于“彭氏土司来自江西”说。其理由如下:一是正史有记载。谢华《湘西土司辑略》是研究铜柱学的奠基之作。此书指出彭氏土司来自江西吉安[10]7。二是地方有传说。湘西北土家族地区,有许多民间故事,显示来自江西。三是家谱有记载。土司彭姓家族和湘西北强宗大姓的家谱,都有这个说法。吉首大学学者田清旺,是溪州铜柱记十八洞长官司中田家洞司田姓土司后裔,他根据永顺彭氏土司族谱和江西吉安彭氏族谱,连世系和辈分用字都相同,证明古来一家。针对彭士愁任溪州刺史,连其父一起只有两代问题,田清旺也提出看法,认为溪州铜柱上彭氏七家,从辈分看已经四代,因而也力主江西迁来说[11]10。四是改土归流时,雍正皇帝诏令永顺末代土司彭肇槐遣返江西原籍居住,中央对此严肃谨慎[11]158。
尽管如此,但我们认为,彭氏土司来自江西不等于说湘西所有彭姓土家人都来自江西;同样,更不能宣布湘西土家族都来自江西。1983年湘西州政府和民委召开土家族历史研讨会,就土生土长说和江西迁来说,各执己见。最早提出溪州刺史彭士愁是汉人且来自江西的是潘光旦。他在《浙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中详细论证彭氏土司来自江西,土家族主要来自于古代巴人。彭官章同意巴人后裔说而不同意彭氏土司来自江西说。由此可知这是互相联系和区别的两个问题:土家族来自于古代巴人,并融合其他邻近古代民族如乌蛮人、濮人等,逐渐形成土家族。
但彭姓土司可能来自江西,而且很多大姓跟着过来,并在保持汉文化的同时,也土家化了。笔者支持这种观点[12]402-424。如今,关于溪州铜柱的研究,已经成为土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老司城申遗的成功,势必会出现更多的研究成果。史学界期待“溪州铜柱学”的极早落幕,更期待土司文化研究落地生根,全面揭开其历史长达八百年土司王朝的真正面纱。
注 释:
① 参见龙海清《湘西溪州铜柱与盘瓠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彭武一《湘西溪州铜柱与土家族历史源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32页;李文君、彭路《溪州铜柱不是图腾柱——与龙海清先生商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彭勃《溪州铜柱不是“盘瓠图腾柱”》,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黄纯艳《论溪州铜柱的设立及其文化内涵——与<湘西溪州铜柱与盘瓠文化>一文作者商榷》,《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彭武文《溪州铜柱及其铭文考辨》,岳楼书社出版社,1994年第98页;雷家森《溪州铜柱树立与迁徙考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