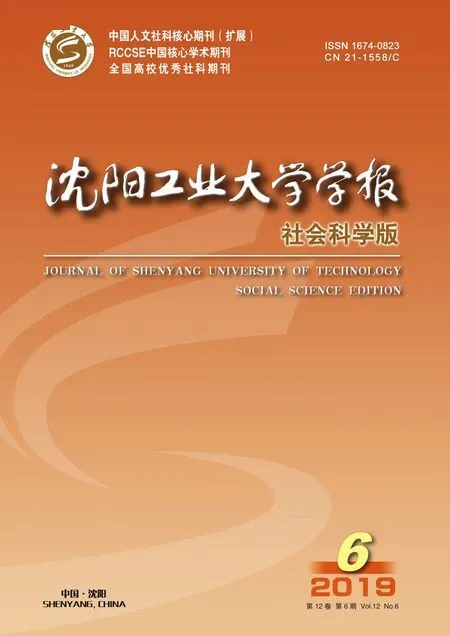国际组织与成员国法律责任多重归属问题研究*
王百卉
(南开大学 法学院, 天津 300350)
一、法律责任多重归属原则的确立背景
1. 一般情形下国际组织承担责任
近年来,随着一些跨国性和全球性问题的加剧,国际组织的重要性愈发突出。正如Niels Blokker所言,在一个充满跨境和全球性问题的世界上,例如近年来埃博拉和打击IS这样的问题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处理这些问题,而制度化的国际合作符合共同利益[1]。可以说,国际组织在处理复杂跨境问题时发挥了巨大作用。例如,2014年联合国安理会针对非洲埃博拉疫情的决定(1)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177 (2014),UN Doc S/RES/2177 (On the Outbreak of the Ebola Virus in,and Its Impact on,West Africa) In it,the Security Council determined “that the unprecedented extent of the Ebola outbreak in Africa constitutes a threat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Preamble) See als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170 (2014),UN Doc S/RES/2170 (On Threats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caused by Terrorist Acts by AI-Qaida).以及2014年安理会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ISIL的打击决定(2)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178 (2014),UN Doc S/RES/2178 (On Threats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caused by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s) In Resolution 2178,the Security Council reaffirmed that “terrorism in all forms and manifestations constitute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threats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Preamble) and took measures against Al-Qaida,ISIS and the AI-Nusrah Front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in which Resolution 2177 was adopted.The UN Secretary-General stated:“The Ebola crisis has evolved into a complex emergency with significant political,social,economic,humanitarian and security dimensions.The suffering and spill-over effects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demand the attention of the entire world.Ebola matters to us all……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is out pacing the response.No single government can manage the crisis on its own.The United Nations cannot do it alone.” (Report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on its 72681 meeting on Peace and Security in Africa-Ebola,UN Doc S/Pv.7268 (2014),pp.2-3) In the Council meeting in which Resolution 2178 was adopted,US President Obama stated:“If there was ever a challenge in our interconnected world that cannot be met by one nation alone,it is this one-terrorists crossing borders and threatening to unleash unspeakable violence.” (Report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on its 7272 meeting on Threats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caused by Terrorist Acts,UN Doc S/Pv.7272 (2014))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应当意识到,关于国际组织仍然存在大量法律问题。1980年以来,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在某些国际组织的活动特别是那些执行项目的活动(如维和行动或执法行动)中,经常会造成伤害,产生很多法律责任问题。例如,1985年,银行和锡中间商因国际锡理事会的破产而受到损害;联合国也无法阻止1995年在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发生的种族灭绝案[1]。当国际组织和成员国在行动中遇到大量法律难题时,国际社会亟需一部成文法来解决这些法律问题。2011年,国际法委员会二读通过了《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标志着对国际组织和成员国法律责任问题的研究有了成文法依据。
关于国际组织和成员国的责任问题,《草案》第3条写到:每一个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均引起该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因此,原则上国际组织应承担独立的法律责任,但《草案》并未对该独立责任进行进一步分析。虽然《草案》中没有详细介绍国际组织的独立责任问题,但为了全面挖掘国际组织和成员国的责任归属问题,有必要从本质上理解该独立责任。
国际组织为什么要独立承担责任、是否有能力承担国际责任,首先要从法律人格上进行分析。只有确立了其自身地位,承认了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才可能产生责任问题。在早期国际组织出现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均未被认同。直到20世纪以后,随着各类国际组织的发展壮大,基于其法律实践的客观现实,其法律人格才得到了国际普遍承认。《草案》中承认了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但这与其责任又有什么关系呢?梁西认为,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就是它成为法律关系主体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2]。饶戈平指出:“所谓国际人格系指具有独立参加国际关系并直接承受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的能力的集合,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3]因此,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是其承担责任的前提。实际上,赋予国际组织一定的国际法人格,就等于在这些国际组织具有国际法人格的受限领域内由其独立承担责任,否则就与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本质相违背[4]。正是因为国际组织有了法律人格,才可以像主权国家一样参与国际事务,在这一过程中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可见,独立的法律人格是现代国际法中国际组织承担责任的基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政府间国际组织是目前的国际法主体之一,由于其国际法主体地位成为条约缔结方。1986年3月21日订立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明确规定,国际组织具有与其他国际法主体缔约的权利。从法理上看,作为国际条约缔约方,国际组织既然享受了条约赋予的权利,也必然要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如果国际组织的行为违反了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就应该承担国际责任[5]。
在国际组织的众多特征中,对于责任问题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独立法律人格。学界往往认为独立人格与独立责任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也被国际法判例多次阐释。可以认为,国际组织之国际法律人格与其独立承担责任之原则应当是牢牢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任何一方被否定则另一方亦不存在。因此,在国际组织和成员国法律责任的归属问题中,通常情况之下国际组织独立承担责任应无疑问。
2. 特殊情形下国际组织和成员国责任归属不明
由于国际组织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且享有自治权,一般来说其应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而成员国不应承担责任。但实践中存在一种比较普遍且有争议的情形,即国际组织法律人格遭到滥用时的责任承担问题。例如,在国际组织决策过程中,成员国对其决定实施影响与控制。其实对于任何国际组织来说,总是有一些国家存在较大的影响力或具有某种形式的主导地位,这从本质上而言是正常的[6],然而如果对这种权力的制约出现了严重失衡,那么就很容易出现法律人格被滥用的情形。又或者在实施层面,成员国在执行国际组织决议的过程中对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滥用,往往造成国际组织和成员国责任归属不明。在这些环境中,成员国保留了一些自由裁量权,这些权利构成了其在国际组织行动方面的责任基础[7]。此时,成员国“浮现在国际组织的面纱之上”,通过介入国际组织的行为进行独立的意思表示,体现了一定的法律人格,进而从不同方面影响国际组织的行为。
下面以南联盟诉北约国家案(即使用武力合法性案)为例,具体阐述成员国在执行国际组织决议过程中对国际组织法律人格进行滥用,从而造成责任归属存在争议的情形。1999年3月21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南斯拉夫进行空袭。南斯拉夫将参与空袭的十个北约成员国诉至国际法院。由于同一系列案件众多,这里以南斯拉夫诉美国为例。南斯拉夫于1999年4月29日向国际法院请求适用临时措施,请求法院命令“美利坚合众国立即停止其使用武力的行动,并且不再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使用或威胁使用任何武力行为”。最后,国际法院以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为由,驳回了南斯拉夫的请求。在本案中值得关注的是对南斯拉夫实施空袭的北约成员国的辩护意见。如英国在其反对意见中认为,其在采纳这一决议之前的行为应当被认为是北约运作的一部分(3)Case concerning Legality of Use of Force (Serbia and Montenegro v.United Kingdom),Preliminary Objection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p.66,para.446.;法国认为,北约具有这样一个法律人格并且不能因此在涉及国际责任问题时被认为是透明的(4)Case concerning Legality of Use of Force (Serbia and Montenegro v.United Kingdom),Preliminary Objection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p.66,para.448.;葡萄牙则称,正如已经被证明的,在科索沃发生的所有活动都是由北约这一主体决定的,其成员国的武装力量被置于北约的命令之下(5)Case concerning Legality of Use of Force (Yugoslavia v.Portugal),Preliminary Objections of the Portuguese Republic,p.40,para.135.,因此北约作为国际法律人格者应在国际法上对其在科索沃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而非其成员国(6)Case concerning Legality of Use of Force (Yugoslavia v.Portugal),Preliminary Objections of the Portuguese Republic,p.40,para.136.,任何该国际组织的责任无论如何都不能涉及其成员国。由此可以看出,北约各成员国都主张将法律责任归属于北约。但在2011年北约主导的对利比亚的空袭行动中,其所作出的回应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在2011年3月31日北约关于利比亚问题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在记者问到是否有北约成员国在利比亚部署地面部队这一问题时,其回答道:“不,我们(在利比亚)并没有地面部队,如果有一些国家(在利比亚)有地面部队存在,这是其国家本身的存在而非北约的存在。”(7)参见http://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71907.htm?selected Locale=en中26’01”至26’17”内容:“No we don’t have NATO forces on the ground,if there are forces by nation,presences by nation is not NATO presence as such that what manner because we respond for NATO.”这与使用武力合法性案中北约成员国的观点截然相反。国际法委员会在2004年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第二次报告中也指出:“该军事行动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焦点是必须把行为归属于某个国际组织还是归属其某些或全体成员。”(8)Giorgio Gaja.Special Rapporteur,Second Report on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CN.4/541 (2004),para.40.
在国际法上,与使用武力合法性案类似的这种责任归属不明的司法实践比比皆是,如2007年欧洲人权法院合并审理的“拜拉米(Behrami)和拜拉米诉法国”和“萨拉马提(Saramati)诉法国、德国和挪威”两个案件以及1974年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2003年联合国在刚果的行动(联刚行动)所产生的法律责任问题(9)见联合国与比利时(《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35卷191页)、希腊(同上,第565卷3页)、意大利(同上,第588卷197页)、卢森堡(同上,第585卷147页)和瑞士(同上,第564卷193页)缔结的规定赔偿的协定。。在这些实践中,越来越明显的是联合国的控制力有限,更加正式和以任务为基础,而派遣国在维和任务期间往往在实地发挥关键作用,因为它们有可能直接向其特遣队发出命令。因此,在联合国维和期间将所有行为归于联合国往往远非现实,国际法中不法行为的可归责性和责任问题非常复杂[8]。
关于法律责任归属不明的争议和分歧,进一步分析其原因会发现,在这些情形中首先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遭到了破坏,其独立承担责任的基础丧失;其次,成员国的介入对行为的归属也产生了影响,从而最终造成责任的归属难以确定。具体来说,在实施这些行为时,国际组织对成员国进行总体的指挥和控制,而成员国对实施的具体行为也进行了控制。成员国虽然是在执行国际组织的决议,但其在实施行为的时候很有可能基于其他目的实施了相似行为。由于这些行为之间界限很模糊,很难确定究竟是哪一方的意志,双方的法律人格在其中均有一定体现,造成国际组织和成员国法律责任归属不明的情况。那么在实践中如果发生这种责任归属不明的情形,应如何确定国际组织和成员国的责任?本文认为,在国际组织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并不排除成员国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将行为归属于国际组织并不排除再将该行为归属于国家,因而应坚持国际组织和成员国法律责任的多重归属原则。
二、适用法律责任多重归属原则的原因
1. 多重归属原则确立的前提
在国际组织和成员国责任归属不明的情形中,确立责任多重归属的前提是明确此时成员国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成员国作为行为实施者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履行国际组织义务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如前文所述,由于国际组织的独立法律人格以及国际组织对其成员国享有的自治权,使得成员国在一般情形下“消失在国际组织的面纱背后”,不承担责任。但在某些情况下,正如Niels Blokker所提出的那样,这种“面纱”可能被刺穿或抬起。此时成员国“在面纱背后清晰可见”,则无论其责任是否与国际组织的责任同时存在,都可以在机构范围内对不法行为负责。如果成员国在制度背景下使用其自由裁量权并以完全自主的方式行事,这种可见性就会变得更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制度上的“面纱”似乎是不合适的[1]。
一方面,成员国潜在的责任几乎是国际组织与成员国在决策和执行方面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成员国将国际组织决策机构纳入其中,并在保护其国家利益的同时可能影响后者最终的决定。成员国在执行国际组织决定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为国际组织并不总是拥有自己的执法机构。如果在这种决策和实施的背景下发生不法行为,成员国可能会因其行为而承担责任[9]。另一方面,成员国责任与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及其权利的转移有关。成员国作为国际组织的创造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一些权利,因此在承担国际法义务时就会产生责任问题。事实上,国家对国际组织约定的遵守必然意味着自愿地限制自身的行动自由,让位于由此产生的新行为者的主体人格。但在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件中,强调的是转移行使主权权利而不是冻结,由此导致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的相互作用。这使得在整个行使主权权利的过程中能够捕获各种各样的行动——由国际组织或其成员国或两者共同作为国际法主体——其各自可能在法律上与责任相关[10]。
因此可以认为,尽管国际组织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和一定的自主权,但成员国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国际组织的制度面纱背后”。由于国际组织保留了一定的透明度,成员国作为国际组织的创造者和参与者在一些情形下仍然可以“浮现于面纱之上”,这对责任归属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可以确定,当国际组织和成员国责任归属不明时,可以适用责任的多重归属,即国际组织和成员国均对不法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
2. 多重归属原则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两起案件为例,从反面论证不适用多重归属原则造成的不利后果,进而确定适用多重归属的现实意义。
2007年,欧洲人权法院合并审理了两起有关联合国维和行动责任归属问题的案件,即拜拉米案(Behrami and Behrami v.France)和萨拉马提案(Saramati v.France,Germany and Norway)。这两个案件的相似之处是均涉及维和部队的行为造成受害国的损失,而受害国起诉要求相关成员国承担责任,并没有起诉联合国。欧洲人权法院首先要解决的是维和部队的不法或不作为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由成员国还是联合国承担责任的问题。法院最终作出的判决是,由于联合国对维和行动有最终控制权,所以不法行为应完全归属于联合国,而欧洲人权法院对联合国无管辖权,所以驳回了起诉(10)Behrami v.France;Saramati v.France (dec.),nos.71412/01 & 78166/01,Eur.Ct.H.R.2007.(Joint Admissibility Decision)。欧洲人权法院未考虑不法行为除归属于联合国外还可能归属于其成员国的问题,也未考虑联合国及其成员国为同一不法行为共同承担责任之情况,仅将责任归属于联合国,从而形成了单一归属的司法判例。
欧洲人权法院未承认责任多重归属原则的后果,一方面是造成人权保护的缺失,这一点一直以来都为国际法学界所批评。由于在联合国的权威下行动,即使《欧洲人权公约》缔约国违反了该公约所规定的义务,也不必承担国家责任,这势必会影响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造成人权保护的空白。一些评论人士在审查上述两案的推理时认为,法院试图回避其作为司法机关的主要任务——按照平等关系提出的事实追求正义。此外,法院似乎没有在治外法权上监督缔约各方部队的行为,因此他们可以自由行事[11]。奥雷尔·萨里也指出,判决使得欧洲国家的维和部队能够避免承担公约中规定的人权义务。另一方面,仅仅将责任归属于国际组织也会造成受害者得不到足够的救济,甚至无法得到赔偿。在传统国际法看来,只有主权国家才享有诉讼权利,可以参与国际争端解决程序,在国际诉讼中占有一席之地[12]。目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国际实践中起诉国际组织的例子并不多。这不是因为受害者没有对国际组织的活动提起诉讼,而是因为没有任何常设国际机构(或组织)有权审议涉及国际组织争端案件,特别是涉及国际组织的案件。例如,根据《联合国国际法院规约》第34条第1款,法院中得为诉讼当事国者,限于国家。即使在欧洲人权法院也不可能起诉国际组织,该司法机构只有在缔约国(仅包括国家)违反《欧洲人权公约》所保护的人权的情况下才会审议争端[13]。因此,当受害者起诉国际组织时,法院会以管辖权豁免为由拒绝审理,导致受害者既无法从国际组织处得到赔偿,又无法向本应承担责任的成员国寻求救济,最终只能以自助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或“自愿”满足罪犯的要求以获得损害赔偿[13]。然而,通过这些方式得到的赔偿远远小于对其造成的损失。
虽然Behrami/Saramati案中的欧洲人权法院将专属责任归咎于联合国,但其最新的判例已经远离这条道路。在阿尔吉达(Al-Jedda)案中,英国军队以及美国和其他联盟伙伴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情况下进入了伊拉克,并且英军对阿尔吉达实施了拘禁,为此阿尔吉达在欧洲人权法院对英国提起了诉讼。法院最终的判决认为,该拘禁行为应归属于英国(11)AI-Jedda v.UK,7 July 2011,Grand Chamber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Judgment,No.27021/08,para.83.(Al-Jedda ECHR Grand Chamber Judgment)。在该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同一行为可归因于联合国和成员国,即承认存在双重或多重归属[14]。
多重归属的适用不仅能弥补单一归属造成的不利后果,而且也具有现实意义。首先,多重归属的适用有利于人权保护。对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受害者提供双重或多重归属保障,使得无论他们身在何处都能在任何人权方面得到最佳保护。通过双重或多重归属监督派遣部队的行为,降低派遣部队对外国受害者所造成的伤害[14]。即使产生责任问题,国际组织此时的豁免权也并不能减少受害者的利益,受害者可以在法院提起针对成员国的诉讼,有利于对受害者的保护。而在现实方面,多重归属的适用能有效减少成员国由于不必担心承担法律责任而实施不法行为的数量,抑制成员国滥用国际组织的集体合法化功能。此外,次要或同时承担责任不会破坏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因此对联合国独立性的关注不会成为否认这种责任的理由。我们认为,成员国并不是由于其成员的身份而承担责任,其只应根据对不正当的行为的“贡献”而承担责任[14]。
综上所述,当国际组织和成员国法律责任归属不明时,应当坚持适用责任的多重归属原则。这是因为:首先,当成员国参与到国际组织的行动中时,在“刺破国际组织面纱”的情形下,存在承担责任的理论基础。其次,将责任仅仅归属于国际组织会造成人权保护方面的空白,不利于对受害者利益的保护,而适用责任的多重归属原则能够弥补人权保护的缺失,有利于成员国履行注意义务,防止滥用其权利实施不法行为。因此,国际社会有必要正式确立责任的多重归属,明确国际组织与成员国之间的责任问题。2009年8月国际法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第47条正式确立了责任的多重归属原则。
三、法律责任多重归属原则的具体适用
1. 多重归属原则的确立过程:从行为归属到责任归属
在国际法学界,关于国际组织与成员国间法律责任的多重归属问题虽然很早就受到关注,但一直都难以达成共识,且在2009年《草案》一读通过以前无相关成文法加以规范。关于成员国的责任问题,首先可以从相关的条约中寻找。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的规定,条约是国际法的一个重要渊源。归纳总结各种国际条约中关于国际组织和成员国责任的规定,为多重归属原则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关于成员国责任方面的条约,最突出的领域就是国际空间法。早在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的第6条就有如下规定:“各缔约国对其(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非政府的团体组织)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所从事的活动,要承担国家责任,并应负责保证本国活动的实施符合本条约的规定。非政府团体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活动,应由有关的缔约国批准,并连续加以监督。保证国际组织遵照本条约之规定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进行活动的责任,应该由该国际组织及参加该国际组织的本条约缔约国共同承担。”[15]606此外,1972年订立的《空间实体造成损失的国际责任公约》,对国际组织及其成员国的责任分配进行了详尽的规制。该条约第22条第3款规定:“若国际政府间组织根据本公约的规定对损害负有责任,该组织及其成员国中的本公约缔约国应承担共同及个别责任。”[15]625在外层空间以及核领域,还有很多条约涉及国际组织和成员国的责任分担问题,但这些条约涉及的领域有限,无法形成一般的法律原则,而且无法适用于当国际组织法律人格被滥用造成成员国和国际组织责任归属不明的情形,因此有关国际组织与成员国法律责任的多重归属一直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直到《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完成,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开始筹备编纂国际组织责任法之时,关于国际组织和成员国法律责任归属的问题才逐渐确立。有关责任的多重归属,在2001年通过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47条中写到:“在数个国家应为同一国际不法行为负责任的情况下,可对每一国家援引涉及该行为的责任。”即如果多国同时违背一项国际义务,则所有国家均须为此负责,只不过这里的主体只是国家而并未涉及国际组织。在编纂《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时,在国际组织与成员国法律责任归属问题上,国际法委员会首先关注的是行为归属问题,在确定了行为归属之后才最终确定了责任的多重归属。
关于行为的归属问题,2004年国际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第二次报告的第二部分——行为归属于国际组织和行为归属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写到:“然而,行为并非一定只能归属于一个主体。同样,也可以设想某一行为应同时归属于一个国际组织及其一个或多个成员的情况。”(12)Giorgio Gaja.Special Rapporteur,Second Report on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CN.4/541 (2004),p.3,Article 6.例如,在1999年多国轰炸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领土的事件中,该军事行动争议的焦点是必须把行为归属于某个国际组织还是归属于某些或全体成员。关于这一问题报告认为:“将行为归属国际组织并不排除再将该行为归属国家,反之,归属国家也并不排除归属国际组织。”报告同时指出,行为的双重归属通常导致共同责任或共同和各自责任(13)Giorgio Gaja.Special Rapporteur,Second Report on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CN.4/541 (2004),p.3,Article 7.。因此,国际法委员会对行为的多重归属是持肯定态度的,且意识到行为归属与责任归属是密不可分的。虽然行为的多重归属已在报告中指出,但是在实践中的应用却很少。例如,在Behrami/Saramati案中,显而易见欧洲人权法院并未考虑成员国的行为,而是直接以联合国对行为行使有效控制为理由确定了联合国的单一责任,并被其他法院援引。行为的归属问题没有得到国际司法界的重视,因而造成责任的多重归属原则也一直没有得到适用。
2009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61届会议一读通过的《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第47条正式确立了责任多重归属原则。在责任多重归属问题上,国际法委员会是由浅入深地从行为归属到最终责任归属考虑的。第47条第1款写到:“在一个国际组织和一个或若干国家或其他组织对同一国际不法行为应负责的情形下,可以对每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援引涉及该行为的责任。”(14)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on Its Sixty-first Session,Text of the Draft Articles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64/10 (2009),p.119,para.7.关于第47条的评注中写到:“本条处理了一国际组织与一个或多个其他实体(国际组织或国家)一起对特定不法行为负责的情况。”(15)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on Its Sixty-first Session,Text of the Draft Articles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64/10 (2009),p.120,para.1.从这一条款中,首先可以看出多重归属原则的适用主体已经从国家扩大到国际组织。其次,条款中涉及行为归属与责任归属两个层次,最后确立了责任的多重归属。
目前,一般理论将国际法律责任定义为:“因国际不当行为或国际法未加禁止的行为而对其他国际法主体及其人民造成的损害,国际法主体所应承担的国际法律后果。”[16]因此,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是确定行为的归属。当确定行为并非只能归属于一个主体时,我们认为责任也并非只能归属于一个主体。在实践中,具体实施行为的主体固然是行为的归属方,但在行为实施过程中还涉及其他相关行为,这些主体也很有可能成为行为的归属方从而承担一定的责任。
2. 多重归属原则的适用标准:有效控制
上文已经确定了国际组织和成员国责任归属不明时应当坚持责任的多重归属原则,但若想确定责任的多重归属,首先要解决的是行为的归属问题。即使国际法学界不排除行为可以归属于不同的主体,对于行为归属也要确定一定的标准,不能任意增加行为主体。例如,如果在国际组织的一个行动中,一个成员国只是负责传递消息,那么是否也要将不法行为归属于这个成员国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所以在实践中,如果没有一个标准对行为归属进行限制,那么有些人就会利用《草案》第47条肆意增加责任主体从而减轻自己的责任,造成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影响国际秩序的维护。总之,在确定成员国责任的时候,要根据各个国家在某个不法行为中的参与程度来判断,也就是说,就某个不法行为而言并不是每个成员都要同等负责的[17]。因此,有必要为多重归属的适用确立一项标准,明确在达到什么条件时可以将行为归属于一个主体,进而确定责任的归属。本文认为,应当坚持以有效控制为标准。
在国际法上,有效控制这个概念首先被作为确定领土主权的一项标准。在国际组织法律责任方面正式提出有效控制的概念则是在《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ARIO)中。在其起草过程中,早期确定了有效控制的标准,因为它与国际军事行动有关。鉴于指挥和控制的正式分配及其行使的事实,国际法委员会认为“与特定行为归属有关的决定性问题似乎是谁有效控制了有关行为”(16)Giorgio Gaja.Special Rapporteur,Second Report on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CN.4/541 (2004),para.40.。国际法协会同样将有效控制确定为行为归属的检验标准(17)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Accoun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Report,Berlin Conference,26 November 2004),p.28.。2009年一读通过的《草案》第6条规定:“一国的机关或一国际组织的机关或代理人在交由另一国际组织支配之后,其行为依国际法应视为后一国际组织的行为,只要该组织对该行为行使有效控制。”由此可以看出,谁对行为实施了有效控制,该行为就应归属于谁。
关于有效控制和行为归属以及责任之间的关系,国际法委员会及国际法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在2011年国际法委员会第63届报告中,关于《草案》第7条的评注写道,归属要求人们确定“谁对有关行为有效控制”。长期以来,控制一直被认为是归因的核心,因为这一概念特别适合用来理解在一个国际法主体和一个需要归属的个人的行为之间的联系[18]。一些学者已经确定了控制在国际法中对归属所起的根本作用:Hyde在论及关于军事活动的国际责任时认为“控制产生责任”[19];Amrallah认为“国际法中国家的责任是以其可能行使的实际控制程度来衡量的”[20];Eagleton肯定说“责任来源于控制”[21]。根据牛津和剑桥在线词典的解释,控制可以定义为“影响或指导人们的行为或事件过程的权力”(18)Oxford Living Dictionaries,https://en.oxford 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control,archived at https://perma.cc/8MSX-H2CR.或对他人的行为施加影响的行为(19)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nline defines “control” as “the act of controlling something or someone,or the power to do this.”See Cambridge Dictionary,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control,archived at https://perna.cc/7K7Z-WQD9.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defines “control” as the ability “to exercise restraint or direction upon the free action of;to hold sway over,exercise power or authority over;to dominate,command.”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Clarendon Press,2nd Ed,1989).。控制的概念与权力(指挥或影响他人行为或事件进程的能力)、权威(发出命令、作出决定的权力和强制服从与影响对某人的行为或某事实施产生效果的能力)(20)Oxford Living Dictionaries,https://en.oxford 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control,archived at https://perma.cc/8MSX-H2CR.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基于这一概念,行为归属应确保对某一行为负有责任的实体是对该行为的发生能够进行有效控制的实体。从本质上讲,有效控制和行为归属及责任归属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正是因为成员国或国际组织控制了一个行为,才使该行为归属于该实体,而行为的归属最终导致了责任之归属。
在分析了有效控制和归属之间的关系后,本文认为有效控制可以作为多重归属原则适用的一项标准。那么在具体的行动中,这一标准如何在国际组织和成员国法律责任的多重归属中具体适用呢?正如国际法委员会在其对ARIO的评论中所解释的那样,有效控制应在三个条件(21)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on Its Sixty-first Session,Text of the Draft Articles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66/10 (2011),p.87,para.8.下进行评估:第一,它必须是“事实”的;第二,是对于士兵的“特定行为”;第三,评估时考虑到国际组织及其成员运作的全部事实情况和具体情况。简而言之,ARIO第7条中对有效控制的检验需要确定哪个实体在具体的事实中真正掌握了有害行为[22]。
首先,在事实要素下,必须确定控制是否具体和实际行使,且超出了正式的行为授权[23]。实际上,对有效控制的检验并不完全抛弃形式方面,而是试图核实成员国向国际组织正式授权的控制权是否真实,或成员国是否确实保留或恢复了控制[24]。关于事实控制,可以通过2014年海牙法院关于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诉荷兰案的判决来阐释。在该案的判决中,海牙地区法院认为“国家确实将荷兰营的指挥和控制移交给联合国”,并且“荷兰营确实被联合国命令并作为联保部队的一个部队运作”(22)Hague District Court 2014,July 16,par 4.37.。但是海牙地区法院还表示,在移交“指挥和控制”之后,提供部队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保留撤兵的权利,并有权停止参加行动(完全指挥)。国家还保留惩罚上述军事人员的权力,对他们进行纪律处分并使他们受到刑法的制裁(23)Hague District Court 2014,July 16,par 4.57.。最后,地区法院在该案中认定了荷兰有效控制的时期和领土(称为“小安全区”),荷兰营在这一时间框架内和这一领土上的所有作为和不作为都可归因于荷兰。由于这一时期的这一行为不属于联合国任务规定的范围,因此法院认为所有行为都属于越权行为。在该案中,处于“小安全区”的一段时期内,荷兰实施了事实要素上的控制:一方面,荷兰保留了对部队的指挥和处分等权利;另一方面,荷兰实际行使了这种控制,并超越了联合国的授权。
其次,重要的是对被指控为不法行为的控制而不是控制整个任务,以及必须通过充分考虑具体情况和事实背景来评估有效控制。这一条件强化了必须在具体情况下进行控制的要求。对整个任务牵头组织的控制不是归因的决定因素,因为对某些行为的控制可以——正式地并且根据命令安排——由成员国行使。例如,成员国可以将一些业务控制权转移到领导该行动的国际组织中,但同时保留对某些特定任务的控制[18]。2004年乔治·加亚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第二次报告中,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有效控制的讨论第48条也提出:“重要的是有效控制程度而不是完全控制权,联合国对国家特遣队从来没有完全的控制权。这一点还为某些行为的双重归属敞开机会。”(24)Giorgio Gaja.Special Rapporteur,Second Report on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CN.4/541 (2004),para.21.例如,Behrami/Saramati案中法院在认定联合国责任时采取的是最终的、完全的控制权标准(25)Behrami v.France,App No.71412/01 & Saramati v.France,Germany and Norway,2 May 2007,Grand Chamber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Admissibility Decision,No.78166/oi.。关于这一标准,国际法委员会在2009年一读通过的《草案》第6条关于Behrami/Saramati案的评注中提到:“人们可以正确地指出,该法院假如适用委员会规定的关于有效控制的标准,则行动的控制似乎比最终的控制更有意义,因为最终的控制几乎没有在有关行动上意味着任何作用。”(26)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on Its Sixty-first Session,Text of the Draft Articles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64/10 (2009),p.120,para.1.不仅国际法委员会,联合国秘书处2008年6月关于联合国驻科索沃过渡时期行政代表团的报告中也与最终控制的标准保持距离。
从本质上看,确定对具体行为的控制是为了解决责任问题。对待责任问题,我们秉持的态度是每个主体都要为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既不能随意增加责任主体,也不能减少任何一个责任主体;每个主体的权利义务都是对等的,既然享受了权利那么就要承担义务,没有享受权利的主体也不应该给其施加义务。最终的控制很有可能造成责任的单一归属,而具体行为控制的标准恰恰能够很好地平衡每个主体之间的关系,确定各自的责任。因此,为了确定责任的多重归属,在判断行为归属时应坚持有效控制标准,而这种有效控制是一种对具体行为的控制,并不是最终的、总体的有效控制。
四、结 论
过去十几年国际上发生的事件表明,国际组织在处理复杂国际性问题上拥有更广泛的权利,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作用日益增强。但在某些情况下国际组织也被作为实施特定成员国战略目标的工具,其法律人格遭到滥用,造成国际组织和成员国的法律责任归属问题日益突出。基于国际组织的独立法律人格及其享有的自治权,一般情况下应坚持国际组织的独立责任。但是在大量的实践中,成员国在执行国际组织决议的过程中会对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进行滥用,此时成员国的法律人格“浮现在国际组织的面纱之上”,造成责任归属不明。在此种情形中,应当坚持责任的多重归属原则。一方面,成员国存在承担责任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将责任仅仅归属于国际组织会造成人权保护方面的空白,而适用责任的多重归属原则能够弥补人权保护的缺失,也有利于成员国履行其注意义务,防止其滥用权利实施不法行为。在具体确定责任的归属方时,结合多重归属原则的确立过程,本文认为首先应从行为归属方面进行分析,因为行为与责任是一体的,如果一个主体成为行为归属方,那么其就符合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而在确定行为归属方时,本文认为应坚持以有效控制为标准,并且这种有效控制是一种对具体行为的事实控制。
综上,对于国际组织和成员国的法律责任多重归属问题,本文认为在成员国执行国际组织的决议过程中对其法律人格进行滥用造成责任归属不明时,首先应摒弃责任的单一归属而适用《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第47条确定的责任多重归属原则;进而需要运用在某一行动中具体行为的有效控制标准确定行为的归属方,最终据此确定责任的归属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