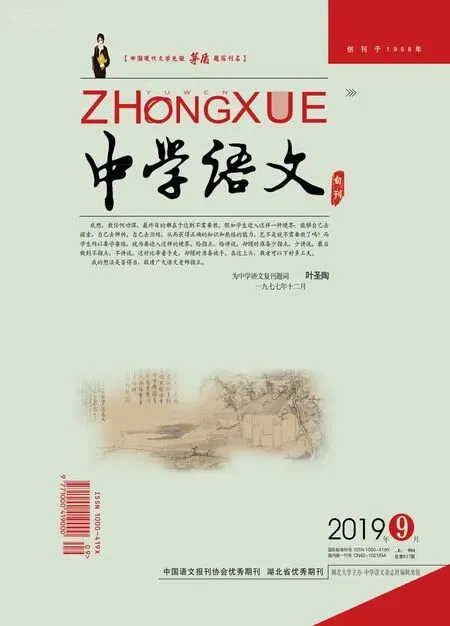熟人社会中孔乙己的自我认知与外部评价
冯明涛
一、孔乙己的熟人社会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熟人社会”的概念,他力求以质朴的语言赋予其大胆朴素的文学化构想:“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冶出来的结果。”在熟人社会中,圈子文化盛行,“积久了的经验”是维系生存的基本法则,人与人乃至人与物之间都相互熟悉,这种熟悉也是人们的一种生活规律和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鲁镇是鲁迅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地方,那里住着孔乙己、祥林嫂、七斤、单四嫂子等人,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
新闻共享,隐私透明。熟人社会流动性小,相对封闭,费孝通说,“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高老夫子》中的话说是“酱在一起”。人很难有隐私,什么都可以成为看的材料和谈资。祥林嫂被婆家劫走,“闹得沸反盈天”;“败坏风俗”的事众人皆知,失去祭祀的资格;连如何“竟依了”第二任男人也成为柳妈的笑料。孔乙己一到酒店就成为新闻人物,人人皆可肆无忌惮地笑几声;偷书被吊打的丑事,被“故意的高声嚷”出来;读过书,没进学,抄书营生,也被人家“背地里议论”;“一副凶脸孔”的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逗他,引人发笑;连偷东西被打了半夜打折了腿,也被当面取笑。“酱”在一起的熟人社会,因为熟,所以无话不说,飞短流长,不惮挖苦讽刺,因为缺少新闻,所以任何一点新与异都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娱乐,“让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且这些快活的人不以为恶,因为在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授受荣辱恩怨都不可能一笔一笔算清,你来我往,总体均衡,“从来如此”未必对,却人人如此。
舆论监督,感情淡漠。舆论是人们对特定话题所反映的多数意见之集合,是一种社会评价和社会心理的集中体现。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具有长久性和非选择性,人人都在看与被看中,社交是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具有长久预期的特点,“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社会性质,面子是头等大事,因而舆论的监督力量尤其明显。在鲁镇,七斤辫子被剪酿成风波后,他要打听咸亨酒店的舆情,因为在舆论的监督下,从众是最好的选择。孔乙己偷书被吊着打、偷东西被打折腿后被众人挖苦、嘲讽、羞辱则是舆论用道德谴责的手段进行监督。然而监督虽有客观效果,却无主观用意,与沸盈的舆论形成反差的是,人们对被议论者的态度是淡漠的, 所谓关心不过是表象。感情淡漠是熟人社会保护精力的手段,是稳定呆滞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所以,在颇有“古风”的鲁镇,祥林嫂丢失阿毛的故事被咀嚼成沉渣后无人问津;料理完单四嫂子的儿子的丧事,红鼻子阿拱依然唱曲儿自乐;孔乙己虽然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在别人看来,他“许是死了”,哪怕“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也泛不起任何涟漪。
矛盾融合,律令自成。在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人们摸索出矛盾却融合的处世之道。单四嫂子一面不希望助她一臂之力的是阿五,一面又觉得阿五有些“侠气”。孔乙己跟酒店里的人相互鄙视,又相互带来优越感;短衣帮明知酒店老板卖酒会羼水也只会亲眼看酒从出坛到入壶,而不会跟老板摊牌阻止;在“教人活泼不得”的酒店里,小伙计可以游刃有余地判断何时可以笑几声;酒店老板一边提醒孔乙己欠着十九个钱呢一边又给他一碗温酒。熟人社会遵循的是小范围内约定俗成的人情规则,人情规则很大的特点就是通融,排斥具有固定性的律令,对是非曲直情感判断的标准根据现实利益做可滑动的通融。但鲁镇并非律令缺失,而是自成一套律令体系,如敬畏权势、崇拜金钱等。敬畏权势可以让人心生秩序感,崇拜金钱可以给人带来优渥感。这种遵从未必是有意识的,而是千百年来无意识的沉淀。人人会意会,遵循不言而喻的规则。酒店老板对小伙计不满意,却碍于荐头的情面而不能将其辞退;孔乙己偷了何家的书被私自吊打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孔乙己写了服辩仍被打折了腿到别人口中却是一句“丁举人家的东西,偷得的么”的奚落。
二、孔乙己的自我认知与外部评价
自我认知是个体对自己存在的觉察、理解和评价,包括对自己的行为和心理状态的认知。外部评价亦称他评,是指被评对象以外的组织或个人依据相应的评价标准对被评者进行的评价活动。
在自我认识时,孔乙己坚持读书人身份,不做半步退让。在衣着上,他坚持穿长衫。尽管“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尽管这件长衫“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补,也没有洗”,尽管要站着喝酒,他也坚持不脱,因为长衫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文化身份的标志,代表着他的文人立场和趣味。长衫帮从他身上得到“人有我优”的优越感,他却可以从短衣帮身上得到“人无我有”的优越感。所以有人问他当真识字么时,他“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在语言上,他坚持使用文言。文言是他的象征身份,也是他的话语舒适区。在与短衣帮说话时,明明可以使用口语,却绝不放弃文言,尤其是与人话语交锋陷入窘境的时候,便全是之乎者也之类让人不懂的话。《阿Q 正传》中的假洋鬼子明知别人不懂洋话却偏说,洋话于他是炫耀的手段,孔乙己明知别人不懂文言却偏说,文言于他即是自我保护又是彪炳身份的手段。在社交上,他坚持与读书识字有关的社交内容。他没有财力“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也就无法融入长衫帮;在短衣帮中强颜撑起的优越感又被他人“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的讥诮消解,让他“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成人世界的社交他是被动的,却也溃败,这让他把社交对象转向少年的“我”,开口便是“你读过书吗”,哪怕“我略略点一点头”都能引出他一大堆“很恳切”的话和“极高兴的样子”,而“我”的毫不热心又让他“显出极惋惜的样子”;在少年身上撞了没趣之后,他又转向孩童,甚至不惜损失对于他来说很宝贵的茴香豆。在孩童身上找优越感即使找到了也胜之不武,他却依旧翻船,或许他只是有社交需求罢了,但他那句“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其实是本我的自然流露,这句话不是说给孩童听的,而是说给自己听,他无时无刻不咀嚼着自己的读书人身份。在品德上,他坚持诚信。在酒店喝酒,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哪怕自欺欺人, 他也强辩 “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偷东西被打断了腿,自知理亏,只得低声狡辩“跌断,跌,跌……”;虫豸一样濒死的阿Q 生怕被人笑话尚且使尽平生的力画一个圆一点圈,清高自守的孔乙己更要维护品德上的优越感,物质上越是支撑不起,他越要在精神上寻求。
然而,由于关注点和视角不同,孔乙己的自我认知和外部评价截然不同。在鲁镇这个熟人社会,孔乙己只是泯然之众,他自我认知的读书人身份,在外部评价中不过是个看与笑的材料。熟人社会注重圈子,讲究“自己人/外人”社会生活模式,排斥圈子外的人事。小说展现的社会环境应是科举未废时,孔乙己能读书,说明他一开始就不在短衣帮的圈子,没落后既不能像范进对科举那样执着,发愤图强,从癞蛤蟆变成文曲星,又不能像范进没中举时那样稳做一个小人物,融入市井小民中。“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身份尴尬,他想通过读书跻身长衫帮,却未进学,不得不堕入短衣帮,可他虽精神上坚守读书人身份而穿长衫,现实中却只能站着喝酒,所以两个圈子都不收留他。长衫圈他高攀不上;短衣圈也视他为异类。因为他背叛,失败后又不归顺。短衣帮的态度,即是对他不幸无能、滑稽酸腐的蔑视,也是对他不幸偏争、不安分守己的愤怒,并将这些情绪通过幸灾乐祸、挖苦嘲讽表现出来;他们够不着也不敢揶揄长衫帮,便通过排挤跟长衫帮有相似性的孔乙己来发泄对长衫圈的不满。于是,孔乙己落入鄙视链的底端。咸亨酒店的人评价孔乙己的标准也尽量跟他自我认识的标准相悖,孔乙己守不住“君子固穷”,饥寒起盗心,或许他真觉得偷书不算偷,人们却打人专打脸,诛人只诛心,说他“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偷的是“丁家的东西”而不说“丁家的书”。所以他的名字可以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从描红纸上摘下来的绰号;他脸上的新伤疤、腿上的残疾、语言上的迂腐、科举上的失败都是别人的笑料;他不会营生,穷困潦倒,便落得一个“好吃懒做”的恶名;他好心搭讪的结果是少受世风浸染的“我”也认为“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连纯真的孩童围住他,也是因为“听到笑声,也赶热闹”,热闹赶完,又“都在笑声里走散了”;他长久经营的诚信换来的也只是掌柜的淡然一句口头提醒——“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
孔乙己自觉不自觉地认定自己生活在一种关注之中,尽管这种注视只是一种浮皮,但依然可以左右他的行为,故面子的本质就是“自卑”,由外部评价左右生活以及日常行为的状态。个体对自我的觉察,或者说意识的形成,是来源于个体对外界环境刺激后,经由记忆和思想产生的反应。对于外部评价的刺激,孔乙己以一种执拗的态度面对。鲁迅在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说国人“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孔乙己偏不融入短衣帮,偏跟他们不一样,以冷眼面对嘲讽。鲁迅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孔乙己虽然偶有不屑置辩的时候,但是终没有孤独者的耐力,忍不住“不十分分辨”,甚至“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去争辩。可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由很多人组成的固化的熟人社会,他要么融入其中,学得意会,要么溺水其中,窒息淹死。他改变不了自己,也没法被熟人社会改变,其结果只能是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