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论的尝试和困境
——亚里士多德的属人的善的统一性问题
王 纬
一、问题的缘起
本文重构并批判当下流行的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出发解答这一问题的尝试,即所谓的“模仿论”阐释。我的讨论分三个部分:首先,我梳理这一问题的文本线索,并简要勾勒学术史上两种对于这一问题的经典回答;之后,我给出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出发解答这一问题的第三种尝试——模仿论——的思路和文本依据;最后,我从文本和理论思路两方面出发批判这种尝试。在结论中,我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区别于其理论哲学)的个体性特征出发,消解这三种阐释(特别是第三种)所基于的问题本身。
二、问题的相关文本线索
(一)我们有文本证据证明亚里士多德对属人的善和幸福持有一种一元论的看法,即,所有从属性的善[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1 1094 a 15。作为达成一个唯一的善的手段而存在,并且因为这个唯一的善而是善的。

最后,最重要地,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了真正的幸福是作为努斯的活动的沉思:


第十卷中还有其他类似的段落。考虑到所有这些例子,我们似乎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所有属人的善构成了一个宏观的目的链条,从处于最底端的金钱和荣誉等外在善开始,通过各种看似的内在善,最终到达了唯一真正的内在善——沉思活动。这个链条中的每个成员都以下一个成员为目的,并以沉思活动为其最终目的,因而它们的可欲性最终地取决于沉思生活的可欲性。
(二)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某些文本及其理路,我们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对于属人的善似乎持有非一元论的看法:

综合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内部似乎存在着对于属人的善和幸福的两种不同理解:按照其中的一种理解,只有沉思生活才是最高善和幸福,而按照另一种理解,合乎伦理德性的实现活动也应该被称为幸福,或者至少是幸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三、对这个问题的传统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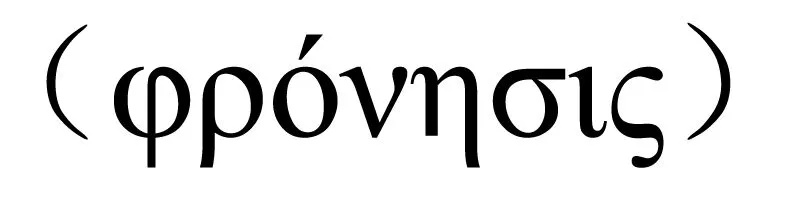
四、模仿论:以里尔(Lear)为代表的第三种阐释
里尔在其著作《幸福生活和最高善》(2004) 中作出了第三种尝试。[注]Gabriel Richardson Lear, Happy Lives and the Highest Goo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里尔的思路在某种意义上接续了库珀(1987)。然而,库珀认为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明言伦理生活的善和沉思生活的善之间的关系,[注]John M. Cooper, “Contemplation and Happiness: A Reconsideration”,Synthese 72, 1987, pp. 201-202: “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似乎更倾向于说:那些在伦理上合德性的活动,……只应被视为幸福的一种。(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幸福的一种),是因为它们与一个幸福的人所进行的沉思活动有着某种联系。与伦理活动不同,沉思活动因为它们的内在特征(这个特征使它们恰好类似于众神的沉思)而直接符合幸福这个称号 。但这个联系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明言。”和库珀不同,里尔所要寻求的,恰恰是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理论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的联系出发,给予亚里士多德的属人的善的理论一个形而上学的理论奠基,从而将伦理生活的善和沉思生活的善在某种意义上调和起来。[注]Lear 的尝试并非完全独创,在她之前,很多学者指出过类似解释的可能性,其中的代表是David Charles, “Aristotle on Well-Being and Intellectual Contempl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s 73, 1999, pp. 205-223. Lear是第一位以专著的形式系统化地尝试这类解释的学者。关于Charles的解释和Lear的解释的区别,参考Gabriel Richardson Lear, Happy Lives and the Highest Good: An Essay on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88 n. 32.里尔的工作是最近亚里士多德学界一系列的试图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与其理论哲学作联系的解释倾向的一部分。举例来说,玛丽斯卡·罗伊尼森(Mariska Leunissen)在其著作《从自然习惯到伦理德性》 中试图给予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一个生物学的理论奠基。[注]Mariska Leunissen, From Natural Character to Moral Virtue in Aristot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以里尔为代表的第三种阐释从《尼各马可伦理学》1.6中的如下段落出发:[注]Gabriel Richardson Lear, Happy Lives and the Highest Good: An Essay on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88 ff.

根据第三种阐释,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谈论的“哲学的另一个分支”是形而上学,[注]当然,“形而上学”是一个后起的概念。 这里的“哲学的另一个分支”,用亚里士多德自己的概念来表述,是“神学”或“第一哲学”。而这种“被普遍地述说着的善”属于《形而上学》第十二卷(Λ)中所论述的作为不动的推动者的神。在里尔看来,为了理解伦理学领域中人类的可实现的善为什么是善的,我们必须探究形而上学领域中属于神的,对人来说无法实现的善,及其在整个世界中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天球为了自身的善而转动,但是它们做这个行为的欲望并不指向自身的善,而指向不动的推动者,即善本身。天球的行为的善之为善依赖于它和善本身的相似性。同样,月下世界中的元素和生物的运动和行为一方面为了自身的可获得的善,一方面是对于天球的永恒的圆周运动的模仿:四元素的相互转化是一种永恒的圆周运动,而生物一代一代的生成也是一种永恒的圆周运动。[注]见《论生成与毁灭》2.10 336b34-337a7。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元素和生物那里,它们对于永恒的圆周运动的模仿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理智行为:模仿的倾向内在于它们的本质结构之中,因而是它们的无意识的自然。[注]Lear也将这种无意识的模仿称为“趋近”(approximation),见Gabriel Richardson Lear, Happy Lives and the Highest Good: An Essay on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0, pp. 72-73, pp. 78-92.
总而言之,作为推动者的神,通过其自身的永恒的沉思活动,为世界确立了善的标准。天球通过永恒的圆周运动模仿或者趋近推动者,而生灭世界中的元素和生物通过模仿天球的永恒运动间接地模仿神的活动。并且,这种模仿或者趋近活动是自然的,并不预设模仿者本身对于永恒的善的意识以及理智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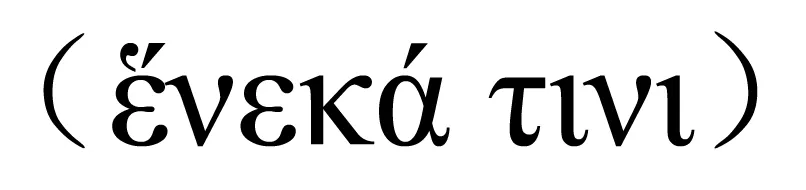
五、模仿论所面临的困难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1.6中,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论述不存在独立于范畴的“普遍的善”这一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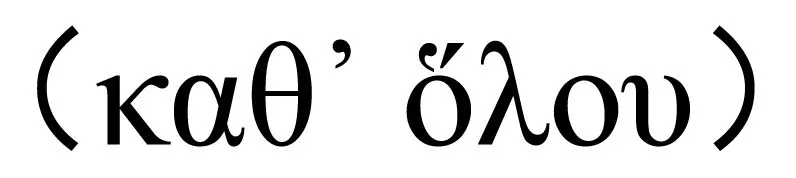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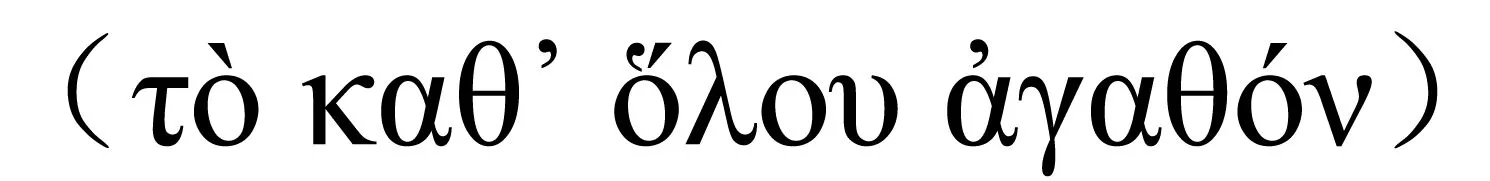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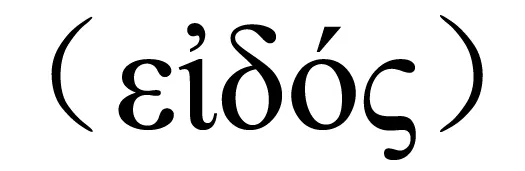
模仿论面临的第二个反驳来自宇宙论。模仿论本身预设了一个作为万物模仿对象的唯一的最高的神:天球直接模仿最高的神,而自然物模仿天球。然而,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并不支持这样的解释。亚里士多德宇宙中的同心天球有47个或者55个,每一个天球都对应一个不动的推动者。[注]见《形而上学》12.8 1073a37-40。因此,除了第一天球之外的所有天球都只是间接地被最高的神推动,且仅限于它们的周日运动,即,最高的神所决定的宇宙中的善仅限于时间(即日夜)的永恒交替。天球模仿不动的推动者这一假设[注]这一解释是成问题的,参见Sarah Broadie, “Que Fait Le Premier Moteur D’Aristote? (Sur La Théologie Du Livre Lambda de La Métaphysique )”, Translated by Jacques Brunschwig,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183 (2), 1993, pp. 375-411.只能解决每一个天球和它自身对应的推动者之间的关系,而对于宇宙的目的论结构来说,关键的是诸推动者的善以及诸天球的善是如何统一的。不动的推动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最高的推动者是否是低层推动者的模仿对象?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说明。《论生存与毁灭》2.10 提到模仿的著名段落只是强调了四元素的循环变化是模仿圆周运动,但并不涉及推动者之间的关系。[注]见《论生成与毁灭》2.10 337a1-7。而《形而上学》9.8中提到的四元素对于不朽之物(即天球和天体)的模仿在于四元素和不朽之物都是现实的,也并不涉及不朽之物之间的关系。[注]见《形而上学》9.8 1050b28-30。
总而言之,模仿论牵涉到一系列的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柏拉图哲学化的倾向。而模仿论之所立足的文本,《尼各马可伦理学》1.6以及《形而上学》Z.7-9,亚里士多德在其中都明确地反对了柏拉图以及柏拉图派的观点。因此,模仿论作为一种试图沟通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至善的理论尝试是不成功的。
六、结 论
如果模仿论是不成功的,那么我们如何解决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关于至善和幸福的阐述的矛盾?如果不能从神的沉思中获得衡量任何善之所以为善的客观标准,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来说,德性所对应的善和幸福究竟因何为善?

作为当代道德哲学研究者,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善的客观标准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我们对于道德辩护(moral justification)的关注以及对于道德休谟主义的警惕。对于我们来说更紧要的问题是,如何避免道德相对主义、如何辩护或者反对某些特定的伦理世界观。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伦理学看似提供了这样一条关于幸福是什么的客观的标准。然而,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问题恰恰是,一方面,伦理的客观性基础并不建立在普遍理性之上,而是基于人的实践和感性意义上的自然禀赋;另一方面,对于善之所以为善的追问本身带有柏拉图主义的色彩:道德正当性的问题会使得我们假设出一个普遍的道德标准,这样一个道德标准因其普遍性而不再是实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