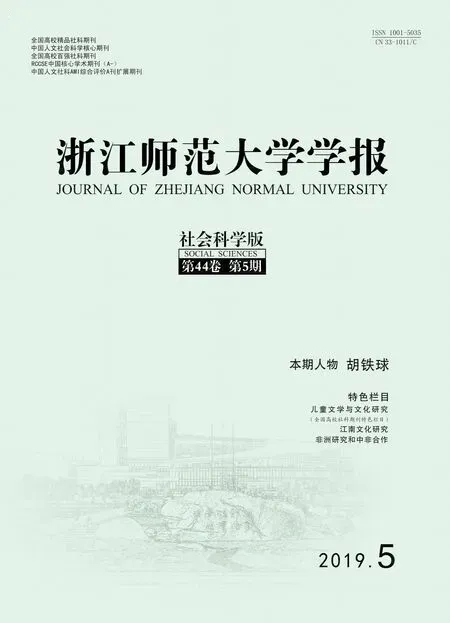城市坊巷文化的可见性生产
——以金华酒坊巷为个案*
张凯滨
(浙江师范大学 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对城市而言,建筑是刻画历史的书卷,时间斑驳了卷面,而残留的痕迹却存储着过往文明的气息。本雅明在拱廊街研究中说道:“对于真正的收藏者,其每一件藏品都是一部百科全书,承载了这一藏品所源于的那个时代的风景、产业及其藏品原主人的所有知识……收藏行为就是一种实际的记忆保存方式。”[1]对他而言,建筑物奠定了巴黎城市空间的语法规则,而拱廊街是现代巴黎城市街道的精神标本,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微型世界”。现代城市里的历史文化街区是居民自我复刻的一件收藏品,是城市的记忆之所,是现代人与城市历史对话的媒介,也是解开城市空间连接过去、面向未来的秘密钥匙。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金华,迄今已有2 300余年的建城史,素有“小邹鲁”之称。地处江北老城区的古子城是婺州古城的核心,是金华城的发源地,也是金华市区唯一保存相对完整的历史街区,而酒坊巷则是古子城历史街区风貌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条街巷。酒坊巷位于古子城历史文化区的中轴线上,是一条呈南北走向的“I”字型巷道,北至石榴巷、南至飘萍路,长约616米,宽4~6米。它是古子城古建筑遗存最集中、文化最丰富的一条街巷,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发现,酒坊巷至今尚存有太史第、名人故居、考寓、民居、商铺、寺庙等传统建筑共计38处。目前,这里基本上仍保持清末民初的街坊布局形态,民居多保留着“前店后坊”的建筑格局。这里丰厚的历史积淀形成了街巷风情、考寓文化、宗教信仰、名人寓所以及抗战遗迹等不同年代、不同面向的多元文化地理景观,是这座浙中城市的文化遗产特区。
隐而不见:场所的遮蔽与传播的失语
坊巷在古代是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在城邑为坊。田野为村。”[2]现实中坊巷是由可见可触摸的建筑构成的街巷,在这里沉淀着一座城市的宗教、风俗、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酒坊巷是一条窄巷,在巷两侧是清一色的白墙灰瓦的民居,一至二层的宅院,每个院子门前或院内都有一个小型天井。这里曾是繁华富庶之地,以前的住户非富即贵,以本地和外来的名人居多。根据笔者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梳理,现在仍有踪迹旧址可寻的名人故居有酒坊巷49号著名记者邵飘萍旧居、71号同盟会会员金品黄故居、84号台湾义勇队旧址、103号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办公处所、112号清季民初浙中知名律师方正南故居、121号著名教育家胡步蟾故居、126号《浙江潮》旧址(黄人望公馆、黄绍竑寓所)等。凯文·林奇说:“语言和图画是很好的媒介,但真实物体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要了解过去,最好的办法是置身于过去建筑和设施的包围当中,并且举止行为就如同在过去一样。”[3]53坊巷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传递历史讯息的“媒介者”,考寓是古代科举制度的痕迹,巷内的酒泉井是金华府酒酿造工艺的见证,“前店后坊”布局的民居是市井生活的真实写照……从文脉传承的角度看,“将性能和表现固定于一个稳定的物质材料上,这是使其长久不衰的最可靠方式。”[4]18坊巷内,经受时间的侵蚀而岿然不倒的建筑作为一种储存城市历史的工具是牢固的、沉重的、神圣化的,38处古迹是在金华的地理空间上加注的时间标签。
同时,坊巷的“老房子”不仅是文物建筑,当下也是市民的居所。置身巷内,由北向南而行,可以看到酒坊巷126号《浙江潮》旧址,其隔壁现在住着一对徐姓老夫妻,就着“前店后坊”的建筑格局开了一家杂货铺。《浙江潮》旧址曾是黄绍竑寓所,为原同盟会会员黄人望先生所赠。黄绍竑与李宗仁、白崇禧并称新桂系三巨头,抗战期间,他在酒坊巷创办了《浙江潮》开展文化宣传抗日工作,后将寓所转赠予《浙江潮》杂志社,成为重要的抗战文化遗址。如今,抗日烽火消散在历史尘埃之中,房子的“旧事”对两位老人而言也有些遥远。不过,73岁的徐老先生对自己小时候租住在黄人望家做长工的生活仍有记忆。而《浙江潮》旧址以北,以季惇叙堂界碑为界,是蒋介石嫡系之一汤恩伯的故居。如今,故居朝东开的铁皮石库大门紧锁,曾经的汤公馆约在1965年拆毁,而当年大花园里的井至今尚存。旧址再往南走几步,是方正南故居。这栋建筑坐西朝东,三进院落,为晚清官宦士绅居所。目前,由方正南的两个孙子及其家人居住。老宅里有两个天井,楼上楼下十二间,门锁生锈、贴着封条的是“公房”,其产权不属于方家人,方氏后人只有可供居住的两间“私房”。这一空间上的划分隐隐诉说着故居产权之变的大历史。
坊巷内曾经的名人故居、考寓、商铺历经沧桑,多次变更户主,如今满眼是破旧残败的老房子。有规划专家认为,这些“老房子”是具有双重属性的“人居型遗产”:一方面,保留了很多物质和非物质遗存,沉淀了诸多文化,所以具有吸引保护举措的“遗产性”。另一方面,人们生活、工作、居住于其间,人的居所每天都在活生生地变化,因而具有“生活性”。[5]如其所言,酒坊巷见证了金华城的时代变迁,就文化遗产价值而言,坊巷内38处历史残迹是现代人想象祖先生活的起点,是建构城市文明的证据,是形塑城市认同的要素。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精神”的定义即“人类自我表达的规律性物质记载”,无疑,酒坊巷在城市精神的意义上是金华城的文化高地,以坊巷为代表的“人居型遗产”是市民传统生活方式的物质化表达,是记录城市时空变化的教育文本,传承着城市文脉。酒坊巷堪称金华的城市之根,作为古子城唯一幸存的原汁原味的历史街区,这里倾注了坊巷居民的地方依恋与私人情感,亦可承载公众的文化记忆,驱动人们的历史想象。金华当地媒体评价:“千年古城看此巷,酒坊巷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6]
然而,对生活其间的居民而言,酒坊巷是一方塌陷的居所、萎缩的社区。巷内现有的停车、排水、消防、环卫等基础硬件和配套设施停留在城市二三十年前的水平,夹杂在周边1.5万平方米的商住楼里,这些土木结构的老房子尤显残破,不协调。平房低矮昏暗,居民生活质量与时代发展严重脱节。如今,这条窄巷里居住的主要是缺少经济来源的老人或者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市民。同时,因历史缘故,街区内的房屋产权结构复杂,房主无心或无力修缮,老房子面临倒塌或失火的潜在危险。更多住户就像方正南故居“公房”的户主一样,搬离酒坊巷,住更宽敞、明亮的楼房。酒坊巷在城市的现代化过程中一度被遗忘了,与繁华的历史两相对照,现实的酒坊巷是衰落的文化空间。
与社区时空停滞的境况相似,是坊巷丰厚的历史在传播向度上的失语。坊巷古有金华酒文化,据史料载,酒坊巷之名源自明代初年酿酒师傅戚寿三在坊间开设酒坊酿制金华酒的历史,巷内酒泉井是珍贵的历史遗存,而坊巷西南侧考古发掘证实的古婺州窑窑址亦多出土酒瓶、酒具;近有邵飘萍、黄宾虹、黄人望等名人故居和金华作为我国五大抗战“文化驿站”之一的抗战文化;还有巷内居民日常生活里的饮食习俗、节日民俗、街巷民谣、传奇故事。然而,现有的文化挖掘与研究几乎是停滞的,除地方文化研究学者蒋金治、朱佩丽、徐卫所著《酒坊巷》外,坊巷文化的论述零星分散在历史文献、现代媒体和坊巷原住民的口传故事之中。同时,酒坊巷往往作为城市旅游开发的客体在当地媒体上出现,单一强调其城市文化的象征意义却缺乏具体文化本身的书写。另一方面,坊巷作为地理媒介的价值被忽视而缺乏营造,直至2017年3月当地政府进行巷内拆迁改造行动。当年,金华市婺城区政府发布酒坊巷区块范围实施房屋征收公告,着手酒坊巷区块保护提升工程。《金华古子城历史街区保护整治详细规划》中将酒坊巷的功能定位为“抗战文化、酒文化展示以及传统居住功能为主,同时兼容古民居建筑群、名人故居、休闲餐饮和老金华生活情景体验等功能”。这意味着沿巷子两侧低矮的历史建筑基本上将被保留和修缮,进行城市文旅与创意产业开发。“这回政府下了很大决心,多年的愿望终于要梦想成真了。”古子城历史文化区管理办公室主任的一句感慨也从侧面印证了坊巷文化一再被遮蔽、不可见的尴尬。
寻求可见:地方依恋与城市精神的表达
金华当地政府以“恢复历史风貌、打造特色街巷”为主题对酒坊巷实施保护提升,希望引入旅游服务业态,营销城市文化资源,树立城市文化品牌,这是政府自上而下参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的经济与文化驱动力。当下,继非遗保护热潮之后,近年来“建成遗产”(built heritage)——以建造方式形成的文化遗产,在文化振兴的政策导向之下,也开始备受地方政府、民间资本的重视。传统文化街区的认定、工程整修、文化开发等一系列工作在各地紧锣密鼓地推行。围绕建成遗产的利用,政商合作延伸出文创、文博、文旅等庞大的产业集群。
然而,遗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高投资的文化工程通常以旗舰开发项目的模式从事“制造传统”,进而衍生“传统的标准化”问题。城市间的历史文化街区相互复制文化消费内容,而脱离地方社会与历史情境的文化展示,人为地制造“文化飞地”。这一模式背后的逻辑是诱惑参观者和游客来到本地区,刺激新的消费,而很少考虑提高本地居民的生活品质。事实上,在遗产旅游开发早期,通常在商业资本和国家权力的干预下,“老房子”腾挪变化、改造整治,让里面的居民整体搬迁,且忽视他们的感受,诸多变故致使遗产本身的价值与社区文化相互剥离。这种规划方式将文化视为脱离历史情境和社会现实的一套符号和意向,将文化问题简化成美学问题,即“装饰和美化问题”,而不是从人们如何使用生活环境并与之发生关系的人类学角度去考虑。[7]86金华之前八咏老街的改造,拆除老建筑,搬迁原住居民,再建仿古街区的做法即是一例。在原住居民全部迁走后,这里的传统文化也不复遗留。
由此,学者们亦在反思追求“文化标准化”和商业化旅游空间再造的缺失,认为重塑并保留原住居民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对地方文化展示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尤为关键。地方(place)有别于空间(space),它是被人、物体、实践和各种表征汇聚的“集合物”,而空间是一种构想的抽象的“几何体”。在欧美现代性研究的语境中,自段义孚提出“恋地情结(Topophilia)”概念开始,“地方”在人本主义地理学语境中即被定义为一种“感知的价值中心”,是社会与文化意义的载体。地方感是人的情感与所处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主观体验与感受,人的记忆、价值等情感因素与地方资源发生情感意义上的互动,而由此产生人对地方的依恋。如“乡愁”所表达的地方依恋就是人与故乡在情感上的深切连结,是人与生养自己的地方互动产生的特殊人地关系。
事实上,中国城市地方感的培育与塑造有双重指向:一方面是城市建设千城一面而无法彰显城市自身的地方历史与文化内涵,成为当下形塑城市文化品牌的负累;另一方面是国内城市的发展正在遭遇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的影响,市民在城市层面的身份认同面临去地方化的危机。在这个时代,一座城市亟需通过塑造地方感来培育城市精神,回应全球激烈的城市竞争并以市民对城市精神的自豪感来抗衡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倾向。城市能够把全球的开放性和建立在独特性基础上的共同体意识结合起来,从而赋予市民独特的精神和身份认同。[8]在全球化语境下,地方代表的是根植于特定地方性语境并与全球化力量持续互动的日常实践,是一种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重构。身份认同即定义“我是谁”的方式,它是一系列社会文化符号和隐喻叙事的产物,而人或群体栖居的地方则是意义或叙事的来源之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通过日常“定居(habitation)”不断重复对地方的体验,即通过与地方的持续互动,使得地方成为定义自我的一个关键元素。人被特定的地方所“标记”,成为地方所定义的客体。[9]贝淡宁所言“城市精神”也正是某一个城市里的市民对地方意义的体验与诠释所作的话语表述,以此来理解自身的身份与自我的存在。如蒙特利尔人宣扬他们的语言身份,耶路撒冷人珍视他们的宗教身份,伦敦人以人文传统和对外开放为傲。
贝淡宁认为,“城市精神”是城市如人一样的属于自己的个性或气质。它区别于政府为满足经济利益而宣传塑造的“城市形象”,是自下而上由居民的想法和思维汇聚而成的。建构与传播城市精神是对自上而下文化旗舰工程开发模式的补充与平衡。城市精神从哪里来?研究者可在阅读研究大量的地方文献史料的基础上,深入调查研究一城一地的历史、人文及其发展现状;再以“漫步城市”的采风方式在城市文化地理的纹路之间寻获体物入微的经验感受,同时采访当地居民或开展讨论搜集创作素材,在城市的古今体验之中索隐钩沉描绘出全面的城市特性。[10]对金华而言,酒坊巷具有横跨古今的历史纵深,是近代名人文化与平民历史文化的重要遗存,留有城市精神生长、变革、延续之痕迹。坊巷这一人文地理空间的时代价值,在于“地方”反哺身份建构的意义。当地媒体曾报道常住上海的金华人俞红在古子城里寻古井、拍古井的故事。她说,常年奔波在外,回乡故地重游,总时不时勾起故乡情结,“在离家的远方越来越关注起家乡的新闻、美景与历史。”古井的背后是一段段令人回味无穷的历史故事,而将蹲坐井边洗菜唠家常的市井生活画面定格时,俞红想起的是多年前在金华老街巷里玩耍的自己。[11]俞红拍摄古井的故事生动地说明地方依恋与城市精神的表达用以培植人的身份认同,是地方文化遗产可持续开发的内在支撑。
婺州古城保护提升指挥部有意使酒坊巷成为古子城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的展示地之一,“让老金华人的传统记忆在此鲜活呈现”,使之成为“活”的古街古巷。[6]由此可见,酒坊巷的修复工程要使之成为金华传统市井生活形态的复原之地,是体验婺州区域独特文化的社区空间。这意味着沉浸在现实生活情境之中的地方依恋与城市精神变得可触、可感、可见,这尤其需要动员本地社区民众参与遗产开发项目,确保文化本土真实性的同时,也履行遗产让社区“增值”的承诺。
地方建构最为重要的特征是主观性与日常生活的体验。一个社区里的人、物、事超越具体的物质形态而具备象征意义,是社会共同体内部的诠释过程。“精神”既体现在特定文化的物质叙述中,又存在于由诠释者组成的实体共同体之中。[12]除酒坊巷的建成遗产外,原住居民对日常生活的诠释,包括家族史、生活口述史等均是塑造地方感的生动素材。居住在《浙江潮》旧址隔壁的徐老先生记得,黄人望家的房子很大,柱子有一个成年人两手合抱起来那么粗,院子也很大,里面种着香泡树、胡桃树、铁树,住在里面很有味道。他回忆,黄人望的小老婆为人很好,每次上街买吃的,不管是自己的孩子,还是租住在这里的孩子,都有一份。徐先生称呼她为“姨娘”。[13]而坊巷内的名人故居、宗祠遗痕、断壁残垣、古井考寓,对当地人来说既不是审美意义上的“美丽”,也不是考古意义上的“历史写本”,而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环境,是某户邻居家或儿时游戏的墙根而已。原住居民们在生活里关注的并非自家建筑是否历史悠久或赏心悦目,而是朝夕相处之间对“老房子”及其周遭体物入微的切身感受。比如他们曾用酒泉井的井水淘米洗菜,酿酒洗衣,还有与邻人在井旁闲话家常。如段义孚所言:“微不足道的事件总有一天能够建构起一种强烈的地方感”。[14]116现有的遗产旗舰开发项目尤其需要珍视这些琐细、杂芜、开放的生活感受。
国际著名城市规划专家西村幸夫说:“因为对自己出生的故乡、自己成长的地方,或者是你所选择生活的城镇的热爱,无论在世界任何的地方都应该是相通的。”[15]18地方的魅力是由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魅力散发而来。西方“遗产热”的历史表明,“身份政治”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是其持续的动力。“活态历史”运动表现的就是平民的生命和生活方式的历史,发出平民的声音。[7]126酒坊巷作为复活老金华传统记忆的场所,将成为城市公共叙述空间与个人传记空间的交汇地带,是公众审视过去的自我、展示身份认同的公共舞台。凯文·林奇也提示,在流动的时代,“亲属关系可以延续,但地点无法延续。我们对父亲生活成长的那条街道感兴趣,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父亲,强化我们的自身身份认知。”[3]63-64酒坊巷内的气氛、形态、居民特性,以及其中的人际关系提供的正是地方感的价值:亲切感。人们彼此间相通的是埋在内心深处的对于地方的亲切经验,“每一次亲切的交流都有一个场所,人们可能在这样的场所不期而遇。存在许多亲切的地方,这样的地方看起来是怎样的呢?它们是专有的,且是私人的。它们可能铭刻在人们的记忆深处,每当回想起它们的时候人们就会获得强烈的满足感。”[14]114平民遗产的魅力就在于人与普通自我过去的世界相遇。
文化展示的民间转向再次提醒我们,遗产的保护性开发不仅在于物本身,还要维持人对物的关系和反应。“保存的物品最好能够反映往日的气韵:规模、空间、路径或林木。如果这些无法做到,那最好去寻找和保存一些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东西,或者与记忆中人的行动直接关联的物件,比如:十字架、座椅、台阶。但被保存之物的基础必须是:用户希望铭记的东西,或者与自身有关联的东西。也就是说,规划者需要尽力了解居民居住了什么和希望记住什么。”[3]63
建构可见性:坊巷空间的媒介化改造
德国史学家耶尔恩·吕森说:“我们要保存过往创造意义的产物,使之有助于当前的生活。”[16]遗产彰显的是历史环境与历史叙事的物质性,关系到人类的普遍利益,是人们认知自我和想象未来的基础。在德布雷看来,遗址或遗迹是死者留下的时间与空间,人类文化的传承即意味着与死者对话,这是后工业时期城市规避意义危机的方式。[4]30身份是21世纪国家与社会的关键词,获得对过去自我的认识是自我身份诉求的有机组成——包括修家谱、考古、遗产旅游等在大众中流行。婺州古城保护提升指挥部定位酒坊巷修复工程的目标是“复原城市记忆,打造旅游、文化综合性景区”,[6]意在吸引远方的游客或是度周末的普通市民来这里旅游、娱乐、购物。酒坊巷的场所价值在于文化层面以视觉体验导向身份认同之建构,而经济层面则以组织消费为现实诉求。这意味着坊巷这一城市空间成为信息传播的舞台,它是视觉上充满可读性且富含历史与文化所指的环境,意味着场所执行媒介的生产与传播功能。执行这一功能的前提是酒坊巷从之前萎缩、失落的地方转变为活力、可见的地方。有诸多方式让一个地方变得可见,“这些方式包括与其他地方竞争或者发生冲突,在视觉上制造突出之处,以及利用艺术、建筑、典礼和仪式所产生的力量”。[14]147从媒介地理学的角度看,空间的媒介化设计引导着坊巷遗产文化的展示。
遗产被看作是“可被参观的历史”(history made visible),以有趣味、可解读、能与参观者沟通的表现方式来展示。遗产绝不只是简单的为了过去保留过去,它总是以满足观众的视角和意愿为目标来塑造其展示。[7]141遗产的符号生产在于地方感的塑造,用人们自己的故事和生活来表达历史,而被吸引的参观者主要是为了寻找身份来到这里。如果我们仿照城市传播的观念,把坊巷理解为一种关系性空间,传播是编织关系网络的社会实践。[17]那么,坊巷空间的媒介化的关键问题即遵循地方的可见性原则,建成遗产如何借助现代传播技术完成物的静态展示向人的动态体验转变。具体而言,要对酒坊巷的旧城古迹、名人寓所、宗祠遗痕、抗战文化、宗教风俗等不同年代的遗产进行叙事重组、各有主次地予以有机编排。这涉及到文化展示的“表述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因各种展览都有其政治和象征意义,就如人类学家詹姆斯·克利福德所指出的,所有文物的展示都有其主观的价值和意义系统(arbitrary systems of value and meaning),并有所取舍和序列安排。[18]根据《金华古子城历史街区保护整治详细规划》对酒坊巷的功能定位,传统民居、抗战遗迹、金华酒是其三大文化展示要素,也是坊巷空间的媒介化改造,建构坊巷文化可见性的入口。
一是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角度,以生活物件为切口,打造酒坊巷传统民居文化带。对现存38处传统建筑予以建筑类型的分类、与之联系的历史事件的梳理,重建建筑、事件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并以此为基础编织符合游客注视原则的文化叙事。聚落或街景之所以吸引人,常常是由于建筑群所具备的一种统一感,其中又会因为人的不同,而有细腻的变化,还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呈现出群体之有机成长,是人们在“动态”的时间和“静态”的大地中,为生存而付出之努力,以住居形式所展现出来的可持续生命。[15]12以水井为例,水井是江南地区常见的生活设施,市井小民,与水息息相关的即生活。金华地下水丰沛,水位高,水井遍布全城。建国初期统计,金华市区共有184口井,比较有名的约有26口,而古子城内就有二三十口有内涵、由不同材料砌作的水井。传统民居的文化叙事,即可聚焦酒坊巷内太史第井、桔香井、瑞山井、聚星井、酒泉井、星君娘娘井等六口水井,搜集古井的传说、故事以及生活口述史,或从当地居民的相册和录像片中寻找日常生活的图像,连缀起巷内名人轶事、宗祠祭典、街巷风情等主题。由于遗产注重个人化,寻找见证社区历史变迁的当地老人,采集个人回忆和轶事,复活酒坊巷市井文化,从而提炼出江南传统民居活态历史的展示主题。凯文·林奇说:“如果我们检视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与我们的童年、与父母甚至祖父母的生活相关的物品是重要的过去提示物,他们直接维系着那些生命中值得纪念的事件:出生、死亡、结婚、离别、毕业。”[3]63所以,通过陈设或保留已经从现代家庭生活中消失的过去年代的物质文化,使游客看到“自己”的生活得到展示,在公共收藏中得到验证——如“我小时候母亲也用过类似的水桶”。这比起知识性或概念性的叙述更轻松一些,从可触摸的“硬件”唤醒想象的“软件”,以此激发参观者的切身记忆和内在经验。
二是挖掘整理酒坊巷抗战文化巷的史实资料,建立以台湾义勇队总部旧址为中心的抗战文化纪念馆。从文化储存与传递的角度看,展览馆、博物馆、廊、室、影视、档案库等的建立意味着文化的流通。创造地方可见性的方式之一是利用著名事件或人物为其添光加彩。设立抗战文化纪念馆是对酒坊巷特殊历史的“召唤”,借此表达这座城市对自身参与抗战的光辉历史的态度和价值观念。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后,国民党浙江省大部分党政军重要机关迁至金华,金华成为我国五大抗战“文化驿站”之一,是东南地区重要的文化中心,被誉为“抗战文化城”,而酒坊巷是抗战文化巷,有《浙江潮》《东南战线》《战时生活》等20余种刊物在此出版发行,还有不少通讯社、编辑部设在这里,国立东南联合大学、省立战时英士大学的教授、学生在巷内活动。周恩来、曹聚仁、冯雪峰、何炳松等人都曾在酒坊巷组织抗日宣传与救亡活动。酒坊巷84号台湾义勇队旧址是台湾义勇队从1939年2月22日成立到1942年5月金华沦陷之前的活动场所,是台湾籍人士在大陆抗日的唯一遗址,2011年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19]以台湾义勇队旧址为中心,联合《浙江潮》《浙江妇女》等旧址建立抗战文化纪念馆,将酒坊巷的抗战叙事嵌入家国情怀的历史大叙事之中,提升酒坊巷在整个国家历史中的能见度。抗战文化要通过陈设战时印刷出版物的实物、多媒体图片展示、视听技术对战时环境的模拟、真人大小的模型、录音旁白以及战时室内装饰与街景的布置等虚实结合的传播技术来表现,加之有故事有情节的叙述来“激活”参观者的记忆与经验,调动心底的“储备”,唤醒心中的“记忆”,从而建构并认同这一地方与国家互构的历史。抗战文化纪念馆所传递的“历史意识”将把解释过去、感受当下与期待未来联系起来,为参观者提供身份认同、理解变迁与发现意义的导向。酒坊巷也将在这种回忆文化的塑造中,作为传递爱国主义价值观的媒介而存在。
三是以酒为媒,树立酒坊巷专属的文化IP。酒坊巷之名亦与巷内提水酿酒的古井酒泉井有关。我们可整合酒泉井、巷内出土的婺州窑酒器、酒具以及地方文献关于金华酒的记载等遗址、实物与文字资料,在巷内选择古民居建立金华酒文化坊与华东地区古酒具数字艺术展。媒介地理学的研究表明,以环境景观、气候、文化、地点、事件、美食、服饰、音乐、历史、背景、情感等为代表的“非媒体为中心的媒介”在人类日常生活实践、互动和体验感知的过程和结果中,各种不同的元素与符号叠加起认知的代码,更加突出了媒介介导下虚与实的空间介导感知。[20]上海近年来改造历史建筑使之成为游客“网红打卡点”的案例就带来实践经验上的启示。新天地和田子坊对石库门里弄的改造,“面粉大王”荣敬宗住宅被改造成为上海时装周Prada艺术活动空间,英商祥生船厂变身文化综合体,上生·新所1920年代的“哥伦比亚圈”高端住宅区变成聚集文创商业的创业园等都证明了老建筑为商业空间品质带来溢价。老建筑,新时尚。建成遗产成为城市漫游者体认都市时空交错的独特载体。金华酒早在1915年就在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金华酒文化坊将是一个集体验、互动和展览三大功能于一体的体验空间,为金华酒赋予更加年轻时尚的产业化色彩,塑造全新的地方酒消费业态。华东地区古酒具数字艺术展以金华乃至浙江出土的酒器、酒具为载体,运用全息、AR、VR、虚拟互动等现代媒介科技,再现华东地区的酒文化,开展穿越时空的对话。酒坊巷已入选浙江省委宣传部公布的2017年度浙江省文化创意街区名单。酒坊巷专属酒文化IP将是其文化创意街区建设的重要入口,以金华酒为主题,延伸出酒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等业态,促进街巷空间内的文化贸易与消费。
结 语
以文化为本,文化可为城市赋能。未来城市的发展趋势是将城市的文化传统与新兴技术有效结合在一起,在延续传统与不断更新之间保持平衡。在金华酒坊巷的个案中,街区作为表达地方依恋和传递城市精神的媒介,允许场所和其参观者对身份有更强烈的诉求。当前,全球化浪潮与“企业化”的地方政府管理双重激荡,各地越来越投入相互竞争以吸引新的投资。地方经济规划往往转向对本地文化资源的营销,以吸引更高层的消费者和旅游者。在城市开发愈来愈标准化的时代,只有少数当地资源可以作为本地身份的“独特”标识来展示。[7]143酒坊巷是标识金华独特身份的稀有遗产资源,通过聆听和搜集社区原住居民的声音塑造地方感,以平民遗产的活态历史回应流动社会人们对身份认同的内在需求。同时,酒坊巷传统民居物质文化、抗战遗迹历史文化和金华酒非物质文化,其作为三个侧面表现从城市历史与平民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城市精神,藉由现代传播技术实现空间的媒介化改造。通过静态的物态展示与动态的互动体验,创造坊巷的可见性,营造文化传统保持与更新的社会生态。从更大范围来看,任何一座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城市,都会面临旧区改造、古建筑保护和再利用与城市发展的矛盾。而这一传播视角下立足文化可见性的金华酒坊巷个案分析,提出挖掘与重构城市的地方感,城市空间的媒介化营造,正是对这一共性问题的思考与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