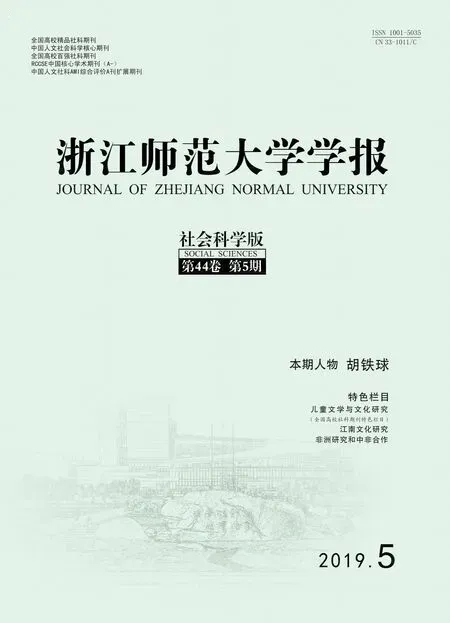论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阅读方法*
高 玉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创作方法,然后是一种作品形态。但更重要的是现实主义是一种阅读方法,本文即对此展开申论。
一、现实主义是任何一种创作方法的因素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称谓,既指作家的创作方式和作品形态,也指阅读方法,即从“现实”的角度阅读作品,并从中寻求现实价值和人生意义。现实主义作为阅读方法之所以对所有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各种作品都有效,根本原因就在于任何创作方法都有现实主义的因素,任何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来,都有或隐或显的“现实”。
以“现实”为中心,从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角度来重审各种文学,传统文学创作方法的划分其实意义有限,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按照“现实”进行重新划分,从而各种文学可以根据它们与生活形态的相似性程度而划分为“现实”的作品与“非现实”的作品,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是典型的“现实”的作品,而“荒诞派”文学、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是典型的“非现实”作品。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拉》、鲁迅的《祝福》《孔乙己》、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是“现实”的作品,而卡夫卡的《变形记》、奥尼尔的《毛猿》、贝特克的《等待戈多》、鲁迅的《铸剑》、残雪的《黑暗地母的礼物》、余华的《现实一种》、莫言的《生死疲劳》是“非现实”的作品。以“现实”为标准,传统文学中也有很多“非现实”的作品,比如神话,中国古代的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古代欧洲的“骑士小说”等。整个中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也是偏“非现实”。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的很多作品则是“现实”作品,比如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黑色幽默小说等,它们除了反映现实生活这一基本特点以外,还大量呈现原生生活形态,如意识流小说,它主要描写人的潜意识与无意识,表面上很杂乱,缺乏逻辑和理性,但它恰恰是对人的复杂心理的真实写照。
但更多的作品则是居于中间状态,也即既有现实的因素,也有虚幻的因素,由构成的比例不同而形成差异性,有的作品重“现实”,有的作品重“非现实”,有的作品则是“现实”与“非现实”并重,整个文学可以形成一条从“现实”的文学到“非现实”的文学的“链条”,任何一种文学作品都可以在这条“链条”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文学史上,绝对的生活实录或写实作品是不存在的,绝对忠实于生活的实录就不是文学作品而是通讯报道或者历史了,但实际上,即使是通讯报道也是经过选择和加工从而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虚构性,按照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的说法,历史也具有虚构性:“针对同一组事件,有许多同样可以理解并且自圆其说,然而却明显相互排斥的看法,对这些看法前后一贯的精心陈述足以摧毁历史学自诩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实在性’的那种自信。”[1]司马迁的《史记》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但其伟大性恰恰在于其虚构有力地加强了它的阅读性因而广为流传,读《史记》,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虚幻的东西,比如“高祖斩蛇”“扁鹊透视”等明显是“非现实”的。同样,绝对虚幻的文学也是不存在的,文学无论怎么想象,它总有“现实”的成分。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说:“不管小说是多么胡说八道,它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经验之中,从中吸取营养,又滋养着人们的经验。”[2]75“胡说八道”是故事上的,可以是“非现实”的,但细节必须是经验,是实在的“现实”。童话是最虚幻的,但它恰恰有很多现实描写,它的场景、情形、心理、逻辑、追求等都是生活化的,否则就没有人愿意阅读和能够读懂。武侠小说所写的那个世界是虚幻的,飞檐走壁还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但水上行走,像鸟一样在空中飞翔,在空中打斗,肉身刀枪不入,骑鲸御蛇,死而复活,随意杀人等,这些绝对是虚幻的;但武侠世界又是人的世界,其中所书写的人的六情七欲,爱情、亲情、吃饭、穿衣、睡觉,人的说话,结婚生子,生老病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却又是现实的,与生活的本真形态没有区别。寓言多以动物、植物为书写对象,但寓言中的动物、植物本质上都是人,其故事也本质上是人的故事,表达的道理也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的道理。《伊索寓言》中农夫和蛇的故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本质上都是人的故事,“恩将仇报”“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都是人类社会现象,人与动物、动物与植物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关系。
所谓文学书写中的“非现实”,主要是指作品的某些环境、故事情节、时间、人物行为、心理和外在造型等不是写实的,而是想象的。文学作品在抽象的层面上可以虚幻,但一旦进入具体细微,就呈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来,表现为细节的生活化,原生形态,根本原因在于细节是生活的“原子”,人对生活“原子”的想象是有限的。神话显然不是现实主义文学,在外在形式上,它是超越经验世界的时间和空间的,但本质上它仍然是现实世界的反映,所以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3]表面上神话似乎完全是想象的,不受任何现实的束缚,但实际上它有很多细节上的真实,我们可以从中读到很多现实生活的内容。《封神演义》显然不是现实主义作品,小说描写了现实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的各种天神,比如哪吒有“三头六臂”,但其实它仍然是以现实生活作为基础,鲁迅说:“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颈子二三尺而已。”[4]文学作品所书写的内容不管其内容在外形上是多么远离生活形态,但它从根本上是从生活中来的,都有生活的影子,文学批评可以对它进行生活溯源。
文学作品可以写一个虚幻的故事,但一旦进入具体的书写,进入细部描写,就必须是生活化的,必须由生活的细节来填充,否则就无法进行下去。文学的内容可以是“非现实”的神鬼,可以是非生活形态的动物和植物甚至是石头,但它们必须是拟人的,否则就是属于动物学、植物学,不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动物、植物要么是自然形态也即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异变为人的隐喻,那就必须“说人话”,按照人的品性和存在方式存在,动物也能开口说话,但必须是合情合理的,所谓“合情合理”指的是人及其社会的“情”和“理”。虚幻和现实在文学中其实能够很好地和平相处,比如卡夫卡《城堡》,写“土地测量员”K作各种努力试图进入城堡,城堡虽近在眼前,就坐落在山上,可以看得见,但K就是进不去。这个故事本身荒诞,是“非现实”的,体现出“表现主义”的先锋性,但小说具体写K的语言、行动、心理等细节却并不荒诞,反而非常现实,所以,《城堡》本质上是一部荒诞的故事里装满了逼真的现实生活细节的小说。正是这样,《城堡》是一本非常好读的现代主义小说,很多人都是没有任何障碍地把它读完了,似乎一下子就读懂了,只有再读第二遍、第三遍和更多遍的时候才会发现这部小说是那么复杂而深刻,表面上现实化、生活化的背后是大量的隐喻和表现,以及抽象的思考和寓言。同样,卡夫卡的《变形记》也是这样,小说写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有一天早上起床时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大甲虫,之后饮食和习性都越来越甲虫化,这当然是荒诞的,但这荒诞故事之中却是大量的“细节的真实”,在格里高尔·萨姆沙的外形上,卡夫卡写出了现实中真实的大甲虫,非常写实,这本身就是忠实于自然。在内在精神上,格里高尔·萨姆沙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他虽然变成了大甲虫但仍然保留人的心理和思维,人的情感以及反应,人的苦闷与孤独。小说是这样开头的:“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象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的身驱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5]这绝对是荒诞的故事,人不可能变成大甲虫,其它如“坚硬得象铁甲一般的背”“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许多只腿”等作为人的细节描写都是“非现实”的,但作为甲虫的细节描写却是“现实”的,读者在阅读时并不特别感到不适,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这些细节的真实,其它如“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稍稍抬了抬头”“看见自己”都是很生活化的描写,都是正常的生活形态,正常的人的心理、行为和思维。
残雪的小说是极端虚幻的,她自我定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6]不论是内在还是外在都非常怪诞,比如人的身体是变形的(如心脏长在胸腔的外面,即“外挂式”的),时间不是流动的,空间不具有物理性,人的行为不可理喻等,完全不是现实的,所以残雪是当今中国作家中最难懂的作家,其作品争议不断。但就是这样的完全想象的、梦魇式的内心化写作,仍然不可能脱离现实,故事和场景可以虚幻,但细节不能完全虚幻。如其中的:
他又推了我一下,这次我真的跌倒了。一个轮子从我的后脑勺压过去,我听见我的头盖骨发出碎裂的声音。
当然我没死。我趁自己还没回到黑屋里,赶紧又把自己再次想像成永植。
这回我是在群鸟中往前跳了,顶着一个压烂了的脑袋。这些鸟们都不飞,像鸭子一样往前赶。
我踩着了一只大鸟的脚,鸟儿的凄厉的叫声划破夜空,它叫出的居然是“永植啊!!”,那么我的确是永植了。我抬起头,看见了山。不过这座山已经不是齐四爷了,它是猴山。鸟儿们立刻蹿到山里头去了,剩下我独自站在那儿。山就在前方。寂静得很,山里头比外面更黑,我又是独腿行走,该如何上山呢?[7]
这里,“我趁自己还没回到黑屋里,赶紧又把自己再次想像成永植”“这些鸟们都不飞,像鸭子一样往前赶”“我抬起头,看见了山”“剩下我独自站在那儿”等都是很生活化的描写,是非常现实的。人类几千年以来产生了无数的文学作品,但还没有产生过与人类现实完全无关的作品,即便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的先锋文学,不管怎么荒诞、反对和颠覆现实主义,它们也仍然无法完全摆脱现实,摆脱生活,因而具有现实主义的因素。文学作品究竟是偏于“现实”还是“非现实”,不是由创作方法决定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很“现实”(现实主义文学也有“非现实”的因素),但“新写实”“意识流”作品也很“现实”。并不是越现代的作品就越虚幻,也不是越先锋的文学作品越虚幻,很多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文学作品也有“现实”的因素。
对于文学来说,日常生活未必是“现实”的,虚幻未必是“非现实”的,有时恰恰相反,虚幻反而更接近生活的本质,是更真实的“现实”。余华说:“几乎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处于和现实的紧张关系中,在他们笔下,只有当现实处于遥远状态时,他们作品中的现实才会闪闪发亮。应该看到,这过去的现实虽然充满了魅力,可它已经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那里面塞满了个人想象和个人理解。真正的现实,也就是作家生活中的现实,是令人费解和难以相处的。”[8]144很多时候,那种模糊和虚幻的现实反而是真正的现实,而生活中的实在反而不是真正的现实,“一些不成功的作家也在描写现实,可是他们笔下的现实说穿了只是一个环境,是固定的、死去的现实。他们看不到人是怎样走过来的,也看不到怎样走去。当他们在描写斤斤计较的人物时,我们会感到作家本人也在斤厅计较。这样的作家是在写实在的作品,而不是现实的作品。”[8]145余华认为最真实的作品反而是“虚伪的作品”,他谈自己的创作体会:“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现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于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9]忠实地描写现实未必是真实的,而虚伪的形式反而更接近现实的真实,不过这种真实是更深层次的真实。
由此可见,任何创作方法都具有现实主义的因素,有时候,作家看似虚幻的描写实际上是为了追求更为本质的真实。在文学中,“现实”与“非现实”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对立,既不存在完全写实的文学,也不存在完全非现实的文学,“现实”与“非现实”总是并存于同一文学作品之中。不论是传统文学还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都有“现实”的成分,有的是立意和主旨上的“现实”,有的是情节上的“现实”,有的是细节上的“现实”,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现实”不是绝对的、单一的,而是相对的、多元的。
二、非现实主义文学也可以从现实的角度来进行阅读
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这主要是从作家创作的角度来说的,即作家在创作中忠实于现实生活,反映生活的本质,刻画典型人物等,但现实主义还是一种阅读方法,现实主义作为阅读方法是从读者阅读的主观角度来说的,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可以撇开作者的创作方法以及创作意图,而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阅读,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对作品进行现实性的理解,可以彰显作品中“现实”的因素而遮蔽作品中“非现实”的因素,或者说可以选择性地忽略那些“非现实”的东西而把焦点集中在“现实”的方面,或者从“现实”的角度解读虚幻,对虚幻进行现实的“还原”。作为文学批评来说,这是不允许的,因为批评需要客观,但阅读具有主观性,阅读理解本质上具有选择性,“误解”是阅读的合理内涵。
现实主义作为阅读方法,可以是整体上的,也即从现实的角度整体理解和把握某部作品或某篇作品,这里,“现实”具有整体性;也可以是具体的,即关注某部作品或某篇作品局部的“现实”方面,这时,“现实”是作品的一个因素。
文学是人写的,是供人阅读或者说消费的,因此它不可能脱离人的生活。对文学是人学这个问题可以有各种回答,其中最普通的概括是“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10]34也即我们通常所说“反映论”,我们可以不同意文学本质“反映”说,但我们不能否认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文学从根本上不过是人及其思想的产物,不仅现实主义文学反映和再现现实生活,传统的浪漫主义、古典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也同样反映现实生活,不同在于,创作方法不同的文学把握现实的方式各有特点,现实主义的文学类型强调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再现现实,浪漫主义的文学类型强调以幻想和理想的方式反映现实,象征主义的文学类型以暗示、隐喻的方式来比附现实,表现主义的文学类型则以变形甚至荒诞的方式来表现现实。“现实”在外形上可以千变万化,但“现实”的实质却是唯一的。对于那些按照生活本来样子书写的作品,现实主义的阅读方法当然是顺理成章的,而对于那些把生活进行了夸张和变形的作品,也可以根据社会生活对它们进行“现实还原”,这就是现实主义的阅读方法。
比如《聊斋志异》中写了很多狐妖、鬼神,他们除了在构成上区别于人以外,也即他们可以肉身消失,可以变形甚至以一种“气”即精神的方式存在,他们以肉身的方式存在时,他们的外形、气质、心理、行为等全是人类的,和普通的人无二致,鲁迅说:“《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崎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叙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诞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是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11]所以,小说中的狐妖、鬼怪都可以还原为人,好的狐妖、鬼怪就是“好人”,坏的狐妖、鬼怪就是坏人。聂小倩除了拥有美女外形以外,还心地善良,是贤妻良母。小说所写的鬼怪的世界其实就是人的世界,官吏贪虐、豪强横行、生灵涂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
《西游记》也是这样,唐僧的三位神仙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其实都可以还原为现实中的人,孙悟空是有缺陷的英雄,他精力充沛,敢作敢为,头脑灵活,能力很强,法力很高,是现实生活中的智人和强人。猪八戒的性格非常复杂,大致可以概括为“可爱的庸人”,好色、好吃懒做但憨厚;逞能但本领有限;胆小怕事且贪图小便宜但不乏忠诚和实在;没有理想和追求,虽非自愿但却贡献很大。沙和尚是性格单一的人,在取经的路上主要责任是牵马,但忠厚老实、任劳任怨,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好人,跟着唐僧和孙悟空走完了“长征”,因而也修成“正果”。不仅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人可以还原为现实中的人,小说中的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王母娘娘、东海龙王、南海龙王等都可以还原为现实中的人,他们可以笼统地称为“统治阶级”。白骨精、黄袍怪、红孩儿、蝎子精、铁扇公主、牛魔王、九头驸马、蜘蛛精、黄狮精、玉兔精等也可以还原为人,总体上他们属于“坏人”,有些则是有优点的“坏人”。小说的主题也非常“现实”,不过是讲了一个艰苦奋斗,披荆斩棘,饱经磨难,终于取得最后胜利的故事。小说在创作方法上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但我们完全可以按照现实主义的方法来阅读它。
爱尔兰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是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品,剧情非常荒诞,两个流浪汉在一棵光秃秃的树下相遇,自称要等待戈多,但戈多是谁,戈多从哪里来,戈多何时来,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等待的过程就是做一些无聊的事,说一些无意义的话,最后来了一个小男孩,告知他们戈多今天不来了。戏剧共两幕,第二幕不过是把第一幕的故事大致重复一遍而已。故事是“非现实”的,但意义却非常“现实”,它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绝望”的心理和事实,人生总是充满希望,但结果往往是“绝望”。等待就是人生,人生就是等待;等待是希望,但等待更是绝望。20世纪哲学对人最大的追问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还有什么文学比《等待戈多》揭示的这种人的状况更“现实”?
其它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比如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印象主义、黑色幽默小说、新小说等都可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进行解读,其中的荒诞、变形、抽象、模糊等都可以进行“现实”还原,在这一意义上,现实主义是一种通用的文学阅读方法。法国文学理论家罗杰·加洛蒂曾提出“无边的现实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没有非现实主义的、即不参照在它之外并独立于它的现实的艺术。”[12]他把毕加索、卡夫卡这些通常被认为是标准的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也归于现实主义。从创作方法及作品形态来说,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它实际上取消了艺术认识现实和概括现实的必要性,也即消解了现实主义。但从阅读的角度来说,现实主义的“无边”和“开放”又是有道理的。[13]什么是现实主义?最权威的定义是:“现实主义据以反映生活、构成形象的原则的共同特点,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偏重于描绘客观的现实生活的精确的画面,描写那些在生活中已经存在或按照生活的规律可能存在的事物,而不是代之以作家自己的愿望。”[10]257-258现实主义具有具体性、客观性、真实性、典型性等特征。试问,纵观古今中外各种文学作品和各种创作方法,有哪一种创作方法及其作品不反映社会生活呢?有哪一种创作方法及其作品不描绘客观现实生活的精确的画面呢?有哪一种创作方法及其作品不具有具体性、客观性、真实性和典型性呢?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创作方法及其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或多或少存在现实主义的因素。
很多现代主义的作品在内容上都书写了荒诞,非理性、神秘等,但荒诞,非理性、神秘也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现实”。在很多阅读者看来,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所描绘的很多都是“魔幻”或“神话”,但马尔克斯坚称他所写的就是拉丁美洲的“现实”,“我认为卡彭铁尔就是把那种神奇的事物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这就是现实生活,而且正是一般所说的我们拉丁美洲的现实生活……它是魔幻式的。”“我们生活在一块大陆上,这里每日每时的生活中现实都与神话羼杂。我们诞生和生活在一个虚幻的现实世界中。”[14]马尔克斯并引荷兰探险家普德·格拉夫的叙述:“他遇到一条溪水在沸腾,在溪水中五分钟可以煮熟鸡蛋。还说,他经过一个地区,在那里不能大声说话,因为阵雨会倾盆而下。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岸一个地方,我看到一个人在一头耳朵里生了虫子的母牛前默默祈祷,并看到在祷告过程中死虫子掉了出来。那个人肯定地说,他可以远距离进行同样的治疗,只要把牲口向他描述一番并告诉他在什么地方。”[15]略萨也说:“确实,小说是在撒谎(它只能如此);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小说在撒谎的同时却道出某种引人注目的真情,而这真情又只能遮遮掩掩、装出并非如此的样子说出来。这样一说便给人一副晦涩难懂的面孔。”[2]71所以,重要的是如何阅读的问题,现实主义的阅读就是一种“还原”,即揭开“遮遮掩掩”和“装出的样子”的面纱,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即“真情”。
同样,在中国人看来,20世纪东欧的小说所描绘的生活很荒诞,是黑色幽默,是“非现实”的,比如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雅罗斯拉夫·哈谢克的《好兵帅克》等,但在东欧人自己看来这些小说所描绘的却很“现实”,幽默但不“黑色”,离奇但不“荒诞”,黑色幽默就是20世纪东欧人的现实。现代科学观之下,巫术、鬼神、灵异等都不是真实的,但千百年来,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它们是真实的存在,事实上,鬼神“现象”是中国古代日常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孔子只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但并不否认怪力乱神。所以中国古代很多“志怪”多归类在“史”类而不是“文学”类,被称为“野史”或者“笔记小说”。《水浒传》写宋江“托梦”而攻打祝家庄,《红楼梦》写赵姨娘用巫术侵害贾宝玉和王熙凤,以今天的科学观来看是不可能的,但中国古代人却相信它是真实的,相信它是现实。今天,科学已经高度发达了,很多神秘现象已经通过科学的方式得到合理的解释,但仍然有大量不能解释的自然和社会现象,这些不能被解释的现象同样是世界的组成部分,是现实,它们会在文学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不同在于,现代主义把文学中所书写的各种神奇、怪诞、诡异、荒谬看作是虚幻,即“非现实”,看作是一种寓言,而现实主义则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现实,看作是“现实”的一种方式。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阅读方法,不仅有文学史根据、阅读实践根据,而且有文学理论和哲学根据。海德格尔认为,“理解”是“此在”(人的存在)在世的基本方式,因此,理解不是方法论,而是本体论:“审视、领会与形成概念、选择、通达……它们本身就是某种特定的存在者的存在样式。”[16]也就是说,“理解”构成了“此在”的基本特征。在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中,读者通过理解活动而将作品带入到自身存在即“此在”的境遇之中,将作品这一存在者把握为“在场”,作品于是在这一“当前化”中得到解释。伽达默尔认为艺术作品不是一个摆在那儿的东西,它存在于意义的显现和理解活动之中,作品所显现的意义并不是作者的意图而是读者所理解到的作品的意义:“创作某个作品的艺术家并不是这个作品的理想解释者。艺术家作为解释者,并不比普遍的接受者有更大的权威性。”[17]277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的过程。”[17]433而这些视域是“在不断的形成中被把握”,“历史视域”不断被“自己现在的理解视域所替代”,于是“在理解的过程中产生一种真正的视域融合”。[17]434在这一意义上,对艺术作品的理解,本质上就是“视域融合”,也即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平等对话。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携带自身原有的“历史视域”与作品对话,在对话中,历史视域被作品激发而不断地形成新的理解视域并重新回返自身。所以,对一部作品的理解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带上读者自身的因素。“接受美学认为,任何文学文本都具有未确定性,都不是决定性的或自足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多层面的未完成的图式结构。”[18]4姚斯认为,读者实质性地参与了作品的存在,甚至决定作品的存在。所以,作品不是纯客观的,作品的意义也不是绝对客观的,而是根据读者的接受不同而不同,“不承认文学本文只有一种绝对的独一无二的意义;认为文学本文是一个多层面的开放式的图式结构,它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仅仅在于人们可以对它作出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既可以因人而异,也可以因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无论哪一种解释都是有意义的,也是合理的。”[18]5在这一意义上,“每一件作品,从古老的岩画到小说《约婚夫妇》,都是向无限的品位开放的作品。”[19]任何作品都可以进行多重解释,[20]不过现实主义的阅读方法是所有解读中最重要、具有最广泛性的解读。因此,按照现实主义的阅读方法阅读非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品,本质上是读者的阅读权力。
从阅读的角度来说,任何类型的作品都与现实生活有关,都与人生有关,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表现,都是“人的文学”,所以都可以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阅读,都可以从中读出现实生活的内容、人生的内容,都可以读出“真理”,都可以读出历史和现实,都可以发现典型。事实上,所有的作品都可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进行阅读,都可以从中读出现实的意味。用现实主义的阅读方法,我们会发现,《伊索寓言》中所有的动物其实都是人,动物的世界其实就是人的世界,动物和动物的关系其实是人与人的关系。英国小说家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写了一群动物,儿童也可以把它当作童话来读,但其实他写的是一个社会。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和《城堡》似乎荒诞不经,但它却无处不是现实,他提前写出了整个20世纪的社会图景。“现实”作为因素在文学中无处不在,所以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阅读方式,从来不会过时。
总之,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并不为现实主义所独享,它以因素的方式融入各种创作方法之中,因而各种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作品都具有“现实”性。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阅读方法可以应用于阅读所有的作品,只不过阅读的结果有差异而已。任何作品的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是通过读者的阅读来实现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阅读方法是实现这种价值的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