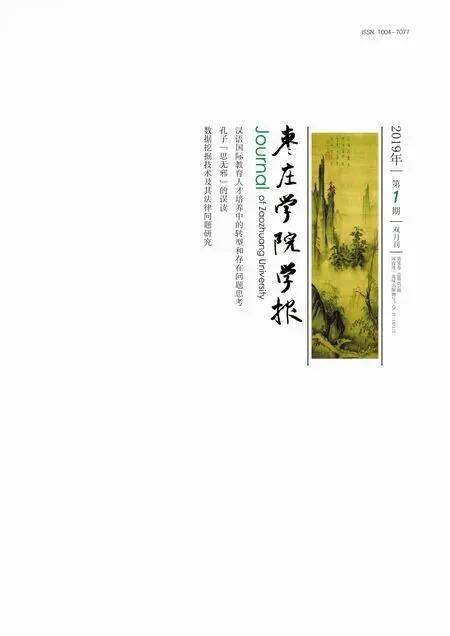世界文化视角下魔幻现实主义的后现代性研究
赵雪媛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相比于自觉自发的文学流派,魔幻现实主义更类似于一种写作风格的倾向。文学史中通常将魔幻现实主义归类为“后现代主义文学”,但对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定义却缺乏定论,罗伯特·冈萨雷斯·埃切瓦里亚(Roberto González Echevarría)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是一个理论真空的地带”[1](P108)。为了将定义简单化,有些文学分类甚至简单地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等同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而对如何真正界定魔幻现实主义与其同后现代的关系语焉不详。
这与“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产生与发展有一定联系。“魔幻现实主义”最早在1925年被弗朗兹·罗(Franz Roh)提出的时候,是用以解释欧洲绘画中后期表现主义画派风格的;而1986年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电影中的魔幻现实主义》(On Magic Realism in Film)中援引这一概念的时候,则是对电影美学的解读和思考。可以说,魔幻现实主义通常被作为一个“文化的”的概念来理解和使用,而不是“文学的”概念。正因如此,作为“文化的”魔幻现实主义与作为“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相互之间有时会产生混淆;更糟糕的是,为了避免混淆而直接切断两者之间的关系,会过于简单粗暴地将“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等同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或者说类同于拉美文学创作的“神奇的现实”的概念。
因此必须明确的是,在这里探寻的“魔幻现实主义”首先是文学的,当然也会是文化的、历史的和社会的,但最重要的是“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与后现代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相互纠缠的。从时间角度来看,“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诞生与“后现代主义”最早都是作为绘画理论而创造出来的,而作为文学理论的“魔幻现实主义”甚至早于作为文学理论的“后现代主义”;从实际成果来看,魔幻现实主义实际上也指出了试图完成后现代构想的一个可行性方案。为了能够真正理解魔幻现实主义与后现代的关系,必须从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开始,从魔幻现实主义概念的流变与被认可的魔幻现实主义文本两方面入手,最终尝试构建以世界视野为角度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概念。
一、打破真实的界限
1925年弗朗兹·罗(Franz Roh)在《魔幻现实主义:后期表现主义》(Nach Expressionismus: Magischer Realismus: Probleme der neuesten europ ischen Malerei )中提出“魔幻现实主义”的概念的时候,想要表达的是一种绘画上对表现主义的一种创新。1927年,也就是弗朗兹·罗的《魔幻现实主义:后期表现主义》出版两年后,意大利杂志《900》的编辑马斯莫·伯坦佩里(Massimo Bontempelli)将“魔幻现实主义”(realismo magico)从艺术领域运用到了文学领域。这本杂志以法语和意大利语发行,继而“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说法在欧洲流行起来。受到《900》的影响,约翰·戴斯尼(Johan Daisne)将“魔幻现实主义”带到了荷兰和比利时,接下来这一概念又传达到了拉美。正是在这里,“魔幻现实主义”的概念通过“翻译和文学性的借用与转化”[2](P60),在拉丁美洲主要作为文学评论的概念使用。
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魔幻现实主义的定义是在不断改变的:“弗朗兹的定义与后期的文学定义毫不相同。”[3](P12)但变化并不等于魔幻现实主义的概念毫无主线可寻。弗朗兹·罗以“魔幻现实主义”来解释绘画中后表现主义的风格,是因为在这类绘画中,梦境、幻觉与现实的界限被模糊了,实物的形象在摹仿的基础上基于幻想产生形变和扭曲,这种幻想被堂而皇之、理所当然地置入现实的场景中,产生一种荒谬而真实的错觉。弗朗兹在书中说道:“相对于‘神秘(mystic)’,我希望用‘魔幻(magic)’这个单词来表明神秘并不是试图表现世界,而是隐藏并悸动在世界面目之后。”[2](P16)当他选取“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说法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意味着一种新的表现目的:艺术的目的通常是摹仿、表现和阐释世界,而“魔幻”却是和现实缠绕的、时常躲在现实世界之后的、难以触碰的,因而它难以直接呈现,而需要对神话、传说、口口相传的故事,采用后现代的戏仿、拼贴或转引才能展现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
“后现代主义”最早提出的时候,是由约翰·沃特金斯·查普曼(John Watkins Chapman)于1880年创造出来、用以区别于法国印象派的创作方法。[4](P12)这一概念被引申用于艺术、音乐、建筑,而“后现代主义文学”这一概念在20世纪40年代才被美国诗人作为文学评论来讨论。“后现代主义”本身即是若干概念的集合——想要简单地总结什么是后现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以追寻的是后现代试图表达的内容和表达的方式。后现代主义的诞生通常被认为是因为现代性在二战后经历的巨大的认同危机:人们开始意识到,现代主义试图努力建构的宏大话语和世界的表象是如此脆弱,而何去何从却没有明确的道路。现代主义曾采用自己的方法探寻世界的本质与“真实”,而后现代主义却怀疑“真实”作为概念的存在,认为对真实的追求和定义是虚幻而无意义的。
魔幻现实主义正是将虚幻与真实不分彼此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仿佛是现实主义的、却又实际上与现实主义相反的状态。当约翰·戴斯尼借用了“魔幻现实主义”(Magisch-realisme)这个概念时,他的理解是:“梦幻和现实构成了人类状况的两极,魔幻的诞生正是通过两者之间的吸引力,特别是当闪现火花、照亮超越、发现现实生活和梦幻之后的真理。”[2](P60)梦幻和真实之间的边界正是我们认知中可以理解的“世界”的边界,而魔幻现实主义恰好游走在边界之上、逐渐模糊边界,如同爱丽丝触碰镜子之后,镜子就变成了可以穿梭的银色雾气。
由于“魔幻现实主义”的描述牵涉到梦幻与真实的双重描述,这就令人很容易将其与广义上被称为“幻想文学”(fantastic literature)的范畴相互混淆。但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因为“魔幻现实主义”有义务与现实发生联系,而“幻想文学”则没有这样的限制(这并不意味着“幻想文学”一定与现实无关)。从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与现实主义相区别的特定叙事方式”——相区别,但是有联系。魔幻现实主义意味着魔幻与现实以某种方式达成了艺术上的和谐,并通过相互交织的方法对世界进行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呈现,由此,平行的界限被打破了,现实与魔幻的叙事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关联,正因如此,“魔幻现实主义是当代后现代主义叙事逻辑的一种可能的选择。”[5](P301)
在魔幻现实主义中“现实”的概念与单纯的“现实主义”完全不同,这种不同并非是内容上的,而是表现方式上的。阿图罗·乌斯拉尔-彼特里(Arturo Uslar-Pietri)在《委内瑞拉的文学与人》(1948)中说:“在故事情节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就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神秘的看法。”[6](P165~169)将魔幻视为“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神秘看法”,是将魔幻引入现实之中而不产生明显的差异与冲突,仿佛魔幻只是难以用科学解释的一种现实而已;但对这种现实的描述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则截然不同,“以魔幻的观点看来的现实主义,是以某种方式将现实拉到基准之外并藐视传统现实主义。”[7](P14)传统现实主义想要表述的一切、想要重现的生活的真相,在魔幻现实主义看来都是徒劳而可笑的。
魔幻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差异,并不意味着魔幻现实主义可以与现实脱离关系:
“尽管对现实主义公然背离,魔幻现实主义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还是关于现实的文学,因为它审视并再现一个在复杂并时常令人感到困惑的世界里生活的经验……魔幻现实主义试图争论的是,仅仅依靠理性主义和科学,无法完全解释人类的经验。绝对的知识是一种幻觉。”[8](P16)
也就是说,魔幻现实主义所想表现的“真实生活”是一种界限模糊的状态,从科学角度上来看仿佛是不真实的,至少是完全说不通的;但在生活中却被视为可信的或者部分可信的,或者是曾经可信的。在传统现实主义中认识的“现实”通常实际上只是一种经验化的感知,任何不符合这种感知的存在会被定义为“不真实”的或者“不科学的”;而魔幻现实主义重新定义的现实则认可“多种理解和建构世界的方法”[8](P12),将非经验化感知的存在视为“无法被定义”或者“无法被解释”的真实。从一定程度上,它认可了真实并非是可以由人类的认知经验来评判的,从而在被认为是幻想的存在与被认定是真实的经验之间构建了某种沟通的桥梁。
二、发现过去的途径
当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坚持“后现代主义对过去或‘已被说过之物’(the already said)的返现不可能是天真无知的……反讽、游戏、嘲仿和自我嘲仿的怀旧是发现过去的一些途径”[9](P306~307)的时候,他揭示了“后现代”这一概念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当现代主义(尤其是先锋派)采用破坏的方式打碎过去的一切、并试图重建一个能够解释和建构所谓现代世界的宏大话语的时候,后现代则意识到这种打碎和重构都是徒劳的,而后现代本身并不准备步其后尘。后现代的视野跨越过现代主义,直接意识到它与被切断的古老历史之间的相似与相反之处:它们在本质上是循环的,而在表面意见上则是相反的。如果继续从理论上或者艺术实践上反驳或者否定现代主义,后现代本身必然再次卷入这一“否定——建构——再否定”的循环,因此它采用一种自觉的反讽的态度,试图将这样的循环直接消解掉。
后现代主义在发现过去的途径中走上了“自觉的反讽”的道路,而魔幻现实主义对传统和传统中的神话文本的态度恰好正是这种“自觉的反讽”的态度。从文学角度来看,当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文本中出现神话(Myth)、民间故事(Folktale)或者童话故事(Fairytale)与现实产生交织的时候,这种交织同时展现出两种完全相反的感受:一方面,文本中的人物对这一切感到理所当然、笃信不疑,仿佛现实与魔幻是水乳交融的,因为在他们生活的文化中有着“本该如此”的传统;而另一方面,读者却明确知道哪些部分是现实中可能发生的(并不是说现实中实际发生的,而是具有发生的合理性的),哪些则是完全“魔幻”的、不科学的、不可能的。作者在其中保持一种暧昧的态度:既不认为这一切是真实的,也并非认定这一切是绝对不会存在的——尽管多半不会在当今现实社会中呈现出这样的状态,但这种被认为是“魔幻”的部分总会是以传说的、民族的、隐喻的方式在特定文化理念中存在着。也就是说,作者在此时同时理解着“魔幻”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其目的并不是论证“魔幻”在现实中的合理性,而是试图采用其中曾经存在的合理性作为一种武器或者工具,用以抵抗或者试图消解导致其非合理性产生的文化根源,这也正是魔幻现实主义在拉美成为蔚为大观的重要文学写作手法的主要原因。也正是这种来自作者的“自觉的反讽”态度产生的不同原因和指向的不同目标,导致魔幻现实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不同风格的文本。
魔幻现实主义的表征首先是破坏性的——与先锋主义式的否定式破坏不同——是对叙事方式的基础性破坏,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表征。从作为文化的魔幻现实主义角度来考虑,这种破坏的原因可以被解释为“在当代资产阶级文化的边缘(特别是存在主义),关于自然与历史意识形态的困惑上升到意识的表层,呈现出一种关于政治与形而上学之间尚未形成铰链式矛盾的形式。”[5](P301)而作为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更为明确地将矛盾展现为魔幻与现实融合背后的对立、科技与传统交融背后的冲突,或者说,是“相信”与“荒谬”之间相互对立的界限。“现实”给出了困惑,而通过建构或者阐释来得到解答的方式已经在现代主义渐趋落寞的尾声宣告此路不通。对理性的怀疑引起了文学趣味上对人类蒙昧时期的兴趣——理性主义无限追寻并试图靠近“真实”,反而越看不清真实;超写实主义成为形式发展的巅峰,而其能够容纳的灵魂却愈加模糊。而后现代的质疑和解构展示着另一种可能:当符号与意义的强力链接发生动摇的时候,真实却从裂隙中隐约可知。
魔幻现实主义对叙事方式的改变来源于它首先质疑我们作为个人习以为常的观念,质疑我们习以为常的“现实”,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彻底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叙事和思维模式。温迪·法里斯(Wendy B. Faris)认为魔幻现实主义在文本上体现为一种对叙事稳定性的破坏:
“魔幻现实主义建立在现代主义小说‘多聚焦’(multifocal)的基础上,魔幻现实主义中自然与叙事声音的起源于作为先驱的现代主义相比,更具有彻底的破坏稳定性,因为在真实的叙事环境中存在着不可改变的元素。”[10](P44~45)
现代主义从形式上对传统文学手法做出了突破,无论是象征的、荒诞的还是意识流的;魔幻现实主义更进一步的是,它破坏的不仅是形式上的叙述手法,更是对真实本身、对生活本身、对理解、对意义的破坏和消解。魔幻现实主义体现出一种对现实不仅是质疑,而且是嘲讽的态度;它的质疑是:当你认为这是真实的时候,这真的是本质的真实吗?
“发现过去”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探寻世界的方式。“过去”采用与现实相反的方式与我们发生联系,神话、童话、民间故事、传说……这些被认为非理性的文本,由于距离现实生活的认知经验越来越遥远,它们的隐喻意反而愈加显著。弗莱(Northrop Frye)用“向后站”[11](P199)来表达拉开一定距离才能看清文学理论批评,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解释后现代主义对“过去”的回望。在“过去”,个人意识尚未登上舞台中心成为主角,人对现实的理解尚未如此笃信不疑。因此通过追溯“过去”的神话,魔幻现实主义展现出对真实的质疑,并且将这样的疑问以反讽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三、文学风格的表征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通常被过于简单地等同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或者说等同于拉美文学创作的“神奇的现实”的概念。这首先是因为文学的鉴赏和评价者来源于与拉美传统文化有着较大距离的西方文明,在这样的理念下,“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12](P428),西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文化主导的,代表着阶级、经济、世俗权力,甚至也包括科技;而“第三世界”的文化则更加原始,更具有诗学的、潜意识的、乃至性欲的力量。不得不说这种看法代表一系列文学评论将西方文化与第三世界文化区分对待的倾向,然而正是这种倾向导致“魔幻现实主义”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混淆不清。
如果说魔幻现实主义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发现过去的一些途径”,这些途径则是指魔幻现实主义是怎样通过“魔幻”的外衣将过去的神话、童话与民间故事带回并融入现代社会的现实的。从表面上来看,这一方法运用得最为流畅的仿佛就是拉美作家,正如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在《这个世界的王国》(El reino de este mundo)的序言中所说:“神奇现实是现实突变的必然产物(即奇迹),是对现实的特殊表现……然而,这种现实的发现首先需要一种信仰。”[13](P470~471)被卡彭铁尔称为“信仰”的,其实本质上是拉丁美洲根深蒂固、并在现代社会乃至各类殖民中得以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的传统文化特征,这种特征与资本主义文化所代表的“现代社会”相差甚远,却与代表自然和历史的“过去的时代”更为贴近。因此可以说,拉丁美洲文化正是最适合魔幻现实主义生根发芽的沃土,事实上,魔幻现实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发展确实是最为兴盛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拉丁美洲是唯一能够生长魔幻现实主义的土壤。当评论家过分关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同时,却近乎遗忘了欧洲文化中长期的民俗文化传统——无论是古老欧洲文明中口口相传的民俗文化,还是民间故事发展而成的童话故事,或者是欧洲文学经典的英雄史诗——这些都是与资本主义文化构建的“现代社会”相反的、来自过去的声音。巴赫金(Ъахтинг,МихаилМихаЙлович)在研究欧洲“狂欢化”理论的历史由来时说: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狂欢节类型的广场节庆活动、某些诙谐仪式和祭祀活动、小丑和傻瓜、巨人、侏儒和残疾人、各种各样的江湖艺人、种类和数量繁多的戏仿体文学等等,都是统一而完整的民间诙谐文化、狂欢节文化的一部分和一分子……狂欢节语言有独特的‘逆向’‘相反’‘颠倒’的逻辑,各种形式的戏仿和滑稽改编、降格、亵渎、打诨式的加冕和脱冕等等,这些独特的狂欢节语言都是现实生活的戏仿,是民众建构的一个‘颠倒的世界’。”[14](P12~13)
这种民俗传统与拉美的民俗传统显然不同,但在历时性地研究欧洲文化中却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后现代主义对戏仿的运用并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可以追溯到过去的文化传统,这意味着即使在资本主义文化影响下的欧洲现代社会中,人们也并没有切断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童话与民间文化构建了西方的文学传统,也构建了欧洲魔幻现实主义中“魔幻”的基石。英国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曾经在描述魔幻现实主义的时候说道:“文学性与民俗性并存”[2](P252),而她的作品也被评价为“融入了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使用了梦幻、魔法、浪漫主义和童话元素来操纵或影响其他现实环境和特点”[15](P18)。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在《凯尔特的薄暮》(The Celtic Twilight)的序言中说:“我所做的,无非只是容许我的这些男人和女人、鬼混合仙人们各行其道,既不用我的任何观点挑剔他们,也不为他们辩解。”[16](P3)当他收集这些民间故事的时候,既不相信也不质疑,因为这都不是文本的意义所在。
欧洲的从古代、中世纪再到近代、现代的文化发展相对而言是比较循序渐进的:每一次科技和文化的“革命”都是下一次申发的基础,每一次发展带来的冲击都有足够的时间得以消化并形成全新文化中的一个部分。因此当魔幻现实主义展现出一种与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的现代性相对立的后现代主义态度时,这种对立带着更多的是探寻和疑惑的态度而不是反抗的态度——这种质疑和反思更多是美学意义上的、文化意义上的、文学意义上的。因此当欧洲作家试图对经典、权威和现代性表示反讽和寻求突破的时候,欧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在文本上展示的态度是最为温和的。
在非洲与美国,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所承载的便与欧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不同。在非洲和美国,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不是平等的,而是有明显的强弱之分,导致在政治、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形成了种族之间的对抗性。传统文化成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在这种对抗中依赖的武器——只有不断强调传统文化中与现实社会的差异,才能够保持不被占优势地位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文化直接吞噬掉。在长期的被占领、被奴役和被边缘化的过程中,少数种族自身也受到了强势文化和主流文化意识的影响,甚至开始反感和憎恨自己的身份;而少数种族自身的文化却因为处于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弱势而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少数族裔的作家或者关心少数族裔身份认同的作家从文本角度开始唤醒人们对民族传统的意识的时候,这类作家通常被认为是“栖息在边界”的、“边缘的作家”,他们小说中的力量来源于“强大的、令人不安的转世神话和历史”[17](P1)——也就是民族的传统和历史。无论是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的印第安文化传统,还是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黑人文化传统,他们所创作的魔幻现实主义是对现实生活中无法发出声音的、缺席的文化发出自己声音的要求:“他们文本的特殊形式真实呈现了他们意识形态的构成的能指,同时也形成了他们的魔幻现实主义、预言和超越现实物质世界的风格……对神话材料的挪用和改写令潜在的缺席呈现出来。”[18](P18)民族的过往和传统的文化被作为无法被消解的声音和决不被同化的内核而存在,以后现代的文化多样性的方式展现出了特殊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声音。
这种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冲突在拉丁美洲,却并非完全是被压迫、试图反抗的过程。拉美文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与资产阶级文化所代表的现代性呈现出强力的对抗态度:它从未试图理解来自西方的文化现代性,也从未试图采用融合的态度来对待。在这个意义上,拉美文化被认为是“原始的”——但它并非是原始的,它只是不同的。拉美作家对经典西班牙文学的接受远远超过对现代欧美文学的接受,不止一位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承认受到《堂吉诃德》的重要影响。拉美自身的民族文化固然是魔幻现实主义不可动摇的基石,但如果仅仅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源头认为是“长时期处于孤独状态的印第安文化遗产”[13](P435),便会割裂开拉美与西班牙文学传统之间紧密的影响联系。
四、结语
以世界视野为角度思考魔幻现实主义,便可以看出“魔幻现实主义”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学风格,而是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下呈现出不同的文学风格表征:以对中世纪传统民间故事、童话、英雄史诗和神话进行拼贴、戏仿的欧洲魔幻现实主义;以追溯传统种族文化传说、展现民族特征性和呈现长期缺席的民族存在为目的的非洲和美国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受到西班牙传统文化影响、基于拉美民族生活中代代相传的“神奇现实”的世界观来创作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但无论是哪一种魔幻现实主义,都在模糊了真实与虚幻界限的基础上,明确地指向了后现代对现代主义的“自觉地反讽”态度。因此,可以说魔幻现实主义中魔幻与现实的交融,实际上呼应着后现代主义“打破界限”的表现方式;而魔幻现实主义中对文化传统、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回归和反讽,实际上正是后现代主义“发现过去”的具体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