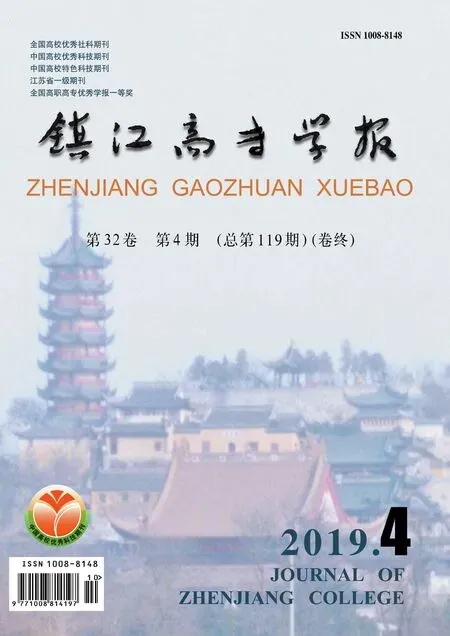论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中的自然
邢 雯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自然世界被众多文人讴歌。在帕斯捷尔纳克的笔下,自然世界更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神性。这个世界里有人类似曾相识的语言、动作、思绪、情感,却又那么神秘、玄妙。风雨雷电、春夏秋冬、草木虫鱼,不像是被赋予了生命,反倒是一番创造了生命的样子。同为俄国“白银时代”抒情诗人的阿赫马托娃曾这样评价帕斯捷尔纳克:“他的诗当中没有人类”[1]97。但是研究自然在其诗歌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就会发现,帕斯捷尔纳克是要借助没有人类面孔的自然世界理解人类社会,探寻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笔者从自然对诗人的情感慰藉、艺术启发和思想启迪三个维度入手,深入解读自然与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密切联系。
1 自然对诗人的情感慰藉
帕斯捷尔纳克生活的时代正是俄国社会动荡、文化转型的时代。1914年,俄国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1922年,一大批学者被流放。社会在不断变化,帕斯捷尔纳克却始终在描写自然。无论是诗人的早期诗集《越过壁垒》,还是后来的诗集《生活——我的姐妹》《主题与变奏》,乃至小说《日瓦戈医生》中的组诗,诗人都在通过对自然世界的感知来应对周遭环境的变化。
他在《又是春光明媚》里写道:
火车走了。路基一片漆黑。
黑暗中我怎么寻找道路?
我只不过离开了几个昼夜,
方向却已经辨不清楚。
钢铁的铿锵在帽中沉寂。
突然,出现了什么样的奇思妙想?
杂乱无章,长舌妇的闲话。
到底搞的是什么名堂?
我在什么地方再次听到
去年就曾听过的河流断断续续的絮语?
啊,大概是一条小溪
昨夜里重新钻出了林地。
这,和往年一样啊,
池塘推动冰块,让水猛涨。
这,真是新的奇迹啊,
如同以前,又是一片春光[2]194。
当诗人选择谛听自然之声的时候,嘈杂的人声与骚乱的心绪便都被关闭在心门之外了。一片静谧之中,诗人的思绪随着溪流畅快地流淌。每一年的春天都如期而至,每一次都给在寒冬中等待的生命带来惊喜。自然空间中的宁静、温暖与人类社会的混乱、寒冷形成对比,这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每当灾难发生,或是日瓦戈对与旁人的谈话感到乏味时,帕斯捷尔纳克总是会将日瓦戈的思绪转向自然。
自然不仅为诗人提供了静心思考的空间,还将他的视野从具体语境下的人类命运拉远,从而使他认识到人世的苦痛磨难之外恒久的生命力[3]。正如马克·斯洛宁所说:“当一般人都在盛赞行动为至上美德时,帕斯捷尔纳克却致力于沉思,考虑一切事物的要理;一般人都在关心工业记录、入党资格及社会主义化竞争,帕斯捷尔纳克则在描写海洋、森林和山峰。”[4]353
诗人的作品中总是洋溢着旺盛的生命力、静默的坚持和对未来的笃定[5]。他在《未来》中写道:“耸立着的枯树枝,/宛如春天的一大堆木墩子。/雪莲花正在/水里和沼泽的严寒中战栗。”[2]104即便是描写冬天,万物都丝毫没有走向死亡的痕迹,反而与春天一样拥有着惊人的生命力。读者很难在帕斯捷尔纳克的书写里读到那种沉入海底的悲痛与绝望。诗人也不像吹响号角的战士那般,急于在冰雪中点燃熊熊烈火。他要做的,是在寒冷与寂静中找到一束光,守护它,珍爱它。
无论人的生老病死还是自然界的草木枯荣都只是浩渺宇宙中周而复始的一部分,死亡之中总是孕育着新的生命。帕斯捷尔纳克曾经借日瓦戈医生之口表达了他对死亡的看法,他认为死亡是不存在的,灵魂会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延续下去。《日瓦戈医生》中各个人物在同一地点以不同方式发生的一次次偶遇正体现了这一点[6]82。个体生命的灵魂在他人身上留存,并且在每一个崭新的时刻实现永恒。躺在病床上,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写下感恩的诗句,“落在床前的一缕微光,/为我带来甜蜜的感知:/我和我的命运,/皆为你无价的恩赐”[7]89。
帕斯捷尔纳克相信宇宙能量恒定不变的法则,社会的变革、疾病和死亡带给人的伤痛都可以在自然世界被治愈。他在诗歌《1919年1月》中写道:
它难以自禁。随身带来了
街上的喧闹,再就无事可做:
本来,人世间就没有
冰雪无法治愈的忧伤[7]206。
帕斯捷尔纳克曾经的恋人叶莲娜曾有这样的评述:“当您痛苦的时候,连大自然都与您一道痛苦,它不会抛弃您,生活、意义和上帝也不会抛弃您。对我而言,我痛苦的时候,生活和大自然并不存在。”[7]162与自然合二为一,使得帕斯捷尔纳克具有感知幸福的能力并执着地去追寻幸福,而这些足以使他不去理会那些令人绝望的事情。
2 自然对诗人艺术创作的启发
自然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艺术启发是多方面的。首先,诗人关注自然世界中蕴含的音乐美,并且尝试运用文字呈现这些动人的旋律。其次,诗人偏好运用副词与形动词组合的方式来展现自然世界中极富动态感的画面。再次,诗人通过拟人、拟物等手法互换人类与自然的角色,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起初,帕斯捷尔纳克梦想成为音乐家。由于意识到自己缺乏灵敏的听力,他不得已放弃了音乐创作的道路,这也促使他重新思考音乐于他的意义。他发现自己迷醉的并非音符与旋律,而是音乐中抒情的成分。文学评论家杜雷林曾在自传体随笔《自己的角落》中写道:“音乐会触动鲍里亚(鲍里亚是家人或关系密切者对帕斯捷尔纳克的爱称)的神经。这是某种抒情的狂烈,是无休止的煎熬;抒情诗的酵母在他身上疯长,折磨他。但是,正像如今所显现,使这些万端感触得以升华的并非音乐的因素,而是诗的因素。”[1]40
不同于其他象征主义诗人借用音乐性的语言丰富诗歌世界,帕斯捷尔纳克是要借诗歌,亦或说是“词语和抒情”,来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帕斯捷尔纳克曾在1913年撰写的一篇散文中回忆自己少年坠马的感受:“他醒过来,身上的石膏板尚未拆掉,狂奔与坠落的节奏仿佛仍在重复。”[1]27他初次切身感受到,词语居然也可能屈从于音乐的节奏。他所追求的音乐艺术不仅是由词语、音符组合呈现出节奏、旋律,更是一个隐喻着人类奥秘的灵性世界。正如诗人自己所说:“世界乃是音乐,找到词语才能找到通往音乐的路。”[1]40
他在诗歌《生活也将如此新鲜》中这样写道:
朝霞,像在对黑暗射击。
砰的一声!——枪弹塞上是火星
在飞驰中渐渐熄灭
生活也将如此新鲜[7]27。
清晨,黑色天空之上升起一抹朝霞,这本是自然世界中一个鲜明而具体的视觉画面,诗人却用表示音效的词语展现出这一画面的动态和乐感。从“砰的一声”到火星渐渐熄灭,一个非常迅疾的动作被戏剧化地放慢、拉长,这既是每个晴朗的清晨都会重复的自然景象,又是一段动人的乐章。诗人还用足以激发读者感官联想的词语描述出它的音色与力度。一声枪响后,万籁俱寂,思绪此时却化为成群的飞鸟在空中飞跃。在诗人眼中,自然世界本身就是诗歌,就是音乐,就是艺术,朝霞的出现和消逝是诗歌舒缓的旋律。
德米特里·贝科夫在《帕斯捷尔纳克传》里提到诗人喜爱的词类是副词和形动词。俄语中的形动词表示一种正在进行的、未完成的状态。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之所以能呈现足具音乐感的动态画面,正是因为他擅于组合运用副词和形动词,细致地呈现事物正在进行的某种状态。比如“一缕挣脱羁绊的阳光落在荨麻上”[7]13,“火车就在犹如巨峰起伏的暴风雪的裹挟下沿月台呼啸而去”[7]11,“用丁香花清洗阳台颤抖的冰川的剪影”[7]112。一切都处在永恒的动态之中,如同一段没有对话和剧情的电影画面,阳光何时散去,火车要奔向何方,似乎诗人在一刻不停地追寻,没有终点,追寻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
人的思绪、样貌也是自然物的思绪和样貌,自然物的恋爱、劳作也是人的恋爱、劳作[8]66。帕斯捷尔纳克笔下没有人的面孔,却处处呈现人的身影和气息。“冰冻耕地上的麝香草莓亮晶晶,而雹子却像热锅中的盐巴劈啪作响”[7]13,由于“热锅中的盐巴劈啪作响”是人类生活常见的场景,自然物“雹子”和人类的距离一下子被拉近了,成为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噼啪”的声响又将这一画面无限延长,让我们仿佛可以闻到锅中食物的香气,感受到一家人在寒冷的冬夜里围着火炉用餐的幸福感。
自然物被拟人化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中常见的艺术手法。“暴风雪在窗户玻璃上,塑造环形和箭状图案”[2]218,这里的“暴风雪”有了掌控人类生活的主动性,似乎是它安排谁在玻璃窗上画满了圈圈和箭头。“我自己也像大雪那样在融化”[7]52、“你就像小树林扔下树叶那样,扔下你的连衫裙”[7]55。无论是拟物还是拟人,诗人的目的都不局限于将描述的主体形象化、具体化,而是要解放语言对于心灵的抑制,努力追赶大自然,探寻裹藏于其中的人类的奥秘。
大自然中的各种气候现象与生物的形态、声响都是灵性世界遗落的信号和线索,诗人逐个采集、收藏,以一种不合逻辑的方式将它们重组,试图解释那些神秘的“不可言说”的事理[9]22。他不知道答案,但是他一直在寻找,带着对另一个世界不可动摇的信任。
3 自然带给诗人的思想启迪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未来派和象征主义诗人都在努力尝试打破逻辑法则对语言的控制,实现心灵的自由。这一点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中尤为明显,他将自然神化,极力恢复先于“逻辑时代”那种与神话思维相对应的语言功能,即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可增生性。
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语言世界里,“我”从被模仿的对象变为模仿者。他写道:“我自己也像大雪那样在融化,我自己也像早晨那样在皱眉头。”[7]45在诗人的笔下,“皱眉头”这样的神情似乎也是人类向自然学来的,人类从世界的中心退居边缘,努力理解自然传达的讯息。甚至有的时候“我”干脆从诗歌中隐退。如:
微风应嘴唇、鬓发和鞋子
下摆和外衣的请求
欠起身来
品尝着玫瑰的芳香。
人们把煤气和热气
洒满砂砾,
这一切都是他们给砂砾留下的污痕,
这一切都是他们招致来的[7]15。
嘴唇、鬓发、鞋子、下摆和外衣纷纷从“我”的身上离开,他们好像被赋予了思维与主动性,与微风嬉闹互动。“我”享受着玫瑰的芳香,享受着微风吹拂裙摆的舒爽。诗的后半部分似乎在提醒“我”,此时的欢快与幸福是自然世界创造的。
大自然不仅被人格化,更被神化,它蕴蓄着出人意料的能量,掌控着人类社会,甚至随时都可以将人类社会吞没。帕斯捷尔纳克本人也对这种自然的魔力感到惧怕。
棵棵大树在林中自行倒下,
云彩扬起草屑
连远方大声啼叫的公鸡,
也在悠扬的鸣唱中一再停歇。
它们带着可怕的惊慌心情,
仿佛大祸就要压顶,
于是这些公鸡就一个个地分开,
大地已预知严寒即将来临[7]84。
然而也只有身处自然之中,人才会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限制。帕斯捷尔纳克隐去人的面孔,意在追求客观化,唯有此时,人才能冲破狭隘与恐惧,真正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探求宇宙之谜。“噢,生动诱人的宇宙之谜/使我异常激动、浑身战栗/诚惶诚恐、热泪盈眶、难以自持,/我一定要为你效劳尽职。”[7]74正如茨维塔耶娃曾经指出的:“抒情之‘我’是所有抒情诗人的目的本身,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里,它服务于他的大自然之‘我’,亦即大自然中一切无穷尽的‘我’。”[1]106
马克·斯洛宁评价帕斯捷尔纳克说:“他要探讨人的内心冲突、情绪之变化以及生存的希望。”[4]353在《冬夜》一诗中,暴风雪无聊地在玻璃窗上画圈圈,映在天花板上的黑影思索着自己的命运,皮鞋从脚下滑落砸在地板上,最后一切都消失在漫天飞雪之中,唯有桌上的蜡烛始终亮着。个人化的百无聊赖、迟疑、痛苦和悲伤被客观世界消解,变成所有人都要经历的一个片段,宇宙将抹去所有的不幸,只留下希望之光。
身处自然之中,人唯一能做的事情便是“劳作”,在自己的家园“劳作”,为了爱与家庭“劳作”,身体上的“劳作”让人融入自然,思想上的“劳作”使人理解自然。就像诗人在《日瓦戈医生》里写下的:“有时候真是多么希望能远远地离开这些平庸的高调和言之无物的陈词滥调,在貌似无声的大自然的沉寂中返璞归真,或者是默默地长久投身于顽强劳作,或者索性沉湎在酣睡、音乐和充满心灵交融之乐的无言之中。”[6]135
庄子有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10]601帕斯捷尔纳克是要通过诗歌探寻呈现自然之美、法、理。在情感层面,自然世界为诗人提供了一个独处的空间,抚慰和疗愈诗人的苦闷与惶惑,给予他信念和力量;在艺术层面,诗人捕捉自然世界的微妙声响与画面,不仅是在寻找创作的灵感,更是要借助诗歌认识自然,呈现天地之大美;而在灵魂层面,诗人一面敏锐地于自然中追寻人的印迹,一面又极力抹去人的主观因素对自然世界的干扰,以此探寻人的真正意义与价值,使人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成为宁静与永恒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