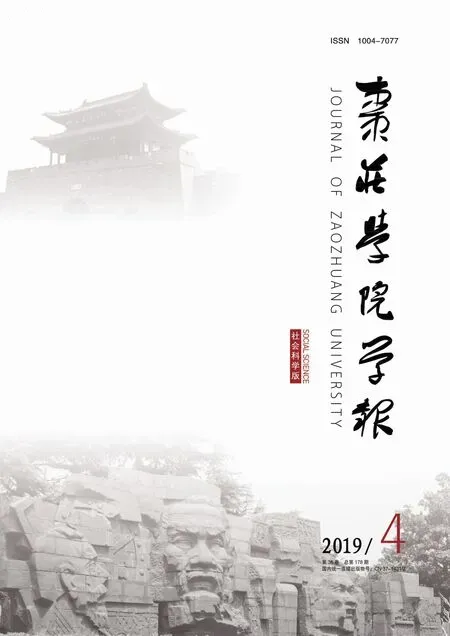从人性论的角度略谈荀子的“他律”
——兼论康德的“自律”
李梦周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在东西方哲学发展的历程中,荀子和康德都对道德、义务、自律等话题进行了研究。荀子关于人性的思想被学界普遍地认定为“性恶论”,因而他在道德的节制和制约方面的思想也被认为持一种“他律”的思想;而康德在道德的节制和制约方面的思想则相反地被认为是持有一种“自律”的思想。似乎一切已经成为定论,但是,有学者开始怀疑并疏理荀子“性恶”是否是真的恶,以此为荀子辩护,于是荀子“性恶论”“他律论”开始动摇。而且,相较之下,荀子、康德大略相同的修持路径,为什么一者是“他律”而另一者则是“自律”?
顺是而下,我们必须重新检验康德的“自律”与荀子的“他律”所依据的人性论的基础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和差别,本文即尝试从两者人性论基础的比较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荀子与“他律”
荀子“性恶论”是历史上的一个定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只有荀子和“性恶论”不可分离,“性恶论”已经成为打在荀子身上的铁的标签。但是,无论如何看荀子,他本人也是性善的,他是在为救世寻求良策。中国古人所有的良策都触及最根本的前提预设,即人性本善。像荀子这样一个以崇高的品德安身立命的人,他怎么可能首先否定自身继而否定世人的立人基石呢?这不是性恶者的表现。
最早只有台湾学者韦政通(1979年)为荀子说了一句惊人的话:“荀子不是人性本恶的主张者。”[1](P220)进入21世纪,学界开始为荀子圆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梁涛先生2015年提出的荀子“性恶、心善说”,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同年,山东大学曾振宇先生以礼为线索,以荀证荀,分层级深入,找到了荀子性善的立论基础,在学术史上第一次解开了荀子“性恶论”的历史性的误读。
诚然,荀子关于人性的主张和观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性恶”就可以概括得了的。关于荀子的“他律”论,也因对这种预设的怀疑而出现松动。荀子在人的道德修习上并不是一种完全的“他律”。虽然不能算作一种纯然的“他律”,但他又与康德的“自律”建立在不同的人性基础之上。
在此,我们换一个角度,不再从《荀子》文本梳理的角度谈起,而从考察荀子的天人关系的思想说起。
荀子是“天人相分”思维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这个主张不仅强调了人是天底下最高贵的物种这一个凸显人的主体性的观点,而且还提出了了解参透天命并合理地使天命为人类所用、人应当成为天和地实现自身化育生命的辅助之物并实现人的这种辅助作用等思想,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天人合一”。
对此,牟钟鉴曾经分析说:“……然而,荀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不是对儒家的一种‘反动’,也不是真的在分裂天人之间的关系。”[2](P47~48)张岱年也指出:“荀子虽然强调‘天人之分’,却也不否认天与人有统一的关系。”[3](P178)
“天人合一”是中国儒家一以贯之的思想,也正是因为如此,儒家把人性看作是由天所赋予的本性。儒家的“性”几乎都具有先天特质的含义,实际上荀子的“性”也并没有脱离儒家的这种基本轨道。虽然与孟子的人性论看似相反,但荀子却同样从天、地、人应当有着不同的责任与分工,起着不同的作用,而实际上天和人又是一体的角度把“性”看作是人的内在具有。
与孔孟一样,荀子也把“性”认定为人一生下来就自然具备的本然的性质和特点,这个“性”是人后天接受教育教化的基础根底。为荀子圆说的学者大多数都怀疑荀子是否自行写作了《性恶》这一篇,这其实依然是误读。我们研读关于荀子的文献,可以明显地看到荀子本身是秉承了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的,也就是说,在荀子思想中实际上是道德的自觉性和道德理性并存的。其为人所诟病《性恶》一篇,所有的立论只停留在人欲与感官功能及其属性上,并不是在人性的深层上。这一点是学界的一个症结。
荀子明确揭示了人性是人类从一出生就自然具备的自然而然的性质和特点。作为人类这一比较特殊的物种不仅仅与生俱来地具有自然的感官上的功能,而且还具有自然的欲望和对对自己有利事物的追求。这里,显然荀子对人性是否本性即善或者即恶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并且他对人先天就存在的欲望进行了正面的肯定。在义利之辨这一种层面之上,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荀子的立场和观点。“荀子将追求利益与追求义一样,将其都作为人的自然的欲求之一,没有好与坏之分。而圣王存在的作用不是为了摒除人们心中的这些自然存在的利与欲之追求,而只是导引其向一个不至于是坏的方向发展罢了。”[4](P47)
如果说道德主要是由“善”来作为价值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是无论孟子的“性善论”,还是之后的“性善恶混论”,通过主张人性天赋的观点就已经表明了道德是由天赋予的。在这一方面,荀子的主张确乎含有一种疑似人性恶的取向在里面。但从更加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他的“性恶”并非是指的真正意义上的性恶。他虽然主张人的德性是通过教化而形成的一种后天的善、并通过修习使其成为人性,但这并不能够证明他是在否定道德是一种先天特质。在道德方面,荀子在主张重视后天教化的同时,实际上是以人的天性之中本身就已经包含着某些道德性的本质和特点为基础的。通读《荀子》的文本,他的关于人与动物之别的论述,从人与兽之间的差异的角度解释了人具有与生俱来的道德特征的观点。
荀子实际上认识到人具有“先天材质”,也就是道德自觉,因此才有可能肯定即使是路人都可以成为大禹那样的圣人。
在这里,荀子认为人作为人的缘由,不在于人具有各种生而就存在的自然本能的欲望,又或者是有足而无毛的体质特征,而在于人具备分别事物不同的理性的才能,在于人具有父子亲情和男女差别的人伦秩序,并且显然荀子也已经将这种人伦道德先天性地赋予了人类自身。
再者,荀子将“义”视为是一个不同于其余生物的人的特别的特征,也已经将义与知认作人的先天之性的一部分。所以,“如果说孟子从内在仁义角度发展出了孔子的仁学本体论的话,那么荀子就从外在礼义角度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本体论……”[5](P7)
说到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人心和人性的问题。在我国传统儒家的思想中,人性和人心往往是相提并论的,但是,荀子将人性和人心进行了分割,分开来使用,使其分别具有了不同的含义,并且荀子分别将它们放置在了一个不同的地位之上,有着明显不同的层级关系或者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荀子将人的自发与自觉涵盖在了性之中,心只是人的志愿的发起者,换言之,心是处于体用关系的“用”的层面上,他认为,如果心顺从人类的欲望,则成为恶。所以,必须有人为的因素加入,由外在的力量进行道德标规。同时,心必须对当下的事物进行关照后进行决断并做出一个相对正确或者完全正确的抉择。荀子特别强调人的欲望和自然的追求是不能够摒弃、也不能够使其淡薄的,而只能够导引、节制和润养,用心的控制功能去进行调节。
在《荀子·王制》一篇中,荀子也提出了人类社会应当明确地进行分工,而又应当组成为一个整体的观点。在这里,荀子讲社会上的工作都要求人去完成和达成,而只有通过这样相对稳定的社会协作和分工,才能够真正地做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的和谐有序;社会角色明确划分,社会秩序才不会混乱,社会才能呈现出一个调和有序的局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人都在尽力而为,进而达到和谐与大治的社会。在这里,荀子就是凭借这样一种观点揭示了群体的规范对于人的本质的启发和维持的重要性。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人性自身实际上是具有道德性的,而关于这种道德性的巩固,就涉及到礼的问题了。《荀子》一书不乏诸如道、德、道德等词语,但荀子并没有有意识地攀升到道德哲学的理性高度,也不是有意识地诠释道德的本体问题。但他的礼却实实在在地是仁与道德的表达,这无疑凸显了他对道德依据的认识。他把礼看作是通往道德和人道的最佳途径。并且在讲至礼的创立和制定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时,荀子认为它是由先王所创造并且制定出来的。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荀子将礼义道德定义为一种后天的产物。在这里,荀子提出的天和地是人这种生物能够产生并发生的本原的观念依旧揭示了礼的来源。如此来说,礼是由圣和王创造并且制定的,天地便是总的依据,并且要根据天道而推及于人道。因此,荀子的“他律”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内在道德意识,而并不能说是“他律”道德。
而且,《荀子·正名》实际上也证明了荀子认为人天生具有理性的认知能力。荀子强调心灵是能够认识并了解而且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心灵具有道德上的认知和实践功能。古代之圣、王,他们完全实现了这种认知,因而只有他们才可以作为道德准绳的制定者。也就是说,人要由古圣王来制定礼的规则和道德的规则,从这种意义来说,这可以认为是“他律”。
但是,古圣王也是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实现道德的理性认知,实现人性的回归,是因为人的本性本来如此。只是一般人顺从表层上的欲望与感官功能,因而其人性之本善被扭曲地表达而成为恶而已。古圣王之道,是对人性本善的正确表达,因而成为到达本善的正确途径。所以,一切他律的道德准绳均来自人性本善的自然表达。由此则不难明白,所谓的“他律”,实际上却是真正的“自律”。
如此,荀子构建后天教化的理论就有了实质性的和实践性的依据和支撑。由此,在人的教化方面,荀子主张教化人的德性使其成为完全的善并使得这种善通过修习成为人的自然本性。在这里,杜维明先生已经说过的一句话,可以很好地概括荀子这一思想的发生和开展的机理,他说:“这样,人的主动参与完善化的过程就取决于自己内在的自我修养与社会理想的相互协调。”[6](P51~52)
二、康德与“自律”
荀子关于人性的主张观念仍然是设立在“人性善”的根底之上的。而将性与心分开,由心来控制性的发挥,并由圣人从外在为世人制定用以约束其行为的礼法制度。这种道德修习上的观点可以说是“他律”,但究其实却是基于人性本善的“自律”。在不觉悟的人那里是“他律”,在觉悟的人那里则一定是“自律”。我们拿康德的道德性观点与荀子的道德性观点进行比较之后,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相似相近之处,但也存在着迥然的不同之处。
从康德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康德毕生所追求的即是建立一种“自律”和自由的道德观点。关于康德的道德哲学,他的专著《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将其用三个章节从不同的深度与广度进行了极好的阐释:“通俗的道德哲学”“道德形而上学”和“实践理性批判”。[7](P20)
这三个层次呈现出从浅到深的递进关系,最终回升并落脚到“自律”可以存在并且成立的依据上,而且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将这种可能性总的概括为人的自在意志,从而阐释出了自己的观点。
与荀子实际上基于性善的“性恶论”的道德观点不同,康德对人性采取的是比较起来相对中立的观点,也就是人性无善无恶,所谓善恶是人为的规定。康德以为,人类的性在无善无恶的根底之上有着趋向好或者趋向坏的这样两种相对立的倾向,好的倾向是由学习而获得的,坏的倾向则是由个体为了谋求本身利益和违背共同的品德和法令规则而引起的。
在这里,康德对恶的理解与荀子对恶的理解显然是有着一定的相近相似之处的。康德理解中的“恶”一般是由后天的环境所引起的,而非常相类似和相近的是,荀子也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确承认恶是人的自然性。康德以为,环境使人类变好或者变坏,道德的作用则在于带领人们走向更好的方向和更好的生活。在康德这里来说,人性并不能够直接地从一开始就被划分成善和恶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而是人在道德上的善恶取决于意志的控制和抉择,而又通过道德法则来约束和规范意志的抉择和行为,契合人类社会广泛法则的行为即是好的,反之才是不好的。
在康德来说,人是感性的,但同时也是脱离不开理性的,而且在此根据之上,证明了道德存在有其必要和可能。由于人的这种本质属性,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有必要建立一种能够直接决定意志抉择与行动的行为和道德的法则规范,并且必须对人进行意志方面上的训练和道德方面上的教导,通过对人意志方面上的训练和道德方面上的教导,人类普遍设立的道德性的行为法则规范才能够得到人们的尊敬和敬重。从而这样才能使道德法则进入人们的心中,成为人类行事的行为标准。康德认为的理性是那种可以完完全全和一切感性条件相分离的特性,因此而得出人类能够完完全全地摒弃感性而使得人类拥有完全的理性并以理性来对一切当下出现的事物进行抉择和决断。
但是,康德与荀子,甚至与中国古代哲学整体思想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他本身并没有实现人性本善的回归,因而他只是“认为”人性是无善无恶的中性质,也就是说,康德并没有实现道德理性的认知,也就没有能够“看到”人性之本善之实质,他只能是凭借自己的思辨去想,他是“自认为”人性是无善无恶的。
既然是“认为”,就不是对真实现实的如实表述。这样,康德所建立起来的所谓的“自律”,就没有天然性与必然性,那些“自律”就缺乏与人性本质的内在逻辑关系。实在来说,这是缺乏人性基础的。一切都是思辨性的主观认为,并不是中国哲学所说的见性之言。所以,既可以这样“认为”,也可以那样“认为”,既没有依据,也就没有像中国哲学那样的征之于古圣王的现实经验。
而且,荀子并没有直接地将人的欲望置于一种需要克制的境地,而是认为其本身也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性,我们需要做的是“起伪”,是用心去引导这种容易走上歧路的性。而康德则将这种感性置于一种需要摒弃的地位,需要人自身用自己的道德去摒弃它,但是他的这个道德却并不是来自人性本善。
从荀子、康德二人的对比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康德所建立的理性的道德“自律”,在人性中找不到真实依据,因而并不通往性善。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其“自律”是无根的,应该说他的“自律”其实正是“他律”。
三、结语
从上面,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荀子和康德在道德的观点方面所具有的区别之处:
荀子在道德观上将人的心与性进行了划分,他的性实际上是以性善为基础的,而他的心则是在“用”的层面上来控制性向好的方向发展。荀子的礼法是由先王根据天道制定的,看似是一种外在的社会规范,是需要一种“化性起伪”的教化来将这种社会规范内化,但是,实际上,这一切的社会规范都是有人性本善的依据的,是人性本善的自然表达,因而也就是通往性善的内在逻辑途径。这种所谓的“他律”,实际上是真正的自律。
而康德的道德则来源于人自己为自己的人为制定,并以此成为公共的社会规范,他所追求的是让普通的大众找到一个解决事情最合理的方法与途径,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也得以完成本身的自由和本身的志向和愿望。但是,他的缺陷却是极为严重的,并没有人性本善的基础。
从人类发展的需要和要求的角度来看,荀子认为的道德教育,它的目的应该是为天下培养各方面素质较高的“君子”和“圣人”。而康德却是走上了个体,大半是从思索个体问题的角度来引出并提出道德教育的目的实际上是最终完成个体的自由和发展。
荀子和康德在对道德教育目标的认识上表现出来的差别,实际上也反映了中西文明之间的固有的不同。那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始终是以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的,而西方文化则几乎从古希腊开始就一直走在强调人自我实现的道路上,中世纪的时候这一走向无疑遭到了曲折,但中世纪之后又迅速地回到了这条道路上,由此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向心力的文化,和一个不具有内在向心力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