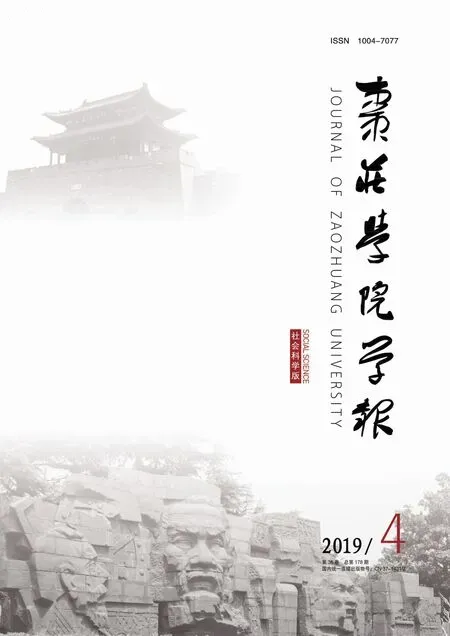21世纪以来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内涵与发展向度
周少川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21世纪以来,我国的古籍整理和古文献的研究呈现可喜的局面。国家启动了古籍保护计划,《中华大典》《儒藏》《清史》《中华再造善本》《中国古籍珍本丛刊》编纂等重大文化工程全面开展,出土文献的研究、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域外汉籍的搜求和出版,古籍整理和古文献研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历史文献学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学科建设不断推进。学科是在科学发展中不断分化和整合而形成的,有的学科是科学分化所产生,有的则是由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整合生成的。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学科内部和学科的外部环境有着多重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历史文献学是一门具有综合性特色的学科,认识其学科发展的历史,把握学科建设的内容与特点,了解学科发展的新方向,会使本学科的创新建设更富有成效。
本文拟就新世纪以来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略陈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历史
历史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正如白寿彝先生在1981年所说的:“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很早就有了。我们可以说,就在这个时候,历史文献学就开始出现了。但如果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来要求,现在还正在建设中。”[1](P510)在我国古代,自孔子整理、编纂《六经》始,就已经有对文献整理研究的实践了。数千年以降,历代文献学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遗存下大量的文献整理研究的成果。不过只有进入20世纪后,才真正出现了以近代学科理念建设文献学学科的探索。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开始问世。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史学家则在文献考据的工作中,为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扩展了范围,充实了内容。特别是陈垣先生,在目录学、校勘学、避讳学、史源学等专学中,以其示范性研究,总结法则和范例,为文献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顾颉刚先生在古书的辨伪方面、陈寅恪先生在中外历史文献的结合利用方面,也分别推动了文献学学科的建设。
然而,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建立,是由白寿彝、张舜徽、刘乃和先生等前辈学者来完成的。20世纪80年代,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和国务院,号召“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教育部提出了“救书、救人、救学科”的一系列有关古籍整理研究和培养整理人才的方案[2](P143~156),时代赋予了文献学学科建立与发展的良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历史文献学迎来了发展的高峰。在学科建设方面,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在1982年出版,二书在数十年文献学发展积累的基础上,对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类书、四部书、丛书、辑佚、辨伪等作出了较系统的梳理,建立了初具规模的文献学学科体系。刘乃和先生则从历史文献的繁富、历史文献的作用和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意义、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和文献学发展史等方面,阐述了学科的专业知识和主要理论问题[3]。与此同时,许多专家、学者对文献学学科涉及的对象、目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尤其是白寿彝先生,更是对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发展历史和分支学科的建立,在理论上构建了运行系统的框架。他认为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内容可分为理论、历史、分类学及应用四个部分,其中理论部分包括:历史和历史文献的关系、历史学与历史文献的关系、历史文献作为史料的局限性、历史文献的多重性、历史文献和相关学科等问题[1](P558~559)。另外,白寿彝先生还谈到了研究历史文献学的意义,以及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等问题[4](P567),提出了学科研究的提纲,为历史文献学建构了理论框架。
此后,关于历史文献学学科构建的论著逐渐增多,以“历史文献学”“古文献学”“文献学”“传统文献学”命名的著作多达十余种,而关于文献学各分支学科的论著、讨论文献学基本理论和学科体系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这些论著充实了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内容,深化了学科理论,推动着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
二、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内涵
新世纪以来的近20年时间,随着我国学术的繁荣,有关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呼声日高,然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对学科建设的内涵的认识却不甚了了,从而造成了定位模糊、名不符实、体系失范等弊病,影响了学科建设的迅速发展。因此,在讨论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时,有必要对上述问题作以下简要的探讨。
首先必须看到,学科是按科学性质而划分的门类,是在科学的发展中不断分化或整合而成的。以历史文献学而言,则是整合了多门学科而形成的一门颇具综合性特色的学科。对于这门综合性学科的建设,规范其学科范畴、认清其建设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如何形成其独特的学科范式呢?从学科建设的层面来看,至少有三个层次。一是关于学科的基本理念,二是学科知识和理论的体系,三是学科的运作保障,也即学科制度、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的建设等等。
第一,学科的基本理念。至少应包括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对象、研究任务,以及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定位等三个方面。对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前辈学者也多有阐论。比如,张舜徽先生在1980年发表的《关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问题》一文中,开篇就讨论了“何谓文献?它的概念,整理对象是什么?”这个问题。他对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还有两点重要的界定:一是不能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文献。区分的界限在于出土文物上有无文字。有文字的出土文物,这些文字可称为文献;无文字的实物,则应属于古器物学的研究对象[5](P6~8)。二是指出,“‘历史文献’四字,自可理解为‘古代文献’”[5](P24)。即将“历史文献”理解为历史上出现的文献,将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确认为古代文献,从而纠正了那种以为历史文献学只以史部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偏狭观念。张先生还阐述了历史文献学学科的研究任务,他说:
研究历史文献的任务,主要是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使之不走弯路错路,这便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职责。[5](P8~9)
近十年来,还有一些学者继续讨论了研究对象的问题,例如董恩林将此进一步确认为“文献的文本形态”[6](P11~19),这是对研究对象的新看法和新解读。
学科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学科的研究领域,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决定了独立的学科特色。因此,研究对象是学科基本理念的重要问题,当前对于文献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依然存有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空间。
对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定位,历来有一种不太妥当的看法,将其看作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按照张舜徽等先生所言,历史文献自可理解为古代文献。由于古代文献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根据,因此,研究古代文献的历史文献学自然是历史学学科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与历史学有着内在的、密不可分的逻辑联系,而不是外在的辅助关系。从历史学学科体系的组成标准来看,即有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世界史、中国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学科,也有以历史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史、史学理论等学科,而历史文献学则是以历史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综上所述,在目前“文献学”还未能成为一级学科的情况下,无论从历史文献学与历史学的渊源关系而言,还是从现行学术管理体制规定的学科体系而言,将历史文献学定位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应是比较妥当的做法。
第二,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自白寿彝先生提出历史文献学应包括的四部分内容之后,很多历史文献学专著都将学科理论、学科历史、专业知识作为学科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目前看来,这种结构还是合理的,但是各部分之中的具体内容仍然值得讨论。
首先,要改变文献学科轻视理论建设的偏见。对于文献学的理论探索,历来有一种偏见,认为文献学研究只有方法,没有理论,也不需要理论。受此影响,多年来文献学的理论建设比较薄弱,这种现象必须改变。因为从根本上讲,文献学研究的实践,如果没有理论总结,就不可能有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和系统化的传承,也不可能有持续的创新发展。在这方面,陈垣先生为我们做出了典范。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校勘成就显著,尤其是清代的乾嘉考据,更是硕果累累。然而,对于校勘之学则未有系统的学理总结。当时学者提出的所谓内校、外校、死校、活校,众说纷纭,却无一足以全面准确地概括校勘之法。只有到了20世纪30年代,陈垣先生在《元典章校补释例》中,才用近代科学的理论,将校勘方法概括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的“校勘四法”,使得校勘学成为一门可以传承,并藉以不断创新的专学。由此可见,理论建设并不是苍白空洞的说教,而是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法门。除了立场、观点、原则等一般性的指导理论外,更多地是从纷繁复杂的专业知识中对法则和学理的提炼,因而应引起充分的重视。
学科理论的内容一直比较薄弱,需要加以充实。总的来说,学科理论应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历史文献学理论的本体论主要在于文献观,要解决文献概念、文献的本质和特征、文献的形态、文献的价值和功能等主要问题。
文献学的认识论,要明确学科的定位及文献学的学科结构;要讨论文献学本身及所属各门专学(目录、版本、校勘,等等)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实践意义和历史发展规律;要思考文献学与传统文化、文献学与当代文化建设等课题。
文献学的方法论,要研究文献学的传统方法,文献学与边缘学科、相关学科的关系,文献学对当代科技成果和国外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吸收等问题。要考虑如何利用当代科学技术成果、引进相关学科和国外文献学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来更新我国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要考虑如何改进和发展文献学研究的传统方法。
历史文献学的专业知识则是关于分支学科的阐述。有的学者将许多学科作为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泛化学科的范围,从而模糊了学科的边界,淡化了学科的特质,不啻抹煞了学科。我认为,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只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注释等六门专学。其他的一些专学,应分属于边缘学科和相关学科。
所谓边缘学科,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同两种或两种以上学科都有交叉关系的学科。比如,以文献学和图书馆学为基础的典藏学。据此而论,典藏、编纂、考证、史源、避讳等专学皆应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边缘学科。而文字、音韵、训诂、金石、档案等专学则应属于历史文献学的相关学科。
第三,关于学科的运作和保障。其中包括了学者的职业化、固定的教席和教学培养计划、学位点、学会组织、专业期刊,以及与之配套的学术制度等等。如果说第一、第二层面主要是关乎学科建设的软件部分的话,第三层面则是学科建设的硬件部分。而且,这一部分较多的涉及到学术管理、行政部门,举凡教席的数量、职称的评定聘任、学位点的设立、重点学科的培育,以及成果的评价指标等等,都要由学术管理和有关行政部门来操作和完成。鉴于目前历史文献学学科受重视程度不够、学术成果(如古籍整理成果)评价指标偏低的现象,在本学科的学科建设中,仍有必要呼吁相关管理部门加大对与本学科发展支持的力度。
当然,就是在学科建设的运作和保障层面,学者本身的努力依然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早在1979年,张舜徽先生就创立了本学科的全国性学术组织——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创办了学术集刊《历史文献研究》(曾名《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30多年来,学会和集刊在推动历史文献学的科研、教学,凝聚学术力量,促进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今后学会也将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
三、历史文献学学科发展的向度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历史文献学与其他人文学科同样,既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面对挑战和机遇,历史文献学学科发展的向度就是要不断深化对学科建设内容的认识,深入持久地开展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科学凝练、精准提升学科的基本理念,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繁荣和发展历史文献学的学术研究。在学术和学科的相互关系中,学术是第一性的、决定的方面,学术的发展决定学科的发展。因此,只有不断繁荣历史文献学的学术研究,取得经典性的学术成果,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学科建设的迅速发展。
历史文献学学科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向度,就是要遵循学科发展的规律,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将文献学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古籍整理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历史文献学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确立和发展,缘于当时兴起的古籍整理高潮急需人才培养和理论、方法的指导;而反过来看,历史文献学的学科知识和内容则是千百年来古籍整理经验和方法的学理总结和升华。因此,历史文献学的发展要从古籍整理的实践中汲取精华,要通过服务于古籍整理实践来实现文献学的学科价值和学术影响。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推动。
一是要从古籍整理的实践中加强理论和方法的总结,近百年来现代意义的古籍整理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该把实践中的理性认识系统归纳、提升到理论层面。比如,要从古籍整理的性质、发展方向和时代的高度认识其意义;把握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以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双创”方针;说明开展古籍整理所必备的前提和条件;要从学理上阐析各类整理方式的目的和功用、程序和方法、具体的学术标准和要求;要从古籍整理的成功案例中梳理值得借鉴的技术和方法,作方法论上的总结。纵观百年古籍整理的发展,其中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堪称经典,比如《四部丛刊》的原版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配版描润、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点、古籍今译的意境与传神、《大中华文库》的外译、古籍数据库建设等等。要通过方法论的总结,既从事实上详细描述各种方法的内容,说明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运用;又从理论上加以抽象和概括,阐明这种方法的特点、运用范围和革新意义。长期以来有一种偏见,认为古籍整理只是技术,不需要理论。其实古籍整理也和其他学科一样,如果没有理论指导和学理基础,就不能有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也不能有系统化传承和持续的创新发展。因此,从文献学的学理层面总结古籍整理的理论和方法,既为文献学增加新的学科内容,又可为古籍整理的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二是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从学科理论的高度,为古籍整理工作制定符合实际操作的学术规范。除了推介古籍整理精品,从正面总结成功经验,还要从反面检讨以往古籍整理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从学术上分析其致误原因。古人曾有致误通例的归纳,我们也可按古籍整理的不同方式分别梳理标点致误通例、校勘致误通例、繁简字转换致误通例等等,以吸取教训,提示来者规避错误。此外,应在学理研讨的基础上制定各类古籍整理形式的规范,从以往对古籍整理成果的评论中,提炼出各类古籍整理成果的评价标准,为不断提高精品意识和整理水平提供借鉴,从而指明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方向。近年出版的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列举7种整理形式的具体要求并加释例予以说明,严谨缜密,即是从文献学的学术要求出发,探索建立古籍整理学术规范的有益尝试。
三是把握新态势,开拓新局面。进入21世纪,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繁荣为文献学研究和古籍整理事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国家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发展战略,既赋予文献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献学学科发展要通过古籍整理实践,直接地为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服务;要遵循“双创”方针,不断开拓古籍整理的新领域,力争在在原创性上有所突破,以解决目前古籍整理出版仍存在的大量简单重复、浪费资源的问题。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也为文献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开辟了广阔前景。数字化、网络化为古文献和古籍的存储、检索、传输、复制、整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随着信息处理功能的不断提高,还有不少新技术可用于简牍字迹的辨认、古书版本的鉴别、古籍碎片的拼缀,等等。文献学的学科发展要密切把握科技发展新态势,研究开发利用新技术,以提高文献研究、古籍整理的效率和水平。并以开阔的视野,借鉴国外整理古籍的科技手段和文献研究的方法,不断开拓古籍整理和学科发展的远大前景。
四是要纠正历史文献学教学与古籍整理实践脱节的现象。多年来,文献学教学存在着教材陈陈相因、内容老旧、结论过时,以及学生的文献学知识只限于纸上谈兵,在点校古籍等整理实践面前不知所措、无能为力等问题。学科建设未能发挥文献学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在培养古籍整理人才、指导古籍整理工作的作用,其症结就在于脱离了古籍整理的实践。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上述关于文献学从古籍整理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丰富和更新文献学学科理论和专业知识外,还要在文献学教学中结合新近古籍整理的实例,传授古籍整理实践的技能和知识,并借鉴陈垣“史源学实习”课程的方法,安排一定的课时,组织学生进行古籍整理实习,让学生了解古籍整理最基本的程序和方法;研究生则可以参加有关古籍整理的项目,让他们在实践中加深对专业知识的认识,增长才干。
最后,历史文献学发展需要良好的学科发展环境。在学科建设的运作层面上,学科发展需要强有力的社会支撑体系,我们期待得到有关管理部门更多的关注,优化管理制度,以及在资金、人员等资源上有更多的投入。在内部环境上,则需要专业的教学科研人员加强自律,克服当前存在的一些学风浮躁、学术肤浅的弊端。在加强学科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学风建设,发扬本学科久已有之的严谨专精、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不断创新进取。只有内外合力,才能把历史文献学建设成为一门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优秀学科。
——盐业古籍整理新成果《河东盐法备览合集简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