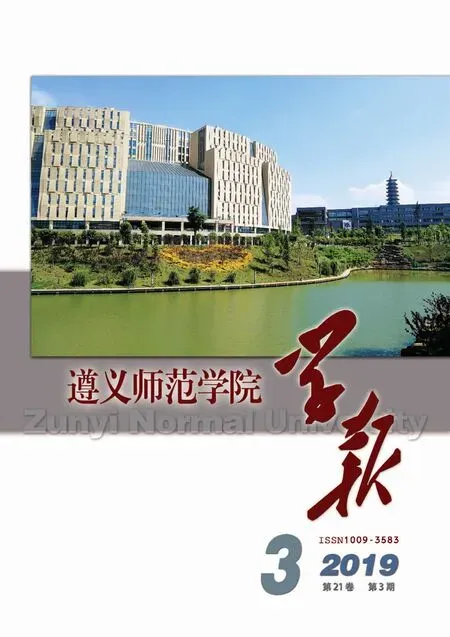遵义会议的酝酿与准备
李懋君,聂国梅,周 璐
(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遵义563006)
研究红军长征史料,会发现有这样一个特点: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常是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在湘江战役之后尤其明显。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确保了红军战略方针的正确性,为赢得长征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建国70周年之际,回顾这一系列会议,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发生的伟大转折的思想轨迹,看到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中走过的一步步坚实的足迹。长征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每个会议成为其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和有机组成。在众多历史合力的作用下,推动了党的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遵义会议则是伟大转折的标志性事件。由此,对每个会议的研究和评价都要放到历史发展的整个链条中去把握。
红军长征转战贵州期间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为红军长征战略转移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和关键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遵义会议前后系列会议的召开,无不是围绕着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酝酿、准备、补充、执行,不断总结和发展完善,直至遵义会议通过的行动方针最终得以顺利实现,由此我们将一系列围绕着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举行的若干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及军委联席会议等,视为遵义会议系列,并划分为酝酿与准备、召开与决议、总结与完善三个阶段。
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酝酿已很久”。自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在1934年至次年,先后召开了三次重要的会议,即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这三次会议的主题都集中在军事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上。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议,周恩来在1943年11月27日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1]杨尚昆在回忆录中指出“湘江一战,红军折兵5万,似乎已濒临绝境。面对这样惨痛的事实,全军上下自然会同前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对比,那时,红军一直能以少胜多,苏区面积不断扩大。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正如彭总所说‘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大家对博古、李德的指挥已由怀疑、不满到完全失去信任,逐渐觉悟到这是他们排斥毛主席的领导、推行错误的战略战术的结果。”[2]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力主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在通道、黎平和猴场会议上得到了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使红军的战局出现了转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奠定了相应的思想基础。
一、通道会议实现初步转兵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八万余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前进的方向在红军到达通道之前都是很明确的,就是到达湘西与贺龙、肖克和王震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而此时,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并非毫无察觉。11月17日,蒋介石南昌行营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匪”计划大纲》中明确表明要“防西窜之匪一部,或者残部,如窜过湘、漓水以西,应以不使该匪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肖合股之目的。”蒋介石调重兵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等着红军向其布好的大口袋里钻。而博古、李德在此危急情况下,仍坚持既定的战略方向,没有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
通道会议就是在这样紧急危险的关头临时决定召开的。当日军委就作出了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及进占黎平的“万万火急”的部署,准备入黔。李德、博古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迫于形势,也不得不进入贵州。但是在十三日给各军团的电令“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的目的”,说明李德、博古等人并未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原计划,只是同意改变行军路线,先西进贵州黎平,再北上湘西。
二、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了战略方向的调整
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为两路纵队向贵州黎平县境进发。以红一、红九军团为右路纵队,于12月13日由通道出发,经湖南靖县、新厂、平茶进入黎平,并于14日经马家团、潭溪、罗团、草鞋铺、五里桥,击溃黔军周芳仁旅第7团,占领黎平县城。这是中央红军入黔以来占领的第一座县城。与此同时,以红三、红五、红八军团及军委纵队为左纵队,由湖南播阳出发,经流团进入贵州黎平县境,随后又经草坪、洪州、地青、中潮、佳所、羊角岩,于15日陆续进入黎平县城。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长征途中的首次政治局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转兵贵州、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的决定。这使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再次肯定。
因为通道会议新调整的行军路线只是一个避敌锋芒的战术行动,没有放弃原有的战略目标,仍然要求我军西进贵州,尔后沿黎平、锦屏北上,去会合红二、红六军团。军委从十二月十三日到十六日所发出的关于行军部署的电令来看,仍然以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为目的,只不过路线变为经过黔东折向湘西。直到十二月十七日才对红军的进军部署作了重大改变。从十八日行动部署来看,可以说此时毛泽东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才得以实现。周恩来 1943年11月27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也谈到这方面的情况。他说:“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聂荣臻回忆录》在谈到黎平会议时也说:“黎平会议是一次重要会议,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许多同志改变了观点,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这说明在黎平会议前夕,中央多数领导人才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
黎平会议彻底地否定了原定的战略方针,决定向黔北进军。随后签署的《军委为执行黎平会议决议作出的行动部署》,将会议决议明确为具体实施的军事部署,对红军以后的作战方针作出了明确指示。如进入黎平后,将政治工作、宣传工作与军事斗争结合起来,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纲领,通过打土豪积极动员组织群众,同时根据民族地区的特点,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为此政治部颁布了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为红军顺利通过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黎平会议只开了一天,由于时间仓促,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战略指挥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纠正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红军就无法改变在军事上的危险被动局面。因此在红军到达遵义前,会议已开始酝酿。王稼祥谈道,在长征到达遵义城前,“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3]伍修权也回忆道,“在进遵义前,王稼祥同志最早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而后占领遵义,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根据陈云于1935年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的记载[4],以及聂荣臻回忆录中有关内容[5],黎平会议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批判了这些错误思想,为遵义会议进一步批判、纠正这些思想及这些思想指导下的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确立积极防御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猴场会议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进军,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为后续甩掉蒋介石围堵红军的几十万大军创造了条件。但“左”倾冒险主义者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此时敌人追兵已至,情势依然万分危急,为避免陷入敌人重围,1934年12月31日夜至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乌江南岸的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
会议经过激烈讨论,否定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主张,依据黎平会议精神,发布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正是由于猴场会议的召开,彻底否决了李德等人再次提出的回师湘西的建议。从当时情况来看,黎平会议决定的执行在中央红军进入乌江流域之后,随着战略方向上的重新争论,面临着有可能被否定的危险。猴场会议作出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对中央红军的战略任务和行动方针作了新的规定。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新的决定精神,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军事负责人又连夜部署并指挥了突破乌江天险的战斗,规划了中央红军向黔北地区进军的计划和步骤,指导中央红军打过乌江,进占遵义,黎平会议提出的进军黔北地区的战略设想才得以实现,转兵贵州这一过程才最后完成。会议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坚持了党委集体领导原则,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否定了党内决策专断。当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同志在他的整风笔记里对此有所提及。三人团”的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同志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则说:“他(指李德)虽然是个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6]《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也指出“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7]陆定一同志1944年在延安中央党校作的《关于遵义会议的报告》中,说得更明确、具体:“由博古一手把他提拔起来,成了个太上总司令。他在领导上是包办一切的。指挥作战时,连一架机关枪应当放在什么地方都要由他在电话中按照军事地图(那时的军事地图,是北洋军阀测量的,是不正确的,只能作为参考,不能用来指挥战斗)指定。他的工作作风和对人的态度是蛮横无理的。”[8]他们的言行,必将影响黎平会议决议的执行。如不过乌江,势必又钻进蒋介石的“大口袋”。此时,排除左倾领导人的军事指挥权关系党和红军的前途和命运。聂荣臻回忆道:“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5]
在这种情况下,猴场会议决定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并责成书记处与军委保持同二、六军团方面的密切联系,加强对于他们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领导。[7]对李德在组织上进行约束,改变了过去由其个人独揽军事大权的做法。
猴场会议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如刘少奇指出“特别是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期间统治全党的以王明、博古等同志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但没有接受过去几次错误路线的教训,而且由于他们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和横蛮武断的作风,把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发展到了党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地步。他们完全不顾当时国内社会各阶级的实际状况,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客观形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采取了极端冒险的政策,在党内生活上也完全破坏了党内的民主制度,发展了过火的党内斗争。”[9]而猴场会议明确规定,“三人团”的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这意味着开始排除“左”倾错误领导人在军事上的独断专行,开始恢复党的集体决策和集体领导的民主集中制,改变了过去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为后续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毛泽东在军事上有了发言权,并在不断的充分讨论之下,赢得了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支持,有利于其正确的军事主张得以贯彻,也有利于重新确立他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可见,遵义会议是经过长期酝酿而最终完成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必要准备,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取得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奠定了基础。红军长征对中国革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系列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但这一伟大转折的实现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成熟的历史轨迹。回顾历史,红军长征过程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的宗旨,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今天仍值得我们不断总结、反思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