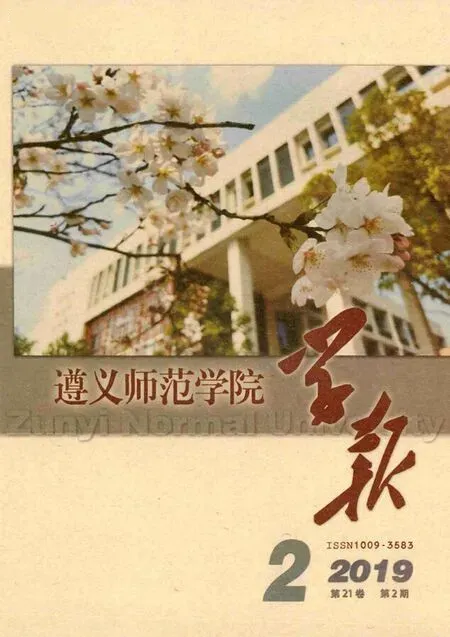《东邪西毒》环形叙事视角下的解读
陈 玲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00)
1994年绝对是难以逾越的电影年,出现了一大批电影杰作,如中国的《重庆森林》《东邪西毒》《活着》《霸王别姬》《阳光灿烂的日子》等,西方的《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低俗小说》《狮子王》等。《东邪西毒》是王家卫光影世界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环形叙事结构谕示永世不得挣脱的人性循环,时间对人的意义消失殆尽,空间对人成为一种束缚与框定,人物最终在虚无的黑洞中无力地自我消耗与消亡。
一、环形叙事结构
环形叙事结构电影是非线性叙事电影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它把故事分割成保持某种关联的叙事片段,再采用蒙太奇手法把叙事片段依据某个主题拼贴成电影;与此同时,把叙事片段拼贴为互为因果的段落,最终使故事结局呈现出无始无终的艺术效果。这类电影的横向文本时间犹如首尾相衔的“圆圈”,纵向的文本时间呈现为一堆时间碎片。
在叙事结构上,《东邪西毒》也是一部环形叙事结构电影。电影根据环形人物关系(桃花、慕容嫣/燕爱慕黄药师,黄药师却爱着欧阳锋大嫂,大嫂爱着欧阳锋,欧阳锋却逃避并在桃花与慕容嫣/燕的身上想象大嫂)将故事分为关于爱情亲情友情的几个叙事片段,但是这些叙事片段并不是以因果关系维系而以循环人物关系为线索。然后利用循环人物关系将叙事片段进行多线索的交叉的拼贴叙述,此处是五组参差交错的人物关系(欧阳锋-大哥-大嫂-慕容嫣/燕-桃花,黄药师-大嫂-慕容嫣/燕-桃花,慕容嫣/燕-欧阳锋-黄药师,盲武士-桃花-黄药师,村姑-弟弟-洪七)进行交替拼贴叙事,使得影片结构上呈现为一幅斑驳零散的图景。参差交错的人物关系环环相扣,故事始于欧阳锋雇佣杀手,中间却是纠缠不清的爱恋关系,桃花与慕容嫣/燕爱慕黄药师,黄药师却爱着欧阳锋大嫂,大嫂爱着欧阳锋,欧阳锋却逃避并在桃花与慕容嫣/燕的身上想象大嫂,故事又终于他雇佣杀手。故事结尾即是开头,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最终,电影形成一个首尾呼应的环形结构,所有的人物都被困在感情的圆圈之中。时间与时间在零碎斑驳的影像中化为灰烬与碎片,人物在时间荒漠与空间碎片中自我沉醉、绝望与耗尽。
二、时间灰烬——后现代的能指游戏
(一)理论背景
“我们可以设想一部只是纯粹延续时间的电影,即一部画面至始至终都是空白的影片。”[1]马塞尔·马尔丹断言,电影是关于时间的艺术。的确,任何艺术都离不开时间,任何一部电影也离不开时间,虽然对时间的体验与表达千变万化。
在传统社会,人们对时间的体验是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时间,它指向彼岸世界而具有解脱与重生意义,并给人一种安全感与神圣感。进入现代社会,神圣时间是可以精确计算的机械的钟表时间,丧失了原本的神圣感而变得越发冰冷。进入后现代社会,时间从精神与机械转向人的身体,从历时性转为了当下的瞬间性,这种转变导致人类与本源时间不断变得隔离疏远。时间的加速而越发轻盈快捷,冷漠地穿梭在任何一个空间角落;时间不再指向终极意义与永恒价值,而转向注重体验瞬间快感,所以临时性与短暂性成为个体快乐幸福之源。这种美学思潮反映在环形叙事电影之中时,电影利用审美化手法将客观时间变成一种圆形时间,解构时间的线性特质与历史性,导致时间可以被任意改造而丧失严肃性变为一种支离破碎、破败残碎的能指游戏。
(二)人与时间的矛盾和对抗
王家卫的电影对时间格外敏感,像《重庆森林》中警察223的保质期独白,《阿飞正传》中阿飞讲述“无根鸟”,《东邪西毒》英文译名为“Ashes of Time”(时间的灰烬),都是关于时间的哲理思考与艺术表达。电影利用沙漠、镜子、醉生梦死酒等意象表达对时间的隐喻与象征。洪七问西毒:“沙漠的后面是什么?”欧阳锋回答:“只不过是另一个沙漠。”然后欧阳锋独白:“每个人都会经过这个阶段。看见一座山,就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我很想告诉他,可能翻过去山后面,你会发觉没有什么特别。回头看,会觉得这边更好。但是他不会相信,以他的性格,自己不试过是不会甘心。”是的,洪七会去寻找时间的意义,他在对抗时间。我们用沙漏去计算与测量时间,它代表过去、现在与未来而并且自身成为一种时间象征。电影中的辽阔无边的沙漠则是一个静止的巨型沙漏,所有人被困在时间荒漠又难觅出路。时间无所谓客观还是主观,也不是机械时间或生命时间,而是冷漠无情的后现代时间,它是一个裹挟众人的巨型沙漏。巨型沙漏的单调重复、无边无际、死气沉沉丧失了勃勃生机而成为众人沉重而永久的惩罚。无论是与时间抗争的洪七,还是对时间无望的欧阳锋、黄药师等人,终将被期待时间的绝望所吞噬。
明镜照物,妍媸毕露,镜子的原本作用是让自己看到自己形象。电影中出现镜子的地方是欧阳锋大嫂对铜镜的自言自语:“我觉得有些话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想,说不说也没什么分别。有些事会变的。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看着镜子,才知道自己输了。在我最美好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人都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那该多好?”镜子是提醒人们时间的一种工具,对人既是催促也是压迫,它提醒西毒大嫂再美好的时光也必将散尽天涯;再次目睹镜中容颜,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酒和时间又有何关系?欧阳锋嫂子托黄药师给欧阳锋带去一壶醉生梦死酒,并且嘱咐:“喝了之后,可以叫你忘掉以前做过的任何事。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如果什么都可以忘了,以后的每一天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你说多开心?”黄药师喝了醉生梦死,忘记很多事,但记得自己爱过一个叫桃花的女子,于是前往桃花岛居住。欧阳锋喝了醉生梦死,经常会望着白驼山,后来醒悟“其实,醉生梦死只不过是嫂子跟他开的一个玩笑。越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忘记的时候,反而记得越清楚。”醉生梦死酒让人忘记烦恼,其实是人与记忆的博弈,本质上是人与时间的矛盾与对抗。但记忆是一种很磨人的东西,该隐瞒的总清醒,该遗忘偏记得。
电影的情节时间从惊蛰篇1——立春篇——夏至篇——白露篇——惊蛰篇2,貌似不同的首尾实则是一个节气。《夏小正》曰:“正月启蛰,言发蛰也。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惊蛰一到,所有人开始忙于春耕。时间悄无声息地从一个惊蛰流转到另一个惊蛰,目睹了巨型沙漏中众人的渺小卑微与徒劳挣扎。从桃花与慕容嫣/燕爱慕黄药师,黄药师却爱着欧阳锋大嫂,大嫂爱着欧阳锋,到欧阳锋逃避并在桃花与慕容嫣/燕的身上想象大嫂的拒绝与被拒绝的痛苦折磨始终未曾停止。一个惊蛰开始,下一批苦情的人又将在西毒的客栈上演。
三、空间碎片——丧失意义的后现代空间
(一)理论背景
随着生产力发展与人类思维能力增强,空间之于人最初的意义——给与我们生存活动的边界与范围,早已面目全非。20世纪以来,空间问题引发了很多学者的关注。爱德华·W·苏贾认为:“对空间的重申以及对后现代地理学的阐释,不仅仅是经验性考察的一个聚焦点,也是对这样一种需要的回应:对具体的社会研究和熟悉情况的政治实践中的空间形式,需要加强注意。”[2]他将空间问题上升到了本体论的地位,足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的确,空间问题早已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了。如今,依赖科技迅猛发展,我们深深体验着时间加速度带来的压迫与拥挤之感;天南地北也是一抬腿的事情,但这科技进步却不是普惠性的,是以能否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划分社会等级的。“由于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时间/空间距离的消失并没有使人类状况向单一化发展,反而使之趋向两极分化。它把一些人从地域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某些社区生成的意义延伸到疆界以外——而同时它剥夺了继续限制另外一些人的领土的意义和赋予同一性的能力。”[3]因此,拥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快的速度已经成为一种权利与身份地位的象征,这反而导致空间贬值。
从前现代、现代到后现代社会,我们对社会变化的体验不仅仅涉及客观物质与思想观念,其中对时间感与空间感的体验也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线索。由于占有空间意味着权利的彰显,所以现代社会对时间与速度的追求目的在于征服更加广袤的空间。但随着科技发展导致时间加速度,后现代社会以追求高速度为荣,空间丧失原初地位;并且,时间加速将空间挤为碎片,空间意义渐渐丧失。
电影的空间是一种“由音乐,由特定的蒙太奇组合节奏,由风格化的色调与构图所唤起的辽阔、幽远的空间联想”[4]。这种思潮反映在电影美学之中,电影空间已不是一种单纯为故事服务的物理空间,更不是传统的以因果逻辑维系的影像空间,而是一种丧失因果逻辑旨在表现人物内心体验的零碎片段的后现代空间。
(二)丧失意义与人浮于世
《东邪西毒》的影像空间是典型的后现代空间,空间因为丧失因果逻辑的维系而失去了线性感,导致影视人物犹如漂浮穿梭于各个空间碎片,同时流露着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飘零之感。电影时间经历惊蛰篇1——立春篇——夏至篇——白露篇——惊蛰篇2,每个篇章之间不以因果逻辑贯通而是散文化拼贴,以及非线性时间连缀的空间变得破碎不堪。因此,电影感染人心之处不是这个新颖的诗意的非武侠故事,而是一个场景、一句台词或者某个人物,整部影片都弥漫着一种碎片化的朦胧暧昧之感,令人感觉意义丧失与人浮于世。显然,人物都在自己的空间里安生与逃避,除了洒脱自在的洪七公之外,其他人物都有一个共性:心事重重、郁郁寡欢。每个人所属的空间都是个人的、排外的、焦虑的、孤独的,所有人都难以逃避时间荒漠的煎熬与精神层面的孤独。
电影采用奇峻多变的摄影角度、多样复杂的广角镜头、倾斜变动的画面构图营造出一个孤独荒凉的影视空间。每个人物既有自己的空间领域,也被空间束缚规定。人物以空间命名而彰显权利地位,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的名称不仅是身份权利,也是性格特征。为情所困的欧阳锋困于沙漠孤独神伤,爱而不得的慕容焉/燕蜗居窑洞心性变异,移情别恋的桃花在五彩河中寂寞难耐,洒脱自在的洪七四海为家,孤苦无依的孝女唯有依靠枯木,这些囚禁肉身的空间不仅是一种物理空间,更是他们人物特征的强化与见证。
四、思想意蕴——虚无的黑洞
德国现代思想家恩斯特·布洛赫在《希望原理》问到:“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我们去往何处?我们在期待什么?什么在期待我们?”[5]这些问题我们耳熟能详,但却始终无解,或许时间才是一切谜的谜底。
欧阳锋深爱大嫂却躲入沙漠,黄药师爱恋西毒大嫂又移情别人,慕容嫣/燕因爱生恨欲杀黄药师,桃花移情别恋而独受煎熬,这群人渴求爱情又害怕被拒绝,宁愿忍受煎熬也不肯去面对,最后白白折磨自己。正如“那沙漠后面会是什么呢”,是另一座沙漠,也是现代人漫无边际的情感荒漠。最后主人公都有了自己的绰号,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被空间定义限制,终身漂泊于天地四极。
“在这里,不再有对世界的有意义的整合,也不再是从‘有意义的眼睛’出发进行对无意义的世界的批判,有的只是蜕化为纯粹呈现性的‘眼睛’的单纯呈现本身。这就是后现代的荒诞。”[6]《东邪西毒》中,人物的生活动机与结果冲突、现象与本质相反,透露着一股荒诞气息。在一个无精神寄托的虚无时代,无所谓意义和价值,也没有对意义丧失的控诉愤怒,只是着眼当下的嬉戏。像环形叙事电影《东邪西毒》,人物原是为了追求美好的爱情,最后却事与愿违,越是抓紧不放,越是痛苦难熬。坚持只能带来痛苦与煎熬,索性,欧阳锋黄药师选择逃避,慕容嫣欲杀阻止自己去追求爱情的哥哥“慕容燕”(实为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折腾纠结半生,最后发现又回到了当初的原点——惊蛰2。影片最后没有明显的爱恨情仇,有的只是空洞平面之上的无力、颓废与游戏。
《东邪西毒》中的时间不再是单纯的展开叙事的手段,而是被叙述的主题之一,还是携带无限循环色彩的圆形时间。本质上,该片反映的时间灰烬问题也是自古以来困扰人类的时间问题。《东邪西毒》中犹如达利《软钟》的时间荒漠,反映了时间高度加速、空间无限拓展的事实。此处反映了后现代时间的瞬间化和极速化体验,以及给人产生的一种压迫之感与无所寄托之感。时间瘫软无力化为一望无垠的漫漫荒漠,空间破碎残破化为一种充满隔阂的束缚与限制;对于心事重重的欧阳锋、黄药师、慕容嫣/燕而言,时间是一种犹如无尽沙粒的丧失意义的精神折磨,空间是一种拒绝沟通与自我保护的躯壳。总之,电影使用富含诗意与意境的手法书写后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在时间荒漠空间碎片中毫无寄托的自我耗尽与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