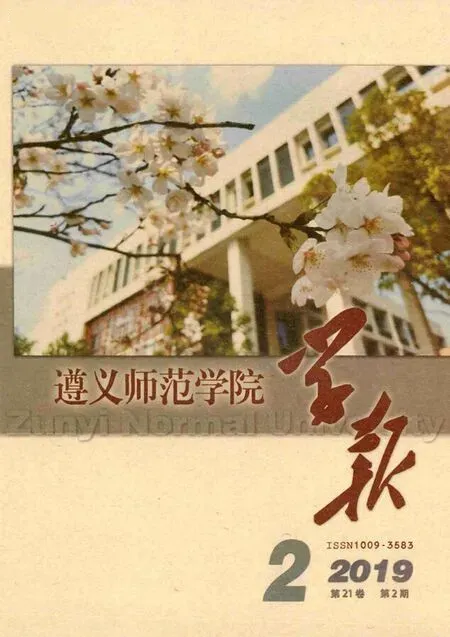一部沉重的历史备忘录
——《土地坑》阅读随想
王明析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人大常委会,贵州务川564399)
一
在《土地坑》⑴一书的封面上,有一句意味深长的“广告语”:本书以独特的视角,讲述农村生活的场景……
我以为,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土地坑》一书的核心。稍有不足者,是“农村生活”之前少了一个“‘文革’期间”的定语。我揣测编辑的良苦用心,大约是不想让这个定语太刺眼。据我所知,《土地坑》现在成书虽然有三十二万字之巨,但原稿已经被删除了十五万字。删去的据说都属于比较特殊的内容。不过即便如此,现在公开出版的这本书,依然为我们保留了相当丰富的历史信息,是一本回忆特殊年代农村生活的历史备忘录。
我把《土地坑》视为一本历史备忘录的主要依据是,书中的土地坑是一个真实地名,与之相邻的几个山寨比如飞羊坡、牛栏门等也实有其名,当年它们都同属务川县丰乐区牛塘公社大坪村大队管辖;而我当年插队的土寨也是大坪村大队五个生产队中的一个,与土地坑的直线距离最多只有三公里。只是土寨与大坪村在《土地坑》一书中没有像飞羊坡、牛栏门那样沿用原名,而是将其改成了小坪村和后寨,其它如偏洋洞、皂池坝、皂角墩等,其地名和方位均能与现实生活完全重合。《土地坑》一书中的主要人物也均能完全对应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有的只是用谐音等方式改了人物的原名,例如书中的主人公岩初,连他申氏的姓都没有改变。
基于此,笔者自以为有充足的理由把《土地坑》一书视为当下文学界比较流行的“非虚构写作”。我认为,这样定义它的文本性质,有助于我们对它的认识和理解:从材料翔实的角度看,它是一本可信的历史备忘录;从它客观而不乏琐屑的纪实特征看,它还有一些小说类叙事作品的冷叙述特征。而这两者的水溶交融,恰好让《土地坑》再现的那段农村生活画卷变得愈发具体生动了。
二
《土地坑》的作者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下乡时间是1968年秋。对中国当代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或许知道,这正是所谓“前期文革”终止的时间。随着红卫兵浪潮的戛然止息,当年在全国各大小城市风流一时的红卫兵绝大多数都下乡当了知青。作者从县城来到农村,虽然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农村严酷的现实环境还是让他有些始料未及。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书中所写的三个知青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从生产劳动到日常生活,他们很快就转变身份成了土地坑生产队的新社员。《土地坑》一书主要以岩初的视觉看日常生活,写他的见闻和亲身体验,以及触景生情的思考。书中很少展开议论,抒情的文字几乎看不到,几乎都是客观记叙,画面感很强,颇为感人。作者自谦此书是“大作文”,但我非常看重的恰恰是这种“大作文”的文体风格,它写人叙事的那些章节段落,很类似有些小说的冷叙述风格;其感受和思考几乎全部都隐藏在对人与事的叙述中,但它又不是小说。所以,我就把他看成是一本用“小说笔法”写成的历史备忘录。
说《土地坑》是一本历史备忘录,还因为我和《土地坑》的作者一样,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也曾是那里的知青。不同的是,1975年我下乡时,作者已经离开了土地坑。而我插队的土寨由于距离土地坑并不远,因此《土地坑》一书中所记叙的很多农村日常生活习俗和生产劳动情形,我都非常熟悉;早已消逝在时间长河的某些山乡生活场景的模糊记忆,比如打田栽秧、秋收秋种这一类农活,以及砍柴、碾米、做饭等一系列生活琐事,都因为阅读《土地坑》又重新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了。由于《土地坑》采用的是纯写实手法,事无巨细地记叙主人公岩初在农村的亲身经历,所以读者不但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那时黔北农村广大农民真实的生产、生活境况,而且还能从这样的境况中进一步看到当时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
《土地坑》全书四章,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第二章标题是《农忙与度荒》,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富深意的标题。按理说,农民直接从事田间耕作,吃饭的问题应该早已解决,至少也是温饱不成问题。但是,我们在书中看到的这方面的情况却令人感到非常遗憾,有些地方的记叙甚至令人感到毛骨悚然。这之前,看过一些所谓“忆苦思甜”的影视作品和书籍,知道历史上农民有“逃荒”一说。《土地坑》虽然没有记叙有人“逃荒”的事,但当地农民却每年都要经历“度春荒”和“度秋荒”的严峻考验。何谓“度春荒”?书中写道:
春耕春种的农活是最忙最累的,此时人们的体力消耗最大,最需要吃饱饭。然而这时却正是农村青黄不接最缺粮的时候。尤其在夏收作物如麦子、豌豆、胡豆、洋芋还没有完全成熟到可收割,各种蔬菜、瓜类、豆类还没有长到可采摘时候,也是农村生活最难最心慌的时候,乡下人习惯把过这段日子称为度春荒。农村有句顺口溜:春荒春荒,食不果腹心发慌。
一个没有当年农村生活体验、没有对那个年代的农村现状做过脚踏实地研究、看过一些真实历史书籍和资料的人,是很难相信作者的记叙的。此前说过,我在距离土地坑不远的土寨插队,因此,阅读本书,它马上就唤醒了我当年的一些记忆。《土地坑》中写到农民用瓜菜充当主粮“度春荒”的心酸生活,也是我所在的生产队常见的现象。书中写到给新洋芋“验蛋”的事,我虽然记不起当年在土寨是否有“验蛋”一说,但“验蛋”的事却亲自见过,包括书中记叙习初在他家洋芋地里“验蛋”,作者发现习初每摘下一个“验蛋”后的合格者时,脸上的那种凝重表情,同样能让我突然记起当年在农村目睹过的类似生活情形——那不仅仅是“凝重”,而且还很愁苦。《土地坑》中记叙农民一年辛劳到头不仅要“度春荒”和“度秋荒”,而且还写了家家户户“除过年过节、贵客临门外,绝不随随便便吃净粮食饭”的心酸生活情形。黑大爷一家虽然有黑大娘的精打细算,不至于在“度春荒”和“度秋荒”中全家人饿肚子,但他们一家一年四季吃的是什么呢?
秋天吃红苕饭,荒瓜饭,冬天吃酸菜饭,春天吃火葱、蒜苗叶煮稀饭。她家菜园里的东西除了要给猪吃外,凡无毒的她都要收拾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比如老青菜叶,是舍不得喂猪的,把它收来,先洗了晾干一下,切碎放一点盐,放在倒坛里卜起,卜到一定时候,拿出来晒干水气,继续放进坛子里卜。就这样,到青黄不接时(再拿来当粮食吃)……
书中记叙的这位知青房东黑大娘,是中国农村千千万万淳朴的农村妇女的典型。她善于持家,任劳任怨,似乎也认命。她丈夫黑大爷对她的评价是:“她这一辈子病不怕,死不怕,就怕饿。”黑大娘自述说:
我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饿。饿饭那几年,那个阵仗现在想起都害怕。饭没得吃的,活路还要做。有一天收工我先回来,准备拿行头去食堂打饭。走到枫香树下,看到离灶房门就几步了,那脚杆就是提不起,好不容易才挪到门边,想要进去,脚就是抬不起,就是跨不过门槛,进不到屋。没办法,我只好手先趴在门槛上,两只手往屋里爬,手先进去了,身子和脚才慢慢跟着拖进屋里来。
这段幸存者的回忆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谁能想到,1949年后,在中国农村居然还会发生这种悲惨事?问题的关键是,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的、真实的历史;类似的事,当时在务川农村各地可谓习以为常,在笔者看过的相关地方档案资料中都有记载,有的已被编入笔者主编的《沧桑务川》一书。在《土地坑》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因为“大跃进”要大练钢铁,大办食堂,农民连家里的最后一口锅都上交集体了,偷偷炒几颗豆子来充饥,还是用的一块偷藏的铁片;而且炒豆子也只能在晚上偷偷地炒,因为只要上面发现哪家冒烟,有人在家里煮东西吃,就会派人来搜查,不但东西要没收,人还要被批斗。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土地坑被饿死的人不是几个(事实上其他生产队也大有人在),用书中当事人转述的话说:“哪个不是那两年走的。”我读《土地坑》最大的感受就是,作者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思想情怀,用真诚的写作态度,为我们还原了当时中国农村最真实、最原始的生活场景,让我们在时间已经流逝多年后的今天,还能透过书中朴实无华的叙述,看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的残酷现实。
人类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恐怕是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无法否定的基本道理。但具体的路径怎样走,彼此的观点与看法则可能大相径庭。人的观点与看法不会凭空产生,它总是在一定的知识吸取、事实认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所谓教育也好,宣传也罢,如果我们讲逻辑,尊重事实,我想许多人都会对中国道路前进的方向形成大致不差的共识。我们今天的经济总量虽然已经非常可观,但农业农村的发展依然是一个大问题;今天解决不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前进之路一定还会有许多致命的羁绊。所以农村的生产力怎么激活,就成了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大问题。改革开放前,怎么搞活农村经济,怎么发展农业,国家有过一些思考和措施。这里既有成功的尝试,也有失败的教训。怎样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需要我们对既往真实的农村生活有充分的了解,才有可能为制定新的政策提供依据,从而避免走弯路,甚至是回头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地坑》所具有的历史备忘录价值不可小觑。从书中所写的众多农村生活景象看,农民的生活是非常艰辛的,一年四季,很多时候都是在为怎么解决温饱而劳心劳力,每年都在愁苦怎么“度春荒”和“度秋荒”,一年难吃几顿像样的净粮食饭——以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惨剧在时隔多年后依然是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凡此种种,实可谓当年农村的大悲剧。如果我们回想后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存包责任制后,土地还是那些土地,人还是那些人,但人们的生活一下子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难道还不能从《土地坑》中找出当年束缚农村生产力的那些原因是什么吗?说穿了,就是实行人民公社带来的恶果。当年认为,人民公社是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而实际上呢?人民公社不仅不是什么金桥,而是一段实实在在的历史弯路。在这条弯路上,中国农民付出了血和泪的沉重代价,但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不仅缺乏自我反省精神,而且还在为人民公社唱赞歌,对于农民在公社体制前面的抵制行为大加打伐,指责农民的抵制行为是愚昧、落后、保守。在《土地坑》中我们可以看到,生产队因为考虑全队住户比较分散,为了避免大集体全队一起出动到某地劳动的费时窝工,偷偷开始分组劳动,不料才实行几天,就被上级指责为走资本主义“回头路”而制止了。1981年3月,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在国家农委党组会议上就曾很激愤地说:“人民公社是瞎指挥,行政手段干预农民。说的不好听,人民公社是剥夺农民的最有力形式。越搞,越不能因地制宜,越瞎指挥。随便变更生产关系,更助长了瞎指挥。一贯反右,更助长了党内说瞎话,不然就是右倾啊!越是说瞎话,越是瞎指挥,这样恶性循环。安徽老百姓,有的关起门来全家饿死。”万里在讲话中虽然是以他熟悉的安徽为例,实际上,《土地坑》也从当时的政策角度为我们分析了当地农村生产力低下,从而导致生产效果极差的原因。比如大集体的出工方式,“人七劳三”的分配原则,“购五留五”的强行摊派。尤其是后面两项基本政策,对今天很多出生在城里的中青年来说,肯定是闻所未闻。
民以食为天,安居才能乐业,在土地坑,人们建房之艰难也是我们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书中写到的进伦―家,祖孙三代几十年居然建不好一所木房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活在土地坑的农民,生活的困窘之相随处可见。凡此种种,都使《土地坑》一书具备了历史备忘录的史料价值,也成了今日普通读者了解当年中国农村生活状况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三
作为一本老知青回忆插队岁月的往事追忆,我自然还很关注作者对那段特殊生活的记叙和描写,因为自己毕竟也当过知青,而且是在距离土地坑不远的地方。因此,我除了想通过阅读来重温自己的青春记忆外,还想看一看作者当年的插队生活情境,以及他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思考或认识。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知青最早出现在1962年。真正形成知青下乡大潮是在1969年,当时聚集在各类城市的、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红卫兵有数百万人,随着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大批“老三届”中学生开始自愿或被逼无奈地奔赴边疆或农村成了知青。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知青上山下乡开始转入正常化,直到1979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才终止。中国知青运动出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有关它的起因和功过得失,自“文革”结束后一直有不同的评价。近些年,随着知青中的佼佼者开始登上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领导岗位,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多有知青生活经历,知青这个群体开始受到社会一部分人的热捧;一些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也开始有意无意炫耀起自己的这段生活经历——其中最为宏亮的声音,大约要数“青春无悔”之类的豪迈感言了。
《土地坑》的作者家学渊源深厚,自身正直而有学养,有独立思考能力,作为同代人中的佼佼者,他怎样看待知青运动和自己上山下乡这段经历,是我很有兴趣了解的一个重要内容。阅读《土地坑》,一开始给我的感觉就很好:它文字简练,叙述朴实,在写人叙事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带出自己的思想情感,很快就唤起了我的共鸣。作者初到土地坑,人生地不熟,虽然乡亲们没有拿他当外人,对他相当热情,但他独自躺在床上时,还是难免有一些前途未卜的迷茫感。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不一定能记起他插队岁月的有些事,但对第一天到达插队地点所经历的一切,我想都应该毕生难忘。《土地坑》有一个地方令我非常感叹和佩服,作者在写到当年的那些人事时,记忆居然是那样清晰!无论生产劳动,还是日常生活,在他的笔下都呈现出一种活灵活现的原生态景象。书中有很多篇幅记叙的是知青与土地坑农民的日常生活交往,通过作者的生动记叙和描述,农民的勤劳善良、幽默豁达、聪明智慧无不跃然纸上,尤其是书中写到的黑大爷、黑大娘、进伦、牛大爷等底层农民,让人感觉非常可亲可敬。我有时与没有当过知青的朋友和学生闲聊,无意间说到知青话题时,他们有人会流露出某种淡淡的遗憾,对知青生活似乎还有一点儿向往,窃以为都是对真实的知青生活缺乏了解所致,是受了某些“不良影视剧”的误导。其实,真实的知青生活是很严酷的,即使偶有诗意,也常伴苦涩。在《土地坑》中,我们虽然看不到作者有明显的哀怨笔触,但他还是很节制地写到了自己的一些思索和感悟。例如书中这段话——
下乡半年多了,我对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逐渐有了自己的一些体会,我相信每个知青都有自己的体会。不大相信现在说的我们这一代知青如何如何的无怨无悔。……我自己觉得当时的我,活得很卑微,在这种大环境下如何像正常人一样活下去的基本方法和手段都没掌握。老实说,在乡下,我一点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想法都没有,更没有像有的知青那样,有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山乡巨变的远大理想。这里的乡亲们也不会认为他们是教育知青的老师,他们内心是把我们当成被政策弄到他们这里的落难者。他们可怜我们,就像天下父母、兄姐可怜自己的子女、兄妹一样。因此他们手把手教我们谋生的手段,言传身教地让我们获得不挨饿、活下去的思路和方法。知青的到来是要分享他们本来就拮据的粮食的,他们内心并不希望我们在这里扎根落户,而是希望我们早点离开。
这是一段非常诚实的文字,应该是对当时在农村插队的千千万万知青普遍心理的真实写照。几十年后回望插队生涯,作者既没有呼天抢地的怨诉,也没有对自己思想认识的人为拔高;他写得是那样朴素,显得相当没有“学问”,丝毫也不“高大上”。但正是这种朴素的坦诚,却道出了千万知青当年最真的想法。事实上,《土地坑》在写到作者的插队经历时,虽然很多地方充满亮色,甚至不乏生动有趣,但“故事”发生的时间毕竟是在一个严酷的时代。因此,作为一个“牛鬼蛇神”的后代,他当时的生活之路注定是有坎坷的。前面说过,《土地坑》在正式出版前,已经被出版社删除了十五万字。我估计,被删除的内容可能就有这类坎坷生活的记叙。现在公开面世的这个版本,全书的尾声一章《铁路会战之选兵》是个很有意味的存在。它虽然只有两千多字,却独立成章,通过记一件小事,反映的时代特色十分鲜明。本章集中出现的所谓“麻五类”“黑五类”“牛鬼蛇神”这些专有词汇,没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即使听过,但对这些词汇的专有含义也肯定不太了解。阅读本章,看得出作者很想参加民兵团去修建湘黔铁路,但由于其父是“牛鬼蛇神”尚未解放,所以他的名字上报后,还是被无情地剔除了。作者在写到这件事时,依然保持着之前不疾不徐的叙事口吻,好像去不去修铁路都无所谓。但结尾却来了这么一段:
十月的一天,小坪村大队参加铁路大会战的几个人都到大队革委会所在地土地坑集中。四个下乡知青,一个回乡知青和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工干三,每人背着一个背包,背包边还插着一把锄头。锄板子兜着背包底部,锄柄直指天空,乍一看,真像带着枪的一支小分队。五个知青无人送行,唯有干三,许林榜、覃义平带着两个姑娘来送行。临走时,覃义平把一个搪帕包着的东西挂在了干三的背包上,对他说:“这里头有二十个煮熟的鸡蛋,你路上和他们打伙吃。本想蒸点粑粑,这个天气又放不得。”说着眼泪流下来了。余主任见了,对覃义平说:“这么多人一起,饿不到他一个人,放心。”随即带着这六人到公社集中去了。看着几个知青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心中一片怅然……
《土地坑》结尾戛然而止的最后这句话十分含蓄内敛,对照全书三十多万字的写人叙事,我似乎可以触摸到作者当时内心的愁苦;这或许是我“同病相怜”的心态所致,因为数年后,我不仅也在距土地坑不远的土寨插队,而且也曾经历了一次类似“落选”的事——我想,这也可能也是我读《土地坑》特别有同感、很喜欢它的原因吧?阅读《土地坑》,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作者的创作境界非常高,在长达三十多万字的篇幅中,他没有陷入“私人叙事”的泥沼,而是着眼于一个村寨的“宏大叙事”,让读者在徐徐展开的一幅幅农村生产、生活画卷中,看到几十年前的中国农村最真实、最原始的生活场景,并因之而感慨、沉思。
可能有人会认为《土地坑》的记叙太琐碎了,事无巨细,什么都在写。不过,我的观点是,如果《土地坑》是一部小说,或者“纪实小说”之类,的确应该对书中的材料有所剪裁,有所取舍,并考虑一个合理的情节主线。但作者并不是在写小说,是在回忆往事;我把它当做一部“历史备忘录”来读,便感觉现在的写法非常好。这种事无巨细、记“流水账”的笔法,因为有小标题,使得全书既可以按顺序阅读,又可以让读者根据自身的兴趣随意翻阅跳读,实在是方便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我读此书甚至还有些遗憾,不过瘾,因为书中对有些事的记载和叙述似乎还有遗漏。不过我想,那可能是有意的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