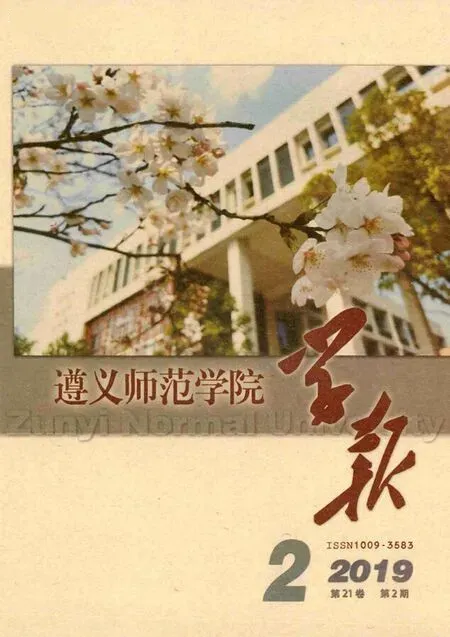托马斯·曼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黄兰花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是 20 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德语作家,其著作为现代德语小说、随笔等文学体裁树立了经典范式,影响深远,被视为歌德之后德语文学的代表。托马斯·曼成名甚早,第一部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不仅让他闻名遐迩,更是使其获得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力之作。之后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颇丰。与此相应,关于托马斯·曼本人及其作品的研究汗牛充栋、层见叠出,其曲折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德国思想史、社会政治相互映照。而在中国,自1928年章明生翻译托马斯·曼的小说集《意志的胜利》以来,对其的译介和研究也有90年之久。在这期间,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应地也影响到托马斯·曼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我们研究托马斯·曼在中国的接受史情况,可大致划分出三个不同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前(1928-1949);建国后三十年(1949-1978);改革开放四十年(1978-2018)来考察其译介和研究的情况。
一、新中国成立前(1928-1949)的托马斯·曼译介
新中国成立前,关于托马斯·曼的研究主要是译介相关的作品和个人资料,对其评价褒贬不一。自晚清洋务运动兴起之后,德国大批作家、诗人如歌德、海涅、尼采、雷马克等作为德国精神和文化的标志性人物被译介进国内学界。托马斯·曼亦是引介中的重要一员。据《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1915-1945)》所载280种期刊目录中统计,共刊载了22篇与托马斯·曼相关的文章,在当时引介的德语作家中排第六,前六位作家分别是歌德(79篇)、海涅(48篇)、尼采(41篇)、霍夫曼(38篇)、雷马克(26篇)。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在托马斯·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一年底(1928),上海启智书局出版的小说集《意志的胜利》也许是其作品在中国首译。该小说集收录了《滑稽的天才》《失望》《一个畸形人的惨败》和《意志的胜利》等四篇短篇小说,并附有一则简短的介绍:
这位作者……是位新古典主义者,现在还生存着。他的著作极富,最著名的是“主人与狗”“怪异的山嶽”“家族的衰落”“奇异的儿童”及这几篇短篇小说。单就这几篇小说而言,已经翻印九十余版了。[1]
上面提到的“怪异的山嶽”就是今译的《魔山》,而“家族的衰落”就是《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庭的没落》,“奇异的儿童”则为《神童》。不过,这本小说集反响平平,直到1929年11月,托马斯·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坛迅速回应,开始真正关注他。一方面快速报导托马斯·曼其人其作,比如1929年12月10日赵景深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托马斯·曼——一九二九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得主》一文,详细介绍了托马斯·曼的生平以及主要著作《布登布鲁克》《在威尼斯境内之死》以及《魔山》;另一方面加快译介步伐,翻译了《衣橱》(段白莼译)、《对镜——托马斯·曼的自传》(江思译)、《一次火车的遇险》(虚白译,1929)、《脱列思丹》(施蛰存译)、《神童》《到坟园之路》(段白莼译,1930)。诺贝尔文学奖引发的这股热潮,不久就因托马斯·曼对一战的态度冷却下来,相关的译介也变得沉寂。从1931到1936年,国内学界仅翻译《殴打》(段可情译,1936)和《托马斯·曼论日耳曼文学》(仲特译,1936)两部作品。其间,杨昌溪发表短文《托马斯·曼描写催眠术》(青年界,1931)、《托马斯曼素描及其德国文学的观察》(文艺月刊,1934),介绍他的创作以及“离开了言论不自由的德国”正在写作的《约瑟及其兄弟》。1933年,托马斯·曼迫于法西斯压力开始流亡。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他再度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1940年以后,国内又先后翻译了《壁橱》《幻灭》(欧阳竞译,1940)、《向墓地去的路上》(杜宣译,1941)、《爱人归来》(即绿蒂在魏玛,夏楚译,1941)、《诗人之恋》(张尚之译,1946)、《火车的失事》(薛生甡译,1948)。此外,《西洋文学》还翻译了托马斯·曼女儿的回忆文章《我们的父亲——托马斯·曼》,近距离了解托马斯·曼。同时还有多则短讯报导托马斯·曼的政治命运、身体状况、写作计划以及出版情况。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发现此阶段译介和研究托马斯·曼及作品,与其政治立场的变化紧密相关。如茅盾、徐霞村对托马斯·曼在一战中支持民族战争的态度大加批判,而又盛赞其在二战中的反法西斯立场,林语堂甚至将托马斯·曼称为“文化战士”,这与当时中国文坛的反法西斯立场不谋而合。总的来说,这段时期对托马斯·曼的译介和研究比较单薄,仅翻译了个别短篇小说,对其重要代表作只有零星介绍,相关的研究也多从政治立场出发,并不曾深入探究曼的创作和思想。
二、建国后三十年(1949―1978)的托马斯·曼研究
建国后托马斯·曼研究基本上延续了上一阶段的特征,仍集中在作品的译介和作家的研究上。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此间的托马斯·曼研究以1966年为界,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后17年”与“文化大革命”两个阶段。但是由于当时国内特殊的政治语境,60年代以后的托马斯·曼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苏联和新成立的民主德国将托马斯·曼树立为20世纪德语文学的代表,盛赞其为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在政治和文化上与苏联和民主德国保持一致的新中国,将其归入值得译介和借鉴的西方作家之列。尤其是从 1955年托马斯·曼逝世开始,中国译介多篇托马斯·曼作品,如《我的时代》《论契科夫》(纪琨译,1955),《托马斯·曼》(列昂·孚希万格著,一愚译,1956)。这个时期分量最重影响最大的托马斯·曼研究当属1962年傅惟慈译《布登勃洛克一家》以及附录的长篇序言。此书在各大运动的间隙中翻译而成,且译文水平极高,《魔山》译者杨武能就曾说:“在重译或复译成风的今天,至今没有人敢另起炉灶的念头。”[2]而附录的长篇序言亦是当时较深入的研究,序言中称托马斯·曼为“德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象编年史家一样,把资本主义社会各阶段的衰落腐朽现象记录在他的作品里”。作者接着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创作手法等方面解读《布登勃洛克一家》,将布家的堕落归结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3]P1-25此篇序言尽管带有很强烈的时代特征,比如特别关注小说中的金钱关系、资本主义的腐化等问题,但在当时已属难得的详细研究了。除了译介托马斯·曼的作品,也有少量研究出现,不过依然围绕着托马斯·曼的政治立场进行。其中,冯至称托马斯·曼为“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代表了德国悠久的人道主义的进步传统”。同时,他还揭示了“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对《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影响,不过对叔本华和尼采的影响避而不谈。另外,黄贤俊赞誉托马斯·曼为“德意志的光荣和荣誉”。而凌宜在其《托马斯·曼和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则批评其不该同情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没落,对1848年法国大革命的描写也“没有显示出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书中的工人形象不够典型等。[4]总而言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三十年间国内对托马斯·曼的理解和接受总体上看与这一时期中国浓厚的社会主义政治语境紧密相关。学界对托马斯·曼政治立场的关注明显多于作品,而且对作品的解读也是意识形态先行,注重挖掘其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多有忽略。
三、改革开放四十年(1978-2018)的托马斯·曼研究
1975年是托马斯·曼的百年诞辰,在德国各种庆典活动热情高涨。1977年之后,托马斯·曼的日记先后发表,为读者的解读提供了另一视阈。德语学界对托马斯·曼的研究一时层出不穷,相关研究突破了文学和美学的界限,延伸至政治、伦理、文化等多个方面。而在中国,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前困蹇的学术环境逐渐得到改善,国际化的学术交流也日益深入、频繁,托马斯·曼也重新引众人关注。80年代以后,国内对托马斯·曼的研究真正起步,相继出版了多部译著,开始出现一些文献基础相对扎实的评论文献。与前两个时期相比,此阶段的托马斯·曼研究在量和质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呈现出研究范围广、研究角度多元化以及研究内容深入等特点。
在这40年中,托马斯·曼的翻译有了新发展,其主要的长篇小说、全部短篇小说,重要散文集也相继推出。《魔山》《死于威尼斯》等都有多个译本。为新时期国内托马斯·曼研究提供了重要研究资料。而在研究方面,80年代的托马斯·曼研究基本停留在阐发“托马斯·曼是批判现实主义者”的命题上,更多强调其著作的阶级代表性。例如,在孙坤荣和孙凤城合写的论文《托马斯·曼和他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中,从小说文本挖掘出大量社会批判的材料,梳理了小说对金钱化的人际关系以及对封建贵族、基督教会和德意志教育制度的批判,同时该文作者也对小说所暴露的错误认识(对1848年革命“不真实”的描写)和颓废态度(“宿命论”)进行了批评。而在董象和诸燮清合写的《论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论文中,也认为此小说“反映了历史长河的流逝和流向——支配资本财富德人们被资本财富所支配,资产阶级一批批地将自己变成历史废料。”[5]除此之外,还有《魔山》“写的是处于低谷时期的资产阶级,作者以深刻的洞察力和无情的笔触,不仅从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方面,而且从它的精神生活方面揭示出这个阶级确实不配有更好的历史命运”;《浮士德博士》的伟大在于“揭示了帝国主义时期毁灭人性、毁灭艺术的反动本质”等论调。
除了从社会批判这个角度来研究托马斯·曼,国内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托马斯·曼作品中的思想、文化,转从现代文学的表现手法、作品的哲理内容进行分析。譬如,舒昌善在其《略论托马斯·曼的现实主义》一文中就提请读者关注托马斯·曼作品中的现代派表现手法:象征、隐喻、意识流、非情节化等等。而刁承俊在其《叔本华、尼采与<布登勃洛克一家>》中阐述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和尼采的没落心理”决定了《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批判内容;张佩芬在《托马斯·曼和黑塞——略论20世纪艺术家小说的思想先驱问题》中也谈到托马斯·曼的哲学渊源,认为黑塞和托马斯·曼这对“精神兄弟”的艺术家小说的核心主题是“思想先驱性”,而这都与尼采息息相关。金惠敏在其《意志与超越―叔本华美学思想研究》中有专章讨论叔本华美学思想对托马斯·曼的影响。
进入90年代,托马斯·曼的研究呈现出多元深化的趋势。根据研究内容的侧重点可分为作品的文学性研究、美学思想研究、比较和接受研究。
第一类,作品的文学性研究。托马斯·曼以意义深邃、富有探索性的小说创作著称,其小说往往杂糅了他关于文化艺术、政治哲学、社会伦理丰富而深刻的思考,且他擅长博采众长,使得其作品包罗万象。因此,国内学者对托马斯·曼作品的解读从原先单一的社会历史批判转变为多元视角的切入,从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探究托马斯·曼及其作品的诗学、哲学、美学和文化等思想观念。
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托马斯·曼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其批判资本主义,宣扬人道主义的立场,论述对象也多集中于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死于威尼斯》《魔山》几个作品。代表性的论文有黄燎宇的《进化的挽歌和颂歌——评<布登勃洛克一家>》,探究托马斯·曼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杨武能的《<魔山>初探》《我译<魔山>二十年》《<魔山>:一个阶级的没落》,文章中作者高度称赞《魔山》,称它是“德语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率先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结合起来的典范”。[6]此外在其《<魔山>:一个阶级的没落》一文中对《魔山》的社会意义进行研究,文章中杨武能将《魔山》视为《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后续之作,象征着欧洲战前代表自由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没落;而叶廷芳的《<魔山>的魔力在哪里》中,分析了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哲理内涵以及作为教育小说的“现代品种”的特征。
90年代后期开始,对托马斯·曼作品和主题有了更广泛和深入的分析。比如,《浮士德博士》进入研究视野。邵思婵认为小说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和“帝国主义时代所有的反动倾向”,杨宏芹围绕“恶魔性”进行阐述,探讨了“恶魔性”的概念、生成背景及其对艺术创作的意义——“恶魔性”已成为西方现代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最大内在驱动力和克服文化危机的手段,而且通过分析小说中的两部虚构的音乐作品如何体现并超越“恶魔性”揭示了托马斯·曼对“恶魔性”的复杂态度。[7]研究角度也更多样,比如张杰的《托马斯·曼的精神故乡:吕贝克》,从城市文学角度入手,讨论城市与市民性格的关系,揭示托马斯·曼独特的文学气质。
在研究主题上,研究者也另辟蹊径,从艺术家、疾病主题、宗教神话、同性恋等不同主题切入。其中艺术家主题研究,重点关注曼托马斯·笔下艺术家与生活、艺术之间的矛盾。这方面用力最多的是对《死于威尼斯》的研究。对《死于威尼斯》的解读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一是阿申巴赫和他钟情的小男孩的原型及电影改编的研究;另一个是探讨艺术家的生存方式,如张弘的《艺术审美的危机——评<死于威尼斯>的艺术家主题》;再一个就是探讨小说的艺术风格,如李昌珂围绕“新古典主义”和“神话”,阐述了托马斯·曼的神话观、文本中神话意象及其关联。[8]除了《死于威尼斯》,研究者们对托马斯·曼其他小说中的艺术家主题也加以重视。如黄燎宇认为,《特里斯坦》和《托里奥·克勒格尔》揭示了艺术家存在的特殊性、优越性、可疑性;《布登勃洛克一家》所刻画的不孝子与叔本华的天才论相映成趣,家族的没落与艺术天才的诞生互为因果,所以这部小说既是挽歌也是颂歌;[9]李茂增结合西欧审美主义的流变,对托马斯·曼早期艺术家三部曲《托尼奥·克勒格尔》、《特里斯坦》和《死于威尼斯》进行重新解读;[9]另外,张佩芬、徐烨也在各自的文章中集中讨论了“美与死”的审美题材和现代社会的审美危机。
疾病和死亡是托马斯·曼作品中极为重要的两个元素。在他看来,疾病和死亡与人性、智性和人的尊严紧密相关。因此对托马斯·曼笔下的疾病和死亡的解读,也成了研究的一个关注热点。如方维规的《“病是精神”或“精神是病”——托马斯·曼论艺术与疾病和死亡的关系》中称,在托马斯·曼的“病的哲学”中,“疾病是一种升华生活、超越现实、提高个性品格和认识能力的状态,是走向更高级的精神健康的起始,托马斯·曼对疾病和死亡的兴趣,是其珍视生命的表现。”[10]涂险峰和黄艳则从《魔山》中的“风景体验”与疾病、死亡和时间问题相联系,探讨其中所面临的“存在”之深渊和精神冲突,分析萦绕魔山之上的各种当代思潮,建构起反讽的“疾病诗学”,实现了从“疾病浪漫化”转向“浪漫疾病化”的现代转型,并展现了欧洲思想喧嚣失序和实验主义价值缺失的现代“疾病”景观。[11]此外还有《布登勃洛克一家:托马斯·曼对德国社会的“病理分析”》,作者通过梳理布家四代人不同的人生际遇,来看疾病的隐喻,进而探讨艺术与疾病、商业社会的关系,以及疾病美学背后的疯狂与虚无,挖掘托马斯·曼对德国“社会病”的独特思考。[12]
宗教神话主题也是国内学界研究托马斯·曼的一个重点。如王莹的《神话与隐喻:<死于威尼斯>的“死亡”隐喻探析》、刘宏的《试析托马斯·曼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基督教因素》等文章探讨托马斯·曼中的神话和宗教主题。
考辨人物形象的论文多以托马斯·曼笔下的艺术家为题,前已梳理,此不赘述。除了艺术家的形象分析,对托马斯·曼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形象颇感兴趣。这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有《“我这个时代”的德国——托马斯·曼长篇小说论析》,作者李昌珂在书中对托马斯·曼主要的长篇小说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评述,作者立足于中国探讨者的眼光,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结合时代、历史、社会以及作家的生活经历、创作意识、文学思想、他人影响等因素,对托马斯·曼的精神内涵、文学价值作一个多纬度的观察和探索,其中对满小说中的各色人物有详细的论述。
第二类,美学思想研究。托马斯·曼著作中的美学思想和内涵也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如贾峰昌的《浪漫主义艺术传统与托马斯·曼》,作者围绕托马斯·曼作为浪漫主义继承者的身份,从“浪漫主义”的意义入手,梳理托马斯·曼对这一思潮的接受和影响,进而探讨托马斯·曼的美学观、文化观及其小说视觉性,探索阅读经典小说的新视角并说明“浪漫主义”思潮的永恒性与发展。[13]而方维规在其《20世纪德国文学思想论稿》中有专章探究托马斯·曼的美学思想,文中作者通过解读唯美主义者托马斯·曼的文学人生,阐发了文学与人性之间的隐秘关系,强调托马斯·曼以“人性论”为美学思考基础。[10]
此外,刘忠晖的博士论文《从“眷注死亡”到“敬奉生命“——托马斯·曼的艺术与文化思想研究》,以浪漫主义——保守主义——人文主义这一思想发展主线,从文论家托马斯·曼的艺术和文化政治思想发展和转变入手,在时代和思想的视域下考察托马斯·曼,力图展现他从一个“眷注死亡”的浪漫主义者变为“敬奉生命”的人文主义者的历程,讨论托马斯·曼的文化意识和政治诉求。[14]
黄金城的《论托马斯·曼的反讽概念》则强调反讽是托马斯·曼一以贯之的文学―政治姿态。其反讽观念和内涵伴随德国现代思想史的进程从尼采式的、到席勒式的、再到浪漫式的,最后认同于歌德的不断调整和改变,具有了客观性与人文主义的内涵。[15]其他的论文还有顾梅珑的《<魔山>与托马斯·曼的审美主义思想》,聚焦于小说中所呈现德疾病、死亡和虚无主义,以及感性和理性的关系,认为托马斯·曼尝试用爱和艺术来化解矛盾,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情怀;王炎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时间观”来分析《魔山》,在他的《小说的时间性与现代性——欧洲成长教育小说叙事的时间性研究》有专门的章节论述,认为“托马斯的时间观是对存在的领悟”;[16]谷裕《由<魔山>看托马斯·曼对保守主义的回应》认为,《魔山》隐含的保守主义思想与20世纪初的保守主义相互应和,体现了作者的审美冲动与人道关怀的张力。[17]
第三类,比较和接受研究。比较研究主要分为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平行研究多聚焦于托马斯·曼与其他作家——乔伊斯、黑塞——的比较,如张月亭的《真与美:詹姆斯·乔伊斯与托马斯·曼艺术观的比较》、吴勇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棱镜中的托马斯·曼和黑塞》等。也有两部作品的平行比较,如莫光华的《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贾宝玉和汉诺悲剧人生之比较》。影响研究既有其他人对托马斯·曼的影响,如,卫茂平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分析,认为《魔山》中论述的亚洲和东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中国”,批评了托马斯·曼这种“面对东方文化的大举近侵”的主张;[18]也有托马斯·曼对他人的影响,如赵佳舒和唐新艳将《魔山》与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做影响研究,从创作主题、象征意义、创作基调以及人物情感方面阐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谷裕以德国成长小说的传统来关照创作于20世纪的现代作品《魔山》,在其专著《德国修养小说研究》中有专章进行论述,其中探讨了在现代语境中,托马斯·曼以20世纪的思维范式以及所关注的问题为导向,颠覆了传统的教养小说模式,表达他对人性的探讨和对人道的追求。
对托马斯·曼的接受研究主要有两个。其一,在《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中,作者卫茂平爬梳了1928至1940年国内学界对托马斯·曼的译介史;[19]另一个则是黄燎宇的《60年代以来中国的托马斯·曼》,当中梳理了建国60年中国托马斯·曼研究状况以及不足之处。[20]
四、研究中的不足及展望
托马斯·曼进入中国视野已有90年,相关的研究层出不穷,但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研究结构不合理。从研究对象而言,存在厚此薄彼的状况:研究早期小说的多且集中于几部小说的解读(尤以《魔山》为最),研究托马斯·曼其他小说的少;研究其虚构作品的多,研究非虚构作品的少。托马斯·曼后期小说《浮士德博士》《约瑟夫兄弟》《绿蒂在魏玛》等都是其代表作,很有研究价值,国内却少有人关注。而且对托马斯·曼的文论、文化随笔、政论等翻译和研究都严重滞后。托马斯·曼一生撰写了大量散文、书信,且这些非虚构作品绝不是无足轻重的闲来之笔,而是一个博大精深、五彩缤纷的精神世界。研究这些作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小说,他的人生和他的时代。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见。
第二,内化挖掘不深。从托马斯·曼相关研究论文的主题分布来看,国内学者多扎堆研究其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和社会背景分析,相比之下,对托马斯·曼本人及其作品的美学思想、哲学观念以及精神内涵等方面的研究既不多也不够深入。然而,我们知道,托马斯·曼的小说以复杂深刻的哲学思辨、广博高深的思想论争闻名,如果仅停留在对其作品表面的文学性阐释,难免浮于表面,不可能深入全面地把握托马斯·曼作品中的精髓。
第三,研究质量不高。进入新世纪以来,对托马斯·曼及其作品相关研究确实增多,各种主题和方向的研究论文层出不穷。但是,研究论文量的提升并没有带来质的飞跃,在这些研究中存在着内容重复、材料单一、论证粗燥的问题。纵览这些研究,我们发现有些论文或大放阙词,无的放矢,或理论观念先行,生搬硬套,或画地为牢,视野狭小。
托马斯·曼作为歌德之后德语文学的代表,其作品及思想理应常读常新,因此,新时代中国对托马斯·曼的研究应当打破僵局,立足文本和历史文献的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发掘其思想深度。首先,我们对托马斯·曼的研究不仅只囿于他的文学著作,还应该更多的关注他大量的论文、随笔和书信等非虚构的作品,将托马斯·曼在这些非虚构作品的思想观念和时代书写融合到文学作品的研究当中,更加全面和立体地理解托马斯·曼。再者,我们不能僵化地定义托马斯·曼。诚然,托马斯·曼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但同时他还是一个文论家、思想家、政治家,因此我们应该不拘一格,从文学、哲学、美学、文化、政治等方面跨专业、跨语种、跨学科进行研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当前国内托马斯·曼相关的翻译仍有巨大的空白,缺乏直接的一手研究资料,因此需要更多专业的、优秀的译者加入,翻译更多更好的作品为研究者提供灵感和材料。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为这位伟大的作家及其作品开辟出新的解读空间,带来新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