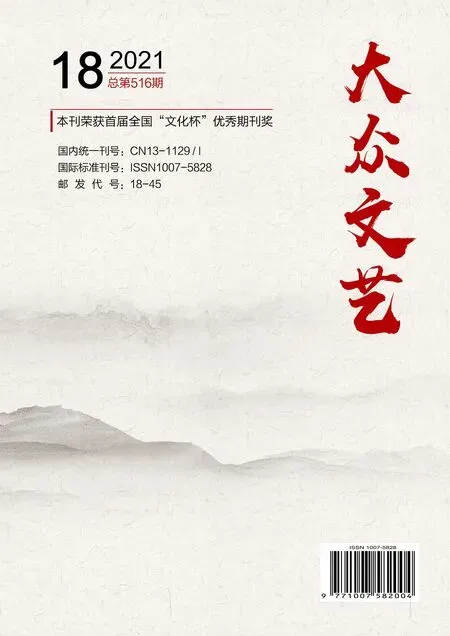是道德标准还是求知标准
——对“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再议
(贵州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550025)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论语》中的著名命题,常被用为一种道德标准,为“诚信”概念的延伸,如杨伯峻的解释:“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聪明智慧”,但钱穆、李泽厚等人认为此命题涉及认识论的层面,故本文对此命题展开进一步阐释。
一、对原命题的反思
如将原命题定义为道德标准是否具有普遍性?按照杨伯峻的解释可将原命题理解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关键在于如何确定“是”?即“知道”这个概念是难以被界定的。这由于“知”的载体是人,人对于自己是否知道是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也就说人对于自己是否知道是模糊的。《集注》认为此命题的是告诫“强不知以为知”的子路,以显不自欺之义。但子路“强为知”的表现又有两种可能,一是子路执着地认为他“所不知”的是他“所知”的;二是子路无法分清何为知、何为不知,前一种可能可以延伸出原命题是一种道德标准,但按照后一种可能,对道德标准的单纯设定反而会造成道德实践中的矛盾出现,即不知何为“所知”与需要依“所知”而行的矛盾。因此把原命题单纯指向道德标准时,则有陷入主观臆断的危机。
那么原命题是否具有认知层面的意义?对原命题中的“不知”概念进行进一步分析,此“不”字显然是对“知”的否定,同时也是对“知”的否定的认识,恰恰说明了人的认知能力具有评判功能、分别功能。如果“不”字是对整个认知功能的否定,则应为不“知之”,即是完全否定,那么知作为一个过程,必有能知和所知,那么不“知之”便是仅能谈论自己能“知之”的(包括能知自己“知之”和能知自己“不知”),对于不能知的,则概不讨论,似乎是一种唯经验论,孔子显然有这种倾向,如:“未知生,焉知死”,即是超验之事持规避态度,但在孔子又说:“五十而知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显然孔子认为超验的“天命”与经验世界的人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且人具有知天的能力,需对此“天命”进行体认。由此观之,原命题中具有涉及认知层面的可能。
综上,单纯将原命题指向道德标准缺乏一定普遍性,但其中亦包含了认知层面的思想,故而对原命题以及其中“知”与“不知”的解释都是需进一步探讨的,为了避免独断论的倾向,下文从古代对原命题的诠释与现实对原命题的诠释入手,对其进行一定的总结。
二、对原命题的释义
(一)命题在古代的训释
知为“志”。在《论语集释》中有此说的论证,首先在《群经平议》提出最后一个“知”应被读作志。在《礼记缁衣篇》中有论证:“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述而志也”,郑注说:“志,犹知也。”以此证明知与志意思应该相通,那孔子之义便是告诉子路何是“志之”。由此推出此命题便是对“志”的论证,且《荀子•子道篇》、《韩诗外传》都有“知”为“志”的论证。
知为“智”。总结下来“智”字训释中有两种解释,一智慧:此说依据《荀子•子道篇》:“知”或“不知”是“言之要”;“能”或“不能”是“行之至”,因此“言要”将为“知”;“行要”将为“仁”,所以此处应是“能”与“知”相对;“仁”与“智”相对,因此此处命题中“知”为“智”;《论语集释》另引《礼记•曲礼》中对于存疑的事不可成言进行论证,依《礼记》注与疏的解释,认为如将疑事成言则会伤害“己智”。因此“知”为“智”。二“本心智”:依黄干《论语注义问答通释》所论,此“知”是“心智之端”在是是非非上的功用,对是是非非的体认,即是非之心,孟子认为其是“四心”之一,因此此心智为本心所发,乃“心之虚明,是非昭著”。
知为“知”。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为:虽未尽知,亦未影响认知,如此为能知之理。由此朱熹认为“知”应是知道、认知之义。《四书发明》中认为学会求知才是“知之”之道,此与朱熹意同。《论语意原》认为此知非普通见闻之知,是对“道”认知。《四书反身录》则认为,子路未明之处便是只认识见闻之知,未识自性本有之知,此为“本性知”。
综上所述,对命题“是知之”的结论可分为三种:1.道德标准;2.道德判断的能力;3.认知“道”的能力,其中后两种都是在认知层面来进行说明。
(二)命题在现代的理解
作为道德标准的理解。此类大多与杨伯峻在《论语译注》所阐释的相似,故不详谈。
作为认知层面的理解。李泽厚引陈栎《四书发明》:“强不知以为知,非惟人不我告,己亦不复求知”展开论述,认为此句是在讨论求知的态度,即是“实用理性的落实”,便是承认人的有限性,唯有通过一定积累,才能由有限转向无限,“认同自己的有限性,才可能超脱;认识自己不知,才可以知”,即为个体自我的内在完善。
钱穆则首先提出人既然有所知,必然会有所不知,但所知和所不知的界限是难辨的,而知与不知即是孔子对于人类知道的能力的定义,这里有两个结论,第一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局限的,第二人并没有对所知与所不知之间有清晰的界定或判断。因此钱穆认为孔子此句“亦孔子教人求知一亲切之指示。”也就是在求知的过程中,需要分辨清楚什么是知、不知及界限。
其次钱穆此段对什么是知,什么是不知有一讨论。认为人对于知和不知的认识是有顺序的,“人类必先有所知,乃始知其有不知”,人们常对“未知之”以“未知之者”进行定义,自以为达到对“未知之”的认知,这就是以“不知”为“知”。
杨国荣则认为对“不知”这种状态的认识本就是一种知。他特别强调“知”和“不知”非对立,应是统一,因为对“不知”的认识,便为求知过程的开始,结合钱穆的思路可得一次第过程,即人必先有知,才知道有所不知,那么正是“知”自己“不知”,这才是真正求知的开始,故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叩其两端即是求知的过程,钱穆更进一步谈此过程为“学日进,心日虚”,这是由于求知之后必然有所得,有一“知”后必又有一“无知”,因此这个求知的过程实际是知“无知”的过程;但反过来说,如认为自己有“知”必不会去“求知”,但显然认为自己的有“知”实际是混淆了知和不知,或是假认“不知”为知。
综上所述,可得四点结论:1.原命题揭示了人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或有限性。2.人无法对所知和所不知的事有清晰的认识,因此需对“知、不知、界限分辨明确。3.人有不知是由于其先有所知。4.人对知的真正认识是由无知开始,而无知贯穿于整个求知过程,故应是知“无知”的过程。
三、对命题的再解释
(一)知之与不知
从上述结论中可得,人之不知是因先有知,因此“知之”应是“不知”的前提,而唯有通过“不知”才能达到一个新“知”,此新知已与原来的“知之”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应就是同无限性距离的差别。每一次“不知”的过程都是对“知之”的否定,即是对现有认识的破除,并依此破除而去建立“新知”。从这个层面来说,“知之”与“不知”并不能单独看待,单独理解则会出现“知之”的主观化,应共同组成一个从有限性达到无限性的过程,即破执立新的过程。因此知之是为了对“无知”的认识,而“无知”则求新“知之”的开始,是不断求知的过程。
对于“知之”和“不知”是能知还是所知这一问题,张学贤按照句法结构来分析,认为此命题属于主宾同语,“前一个‘知之’‘不知’指客观事实,后一个‘知之’‘不知’指主观认识。”。对命题的解释应为所“知之”(主体)已知之,而所“不知”(主体)还不知(即知“不知”),不知则需求知,如此循环,则称为“知”,故此过程乃一动态的过程,追求认知“无限性”的过程。
(二)是知也与循环求知
“是知也”此句是对“知”“不知”过程的一个总结或结论,经过上述的论证,“知”“不知”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求知过程,“知之”和“不知”一直相互作用,追求着无限性。但对此结论还需依据古训来佐证,故依古训分别进行讨论。
按照上节对“知”、“不知”过程的论述,如将此过程的定义解释为“志”,即应这样向往之。虽大意解释上较通顺,但“志”字在《论语》中更是指一种倾向性,如:“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但孔子认为“志”的倾向性更应向“仁”上用功“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因此应不是此字。
虽然“智”常会被简写为“知”,但在《论语》中字义为“知”和“智”的语句有一定差别。《论语》常有“知者”这一概念,此“知”认为是别人所具有的一种境界或能力,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孔子对“知者”的能力或境界的描述则是“不惑”,按《说文解字》来看,“智,识词也”,而“知,词也”,因此智是能够识何谓“词”的能力,也就是对于“词”则有“不惑”的能力,故“知者”之“知”应为“智义”。而在“ 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中可以发现,孔子分君子有三道,其中一道即为“知者”,由上可知应为“智者”,而孔子所述的“道者三,我无能”则与原命题中的“知”、“不知”思维模式一致,即为知“道者三”,而知“无能”(无知),所蕴含义即是对此三道的认知的超越,不过并不是说“仁”、“知(智)”、“勇”三者是有限的,应是对其的认知和定义是有限的,也因此子贡认为孔子行为才是道。也就是说真正的道并非为有所谓标准的道,而唯有“无能之道”才是真道,故也只有建立在“无知”上的“知”才是真知,也就说对有限性的否定则是对其无限性的开启。
孔子的“是知也”注重突出对“知之”的超越,和对“不知”的认可,这种超越和认可是同时且连续进行的,但实际上这种认可也是需要超越的,这种思想贯穿于孔子的仁学思想之中,他强调“不知仁”:
“不知其仁,焉用佞?”
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子曰:“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但孔子又认为“仁”是可被知的,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因此所谓不知“仁”也就是对“知之”仁的否定,目的在于对真“仁”的确定(即无限性的达到)。因此“是知也”之“知”应是对“知之为知之”和“不知为不知”的总结,应将两个概念都包含在其中,此“知”包括了能知、所知,故此“知”应为无分别体;又含摄了“知之”、“不知”,故此“知”又为有分别用。因此将“知”理解为本性之体的妙用,呈现为“知”与“不知”的相互超越的过程。故而原命题实际体现了孔子对求知标准的设定。
孔子“知之为知之”的命题不仅是单纯的道德标准,更体现出一定的求知标准,在孔子看来真正的“知”需要在这种相互超越的过程中呈现,以此来保证“知”的准确性或真实性,避免了蒙蔽、独断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