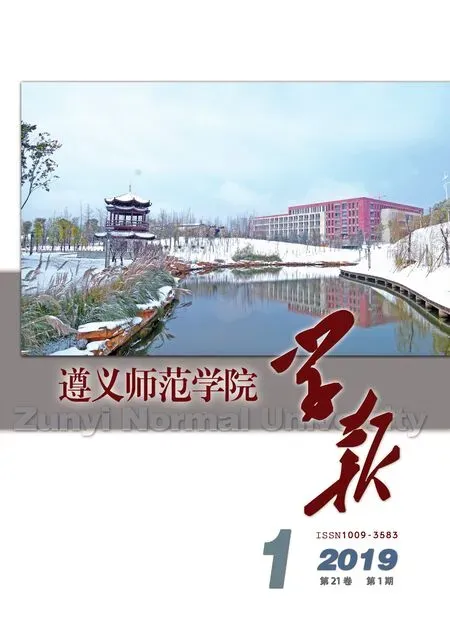游离于理想与现实之间
——论冉正万长篇小说《洗骨记》
李丹丹,肖太云
(长江师范学院重庆当代作家研究中心,重庆涪陵408100)
新时期以来,贵州本土作家的写作在不断崛起,其中冉正万尤为耀眼。他以勤勉的创作态度和灵性十足的创作手法,凭借对文学终极意义的追求,对文学诗性的坚守,书写出许多优秀的作品。他的短篇《飞鼠》《连环套》《飞机》,中篇《乡村生活》《奔命》《露草珠花》等都深受读者喜爱。同时他的长篇小说《银来鱼》《纸坊》《洗骨记》等作品也以很强的可读性而颇受读者欢迎。其中,《洗骨记》是冉正万对人的生存困境的理性思考、对人的诗意存在的理想表达,具有人文情怀的一部力作。
弗洛伊德认为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冉正万用他手中的笔书写他心中的梦。《洗骨记》是冉正万的一个梦境,在这一飘渺的梦境中,折射着作者对现实痛苦与无奈的思考,也有他梦境中的驰骋想象。梦中交织裹挟着现实与理想的不断冲突,冲突过程中夹杂着失落与无力。但作品并不仅仅只是揭露生活赋予的伤痕,更多的是表现在无限挣扎的睡梦中正视伤痛,以及治愈伤痛的力量,并抚慰更多的人。
一、现实的疼痛及理想的人性
小说主人公马也生活在贵州的闭塞山村——甲定。小说讲述了地质队子弟马也从高中时代到而立之年的故事,讲述了马也以及与之有关的曾萝卜、高元果果、李元强几个年轻人面对青春的不安与困惑。在封闭大山里有一股蠢蠢欲动的力量——有关于爱情、未来以及人生,这种与生俱来的向往牵引着他们,但在这种蓄势待发的前行中,却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冉正万在揭露现实的同时也有对理想人性的向往:生活只能压垮身体,但压不垮精神。马也身上既有对现实生活的无所适从,也有对理想人性的勇敢向往。冉正万在马也身上注入了自己的独特思考:人的一生,被投掷于土地上,不得不面对生活的苦难与折磨,但人并不能被人生之不幸所吓倒或击垮。冉正万通过马也鼓励人们面对痛苦时不忘微笑,在感到困顿时不忘记还要继续出发,在迷惑时不要停止找寻。
(一)现实的疼痛
《洗骨记》揭示了黔北农村青年人的生存状貌。小说采用双重角度叙事,情节上多呈递进关系,以马也成长历程为线索。叙述过程中直面生存的尴尬与无奈。冉正万站在故事之外,冷静地讲述了个体面对亲情、爱情、乡土时的无助,为读者展现了黔北农村青年人孤独、压抑的生活境况。
1.失落的亲情
家庭是个体最具归属感的地方之一,然而在作品中,家仅仅做为一个名词存在于马也的脑海之中,不幸的家庭环境注定了马也敏感的人生。家的天伦之乐对马也来说只存在于他午夜梦回时的猜想,这份猜想带给他的是对生活的不解。在马也四岁以前,他拥有完整的家庭,但冉正万却含蓄地向读者表示这并不是一个温馨家庭。远离物流横欲的贵州山村,马也父亲的爱情留不住妻子,在马也来不及对家庭有清晰记忆的年龄,母亲就带着姐姐离开。作品中在马也第一次带着对华华老师的幻想,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手淫后便打开记忆的闸门,重现抛弃他的亲人。他说:“我四岁过后就没有再看到过她们,她们的长相我就记不得了,平时也很少想起她们,今晚上突然想起来,大慨她们都是女人的缘故吧。”[1]P15母爱对马也来说是一种不明确的印象,不需要被记得,更不需要被刻意地遗忘。马也只是在面对华华老师时,在面对翠青蛇时,联想到了在他思想之河里越来越远的母亲和姐姐,但她们终会被记忆的长河洗刷得无影无踪。
虽然缺少母爱的马也会有父爱的弥补,但马也注定不能拥有来自父母的温馨体验。马也三年级之前和父亲一起生活在磨沟汞矿上,然后转到砂子哨磷矿,到上中学的时候搬去甲定。现实生活总是伴随着未知事件的发生而出现意外,马也只能在无力承受的年龄承担生活的意外——甲定的溶洞无情地吞噬了父亲。先是母亲的遗弃,再是父亲的失踪,马也成了一个弃儿。这样的童年经历造成了他孤僻敏感的性格。
2.阵痛的爱情
爱情是成长过程中的一大主题之一。在小说开篇处冉正万以马也的口吻说:“她来甲定那天,天空飘着白云。”[1]P1在马也、高元果果、曾萝卜、李元强无忧无虑嬉笑玩乐中,华华老师来到这个长期与世隔绝的地方——甲定。作者以蘑菇腐烂的香味释放在空气中为读者暗示主人公心理的转变。一成不变的生活让甲定像一潭静谧的死水,但平静的表面下在酝酿着波涛。马也说:“在无忧无虑当中,我常常感到一种莫名奇妙的不安,好像有什么是要等我去完成,也好像什么东西在被不知不觉中失去。”[1]P1青春的压抑与躁动,华华的到来让平静无聊的生活掀起波澜。山路崎岖的黔北迎来身穿白色连衣裙提红色皮箱的华华,当圣洁与火热向马也袭来时,他孤僻敏感的性格让他不知所措。在神圣的未知躁动面前,一群青年感到蠢笨、惭愧和怯懦。马也内心激动,身体却不动声色在松林深处窥探着一切,内心洋溢着兴奋与激情,但又被懦弱打败。马也说:“我感到全身不舒服,手脚肿胀,脑子迟钝,有种压抑感。”[1]P3对华华无限地向往同时又不自觉地感到自卑。漂亮的华华成为马也的语文老师,作为马也心中美好的圣洁化身,马也用尽全力维护她,在和伙伴们玩笑时不准以华华老师为调侃对象,阻止朋友对她的一切幻想。这种隐秘的情感让马也感到更加美好,他时刻幻想着华华注视着他所做的一切,他勇敢地在河里游泳以憋气的时间长短来寻求自信,让自己不再是他人眼里的“恶棍”“刀头儿”,同时他不受控制地对华华产生性幻想。在全情投入的阅读体验中,冉正万表现的生命情态描写不容读者多想,纯粹的生命力让我们合理接受作者笔下虚拟的激情。华华成为马也的精神引领,他开始认真听课,努力学习,在华华的鼓励下尝试画猫以及人体绘画,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幻想。但华华与马也的情感注定是一场回忆,初遇时华华已为人妻,她是马也的情感寄托,唤醒了马也灵魂深处的东西,却也因中途停止而加深了马也的痛苦。马也顺利考上大学后,华华老师离他而去。一段青春幻想在懦弱、自私、怀疑、散漫中随岁月逝去。
冉正万笔下的马也逃不过“贪”“嗔”“痴”。被欲望与胆怯笼罩的马也与华华的爱情是一个令人惋惜的梦境,而马也却执着于这虚无缥缈的梦境中,近乎以一生的幸福为代价。在马也回到甲定后,拼命寻找华华。余下的岁月也一样,寻遍华华的老家和华华曾说过的谋生之地,最后托朋友打听她的下落。华华是马也心口的伤,为着那些不可琢磨的瞬间,马也固执地为她奔跑。他认为她在哪里,终点就在哪里。这是种近乎偏执地寻找,马也在看到与“华”有关的文字,就会舔舐自己内心的伤口。他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他深入骨髓的恋人。马也注定不能获取家庭的幸福,他与妻子黄月欣的婚姻没有美满,妻子性情暴躁、世俗、聒噪,她无法引领马也的精神,也无法拉他离开暗河。他们在争吵与暴力中分道扬镳,马也中年承受的家庭分裂的痛楚,失去与女儿的亲情,无处安放的爱情也让马也的世界多了一份伤感与忧愁。马也无法挣脱命运的无情,这是冉正万的思考:人如何追求温暖以及精神的美好寄托。
3.变迁的乡土
马也的成长也伴随着环境的变迁而改变。家在贵州的山村,但他从小不断迁移,三年级之前生活在磨沟汞矿,之后生活在砂子哨磷矿,中学时代生活在甲定,大学生活在遵义。与世隔绝的黔北甲定是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所,也是马也心灵的故土所在。在马也记忆里甲定虽然地理位置偏远,但环境优美。在冉正万的诗意描写下,甲定充满鸟语花香,马也和曾萝卜、李元强等的乐趣是在松树林里抓松鼠,在路边为华华老师摘取美丽的花朵,人和自然一派和谐的景象。但是宁静环境却孕育着不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值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大力发展经济,市场经济加速了中国向现代化进程的迈进。矿产资源丰富的黔北没能落下工业发展的队伍,甲定开始进驻地质队,无数的地质工人扎根于此,展开采矿大业。马也和其他人也相继迁入这个环境艰苦的地方,长期与世隔绝,在这种集体苦闷的生存环境中增添了马也的痛苦。环境的影响并不只是如此,其中有冉正万对现代化的反思。矿场卷走了马也的父亲马晓元,同样也带走了华华丈夫夏维凡的生命。马晓元和华华两个与马也生命息息相关的人同时发生意外,增添了马也生命中的悲剧与不幸。冉正万以文学的方式沉思,在社会不断进步的时候,经济发展需要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工业发展需要无数个体的生命祭奠。在这祭奠过程中,人性中隐藏和克制的阴暗面不断地被激发:人与人的冷漠、个体的欲望、自私、偏激、软弱、自卫等。社会环境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冲击着马也的心灵。当中年马也回到故乡时,他看到的景象是“我们采过蘑菇的松林,现在一颗树也没有了。李元强搬到旧盘去了,夏维凡的坟墓也不见了。”[1]P192马也说:“哪怕整个甲定从地球上挖掉,那也是我们梦回萦绕的地方。”[1]P193故乡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给马也增添伤感。
(二)理想的人性
史铁生认为人的灵魂应该在现实的苦难中得到升华。虽然生命的历程无法拒绝不如意的现实,但应勇于面对生活的不如意,以自身的努力化解痛苦,更要在这一过程中矢志不渝地保持希翼,有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海德格尔说:“人的个体性存在,既在时间之内又在时间之外,因为时间的流动,会导致人的变化,但唯一恒定的是人自身的诗意生存状态。”[2]面对苦难,作者寄予了美好的幻想,即是对马也理想人性的书写。
1.诗意的寻找
生命因为遗憾而增添另外一种美,马也自幼缺爱,在看不到温情的世界里,但他并没有采取游戏人间、消极逃避的态度。尽管在隐秘的哀伤下有对生活的失落感,但他一直努力寻求平静而有所寄托的内心,所以小说中产生了一系列马也情感寄托的对象。蛇作为独特寓意的形象引领马也寻觅理想的自我。马晓元离开两年后出现了一条蛇,马也认定它是自己父亲所变,赋予蛇独特的意义。冉正万以一种对神秘隐晦事物的钟爱,展示个体是如何面对缺失的不幸。在马也生命中突然离场的马晓元,把马也推向孤立无援的境地,他希望父亲仅仅是消失了,而不是命丧暗河。马也固执地把对父亲的情感转移到蛇身上,斟酌着对蛇的合理称呼。
冉正万对猫有一种独特的认知,从处女作《苍老的指甲和宵遁的猫》到《洗骨记》,都表现出对猫的喜爱。猫是在马也一种孤独的寄托和对爱的渴望。从小到大他一直保持着对猫的喜爱,在自己养的猫死亡后,华华老师送给他一只猫,他一直爱不释手。冉正万给了我们解释,他说猫和马也有相似之处,在黑夜中瞪大着眼在守望。马也自幼孤僻,少言寡语,小时候无法正常融入人群中,排斥新的人群,成年后虽如愿当上画家,但同事关系同样让他压抑。不满人性中的猜忌、嫉妒、冷漠,在对华华的偏执思恋中让他有勇气保持清高,背对世俗。猫是马也苦闷无果之爱情的安放,亦是对华华老师爱情的替代,亦是他重拾生活激情的所在。
2.幻想的存在
冉正万的小说多有压抑、无奈、辛酸的阅读体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与迷茫让马也活在恐惧之中,这种恐惧贯穿着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马也通过画猫找到纯净的快乐,猫帮助他走出甲定,让他走向更远的精神生活领域。在物资匮乏和孤立无援的境地中至少有画猫这一件事给他安慰。当周围人都吃着月饼,沉浸在节日的喜悦时,被人遗忘的马也通过画猫来抵御孤独与饥饿。在冉正万看来,饥饿体现了人存在于人世中肉身所需要承受的苦难。他借马也的身份说:“画家无论画什么,画来画去都是画他内心那个虚拟的自足的世界。”[1]P171马也所画的猫通过描绘眼睛来观察神情各异,个性敏锐的人,这正是他的写照:恐惧忧郁、目空一切,在最低处昂首仰望。猫打开了马也的心灵之门,打开这扇门,是他逃离苦难的一个出口。这正是冉正万以敏锐的洞察力极力描绘他所理解的生活,并赋予这种无望的生活一个充满希望的出口。
3.坚韧的追逐
冉正万有一种英雄唯美主义,小说中的马也既狂热又清醒,既迷惑又睿智,既散漫又坚定。当面对生活的打击时,马也坚持自我,遵循内心。为了坚守他们朦胧的感情,成年后的马也选择了在横坡支教。冉正万对他的行为不吝笔墨地给予高度赞誉,他至始至终都有一种理念:过程中希望屡次幻灭,但不放弃寻找另一个全新的马也,战胜和超脱一切。在横坡支教,马也付出了自己两年的青春与热血,与学生相处自然,并与其中几位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马也受伤时学生一起组织前来探望他,并亲切地称他为“爸爸”。在支教的过程中,马也找到自己的存在方式,在他我中寻找到了自我。
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及自救
《洗骨记》极大地表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冉正万以现实凸显理想,以理想反映现实,在诗意的书写下展现黔北个体被创伤的生存状况。对生存的焦虑是冉正万绝不回避的现实境况,但文学并不是仅仅反映生活,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如何利用其艺术效益积极发挥社会教化作用也是作品的价值。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给马也带来了生存上的焦虑,为此,冉正万赋予马也对爱与善的终极追求。
(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文学是人学,是表现生命真实的形态,表现人如何在社会进程中摆脱动物性。灵与肉向来就是一个矛盾体。马也青年时期饱受这一矛盾体的折磨,身体不可自拔地陷入欲望的泥淖,沉浸于原始的快乐,可是每当欲望得到释放时心灵却遭受拷问。马也对性的压抑与幻想让他圣洁的灵魂受到玷污,永无止境的幻想与灵的向善形成强烈的冲突。
1.肉身与精神的博弈
华华老师的出现,唤醒了马也对异性的好奇心,他开始陷入对华华的无边幻想中。身体的沉睡需要另一个身体唤醒,当白色的连衣裙红色的皮箱,婀娜多姿的体态出现在马也的生活中时,便开启了马也最原始的欲望。作为身体的唤醒者,马也最先关注的也是身体,后来也常沉迷于曼妙的身姿。身体不断地发出自慰的命令,但每当在夜晚释放之后,马也便会很快陷入无限的自责与羞愧中,一开始时马也只是敢想却不付诸实际行动。“我翻身下床,做了几十个俯卧撑,这时控制手淫的最好办法。”[1]P15但随着华华作为老师出现在教室里,一方面鼓励马也学习描绘他的人生蓝图,同时也作为异性不断地撩动马也的欲望:去马也的房子,给马也送猫和手表,陪马也看电影,在丈夫死后和马也自由的歌唱等。华华的这些行为激发了马也的原始欲望,在释放了自己的欲望之后又不断地谴责自己,陷入无尽的自责与羞愧之中。
马也爱的轨迹一开始是纯真的,接着陷入对华华身体的遐想,然后是情不自禁的自慰,最后陷入无尽的忏悔。他有过对恋爱蓝图的美好想象,以英雄的姿态站在华华面前,但胆小与怯懦让他不能实现爱情理想。爱情的失意,加上欲望的驱使,他堕落了,陷入欲望的泥潭。无法实现精神的爱恋,动物性在生命里苏醒,屈从于欲望的桎梏。就在马也认为高考后幸福生活即将来临时,变故发生了,华华在他的生命里消失了。在一段时间里征服华华成为存在的意义,中年时才慢慢走出对华华肉身的向往,情欲淡去,才展现出精神的向善。尤其是马也支教的经历,华华成为他的精神向导。马也幻想自己是一个英雄,冉正万把马也打造成一个征服欲望的勇者,通过对善的追求来净化灵魂,这种冲突却赤裸裸地呈现在马也的人生道路上。
2.地面与天空的挣扎
地面是冉正万对存在的思索,《洗骨记》对存在有着诗意的表达,对紧贴于地面的存在有深情的呼唤。地面是存在的载体,是生命的魂根。在中国的神话故事里,女娲用泥土创造了生命,人之于地面,是本源性的生存。地面是人的生活场所,也是生活的本身。地面对于人,不仅是引领我们走向生命的终极,而是思考生命的根与底。有了地面生命才有所依托,地面就是平静的日常生活。地面生命有闲适、静谧也有风暴和残缺。地面具有延续性,每一代人都会在此留下生命的足迹,每一个人都应保留对生活本身的感知。冉正万在喧嚣的时代依旧保持对生命的敏锐,地面是一群人的生命体验。在甲定的地面上,人们的生活不是消极的体验,而是积极的拥抱。作者竭力展现地面的原生态,以马也为代表的群体,他们是真实平凡的个体,拥有可感、可触的缺点。生命充满瑕疵:华华的软弱、刘爱的感伤、祝同法的情欲、祝伯妈的蛮横等等,都展现了生活与地面的真实与丰富。地面赐予人感伤,冉正万以知识分子的话语,表达对生命的理解,让人们学会仰望天空。《洗骨记》不是对生活的照搬和模仿,而是体现人物的精神世界。生命本身仿佛就有受难精神,而天空就是归属。“升天”一词表现冉正万对天空的思考——自由、死亡、纯净、解脱。冉正万笔下的芸芸众生承受生活的磨难但不忘通过努力实现对天空的追随。
凭借作家个体经验对生命细节的雕琢,冉正万塑造的不是空洞的生命体。马也身上具有复杂的人性,既有现实生活经验在他身上体现,同时也有一种灵魂的升华。马也生活在大地之上,有土地赐予他的悲伤,为生存而伤感,为故乡而失落,为爱情而阴郁。孤独、压抑与自我保护紧密地环绕着他。可贵的是地面的苦楚像阴霾一样驱之不散时,马也不忘挣扎着仰望天空。他经历父母的离去,华华的远走,妻儿的遗弃,生活的嘲弄,但带着对光明的期望,仍然追求生命的寂静处所,圣洁之处,坚守用爱对抗生存的阴暗,拥抱朴实的信念,从而走出对不幸的自怨自艾,对生活的偏执回避,走向开阔的未来。
冉正万让马也在地面和天空中挣扎,何尝不是作家自己的突围。写作不仅是展现一个生命,而是塑造一个有灵魂气息的个体,一个拥有生活勇气,敢于走出阴霾的勇者。冉正万为我们建造了一个乌托邦:人可以从绝对的绝望中求得解脱,天空永远在不远处召唤着受苦之人。冉正万深受佛家思想的影响,人如何面对不幸,怎样化解苦楚,他给出了答案:敢于直面地面和天空之间的冲突,努力突围,勇于在黑暗中找寻光明。横坡的支教经历及刘爱的爱情,给了马也向善的参照。在华华的生命结束之前,马也踟蹰于地面与天空两个世界里,无法真正的解脱与释怀。庆幸他的坚持,一份厚重的生命挣扎的体验才能呈现在读者面前。
(二)现实感与理想性洗濯中的自救
生活就像一条深不见底的暗河,马也的肉体和灵魂都被投掷于这条暗河当中,正如小说题目“洗骨记”的喻义:马也的骨头、血液、灵魂都在经受洗濯。暗河洗涤了马也生命的苦痛,净化了马也性格中的缺陷,冲刷了血液里的污垢。马也勇敢地跳入生命的暗河,在理想与崇高的洗濯中拨开生活的迷雾,焕然一新地迎接生活,完成了自我救赎。
1.死亡孕育新生
华华对于马也来说是年少的梦,是生活美好的寄托,是生命存在的理由。这份沉重隐秘的爱既是马也的甜蜜回忆,亦是难以忘怀的伤痛。忠于年少时期的初恋致使马也无法再爱上任何异性,他相信他的爱会笼罩华华全身。因为华华当过老师,他也想体验这样的生活,便去支教。华华是一份回忆,也是见证和激发马也人性弱点的力量,她的到来让马也意味到自己有什么东西在改变,也有东西在失去。改变的是怯懦、惭愧、自私,失去的是纯真与快乐。马也带着堂吉柯德的狂热走在寻找华华的道路上,他幻想重逢时的喜悦与誓言:“我会对自己说,好好地爱吧活吧哭吧笑吧,因为你爱的人回到你身边。”[1]P208可当马也重见华华时并没有喜悦和拥抱,只是对病魔折磨的面容改变的吃惊。失去往日音容的华华让马也措手不及——他喜欢只是记忆中的那个华华。
真正面对回忆里的人时,却固执地希望依恋的人依然存在于回忆里,而没有勇气握手和拥抱。华华一如既往地对马也表现善良、慈爱,还多了一份以往没有的淡淡渴望,但马也却退却了。他像被什么东西骤然拖了一把,无法直视华华。他不再像年少时迷恋她。取而代之的是一份面对生命日渐消逝的悲哀。“我好像被什么东西压倒了、碰伤了,生活曾经对我许下的诺言落空了。”[1]P211马也沉重的爱情随着华华生命的消亡而烟消云散,她的死亡让马也从偏执的迷恋中挣脱,也让他从欲望的泥淖中解放。华华的死亡让马也实现了超脱,从对华华“肉”的迷恋到对刘爱“灵”的追寻,马也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提升,重拾了童年的纯粹,在华华死亡后马也走出过去,释怀曾经,以崭新的姿态重获新生。
2.善与爱的启程
在阐释个体生命存在的苦痛时,善与爱才是作家的终极追求。“拯救恰是在万物众生的缘缘相系之中才能成立。”[3]刘爱是马也生命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相比于华华,刘爱是一个独立、阳光、善良、率真的姑娘,对爱情有自己的美好向往,在横坡这个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的山村,她自然而然地萌发了对马也的爱慕之情。乐观、开朗的刘爱用自己的美丽和善良感染马也,给他阴暗的生活带来了阳光。从横坡回来之后,马也意识到:“最近几天老是静不下来。似乎有一种东西正在复苏,可以理解为对异性的渴望,但远不止于此。”[1]P184马也陷入了对刘爱的想念中,爱情在他身体里发酵。受到妻子黄月欣的伤害后,刘爱温柔、善良与无微不至的照顾,令马也感动,于是两个人坠入爱河。马也对刘爱的爱不同于华华,对后者是身体的迷恋,当肉身陨逝时,爱即刻消逝;对前者是心灵的爱恋,他们彼此惺惺相惜,互为知己。刘爱是爱与善的美好化身,她的出现治愈了马也的心灵创伤,让他重新开始爱与善的启程。
三、《洗骨记》对民族和人性的思考
文学是人学,作品总是会蕴藏民族文化内涵。在冉正万的创作中,读者可以感受到由民族血脉和民族文化所酝酿出的民族认同感。怀着对民族的感情,把视角投向贵州大地上平凡的生命个体。通过对个体充满苦难的生命追寻历程和真实生活状态的描写,体现他对民族文化的思考。马也是一匹驰骋草原的骏马,马代表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敢于直面生活的荆棘与阻碍,战胜生命的不幸,克服自我的弱点,从未放弃对生活的憧憬和追求。小说中女性华华,名字让人不由自主的想到中华民族、华夏文明等。华华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成人之美的美德,她爱马也,但为了马也的未来,不想耽误和连累马也而主动离开他。儒家思想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仁者爱人。“善”与“仁”在华华身上集中体现,在她坎坷的生命历程中,在马也的生命里播撒仁爱的种子。对于小说中另一女性刘爱,具有寓意,冉正万想让我们的生活“留爱”。刘爱像远离尘世的水晶,空灵而灵动,闪烁着动人的光辉,她质朴纯粹、善良乐观、真挚坚强,带着宽容和理解与马也共谱爱与善的赞歌。在这个意义上,冉正万通过《洗骨记》传承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赞誉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呼唤仁爱与真诚。
小说《洗骨记》从一种对个体生命的书写开始,最终抵达对人性的思考。对个体生命智慧的表述,小说从自我经验、自我情感、自我感悟为出发点,审视个体如何正视生活中的不幸与迷惑,对美好情感的追寻,平衡自我与世界的焦虑,以不懈努力保持心灵的圣洁和高洁的精神世界。小说中展现人情体验,讴歌美好人性。冉正万围绕马也的成长来阐释生活中质朴的感情和美好的人性:对于亲情,有缺失的抱憾;对于友情,贵在互相坦诚、互相帮助;对于爱情,在于尊重以及互相理解和宽容;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于相互团结和相互信任。这些人类普遍的情感,生动形象地表达在冉正万塑造的人物形象上。在阅读小说文本时,读者可以感受到另一个生命真实的脉搏跳动,沉浸于悠远的遐想,获取抚慰精神的力量。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在“真、善、美”诗意追寻的人生道路上呼唤美好的人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面临着异化的困境,在金钱、名利、功名的束缚下,让生命变得沉重。如何挣脱这份沉重,冉正万的这篇作品给了我们答案:孜孜不倦地追寻爱与善。文学应给人生活的启迪,生命充满不幸、压抑,苦闷与困惑,但冉正万通过文学为个体存在指引出路:坚忍不拔,乐观向上,勇于追求,带着对善与爱的永恒去追寻信仰。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心目中的作家,必须有充满现代气息的和普世精神的率真。”[4]他以对文学净土的守护,以感性的文学艺术,淡化人们对苦难和恐惧的关注,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启迪人们面对生活时乐观面对,永怀希望。
四、结语
从鲁迅、史铁生、海子、张炜到贵州作家冉正万,他们都以慈爱的笔触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希望通过文学作品唤醒人们的心灵。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存在价值,在于引领读者从中体悟人生的真谛,提升精神境界。纵观冉正万的一系列创作,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人的生存境遇,审视人的生命形态,无一例外都体现了对平凡生命个体的尊重,表现人的高贵与尊严,自始自终教人向善,表现对人性的关怀与思索。他的创作大多以拯救人性为己任,让文学承担起唤醒人性的责任,通过对人物命运与社会变迁的错位,凸显人物的悲剧性,来反映人物的社会性与人性[5],从而达到作家创作主题的升华。小说高扬人性的善与爱,给当下人们的生存方式以精神的启迪。秉承着作家的创作对社会、读者有所启迪的创作态度,冉正万的文学道路将会得到更多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