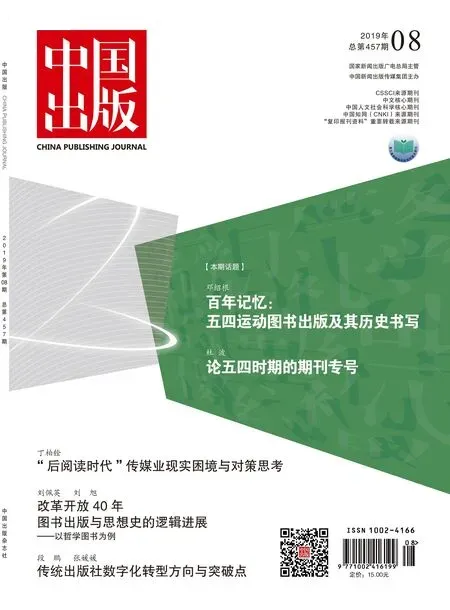人工智能数据新闻作品著作权归属问题探析
□文│沈思言 刘 建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用于撰写新闻稿、“创作”新闻作品等已成为常态。但是,对于经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数据新闻著作权归属问题,目前在法律上则存在争议,[1]国际上也未达一致。由此,本文拟对人工智能所创作的数据新闻作品(以下简称“人工智能数据新闻”)的著作权归属问题进行剖析,以探讨分析其归属的困难之处和解困思路。
一、人工智能数据新闻的内涵与属性
何谓人工智能创作的数据新闻?其性质是否属于作品?与传统意义上的一般新闻作品相比较而言,有何主要区别?其具备哪些特殊性,继而引发其著作权归属的探讨和分析?这是本文展开讨论的前提。
1.人工智能数据新闻的内涵讨论
要了解“人工智能数据新闻”的内涵,首先要了解“数据新闻”的内涵。“数据新闻”是指运用大数据技术在“众包模式”下,从海量数据中发现新闻线索,并通过可视化技术生成新闻报道,具有独创性且能被多次复制的新闻作品。早在1821 年5 月5 日,英国《卫报》便进行了人类新闻史上第一次数据新闻报道的尝试。
那么,什么是“人工智能数据新闻”呢?在现有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条件下,“数据新闻”的可视化呈现往往由“人”来操作辅助完成。而若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数据新闻制作进一步结合,在更大程度上取代“人”在数据新闻制作中的作用程度,便是经由人工智能创作的数据新闻。具体而言,人工智能数据新闻是指计算机在人的操作下利用一定算法对海量数据进行挖掘与整合自动生成的新闻报道。
2.人工智能数据新闻的属性讨论
新闻作品是指新闻主体在新闻活动中创作反映的新闻事实,必须包含“三要素”,即独创性、可复制性和智力成果,[2]其中,独创性是关键要素。依据大多数国家著作权法和版权国际公约的规定,新闻作品一般属于作品,并享有著作权。人工智能数据新闻是否属于新闻作品是其著作权归属问题探讨的前提。学界就此问题尚存在争议。
从著作权法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数据新闻是否达到了最低限度的创造性,是判定其是否为新闻作品的关键。而对于人工智能数据新闻是否具有独创性问题,学界也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人工智能作品是经由检索产生的,并非独立创作而成,因而缺乏独创性。本文认为,在大多数人工智能作品创作中,大量不存在著作权归属争议的数据材料仅仅是为数据新闻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在此过程中创作者在应用人工智能的过程中赋予了数据新闻以新思想、新观点,故数据新闻经过人工智能的再创造,大部分情况下已经具备了新作品的属性。从创作过程来看,即便人工智能产生数据新闻是单纯机械运算和程序执行的结果或人工智能设计者预设行为的结果,其创作过程离不开人的参与及其智力付出。保护作品智力成果是著作权或知识产权的基本特点。另外,人工智能创作的数据新闻具有可复制性特点也非常明显。
当然,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的数据新闻,判断其是否为新作品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若在数据新闻创作中将既有数据作为素材使用,并在将既有数据素材通过人工智能编排为数据新闻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原有作品素材的新观点、新思想,则相比于既有的数据材料而言,人工智能创作的数据新闻是一种再创作的作品,应当享有著作权。但是,如果创作者在人工智能辅助下将既有数据片段组合成数据新闻的过程中没有形成新思想、新观点,则不具有独创性,便不适合赋予著作权。[3]因而,判断人工智能创作的数据新闻是否属于作品,也即是否应当赋予其创作者著作权的关键在于判断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数据新闻是否具备了不同于既有数据思想观点的新思想、新观点,即是否具备了作为新作品的独创性。换句话说,具备了独创性的人工智能数据新闻当属新闻作品,并应当享有著作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享有著作权的前提下,人工智能数据新闻与传统的一般新闻相比依然有其明显的特殊性。这也是其著作权归属不能完全照搬传统一般新闻作品著作权归属原则的直接原因。
二、人工智能数据新闻著作权主体界定
由于人工智能的参与,以及参与创作者的多元化等现实因素的存在,使得人工智能数据新闻著作权的主体界定有待商榷。主要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讨论。
1.人工智能可否作为著作权的主体
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可以作为著作权主体,学界至今没有定论。目前国际上的现行立法大都持否定态度,例如美国的法律解释直接将人工智能等非人类形式排除在著作权权利主体范围以外;英国立法也规定“在没有人的作品的情况下由计算机产生的作品”,作者是“进行创作所必需安排的人”。[4]
笔者以为,人工智能不可以作为著作权主体。原因在于:
第一,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作品”,它是权利的客体。因为“创作”是指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而智力活动只有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自然人才可以做到。如果将著作权归属为人工智能所享有,那么既违背了权利客体和权利主体不可互换的私法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常规逻辑。《美国版权法》第106 条在规定著作财产权时,对权利主体的表述是著作权人(copyright owner)而不是作者(author)。[5]因此,虽然人工智能直接产生了具备一般原创性的作品,作品应受到著作权的保护,但著作权人不应归为“直接”产生作品、可视为“作者”的机器人,而最终应归属于从智力源头“间接”产生作品的人类(具体表现为自然人或法人)。
第二,人工智能不适合享有经济利益。著作权又叫版权,自英国《安娜法令》作为人类第一部《版权法》颁布以来,著作权的设立旨在通过赋予主体一定经济利益而达到鼓励创作,促进文化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如果机器人作为著作权主体,不仅经济利益就其本身而言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它既不能消费,也无法继承或赠与,而且也起不到鼓励创作的作用,达不到著作权法原本的立法目的。
第三,人工智能无法成为诉讼主体。因为当著作权受到侵害时,机器人不能作为诉讼主体参与诉讼,也不具备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完成诉讼程序的能力。
2.在多个参与创作者中该如何归属著作权
基于以上分析,人工智能不能作为著作权主体,那么著作权主体就只能在参与创造的人类中选择。目前,国内外对于人工智能数据新闻的著作权主体主要有3 种主张。
第一种是归程序设计者享有。这种情况的作品生成模式是指,人工智能根据程序编写者事先设定好的程序模板,仅仅检索修改一些时间、地点、人物等替换性词语即可完成的数据新闻。著作权应归人工智能程序设计者所有。如美国《洛杉矶时报》曾利用机器人自动检索美国地质勘探局发布的有关数据,填入模板,程序运行后自动生成新闻稿,并在地震发生3 分钟内发布。人工智能的程序设计者对于数据新闻作品的贡献最大,当为著作权主体无异议,但同时,笔者以为,因为人工智能的开发耗资巨大,有必要在著作权中也适当考虑投资者的利益。
第二种是归人工智能委托人享有。这种情况的作品创生模式是指,程序不仅要把检索信息填充到设定模板,通过人工智能的学习后,再经过亿万次运算才“创作”出来的稿件。美国联合通讯社和人工智能公司开发了一个名为“作家”(Wordsmith)的人工智能新闻写作平台,该平台具有数据获取准确快速等优势,尤其适合财经和体育等新闻领域,目前每个月平均有1000 多篇作品产出。我国也有机器人独立完成的新闻作品,例如2015 年9 月,“腾讯财经”发布的一篇题为“8 月CPI(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0% 创12 个月新高”的稿件,这是我国名为“梦作家”(Dreamwriter)机器人的首个作品。对于该类数据新闻属于百分之百由人工智能创作完成的“孤儿”作品,其著作权归属可按照法人作品的制度安排。依照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应属委托作品。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著作权由委托人享有。[6]
第三种是归新闻机构享有。这种情况的数据新闻生成模式是指,在经过人工智能依照程序完成稿件创作后,还需要编辑者根据新闻的特点、读者的阅读心态再将新闻稿加以润色和修改。因此,这种数据新闻作品加入了编辑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且观点具有创造性。但因为编写新闻稿的人隶属于新闻机构的专业团队,利用人工智能编发新闻作品的行为属于一种职务行为,因此著作权最终应归属于其所隶属的新闻机构。
三、著作权归属解困思路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对于人工智能数据新闻作品著作权的归属问题虽然在如上探讨中有了一定认识,然若将之付诸立法和司法层面的具体应用依然会面对诸多问题。
1.人工智能数据新闻的著作权归属困难分析
人工智能的参与导致权利主客体难以统一。早在20 世纪50 年代计算机发展的早期,就有数学家利用计算机整合以往歌曲进行上万次运算后,“创造”出几千首新歌的情况,但是所创“作品”的版权却遭遇美国版权局的拒绝。这是因为,创作客体脱离了人的参与就被“独立”创造出来了,这和以往认定归属权的方式不一致。又比如通过对几百上千人的作品反复学习一万次后实现创造出的新作品,若将其定义为“集体作品”,但该作品又没有任何“人”的参与,在客体界定和权利归属上仍然难以做到统一。
参与创作者多元化导致权利主体判断困难。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的数据新闻作品,它既可以是基于委托合同的委托作品,也可以是基于职务行为产生的特殊职务作品,还可以是法人作品。[7]对于我国的著作权法法律关系比较明确的委托作品和特殊职务作品,著作权的认定是显而易见的,分别是在人工智能的创作人和投资人之前签订的委托合同关系或者是劳动雇佣关系。但是法人作品的著作权因为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就难以明确认定。法人作品的法律关系既可能是劳动关系的雇佣合同,也可能是委托关系的委托合同,这对人工智能数据新闻作品的著作权认定造成极大困扰。比如,由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在公司指定任务下研发出人工智能机器人,利用机器人自动生成数据新闻作品,这不知应该归为特殊职务作品还是法人作品。因为设计研发人工智能软件的是公司,程序设计员是根据公司的指令进行研发,同时一旦人工智能软件出现任何问题,法律责任也是由公司来承担。
相关立法滞后导致著作权保护机制不健全。人工智能作品的出现因其特殊性会推动未来知识产权的发展。例如,企业策划、程序员执行、责任由公司承担,这三点满足法人作品的三个构成条件。程序员编写人工智能运行程序也是他的工作职责,他编写程序所需要的物质条件都离不开公司的支持,如使用的大型计算机、资料和其他需要编写程序所需要的资金。软件就属于特殊职务作品。
2.人工智能数据新闻的著作权归属解困思路
利用人工智能实现新闻创作新形式是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无论新闻产生技术如何改变,保护著作权人权益、鼓励创作以推进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立法目的不会改变。
健全相关立法体系,明确著作权权利归属。人工智能在国内外新闻界中的应用已是客观事实,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信息社会新闻作品创作的发展趋势。日本目前已经开始对人工智能立法工作,拟以法律条文形式实现对人工智能相关利益者的保护,以防止出现诉讼时无法可依。我国当加快有关人工智能作品著作权保护的立法或修法工作进程,以健全相关著作权法立法体系。
对于人工智能作品著作权归属不明确的问题,我国应当积极借鉴国内外学界对于该问题的法理探讨成果,并结合我国人工智能数据新闻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及时进行相关立法的组织和筹备工作,争取尽快在我国著作权法律体系中对该领域做出明确规定,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权利各方的权责关系。另外,还要结合人工智能数据新闻的发展趋势,充分分析其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著作权归属纠纷,在立法建设中做出提前规范,以确保该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考虑多个参与创作者利益,明确相关主体权责。在对人工智能数据新闻作品归属权进行认定时,应该考虑人工智能软件编写作者和人工智能投资人两者的约定或合同。如果两者之前没有明确约定或合同时,应该参考劳动雇佣关系法或是委托创作合同法,比较作品属于哪种类型而加以区分认定。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投资人将根据劳动合同使得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内部化,职务作品应运而生,但是投资人不但需要对企业内部人员进行管理,还需要对人工智能创造出的作品承担各种法律责任。因此特殊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在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形下应当由人工智能的投资人享有。而对于委托作品,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受托人作为人工智能的直接“作者”,需要独立承担人工智能在研发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因此,如果在委托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人工智能数据新闻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问题时,笔者建议著作权应该由受托人享有,但是由于委托人提供人工智能研发过程的资金等,可以在协商的情况下赋予其免费使用人工智能软件等优势权益。
确立自然人共享原则,合理分配著作权权益。著作权制度的实质就是一种产权的制度。基于科斯定理可知对归属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因素就是交易成本。私有产权、公有产权和共有产权三者相比较,很显然私有产权的交易成本最小。所以纵观各国著作权制度几乎都以私有著作权为主。只有凭借这种模式进行操作,将社会收益纳入个人收益中,才能激发创作者的创作热情,鼓励他们积极创作。在人工智能数据新闻的著作权权利利益分配中,在将人工智能所有者、使用者、数据信息来源者以及程序设计者等确立为著作权权利主体或拟定者的前提下,可以依据各方在作品生成过程中的实际贡献率合理确定著作权的主体结构及其收益的分配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