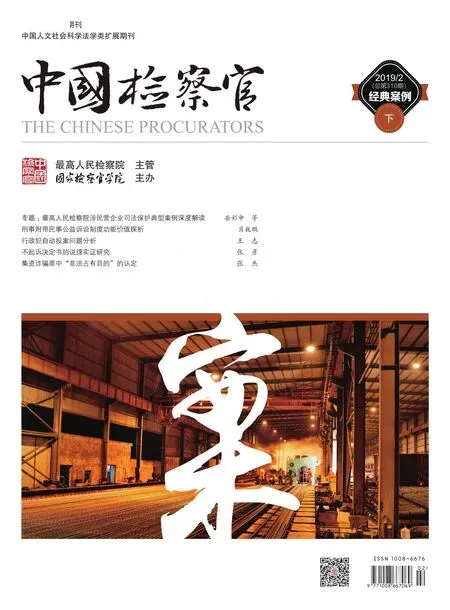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功能价值探析*
● /文
2018年3月1日“两高”《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20条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这意味着“《解释》在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基础上,增加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一新的案件类型”。[1]然而,与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工作相比,当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似乎还没有引起实务界的普遍重视,主要表现为:一是该项工作在各地发展不均衡。例如,根据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办案通报,2018年该省检察机关对环境资源犯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69件,其中上饶市、赣州市共提起40件,其余9个地市合计才提起29件,数据显示一些检察院未开展该项工作。二是实践中被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数与被提起公诉的环境资源犯罪案件数严重不成比例。例如,在2018年3月2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江西省X市检察机关对环境资源犯罪案件提起公诉53件81人,其中无一件案件被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事实上,作为一项新的公益诉讼案件类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进一步丰富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手段,拓宽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具有较强的制度功能和实践价值。本文以三起案件为例,阐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价值,以期引起司法实务界对该项制度的重视,进而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全面平衡协调发展。
一、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司法活动本身不产生社会财富,相反会消耗社会资源。因此,只有合理设计司法制度和程序,才能既不损害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又能降低司法活动所耗费的社会资源。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七章专门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其初衷就是为了在维护法律公正的前提下,兼顾效率。”[2]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就司法机关而言,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减少因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开进行所带来的重复性工作,从而节省大量人力和时间;第二,就刑事被告人、附带民事原告等当事人而言,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让他们针对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在一次庭审中一并陈述、辩论,从而避免当事人因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开进行所带来的讼累;第三,就鉴定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而言,附带民事诉讼也可以让他们避免虽同一起案件却需分别参加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所带来的麻烦。
同理,检察机关根据《解释》第20条规定,对环境资源犯罪、食品药品犯罪提起刑事公诉时,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将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合并到一个诉讼程序中,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一并解决,使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避免了诉讼活动的重复,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精力和财力,也让被告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免受二次或多次诉讼的讼累,“同时也有助于保持案件审理在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事实认定上的一致性和裁判体现价值的协调性。”[3]因此,“为节约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妥善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解释》在第20条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4]
[案例一]2016年1月至4月,某中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公司”)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无环境审批手续、无有效污染治理设施的情况下,非法从湖南衡阳、江西新余等地购入危险废物铅泥、机头灰等原料,非法生产提炼铁渣、锌渣、金属铟等产品。生产过程中,中安公司将未经处理的含镉、铊、镍等重金属及砷的废液、废水,通过私设暗管的方式直接排入袁河,严重污染仙女湖水体,造成特别重大环境突发事件。2017年1月11日,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检察院以污染环境罪对中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某华、监事曾某军、管理人员孔某泉、员工宋某光、投资人钟某以及非法销售危险废物给中安公司的相关公司责任人凌某、余某、赵某强等8人提起公诉。2017年4月1日,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法院对上述8名被告人分别判处6个月至2年6个月有期徒刑,以及分别并处10至25万元罚金。2017年3月30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向江西省新余市中级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诉请中安公司、非法销售危险废物的相关公司承担污染事件应急处置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新余市检察院对此也予以支持起诉。2017年12月25日,新余市中级法院对该公益诉讼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中安公司、非法销售危险废物的相关公司赔偿应急处置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共计3678万元,同时向原告支付律师费、差旅费共计20万元。一审宣判后,原告与被告均不服,向江西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6月15日,江西省高级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5]
从中安公司污染仙女湖水体一案的办理情况来看,该案历经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二个程序才让被告人、被告单位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虽民事诉讼中原告提交的证据与刑事诉讼中控方证据基本无异,却牵扯了二地三级审判机关、二地检察机关的参与,使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在对证据审查采信、案件事实认定上做了大量重复性工作,同时相关责任人、单位也历经刑事、民事诉讼的讼累。
可以说,从该案办理的最终结果来看,被告人、被告单位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不是赢家。因为,如果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时就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一审法院对8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与相关公司的民事责任一并审理,至少可以减少因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而引起的大量重复司法劳动,节省司法资源,同时对于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被告单位来说,也可以不负担向中华环保联合会支付律师费、差旅费20万元以及民事诉讼中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此可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首要功效便是,可以减少司法机关工作量以及减轻当事人讼累,进而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二、及时解决被告人刑民责任,有效维护公共利益
目前,随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针对环境资源犯罪、食品药品犯罪,检察机关维护公共利益的路径主要有二:一是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对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使犯罪分子受到刑事处罚,以维持社会安宁、稳定;二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对犯罪行为提起公益诉讼,使犯罪分子承担民事责任,以弥补犯罪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通常情况下,检察机关依赖这二种路径,就能完成打击环境资源犯罪、食品药品犯罪,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
然而,实践常常出现一些例外情形。由于我国采取“先刑后民”的审判原则,如果对环境资源犯罪、食品药品犯罪必须等到刑事判决后,再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这就有可能出现社会公共利益不能及时得到弥补、损失得不到有效赔偿等情况。因此,将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合并审理,对犯罪分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解决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脱节问题的唯一路径。
[案例二]2014年3月至12月,某良鑫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鑫公司”)在未取得环评审批和处置危险废物合法手续、未建设污染防治设施的情况下,购买危险废物原料生产提炼贵重金属“铟”,并将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直接倾倒在公司周边山上,造成周边农用地基本功能丧失、周边树林大片死亡的重大环境污染后果。经鉴定,该固体废弃物系含砷浸出毒性的危险废物,重1940吨,处置该1940吨危险废物的最低成本为295万元。经审理,2016年12月,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认定良鑫公司法定代表人付某、股东何某喜、陈某珠构成污染环境罪,对3人分别判处1年至1年6个月不等有期徒刑,以及分别并处罚金5万元。事后,针对良鑫公司已造成的污染环境后果,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检察院向渝水区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该局对1940吨危险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置,督促该局起诉良鑫公司环境污染侵权。收到检察建议后,该局共花费337万元对1940吨危险废物进行了无害化处置,并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同时,渝水区检察院也启动支持起诉程序,向法院提交支持起诉书。可是,2017年11月10日,渝水区法院以起诉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该局的起诉。至此,渝水区环保局为处置1940吨危险废物所花费的337万元费用没有得到任何弥补。[6]
其实,本案中检察机关在法院驳回渝水区环保局的起诉后,还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第2款对良鑫公司和3名被告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赔偿因处置1940吨危险废物所花费的337万元费用。然而,现实的问题是:这337万元费用能追偿到位吗?如果追偿到位,3名被告人的刑事处罚是否需要重新考量?
事实上,由于各被告人的刑事处罚已确定以及良鑫公司已名存实亡,即便检察机关在法院驳回渝水区环保局的起诉后,再对良鑫公司和3名被告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但3名被告人在坐牢之余以及良鑫公司名存实亡的情况下,赔偿经济损失已无可能。可以说,本案的教训就是,在追究3名被告人刑事责任时,没有同时一并追究其民事责任,错过对被告人追偿的最佳时机,致使3名被告人在承担刑事责任后没有对公共利益损失进行赔偿。由此可见,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能够为审判机关在分配被告人刑民责任时提供可供选择的路径或机会,从而及时有效地维护公共利益。
三、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恢复性司法理念认为犯罪是对个人的侵害,主张与犯罪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共同参与对犯罪的处理,以修复被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恢复性司法推动了刑罚观念的重大进步,是对传统刑事司法的重要补充,已成为现代刑事司法的一个重要范式。正是因为恢复性司法秉持结果修复、强调问题解决的理念,已被实务界大量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例如,当前司法实务界通过“补植复绿”“增殖放养”“复垦土地”等“恢复生态环境”形式,将恢复性司法理念大量适用于环境资源犯罪案件的处理中,以期在惩治环境资源犯罪的同时,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生态环境。然而,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实践运用时还存在着一个制度上的困难:恢复性司法适用方式在刑事实体法上缺乏相应规定。以环境资源犯罪案件中司法实务常常使用的“补植复绿”为例,“补植复绿”作为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虽然在《森林法》中有相应规定,但《刑法》并未引入,因此,从属性讲,“补植复绿”只是一种行政处罚而已。正因如此,致使司法机关在处理环境资源犯罪案件时要求犯罪主体“补植复绿”,存在着逾越刑法规定的嫌疑,这也势必产生对刑事犯罪直接适用行政处罚是否合法的质疑,毕竟我国《刑法》第37条明确规定行政处罚权由行政主管部门行使。
目前,随着《解释》确立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环境资源犯罪、食品药品犯罪案件中,这一恢复性司法理念运用的制度困难就迎刃而解。因为,检察机关通过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除要求被告人承担刑事处罚、赔偿经济损失外,可以根据具体案情要求被告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审判机关也可以基于被告人悔罪表现以及挽回损失情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努力化解社会矛盾,尽量减少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案例三]2010年3月,广东省惠州市农民陈某良和曾某强未经林业部门批准,擅自砍伐墩子林场林木并出售。经测量,两人盗伐的林木蓄积量为27立方米,盗伐迹地面积5.5亩。经审理,惠州市惠城区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陈某良、曾某强构成盗伐林木罪,分别判处两被告人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3000元。一审宣判后,陈某良和曾某强不服,向惠州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同时,惠城区检察院也提出抗诉。二审期间,陈某良、曾某强多次向法官表示,愿意接受损坏林木价值5倍的赔偿惩罚以及在林业部门指定的林地补种树木。鉴于上诉人认罪态度较好,惠州市中级法院对两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以及分别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同时还判处两上诉人在惠州市林业局指定的10亩林地义务种植500棵树。[7]
本案中,陈某良和曾某强从盗伐林木判处实刑,到承诺补植林木获得缓刑,其“故事”受到了当时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对此,有质疑者认为,尽管二审法院的判决是出于恢复性司法理念而作出的,具有“人性化”的一面,但是该判决对被告人直接处以“种树”的刑事惩罚并无明确的刑法依据,不具有合法性,因为“以‘种树’行为而论,这接近于民事赔偿中‘恢复原状’,理应在民事诉讼中得以体现。”[8]
确实,《刑法》第36条第1款只规定了“赔偿经济损失”这一种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本案中二审法院直接判罚被告人补种林木的刑事判决明显超出刑法规定。应该说,为追求社会效果,陈某良和曾某强盗伐林木案在当时如此处理实属无奈,但如果是现在,则完全可以通过启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从而判处被告人补种林木,使案件的办理体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注释:
[1]徐日丹、闫晶晶:《“两高”出台司法解释规范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载《检察日报》2018年3月3日。
[2]朱国宁、邱湘蓉、贾秀霞、强文敏:《检察机关在公诉环节对附带民事诉讼审判活动监督机制的探索》,载《法制与经济》2014年第11期。
[3]周伟等:《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检察院诉吴明安等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载《中国检察官》2018年7月(下)。
[4]徐日丹、闫晶晶:《依法保障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权利——“两高”〈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解读》,载《检察日报》2018年3月3日。
[5]参见(2017)赣0902刑初49号刑事判决书,(2018)赣民终189号民事判决书。
[6]参见(2016)赣0502刑初148号刑事判决书,(2016)赣0502刑初276号刑事判决书,(2016)赣0502刑初366号刑事判决书,(2016)赣0502民初2183号民事裁定书。
[7]参见林晔晗等:《惠州对盗林者适用非监禁刑》,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12月31日;孔博、毛一竹:《广东两名盗林犯承诺造林改判缓刑》,载《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1月9日。
[8]王琳:《盗林犯被判种树于法无据》,载《新京报》2011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