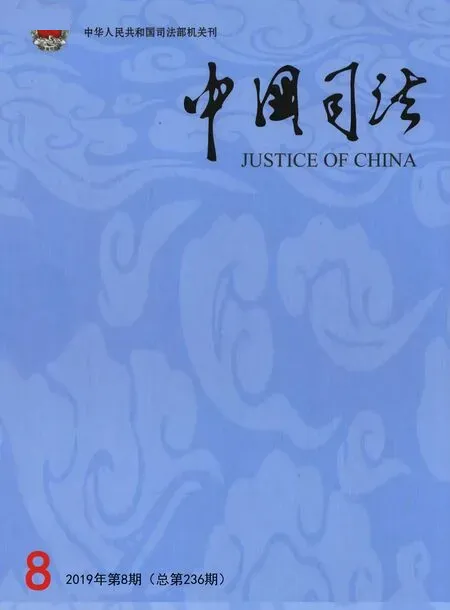社区戒毒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以吸毒成瘾人员的病人身份为视角
何显兵(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
2008年生效的《禁毒法》正式规定了社区戒毒,此后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社区戒毒体系;同时,由于《禁毒法》第48条第2款规定“社区康复参照本法关于社区戒毒的规定实施”,因此社区戒毒与社区康复虽为不同的法律术语,但其工作机制基本相同。2018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2018年查处吸毒人员71.7万人次,处置强制隔离戒毒27.9万人次,责令社区戒毒社区康复24.2万人次。但是,学术研究和实证调研均显示,社区戒毒工作机制尚不完善,对社区戒毒的性质认识并不统一,社区戒毒的实际效果存在疑问。本文拟对社区戒毒机制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并对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进行反思,以期提出完善的对策。
一、社区戒毒机制存在问题的根本:对吸毒成瘾者的标签化
调研显示,我国社区戒毒机制普遍存在如下问题:机构设置不到位,协调指导无实效;社区戒毒工作未有效形成工作合力;吸毒成瘾者流动性大,管控难;社工队伍人员中缺乏专业技能人才;社区戒毒工作管理人员配置不合理;等等①参见韩永泉:《我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现状及对策——重庆市江北区的实践视角》,《人民法治》,2018年第6期。。这些问题在几乎所有的调研论文中都可以得到印证,本文不再重复引用相关文献证实上述问题,而着重关注吸毒成瘾者被标定为“危险分子”这一标签化过程及其带来的影响。
(一)吸毒成瘾者易被标定为“危险分子”
吸毒成瘾者到底是什么身份?学术界曾在《禁毒法》制定的过程中进行了深入讨论,但仍然存在分歧。 2006年6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禁毒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存仪在答记者问时提到:“有专家建议要把吸毒行为定为犯罪,这就涉及到对吸毒者如何定位的问题。通过多年的禁毒实践和相关的医学研究证明,吸毒者是具有病人、违法者、受害者多重属性的。②“新闻办就近期破获一批毒品大案等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wfb/2006-06/22/content_317174.htm[2019-5-22]。”但是,在实践中,吸毒成瘾者往往被标定为“危险分子”,强调对吸毒成瘾者的“管控”。吸毒成瘾者为什么在实践中易被标定为“危险分子”,禁毒部门最直观的认识是“客观上诱发了许多违法犯罪行为”,同时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实务界普遍将“禁毒”与“防艾”结合起来认识。
1.吸毒是否易诱发犯罪行为。美国国家禁毒办公室2014年发布的数据显示,83%的被捕者在逮捕前48小时内至少服用过一种药物,50%的被捕者服用过不止一种药物③Hunt E,Peters RH,Kremling J. Behavioral health treatment history among persons in the justice system: Findings from the Arrestee Drug Abuse Monitoring II Program.Psychiatr R ehabil,2015,38( 1) : 7 - 15.。这种关联性数据能够证实吸毒容易诱发犯罪吗?有论者指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研究表明滥用毒品和犯罪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两者之间更多属于指示性而非总结性的关系”④郭笑等:《毒品滥用与犯罪的关联》,《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18年第3期。。尽管美国等国家在逮捕犯罪嫌疑人时通常会进行尿检并进而获得吸毒数据,但是毒品滥用与犯罪发生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仍然需要细致辨别——到底是吸毒者犯罪率高,还是犯罪者吸毒率高?换句话说,是吸毒导致犯罪,还是吸毒只是犯罪者的一个标识意义?
要证明毒品滥用与犯罪发生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要进行如下分析:首先,统计所有被拘留者(包括治安拘留和刑事拘留)中吸毒和不吸毒的数据与比例;其次,统计所有吸毒者中存在犯罪记录的比例;最后,根据犯罪类型精准研究毒品滥用与犯罪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缺乏上述研究,所谓“吸毒易诱发犯罪行为”的结论就是零碎的感性判断而非科学结论。从犯罪学的角度观察,“吸毒客观上诱发了许多违法犯罪行为”的观点站不住脚,其合理性存在重大疑问。国内论者论证上述观点的依据往往并非司法统计数据,而是个案⑤例如《人民法院报》于2016年6月24日发布《毒品犯罪及吸毒诱发次生犯罪十大典型案例》,其中“陈万寿故意杀人案”即为吸毒致幻后杀死无辜幼儿,罪行极其严重。。虽然不可否认,实践中的确存在部分吸毒与犯罪之间的关联特征,但这种关联特征是否为因果关系,并以“吸毒行为易诱发犯罪”为由,将吸毒成瘾者标定为“危险分子”缺乏实证依据,不宜以此作为强化管控、固化标签效应的正当依据。
2.禁毒与防艾的关联性明显降低。吸毒成瘾者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是共用注射器,这曾是中国艾滋病的重要传染因素。但随着防艾知识的普及,吸毒成瘾者共用注射器感染艾滋病已经占比极低。2015年北京市艾滋病疫情及特点情况显示,经性传播的比例达到96%,其中超过七成为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⑥谭卓瞾:《世界艾滋病日来了,性传播是主要感染途径》,《现代养生》,2016年第1期。。地方实证研究显示,广西贵港市吸毒人群HIV/AIDS流行及相关危险行为呈明显下降趋势⑦赖菁贞等:《2010—2015年广西贵港市吸毒人群艾滋病及相关危险行为的变化趋势分析》,《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从前述数据可知,将吸毒与艾滋病联系对待已经基本没有必要,甚至可以说,吸毒与艾滋病之间已基本缺乏关联。当然,反驳者可能会认为,吸毒往往伴随性乱或者吸毒致幻后发生性关系多不采用安全套,但这种认识缺乏统计数据支撑,不足以成为将吸毒与艾滋病联系认识的妥当理由。吸毒成瘾者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是使用共同的静脉注射器,但这并不能证明吸毒成瘾者容易感染艾滋病,而只能证明使用共同的静脉注射器容易传播艾滋病,两者不可混淆。事实上,使用共同的注射器容易传播各种疾病,跟是否吸毒没有本质关联。
(二)吸毒成瘾者的危险标签产生的后果
首先,对吸毒成瘾者的危险标签导致严重的社会排斥。所谓社会排斥,是指通过某种方式阻隔个体全面参与社会,这既可能是特定群体被主流社会排斥,也可能是特定群体自我排斥于主流社会⑧[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293页。。本文认为,将吸毒成瘾者标定为“危险分子”尤其是将吸毒与艾滋病结合认识的观点,事实上成为妖魔化吸毒成瘾者的理论基础。妖魔化吸毒成瘾者,并将吸毒成瘾者标定为“危险分子”——易传播艾滋病、易实施严重暴力犯罪者的危险形象,将大大增加吸毒成瘾者的社会排斥。负面的标签效应、被驱逐出正常社会生活,导致吸毒成瘾者不仅遭受毒品的困扰,心理上也易因社会疏离导致情感疏离,最终产生“自我放逐”“自我抛弃”效应,戒毒工作将更难取得成效。公众对越轨行为的态度使行动者丧失了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的生活,由此引发的社会排斥将吸毒成瘾者压缩成狭窄的越轨群体,从而可能激发更强大的标签效应,强化越轨心理结构⑨[美]霍华德·S·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张默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现有国内学术研究已经充分证明,社会排斥是导致吸毒成瘾者戒后复吸的重要因素⑩姚维:《毒品成瘾者戒毒-复吸过程中的社会支持研究》,《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17年第1期。。
其次,社区戒毒异化为“非强制隔离戒毒”。研究表明,戒除毒瘾并不再复吸,社会支持至关重要。社区戒毒的本质是在不阻断吸毒成瘾者正常家庭、社会联系的一种治疗康复手段,并同时寄希望于动员社会资源、发挥社区力量参与戒毒康复。但是,对吸毒成瘾者的危险标签导致社区戒毒几乎不可能获得社区支持。正因为将吸毒成瘾者标定为“危险分子”,所以社区戒毒在实践中异化为“非强制隔离戒毒”——正因为其危险,公众不敢积极参与,从而只有政府力量孤军奋战。按照《禁毒法》和《戒毒条例》的规定,社区戒毒的本质应当是多元参与、社会化参与的社区戒毒模式。但与社区矫正的社会化参与对比,社区戒毒工作的社会化参与极低,所谓的“社工”是指社会工作者,而非社会志愿者,社区力量和社区资源基本未参与到社区戒毒工作中来。由此导致社区戒毒仅仅是非机构处遇,成为强制隔离戒毒的次级惩戒措施,没有社会力量参与的社区戒毒,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戒毒,而仅仅是“非强制隔离戒毒”。在缺少社会参与的情况下,以管控为导向的戒毒体系对社区戒毒人员的管控显然难以真正落实,单凭政府的“孤独”行动,不能有效动员最大范围的社区力量参与,社区戒毒的社区参与就很容易沦为形式。根据笔者的调研,现有戒毒机构床位十分紧张,已经呈超负荷运转状态。某省司法厅戒毒管理局所辖的M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设计收治人员为三千人,实际收治人员达到五千人。社区戒毒在缺乏社区资源的支持下,实际上异化为强制隔离戒毒所收治能力有限背景下的不得已而采取的退出机制,未实现“社区”戒毒的制度设计初衷。
应当说,社区戒毒工作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上述两个根本性问题。不能对上述问题作出妥当的回应,社区戒毒工作机制就不可能真正回归本位并得到系统性的完善。
二、对社区戒毒机制的反思
完善社区戒毒工作机制,需以对社区戒毒的宗旨、性质的妥当认识为前提。对此,本文拟廓清如下认识:
(一)惩罚抑或治疗
如前文所述,我国目前将吸毒成瘾者定位为违法者、病人、受害者。但我国不同法律之间对吸毒者的法律属性定位存在冲突,惩罚模式与治疗模式存在交错甚至存在冲突。从《戒毒条例》来看,强制戒毒措施具有明显的惩罚导向,戒毒实践建立了三级强制戒毒体系:第一级,公安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第二级,司法行政部门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第三级,社区戒毒(康复)。社区戒毒并非自愿戒毒而是强制戒毒措施的一种,即便是社区康复,本质上也是强制戒毒的一种。《戒毒条例》区别了公安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与司法行政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这显然是将公安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界定为最严厉的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明显体现了惩罚性。但是,《全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规划》)规定,社区戒毒是“集生理脱毒、心理康复、就业扶持、回归社会于一体的戒毒康复模式”,这显然是将社区戒毒界定为治疗模式,其工作重心完全未提及惩罚、管控。
由上可知,目前我国的戒毒模式实际上将吸毒成瘾者分为两个环节予以不同定位:《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吸毒成瘾者界定为违法者而予以惩罚;《禁毒法》和《戒毒条例》则将吸毒成瘾者既定位于违法者同时又定位于病人,从而兼采惩罚模式与治疗模式。而从《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规划》来看,则将社区戒毒明确定位于治疗模式。不同的法律之间似乎准确定位了吸毒成瘾者的三种属性,但是这三种属性之间到底谁是主导属性存在争议,并由此可能带来不同的戒毒模式:如果将吸毒成瘾者的首要属性定位于违法者,则戒毒必然以惩罚、管控为导向,这是惩罚模式;如果将吸毒成瘾者的首要属性定位于病人或者受害者,则戒毒必然以治疗、保护为导向,这是治疗模式。
本文认为,应当将社区戒毒定位为治疗模式而淡化惩罚性,理由在于:首先,惩罚无助于戒毒。吸毒成瘾首先是种精神疾病,吸毒成瘾者的第一身份是病人,需要的是治疗而非惩罚,惩罚对其没有任何效果,反而增强社会排斥。边沁就曾谈到,在醉迷的情况下惩罚必定无效,而惩罚无效就不适宜于惩罚11[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宏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19~220页。。其次,《禁毒法》和《戒毒条例》已经明确将吸毒成瘾者首先界定为病人12《禁毒法》第31条规定,“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吸毒人员戒除毒瘾,教育和挽救吸毒人员”,对吸毒成瘾者的处遇是“戒除毒瘾”“教育和挽救”。可见,《禁毒法》事实上首先将吸毒成瘾者界定为病人。《戒毒条例》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戒毒工作,帮助吸毒成瘾人员戒除毒瘾,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制定本条例”,《戒毒条例》的立法目的首先是“规范戒毒工作,帮助吸毒成瘾成员戒除毒瘾”,可见《戒毒条例》同样首先将吸毒成瘾者定位为需要“戒除毒瘾”的人员,也即吸毒成瘾者的首要身份是病人。,但受制于传统的惩罚模式,而不得不兼顾惩罚模式与治疗模式,但这两种模式本身存在矛盾,需要与时俱进,抛弃惩罚模式而采治疗模式。在此观念指导下,应当废除《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吸毒应当治安拘留的规定,而根据具体情况纳入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的矫正体系。
(二)管控抑或福利
如果将吸毒成瘾者标定为“危险分子”,则戒毒必采管控模式;如果将吸毒成瘾者界定为“病人、受害人”,则戒毒必采福利模式。
何谓管控模式?认为吸毒成瘾者易诱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或者传播艾滋病,这必然要求在戒毒包括社区戒毒过程中,随时管控吸毒成瘾者。这种管控,一方面是防止吸毒成瘾者在戒毒过程中继续吸毒;另一方面则是防止吸毒成瘾者在戒毒过程中因吸毒实施其他违法犯罪行为。为了实现管控的目标,一方面,《禁毒法》和《戒毒条例》规定,在社区戒毒中,公安机关不仅掌握着社区戒毒人员定期检测的执行权,同时在社区戒毒执行期间约束着社区戒毒人员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公安机关通过“动态管控机制”监管吸毒成瘾者,甚至成为对戒毒人员的终身“前科制度”。
何谓福利模式?就是将吸毒成瘾者界定为“病人、受害人”这一弱势群体身份,对其开展《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规划》所指的“生理脱毒、心理康复、就业扶持、回归社会”四位一体的全面帮助保护、辅导援助。《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规划》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关怀救助,注重人性化关爱帮扶,最大限度地教育、感化和挽救戒毒康复人员”,这显然并不强调管控,而是强调人性化的帮助、救助与治疗。不过,《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规划》并未采取单一的福利模式,而是采取了管控模式与福利模式相结合的戒毒模式,“对发现的吸毒成瘾人员,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应当严格依法作出社区戒毒决定,对强制隔离戒毒出所人员,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应当按规定作出社区康复决定,督促其到户籍地或实际居住地按时报到,并录入吸毒者动态管控系统”的规定,就是管控模式的鲜明体现。
由上可知,我国目前对社区戒毒采取的是管控为主、福利为辅的模式,即在管控到位的前提下注重日常戒毒工作中的帮助保护、辅导援助。但在实践中,往往重管控、轻福利。本文认为,社区戒毒应当采福利模式而非管控模式,理由在于:首先,如前文所述,吸毒成瘾者首先是病人,病人需要的是关爱、治疗而非单纯的管控。其次,福利模式降低对吸毒成瘾者的正式社会控制,但会提升非正式社会控制,通过增强社区联系、强化社会参与,彻底的福利模式将比管控模式更为有效,而这已经为欧美国家长达百年的戒毒实践所证明。最后,管控模式违反社区戒毒的基本理念,既然是社区戒毒,说明其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均不高,如果认为其复吸率和人身危险性较高,则可采用强制隔离戒毒这一管控模式。
(三)一元抑或多元
按《禁毒法》和《戒毒条例》的本意,社区戒毒工作应当是多元的。例如,《戒毒条例》第8条规定:国家鼓励、扶持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参与戒毒科研、戒毒社会服务和戒毒社会公益事业。再如,中共中央、国务院2014年7月印发的《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禁毒委员会组织协调、有关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禁毒工作社会化格局真正形成;《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规划》也提出,广泛动员各方面社会力量,统筹利用各方面社会资源。但是,我国的社区戒毒工作存在着“社会化”的表象与“行政化”的本质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一种披着“社会化”外衣的“行政化”本质的社区戒毒措施现状13何亭苇、包涵:《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社区戒毒制度的反思与改良》,《广西警察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正是由于实质工作均为行政主导,所以无论是《禁毒法》还是《戒毒条例》乃至于《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规划》反复强调“社会化”工作格局,却对社区戒毒的实践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政府主导落到了实处、社会参与却成为空洞的口号,这种戒毒工作的实际导致基层党委政府不堪重负,无力独自承担戒毒工作,只能集中精力进行管控,而对帮助保护、医疗救助等福利供给有心无力,以至于社区戒毒异化为简单的“非强制隔离戒毒”,难以取得实质效果。多元化参与社区戒毒,学术界和实务界均已达成共识。为真正实现多元化参与,需要更新理念,真正确立吸毒成瘾者的病人属性。
三、社区戒毒机制的应然走向
(一)明确定位吸毒成瘾者的“病人”属性
对吸毒成瘾者的首要身份进行何种界定,决定了戒毒机制的不同价值取向,并进而决定了不同的戒毒模式。因此,必须从医学上、法律上清晰界定吸毒成瘾者的身份。“药物依赖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疾病,是个人、环境和社会交互作用而导致的一种成瘾性疾病。14李建华等:《科学认识吸毒成瘾,适时调整治疗策略——调整中国药物依赖治疗策略专家建议》,《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2017年第2期。”可见,医学界普遍认为,吸毒成瘾本身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并不是简单的违法行为。对于病人,需要的是治疗而非惩罚,惩罚对其毫无意义。按照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此处需要区分吸毒行为与吸毒成瘾者,单纯的吸毒行为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上的行政违法行为,应当受到治安拘留等处罚15但从长远来看,最终应当废除对吸毒成瘾者的行政拘留措施,而代之以戒毒措施。;只有屡次吸毒并达到成瘾的违法者,才可能受到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等处遇。对于吸毒行为的惩罚措施,只有治安拘留等行政处罚;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等,应当界定为治疗措施而非惩罚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强制隔离戒毒的本质与强制治疗完全相同,都属于“父爱”式的国家福利主义措施。将吸毒成瘾者界定为“病人”,明确强制戒毒的医疗性质、福利性质,去除吸毒成瘾者“违法者”这一标签所带来的“污名化效应”,增加社会支持,扩大社会参与。戒毒机构的人员应增加具有医学、护理、心理、教育背景的人员,不占警察编制,从而逐步转变为特殊专门医院。
(二)将戒毒工作整体移交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执行
本文主张戒毒工作应当从公安机关剥离,整体移交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变多头管理体制为司法行政机关整体负责体制。理由在于:
1.《禁毒法》和《戒毒条例》规定的戒毒措施体系混乱,难以形成合力。首先,强制隔离戒毒所既有公安机关管辖的戒毒所,也有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戒毒所,而且规定“被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在公安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执行强制隔离戒毒3个月至6个月后,转至司法行政部门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继续执行强制隔离戒毒”,给人感觉似乎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所更为严厉。其次,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由街道办、乡镇政府具体负责不伦不类。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是专业性极强的专业技术工作,而不是政策性强的行政管理工作,社区戒毒、社区康复过程中,公安机关与街道办、乡镇政府之间是什么关系从来没有厘清,这是社区戒毒工作在实践中管理机制不顺畅的重要原因。整体移交司法行政机关,不仅没有理论上的障碍,反而符合国际总体趋势。
2.《禁毒法》规定,由公安机关决定是否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而公安机关又具体承担了强制隔离戒毒工作、实际承担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的主管和指导工作。运动员与裁判员不宜身份重合,且公安机关的长项是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监控、防范和打击,而不是具体的戒毒康复这一专业技术性强的戒毒治疗工作。同时,将戒毒工作脱离公安机关,有利于减少“违法者”这一污名化机制,有利于戒毒工作的专业化、医疗化、人道化。
(三)将社区戒毒纳入社区矫正工作体系
研究证实,社区戒毒工作体系尚不完善,实践中存在诸多困难。本文认为,完全可以将社区戒毒纳入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建立大社区监督体系。
反对者可能认为,社区戒毒不是刑罚执行,社区矫正属于刑罚执行,两者不属同一类型,不应纳入同一体系。但本文不赞同上述看法,理由在于:(1)社区戒毒除了戒毒治疗以外,还包括其他社会福利性质的活动,如《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规划》强调社区戒毒是融“生理脱毒、心理康复、就业扶持、回归社会”于一体的综合性活动,心理康复、就业扶持、回归社会与社区矫正在内容上存在较大重合,工作方式方法上存在很高的相似度。(2)较早期,笔者主张将检察机关的附条件不起诉纳入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受到诸多质疑,理由之一就是附条件不起诉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非罪犯。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附条件不起诉采用委托管理的方式纳入了社区矫正工作体系16例见刘志丰:《江西寻乌检察院推进附条件不起诉与社区矫正“无缝对接”》,载正义网,http://www.jcrb.com/procuratorate/jckx/201304/t20130409_1084750.html[2019-5-2]。;也有越来越多的文章赞同这种工作及机制17例见吴有双、吴越千:《附条件不起诉对象应纳入社区矫正》,《检察日报》,2014年3月19日,第3版。。
实际上,纳入同一工作体系,并不意味着必须属于同一性质,只要有利于整合资源、推进工作,纳入同一工作体系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自2003年社区矫正开展试点至今,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区矫正工作机制和工作体系,而社区戒毒在社会化参与、社会工作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将社区戒毒纳入社区矫正工作体系,有利于整合社区资源,依托于现有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工作方法,实现最佳社会化参与、多元化参与的社区戒毒工作机制。当然,这种纳入并非指社区矫正与社区戒毒在法律属性上同一,而是指在社会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工作机制上存在相似性。社区戒毒的实质,就在于将吸毒成瘾者放在社区中戒毒,这就必然要求充分利用社区各种资源,动员社区内各种群众力量参与戒毒工作尤其是戒毒过程附随的社会工作,将大大增强戒毒工作的力量。尽管社区矫正目前的社会化参与仍然不足,但比起社区戒毒工作来说则大有优势,将社区戒毒纳入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就是要借鉴目前已经略成雏形的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化参与方式,将社区矫正、社区戒毒与社区建设、社区发展结合起来,形成共振、互动机制。发动社区资源、整合社区力量参与社区戒毒,既可以考虑北京的专职社工模式,也可以考虑上海的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当然从长远来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更符合目前中国社会化参与的现实。
社区戒毒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首先是因为对吸毒成瘾者的身份界定为“违法者”还是“病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决定着社区戒毒乃至于整个戒毒体系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认为,吸毒成瘾者首先是“病人”,吸毒成瘾是一种慢性病、精神疾病,这已经为医学研究结论所证实。在此基础上,明确强制戒毒的国家福利性质,并以此重构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机制,方能扩大社会参与,真正实现“社区”戒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