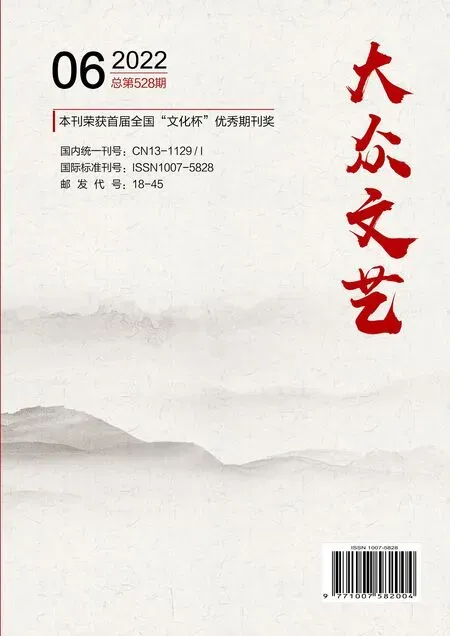从李唐看宋代绘画的审美思想
(北京师范大学 100875)
一、从社会层面分析
(一)政治环境
宋朝的政治环境比较特殊,建立宋朝的统治者把解决来自内部的威胁,放到了最首要的位置。所以把重文轻武作为指导思想,通过各种政治改革,两宋几乎没有权臣和外戚的专权,也没有武将的叛乱。宋代的农民起义规模比起汉唐更是相去甚远。但政治问题的解决,并不仅仅是依靠高度的中央集权,事实上宋朝的政治环境是非常清明和自由的。宋朝的市民阶层比起其他的朝代,相对有着很大的自由和权利。尤其是北宋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言论自由,直接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科学的进步。
(二)经济发展
宋朝的经济发展是极其令人瞩目的,所以两宋有着前所未有的超强经济实力。以至于很多的军事外交问题也是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的。虽然没有了汉唐的尚武与霸气,但也确实给社会带来了相对的安定。所有的这一切因素,为两宋文化的全面快速发展打下了前所未有的坚实基础。相对于文学、艺术、科学甚至包括陶瓷艺术的发展,更为重要也更加影响深远的,是哲学思想和美学上的成就。具体地说就是理学思想的形成,并逐渐地把自身和儒学都推向成熟。在两宋的文化思想中,理学最终占据了最主流的地位,它不但影响了政治、经济,也影响了文学、艺术和审美的发展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理学的思想造就了宋代绘画独特的写实风格,并最终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三)与唐朝艺术的差别
1.理性光辉
和唐代的绘画艺术相比,两宋绘画虽少了一些浑然天成的霸气,也不同于唐朝绘画特有的雍容大度,但宋代的绘画却多了一份理性和冷静,以及这种理性所带来的端庄的气质。这种端庄是空前绝后的,或许正因为如此,两宋的绘画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高峰。这里所谓的端庄,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第一是技法,第二就是气质。从技法的层面来看,这种端庄说白了就是处处讲究。用笔用墨讲究,布局造型讲究,整幅画的格调和气息更是讲究到极致。然而宋人的讲究并没有丝毫的做作,反而让人感觉无比的从容、无比的自信、无比的自然而然。人们陶醉于自己的文化之中,沉着地思考着一切,也沉着地享受着一切。所以在宋代,品茶和焚香如饮食起居一样,是他们的生活常态,即使是最普通的底层百姓也几乎莫不如此。虽然宋代不再崇尚武力,时常遭受外族的侵扰,但崖山之前宋人还没有真正品尝过亡国亡族的苦涩,所以内心仍有着不可动摇的民族自信,尤其是文化上的自信,这一点几乎在所有宋代的艺术作品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这或许就是所谓的“理性的光辉”。
2.山水巨匠
宋代绘画的成就首推山水。早在五代的荆、关、董、巨四位山水巨匠,就已经开了宋朝山水的法度之先;而宋初的范宽更是登峰造极,《溪山行旅图》以凝重的笔墨、宏大的全景式构图,不仅描绘了北方山水雄厚端庄的气势,更是表现出了那个时代人文精神中的厚重与深邃。而李唐作为南宋、北宋承上启下的重要画家,他的作品可能是认识和了解宋代绘画更有代表性的范本。李唐做为宋四家之首,是北宋绘画过渡到南宋绘画的第一人。他学习并综合了荆浩、关同、郭熙、范宽等人的笔墨之法,善用刮铁、马牙、斧劈等皴法。另外他曾任徽宗、钦宗、高宗三朝的画院待诏。李唐在绘画审美上深受徽宗和二米的影响,又加以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
二、唐宋笔墨构架对比
(一)线条
李唐的笔墨技法相当成熟,尤其是对线条的运用。有很多美术史上的观点,认为中国画的线条之法完成于南宋。而最早的线条之法可追溯到上古时期,周朝青铜器上的花纹用线“沈而压多,细而尖,速度小”(引述自《唐宋之绘画》),那种线条古拙而带有鬼气,可以说是线条之法的起源。到了唐宋时期,线条的柔韧性逐渐增加,而鬼气则渐隐,多了柔美雍容之感。后来山水画的兴起又使线条缩短了长度,唐朝李思训等人复兴起了古线法,小斧劈皴便是古代线条的发展,但李氏一派在唐宋之交颇为不振,直至北宋中后才有所回转,入南宋以后,李唐和刘松年等人大振其宗风,强硬的线条开始盛行。宋高宗就曾称赞李唐“可比唐李思训”。李唐在小斧劈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创造,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大斧劈皴。大斧劈适合表现大面积的山石,山石着墨兼水,笔迹宽阔简洁,刚劲有力又不柴不燥,湿笔与飞白相间,虽南宋山水画多取小景,但仍然能够书写出山川的磅礴之气。明代曹昭评:“其石大斧劈皴,水不用鱼鳞觳纹,有盘涡动荡之势,观者神惊目眩,此奇妙也。”(引述自《格古要论》)李唐不仅在石法上有所创造,画水也打破了一贯的程式,创造出一种动荡之势。李唐的笔法对后来的画家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说引导了整个南宋的画风,从技法风格上看,宋四家之中的另外三人刘松年、马远、夏圭都有对李唐绘画的继承和学习。
(二)笔墨
李唐的笔墨技法若从表面上看,只是时代传承的自然结果,但是当我们站在文化的高度上深刻解读,可能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当时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外现。占据主流的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核心就是“格物”,至于到底什么是格物的内涵,理论界好像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大体上就是说穷尽事物的道理而获得智慧。这种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影响了宋代绘画的写实风格。宋代绘画的写实,不同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写实,宋代的写实是通过格物来观照这个世界的。世间万物都蕴含着至高无上的道理和智慧,只有静心澄怀、用心参悟,才能领略其中的奥妙。那么用笔墨去表现眼前的事物,就绝不能仅取其形,而要去参悟其内在的真理与智慧。这样的笔墨就不再限于绘画语言的范畴了,而是具有了一种哲学语言的意味。这样的绘画自然会使画家获得一种超越,更加强化了其文化上的自信,让他们和绘画一同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端庄与法度。这种端庄与法度不仅是宋代绘画的气质,也是宋代文学的气质,更是宋人本身独有的时代气质。
(三)构图
南宋的山水画在构图上也有有别于前朝。宋朝初期山水绘画几乎都是主峰突出,居于正中,上下空间开阔的全景构图。但随着文治的不断推进与完善,宋人开疆扩土的欲望逐渐减弱,对于追求宏伟雄壮的山河之气的热情也有所消退,加上理学思想的影响,人们的审美趣味开始往简洁空灵上转变,山水画不再总是恢宏的全景式取景,描绘树石草芥的小幅作品随之增多。董其昌在《容台集》中讲道“宋以前人都不作小幅,小幅自南宋以后始盛。”南宋以后盛兴“小幅”画,是宋徽宗提倡起来的风气。徽宗在宋代山水画的发展上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他间妙的画格与二米相近,喜作小幅这一点也相类似,徽宗与二米创立的小画之体实为南宋院体画之宗。
李唐本是北宋的画院待诏,受到徽宗影响,在山水画的取景布局上也多使用小景。如他的《采薇图》《清溪渔隐图》皆是截取部分近景,画面不留天地,树木也只画其根不画其冠。宋人极其讲究对树石造型及布局的处理,有着高度的提炼和概括性,这明显不同于西方的风景画,这种布局和经营的观念也是通过格物来认识自然,借助空灵虚静之景探寻事物的本真。空间安排上李唐多采用平远式构图,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一种空间表现形式,平远式构图善于表现深邃空灵的意境,它彻底打破了作品对时空的限制,以小见大,从无生有,强调了山水画在时间上的随意性和空间表达上的无限可能,无论作画还是读画都如亲历一场山水之游,无论画者还是观者都可以由一张画纸延伸出无限的想象,从而摆脱世俗和欲望的束缚,达到精神的解放。
概上所诉,宋代的文化因为理性的光辉而显得更加成熟,它弱化了唐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却多了一种冷静的思辨与观照。市民阶层的兴起让两宋文化更世俗、更现实也更自由。格物的思维方式又让宋人不会忽视事物的任何精微与奥妙。他们用笔墨去思考,用绘画去修炼,用对世间万物的观照,让自己获得对物的超越。所以严谨的法度是宋代绘画艺术的风骨,而端庄的气度则是宋代绘画艺术的灵魂所在。
由北而入南的画家李唐,身处时代巨变的漩涡,他不仅具有敏感的艺术感受力,还有着多变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艺术修养,这使得他的绘画具有了最典型的宋文化特征。宋代文化艺术的迷人气息,通过李唐和其他同时期艺术家的作品跨越千年的时空,给我们传递着文明古国的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