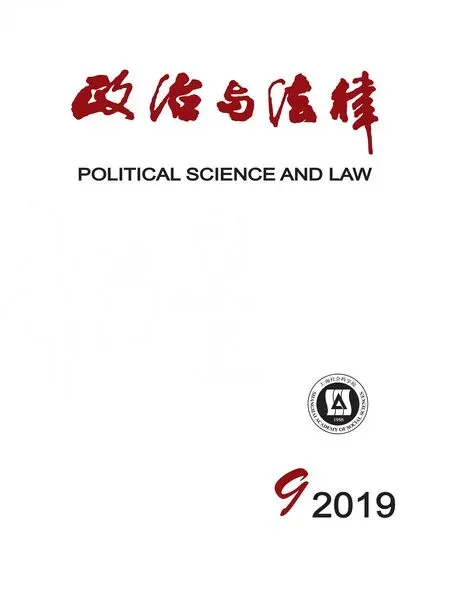论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
(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1189)
随着我国游戏产业的迅速发展,(1)2018年我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144.4亿元,同比增长23.6%;游戏用户规模达到6.72亿人。参见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中心:《2018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http://www.199it.com/archives/810700.html,2019年5月15日访问。虚拟财产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早在2013年,我国网络游戏市场的日均虚拟财产交易额就超过5000万元。(2)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13年网游日均虚拟财产交易额超过5000万》,http://b2b.toocle.com/detail--6115052.html,2019年5月15日访问。正因为虚拟财产蕴含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窃取虚拟财产的行为也日益增多。调查显示,61%的玩家有过虚拟财产被盗的经历。(3)参见皮勇、张晶:《论盗窃网络虚拟财产行为的性质》,《信息网络安全》2006年第10期。那么,窃取虚拟财产的行为应该如何定性呢?在我国刑法学界,除极个别学者主张无罪论外,(4)参见侯国云:《论网络虚拟财产刑事保护的不当性》,《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主流观点都赞同将窃取虚拟财产的行为以犯罪论处,但对于具体的罪名,司法实践分歧极大。例如,对于窃取QQ号码的案件,有的法院认定为侵犯通讯自由罪,(5)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06)深南法刑初字第56号刑事判决书。有的法院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6)参见俞康、张诚、李少麟:《腾讯员工盗卖QQ号获利40万获刑两年》,《南方都市报》2013年2月26日,第AA10版。同样是对于此类案件,有的一审法院认定为侵犯通讯自由罪,二审法院认定为盗窃罪;(7)参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郑刑二终字第 251号刑事判决书。对于窃取游戏金币的案件,有的一审时检察院以盗窃罪起诉,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宣判,二审法院又改判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8)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宿中刑终字第0055号刑事判决书。实践中的这种分歧和混乱局面,反映了新型网络犯罪给传统刑法理论带来的冲击,也反映了网络时代我国刑法理论研究的不足。面对日趋严重的网络犯罪,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和犯罪治理模式或许到了需要反省和提升的时候了。
一、虚拟财产的界定
关于虚拟财产的内涵,学界存在广义与狭义两种立场。广义说把“虚拟财产”理解为“以虚拟形式存在的财产”。所谓“虚拟”,一方面是指虚拟财产不是“实体的”,而是由计算机技术“模拟的”,另一方面是指虚拟财产不是“物理的”,而是“信息的”。(9)参见林旭霞:《虚拟财产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例如,美国学者Fairfield认为,虚拟财产是模仿现实财产之排他性、持久性和互联性特征的代码。(10)Fairfield认为,任何真实财产(例如一支笔)都具有三个特征。如果这支笔在我手中,它就不可能在你手中,这是排他性;如果我放下笔离开房间,它还会在那里而不会消失,这是持久性;如果得到我的同意,你可以使用这支笔,这是互联性。虚拟财产也必须具有这三个特征。See Joshua A.T. Fairfield, Virtual Property, 85 B.U. L. Rev. 1047, 1054 (2005).狭义说把“虚拟财产”理解为“存在于虚拟世界的财产”。虚拟世界可以分为异步互动的虚拟世界,如电子信箱、电子布告栏(BBS)等,以及同步互动的虚拟世界,如网络聊天系统、大型多人在线游戏(MMOG)等。(11)参见黄少华、翟本瑞:《网络社会学:学科定位与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页。
笔者赞同狭义说,即把虚拟财产界定为“虚拟世界中的财产”。广义说外延过宽,把一些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财产当作了虚拟财产,从而将不同法律关系的客体混为一谈,不利于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广义说认为,虚拟财产除了虚拟世界中的财产外,还包括银行账号、电子货币、比特币,甚至还包括电子商标、电子作品、音频、视频等。(12)参见前注,Joshua A.T. Fairfield文;刘惠荣:《虚拟财产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Jennifer Gong, Defining and Addressing Virtual Property in International Treaties, 17 B.U. J. Sci. & Tech. L. 101, 137 (2011);梅夏英、许可:《虚拟财产继承的理论与立法问题》,《法学家》2013年第6期。然而,这些财产大多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发达之前就已经存在,它们或者是债权的客体(银行账号),或者是物权的客体(货币),或者是知识产权的客体(商标、作品),或者同时体现了物权和知识产权(录音带及其中的音乐作品、录像带及其中的影像作品)。只不过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发达以后,这些真实财产多了一种存在和交换的方式,即在实物之外增加了一种数字化存在方式(电磁记录),在实物流通之外多了一种网络传输的交换方式。然而,不管存在方式和交换方式如何变化,这些数字化的财产仍然是真实财产,而不是虚拟财产。例如,电子货币本身就是真实财产,不能将其混同于Q币、游戏币等虚拟货币。“所谓电子货币,就是将现金转化为更利于使用的形态(借记卡使存款使用简便化),从纸币或贵金属转换为电子数据的形态。”(13)[日]野口悠纪雄:《虚拟货币革命:比特币只是开始》,邓一多、张蕊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它实际上是我们的现实财富在网络环境中使用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14)蒋惠岭主编:《网络刑事司法热点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33页。
需要注意的是,比特币既不是电子货币,也不同于货币类虚拟财产。“比特币是一种没有发行者和管理者的货币”。(15)同前注,野口悠纪雄书,第4页。换言之,比特币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私货币,所有参与人通过P2P网络对比特币进行发行和管理。比特币明显不同于金融机构发行的电子货币,也不同于游戏运营商发行的虚拟货币。比特币在很多国家被允许作为贸易支付手段,属于现实财产。因此,盗窃电子货币和比特币这两种现实财产的行为,可以直接认定为盗窃罪,不能也没有必要与“盗窃虚拟财产”的定性问题混在一起。例如,电子商标、电子作品、音频、视频原本就是知识产权的客体,未经许可使用或者复制发行这些电磁记录的行为应该认定为侵犯知识产权罪,其与“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如何定性没有联系。把两者混同起来,只能徒增问题的复杂性。
另外,刑法理论与实务往往也把手机的上网流量归入虚拟财产,进而在虚拟财产这一范畴内探讨盗窃流量包的行为如何定性。(16)参见赵文胜、梁根林、曲新久等:《盗窃“流量包”等虚拟财产如何适用法律》,《人民检察》2014年第4期。实际上,流量既不是数据,也不是信息,而是数据和信息传输的字节数,是一种计量和计费的单位。从法律责任来看,盗窃流量包的行为同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号码一样,指向的是享受网络服务而不缴纳费用的利益。“这种享受服务却不交付对价的行为,显然是一种获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17)黎宏:《论盗窃财产性利益》,《清华法学》2013年第6期。因此,窃取流量包的行为原本就应该直接认定为窃取财产性利益的盗窃罪,而不涉及虚拟财产的问题。
综上所述,把现实世界中数字化的真实财产当作虚拟世界中的虚拟财产,实际上是把两个不同世界的东西混为一谈,不利于理解虚拟财产的属性,也不利于研究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问题。因此,应该把虚拟财产界定为虚拟世界中的财产。实际上,在网络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虚拟世界和虚拟财产。例如我国古代神话故事《孙悟空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中的“天宫”“龙王殿”就是虚拟世界,孙悟空和哪吒就是虚拟角色(avatar),孙悟空使用的金箍棒、哪吒使用风火轮和乾坤圈等就是虚拟装备。只不过那个时代的虚拟世界还是封闭的,无法与现实世界进行互动。现代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开放、互动的现代虚拟世界得以出现。在现代虚拟世界中,用户化身为虚拟角色(avatar),在3D的虚拟环境中遨游,随意同其他虚拟角色以及动植物进行互动。(18)See Nelson DaCunha, Virtual Property, Real Concerns, 4 Akron Intell. Prop. J. 35,39 (2010).更为重要的是,现代虚拟世界中的虚拟装备、道具可以在用户之间以真实的货币进行交易。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虚拟财产才会成为法律关注的对象。根据虚拟财产在虚拟世界中的作用,可以大致将其分为三类,即账号类虚拟财产(网络游戏账号、QQ号码等),物品类虚拟财产(网络游戏的装备、游戏、化身等),货币类虚拟财产(Q币、金币等)。(19)参见江波:《虚拟财产司法保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4页;陈兴良:《虚拟财产的刑法属性及其保护路径》,《中国法学》2017年第2期。当然,虚拟财产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其会随着虚拟世界的创新而补充新的内容。在界定了虚拟财产的范畴以后,需要考虑的是刑法如何保护虚拟财产。对此,直接保护路径是我国的主流,但是这一路径的合理性值得商榷。
二、对直接保护路径的批判
直接保护路径直接把虚拟世界中的“虚拟财产”等同于现实世界中的“财物”,并以侵犯财产罪来处罚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这是我国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20)参见上注,陈兴良文;张明楷:《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性质》,《法学》2015年第3期;赵秉志、阴建峰:《侵犯虚拟财产的刑法规制研究》,《法律科学》2008年第4期;于志刚、于冲:《网络犯罪的裁判经验与学理思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326页以下;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页;黎宏:《刑法学各论》,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91页。也是司法实践的传统做法。(21)根据我国学者统计,在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案件中,以盗窃罪、诈骗罪、职务侵占罪等侵犯财产罪论处的比例为58%。参见刘品新、张艺贞:《虚拟财产的价值证明:从传统机制到电子数据鉴定机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然而,这一保护路径存在很大的问题,会引起理论与实践的诸多混乱。
(一)虚拟财产不属于刑法中的财物
把虚拟财产解释为刑法中的财物,在方法论与法益论上都值得商榷。
1.从方法论来看,把虚拟财产解释为财物属于类比而不是涵摄
按照法律适用的三段论方法,大前提是“对于T中的每个事例均赋予法效果R”(T→R),小前提是“S为T的一个事例”(S=T),结论是“对于S应赋予法律效果R”(S→R)。其中确定小前提(S=T)的过程被称为“涵摄”。其逻辑是:T籍由要素m1、 m2、m3而被穷尽描述;S具有m1、 m2、m3等要素;因此S是T的一个事例。(22)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0~152页。据此,只有当虚拟财产具有财物的全部要素m1、 m2、m3时,才可以将虚拟财产涵摄于财物概念。然而,采取直接保护路径的学者基本上都不分析财物这一概念的“要素”,也不探索虚拟财产的“要素”,只是以“特征分析”取代“要素分析”。申言之,采取直接保护路径的学者往往都只分析财物的“特征”以及虚拟财产的“特征”,认为虚拟财产完全具备财物的“特征”,从而肯定虚拟财产属于财物。例如,张明楷教授认为财物具有管理可能性、转移可能性、价值性三个特征,而虚拟财产也完全具有这三个特征,所以虚拟财产属于财物。(23)参见前注,张明楷文。以“特征分析”取代“要素分析”实际上是用“类比”取代“涵摄”,超出了解释的范围而落入了类推的模式。在此使用类推方法和模式的错误在于以事例之间的类似关系对三段论进行了歪曲和改造,其结果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大前提是“对于T中的每个事例均赋予法效果R”(T→R);小前提是“S与T中的事例具有类似性”(S∽T);结论是“对于S应赋予法律效果R”(S→R)。(24)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质言之,类推在小前提的建构过程中,用“类比”取代了“涵摄”。其逻辑错误在于,不是因为虚拟财产具备财物的全部要素m1、 m2、m3,而是因为虚拟财产在M1、 M2、M3等特征上与财物具有类似性,所以肯定虚拟财产属于财物。然而,特征不同于要素,要素是事物内部固有的属性,而特征是从不同角度对事物进行外部观察而得出的认知。不同的观察者用不同的标准和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虚拟财产归纳出不同的特征,既可以归纳出与财物相似的特征,如三特征说,(25)认为虚拟财产具有排他性、持久性、互联性。参见前注,Joshua A.T. Fairfield文。四特征说,(26)四特征说认为虚拟财产具有无形性、价值性、现实转化性、合法性。参见前注,赵秉志、阴建峰文。或者五特征说,(27)五特征说认为虚拟财产具有排他性、持久性、互联性、次级市场性、用户可添加价值性。See Charles Blazer, The Five Indicia of Virtual Property, 5 Pierce L. Rev. 137, 139(2006)。也可以归纳出与财物不同的特征。(28)例如有学者认为,虚拟财产具有影像性、局限性、期限性、动荡性,而这些都与财物的特征不同,因此虚拟财产不是财物。参见侯国云、么惠君:《虚拟财产的性质与法律规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4期。总之,既不能因为虚拟财产具有与财物相同的特征就肯定其属于财物,也不能因为虚拟财产具有与财物不同的特征就否定其属于财物。
2.从法益论来看,虚拟财产仅仅是先于法益的纯粹利益
我国学者之所以肯定虚拟财产属于财物,除了虚拟财产具有与财物相似的特征外,另有两条重要论据:一是虚拟财产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形成了价值和财产权;二是虚拟财产可以与现实货币进行交易。这两条理由都值得怀疑。
(1)虚拟财产不是劳动创造的,不具有劳动所形成的价值和财产权
我国学者大多倾向于认为,虚拟财产是由玩家通过劳动并伴随时间与金钱的投入而创造出来的。(29)参见前注,陈兴良文;前注,张明楷文;前注,赵秉志、阴建峰文;前注,于志刚、于冲书,第329页;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穗中法刑二终字第68号刑事判决书。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理由不在于打游戏的过程不是劳动,(30)有的学者认为,打游戏不是劳动,“玩家都不过是动动手指而已”,因而不存在劳动创造的价值。参见前注,侯国云、么惠君文。而在于这一观点误解了创设虚拟财产的事实情况。
网络游戏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角色升级类网络游戏,我国运营的网络游戏均属于此类;二是模拟人生类网络游戏,如美国的《第二人生》(Second Life)等,我国不存在这类游戏。从技术上来看,在角色升级类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并非玩家“创造”出来的,而是玩家在游戏打怪过程中触发掉落的。实际上,这类游戏中的虚拟财产都是游戏设计者事先编写好并由脚本代码对其进行控制的,在游戏进行到触发条件成就时才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然而,在以《第二人生》为代表的模拟人生类游戏中,情况则有所不同。游戏设计者并没有把所有可能出现的虚拟财产都编写好,设计者只提供一块空无一物的虚拟土地,同时向玩家提供基本的3D实时编辑器和脚本编辑工具。玩家可以在土地上运用编辑工具“建造”3D的住房、商场、体育馆、家具、汽车等虚拟财产。(31)参见前注,江波书,第26~ 30页;前注,Nelson DaCunha文。
可见,在我国运营的角色升级类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并非玩家创造出来的,因此也就无从谈论玩家的劳动创造了虚拟财产的价值。虽然不同的游戏装备会有不同的定价,但这个定价不像真实财物一样是由凝聚在其中的抽象劳动量来决定的。事实上,这个定价也是由游戏设计者事先设计好了的。(32)游戏装备的定价公式为:攻击次数×[损坏后的平均攻击力+(全新时的平均攻击力-损坏后的平均攻击力)÷2 ]。例如,如果一把剑的攻击次数被设定为3600次,损坏后的平均攻击力被设定为1,全新时的平均攻击力被设定为8,那么其交易值为“3600×[1+(8-1) ÷2]=16200”。参见前注,江波书,第23页。然而,在模拟人生类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确实是由玩家通过自己的劳动设计出来的,那么能否说玩家创造了虚拟财产的财产价值或财产权呢?对此,有的学者根据洛克劳动理论,认为当玩家的劳动注入虚拟财产以后,玩家就取得了对虚拟财产的财产权。(33)See F. Gregory Lastowka & Dan Hunter, The Laws of the Virtual Worlds, 92 Cal. L. Rev. 1, 46 (2004). 参见前注,Nelson DaCunha文。然而,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洛克劳动理论只能解释最先从“自然界”获得财物的人对该财物拥有财产权,而不能证明在虚拟世界的“野外”获得虚拟财产的人也对该虚拟财产拥有财产权。换言之,玩家对虚拟财产并不拥有财产权。(34)See Christopher J. Cifrino, Virtual Property, Virtual Rights: Why Contract Law, Not Property Law, Must Be the Governing Paradigm in the Law of Virtual Worlds, 55 B.C. L. Rev. 235, 252 (2014).
(2)可交易性并不能使虚拟财产的经济利益上升为财产法益
有的学者认为,当网络游戏的玩家人数较少时,虚拟财产不能交易,不具有财产性,但当玩家的人数不断增多时,围绕虚拟财产形成了游戏内外两个交易市场,此时虚拟财产成为财产罪的犯罪对象,虚拟财产所蕴含的经济利益上升为刑法中的财产法益。(35)参见董玉庭:《论刑法中财物概念之解释》,《当代法学》2012年第6期。
不可否认,虚拟财产与金钱的交易确实普遍存在,并且这种交易都处于法律规制不明确的灰色状态,(36)参见前注,Joshua A.T. Fairfield文。为此有学者主张,“应当把虚拟财产与真实财产的兑换行为犯罪化”。(37)参见前注④,侯国云文。虽然可交易性说明虚拟财产确实具有经济利益,但这种利益属于法益之前的生活利益,还没有上升为法益。例如,性服务也可以通过交易带来经济利益,但这种利益不可能上升为法益。利益与法益具有重要区别。“所谓法益,是由法所保护的利益。所有的法益都是生活利益,是个人或者共同社会的利益。产生这种利益的不是法秩序,而是生活,但是,法的保护把生活利益提高为法益。”(38)[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利益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发展需要的客体对象。”(39)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虚拟财产仅仅是能够满足社会成员物质或精神需要的利益。这种利益要上升为法益,必须具备三重承认:首先是个人的承认,即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承认或要求该种生活利益得到刑法的保护;其次是社会的承认,即社会多数成员承认或要求该生活利益得到刑法的保护;最后是法的承认。(40)参见[日]关哲夫:《法益概念与多元的保护法益论》,王充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虚拟财产虽然具有个人的承认,但难以判断存在社会的承认以及法的承认,201年颁布的我国《民法总则》也没有把虚拟财产规定为物权或者债权的客体。(41)在我国《民法总则》的制定过程中,草案曾经把虚拟财产规定为物权的客体,但是部分学者反对态度异常激烈,认为网络虚拟财产根本就不是物,也不是物权的客体,同时社会上对网络虚拟财产物的属性的反对意见较多,最终我国《民法总则》并未承认虚拟财产是物权的客体。因此尚不能说虚拟财产的交换性利益已经上升为刑法中的财产法益了。
(二)直接保护路径的困境
直接保护路径在肯定虚拟财产属于财物以后,把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认定为侵犯财产罪。然而,这一路径引起了犯罪论与刑罚论的混乱。
1.直接保护路径滥用了犯罪成立理论
直接保护路径把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直接作为侵犯财产罪来处理,是对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理论的滥用。
(1)直接保护路径模糊了构成要件的类型化意义
赞同直接保护路径的学者虽然都认为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构成侵犯财产罪,但在具体罪名的认定上存在分歧。(42)据国外学者统计,在网络游戏犯罪中盗窃罪占73.4%,诈骗罪占20.2%。See Andrea Vanina Arias,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Swords and Armor: Regulating the Theft of Virtual Goods, 57 Emory L.J. 1301, 1304 (2008).有的学者认为,非法获取物品类虚拟财产构成盗窃罪,因为被害人丧失该虚拟物品即丧失权利;非法获取账号类虚拟财产构成诈骗罪,因为行为人获取账号后还必须冒充权利人才能使用或者出售。(43)参见田宏杰、肖鹏、周时雨:《网络虚拟财产的界定及刑法保护》,《人民检察》2015年第5期。主流观点认为,非法获取他人虚拟财产的行为都构成盗窃罪,不论行为对象是物品类还是账号类虚拟财产。(44)参见前注,陈兴良文。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首先,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同时包含“窃取”与“欺诈”的行为要素。对于账号类虚拟财产来说,行为人首先必须获取该账号及其密码,然后还需冒用权利人的身份。这其中同时存在“窃取”与“欺诈”要素,单独以诈骗罪论处并不合适。同样,非法获取物品类虚拟财产的行为也同时包含了“窃取”和“欺诈”要素。因为任何一个虚拟物品的数据中都包含一个“出生记录”,以标明该物品是什么时间从什么怪物身上打下来的。(45)参见寿步、徐彦冰、融天明:《对非正常途径制作销售虚拟装备不应定罪处罚》,《电子知识产权》2007年第11期。因此行为人窃取虚拟物品后必须隐瞒该“出生记录”才能使用或者出售,这具有明显的欺诈性质,难以单独构成盗窃罪。可见,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不论其对象是什么,都同时包含“窃取”与“欺诈”要素,单独认定为盗窃罪或者诈骗罪都不合适。并且,由于“诈骗罪与盗窃罪是对立关系”,(46)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9页。也不能认为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竞合。
其次,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不存在“占有转移”。盗窃罪与诈骗罪都是转移占有的犯罪,那么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是否具有“占有转移”要素呢?我国学界往往把“虚拟财产能否占有转移”当作“财产性利益能否转移”的下位命题,肯定后一命题的学者也会肯定前一命题,(47)参见马寅翔:《占有概念的规范本质及其展开》,《中外法学》2015年第3期。否定后一命题的学者也会否定前一命题。(48)参见徐凌波:《虚拟财产犯罪的教义学展开》,《法学家》2017年第4期。笔者认为,上述两个命题并无必然联系,即使肯定财产性利益能够占有转移,也不能肯定虚拟财产的占有转移。这不仅仅是因为虚拟财产不属于财产性利益,而且是因为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对虚拟财产不存现实的“占有”。对虚拟财产的所谓占有完全不同于对财物的现实占有:现实占有体现了一种人际关系,而虚拟财产的占有纯属一种代码关系。申言之,对虚拟财产的所谓占有完全是由代码所定义的一种关系。代码既可以定义为与现实相似的占有关系(例如某角色把蛋糕吃掉以后,蛋糕灭失,对蛋糕的占有关系消灭),也可以定义与现实不同的占有关系(例如这块被吃过的蛋糕又神奇地重现了,对蛋糕的占有关系并未消灭)。(49)参见[美]劳伦斯·莱斯格:《代码2.0》,李旭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另一方面,虚拟财产的转移也不是“占有转移”。表面上来看,一方虚拟财产减少的同时对方虚拟财产得到了增加,但实际上并非一方的数据“转移”到了对方的账户中,而是代码对双方的数据进行修改的结果。这一过程中并不存在“占有转移”,只存在“利益转移”。应该区分“占有转移”与“利益转移”,利益转移的行为可能构成侵占罪,但不能构成盗窃罪或诈骗罪。(50)参见前注,徐凌波文。
(2)直接保护路径扭曲了违法性的判断
按照直接保护路径,虚拟财产属于财物,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构成财产罪。既然如此,则网络游戏中游戏角色之间窃取或故意毁坏虚拟财产的行为也符合财产罪的构成要件。不过,即使是赞同直接保护路径的学者也会否认这种行为的可罚性。那么,这种构成要件符合性行为的出罪事由是什么呢?赞同直接保护路径的学者往往求助于违法阻却事由中的同意规则。例如,美国学者Fairfield认为,如果在游戏过程中玩家A拔出虚拟刀刺死了B的化身,那么A的行为完全不可罚;如果玩家A通过黑客技术侵入B的账户后删除了B的化身,那么A的行为应该受到刑事处罚。两行为的区别在于,前者中玩家对于战斗达成了合意,而后者中的黑客行为超出了同意的范围。(51)See Joshua A.T. Fairfield, The Magic Circle, 11 Vand. J. Ent. & Tech. L. 823,836 (2009).
然而,采取同意规则来阻却违法性的做法值得商榷。玩家点击同意“最终用户许可协议”(EULAs)并加入网络游戏,只是表明其同意遵守游戏规则,并不表明其同意放弃自己的利益。游戏规则复杂多样,有的游戏规则允许角色之间的盗窃行为,(52)例如,在Ultima Online 游戏里面,你可以偷偷溜进别人的住宅,练习你的盗窃技巧,盗窃别人的物品。参见前注,劳伦斯·莱斯格书,第377页。但也有不少游戏规则禁止角色之间的盗窃行为。(53)参见前注,Nelson DaCunha文。对于前者,可以依据同意规则来排除构成要件符合性行为的违法性;对于后者,则同意规则无用武之地。例如,在《第二人生》虚拟世界发生这样一件事:丹克养了一条狗,邻居玛莎栽种了一些异常美丽却含有剧毒的花,有一天花瓣飘落到丹克的院子里毒死了丹克家的狗。丹克为此十分生气并同玛莎争吵起来。(54)参见前注,劳伦斯·莱斯格书,第11~12页。显然,丹克及其背后的玩家并不认为自己“同意”虚拟狗被毒死这一危害结果。当然,邻居玛莎及其背后的玩家也不可能承担过失或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的刑事责任,即使其故意把有毒的花丢到丹克的院子里。其根本原因在于,虚拟世界不同于现实世界,虚拟财产不同于现实财物,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不论是纯粹发生在虚拟世界中还是从现实世界侵入虚拟世界)不能直接按照现实世界中的侵犯财产罪来处理。(55)也许有人会认为,纯粹发生在虚拟世界中的盗窃,只是一种游戏行为,不是盗窃罪的实行行为,因此无法成立盗窃罪。然而,实行行为是指法益侵害行为,既然肯定了虚拟财产属于刑法中的财物,就应该同样肯定侵犯虚拟财产的游戏行为也是盗窃罪的实行行为。
2.直接保护路径导致罪刑不均衡
除了犯罪论中的问题外,直接保护路径在刑罚论也会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计算虚拟财产的数额,如何做到罪刑均衡。
陈兴良教授归纳出计算虚拟财产数额的四种方法:根据网络公司的标价计算;根据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交易价计算;根据网络公司与代理商之间的交易价计算;根据销赃数额计算。他认为这些方法“足以应对各种侵犯虚拟财产的犯罪案件”。(56)参见前注,陈兴良文。然而,现实的问题不是缺少计算数额的方法,而是如何实现罪刑均衡,而且方法越多,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可能就越突出。例如:被告人雒彬彬利用职权私自生成游戏中的“金锭”2900余万枚,按游戏公司的标价计算,数额是197万元,而实际的销赃数额是56万元。一审判决认定为盗窃罪,盗窃的数额是197万余元,因而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3年。该量刑明显畸重。二审判决认为被告构成的不是盗窃罪而是职务侵占罪,数额也不是197万元,而是56万元,判处被告有期徒刑6年。(57)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刑终字第66号刑事判决书。虽然该案的二审法院作了改判,但是该二审判决也存在问题:在存在游戏公司有效标价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根据销赃数额来量刑?因为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财产罪中的销赃数额不是影响法益侵害性的根据,也不是量刑的根据。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8号)也删除了1998年相关司法解释中按销赃数额来确定盗窃数额的规定,转而明确规定“被盗财物有有效价格证明的,根据有效价格证明认定”。
由此可见,直接保护路径会陷入一个量刑困境:根据虚拟财产的价格量刑可能导致量刑畸重,为了克服量刑畸重的弊端又可能偏离财产罪的法益保护原则。为了克服这一量刑困境,张明楷教授提出一个改良方案:在盗窃“用户”虚拟财产的情况下,按照价格来确定数额;在盗窃“游戏公司”虚拟财产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量刑畸重,按照情节而不是数额来量刑。其理由是,法益的价值与法益的主体密切相关。(58)参见前注,张明楷文。然而这一方案也值得商榷。在某些场合,法益的价值确实与法益的主体密切相关。例如同一型号的电缆相对于电缆的生产厂家、公用电信设施的所有人、军用设施的所有人、废品店的老板等不同主体来说价值确实不同。这种价值的差异主要是通过电缆所反映的不同罪名及不同法益所决定的。对于同一罪名,法益的价值不应根据主体的不同而差异悬殊。(59)我国司法解释规定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酌情从严惩处”。参见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这只是一个例外规定,不具有普遍性,也不能量刑过于悬殊。如果窃取虚拟财产的行为都构成盗窃罪,就没有理由认为对于用户和游戏公司而言,同等的虚拟财产具有不同的价值。不能说盗窃穷人的钱按照数额量刑,盗窃亿万富翁的钱按照情节量刑;也不能说盗窃穷人3000元钱属于数额较大构成犯罪,而盗窃亿万富翁3000元钱属于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
综上所述,直接保护路径直接把虚拟财产解释为刑法中的财物,把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认定为财产罪。然而,把虚拟财产解释为财物在方法论与法益论上都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把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认定为财产罪在犯罪论与刑罚论方面都造成了混乱。导致这些问题和混乱的根源在于,直接保护路径忽视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本质区别,用现实世界中的传统刑法思维来处理虚拟世界中的犯罪事实。因此,探索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路径,必须从澄清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入手。
三、刑法对虚拟财产的作用点
虚拟财产属于虚拟世界,而刑法是现实世界的行为规范,那么现实世界的刑法能否规范虚拟世界呢?这一问题涉及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以及刑法的适用范围。只有在正确理解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后,才能找到刑法保护虚拟财产的作用点。
(一)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关于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主要存在混同说、分立说与双重性说三种不同观点。混同说是上述直接保护路径的理论基础,分立说则会否认刑法对虚拟财产的保护作用,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只有双重性说才正确把握了这两个世界的关系。
1.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混同说
这种观点认为:“在‘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没有界限。相反,所有的所谓‘虚拟’行为都源于真实的人,并影响真实的人,尽管其通过了计算机的中介。因此,‘虚拟’行为与‘真实’行为之间的区别是无益的”。(60)See Joshua A.T. Fairfield, The Magic Circle, 11 Vand. J. Ent. & Tech. L. 825, 825 (2009).“任何人都是在现实生活中使用虚拟财产,使虚拟财产为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服务。”(61)参见前注,张明楷文。按照这种观点,既然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混同在一起,那么法律当然既适用于现实世界也适用于虚拟世界,“说虚拟世界不受现实世界法律规制是不可信的”。(62)参见前注,Joshua A.T. Fairfield文。前述直接保护路径的理论基础就是这种混同说。
然而,对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不加区别的观点值得商榷。现实世界是人类生活工作的场所,受国家制定法的规范;虚拟世界是虚拟角色“生活工作”的场所,只能由工程师编写的代码所控制,法律无法直接规范虚拟角色的行为。(63)虽然在比喻意义上可以说,法律是现实世界中规制人们行为的“代码”,代码是虚拟世界中规制角色行为的“法律”(参见前注,劳伦斯·莱斯格书,第81页),但是,代码和法律本质上完全不同。把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混同起来会导致虚拟财产的外延不清,导致把对真实财产的思维方式运用到虚拟财产。例如张明楷教授认为:“至于人们能否从电脑中取出虚拟财产,则并不重要。……电子记账式国库券是财物,我们现在也无法将它拿到电脑之外。”(64)参见前注,张明楷文。然而,把电子记账式国库券与虚拟财产作对比并不恰当,两者虽然都以电子形式存在,却有着本质区别:国库券是由国家发行的有价证券,而虚拟财产是由公司发行的虚拟经济要素。不能以电子记账式国库券属于财物来论证虚拟财产也属于财物。陈兴良教授也认为,正如当年电力的出现给财物概念带来的冲击一样,虚拟财产的出现同样给财物概念带来了巨大冲击;也正如财物概念最终容纳了电力一样,财物概念同样终将容纳虚拟财产。(65)参见前注,陈兴良文。然而,电力等无体物本质上是有体物的延伸,属于现实世界经济体的重要因素;虚拟财产既不是有体物也不是无体物,只是虚拟世界经济体中的要素。以电力属于财物这一前提无法推出虚拟财产也属于财物这一结论。
2.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分立说
与上述混同说完全相反,分立说认为虚拟世界是完全独立于现实世界的,现实世界不影响虚拟世界,虚拟世界也不影响现实世界。国外学者以魔圈理论来解释虚拟世界的独立性。所谓“魔圈”(magic circle)是指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隐喻性界限,按照魔圈理论,发生在虚拟世界的行为不是真的,不受现实世界法律的制裁。(66)参见前注,Joshua A.T. Fairfield文。在魔圈之内,生命被一套特殊规则管理,人可以起死回生;而在魔圈之外,生命被现实规则管理。(67)Yen-Shyang Tseng,Governing Virtual Worlds: Interration 2.0, 35 Wash. U. J.L. & Pol'y 547, 560 (2011).在魔圈之内的杀人、强奸、抢劫都不会构成真正的犯罪。(68)See Orin S. Kerr,Criminal Law in Virtual Worlds, 2008 U. Chi. Legal F. 415, 418 (2008).我国也有学者认为,虚拟财产在现实世界中没有效用,一把在虚拟世界中削铁如泥的魔剑,在现实世界中什么都不算。(69)参见前注,侯国云、么惠君文。并且,有学者主张:“让虚拟财产永远待在虚拟世界……不是应当把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犯罪化,而是应当把虚拟财产与真实财产的兑换行为犯罪化。”(70)参见前注④,侯国云文。“现实的法律只调整现实世界的社会关系,虚拟世界中的纠纷最好在虚拟世界解决。”(71)陈甦:《虚拟财产在何种情形下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人民法院报》2004年2月12日,第3版。然而,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主张连虚拟财产的影响也必须封闭在虚拟世界,禁止虚拟财产与现实财产进行交易的观点是不可行的。事实上,围绕虚拟财产的交易,各国都普遍存在游戏内与游戏外两个市场。在虚拟财产的交易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强行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画一个“魔圈”的作法并不可行。换言之,虽然虚拟财产仍然处于虚拟世界之内,虚拟财产本身无法从虚拟世界进入现实世界,但由虚拟财产所产生的利益或者影响已经越过虚拟世界而进入了现实世界。因此,对于虚拟财产给现实世界造成的影响,现实法律不能置之不理。
3.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双重性说
这种观点认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既不是混同在一起的,也不是完全割裂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都是围绕人类物质或精神活动展开的,是人类活动的双重世界,两者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一方面,虚拟世界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图形化的三维世界,而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真实的三维世界,所以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具有区别,两者不能混同起来。另一方面,虚拟世界建立在网络之上,而网络又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因此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无法割裂开来。正因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所以对虚拟世界中的活动可以从虚拟与物理两个方面解读。虚拟的解读侧重于用户的体验,从这个角度可以说用户进入虚拟世界,在里面购物,聊天,听音乐;与此不同,物理的解读聚焦于实际发生的事实而不是用户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用户并没有进入虚拟世界,他只是登录了位于世界某处的服务器并收发信息。(72)See Orin S. Kerr, Criminal Law in Virtual Worlds, 2008 U. Chi. Legal F. 415, 418 (2008).
笔者赞同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双重性说,这种观点符合哲学本体论的最新研究成果。长期以来,哲学家们坚持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层结构,但是20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波普尔摆脱世界二层结构的传统观点,提出世界三层结构的理论。他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客观的物理世界(第一世界),第二层是主观的精神世界(第二世界),第三层是客观的精神世界(第三世界)。(73)参见[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78页。这一理论在传统的客观物理世界(第一世界)与主观精神世界(第二世界)之外,提出了客观精神世界(第三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前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混同说和分立说都是以传统的世界二层结构理论为基础的。其中,混同说实际上认为虚拟世界及其虚拟财产属于客观物理世界(第一世界),完全应该适用刑法的规定;分立说实际上认为虚拟世界及其虚拟财产属于主观精神世界(第二世界),不能适用刑法的规定。这两种看法都不合理。虚拟世界既不属于客观物理世界(第一世界),也不属于主观精神世界(第二世界),而属于客观精神世界(第三世界)。(74)参见殷正坤:《波普尔的世界3和虚拟世界》,《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相应地,虚拟财产既不是客观物理世界中的财物,也不是主观精神世界中的思想,而是客观精神世界中的东西。举例来说,“眼中之竹”属于客观的物理世界;“胸中之竹”属于主观精神世界;“笔下之竹”属于客观精神世界。(75)参见向波:《知识、信息与知识产权的对象》,《知识产权》2011年第1期。当这种“笔下之竹”不是画在纸本上,而是通过代码数据的形式显示在网络游戏中时,它就成了所谓的虚拟财产。前述混同说和以混同说为基础的直接保护路径,把“笔下之竹”当作“眼中之竹”并主张窃取“笔下之竹”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前述分立说则把“笔下之竹”当作“胸中之竹”,并主张窃取“笔下之竹”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这两种观点都有混淆不同语境的嫌疑。那么,窃取“笔下之竹”的行为能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呢?这就涉及刑法的调整对象问题。
(二)双重世界中刑法的调整对象
在双重世界中,刑法只能调整现实世界中的财物,虚拟财产属于虚拟世界。这一“落差”决定了刑法对虚拟财产鞭长莫及,无法将其作为调整对象。需要注意的是,认为虚拟财产不是刑法的调整对象,并不意味着刑法不能保护虚拟财产。刑法虽然不能进入虚拟世界调整虚拟财产,但有可能在现实世界中筑起一道堤坝,防止现实世界的人们非法侵入虚拟世界去窃取虚拟财产。实际上,完全可能存在一个“中间层”,刑法通过直接保护“中间层”来间接保护虚拟财产。那么,这一“中间层”是什么?
围绕虚拟财产的保护问题存在三个相关概念,即虚拟财产本身、虚拟财产所生利益、建构虚拟财产的代码数据。我国学者往往把这三个概念混同在一起不加区分,认为虚拟财产同时具有财物性、利益性与数据性。(76)参见前注,陈兴良文。然而,把这三个概念混在一起不利于对刑法调整对象的把握。实际上,“虚拟财产本身”属于虚拟世界,而“虚拟财产所生利益”以及“建构虚拟财产的代码数据”属于现实世界。用个比喻来说,虚拟财产就像虚拟世界中的一棵树,但这棵树的根系(代码数据)却深埋在现实世界的尘土中,这棵树的果实(利益)也会落入现实世界。在这三个概念中,虚拟财产本身不是法律的调整对象,虚拟财产所生利益是民法的调整对象,只有建构虚拟财产的代码数据才是刑法的调整对象。
1.虚拟财产所生利益属于民法的调整对象
如前所述,虚拟财产能够给用户和网游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这种经济利益尚未上升为刑法中的财产法益,因此对这种经济利益,用刑法来保护是多余的,用民法来保护才更加有效。实践中侵犯虚拟财产的案件主要表现为两类。
第一类是行为人侵入游戏运营商的游戏系统私自生成或者复制虚拟财产销售牟利的案件。对于这类案件,游戏运营商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检测到私自生成或者复制的非正常虚拟财产,并能够轻易地删除这些非正常虚拟财产,甚至可以冻结不法行为人的账号。因此,在被害人自己能够有效保护虚拟财产所生利益的情况下,刑法或民法的干预都显得多余。
第二类是行为人侵入用户的游戏账户转移虚拟财产的案件。表面来看,这种损失是用户自身系统漏洞造成的,但用户系统是与整个游戏系统相连接的,既然用户能够通过自身有漏洞的系统登录游戏运营商的游戏系统,反过来也就说明整个游戏系统存在漏洞。换言之,网络游戏运营商没有尽到维护游戏系统安全的义务,应该承担合同不完全履行的违约责任并恢复用户的虚拟财产。(77)参见江波、张金平:《虚拟财产交易纠纷案件的司法审判难点——以网络游戏装备交易纠纷为视角》,张平主编:《网络法律评论(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用户要求游戏运营商恢复虚拟财产的纠纷,法院一般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进而依据我国《合同法》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处理。(78)参见陈惠珍、杜灵燕:《网络游戏服务合同纠纷类型解析》,《法律适用》2010年第4期。例如,在李宏晨诉北极冰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该案的一审、二审两级法院都认为北极冰公司对李宏晨虚拟物品被盗承担保障不力的责任,判决其恢复李宏晨丢失的虚拟装备。(79)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4)二中民终字第02877号民事判决书。又如,在马杰诉盛大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盛大公司应该对用户游戏装备被盗承担保障不力的责任,判决其恢复马杰丢失的游戏装备。(80)参见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07)澄民一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书。国外也有学者认为:“当案件到达法院时,最终用户许可协议(EULAs)以及合同法支配着审判结果。”(81)参见前注,Christopher J. Cifrino文。
2.建构虚拟财产的代码数据属于刑法的调整对象
代码和虚拟财产关系密切,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不是直接作用于虚拟财产本身,而是作用于代码上。代码就是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和传输的数据,(82)《欧洲网络犯罪公约》规定:“计算机数据是指,任何事实、信息或概念的表现形式,该形式采用一个适合计算机系统进行处理的格式,包括能确保计算机执行某项功能的程序。”Convention on Cybercrime of Europe. Budapest. 23. Ⅺ. 2001.根据此规定,代码也属于计算机数据。属于刑法的调整对象。首先,代码架构了虚拟财产的特征。例如,代码架构了虚拟世界的稀缺性。虚拟财产作为电磁记录,技术上原本是可以复制的,但如果允许对虚拟财产进行复制,则虚拟财产本身将不复存在。因此代码工程师必然会编写代码禁止虚拟财产的可复制性,人为地创造出虚拟财产的稀缺性。(83)参见前注,江波书,第37页。又如,代码架构了虚拟财产的可转移性。虚拟财产虽然不可复制,但必须能够转移。虚拟财产的转移,是指代码将一方账户中虚拟财产的电磁记录删除,同时在另一方账户中创建相应的电磁记录。其次,代码与虚拟财产属于同一事物不同层面的东西。网络系统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最底层是“物理”层,包括计算机以及连接计算机接的网线;中间层是“逻辑”层,即那些让硬件运行的代码;最顶层是“内容”层,即通过网线传输的有意义的东西,包括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84)参见[美]劳伦斯·莱斯格:《思想的未来:网络时代公共知识领域的警世喻言》,李旭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人们所能够感知的游戏角色、游戏装备、游戏道具等虚拟财产都处于网络系统的“内容”层,这种内容本身属于思想的产物,属于客观的精神世界,不是刑法调整的对象。建构虚拟财产的代码居于网络系统的中间层,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是刑法的调整对象。最后,窃取虚拟财产的行为不能直接作用于虚拟财产本身(行为人无法直接把虚拟财产拿走),而只能作用于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代码数据。行为人只能通过对计算信息系统中的数据进行复制、删除、修改、增加等操作,才能将他人账户中的虚拟财产转归自己。因此,刑法只有通过对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保护来间接保护虚拟财产,这是刑法保护虚拟财产的唯一路径。
四、虚拟财产间接保护路径的提倡
所谓间接保护路径,是指刑法只能通过直接保护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来间接保护虚拟财产。那么,刑法应该怎样保护与虚拟财产相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呢?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意见认为:“利用计算机窃取他人游戏币非法销售获利行为目前宜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定罪处罚。”(85)喻海松:《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利用计算机窃取他人游戏币非法销售获利如何定性问题的研究意见》,载张军主编:《司法研究与指导》(2012年第2辑,总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页。我国学界也有学者持这一观点。(86)参见刘明祥:《窃取网络虚拟财产行为定性探究》,《法学》2016年第1期;梁根林:《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人民检察》2014年第1期。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失片面。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处罚的是获取数据的行为。如果仅仅获取数据,而不对数据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等破坏性操作,是不可能侵犯虚拟财产的。因此,应该以“破坏数据罪”而不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来保护虚拟财产。以下笔者将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简称为非法获取数据罪。(87)这里的“破坏数据罪”是指我国《刑法》第286条第2款规定的行为类型。我国《刑法》第286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行为。其第1款规定的行为是“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这种行为相当于《欧洲网络犯罪公约》中的“系统干扰罪”(System interference)。其第2款规定的行为是“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这种行为相当于《欧洲网络犯罪公约》中的“数据干扰罪”(Data interference)。我国司法实践将这两类行为都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笔者认为这种罪名归纳存在问题,第一种行为可以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第二种行为应该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以下简称:破坏数据罪)。
(一)“非法获取游戏账户+转移虚拟财产”构成非法获取数据罪与破坏数据罪的牵连犯
游戏装备、游戏币等虚拟财产都被保管在游戏账户之内,因此实践中的案件多表现为先获取游戏账户,然后转移账户中的虚拟财产。获取游戏账户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植入木马程序等技术手段获取;二是从他人处购买。第二种行为方式的定性放在下文论述,这里先分析第一种行为方式的定性。对于行为人通过技术手段非法获取游戏账户并转移虚拟财产的案件,我国司法实践多认定为非法获取数据罪。例如:董勇、李文章通过在网上挂载木马程序的方式非法获取网络游戏“九阴真经”的客户账号9000余组,并将这些游戏账户内的虚拟财产转移至自己账户出售牟利,被认定为非法获取数据罪。(88)参见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3)姑苏刑初字第0273号刑事判决书。又如,叶某先后在被害人郑某、董某、章某的电脑中植入木马程序,获得被害人游戏账号和密码,随后将郑某6亿多两、董某1亿多两、章某11亿多两游戏银子转卖牟利,被认定为非法获取数据罪。(89)参见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4)金婺刑初字第28号刑事判决书。再如,刘某在钓鱼网站发布木马程序获取他人游戏账号信息2700余组,并从中盗取玩家游戏“欢乐豆”出售牟利,被认定为非法获取数据罪。(90)参见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人民法院(2014)浦刑初字第0187号刑事判决书。再又如,刘某通过互联网外挂木马程序,并在游戏内“喊话”,吸引网络游戏“九阴真经”的玩家点击木马程序,获取游戏玩家的账号和密码9267组,并转移游戏玩家的虚拟财产,被认定为非法获取数据罪。(91)参见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5)姑苏刑初字第00284号刑事判决书。
笔者认为,这些判决都存在以偏概全和评价不全面的弊端。在这类案件中,一般会有两个行为,行为人首先采取技术手段非法获取游戏账号和密码,然后从被害人的账户中转移虚拟财产。前一行为属于“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后一行为属于“破坏数据”的行为。所谓获取,主要表现为下载、复制、频繁地浏览。(92)See Liên Payne and Julie Bauman: Cloud Computing Legal Deskbook (Sheppard Mullin, 2017), § 12:1.获取行为“仅限于非法复制或者直接使用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数据,而没有采取植入病毒、埋伏数据炸弹、直接删除、随意修改等方式对数据进行破坏”。(93)赵秉志主编:《刑法修正案(七)专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页。可见,获取数据的结果只是获得了该数据的复制件,并不会导致计算机信息系统失去该数据。如果一方得到某数据的同时,相对方必然失去该数据,那么该行为就不再是“获取数据”而是“破坏数据”了,即一方增加了数据,而相对方的数据被删除或者修改。可见,转移虚拟财产的行为不是获取数据,而是破坏数据。这种行为已经超出非法获取数据罪的行为类型,而是落入了我国《刑法》第286条第2款的破坏数据罪的适用范围。上述判决都只是对获取数据进行了评价,遗漏了对破坏(删除、修改、增加)数据进行评价。
进一步看,行为人利用技术手段非法获取游戏账户并转移虚拟财产的案件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行为人获取游戏账户后随即修改密码并转移其中虚拟财产;二是行为人获取游戏账户后随即转移其中虚拟财产,并不修改密码。无论哪一种情况,案件过程都包括获取数据与破坏数据两个行为。在整个案件过程中,获取数据是手段行为,破坏数据是目的行为,两者之间形成牵连关系。因此,对这类案件应该根据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从一重处罚,即以破坏数据罪处罚,而不是以非法获取数据罪处罚。需要注意的是,切不可把“获取数据”中的获取与“获取虚拟财产”中的获取等同起来。前一个“获取”是指通过下载、复制、浏览等方法取得数据复制件,后一个“获取”是指通过删除、修改、增加数据等手段取得对虚拟财产数据的控制权。不能因为都有“获取”一词,就把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认定为非法获取数据罪。
(二)“收购游戏账户+转移虚拟财产”构成破坏数据罪而不是其他犯罪
如果行为人不是自己非法获取游戏账户,而是收购他人非法获取的游戏账户,然后转移其中的虚拟财产,应该如何处理呢?对此,我国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议较大。例如,被告人岳曾伟从他人处购得8.2万余个游戏账号及密码,然后登录游戏账户窃取其中游戏金币7.9亿余个,销售游戏金币违法所得72万余元。一审法院判决岳曾伟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二审法院判决岳曾伟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岳曾伟案)(94)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宿中刑终字第0055号刑事判决书。学界的有力观点则认为,岳曾伟的行为应该构成盗窃罪。(95)参见前注,陈兴良文;前注,张明楷文。
笔者认为,上述定性都值得商榷。首先,定性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一审判决只处罚了行为人收购游戏账号和密码的行为,而没有评价行为人转移游戏账户中游戏金币的行为。在整个案件中,转移游戏金币才是处罚的重点,收购游戏账户只是转移游戏金币的预备行为。其次,该案也不应定性为盗窃罪,以盗窃罪论处采取的是前述直接保护路径。从岳曾伟案的行为对象来看,游戏币或者游戏账号及其密码都无法解释为财物。从行为方式来看,转移虚拟财产的行为只是一种“利益转移”而不是“占有转移”,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最后,定性为非法获取数据罪的二审判决存在对“获取”的错误理解。如前所述,“获取”仅限于取得数据的复制件。行为人取得虚拟财产的过程并不是获取数据,而是在破坏(删除、修改、增加)数据,因此应该被评价为破坏数据罪而不是非法获取数据罪。
(三)“雇员进入公司游戏系统+私自生成或复制虚拟财产”构成破坏数据罪而不是其他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85条第2款的规定,非法获取数据罪必须采取“侵入或者其他技术手段”。通说认为,侵入“是指未经授权或者他人同意,通过技术手段进入计算机信息系统”。(96)朗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91页。换言之,侵入必须同时具备非法性(未经许可)和技术性(利用木马程序等技术手段),两者缺一不可。游戏公司的雇员利用职务便利进入游戏系统的行为并没有利用技术手段,不符合非法获取数据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对于雇员进入游戏系统私自生成或复制虚拟财产的行为如何定性,理论与实务存在分歧。司法实务界倾向于把这种行为认定为职务侵占罪,(97)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6)浦刑初字第929号刑事判决书(王一辉职务侵占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刑终字第66号刑事判决书(雒彬彬职务侵占案)学界既有学者支持职务侵占罪的定性,(98)参见前注,张明楷文。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99)参见前注,刘明祥文。或者不构成犯罪。(100)参见张弛:《窃取虚拟财产行为的法益审视》,《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8期。
笔者认为,利用职务便利并非利用技术手段,雇员的行为不构成非法获取数据罪;虚拟财产不是财物,雇员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复制游戏装备或游戏币销售牟利的行为不同于复制发行计算机软件的行为,雇员的行为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认为雇员利用职务便利取得虚拟财产不构成犯罪的观点也不合理。这类案件应该以破坏数据罪论处。
首先,雇员进入游戏系统的行为具有非法性。雇员利用职务便利进入游戏系统的行为虽然不具有技术性,但也不像有的学者所言属于“合法进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以计算机犯罪论处”。(101)参见前注,张明楷文。对于雇员进入其任职的公司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能否认定为非法,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未经许可”。对此,理论与实务存在两种观点。狭义说认为,只要雇员在开始时被允许进入计算机,就已经取得了授权,即使其随后不正当地使用或滥用了雇主的机密数据,也不构成未经允许的非法行为。广义说认为,当雇员滥用或者窃取公司数据时,他就违背了雇主利益,并因此失去了雇主的授权而具有非法性,即使他最初的进入是被允许的。美国的绝大多数巡回法庭采用广义说。(102)See Thomas E. Booms, Hacking into Federal Court: Employee "Authorization" Under the Computer Fraud and Abuse Act, 13 Vand. J. Ent. & Tech. L. 543, 551 (2011).因此只要对“未经许可”采取广义说,则不仅游戏公司工作人员私自生成或者复制虚拟财产销售的行为具有非法性,而且其进入游戏系统的行为也具有非法性,完全可以成立破坏数据罪。破坏数据罪只需要侵入行为的非法性,而不像非法获取数据罪那样同时要求侵入行为的技术性。
其次,私自生成或复制虚拟财产的过程就是修改或增加数据的过程。例如,王一辉利用职务便利进入盛大公司游戏系统打开“热血传奇”服务器6000端口,通过增加、修改数据库Mir.DB文件中的数据,在共同犯罪人金珂创建的游戏人物身上增加或修改游戏武器及装备,然后由金珂将游戏人物身上的武器及装备通过网站或私下交易出售给其他游戏玩家。后来王一辉觉得这一操作方法比较麻烦,就让金珂从网上下载了“热血传奇”私服游戏服务器端,并生成伪造的数据包,将每次修改后的数据包发送到服务器,王一辉在收到数据包后,提取数据信息再传送到数据库中,在游戏人物的身上增加或修改游戏武器及装备。(103)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沪一中刑终字第285号刑事判决书。可见,王一辉上述两种操作行为都是修改或增加数据的行为,完全符合破坏数据罪的构成要件。然而,法院判决王一辉构成职务侵占罪。这一定性很值得商榷,法官完全将财产犯罪的传统思维照搬到了现代网络犯罪的法律适用中。
(四)“抢劫虚拟财产”构成破坏数据罪的间接正犯而不是抢劫罪
实践中以暴力、胁迫手段“抢劫”虚拟财产的案件时有发生。例如,孙洋等四人在网吧对他人进行殴打、威胁,迫使被害人从其游戏账户转出100个Q币、1100余万个游戏币和其他游戏装备。该四人分别用抢来的Q币和游戏币对自己的游戏装备进行了升级。法院判决孙洋等人构成抢劫罪。(104)参见霍仕明、张国强:《虚拟财产遭遇真实抢劫的量刑困惑》,《法制日报》2009年6月4日,第9版。荷兰也发生过类似案例,两名少年用刀威胁一同学把虚拟物品转移到他们账户上,法院判决两被告构成贼盗罪(相当于我国的抢劫罪)。(105)参见前注,Joshua A.T. Fairfield文。我国也有学者赞同抢劫罪的定性,认为“这种行为并没有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也不符合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构成要件,更没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106)同前注,张明楷文。
笔者不赞同抢劫罪的定性。首先,抢劫罪属于财产罪中的第一重罪,行为人为了得到几个游戏币或游戏装备就被判处抢劫罪,一般人难以接受。其次,暴力、胁迫等手段虽然不是技术手段,不符合非法获取数据罪的构成要件,但并非不能构成破坏数据罪。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强迫被害人自杀、自伤、自损的,构成相关犯罪的间接正犯。(107)参见前注,张明楷书,第403页。因此,强迫被害人对自己游戏账户中的数据进行删除、修改的,完全可以成立破坏数据罪的间接正犯。
(五)“单纯获取游戏账号及密码”不是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可以构成非法获取数据罪
单纯获取游戏账号及其密码的行为不是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因为,如果行为人只是单纯获取他人游戏账号及密码,既没有修改密码也没有转移账户中的虚拟财产,就不可能造成侵犯他人虚拟财产的危害后果。那么,如何认定这种行为的性质呢?从行为方式来看,获取账号及其密码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木马程序等技术手段;二是通过偷窥、监控等非技术手段。第二种手段所能获得的账号和密码相当有限,可能会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但不会构成财产罪或计算机犯罪。第一种行为方式应该以非法获取数据罪论处。具体来说,如果行为人获取账号及密码后又修改了密码或者转移了账户中的虚拟财产,则如文所述,按照非法获取数据罪与破坏数据罪的牵连犯,以破坏数据罪论处。如果行为人获取游戏账号及密码后将其出售给他人以转移虚拟财产,在行为人与收购人之间事前有通谋的情况下,成立破坏数据罪的共同犯罪;在行为人与收购人之间没有通谋的情况下,出售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或者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单纯的获取行为构成非法获取数据罪。我国司法实践对于这类行为的定性是准确的。例如,王某将木马程序上传到网页,随玩家点击后植入其计算系统,继而利用该木马程序获取“CSOL”、“魔域”等网络游戏玩家的账号和密码并予以销售,违法所得50余万元,被法院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108)参见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2013)台临刑重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又如,崔为丰通过在服务器上植入木马的方式,窃取DNF(地下城与勇士)、LOL(英雄联盟)等的QQ游戏账号和密码48万余组,并将所得账号和密码销售牟利,违法所得人民币7万余元,被法院认定为非法获取数据罪。(109)参见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苏1291刑初56号刑事判决书。
五、余 论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刑法以保护个人法益为核心,权利人对财产的占有方式以及犯罪人对财产的侵害方式都是可以直观感受的。在网络社会中,个人只是庞大互联网系统中的一个端口,个人法益汇入了网络安全法益,网络安全法益成了网络社会的核心。根据我国《网络安全法》的规定,网络安全的内涵包括“网络处于稳定可靠运行的状态”以及“网络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因此,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问题应该摆脱财产犯罪的传统思维惯性,采用网络犯罪的思维方式,立足于网络安全法益来寻找解决路径。可用预见,随着网络社会的深入发展,未来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新型网络犯罪(如窃取大数据、窃取云计算服务等)。对于这些网络犯罪,人们也应该放弃财产犯罪的传统思维方式,在保护网络安全法益背景下探索刑事司法或立法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