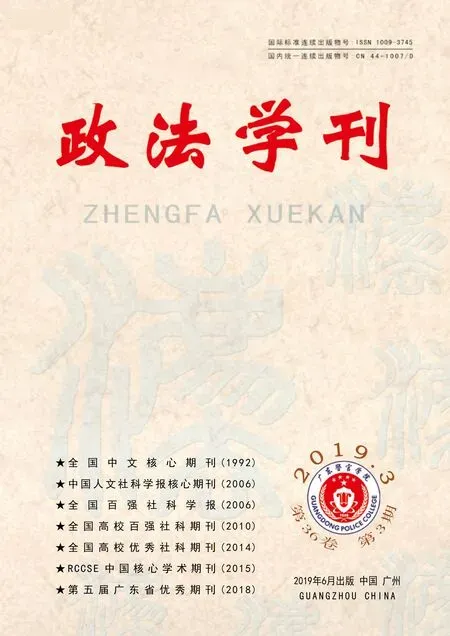国家管辖豁免的转向
——以“一带一路”工程商业争端为视角
张连举,袁 茜
(1. 广东警官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 广州 510232;2. 南开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071)
一、新近“一带一路”工程商业争端案例是否表明对豁免立场转变
自2015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与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至今,历经四年的变迁发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类基建项目为众多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腾飞的翅膀,但与此同时,由于工程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①可能面临的风险包括东道国的政治环境变化产生的政治风险、极端民族主义活动等文化风险、战争等安全风险、国企和央企内部管理风险、金融危机等市场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等等。[1],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经常遭遇激烈的竞争和严峻的挑战,承受着巨大经济损失的压力。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除了事前风险防范,中国企业在海外承包项目执行过程中,与签署合同的东道国产生纠纷以后,能否在我国法院起诉?东道国政府机关能否援引国家司法管辖豁免?国际法所说的国家司法豁免,是指根据国家主权、独立、平等、尊严等理由,国家的行为和财产免受外国法院管辖。②国家的司法豁免原则的内容,包括以下三点:(一)一国法院不受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的诉讼,除非后者同意;(二)外国可以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法院可以受理被告所提出的同本案有直接关系的反诉;(三)即使外国在法院败诉,他也不受强制执行。本文所论述的是狭义的国家司法豁免,是指非经一国明示同意,其他国家法院不得对以该国为被告或者以该国财产为诉讼标的的案件行使司法管辖权。[2]按照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绝对豁免立场,一国法院无权受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的诉讼,这从根本上限制了我国企业通过本国法院获得救济的途径。但查阅有关司法案例,最近几年我国法院在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已经悄然发生转变。2019年2月,在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诉埃塞俄比亚公路局侵权责任纠纷案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9] 京民初字第225号民事裁定书。中,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埃塞俄比亚公路局(Ethiopian Roads Authority)没有履约保函项下的付款请求权却滥用请求权、可能存在欺诈性索兑履约保函为由,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支付独立保函项下的款项的申请,法院经审查,裁定中止银行向埃塞俄比亚公路局支付保函项下的款项,这一案件涉及我国对于埃塞俄比亚公路局是否具有司法管辖权的问题。此前的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诉叙利亚输电总局(PETE)买卖合同纠纷案②参见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 衡中法民三初字第84号民事裁定书。、成都华川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诉格鲁吉亚共和国司法部等信用证欺诈纠纷案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 最高法民终字第143号民事裁定书。都涉及此问题。更早的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诉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侵权责任纠纷案④中国海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外”)牵头组成的联合体于2009年9月中标波兰A2高速公路A、C标段,根据合同,中国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德意志银行为项目提供无条件见索即付(First Demand with No condition)保函,受益人无需证明违约,只要出具索赔声明,银行就应承担付款责任,其中中方银行提供了约3000万美元的担保金。在合同执行过程中,由于联合体与业主波兰公路管理局存在重大分歧,中海外联合体于2011年6月初决定放弃该项目。6月13日,波兰公路管理局宣布解除与中海外联合体签署的工程承包协议,并于合同终止后向提供独立保函的银行提出支付银行担保金的要求。中海外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保函欺诈构成侵权为由起诉波兰公路管理局,认为索赔行为将造成其财产权益损失,请求终止并解除担保银行的担保责任。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 一中民初字第13687-2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中海外案”)中,虽然被告波兰国家公路及高速路管理局(以下简称“波兰公路局”)提出了管辖权异议,但北京一中院以侵权行为地在北京为由予以驳回,并对外国政府机关行使了管辖权。
上述案件的特殊性在于争端主体同时涉及到了私人主体和国家,原告均为国内企业,被告都是能够代表一国的外国政府机关。我国法院审理此类案件,首先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我国法院是否享有对被告为外国国家政府的案件的司法管辖权?以上几个案例中,法院虽在裁定书中没有具体论述国家豁免权问题,但都对一个正式的外国政府行使了管辖权。这至少表明,我国法院在实践中已经实际放弃了传统的绝对豁免理论,我国司法实践已经走在了国家立法的前面,对限制豁免论进行了有益探索。考虑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往愈加密切的现实,国内企业起诉东道国的基建项目商业纠纷将不可避免。然而,受到绝对豁免立场的约束,一方面我国限制了国内企业通过本国法院进行救济的途径而无益于中国企业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也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惑和障碍,如前述案件,各级法院虽然都对外国主权机构行使了管辖权,但是都没有具体论述如何解决国家豁免问题,法官对这一问题的回避态度与我国法律对国家豁免问题缺少明确的依据和理论研究的模糊状态有关。以此为契机出台一部明确、可操作性强的法律,解决“无法可依”的现状实属必要;此外,在正式立法前,还需要澄清符合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的国家豁免的基本理论。
二、从国际趋势看我国转向限制豁免立场的必要性
(一)限制豁免论的孕育和发展
20世纪以前,国家职能集中于政治、军事、外交等非商业职能,绝对豁免在国际法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这一时期法院遇到的案例主要涉及国家的军舰和国家所有、经营的船舶纠纷,例如“比利时国会号”案。但实际上,在绝对豁免盛行的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新理论的倾向,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法院在一战之前就采取了限制豁免的立场,外国国家在纯私法范围内不能主张豁免;[3]在一些典型案例中,也能看到不同法官的异见,如美国“交易号”案。⑤1812年“交易号”判词中曾指出:在君主的私人财产与支撑君主权力且维护国家尊严和独立的武装力量之间有着明显区别。一个君主,如果在外国取得了私人财产,可因此认为他已将该财产置于该国的领土管辖权之下,且已放弃了本人的君主身份而取得了私人身份,但就其拥有的武装力量的任何部分而言,则不能作这种假定。[4] 29
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国家从事商业活动愈加普遍,参与民商事交往的国家具有二重身份,既是民商事法律关系当事人又是国家主权者。在私人主体与外国国家的商业纠纷中,绝对豁免理论受到普遍质疑,平衡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限制豁免理论得到发展。[4] 143为使私人主体权利能够得到法院救济,一些国家通过国内立法、判例和国际条约对国家管辖豁免予以限制。[5] 149
在国家豁免问题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普通法系国家率先以成文法方式规定了司法管辖豁免的例外情形,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多以判例形式确立了向限制豁免主义的转型。美国从政府利益主导到以法律保障,完成了向限制豁免主义立场的转变。初期,在涉及国家豁免的案件中,国务院的意见对法院有重要影响力[4] 61,但政府意见的不稳定性导致法院判决出现前后反复不一的混乱状况。1952年,美国国务院代理法律顾问泰特宣布“对某类案件不再授予主权豁免”,主张对一国的私行为不予豁免。[6] 1171976年,美国率先通过《外国主权豁免法》,以立法确认进入限制豁免理论的新时期。英国在经历了法官之间的多次激烈交锋后,通过1978年《国家豁免法》,完成了这一“行动迟缓”的转变。随后,英联邦的大多数国家都受到其影响制定限制豁免原则的成文立法。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法国、德国则至今没有专门的国家豁免立法,法国国内法对国家私法行为和公法行为的区分为解决国家豁免问题提供了思路。[7]德国法院审判的“伊朗王国案”标志着德国放弃了绝对豁免理论。[7]不仅英美、欧洲大陆国家大多采限制豁免论,我国的亚洲近邻日本也在2009年正式通过《日本外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法》,完成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向国内法的转化;韩国则通过一系列法院判决确立了限制豁免的立场。[8]
(三)限制豁免正在成为习惯国际法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丑)项,习惯国际法是国际法的重要渊源。随着政府经济职能增强,国家对外民商事活动发展,为解决国家与私人主体之间的纠纷,各国逐渐转向限制豁免立场,那么,限制豁免是否已经或者正在形成习惯国际法?依据主流观点,习惯国际法由国家实践(state practice)和法律确信(opinio juris)两要素构成。国家实践须是各国反复多次的具有一致性的行为,法律确信作为主观要素需借客观表现形式加以识别,例如国内法院的判决、以国家名义发表的公开声明等。国际社会实践方面,目前采取限制豁免理论的国家与采取绝对豁免理论的国家相比,前者数量已明显超过后者。[9] 1121982年联合国所调查的一百五十个国家中只有十几个明确支持绝对豁免[4] 228,其他多数国家,无论原创还是效仿,都已转向限制豁免论。①其中,亚洲国家有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老挝、叙利亚、科威特;拉美国家有巴西、委内瑞拉、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特里尼达和多巴哥;非洲国家如苏丹;西欧国家如葡萄牙。[10] 141-142由此可初步得出限制豁免成为习惯国际法的结论。进一步讲,成文条约可对习惯国际法进行编纂从而成为习惯国际法存在的重要证据。限制豁免论成文条约的最早尝试是1926年《统一国有船舶豁免的某些规则的国际公约》,认为国有商船和私人一样应当承担责任。[4] 631972年《欧洲国家豁免公约》开放签署,限制豁免论在欧洲进入区域一体化阶段,公约规定国家的“管理权行为”不属于国家司法管辖豁免范围,从而确立了司法管辖的限制豁免主义立场,公约也是欧洲各国对限制豁免论实践经验的一项证据。随着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全球性的有关国家豁免的国际公约应运而生。2004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在明确承认国家豁免原则的同时,规定了“不得援引国家豁免的诉讼”,清楚地说明国家豁免是有限度的。虽然各国对公约内容存在严重分歧,但各国争议实际不在于采取绝对豁免还是限制豁免立场,而是限制豁免的范围和程度问题,例如确定商业合同的标准是合同目的还是性质,国家豁免是否受一般国际法的有关规则制约等。因此,公约批准国未达生效数量不能否证限制豁免论正在成为习惯国际法的事实。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诸如中海外案的涉及国家关系豁免问题的工程商业纠纷可能还会出现,对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和认定有助于我国正确理解和适用习惯国际法以解决争议。[11]总之,从国际趋势看,我国有必要适时转向限制豁免论,积极解决国际商事争议。
三、适时转向限制豁免立场的内在动因
在一国对外国政府的管辖豁免问题上,国际趋势与国内法治紧密相连。我们应在把握国际形势基础上,研究如何更好的维护国家的利益,因此,需要选择适应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的国家管辖豁免理论。
从司法实践经验看,绝对豁免立场不是维护而是损害我国利益。一方面,我国法院受理以外国国家或政府为被告的司法实践极少。1927年李柴爱夫兄弟诉苏维埃商船队案是涉及国家豁免问题的最早探索。[12] 685-7002008年“芬兰大使馆案”未予受理。日本在二战期间对我国公民实施的强迫劳动、买卖慰安妇等行为,无论从严重侵犯人权还是从具有商业营利目的角度都不宜适用国家豁免[13],但是这些民间受害者在中国法院对日本国提起索赔诉讼的案件都没有被我国法院受理。2008年美国对冲基金公司诉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铁集团案①参见香港高院杂项案件2008年928号、高院民事上诉案件2008年373号和民事上诉案件2009年43号、终院民事上诉案2010年第5号,第6号及第7号。(以下简称“刚果(金)豁免案”)被解读为我国坚持绝对豁免论。另一方面,虽然我国政府旗帜鲜明主张绝对豁免理论,但我国在国外法院受诉的案例颇多,例如两航公司案②Jackson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96 F. Supp. 386 (N.D. Ala. 1984).、湖广铁路债券案[14] 349-350、仰融案③Yang Rong and Broadsino Company,Ltd.v Liaoning Provincial Government,362 F.Supp.2d 83 ( D.D.C.2005 ).、莫里斯诉中国案。④Morris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478 F. Supp. 2d 561 (S.D.N.Y. 2007).最近,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被美国法院以“藐视法庭”裁定缴纳罚款。[15]从表面上看,绝对豁免立场使我国在成为被诉当事人时得以拒绝接受任何外国法院的管辖权,但实际并非如此。国家司法管辖豁免在国际法主流观点上被认为是对法院地国管辖权的一种限制[16],由于管辖权问题属程序问题,适用法院地法律处理是简便易行的通常做法,对外国国家及其财产是否具有管辖权的决定权属于该国法院。虽然被诉当事国可以以本国坚持绝对豁免为由主张国家豁免,但其抗辩不具有决定作用,法院以及法院地法律对此具有决定性的优越地位。[17]从前述湖广铁路债券案、莫里斯诉中国案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美国法院撤销判决的理由是“《外国主权豁免法》不具有溯及力”,“诉讼时效经过”,并不意味着其认可我国主张的绝对豁免理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我国坚持绝对豁免论,不能受理以他国为被告的案件,而采限制豁免论的国家则在本国法院接受对我国提起的诉讼,或对我国财产进行扣押。[18]
近年来,我国参加的承认限制豁免论的国际条约和国内一些零散立法表明,我国绝对管辖豁免态度有所松动,正在发生符合国情的缓慢转向。国际条约方面,我国批准的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专用于政府非商业性服务的船舶的豁免权;批准的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只承认用于非商业目的的国有船舶、国有货物的豁免权;我国积极参与起草并签署《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实际承认了限制豁免理论的合理性,且负有“不得采取足以妨碍公约目的和宗旨的行动”的义务;2016年,我国牵头筹建的亚投行正式开业,其“基本大法”《AIIB协定》表明了限制豁免立场。⑤规定银行为筹资而通过借款或其他形式行使的筹资权、债务担保权、买卖或承销债券权或有关权力时不享有豁免。国内的一些零散立法也见证了我国国家豁免态度谨慎的发展变化。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将从事商业活动的外国政府船舶规定为豁免例外;2005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中央银行财产司法强制措施豁免法》(以下简称“《强制措施豁免法》”),以外国中央银行财产的绝对执行豁免权为原则,放弃豁免为例外。⑥但其内容仅关于在法院诉讼中免于强制措施的豁免,未涉及管辖豁免,我国的自然人和法人不能依该法向我国法院提起对他国的诉讼。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涉及特权与豁免的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表明,经最高人民法院同意,我国法院有受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或者第三人的案件的可能性,这可视为对限制豁免理论的承认。
为了解目前我国学术主流观点,笔者对中国知网上有关国家豁免理论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共检索到相关文献58篇。经过统计,支持我国采取限制豁免立场的有49篇,占绝大多数。其中,郭玉军教授、徐锦堂教授旗帜鲜明地认为限制豁免论正确处理了国际公法关系、国际私法关系[16],杨玲教授通过对欧洲国家豁免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反思我国坚持绝对豁免论对国家利益和国家财产保护无益[7],何志鹏教授、都青博士则从日本、韩国比较法角度建议慎重考虑国家豁免适用范围[8],莫世健教授、陈石博士从亚投行协定的限制豁免立场对中国绝对豁免立场的挑战考虑中国适时转换立场[19]明确支持我国采取绝对豁免立场的文献只有三篇,其中《绝对豁免的主权论支持》一文指出限制豁免主义有其致命的弱点和不可协调性[19],另两篇文献认为绝对豁免与限制豁免之间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支持混合标准;还有四篇文献没有明确的态度。可见,从中国知网有关国家豁免理论的文献数量这一角度看,建议我国采取限制豁免立场的观点已经成为主流。
经过以上分析,目前我国从绝对豁免论转向限制豁免论已经不存在立法和理论障碍,那么,刚果(金)豁免案中人大释法是否导致我国国家豁免政策的发展因此中断呢?笔者认为,第一,严格来讲,刚果(金)豁免案是香港地区的法院所审理的案件,且只是孤立的个案,不具有普遍意义,不能阻断我国长期的国家豁免政策发展进程。第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正面回答我国国家豁免问题采取是绝对豁免立场还是限制豁免立场这一问题[19],即从全国人大常委的释法不能直接得出全国人大支持绝对豁免的结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1年8月26日作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解释,该解释只是表明国家豁免问题属于国家对外关系中的外交事务,香港作为中国的地方行政单位,应当和中央政府采取的原则和政策一致。[4] 128这与绝对豁免、限制豁免理论的采纳严格来说是两个问题。虽然从结果看,香港法院最终判决对该案无司法管辖权,被解读为全国人大支持绝对豁免理论,但该解释并非直接针对绝对豁免、限制豁免理论的争议,认为全国人大支持绝对豁免论是根据该解释的上下文推断而来。因此,该案也不构成我国采限制豁免论的障碍。
四、发挥限制豁免立法对完善“一带一路”工程商业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
(一)立法建议:制定限制豁免立场的单行法
前已述及,无论从国际形势还是国内法治发展来看,目前我国应当适时转向限制豁免论已经成为主流观点,接下来我们需要思考实现国家豁免立场转变的具体途径。首先,通过颁布统一的国家豁免立法明确我国限制豁免立场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笔者认为,国家豁免立法需要规定国家豁免的一般原则、司法豁免放弃、不得援引国家豁免的各种情形、司法程序、执行豁免等各领域、全方面的内容,而“一带一路”框架下各类基建项目的开展只是近几年的事情,所遇到的工程商业争端中涉及限制豁免论也仅是国家司法管辖豁免的一个具体领域,尚不足以支持制定一部统一、全面的国家豁免法。[21]从比较法的角度看,世界各国放弃绝对豁免论,转向限制豁免论的历史进程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反复和“新学说的痛苦的分娩过程”,因此,我国制定统一国家豁免法的倡议还为时尚早。其次,根据前文介绍,大陆法系国家多以判例形式确立了向限制豁免主义的转型,那么,我国能否通过判例积累经验,由法院推动规则的建立?事实上,我国的典型案例制度和案例指导制度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填补法律空白的作用,但是,作为成文法传统深厚的国家,在我国即使是指导性案例也必须以既有法律为据,结合案情做出,其产生天然地受控于既存立法之下,加之实践操作中的困难,在我国以判例创设限制豁免规则尚存在障碍。[22]因此,在颁布统一的国家豁免立法前,通过制定单行法的方式解决我国“一带一路”走出去过程中的国家管辖豁免问题不失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
单行立法可以是一个针对具体的“一带一路”项目领域内东道国政府主权豁免问题的法律。在主体上,主要适用于“一带一路”项目争端中被私人主体起诉的东道国政府,“一带一路”项目是一个较为开放的概念,还应当明确界定东道国政府的范围。在内容上,应当参照《公约》,主要以行为性质、辅之以行为目的为标准,将“一带一路”项目中东道国国家行为区分为主权行为和商业交易行为。参照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的“一带一路”工程商业争端案例,确认东道国政府参与项目股权投资、签订项目工程协议、债务担保等行为为商业交易行为,东道国政府在行使这些权利时不享有豁免。凡属这类案件,在中国境内,可向有充分管辖权的主管法院对东道国政府提起诉讼,这也符合商事平等原则。此外,可以参考《强制措施豁免法》,规定豁免的形式包括诉讼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认可东道国政府以明示方式放弃豁免的法律效力,在东道国政府已经明示接受中国司法管辖的情况下,不能再援引国家管辖豁免。总之,以简洁明了、操作性强的条文解决“一带一路”工程商业争端中法院“无法可依”的问题。
(二)立法对完善“一带一路”工程商业争端解决机制的意义
制定限制豁免原则的单行立法,能够为“走出去”过程中与东道国产生工程商业纠纷的企业在我国法院获得权利救济提供可能性,为国内司法层面“一带一路”工程商业争端的解决提供保障,从而助力构建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与国内司法机制相结合的“一带一路”区域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近年来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建项目的蓬勃发展,也发生了不少涉外工程商业争端,其中私人主体之间的争端由私法相关规定解决,而国内企业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由于涉及外国国家主权问题则较为复杂。我国企业如何在工程商业争端中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结合《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企业可以考虑“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既可以利用磋商、和解、调解等非对抗的“东方智慧”,也可以提交国际仲裁。另外,对我国企业来说,法院诉讼也不失为一种具有较大优势的纠纷解决方式,不但诉讼方便,可以申请法院采取财产或证据保全等措施,而且具有上诉纠错机制。[15]
最高法《若干意见》指出,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协议选择司法管辖的权利。在中海案中,抛开合同中删除ICSID仲裁纠纷处理条款的签约管理失守问题,中海外和波兰公路管理局选择国内法院的司法管辖协议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受到充分尊重。评论者提出,合同约定由波兰法院管辖,适用波兰法律解决纠纷对我国企业明显不利,但退一步讲,按照我国以往的绝对豁免立场,我国法院不会受理以外国政府为被告的案件,该合同也不可能约定由我国法院管辖,这更造成了中国企业“里外吃亏”的局面。而如果确立限制豁免论,在合同签订阶段,约定由中国法院管辖就具备正当性和可能性,这至少为当事人协议由中国法院管辖提供了选择权和法律依据;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发生工程商业争端,引起诉讼后,企业可以在我国法院起诉外国政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总之,“一带一路”区域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互为补充的纠纷解决机制,限制豁免立法有助于国内法院为“一带一路”工程商业争端的解决提供国内司法层面保障。
另一方面,在处理“一带一路”工程商业争端时,法官可以以法为据,“以理服人”,提高裁判文书质量。在本文首段介绍的案件中,法院虽然都对外国主权机构行使了管辖权,但是都没有具体论述国家豁免问题。例如波兰案中涉及我国法院能否受理被告为外国国家机关案件的问题,因此如何论证本案中外国国家政府不享有司法管辖豁免,便成为法院首先应当回答的问题。遗憾的是,法官没有进行任何说理分析,便直接根据侵权行为地认定我国法院有管辖权,这实际上是回避了国家司法管辖豁免问题。退一步讲,即使法官认为波兰高速公路管理局没有主张豁免权表明其愿意接受司法管辖,也应当论证其是否以实际行为默示放弃了管辖豁免权,而不应避而不谈。在以单行立法的形式解决了“无法可依”的问题后,法官可以在判决书中写明:豁免属于管辖权的限制问题,处理管辖权问题属于程序问题,根据国际社会惯常做法,适用法院地法律。根据我国关于“一带一路”项目领域内东道国政府主权豁免问题的单行立法,东道国政府行为属于商业交易行为,不享有管辖豁免。而后再论证管辖权协议的成立和效力,我国法院是否取得合法管辖权的问题。另有学者提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各国法治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当事人不愿意将争议提交至一国国内法院管辖可能存在对地区保护主义的疑虑。因此,在我国确立限制豁免态度后,东道国政府是否愿意把案件提交我国国内法院审判,也与我国法院的专业性和中立性,以及判决的被承认和执行程度[15]密切相关。因此,我国法院还需进一步提高审判质量,增强东道国政府对我国法院的信任感。首先,考虑到“一带一路”工程商业纠纷涉及专业技术较多,需要造就知识复合、能够站在理论前沿和在国际民商事审判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官;其次,平等对待中外当事人,坚持审判公开透明,维护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内企业和东道国政府等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此外,通过与沿线国家法院开展司法合作,着力解决判决的承认执行问题,对于尚未与我国签订司法协助条约的国家,要秉持协商互惠原则妥善处理[23],避免“赢了官司输了执行”,最终提高我国法院的审判质量和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