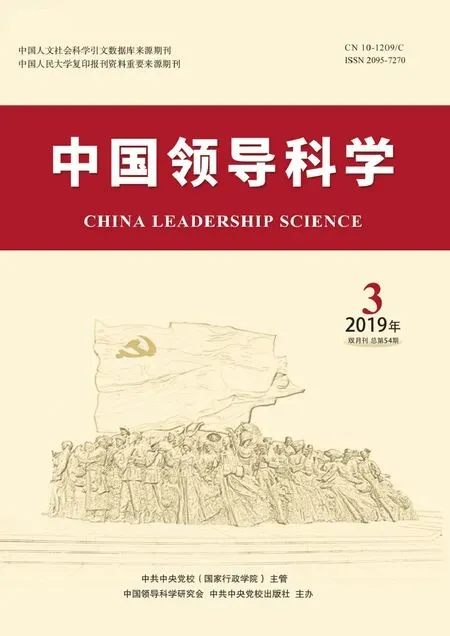《资治通鉴》中的领导激励论
◎江 文
领导效能是检验领导力的关键指标,而领导效能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追随者对激励的感知。因此,正确、恰当地对追随者进行引导和激励,是领导者的关键任务。自20 世纪初以来,西方许多管理学和领导学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如何进行激励的问题,提出了众多关于激励的理论。根据这些理论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将其归划分为内容型激励理论(Content Perspectives on Motivation)、 过 程 型激励理论(Process Perspectives on Motivation)、行为改造型激励理论(Behavior Modification Perspectives on Motivation)和综合激励模式理论(Integration Perspectives on Motivation)四大类。
事实上,中国古代领导思想对领导激励也有广泛而深入的关注。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作为领导者必读之书,尤为关注领导激励问题。《资治通鉴》的领导激励思想主要包括了赏罚分明、目标同一、率先垂范、公平公正等激励理念。对于这些激励方法的讨论,在许多传统典籍中业已存在,比如《孙子兵法》谈到了“上下同欲者胜”“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等领导激励理念,《孔子家语》也提到了“以身先之”“以道御之”的表率激励法等。笔者以为,研究《资治通鉴》中的领导激励,有必要脱离具体的“激励之术”的层面,而是站在“激励之道”的高度来深刻理解本书中的激励思想。借助西方领导激励理论框架与成果,全面系统研究《资治通鉴》中的领导激励思想,对完善具有中国气派的领导学理论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一、基于不同人性假设下的激励行为
美国工业心理学家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认为,有关人的性质和人的行为的假设对于领导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不同类型的领导者根据其对人性假设的不同,可用不同的方式来管理和激励追随者。在《资治通鉴》的许多经典案例中,对西方管理学和领导学理论的三种人性假设都有所涉及。
(一)“经济人”假设下的领导激励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方管理学界产生了以泰勒(F.W.Taylor)为代表人物的古典管理理论。该理论秉持“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行为是在追求本身最大的利益,工作的动机也只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为此领导者应该善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通过考核监督来奖励先进,鞭策后进。
在《资治通鉴》中,最为典型的“经济人”假设的激励案例就是商鞅变法。《资治通鉴》记载,商鞅变法开始之初,遭到了秦国大部分人的反对。于是,商鞅进言秦孝公说:“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1]商鞅这番话中将普通人的定位于“不可虑始”“安于故俗”,实际上就是将人视作“经济人”。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性假设,商鞅在随后的变法过程中将秦国原有的爵制加以改造,重新制定爵位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其基本精神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以军功作为赏爵的唯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都可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者,则要削夺爵级。这几乎是最早的绩效激励的雏形。商鞅的军功爵制改革达到了几重效果:一是激励战士,提升士气,迅速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二是打击旧的宗法贵族势力;三是从制度上为庶民打开通往爵位的大门,为建立官僚制新型国家铺平道路。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基于“经济人”的假设的激励只能是“霸道”而非“王道”。在国家积贫积弱之时运用这种激励方式能够迅速地调动平民的积极性,扩充国家实力。但是一旦国家进入建设时期,如果仍然采取这种强激励的刺激,反倒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国家治理的绩效水平。秦朝二世而亡,其根源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从领导科学的视角来看,“仁义不施”又源于强势的领导者忽视了管理中人性的因素而导致的,这值得当今的领导者引以为戒。
(二)“社会人”假设下的领导激励
20 世纪20 年代前后,西方管理学界依据霍桑试验提出了“社会人”的假设。[2]这种理论认为,人不单纯追求物质和金钱,还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需要。满足人的社会需求、尊重需求等更高层次的需求,往往比经济报酬更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将“社会人”假设激励用的最纯熟的领导者当属唐太宗李世民。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艺术的巅峰时代,其音乐不仅水平极高而且种类广泛。反映李世民在开创唐朝的过程中所立下汗马功劳的《秦王破阵乐》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据《资治通鉴》记载,在唐朝初年,负责外交招待的大臣萧瑀曾对《秦王破阵乐》的修改提出了建议,希望对歌舞进行改编,加入李世民征服刘武周、李密、窦建德和王世充的内容。这些都是唐朝开创中的大型精彩战役。
就艺术角度而言,萧瑀的建议是合理的。然而,唐太宗没有同意这个建议。李世民认为:“朕以见在将相,多有曾经受彼驱使者,既经为一日君臣,今若重见其被擒获之势,必当有所不忍,我为此等,所以不为也。”原来,李世民认为参加酒宴的文武大臣中,有不少人就在刘武周、窦建德等人手下当过将领,例如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魏征等。现在把他们过去的领导失败的惨状搬到舞台上来,岂不是伤他们的心吗?在李世民看来,侮辱追随者曾经的领导者,就是侮辱追随者自身。
李世民这种对下属自尊心和荣辱感的洞察和尊重,是许多领导者所不及的。古代许多领导者能够做到“用人如器”,即根据人才的不同特性与特长来有针对性的使用,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像李世民那样“用人如人”,即把追随者看成是一个具有丰富情感和独立人格的“社会人”,通过满足追随者高层次的需要来赢得人心。
(三)“复杂人”假设下的领导激励
在20 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心理学家沙因(Edgar H.Schein)提出了“复杂人”假设。沙因认为人有着复杂且易变的动机,但没有一种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万能激励方法。必须根据不同人的需求的变化,采用适宜的激励方法。
在中国古代,人们习惯于以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评判人物,往往将大臣划分为奸佞与忠良两大类。然而,社会与人性是复杂的,有些人物是不能简单归类的。《资治通鉴》是一部反映人性的史学著作,特别是对王朝兴衰,国运转换之际的人性变化描写的入木三分。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的故事,集中反映了“复杂人”的领导激励问题。
裴矩历仕北齐、北周,在隋朝时也受到隋文帝和隋炀帝的信任,与苏威、宇文述、裴蕴、虞世基掌握朝政,合称“五贵”。隋灭以后,裴矩率余部降唐,此后又被李世民委以重任,先后任殿中侍御史、民部尚书。 裴矩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够留名,并不是其领导才能的卓越,而是在不同朝代截然不同的政治表现。
《资治通鉴》记载,为助隋炀帝成就“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梦想,裴矩不顾国内民变频起的局势,支持发动对高丽战争,三次出兵过百万,终究无功而返,严重消耗国力,动摇国本。此外,裴矩在隋朝还留下了逢迎领导、投其所好的恶名。但入唐以后,裴矩仿佛脱胎换骨,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恪尽职守,秉公办事。唐太宗即位之初,裴矩更能诤言直谏,敢于为皇帝纠错。针对裴矩在隋唐的不同表现,司马光这样评述:“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也。”司马光的见解十分精辟,他认为裴矩前后判若两人并不矛盾,只是遇到不同的君主,做出不同的反应。正是这种不同的政治风气,才是导致前后裴矩判若两人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裴矩的人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真有什么改变。隋炀帝喜欢阿谀奉承之人,裴矩自然迎合他的意思。唐太宗力倡清明的政治风气,自然能够化佞为直、化伪为忠。
裴矩的案例生动说明了,人的动机虽然复杂,但也并非无一定规律可循。关键在于领导者自身能够以身作则,形成良好的政治风气和政治生态,才能激发追随者积极的工作动机,促使追随者行为向积极的一面转变。反之,如果领导者一味苛求追随者人格的瑕疵和动机的复杂,而不从自身方面寻找原因,那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领导思维。
二、平衡激励与约束的关系
司马光在《稽古录》里谈到了平衡激励与约束关系的问题:“凡御下之道,恩过则骄,骄则不可不戢之以威;威过则怨,怨则不可不施之以恩。”[3]激励与约束的关系,正如“恩”与“威”的关系一样,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资治通鉴》中多处案例都闪烁着激励与约束辩证法的光芒。
(一)系统性的激励思维
在激励的内容上,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统一。《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大量的古代帝王通过“赐姓”来激励功臣的案例。比如唐代罗艺“武德三年,奉表归国,诏封燕王,赐姓李氏,预宗正属籍”。初唐时期著名将领徐勣也被赐国姓“李”,后称“李勣”。后唐时期为了笼络外蕃,赐姓更加频繁,如后唐庄宗“赐(奚王)扫剌姓李名绍威”。[4]中国古代的赐姓从表面上看只是对名号进行赐予的精神激励,但实际上却有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与之同步,用赐以名号使被赐者与统治家族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方式,激发其荣誉感,实现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的结合。
在激励的对象上,坚持全面激励与重点激励相结合。全面激励意味着组织成员利益均沾,重点激励则能够以点带面,起到示范效应。在这方面《资治通鉴》的典型案例之一是刘邦分封众功臣的故事。西汉初年功臣众多,刘邦一开始的封赏并不能服众。在谋士张良的建议下,先封刘邦平生最看不起的雍齿为什邡侯。群臣见雍齿受封,都高兴地说:“雍齿都封了侯,我们还怕什么呢?”至此稳定了功臣之心。
在激励的过程中,要坚持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相统一。程序公正能够保证法度一致,结果公正则能够体现激励的正向作用。《资治通鉴》中记载,泰始三年(267 年),司隶校尉李憙上奏:原立进县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故尚书仆射武陔各自侵占官府三更稻田,请求免去山涛、司马睦等官职号。李憙所弹劾的山涛、司马睦,一个是武帝的亲信大臣,一个是武帝的宗室兄弟,武帝不忍将他俩治罪,于是诿过于小县官刘友,有意为权贵开脱罪责。
对此,司马光批评说:“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且四臣同罪,刘友伏诛而涛等不问,避贵施贱,可谓政乎。”[5]批评晋武帝赏罚不明,避重就轻。也正是因为晋武帝的庇护与纵容,导致西晋一朝吏治日益腐败,贪墨奢侈之风盛行。这从反面说明了激励公平性对于领导制度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有耻且格的约束之道
激励通常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激励,而约束往往又是建立在激励基础上的。在《资治通鉴》中,对约束的关注放在与激励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而司马光在论及约束时,特别强调以人为本,注重教导人“有耻且格”,鼓励官员通过自我检点归于正道。
《资治通鉴》记载,初唐时期名将侯君集参与太子李承乾谋反之事获死罪。唐太宗召见侯君集对他说:“朕不欲令刀笔吏辱公,故自鞫公耳。”临刑之前太宗又对侯君集说:“与你永别了!”因而流下眼泪。君集也磕头表示服罪。这段历史今天读来今天仍让人动容,面对犯下重大错误的下属,领导者可以运用峻法惩罚,甚至可以运用酷刑侮辱,但是唐太宗李世民依然能够从人性的尊重需求出发,礼法并用进行惩罚,体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
纵观李唐一朝,关于在约束下属时注重廉耻的论述还有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魏征在《论治道疏》中谈到的:“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维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大臣苟免,则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则矫伪成俗。矫伪成俗,则不可以臻至治矣。”对犯错误的领导者在人格上给予尊重,在处理方式上给予适当照顾。这样的约束之道更加能够唤醒人性中善的一面,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在严刑峻法的理性之外,彰显了人性光辉。
三、《资治通鉴》激励思想的价值
《资治通鉴》以其丰富的案例和深刻的评论对领导激励理论进行了入木三分的阐述。在系统掌握西方领导激励理论的基础之上,深入挖掘本书中蕴含的领导激励思想,可以发现其中独特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一)用权变思维弥补西方领导激励理论的不足
从研究方法来看,中国古人是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提出激励方法,对激励的机理缺乏理论的深入分析。西方的激励理论则是在实验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实验、实践的结果,找出其激励机理,建构系统的理论体系,揭示出激励的一般规律。但是,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领导激励方面更加强调权变性。而这一点是西方的领导激励理论所不及的。
比如哈佛大学心理学家B·F·斯金纳(B. F. Skinner) 提 出 强 化 理 论(Reinforcement Theory)是经典的激励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人可以通过对工作环境的专门设计,并对取得较好业绩的加以正面强化(Positive Reinforcement),奖励那些符合组织目标的行为;对业绩差的施加负面强化(Negative Reinforcement),来惩罚那些不符合组织目标的行为,以此达到激励的目的。事实上,在中国传统领导智慧的视野中,正面强化和负面强化本来就是相对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二分的,在某些情境下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资治通鉴》曾记载,楚汉相争之时,淮南王英布投奔刘邦。英布到时,刘邦正坐在床上洗脚,极其傲慢。英布见状怒火燃胸后悔前来,甚至想要自杀。可当他来到为他准备的住所时,见到帐幔、用器、饮食、侍从官员和刘邦那么豪华,英布又喜出望外。颜师古注《汉书》将刘邦见英布的领导艺术说得非常通透:“高祖以布先久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礼,令布折服,既而美其帷帐,厚其饮食,多其从官,以悦其心,此权道也。”在中国式的领导艺术中,负强化未必就是惩罚,反而能够因人而异,通过正负强化的运用次序不同以及之间的落差,来更加深刻的影响追随者。这种精妙的激励艺术也是西方公式化的激励理论所不及的。
(二)用“柔性约束”为激励—约束制度失衡问题提供了借鉴
《资治通鉴》展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卓越领导者系统化的激励艺术和“有耻且格”的约束艺术。这对理解当下干部队伍建设当中出现的激励—约束失衡的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2018 年8 月至9 月,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围绕“干部干事创业动力及其影响因素”这一主题,面向党员干部展开了大型问卷调查。从一些调查结果可以发现,超半数的受访干部对“缺少明确、有效的激励机制,限制约束太多、内在动力不足”等因素认同的比例较高。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之后,自2018 年起,中央出台了许多激励性比较强的政策文件,期望更进一步的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新的政策导向为干部队伍的约束和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对犯错误的干部容错纠错,如何对工作有失误的干部进行面谈、如何在法律之外给予干部人格上的尊重,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加科学、更具艺术的回答。
在这一方面,《资治通鉴》中强调的“礼义廉耻”“明赏慎罚”“刑赏贵公”的观点都对全面从严治党之下的干部监督与约束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在严控监督底线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塑造干部队伍的使命感、荣誉感和工作动力,有赖于汲取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实现从“严督”到“善督”转变,提振干部队伍的整体士气。
(三)用系统思维对提升领导者激励艺术提供路径方法
《资治通鉴》的众多经典案例全面涵盖了领导激励的各个方面,是一个系统全面的方法体系。在激励的人性假设方面,强调领导者要因时而动,因势而异,在不同的情境之下深刻洞察和把握人性的本质,而非简单地将人性划分为“经济人”“社会人”或“复杂人”。在激励的具体方法上,强调领导者要注意系统性把握激励的内容、节奏、力度、时机和范围,而非简单地运用正面强化和负面强化。在激励与约束的关系上,强调领导者要运用辩证的思维,平衡激励与约束的关系,特别要做到寓激励于约束,运用高超的领导艺术在约束和监督中唤起下属的廉耻之心,达到“自律”的最高境界。这些思想方法是非常具体化、可操作化的实践总结,对于提升领导者的激励艺术有弥足珍贵的教育意义。
一言以蔽之,《资治通鉴》中的领导激励思想是系统的而非是零碎的,是实际的而非空洞的。它彰显了这么一个朴实但又令人忽视的道理:激励之术,在于信赏必罚,公正无偏。但激励之道,则在于洞察国运之大势起伏,也在于洞悉人性之善恶分际。很显然,激励并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术”的层面的一种领导艺术,更是一种领导者“人性观”和“价值观”的反映。以道御术,则激励得法;以术御道,则终失人心。这就是《资治通鉴》独特的思想魅力。
[注 释]
[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273-298.
[2]道格拉斯·麦格雷戈.企业的人性面[M].韩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11-98.
[3]司马光.稽古录[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32-53.
[4]张淑一.从激励机制看中国古代赐姓[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1, 31(3):40-43.
[5]庞天佑.论司马光的历史盛衰总结[J]. 武陵学刊, 2016, 41(3):6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