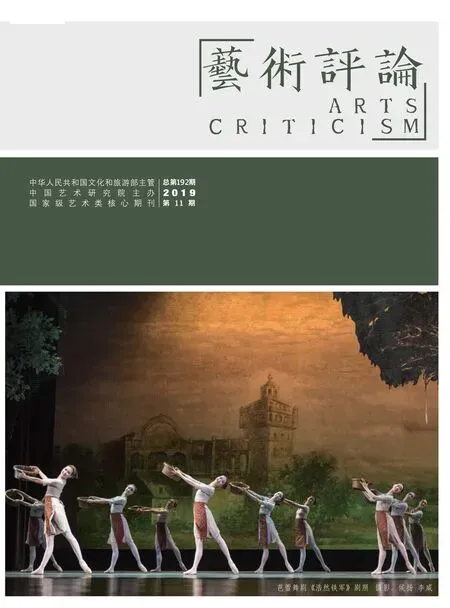新旧剧论争的世纪回望
[内容提要]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杂志曾经组织了一场新旧剧论争,在社会学层面上比较了东西两种不同形态的舞台样式——话剧与戏曲的优劣,这场并非逻辑完备和理性充盈的论争却推动了中国戏剧的观念变革,引发了文艺界对于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西化与民族化辩证关系以及话剧、戏曲不同审美特质的长期和深入思考,影响甚至支配了话剧和戏曲后续的社会实践。今天站在世纪崖岸上回望,我们得到深刻的历史启示。
1918年,吹响新文化运动号角的《新青年》杂志聚焦戏剧观,继6月15日在第4卷第6号刊发“易卜生专号”并附录张厚载、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关于“新文学及中国旧剧”的通信之后,10月15日又在第5卷第4号组织“戏剧改良专号”,刊登了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再议戏剧改良》、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张厚载《我的中国旧戏观》一组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构成了新旧剧论争的正式擂台。论争掀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戏剧史的开篇,对于20世纪中国话剧和戏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余音则回响了百年。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回头总结百年来话剧与戏曲路径,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一、论争的文化动因
近代史上的西潮东渐造成东西两大文明的相遇与冲突,两者自然要相较优劣。时值中国积贫积弱、遭受瓜分,亟盼鼎故革新。而维新改革失败,共和尝试流产,新文化派乃猛烈冲击守旧势力,批判旧国民性,否定传统文化,呼吁效法西方并实施彻底革新。革新首从文学始,文学从白话文始,一场具有工具理性意义的启蒙民众、改良社会的文学革命拉开序幕。之所以选择戏剧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是因为新文化派发现西洋人对戏剧情有独衷。陈独秀1915年撰文《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说:“现在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居第二流,以实现于剧场,感触人生愈切也。”而他们发现,戏曲在中国民众中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如陈独秀1905年撰文《论戏曲》说:“世上没有一个不喜欢(戏曲),无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都诚心悦意,受他的教训,他可算得是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因而他们知晓,若将戏剧用作文学革命的工具,一定能够深入民众身心。但是当下的流行剧种如京剧之类却是如此之谫陋,无以承担时代的重任,如钱玄同所说:“若今之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固不可因其为戏剧之故,遂谓有文学上之价值也。”如陈独秀所述:“剧之为物,所以见重于欧洲者,以其为文学、美术、科学之结晶耳。吾国之剧,在文学上、美术上、科学上果有丝毫价值耶?”因而必须发动一场戏剧改良运动,傅斯年说:“现在戏剧的情形,不容不改良。真正的新剧,不容不创造。”改良的目的,鲁迅说是“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底文学的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洪深说:“改良中国原有的戏剧,他底目的,是要把戏剧作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
事实上改良不自此时始。戊戌变法后,维新派已经纷纷创作鼓吹时事的戏曲,如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发表传奇剧本《劫灰梦》,接续又发表了《新罗马》《侠情记》。1904年柳亚子与陈去病、汪笑侬在上海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已经疾呼戏剧改良。积极从事京剧改良的代表人物汪笑侬自己动手改编创作了众多时事新剧,并进行舞台表现方式的改革。在这种时代情势下,穿时装、发议论的时事新戏一时风靡。但写意化、程式化的戏曲无法直接反映现实生活,于是舞台上了出现许多不古不新不土不洋的怪胎,例如爱国志士登台,“把手插在西装裤子袋里扯四门唱西皮”,台上新出现的“言论老生”和“言论小生”往往脱离角色而大发政治议论等等,很快遭到观众厌倦和抵制,随后戏曲舞台仍然被歌舞升平色情迷信所充斥。欧阳予倩所以说:“今日之剧界,腐败极矣!”1907年一个新的契机出现,留日学生李叔同、陆镜若、欧阳予倩等组织春柳社在东京上演文明新戏《黑奴吁天录》《热血》等获得成功,回国后又组织新剧同志会等演出新剧、宣传革命,一时间全国的新剧运动蒸蒸日上。但辛亥革命夭折后环境转暗,新剧也在资本操纵下败落成了低级庸俗的商业噱头。欧阳予倩说:“新戏萌芽初拙,即遭蹂躏,目下如腐草败叶,不堪过问。”宋春舫说:“吾国新剧界,每况愈下,春柳后,广陵散盖绝响矣。呜呼,靡靡之音,足以亡国。”新、旧戏改良遭挫的现实,使得新文化派将标杆直指西方,呼唤更彻底的戏剧改革。
二、方枘圆凿的观念对峙
新文化派改良戏剧的主流观点,是荡涤中国落后保守的旧戏,倡导西洋新剧和悲剧。这场论争的组织者是胡适,而他也正是1919年写出据称是中国第一个白话剧本《终身大事》的人。胡适在陈独秀支持下发起这场论争,是为了贯彻他和同人的文学进化与戏剧改良观,在文学领域他们呼吁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白话文学,在戏剧领域他们呼吁西洋式的白话戏剧,对于推动中国文学革命与戏剧革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发言的新文化派人士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其中多数为激进派,如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周作人,与胡适一样,他们都采取了决绝态度,主张彻底废除中国的旧戏,而用西洋话剧取而代之,少数温和者如欧阳予倩则认为旧戏可以也应该加以改造和利用。至于与新文化派对立的反派代表则只有张厚载一人,胡适特地邀请他撰文阐述不同的观点,在新文化派主流阵地《新青年》上用作附录,这一方面体现了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学术民主思想,另一方面也为新文化派的理论声讨竖立一个靶底。
应该说,除了欧阳予倩直接为戏剧人士外,胡适是参与论争的几位新文化派同人里戏剧修养最高的。他读过许多古代和外国剧本,熟稔其情节结构,懂得戏剧剪裁法,对中国与西方戏剧的舞台演出也很熟悉。他文章里对中国戏剧史有简单明了的勾勒,也论及西方戏剧的“三一律”。这些是他能写出第一个白话剧本的文化积累,更是他发起“戏剧改良论争”的眼界与理论前提。胡适运用文学进化观念,复倡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也是很有见地的。但他机械地搬用进化论来解释人类戏剧现象,尤其是把文化与美学形态完全不同的中国戏曲与西方话剧看作是人类进化阶段上先后阶梯的生成物,甚至以为后者一定取代前者,则酿为历史笑柄。例如他认为西方话剧是进化完成的艺术,中国戏曲则是进化未完成的艺术,他说:“在中国戏剧进化史上,乐曲一部分本可以渐渐废去,但也依旧存留,遂成一种‘遗形物’。此外如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等等,都是这一类的‘遗形物’,早就可以不用了,但相沿下来至今不改。西洋的戏剧在古代也曾经过许多幼稚的阶段,如‘和歌’(Chorous)、面具、‘过门’、‘背躬’(Aside)、武场……等等。但这种‘遗形物’,在西洋久已成了历史上的古迹,渐渐的都淘汰完了。这些东西淘汰干净,方才有纯粹戏剧出世。”他认为中国旧戏始终未能脱离乐曲的束缚,认为乐曲以及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龙套等等,都是前一时代留下的“遗形物”,阻碍了它的进化,“这种‘遗形物’不扫除干净,中国戏剧永远没有完全革新的希望”。而西洋戏剧扫除了“遗形物”,就实现了“自由发展的进化”。所以,中国戏剧必须“扫除旧日的种种‘遗形物’,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展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出于这种认识,胡适明确提出了“废唱”的要求,他说:“今后戏剧或将全废唱本而归于说白。”另外几位激进派同仁与胡适的看法一致,他们自知对戏剧了解不多,干脆先自判为“门外汉”,然后对戏曲发难。钱玄同说,脸谱、对唱、乱打(武打)等同于清遗老的男人辫子、女人小脚,是野蛮人不肯进化为文明人的遗留物。陈独秀说:“至于‘打脸’‘打把子’二法,尤为完全暴露我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而与美感的技术立于绝对相反之地位。”傅斯年的措辞更为激烈:“(戏曲)好比猴子,进化到毛人,就停住了,再也不能变人了。真正的戏剧,纯是人生动作和精神的表象,不是各种把戏的集合。可怜中国戏剧界,自从宋朝到了现在经七八百年的进化,还没有真正戏剧,还把那‘百衲体’的把戏,当做戏剧正宗!”他们的一致结论是必须用西洋戏剧取代中国戏曲:“至于建设一面,也只有兴行欧洲式的新戏一法。”“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戏,决不是那脸谱派的戏。要不把那扮不像人的人、说不像话的话全数扫除、尽情推翻,真戏怎样能推行呢?”
与前述新文化派诸公不同,欧阳予倩是另外一种存在。他的文章本不为论争而发,系总结自己亲历戏剧改良经验之谈,当年先发表于日本人在上海办的《讼报》上。但因他也是留学日本回来并积极从事新剧演出的新文化人士,其文章恰好也谈到戏剧观,因而被胡适选中,征得他同意再发表于《新青年》作为附录,于是列入了论争行列。欧阳予倩的看法与诸公显然不同,他认为“中国旧剧,非不可存。惟恶习惯太多,非汰洗净尽不可。”“倘若旧戏能把表演的技术活用而成为现代新思想的工具,那又何尝不可存在?”他还提出两条富有创意的建设性意见:“须组织关于戏剧之文字”,包括剧本、剧评、剧论;“须养成演剧之人才”,即创办新型戏剧学校培养学生。事实上欧阳予倩一直在实践自己这种主张,此前他在舞台上进行了持续的戏曲改良,自编自演了众多的文明新戏和改良京剧,此后则先后开办了南通伶工学社、广东戏剧研究所、广西艺术馆,培养了许多新式演剧人才。
反对派的代表张厚载事实上并非文学革命的完全抵制者,只是认为旧文化仍有利用的价值。张厚载先后在北京五城中学堂、天津新学书院、北大法科政治系读书,接受的完全是新式教育,但他又是维新派林纾的入室弟子,推崇桐城派古文,因而立场在文学革命与文学改良之间。他喜欢京剧,与梅兰芳、齐如山及许多京剧票友交往密切,1911年始在《亚细亚报》《公言报》发表系列戏曲评论文章,显示出相当的理论修养,对京剧欣赏有着不俗见地。他在论争中既表明了支持改良的立场,“对于改良文字,极表赞成”,又强调戏曲对于中国民众有着特殊价值、不应废除:“中国旧戏,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可以完全保存。社会急进派必定要如何如何的改良,多是不可能……拿现在的社会情形看来,恐怕旧戏的精神,终究是不能破坏或消灭的了。”这与文化改良派的老式旗手林纾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相近。与陈独秀1917年2月1日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同一天,林纾在天津《大公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强调推行白话文不必一定要废除古文,古文有文脉传承的作用,即如文艺复兴的欧洲人不废拉丁文,中国亦应保留古文之脉。这些意见从文化发展规律来说是有道理的,也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无论文学还是戏剧后来的进展都给了他们的观点以支撑。但忽略时代的精神需求,一味强调古文与戏曲审美的特殊价值,在那个狂飙突进而非学理探讨的时代,他们自然是守旧和阻碍历史进程的。当然,张厚载后来加入林纾阵营,并因恶意诅咒新文化派而被北大开除,从此沉沦,这却是历史的悲剧。
事实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傅斯年、周作人等人的论述,从精神内涵到社会功能全面否定旧戏,只是一种预设的政治性价值宣判——都是借批判旧戏来抨击旧文化,因而他们矛头所指其实并非专一为戏曲。但戏曲实为影响民众最为深入的艺术形式,对旧戏进行彻底的精神清算,就掘了旧文化的坟,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而推动文化和社会变革——这是新文化派同人矫枉过正的有意之举。作为反驳一方的张厚载则属于逆历史潮流而动,非要去捉寻人家论说中的瑕隙,强说戏曲仍有价值而并非一无是处。这是一场焦点错位的论争:一方抨击戏曲缺乏揭示思想、改造社会的功能;一方则强调戏曲有其审美原则。二者的出发点、所论内涵大相径庭,效果则是方枘圆凿。事后北大戏剧教授宋春舫曾评说新文化派的偏激之弊:“大抵对于吾国戏剧毫无门径,又受欧美物质文明之感触,遂致因噎废食、创言破坏。不知白话剧不能独立,必恃歌剧为后盾。”其看法应该说是公允的。
三、广远的影响
论争起到了解放思想、矫枉过正的警醒震世作用,使人们进一步明确了文学与戏剧的社会功能与时代任务,促进了戏曲的改良与话剧的成熟,也使业界人士洞晓了戏曲之短与话剧之长,从而能够更好地运用戏剧来提升时代精神和推动社会进步。但新文化派决绝抛弃民族审美形式的激进态度也引发了文艺界对于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西化与民族化辩证关系以及话剧、戏曲不同审美特质的长期和深入思考。人们开始从学理上探讨舶来品话剧与“国货”戏曲的精神特质与美学内涵,希望能够贴切把握它并熟练运用,使之成为符合时代要求的文艺样式。例如利用戏曲的为民众所欢迎和以情动人,吸收话剧的思想性与现实性,提高其斗争武器的功能,戏曲于是从改良到改革到“戏改”,走过了百年历程。例如提出话剧民族化路径,意即话剧向民众所熟悉的戏曲审美内核靠拢,调动单线叙事、讲故事、人物类型化、大团圆等传统因子,张扬象征性、抽象化、写意化内蕴,对以后写意戏剧的理论形成、对新时期戏剧均产生深远影响。下面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概括。
(一)横扫了旧文化笼罩在时代天幕上的乌烟瘴气,涤荡了戏曲剧坛的污泥浊水,促进了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把晚清以来对戏曲改良的认识提升到改造国民性的高度,明确了戏剧发展的正确途径
20世纪初始的戏曲,早已将早期如元杂剧的青春朝气丧失殆尽,累积的痼疾沉疴则使之一派病容气息奄奄,舞台上充斥着奸盗淫杀与歌舞升平。一边志士们为了雪耻洗辱富国强兵苦苦谋策,另一边遗老遗少拖着辫子迈着方步悠然出入戏楼品茗饮酒赏色观花。透过新文化派对旧剧的严厉抨击,戏曲越发凸显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末期中国社会中的畸变与没落,其作为旧文化代言人的角色身份一览无余,因而遭到寻求时代突破精神的人们所唾弃,改良戏曲则成为改造国民性的前提和重要任务。新文化派决绝冲击旧戏、旧文化的直接结果是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文学革命迎来了最大的成果,社会转向政治改革的方向,从此中国历史拉开崭新的一幕。
论争使人们认识到戏剧必须符合社会的精神与功用要求、必须反映现实生活和体现时代精神,从而明晰了戏剧的正确途径。例如欧阳予倩论剧本创作:“一剧本之作用,必能代表一种社会,或发挥一种理想,以解决人生之难问题,转移误谬之思潮。演剧者,根据剧本,配饰以相当之美术品(如布景、衣装等),务使剧本与演者之精神一致表现于舞台之上,乃可利用于今日鱼龙漫衍之舞台也。”时代要求戏剧用强健精神取代风花雪月、为现实发声而横扫一切无病呻吟,从而走上健硕的道路。论争还廓清了戏曲评论的正确范畴、扫荡了观花捧角恶习,亦如欧阳予倩所说:“吾所谓正当之剧评者,必根据剧本、必根据人情事理以立论。剧评家必有社会心理学、伦理学、美学、剧本学之知识。剧评有监督剧场及俳优,启人猛醒、促进改良之责,决不容率尔操觚、鲁莽从事也……吾所望于今日之评剧家者,在诱导演剧者断弃其顽梗之主张而趋重于事理人情而已……剧论之最要者,在名剧本之分析,及舞台上之研究……故不欲改良戏剧则已,欲改良戏剧,非亟倡正确之剧论不可。如云‘某处宜下锣’,或‘某处不似老谭所唱’,所论非戏剧,不能羼入剧论也。”实践和理论道路的廓清,使得戏剧朝向健康方向发展下去。
(二)对西方话剧在中国舞台上真正立足、为民众所广泛接受,为中国一批新剧作家致力于话剧写作、拿出靓丽的成果,为话剧走向舞台成熟、成为与戏曲并立的艺术样式,起到推波助澜的巨大舆论作用

(三)促成了戏曲的求新、求变与追求时代价值,推动了戏曲内核的现代性更代,还进一步引发了梅兰芳、程艳秋的欧美演出与考察,带出另外一个评价戏曲的西方视角,使得人们深入探寻戏曲的美学原理
新文化派代表时代潮流对戏曲所进行的严苛抨击与批判,构成戏曲求新、求变以追求现代性和时代价值的巨大促动力。京剧四大名旦“梅、尚、程、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崛起,各自以创新剧目、改造舞台惊艳于世人,而富连成社对新式人才的培养也使京剧各个行当人才济济,共同造就京剧又一个黄金时期的到来。正如程砚秋所说:“很有价值的旧房子修葺起来,或者比偷工减料的新房子也许还来得可靠些。”各地的戏曲改良促成了一些地方剧种的崛起。如王镇南、樊粹庭等进步文人推动河南梆子改革并为之编写《中法战争》《五卅惨案》《涤耻血》这类新剧本引起轰动,豫剧很快发展成沿陇海线延伸、覆盖了中原大地和北半部中国的大剧种。起于河北唐山“蹦蹦戏”的评剧,经成兆才1919年以河北滦县真实案件为素材创作出《杨三姐告状》,演出一时风靡,该剧成为评剧经典剧目,盛演百年,至今不衰,评剧则迅速发展为流行于华北、东北地区的大剧种。沪剧、曲剧则是在话剧影响下产生的以反映现实生活见长的新剧种,为地方观众所欢迎。戏曲的盛况甚至改变了一些新文化主将的观点。如胡适1928年在一次演讲中说:“社会上无论何种职业,不但三十六行,就是三万六千行,也都是社会所需要的。”“梅兰芳是需要的!小叫天(谭鑫培)是需要的!”而曾经公开撰文称“旧戏之应废”的周作人,则在更早的1924年初就发表了《中国戏剧的三条路》,对自己之前的观点做了修正:“旧剧是民众需要的戏剧,我们不能使他灭亡,只应加以改良而使其兴盛。”是戏曲的自新局面使时代认知发生了巨大转折。
京剧四大名旦声名鹊起,却由于新文化派对戏曲的贬损而使其颇感价值失落。但是一些来华的欧美人士,以及游学归国戏剧人士如宋春舫、张彭春、齐如山等人对戏曲的价值认定,又让他们意识到世界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评价体系,遂引发了梅兰芳1930年、1935年的访美与访苏演出,程砚秋1932年的赴欧洲考察戏剧。果不其然,从欧美反馈回来的信息令戏曲界精神陡振:梅兰芳的舞台艺术获得世界性的普遍赞誉,欧美戏剧界有人称之为“一个完全合乎理想的统一体、一种艺术品”。程砚秋考察欧洲戏剧期间,一些西方戏剧家如兑勒、莱因哈特曾向他表示对中国戏曲的倾慕,兑勒称中国戏曲是“珍贵的写意的演剧术”,《小巴黎报》主笔还很惊奇地问程砚秋:“中国戏剧已经进步到了写意的演剧术,已有很高的价值了,你还来欧洲考察什么?”西方反馈使戏曲获得了艺术自信力,民众需求更使戏曲获得时代性发展。田汉说:“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动员广大军民。而广大军民最熟悉的艺术形式便是旧剧。因而改革旧剧使适合当前需要成为迫切之课题。”由此,从“旧瓶装新酒”以促进其内容现代性开始,“戏改”在延安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序幕,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戏曲改革通过国家意志的方式正式确立下来。今天戏曲已经作为东方审美凝聚物的代表,正在塑造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前景。
(四)引动了理论界长期以来对话剧与戏曲审美特质的研究与比较,人们逐渐把握了两者功能的同与不同,日益自觉地发挥其各自审美特长来进行舞台建设,尤其对话剧民族化和戏曲改革的长期实践构成理论指导
事实上论争中的一些论述已经触及戏曲的审美特质,今天我们归纳出的戏曲特点:综合性、写意性、虚拟性、程式化等,论争中都涉及了。例如戏曲歌唱是东方审美的凝结物,其原理出自中国古代乐论“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有着特殊的美学价值和言情价值。为反对胡适的“废唱”说,张厚载已经认定戏曲“唱功有表示感情的力量”。而1930年美国剧评家斯达克·扬在观看了梅兰芳的演出后,也有过类似的表述:“我发现每逢感情激动得似乎需要歌唱,人物就唱起来,这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情绪一旦激昂就会很自然地引吭高歌——依我看来,这是戏剧艺术高度发展中的一种正常而必然的现象。”又如为反对新文化派摒弃暗寓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的戏曲脸谱,张厚载已经作出脸谱“隐寓褒贬之意”的评价。戏曲的虚拟化表演蕴含了深厚的美学积淀,后来受到西方现代派戏剧家的推崇与模仿,胡适在论争中业已作出了总结:“跳过桌子便是跳墙,站在桌上便是登山,四个跑龙套便是一千人马,转两个湾便是行了几十里路,翻几个斤斗、做几个手势便是一场大战。”只是当时他却作出反向判断,斥之为幼稚。其时不赞同胡适等人观点的留学归国人士亦大有人在,如宋春舫、余上沅、熊佛西、赵太侔等。宋春舫的看法较为深刻完整,他清楚地认识到话剧与戏曲分属两个不同的审美体系,有着各自不同的美学价值与功能,话剧偏重于写实,注重对人生的真实描绘,而戏曲偏重于写意,注重对生活美的提炼,故二者不能偏废。他说:“歌剧是‘艺术的’;白话剧是‘人生观’的。”1925年赵太侔、余上沅等人发起的“国剧运动”还分别探讨了话剧的写实与戏曲的写意特征,并论及戏剧的假定性问题。以后,国人用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理论探讨和舞台实践,来深入发掘话剧与戏曲的内涵与外延、审美特质和内在精神,逐渐建立起清晰的认识论构架。
今天的中国戏剧正走在良性发展的道路上,并在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世界格局中占有自己的舞台位置。回望一个世纪前的新旧剧论争,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戏剧最初寻径的左冲右突与夺路而出,以及后来长期的奋进、受阻、迂回、徘徊的筚路蓝缕轨迹,直至走上理性自觉的路径,我们不禁慨叹艺术前行竟然也是如此的艰难险阻、波澜壮阔!
注释:
[1]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J].《新青年》第1卷第3号,1915-11-15.
[2]三爱.论戏曲[J].安徽俗画报(11),1905年8月.
[3]钱玄同.致陈独秀信[J].《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3.
[4][19]陈独秀为《新青年》第4卷第6号“新文学及中国旧戏”栏目所写通信文字.1918-6-15.
[5][20][31]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J].《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10-15.
[6]鲁迅.《奔流》编校后记[M]//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63.
[7]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M]//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九册).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20.
[8]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57.
[9][10][23][25][29][30]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M]//欧阳予倩全集(第五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3,1,2,2,1,2-3.
[11]宋春舫.世界新剧谭[M]//宋春舫论剧(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23:259.
[12]王国维.宋元戏曲考[M]//王国维戏曲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3.
[13][14][15][16][44]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J].《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10-15.
[17]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J].《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5-1.
[18]钱玄同.今之所谓“评剧家”[J].《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8-15.
[21][35]周作人.随感录[J].《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10-15.
[22]钱玄同.随感录[J].《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7-15.
[24]欧阳予倩.明日的新歌剧[M]//欧阳予倩全集(第五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299.
[26]张厚载为《新青年》第4卷第6号“新文学及中国旧戏”栏目所写通信文字.1918-6-15.
[27]林纾.论古文之不宜废[N].天津《大公报》,1917-2-1.
[28]宋春舫.戏剧改良平议[M]//宋春舫戏剧论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23:265.
[32]汪优游.与创造新剧诸君商榷[J].《戏剧》第1卷第1期,1921.
[33]《申报》记者.对于改良旧剧的感想:新屋未成旧屋须爱护[N].申报,1933-11-4.
[34]见毕云程.胡适之先生职业观[J].《生活》第3卷第38期,1928-8-5.
[36]周作人.中国戏剧的三条路[J].《东方杂志》第21卷第2期,1924-1-25.
[37][43]〔美〕斯达克·扬.梅兰芳[J].梅邵武译,《戏曲研究》第11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
[38][39]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M]//程砚秋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08.
[40]田汉.关于旧剧改革[M]//翁思再主编.京剧丛谈百年录(上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99.
[41]《毛诗序》,《十三经注疏》(上册)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79:270.
[42]张厚载.我的中国旧戏观[J].《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10-15.
[45]宋春舫.改良中国戏剧[M]//宋春舫戏剧论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23: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