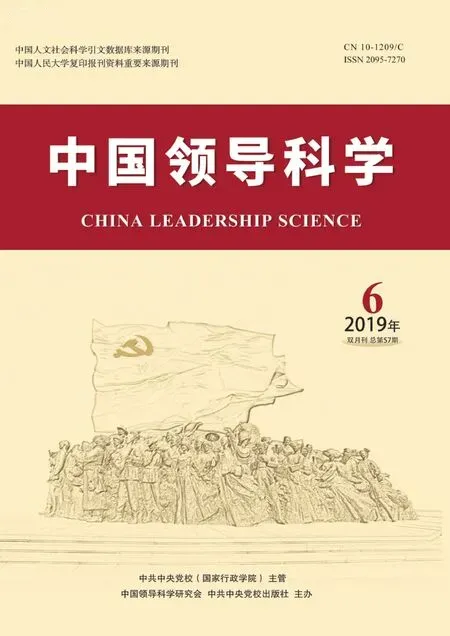信马由缰的甩手掌柜和罕见的管控者
——里根总统的领导风格
◎ 樊 超
领导人的领导风格本质上反映的是他们的决策模式以及基于此所产生的特征。在当今时代的政治制度设计中,无论各国政体如何设计,无论影响公共政策的因素如何多元、政策产生的过程如何复杂曲折、各类行为主体的互动如何迂回,最终都需要由领导人及其领导下的职能部门直接完成从政策蓝本到政策成型的最后环节。简而言之,行政机关中最顶层的政治精英才是制定公共政策的直接载体。[1]因而,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界,都承认领导人在决策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和关键性作用。以美国领导人的领导风格而言,领导人与职能部门合作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既存在领导人绝对控制领导职能部门的风格,也存在领导人信马由缰,放任职能部门自动运作的风格。尽管后者在领导人风格和决策案例中占据的比率较低,但鉴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仍然需要研究和应对美国总统放任式的领导风格。
一、谁在做决策?
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经咨询并取得参议院同意,总统有权任命行政部门首长、大使、公使、领事、最高法院法官和任命手续未由本宪法另行规定而应由法律规定的合众国所有其他官员。但国会认为适当时,应依法将这类低级官员的任命授予总统一人、法院或各部部长。[2]宪法赋予了总统对行政官员的任命权,也就赋予了总统在行政系统内的最高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总统在各个行政首长及其职能部门的襄助下,完成宪法赋予的行政职责。从理论上讲,在总统与职能部门合作制定政策的工作框架内,总统处于领导地位,在决策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从现实情境来考虑,总统及其所任命的行政首长们大多是职业政客,并不具备在各行各业的专业知识,甚至作为平常人的一分子,总统不仅专业知识有限,而且精力体能有限,决策兴趣有限。在这样的条件下,总统实际上只能依赖行政职能部门形成的庞大文官系统来帮助自己,以此扩展自己的工作量,弥补自己在专业知识和精力体能上的不足。与此相应,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可以要求每个行政部门长官就他们各自职责有关的任何事项提出书面意见”[3]。这种情形实际上决定了总统领导行政系统的两个基本内容和特点。
第一,总统亲自参与的行政系统运作是极其有限的。换言之,总统对行政系统的领导是对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做出指令回应和综合性处理。总统在决策中参与度最高的环节,就是开启决策、设置决策议程的环节,以及从政策备选方案中抉择最终政策的政策制定环节。除此之外,无论是激发决策的情报和信息,还是酝酿政策备选项的专业准备,抑或是政策的执行过程,都是依赖甚至是彻底由行政职能部门来完成的。
在政策研究中,如何界定和描述政策是研究的起点。而研究者总是面临究竟是采集政策文本还是政策实施结果的选择。如果以政策最终执行实施的结果作为定义政策的标准,那么职能部门在制定政策上则发挥着更为强大的作用。因为“法律和政策总是比较原则的,在运用于具体事例时,必须考虑到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而决定应如何执行。行政官员对法律和政策的解释,事实上起到制定政策的作用,即使最低一级的行政官员也在某种程度上起着这种作用”[4]。也就是说,职能部门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所享有的自由裁量空间与权力,实际上决定了政策的最终面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总统的工作不过是在行政职能部门所提供的素材和选项框架内进行工作或创造。当总统对行政职能部门的领导强度减弱乃至缺失时,政策实际上就变成了各个职能部门自行运作、折中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政策施加影响的行为体,都应该将工作的重心从总统挪向行政职能部门。
第二,总统对行政系统的领导还包括协调、整合各个职能部门的运作。现代国家制度的成功之处在于,政府机构按照业务范围划分为不同的职能部门,每个部门负责一个领域的事务,各部门之间有序合作,才能保证庞大的政府可以顺利运作、落实政府的职能。[5]在通常情况下,总统不具备过问职能部门具体工作的条件。根据以往的业务经验而制定的预案和早已形成的日常标准操作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职能部门会自行运作。[6]其过程并不直接体现总统的领导能力与智力水准,而是更多地反映了职能部门各自独有的业务标准,以及基于此而产生的相对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基于官僚政治斗争的本能,各个部门出现权力争斗,[7]还是出于各个职能部门在业务标准、职业操守上的鸿沟与隔膜,都会使各职能部门在协作问题上存在某种天然的缺陷。所以,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组织或社会共同体都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权威”或“支配”作为基础。否则,任何组织都无法达成自己的目标。[8]
为了保证行政系统的正常运作,总统要凭借自己在行政系统的至高权威,组织和协调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美国并不存在一项关于职能部门之间关系或协作关系的成文法或规章,因此,总统的协调行为需要是动态的和常态化的。一旦总统作为最终协调者、仲裁者的身份或功能缺失,无论是职能部门之间潜在的争斗,还是等待总统裁决的时间间隔,都会拖慢决策的节奏。无论客体是本国受众,还是外国政府,这都会极大地改变政策客体的应对美国行政系统方式,并最终改变它们之间的互动方式。
总体而言,美国总统基于其在行政体系内的最高权力与权威,掌握有最终决策的权力。但总统的这种领导权或决策权也是相对的。在现代政府治理方式下,各个职能部门具备成熟的社会管理方法和相对独立的运作模式。总统的领导作用在于如何启动决策程序和分配任务,一旦总统对职能部门的把控力度降低,政策将更多地反映职能部门的专业标准、方案与利益诉求。在美国的历史上,里根总统就是一个以放任风格领导职能部门的极端案例。他对领导职责的刻意逃避,导致了两类严重的行政困境:一是大量政策议题无法启动,只能在职能部门的日常标准操作程序的框架内推进;二是总统的幕僚团队、行政部门首长之间出现意见分歧乃至内斗之时,总统的协调仲裁功能缺位,导致政策久拖不决。这都给美国的内政外交留下了重大的影响。
二、放任式领导风格
根据里根对决策议题的领导和介入程度,政府在决策上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即最常见的放任模式和罕见的管控模式。放任模式是里根执政生涯中最常见的领导模式。当里根遇到政策议题时,“并不会对其花费多少精力,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做决策”。他在内阁会议上会走神、涂鸦、打瞌睡。[9]所以,里根喜欢将具体事务交给下属去做。他自己投入精力最多的事情是演讲和准备演讲,最热衷的事情就是度假和睡懒觉。[10]
在此模式下,由于总统领导的严重缺位,大多数政策要么在启动后就被委派给行政职能部门处理和抉择,要么就长期处于未激活、未启动的状态,而是由行政职能部门按照以往的政策惯性或日常标准操作程序,对问题做出被动式的回应。里根上任第二年,美国舆论就注意到里根独特的领导风格,并做了如下评论:“里根先生经常做的只不过是批准顾问们的决定罢了。”[11]毫不夸张地说,里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人……真正的决策者与其说是里根,不如说是为其理念而战的工作人员。[12]
里根政府刚刚上任,中美关系立即就成为里根领导风格的受害者。在竞选阶段大放亲台言论的里根,引起中国政府的警惕。为彻底解决美国对台军售问题,里根政府甫一上任,中国政府就开始向美方施压,希望能开启谈判进程解决对台军售问题。但很少过问政事的里根,既不在意中方的诉求,也未认真对待这一议题,只是将此事交予国务卿黑格处理。被迫无奈的中国政府只好利用坎昆会议的首脑外交机会,通过政府总理向里根提出中美谈判解决对台军售问题。甚至外长黄华罕见地动用了最后通牒,才迫使里根同意开启谈判。[13]
更为罕见的是,中美围绕对台军售问题的谈判,明明已经构成了中美外交关系的危机,却未能让中美关系纳入里根的决策议程。甚至直到1984年初,中美两国领导人即将展开互访之际,美国政府才发觉,里根上任三年以来,尚未制定对华政策。与中国的互动要么是遵循惯例,要么是按照国务院的专业程序做出回应。因而在两国领导人互访之前,匆忙通令各个职能部门合作,制定出了正式的对华政策。[14]
访华结束之后,里根再次将对华政策与事务交由国务卿舒尔茨操持。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鲍威尔也曾回忆:“总统的消极管理风格让我们身负重担。直到我们适应了这一风格后,仍觉得很难在没有明确决策的情况下执行建议。……弗兰克(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曾抱怨:‘我的天,我们不是雇来领导国家的!’”[15]回顾里根执政时期,放任的领导风格几乎占据着主导地位并贯穿始终。但此类领导风格并非成熟的领导模式,在处理日常决策议题时,放手让职能部门和专业意见驾驭决策可以收到奇效。但面对复杂的决策议题时,任何内政或国际环境的干扰因素,都可能将政策引向不确定的前景,因而需要全面的情报与方案备选项,而这恰恰是放任式领导风格无法完成的。里根执政期间面临的最大危机——伊朗门事件就诠释了这一原理。[16]
三、罕见的管控式领导风格
在管控模式下,里根即便因为罕见的兴趣或危机而专心驾驭行政系统,也会因为专业知识的欠缺而使决策带有极强的主观情感特征。在管控式领导风格下,里根决策的原则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依赖朴素的意识形态等感情、感性因素作为取舍备用方案的标准;一种是按照自己最钟爱的人际关系标准打造和维系自己的内阁班底。法国总统密特朗曾经对施密特评价过里根:“这是一个没有想法、没有文化的人,他肯定算是那类自由主义分子,但透过表象你会发现他并不笨,他有很强的感知力,有极其良好的意图,遇到用智力无法理解的事情,他就用本能去感知。”[17]因而当里根介入和管控决策进程的时候,他对决策备选方案进行抉择时,主要依赖的是意识形态、从生活中积累的朴素的感情、幕僚团队和第一夫人给他的建议。
里根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自身的感情和朴素的生活阅历,而非依赖专业知识的支撑。演员出身的里根没有任何外交经验和外交专业培训的经历,他不喜欢出国旅行,也没怎么出过国。距离他任职最近的出国旅行还是1978年的时候,他为准备总统竞选而进行的出访,而台湾岛则是他到访的目的地之一。此次访问进一步密切了里根及其幕僚与台湾当局的关系。[18]因而,对台湾当局形成的亲台姿态成为他对华政策当中最顽固也是最稳定的底色。在里根所有涉及台湾问题的言谈中,尤其是在中美围绕对台军售问题而展开激烈谈判的过程中,他都坚持对台湾的责任和义务。[19]这些亲台理念并非源自任何的国际关系原理或外交原则。
按理说,一个对苏联发起新冷战的强硬总统,本应急切拉拢中国政府,利用当时的中苏对抗,强化自身的外交资源。但里根的现实选择却暴露出他在决策中对直觉的倚重。需要指出的是,里根的幕僚对他的这种朴素的直觉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不少幕僚都与台湾当局有着长久的利益联系,并持亲台立场。他们包括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迪弗、财政部长里甘、总统法律顾问米斯等。[20]当然,对里根影响最大的要数他的夫人南希。她“是里根的白宫里一支强大得惊人的力量”。她清除过所有位高权重的里根幕僚,最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白宫办公厅主任”[21]。甚至连美国政要也提醒中国驻美外交官,“不要低估里根夫人的作用”。[22]
除去危机情形,里根还会在内阁班底秩序失控时开启管控式领导风格。里根有着极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喜欢与人为善。在总统任期内,他一直希望“他的属下之间一团和气,洋溢在一团和气的氛围中”。[23]但他经常性的放任式领导风格,却容易放大行政部门间的协调困难,极端时甚至会出现属下争权内斗的情形。这又逼迫里根不得不开启管控式领导风格,理顺下属之间的关系。
黑格与里根团队的其他成员存在着政策和权力的矛盾,其易怒的性格又使这种矛盾逐渐变得尖锐而不可收拾。最后,黑格几乎与里根的每一位高级顾问都矛盾频发。对华政策一度就成为黑格与艾伦、温伯格、李洁明等人争斗的战场。[24]里根认为黑格只想在内阁中大权独揽,在外交政策上排挤所有阁员甚至里根自己。这既导致政府运作的不畅,也破坏了里根对祥和的人际关系的坚守,因而解除了黑格的职务。[25]
越来越多的政策研究成果表明,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决策才是决策过程中的常见模式。[26]这实际上对领导人的领导风格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过于放任的领导风格可以充分激励职能部门的专业建议,但也存在部门争权导致的决策拖沓,贻误时机;过于严紧的管控领导风格可以防止混乱的决策过程,但却又把精力和知识能力有限的领导人逼入亲力亲为的决策全过程,把政策陷入和专业知识隔绝的险境。明确区隔领导人的协调、抉择功能与职能部门的情报及方案规划功能,可能是克服领导风格这种两难境地的出路。随着西方一批政治素人裹挟着民族主义情绪上台,可能将领导风格的这种两难境地推向极端甚至是极端之间的摇摆。
[注 释]
[1]Thomas R. Dye and Harmon Zeigler, The Irony of Democracy: An Uncommo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olitics, 14th Edition [M].Boston, MA: Wadsworth, 2009: 1-2.
[2][3]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 About America: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 World Book, Inc,2004: 25, 26-27.
[4] 李道揆. 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下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61.
[5]张清敏. 对外政策分析[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91.
[6][7]格雷厄姆·艾莉森、菲利普·泽利科. 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M]. 王伟光,王云萍 , 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5:163-164,285-288.
[8]马克斯·韦伯. 支配社会学[M]. 康乐、简惠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
[9]How Reagan Decides, Time, December 13,1982, p. 15. Laurence Leamer. Make-Believe: The story of Nancy & Ronald Reagan [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3:344.
[10]Time, February 6, 1984: 23. Lou Cannon.Reagan [M]. New York: Putnam's, 1982:398.
[11]Howell Raines. “With Haig Leaving, Reagan Closes a Compatible Inner Circle,” New York Times, July 4, 1982.
[12]Mark Hertsgaard. On Bended Knee: The Press and the Reagan Presidency [M]. New York:Farrar Straus Giroux, 1988: 26.
[13]Donald Reagan. The Reagan Diaries [M]. New York: Harper, 2007: 10, 23, 45, 46.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261-262.
[14]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Premier Zhao Ziyang, January 9, 1984: 1-3.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 PR01513. The President's Visit to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pril 21,1984: 2-4.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 PR01529.
[15]Collin Powell. My American Journey [M].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334.
[16]David Mervin. Ronald Reagan an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M]. UK: Longman Group, 1990: 159.
[17]埃德蒙·莫里斯. 荷兰人:里根传(下册)[M].李小平等,译.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591.
[18]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M]. New York:Alfred A. Knopf, 1999: 115.
[19]Donald Reagan. The Reagan Diaries [M]. New York: Harper, 2007: 10, 46, 61-62, 75,76, 83, 84, 98.
[20]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178.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115.
[21]Mark Hertsgaard. On Bended Knee: The Press and the Reagan Presidency [M]. New York:Farrar Straus Giroux, 1988: 24. Jane Mayer and Doyle McManus. Landslide: The Un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84-1988 [M].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8: 380.
[22]张颖. 外交风云亲历记[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 2008: 60.
[23]Lou Cannon. Reagan [M]. New York:Putnam's, 1982: 376.
[24]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M]. New York:Alfred A. Knopf, 1999: 120.
[25]Donald Reagan. An American Life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0: 361-362.“The Phrase is Howell Raines”, New York Times, July 4, 1982.
[26]Gustavo Barros. Herbert A. Simon and the concept of rationality: Boundaries and procedures. Brazi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0, n° 3 (119),July-September/2010: 457-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