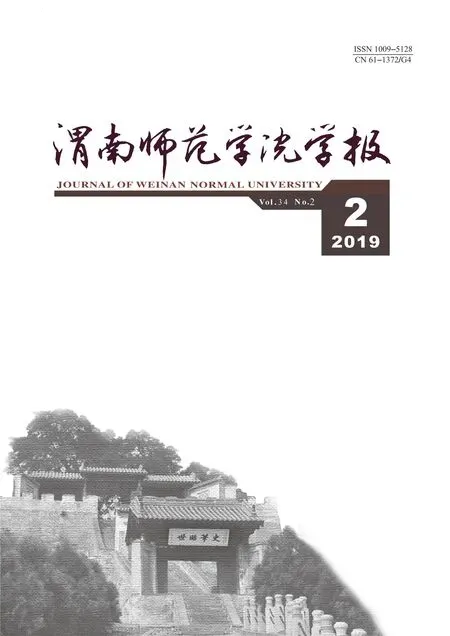宾纳与江亢虎英译《唐诗三百首》研究
朱 斌
(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重庆 400031)
一、引言
《唐诗三百首》是中华文明千年的文化积淀,承载着人类文明的精髓,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刊行以来,便成为国内外传播最广的唐诗选本,英译本已达20余种。1929年,美国诗人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1881—1968)与中国学者江亢虎(Kiang Kanghu,1883—1954)合作翻译的《群玉山头:唐诗三百首》(TheJadeMountain:AChineseAnthology: 300PoemsoftheT’angDynasty)为英语世界的第一个全译本。1973年,静霓·韩登(Innes Herdan)的英译《唐诗三百首》(TheThreeHundredTangPoems)在中国台湾出版;1987年,许渊冲、陆佩弦和吴钧陶编译双语版的《唐诗三百首新译》(300TangPoems:ANewTranslation)在中国香港出版;2009年,彼得· 哈里斯(Peter Harris)英译的《唐诗三百首》(ThreeHundredTangPoems)在美国纽约出版;2011年,杰菲里·沃特斯(Geoffrey Waters)、迈克尔·法曼(Michael Farman)和戴维·伦德(David Lunde)合译的《唐诗三百首》(ThreeHundredTangPoem)在美国纽约出版;同年,曾培慈(Betty Tseng)的《英译唐诗三百首》(EnglishTranslationof320TangPoems)通过网络公开发行。[1]然而,在众多译本中,宾纳和江亢虎的译本在英语世界接受度最高、影响最为持久,甚至被“经典化”,不失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又一成功案例。描述两人合作翻译的缘起、过程和策略,分析考察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译者动机,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一文化现象的理解,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二、翻译的缘起
(一)社会文化语境:战后中国文学迎来进入美国文学系统的契机
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浩劫惨不忍睹,它将资本主义的弊端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一些西方进步人士心理上发生了巨变,开始对曾引以为豪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心生怀疑。他们察觉:“社会的严酷现实和人的复杂思想观念远不像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许多文学家、艺术家所描绘得那般美好。”[4]为弥补自身文化思想的缺陷,他们开始在本国文化之外寻求可资借鉴的良方。对大洋彼岸的东方文化的“意外收获”让他们欣喜若狂,因为“注重生活经验本身,注重感觉和体悟”的道家思想和禅宗思想正好弥补了西方惯用逻辑思维。[5]15战后西方人对东方的哲学、宗教进行了殚精的研究,甚至对于中国最无根据的迷信(算命、圆光、招魂等),都有人专门去研究考证,例如英国的罗基(Lodge),比利时的墨德林(Motherine)[6]275。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曾受邀作为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到中国讲学10个月,回国后在各大报纸上发表关于中国的文章,后出版专著《中国问题》(TheProblemofChina,1922)。他在书中指出:
我们的西方文明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用心理学家的话来说是精力过剩的合理化。我们的工业主义、军国主义、热爱进步、传教狂热、扩张势力、控制和组织社团,这一切都是因为精力太过旺盛。……我认为,从人类的整体利益来看,欧美人颐指气使的狂妄自信比起中国人的慢性子来会产生更大的负面效果。“大战”(一战)的爆发表明我们的文明中有那么一些瑕疵,而俄国与中国的情况则使我相信这两个国家能使我们分清对错。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7]7
可见,以罗素为代表的西方人士对西方思想的弊病已有清醒的认识。他也坦言,中国之行实际上是抱着寻求新的希望之心前往的,而事实证明他在中国找到了西方社会所缺失的品质和德行:“崇尚礼让、和气、智慧和美,懂得真正人生之乐的文化精神。”[8]117
引进新思想和新文化,翻译的作用自当不能被忽视。战后“许多美国一流的诗人、作家与学者纷纷投身翻译事业,积极参与构建新的文学规范”[9]198,渴望借助翻译中国文学探寻美国文化自救之路。此背景下,20世纪的头30年,现代英美诗坛积极向中国诗坛学习,在英语世界掀起了一股翻译中国诗歌的热潮,多部中国诗歌英文版相继问世。比如,克莱默·宾(L.A.Cranmer Byng)编译的《玉琵琶:中国古诗选》(ALuteofJade:BeingSelectionsfromtheClassicalPoetsofChina,1909);瓦德尔(HelenWaddell)翻译的《中国抒情诗》(LyricsfromtheChinese,1913);美国诗人庞德(EzraPound)根据欧·费诺罗萨(ErnestFranciscoFenollosa)手稿翻译的《神州集》(Cathay,1915);阿瑟·韦利(ArthurWaley,1889—1966)所著的《汉诗选译170首》(AHundredandSeventyChinesePoems,1918);弗莱彻(W.J.Bainbridge-Fletcher)翻译的《汉诗精华续编》(MoreGemsfromChineseVerse,1919);中国译者蔡廷干编译的《唐诗英韵》(ChinesePoemsinEnglishRhyme,1923),等等。[10]7-8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左右,英美文坛正处于吸收边缘文学的时期,中国古典诗歌迎来进入英美世界的良好契机。
(二)译者用心:“无心插柳”抑或“有心栽花”
1918年,宾纳与江亢虎相遇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时他们均在此任教。1920年,两人开始着手合作翻译《唐诗三百首》。论及两位译者的具体译介动机,有学者指出,江亢虎从事诗歌翻译纯属“无心插柳”,只是“处于政治低谷时期的一种情绪排遣”,而宾纳则是带有强烈的译介动机,属于“有心栽花”。[11]的确,宾纳对自身所处文化风貌的变迁和匮乏相当敏感。一战期间,他敏锐地意识到西方的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已不足以令他们感到满足,急需要向东方文化寻求自救之道。而正是基于此,宾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启了他的首次亚洲之行,一方面是逃避他非常反感的战争,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在异域国度找到本国文化所缺失的东西,以达到东西互补的目的。事实证明,宾纳的中国之行让他备受鼓舞,发现中国文化正是本国文化迫切需要了解和学习的。他回国后便开始潜心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12]47
宾纳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唐诗的热爱可能还源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宾纳自身对战争的极度反感与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性格特点不谋而合。中国历史上虽然战事连绵,但普通老百姓天性是喜好和平的。[7]154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些诗歌中看到根植于中国人民内心的和平主义思想。例如,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作品《新丰折臂翁》,该诗描述了一个普通老百姓为躲避服兵役,避免打仗,夜间自断右臂的故事。第二,《唐诗三百首》中包含了大量关于中国战争内容的诗歌:控诉战争之罪恶的诗,如杜甫的《兵车行》和高适的《燕歌行》;描写官兵疾苦和战争惨烈的诗,如王昌龄的《从军行》;批判战争给人民带来痛苦的诗,如金昌绪的《春怨》。宾纳深受一战之苦,他试图通过介绍关于战争题材的诗歌,唤起国民对战争的反思。
然而,宾纳对唐诗的热爱以及选择《唐诗三百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江亢虎的介入。可以说,没有江亢虎的指点,宾纳就不会从事《唐诗三百首》的翻译。据宾纳回忆,一接触江亢虎就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且在交往中发现他还是一位有教养的学者和能够激发兴趣的同道。此前,宾纳对亚洲文化可以说是知之甚少。然而,他在与江氏的交流中,后者言语中所提到的唐朝诗人深深地触动了他。[13]3-4在宾纳看来,唐朝诗人生活中的佛教和道家文化正好可以弥补基督教文明的不足,因此,他请教江亢虎是否可以和自己合作翻译王维的诗,而江亢虎提议他翻译《唐诗三百首》(618—906),他立即欣然接受。[12]5-6实际上,之所以推荐《唐诗三百首》,江亢虎本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对于那些受过良好国学教育的中国学者而言,《唐诗三百首》可能不是他们青睐的读本,因为他们自小便习之,已烂熟于心。然而,对于没有相关背景知识的西方读者而言,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要恰当理解和鉴赏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他们首先必须在学校就开始熟悉每个中国儿童所熟知的作品,然后才能开始更深层次的学习。”[14]17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江亢虎和宾纳翻译《唐诗三百首》的抉择是明智之举。
三、翻译的过程和理念
江亢虎为知名的中国学者,精通双语,而宾纳为著名的美国诗人,不懂汉语。这两位译者是如何开展翻译合作的? 他们又秉承了怎样的翻译理念?
(一)翻译过程:“两道手”翻译模式
《唐诗三百首》的翻译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首先由江亢虎将诗歌直译成英文,也就是语际翻译;其次由宾纳将江氏的英译本润色,转化为地道的英语诗歌表达形式,也就是语内翻译[11];最后再交由江氏修订校对,并提供注释和传记信息。他们的交流沟通往往是通过书信。这样的翻译模式在西方早期的翻译史上例子很多。有学者指出:“翻译中国诗的艺术是意象派运动的一个副产物……中国诗最好的译者多半是诗人或爱好写诗的人,依靠别人译的初稿来翻译。”[15]479比如,庞德翻译的《中国》(1915))和艾米·洛威尔翻译的《松花筏》(1921)。这样的翻译模式实际上是郭沫若所倡导的“两道手”翻译法。他的女儿郭庶英、郭平英在整理《英译译稿》的后记中指出:
至于译诗,他推荐“两道手”的译法,先由懂外文的人直译成原文,再由诗人进行诗化。这样的“两道手”对于父亲来说,正可以一身而任之。他既通外文,又是诗人。所译是诗,译文同样是诗,有时候诗意甚至更浓。父亲的这种翻译风格,自然也是贯穿在他晚年的这一本中。[16]147
对于这样的“两道手”翻译模式,美国诗人蒂金斯(Eunice Tietjens,1884—1944)曾在《诗歌》(Poetry,1930)称,《唐诗三百首》英译本是迷人而学术的、敏感而实际的、人性而可信赖的。其高度肯定了这种翻译模式并宣称,一个受人敬仰的中国学者与一个知名的西方诗人的合作翻译可谓是理想的合作模式,因为在该模式下任何一方合作者可能缺失的品质可以得到另一方充分的补充。[12]47
(二)翻译理念:严谨的翻译态度
“两道手”翻译方法的成功关键在于:合作者要志同道合;合作者水平要高;合作者可以优势互补。马会娟将这种不懂汉语的西方诗人与中方双语人士合作翻译诗歌的方式称为“非正规的翻译操作模式”[17]。她指出,选择理想的合作伙伴至关重要,因为翻译的最终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作者的水平。例如,由于合作者的水平不高,美国诗人芬科尔(Donald Finkel)翻译的诗集 《破碎的镜子:中国民主运动诗歌选》(ASplinteredMirror:ChinesePoetryfromtheDemocracyMovement)的翻译效果就不理想。[17]然而,宾纳和江亢虎可算是遇到了知音,两人对于学问和翻译均是态度严谨的,可算是理想的合作伙伴。首先,宾纳在翻译《唐诗三百首》过程中可谓是“煞费苦心”。据他本人回忆:“他(江氏)将所译的英文初稿交我后,我会努力地进行打磨润色,然后我们就能够对译本的准确性(accuracy)进行翻译校对,一般这样的工作前前后后要反复很多次。”[13]6-7为了了解几种中国花草鱼虫的拉丁学名和相对准确的英译,他曾多次致信向身处纽约的中国学者许地山(Hsu Ti-shan)请教。[18]111-112其次,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必然面临一个抉择的过程:是翻译其字面意思,还是翻译其比喻意思呢?这一难题在诗歌翻译中尤为突出,因为诗歌欲真正表达的意义往往在于比喻意思,而比喻意思的理解往往又是最难把握的。对于这一点许多人可能会错误地认为,宾纳所作的工作仅仅是将江氏的英文译文转换成了近似的英文诗歌。其实不然。有学者就曾指出:“他(宾纳)对诗歌的形式和内容作了大量的研究。通过综合他个人情感(sensibilities)的过程,他和江亢虎反复商讨译文,写出的诗歌仍然是最忠实于原诗精神的诗歌。”[12]47换言之,宾纳所谓的准确性,更看重的是译诗要符合原诗的精神。
译文的准确度主要是依靠江亢虎来把握的,宾纳本人也对准确度极其重视。他在1928年写给江亢虎的信中,强烈要求给他的译文做最后的检查,写到:“不要……让我的译本不准确。”[14]24何为不准确?在Burton Watson看来:“对原文的措辞和句法微小的偏离不算是不准确,那些对作者意图彻底地扭曲或者误释的翻译才算不准确。”[14]23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宾纳的译文几乎奇迹般地避免了基本错误。而这一切自当主要归功于江亢虎”[14]23。
江亢虎的翻译态度又如何呢?他是否有自己的译诗理念呢? 实际上,直接论述江亢虎如何从事翻译以及他对翻译工作所秉持的翻译态度的相关文献几乎没有。然而,我们通过对江氏在不同场合的一些相关言论的分析,可以管窥江氏关于译诗的理念的“蛛丝马迹”。
江亢虎对中国文化非常自信。1920年10月4日,他在江西教育会讲演时针对国人对本国文化的“不自信”,甚至“怀疑”,表示很不满。在他看来,“外人(西方人)抹杀我们的文化,我们不去怪他,若是本国人也都自己看不起自己,那就是思想上亡国,实在是最可痛心的!” 同时他也指出:“文化本身,自有价值,自有魅力,不必定要借着国势去传播。”[6]273然而,在面对西方人士对我国文化曲解时他自己又表现得非常生气。他在美国深切感受到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和歧视,著作中大量存在“对中国事物的歪曲描写”,而那些西方著作的作者“很少有人懂得中国话”,而“能读懂中国典籍的汉学家更是少之又少”[19]。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最终解释权应该是我们国人,而不是外国人。1933年,江亢虎曾在《纽约时报》上发文,严厉批评当时获普利策奖的赛珍珠,称她“在作品中恶意丑化中国人形象”,对其在对中国的细节描述方面的谬误进行了指正,认为赛珍珠没有权利解释中国问题,而只有中国人才能干这个事。[20]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江亢虎的翻译态度也是非常严谨的,更加强调“以我为本”的思想,希望准确地表达中国文化。
四、翻译的策略
有学者指出,宾纳所译《唐诗三百首》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当时人们对于中国元素的持续热爱;第二,该版本可读性强,富有诗学情感,比一般译本准确度高;第三,赞助人阿瑟·韦利和雷克斯罗斯对诗歌的高度评价可能帮助推动了诗歌的影响力。[21]309实际上,除此之外,译本的受欢迎程度与译者巧妙地运用翻译策略紧密相关。一种语言文字“移植”到另一种新的语言环境中时,为了避免“水土不服”,必然要尽快熟悉目标文化的土壤和水分。要达到这一目标,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就要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为了迎合目标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对原作进行“创造性叛逆”。而这种“创造性叛逆”表现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译者对原作的客观背离”[22]106。宾纳和江亢虎两位译者对《唐诗三百首》的创造性叛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诗歌翻译形式的创造性叛逆:自由体的运用;第二,诗歌战争意象的创造性叛逆:战争意象的凸显;第三,诗歌文化负载词的创造性叛逆:文化意象的选择性再现。这种创造性叛逆可谓是极其成功的,不但将原诗的精神巧妙地表达出来,而且让原文在异国他乡成功地得以重生,被赋予了“第二次生命”。
(一)诗歌形式的创造性叛逆:自由体的运用
戴维·康诺利(David Connolly)认为:“诗歌形式要随时代和社会价值的变化而变化,在某种文化或某个时代里具有意义的形式在另外的文化和时代里可能没有效果了。”[10]90格律诗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可谓大行其道,如果诗歌中没有了韵基本上就不能称作诗歌了。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在一战前后,传统的格律诗体由于因形损义、刻板单调和陈词滥调等弊端逐渐遭受质疑和挑战。许多西方诗人开始打破格律诗的限制,大胆尝试多样的诗歌创作形式,这也必然影响到诗歌翻译。[10]90-91然而,当时采用自由体译诗的并不多,仅有庞德的《神州集》(1915)、威利的《汉诗选译170首》(1918),以及埃斯柯夫人和洛威尔合译的《松花笺》(1921)。宾纳虽然不是自由诗的革新者,但他在自己的翻译中运用了该新形式,足以体现其敏锐的判断力和远见。这也是为什么时至今日它们仍然可读和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原因之一。[14]26宾纳曾致信桑德堡(Card Sandburg)说明用自由诗译中国古诗的用意:
我希望把中国诗译成人性的语言,这样西方人就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要他们注意到我的努力,他们会看到中国人简朴的人性,也看到我们精神中虽然有那么多恶毒的东西,也有与人类相通之处;我很高兴能够揭露那些文化学的翻译家,他们把文字搞得不东不西,而且纠缠于他们认为是五彩缤纷的新奇形象,他们不知道应该当作的事情是把这些古代诗人那种活生生的简朴无华的风格传达出来。[18]204-205
可见,宾纳对传统格律诗译诗的现状已严重不满,批判那些固守传统不懂变通的翻译家未能真正翻译出中国诗的精髓,而提倡用不一样的方式把中国古代诗人那种独特风格表达出来。这个方式就是当时正在兴起的自由体译诗风。显然,宾纳在翻译过程中省略了原诗的韵律韵脚,顺应了当时的主流诗学规范,与新诗运动总趋势保持了一致。自由体译诗成功地避免了因韵损义的风险,更加到位地译出了原诗的精神。试看宾纳对杜甫《春望》的翻译。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掻更短,浑欲不胜簪。
Though a countrybe sundered, hills and rivers endure,
And spring comes green again to trees and grasses.
Where petals have been shed like tears,
And lonely birds have sung their grief.
After the war-fires of three months,
One message from home is worth a ton of gold.
I stroke my white hair. It has grown too thin,
To hold the hairpins any more.
(二)诗歌战争意象的创造性叛逆:战争意象的凸显
总的来说,译者译诗遵从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如果我们就借此认为《唐诗三百首》译本可以在英美世界大行其道,那未免有些太过简单了。实际上,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于译本在基于目标文化传统规范遵从的前提下对诗歌进行了巧妙的创造性叛逆。《唐诗三百首》中关于战争题材的诗歌较多,译者在处理这些诗歌时巧用心思,将战争主题显化,以迎合目标读者对战争主题的期待。试看他们对王昌龄《闺怨》的翻译。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Too young to have learned what sorrow means,
Attired for spring, she climbs to her chamber…
The new green of the street-willows is wounding her heart—
Just for a title she sent him to war.
该诗巧妙地描写了一个丈夫在外征战的妻子的心理变化过程:从先前的不知愁到后面的后悔。宋朝陈师道《九月九日魏衍见过》诗中有曰:“一经从白首,万里有封侯。”在古代,“封侯”,即封侯拜爵,泛指显赫功名。往往只有在军功上有所建树,才能有机会获得封侯的赏赐,所以“觅封侯”就成了从军的代名词。此处,Innes Herdan[22]652、Peter Harris[23]212、许渊冲[24]48分别将封侯翻译成“seek official appointment”“looking for fame and glory”和“seeking fame”。这三种翻译应该说都比较忠实于原文的意思。而宾纳却将其翻译为“war”。译者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前面我们提到宾纳本身是非常强调译文的准确性的,再加上中国学者江亢虎的帮助,按理不应该不能正确理解这句话的意思。结合译者本人对战争的反感这一事实,不难得出此处他的有意“误读”或许是想借中国怨妇之口表达自己对一战的痛恨之情。试想,美国的反战民众在读到此诗句时,会有何感想?他们势必会将中国人民饱受的战争之苦和自己本国正在发生的战争想联系起来,从而拉近了当时西方读者与千年前的中国民众的心理距离。再看对王翰《凉州词》的翻译。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They sing, they drain their cups of jade,
They strum on horseback their guitars.
Why laugh when they fall asleep drunk on thesand?
How many soldiers ever come home?
古时候的沙场指的就是战场的意思。许渊冲[25]13和Innes Herdan[23]658将其译为“battleground”和“battlefield”,应该是比较准确地传达出原文的意思。宾纳并未将此概念译为通俗意义上的战场,而是故意将其译为“沙地”。我们知道,沙地的环境恶劣,本身行进就比较困难,更何况在这样的地方打仗?其残酷的环境可想而知。所以说,此处为了迎合目标读者对残酷的战争的认识,译者对当时的战争环境的残酷性的一种夸张式想象。这样做的目的或许可以让读者在阅读到此处时,立即联想到一战的民不聊生、伤亡惨重的凄凉场面,从而引起战争时期人们的共鸣。
(三)诗歌文化负载词的创造性叛逆:文化意象的选择性再现
美国著名翻译家、汉学家华兹生研究了《唐诗三百首》英译本后指出,为了让对中国诗歌不怎么熟悉的英语读者能快速准确地欣赏中国诗歌,宾纳在翻译中“用一般的地理词汇去替换原文中具体的地点名字或者干脆回避典故”[14]26,以让译文的可接受性更强。
为了考虑读者的接受,译者在处理一些西方不熟悉的概念,尤其是文化负载词时,往往做了一些合理的“妥协”,选择性再现了部分文化意象。例如使用西方熟知的词语去近似表达中文的文化概念,因为这样的词本身在西方没有相对应的概念,而且近似地表达本身不影响读者对整首诗意思的表达和接受效果。例如,将王翰《凉州词》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中的“琵琶”翻译成西方乐器“吉他”(guitar)。“琵琶”这种弹拨乐器大约在中国秦朝出现,在西方没有完全一致的乐器。此处,译者将其近似译为吉他,虽然意思不完全准确,但不影响整首诗意思的理解,反而更加利于目标读者的理解;张籍《没蕃故人》诗句“前年戎月支,城下没全师”中的 “月支”译为现代英语地名“Tibet”。可以说,译者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始终是以目标读者的接受度为第一考量标准。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对杜牧《遣怀》的翻译。
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With my wine-bottle,watching by river and lake,
For a lady so tiny as to dance on my palm,
I awake, after dreaming ten years in Yangzhou,
Known as fickle, even in the Street of Blue Houses.
Note: The Blue Houses are the quarters of the dancing-girls.
这首诗追悔了诗人常去妓院、空度年华的生活。“青楼”在古诗中常有两种意思:一指用青漆粉刷的豪华房子,常指帝王之居。例如,《随园诗话》有曰:“齐武帝于兴光楼上施青漆,谓之青楼”;二指歌馆妓院,例如,《捣练篇》中有:“月华吐艳明烛,青楼妇唱衣曲”。此诗句中,许渊冲[25]321将其翻译为“mansions green”,并作注“brothels”;Peter Harris[24]85将其翻译成“a libertine of the blue houses”;Innes Herdan[23]722将其翻译成 “a drifter even in the blue pavilions”,并作注 “The blue pavilions were the houses of courtesans”。可见,上述译文普遍将“青楼”理解为“妓院”,基本上是忠实于原文意思的。宾纳并没有直接翻译成西方相对应的概念“whorehouse”或者“brothel”,而是进行了“创造性误读”。他首先在正文中翻译成“Blue Houses”, 基本保留了原文意象,接着在后面作注“舞女的住处”(The Quarters of Dancing-girls)。江亢虎国学底子深厚,不可能不懂此处的青楼指的是风花雪月的妓院。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处理呢?正如宾纳译诗前沿所论,中国古典诗歌的意思可能会有多种阐释,往往他和江亢虎会反复讨论,然后选择他们两人更喜欢的意思进行翻译。显然,这样的处理方式也是译者良苦用心的结果。他们试图借用西方现行的概念“舞女居住的场所”这一中性的意象去表达原诗中所表达的“妓院”这一消极意象,以树立中国文人的正面形象,以增强西方读者对中国文人的敬仰之情和认同感。另一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译者对读者的关照,好像在遥远的东方古代社会,那里的人们和现代的西方人士一样,都喜欢在歌舞厅和俱乐部里跳舞。这样的创造性叛逆自然拉近了原作与西方读者的心理距离,从而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五、结语
宾纳和江亢虎合作翻译的《唐诗三百首》在英语世界不断地重印和再版,而且被选为教材使用。2014年,赖夏传媒(Lionshare Media)基于他们的译本重新出版了《唐诗三百首》双语版,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仔细研究该合作翻译的缘起、过程和策略,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唐诗三百首》的翻译兴趣和版本选择源于目标文化对源语文化的需求,译者正是在顺应这一历史趋势的前提下结合译者的动机做出的明智之举。第二,“两道手”翻译模式和译者严谨的翻译态度保证了译本翻译顺利地开展。第三,为了顺应目标文化的主流诗学、意识形态,结合译者的个人目的,译者在翻译中对原文进行了创造性叛逆,表现为:译者运用自由体译诗对原诗的形式进行了创造性叛逆;译者通过有意凸显战争意象主题对原诗战争意象进行创造性叛逆;译者借助选择性地再现文化意象对原诗文化负载词进行创造性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