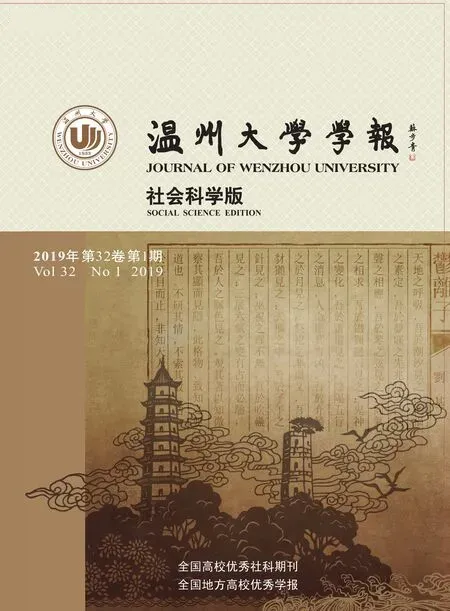晚清时期南戏《琵琶记》多形态西传与译介研究
张秋林
(温州商学院外语外贸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晚清时期,西方国家通过系列战争和不平等条约逐渐打开中国大门,迫使中国人民开始“睁眼看世界”,发轫于明朝末年的“西学东渐”思潮在晚期国人求强求富、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潮中达到极盛,近代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被大量引进中国。然而,文化传播向来是双向的,一切文化,不管它处于优势还是劣势,只要它是有活力的,就会发生传播。中国闭关锁国的局势被打破后与世界交往更加频繁,积淀了5 000年的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也被更多的西人发现、认识、并在更广范围内传播着,逐渐汇聚起一股“东学西传”之风。中国古典戏曲《琵琶记》作为“南曲之首”,因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和“风化”优先的创作宗旨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本文将梳理晚清时期《琵琶记》分别以诗、小说、戏曲的体裁形式在西方世界进行的文本译介传播。
一、节译的中国诗作
《亚洲杂志》(1816 - 1845)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创办,其创刊宗旨之一是向英语读者译介浩瀚的东方文学宝库,当时的西士认为印度文学、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是东方文学的3大来源,因此,自创刊起就与中国文学紧密《亚洲杂志》,成为西方世界传播中国译介文学与汉学研究的重要载体。1840年,《亚洲杂志》刊登了无名氏翻译的《中国诗作:〈琵琶记〉节选》(Chinese Poetry:Extracts fromPe Pa Ke)①本诗为匿名者翻译,载于《亚洲杂志》(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1840年第31卷107页。,匿名译者将《琵琶记·副末开场》中的【水调歌头】和第2出《高堂称庆》中【宝鼎儿】和【锦堂月】3段曲词巧妙组合成一首独立的诗。全诗以自然与人生关系为主题,通过对风卷云舒、花开花谢、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等自然景象的描写,抒发了诗人感叹人生立命、时光易逝的普世人文情怀。这种寓情于景,以诗意语言描绘大自然物象与心灵的真实情感,较符合当时英国本土流行的浪漫主义诗歌文化。以【水调歌头】曲词的英语译文回译成中文并与原文对比为例,以期探讨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文化意识,见表1(回译部分字体加粗的语句表示该句与原文语义出入较大)。

表1 无名氏译《琵琶记·水调歌头》的原文、英译与回译对比
首先,译者因不熟悉中文句法,僵化理解某些词语而出现误译,如“少甚”(不缺少)误解为“缺少”;“琐碎”(散碎)误解为“锁被打碎”;“不关”(与……无关)理解为“没有关隘”。其次,译者因对中国戏曲文学常识及中国文化掌握不充分而出现随意发挥的译介现象。这段曲词位于《琵琶记·副末开场》开篇之首,本是作者表达著书立意的关键之笔:“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1]即一部戏剧作品如果没有起到教化作用,纵然故事精彩也谓徒劳无功,强调《琵琶记》与众多其它戏文的区别在于强调“风化”作用,但译者将之误译为“卷风袭来无关可当,却又随心悠然离去”,描述了大自然中的“风”既能所向披靡,席卷一切,又可风轻云淡、怡然自得的双重特性。原文中“知音君子,这般另做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几句原本是作者期待未来遇上知音读者,不要着眼于戏中的诙谐动作、语言或是词曲宫调,而是从故事内容切入评判剧作水平之高低,这儿的“知音君子”是指能够懂作者心声的读者,可谓知己,译者却将其泛化为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正人君子”:君子不浮夸,不戏谑,但求能拥有孝子与贤妻,与作者的本意相去甚远。
尽管译文存在一些误译,但毋庸置疑,译者是站在尊重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最大限度地忠实于中国文化的呈现。《中国诗作》的标题用最直白的方式向中国诗致敬,其脚注不仅介绍了原诗的出处、原作者高则诚的名字,还对“芸编”“神”“风”等文化词加注解释,此外,译者对【宝鼎儿】曲词中“人老去星星非故,春又来年年依旧”一句感慨颇深,还在脚注中补充了几段与本句意思相近的中国诗文,分别选自《中国少年百科全书》(The Chinese Juvenile Encyclopedia)和马礼逊字典(Morrison's Dictionary),补充的诗句与正文诗句把中国诗词中常见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意境渲染得淋淋尽致,巧妙地为西方读者构建起一种启发性、互文性的解读。西方的坚船利炮尚未彻底打开国门之前,无名氏的译文整体彰显出译者对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尊重。19世纪中叶前,除《亚洲杂志》外,西方有关中国研究的英文刊物寥寥无几,为此,《亚洲杂志》成为东方文学研究的主流期刊之一。这篇刊登在《亚洲杂志》的《琵琶记》节译诗文,虽然还无法让西方读者得知《琵琶记》是一部怎样的中国戏曲作品,但至少让读者对中国戏曲的雅致语言、诗情意境有了一种初步的朦胧认识,《琵琶记》借着《亚洲杂志》在西方世界的广泛影响力而被一些英语读者熟知。
二、译介的“才子书”小说
来华传教士与汉学家是早期推动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传播的主导力量,译介对象从最初的儒家典籍逐步扩展到小说、诗歌、戏曲等文学体裁。晚清以降,众多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译介表现出浓厚兴趣。国内学人[2]通过梳理《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32 - 1851)中相关文献,总结出传教士热衷研究中国小说有三点原因:一是为了学习汉语,降低语言障碍的需要;二是为了构建“中国形象”的需要,通过小说这面镜子折射中国历史、文化习俗、民族性格、日常生活等全方位形象;三是为传教工作服务。英国圣道公会传教士甘淋(G. T. Candlin,1853 - 1924)在《中国小说》(Chinese Fiction)中还提出了两个新的观点:一是为了构建世界文学框架的需要,“英国已经大量引进了俄、法、德等国的小说文学,现在有必要扩大到天朝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伟大、古老、鹤立独行的民族,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若将中国文学置之门外,我们将不够资格称是世界文学”[3]1;二是为了普及中国通俗文学的需要,因为西方有关中国道德、历史、诗歌等领域的介绍已硕果累累,但“即使是最博学且富同情心的西方读者,对中国丰富的小说文学知之甚少,几乎是一片空白”[3]2。
明末清初,文学评论家毛声山将自己评点的《琵琶记》命名为《第七才子书》。毛声山的点评探微析幽,其帮助世人重新认识了《琵琶记》的艺术价值和文学成就,并进一步明确了《琵琶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如清尤侗所言:“岂东嘉之才,当时未之或知者乎?三百余年,毛子出而表章之,而第七才子之名始著,则又东嘉之幸也”[4]。在西方,“十才子书”也是西人认识、评价中国小说的重要凭借,1820年,英国人汤姆斯在摘译《名相董卓之死》时首次提到“第一才子书”[5]的概念,此后,“才子书”作为评价中国小说体系的术语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借着“第七才子书”的光环,但凡论述中国小说的著述中多少都会提及《琵琶记》,但是,炫耀光环的副作用致使晚清时期大多数西士都视《琵琶记》为通俗小说,流于介绍故事梗概的表面,未深入戏剧体裁或范式的研究。如1897年,美国传教士丁义华[6]撰文《中国小说》(Chinese Fiction)逐一介绍中国“十才子书”的剧情并做简要评论,“第七才子书”《琵琶记》自然也在其列。1898年,英国传教士甘淋将《琵琶记》列入中国最富盛名的14部小说名单之中,并将其体裁定义为“戏曲小说”[3]44。汉学家翟里斯在《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对《琵琶记》的介绍[7]则是“为了剧情而剧情”,剧中连人物姓名都不曾提及,仅以“一个才华横溢的中国书生”“这个年轻人”“他的妻子”“他新娶的妻子”分别代替蔡邕、赵五娘、牛氏等男女主人公来发展剧情。下文重点介绍传教士甘淋对《琵琶记》的译介。
甘淋1878年入华,在河北一带传教,20世纪初期曾先后任汇文大学堂和燕京大学的神学教授。甘淋认为《琵琶记》“故事简明、语言自然、具有感伤力,是一部绝妙的文学作品”[3]45,特别值得推荐给西方读者。甘淋以夹叙夹议地方式介绍《琵琶记》的剧情,间接表达了个人对作品的理解和文化态度:“《琵琶记》中男性角色的行为动机不同于英国人应避免的雷区作法,男主人公蔡邕的行为也不同于相同处境下英国绅士会采取的行动”[3]45,换言之,甘淋依照西方价值体系,对《琵琶记》中的男性角色多了一份哀叹和期许即蔡公不应该过多干涉和强逼儿子去应试、牛丞相不应该蛮横包办女儿婚姻、蔡邕应表现得更勇敢以便捍卫个人婚姻。甘淋对《琵琶记》一夫多妻的大团圆结尾也持保留态度,认为“男主人心安理得与两位妻子一起生活,这是故事结尾的唯一不足”[3]49。然而,在这样一番坦诚评价后,甘淋又进行了换位思考,他表示能够理解原作者的设计意图,因为“我们必须从作者所处的社会风俗、情感习惯来阅读他的作品,这样一来,我们会发现作者用高超的技巧把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巧妙地结合起来”[3]45。可见,甘淋能够善意理解、接受文学作品中因文化、意识形态差异而引起的“陌生化”,对中国文学作品基本持肯定态度。
在传播中国通俗文学方面,甘淋认为像《琵琶记》这么优秀的作品非常有必要译成英文,尽管翻译难度很大。甘淋选译了《情诉荷池》的大部分戏文,笔者认为原因有二。首先,甘淋把《琵琶记》作为言情小说代表作进行了译介,而《琵琶记》全剧中最直接、集中体现男女情爱冲突的戏非《情诉荷池》莫属,戏中尤其以蔡邕与新婚妻子牛氏的一段充满潜台词的对白描写最为动人,隐约却细腻地传达出蔡邕既撇不下新人,又留恋旧人的矛盾心情。其次,《情诉荷池》全篇旁征博引,文采斐然,把中国通俗小说(戏曲)多诗词歌赋的特质凸显了出来。
在翻译策略方面,甘淋省去了戏文中的曲牌名与词牌名,把角色简化成人物在戏中的身份,如“生”译成“新郎”,“末”译为“侍从”,“贴”译为“新娘”,帮助读者理清人物关系。甘淋保留了原剧中“介”的特征,“介”是南戏中人物动作的提示语,如“生上”(Enter bridegroom),“生弹”(Bridegroom plays)。甘淋以无韵诗译原文韵文唱词,译文整体上做到了达意、传神和意境美。如“闲庭槐影转,深院荷香满”一句译为“The court with shade of locust tree is thick, and odors of the lotus weight the screens”[3]46,原句中“转”“满”二字极为传神,而译文中“thick”“weight”二词也生动再现了夏日时节,满院疏影斜斜,荷香飘荡的意境,显示了译者娴熟的文字驾驭翻译能力。甘淋坦言自己翻译《琵琶记》时,“为了如实地把原文的内容而不是形式呈现给读者,原文不得已做了很多的‘牺牲’”[3]45。分析译文特征会发现甘淋所谓的“牺牲”不仅包括因中英语言表义系统差异(译文无法保留原文的文字对称、押韵等结构形式),还包括删除原文中无关重要的内容(尤其是两段词曲间插科打诨的语句多有略去),使故事情节更加紧凑、集中,而最大的“牺牲”,或许是对原文中文化信息的简单化处理,例如以蔡邕【懒画眉】唱曲中的一小节为例[3]47(见表2)。
这节曲词包含了中国古琴文化史上舜帝做五弦之琴,伯牙鼓琴与钟子期成为知音以及伯牙创作传世名曲《水仙操》等几个重要典故,译文没有加注解释典故内涵,而是把原文作者借用典故要想表达的语境情感挖掘出来,如“南熏”译为“the perfumed south”,“流水共高山”译为“the running streams and lofty hills”,“似离别当年怀水仙”句中没有出现与《水仙操》中任何与伯牙相关的词语,而是情景化为蔡邕一想起当年离家时亲人脸上的愁云就倍感心痛,思乡之情就愈发浓烈之神态,译文恰如其分地还原了蔡邕“宦海风波,已尝恶趣;故乡离别,何日去怀?”[8]的伤感情绪,实为妙译。总之,甘淋将《琵琶记》当做通俗小说推荐给西方读者的动机决定了他的译文更注重传递原作中的情节及人物形象的塑造、细节的描写等要素,而不是深挖文字所蕴含的中国文化。毕竟通俗小说译本只有减少桀骜难懂的文化术语才能适应更广泛读者群的需求。

表2 传教士甘淋译《琵琶记·情诉荷池》节选译文
三、编译的戏剧
1841年,法国汉学家安托万·巴赞(Antoine Pierre Louis Bazin)(1799 - 1863)翻译的《琵琶记》法译本由巴黎皇家图书馆出版。巴赞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茹理安·儒莲(Julien Stanislas)(1797 - 1873),在中国戏曲翻译与研究方面功底深厚,他在翻译《琵琶记》之前,已完成了《㑇梅香》《合汗衫》《货郎旦》《窦娥冤》4部元杂剧的翻译工作,巴赞在《琵琶记》的译本中充分显示了其汉学家的专业功底及翻译特色。
译作正文前依次是译者导言、序言、全剧人物表和剧情梗概介绍。译者导言部分宏观介绍了《琵琶记》的艺术价值、翻译目的、中文版本等主要问题。巴赞指出“我们有理由说,高则诚就是英国的莎士比亚,他作品的每一个字词都会引发评论家的点评”[9]X。巴赞向西方读者译介《琵琶记》的原因:“帮助欧洲读者了解14至15世纪这百年间戏剧艺术在中国的发展状况”[9]XI;“通过对译作前附录的序言作横向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学批评在康熙年间取得的进步”[9]XII;“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宗教及哲学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确切演变情况”[9]XIV。巴赞还说明自己翻译《琵琶记》参考的3个中文版本,“翻译时,为方便自己,我时而依据这个版本,时而依据另一版本”[9]XIX。第1个是皇家图书馆版,该版最大的优点是内含标注符号和42张版画;第2个是程士任版本,文内含有评注;第3个是其老师儒莲的翻译版本,这个版本与皇家图书馆版本几乎相同。李声凤[10]根据巴赞在译者导言中的记述亲临法国国家图书馆查核后进行确认,巴赞所提的第1个版本收录于《西厢琵琶合刻》,大约近于国图所藏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汪光华玩虎轩刻本。第2个版本为《成裕堂绘像第七才子书》,正文前有雍正乙卯(1735)程士任所作《重刻绣像第七才子书序》,大约为雍正乙卯程士任校刊本之翻刻本。总之,巴赞在译作正文前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与《琵琶记》息息相关的丰厚“副文本”。其尤其强调《琵琶记》不同版本的差异,从毛纶对《琵琶记》的点评以及附录程士任所作《重刻绣像第七才子书序》中反观中国文学评论的发展态势,做到了一名汉学家开始一部译作前应有的专业态度和专业实力。
巴赞将《琵琶记》第1回目《副末开场》改为《剧情梗概》,其巧妙设计了“舞台监督”一角代替原文的“副末”角色,“舞台监督”开演前与演员对话,自然完成戏情介绍并过渡到正戏。
(舞台监督拉开帷幕,演员们聚集在演出大厅里)[9]23
舞台监督(对演员们说):先生们,今天你们要给我们展现一段什么历史故事?你们要表演唐朝的戏剧吗?
演员们回答:我们将表演《琵琶记》也叫《三不从》。
舞台监督:哦,哦!《琵琶记》!那你们要让人们多笑一点,少哭一点。不管怎么样,开始演出《琵琶记》,但是,等一下,我先介绍一下故事梗概。观众们至少要知道这部戏剧的主题。
舞台监督还向观众解释法译本所作改动的原因:“先生们,我不想让这个表演占据太多时间,我们今天尝试完成表演;删减一些无关重要的部分。”[9]26舞台监督提到的“删减一些无关重要的部分”即指巴赞译本对原文回目所做的相关调整。《琵琶记》中文回目原有42出,巴赞《琵琶记》法译本经过改写、删除、整合相关回目,最后仅剩24场。对照中文原作回目,巴赞译本回目主要变动如下:原作《副末开场》(第1出)改成译作中的篇首剧情梗概;原作《蔡公逼试》(第3出)提前至译作的第一场;原作《杏园春宴》(第10出)和《奉旨招婿》(第12出)合并改写为译作的第6场;译作全剧在《书馆悲逢》中结束;《琵琶记》中文回目共有16出在法译本中被删除,分别为《高堂称寿》《南浦嘱别》《临妆感叹》《官媒议婚》《金闺愁配》《强就鸾凤》《官邸忧思》《中秋望月》《几言谏父》《路途劳顿》《张公遇使》《散发归林》《李旺回话》《风木余恨》《一门旌奖》。巴赞巧妙地利用中国戏曲中“剧中人”之口阐述自己对原文本所作的改动,既体现了译者对原作的尊重,也发挥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巴赞《琵琶记》法译本遵循了西方戏剧剧本结构,每场开篇增加了出场人物和故事发生地的介绍,这是中文原作没有的。法译本删除了原作中的大部分曲词,仅保留对推动剧情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少量曲词,每段曲词前用文字“(他唱)”或“(她唱)”提示,这些被保留的唱段类似西方戏剧中的独白,用以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情感状态,唱词和宾白都以无韵文进行翻译,显然,巴赞的译本是以人物对白为主、少量唱段为辅的共同合力下完成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巴赞译本与甘淋的小说译本一样,保留并发扬了中国南戏中“介”的特色。巴赞译本中 “介”的数量远远多于原作,其添加了许多描写人物神情、情绪状态的“介”,如第1场中出现的“介”有:蔡邕(愁眉不展地)、蔡邕(唱)、蔡邕(看起来很激动)、蔡邕(跪下对天发誓)、张太公(边唱边走上台)、张太公(向蔡邕行礼,蔡邕回礼)、张太公(唱)、蔡员外和蔡母(进入舞台)、蔡母(激动地对蔡邕说)、张太公(笑眯眯地)、蔡母(生气地)等,为此,巴赞《琵琶记》法译本不仅是一部可读的文本,也是一部可演的剧本。
从宏观角度分析,巴赞的《琵琶记》法译本采用了编译策略。编译是指“为了更适应特定的读者或者翻译目的,译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文的内容与形式,用特别自由的方法翻译原文,译本中往往隐含了大量改变”[11]。巴赞对《琵琶记》原作的各种删减、调整、增添的处理方法,恰如其分地印证了加拿大翻译研究学者安妮·布赖斯教授对编译所下定义即“重新划分原作版块,并以译作观众的名义进行合并”[12]。从微观层次看,巴赞译本还呈现出多脚注的“厚翻译”特征,脚注往往用来解释原文典故来源和文化词内涵,“我原本可以翻译一部时代更晚的作品,但是文学巨著稀少,即便在中国也是如此。而且,某些读者可能会从时代没那么久远的译作中觉察到欧洲对中国的影响。《琵琶记》向我们如实展示了15世纪初期中国的社会风俗,或许在亚洲文明史上,没有哪部作品比《琵琶记》所反映的这个时代更值得引起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关注了。”[9]XIV-XV巴赞《琵琶记》法译本承载着传播中国戏剧文学作品和为西方历史学家、哲学家提供研究文献的双重翻译使命。
巴赞《琵琶记》法译本的出版使《琵琶记》第一次以戏剧作品的形式出现在西方,其推动了19世纪及20世纪西方对《琵琶记》文本传播和舞台演出的后续研究。1895年,英国文学月刊《十九世纪》刊登了乔治·亚当斯的《中国戏剧》[13]一文。1901年,又刊登了英国比较文学先驱者波斯奈特《琵琶记或三不从》[14]一文,两位学者对《琵琶记》的评述都是根据巴赞《琵琶记》法译本转译成为英文来展开的。1946年,根据巴赞的《琵琶记》法译本,威尔·艾尔和西德尼·霍华德将《琵琶记》改编成一部3幕12场的英语音乐剧[15],并在百老汇演出142场。巴赞的《琵琶记》法译本不仅解决了演员演出剧本的来源问题,而且法译本中“舞台监督”的角色和“戏中戏”的形式也被音乐剧沿用。
四、结 语
晚清时期,“南曲之首”《琵琶记》实现了以诗歌、小说、戏曲的3种形态方式在西方的传播。三种形态的译文各具特色,其是译者不同社会身份和译介目的共同影响的结果。《中国诗作》译者匿名,根据译者从《马礼逊字典》《中国少年百科全书》两大汉语学习工具书中选取的语料佐证中国诗文化的细节中可以推测,译者对中国文化、尤其对中国诗词很感兴趣,其汉语水平已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但其却还不属于专业的汉学研究人员,因其译本脚注中的互文性资料来自学习工具书,而不是由中文原著或英语译作等一手资料来进行翻译的。译者非专业的研究背景解释了译作出误译的原因,或许还是译者为防后人诟病,采取匿名发表的原因之一。甘淋对“戏曲体小说”《琵琶记》的译介也反映了译者作为来华传教士的特殊身份。甘淋1878年来华传教,至其翻译出版《中国小说》(1898)时已在中国生活了20年,所以甘淋《情诉荷池》的译文对原文理解准确,但节选译文却更注重传递故事情节,简单化处理文化信息;另一方面,甘淋对中国的民族特色、社会风俗有着更真实的体悟和更客观的认识,其不仅起身为中国文学辩护,而且还进行换位思考,对《琵琶记》的故事设计、人物性格多了份理解和认同,这不是一般的西方汉学研究者能够达到的境界。汉学家巴赞在中国戏曲翻译和研究方面积累深厚,对《琵琶记》的编译显得游刃有余,他既能够按照西方戏剧标准对《琵琶记》的呈现方式进行改编。如提供人物表,又尽量保持中国戏剧的一些特色;保留少量唱段和增添大量“介”,使西方第一次有机会欣赏作为戏剧体裁的《琵琶记》。巴赞《琵琶记》译本用大量脚注补充与中国文化、社会风俗相关的知识,体现了巴赞注重透过文学作品之窗看中国风俗文化的翻译风格。总之,晚清时期,三位西方人士从各自专长的角度来译介《琵琶记》,希望读者能够从译作中认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这是他们共同的目标,《琵琶记》三种不同形态的译作较好地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群的阅读需求,为20世纪《琵琶记》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