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和抵达
湖南/叶 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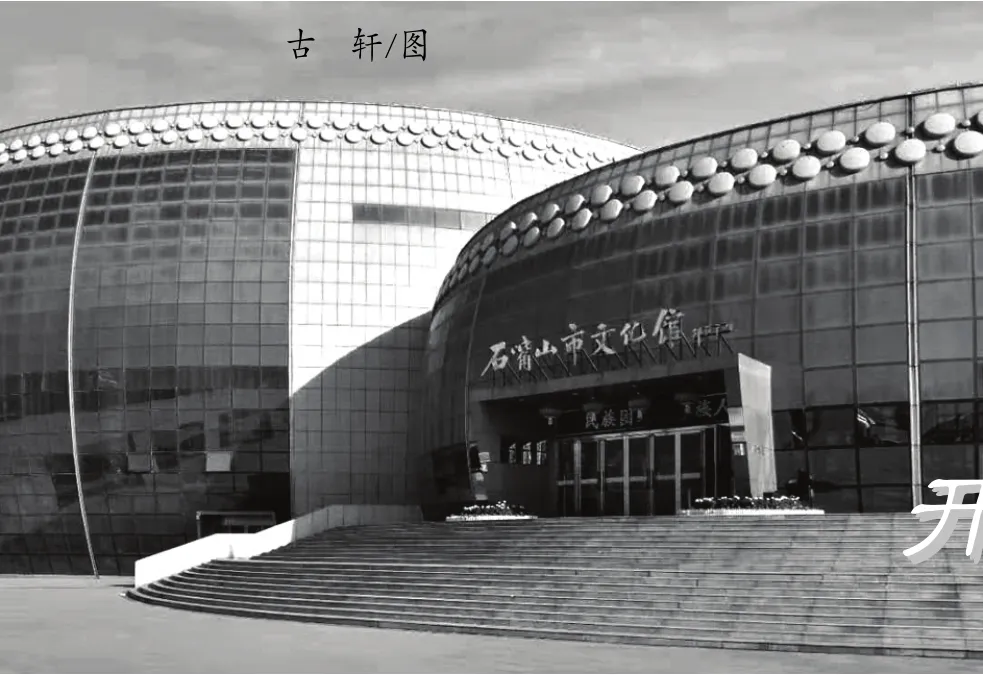
寻找转世重生的灵魂
白兰花在梦里摇曳,每一片花瓣都在向我招手。
梦境戛然而止。
满室幽香萦绕,梦境来不及撤退。余香是隐匿着的文字,娟秀的毛笔小楷若隐若现——那是我母亲温暖的手迹啊!
我一直不相信灵魂会凭空消失。
她离开16年了,我固执地相信灵魂是一种物质,她将以另外的形式转世重生。我一直在寻找她转世的迹象:
若托生为人,她当是一个少女。
若托生为树,她也是一棵大树。
转世的灵魂是随机的,就像凭空跌落尘世的几行诗,就像毫无征兆降临的漫天雪。
已经16年了。每一次重逢都是凌晨的梦境,68岁生日那天梦中惊醒,期待的梦中重逢的人已不得见,只听见有一朵花在喊我。醒来之后——梦中的白兰花还在满屏播放。
我披衣起床,推门而出,一匹白猫窜出来,引导我在暗夜的幽光里前行。路边,黑狗凄惶地瞥我一眼。浓密的树阴,空中有暗香在指引,与引路的白猫形成双重导航。白猫引我至一株白兰树下,隆冬的枝上独立一朵半开的花。
我的眼睛盈满泪水。
冬日黎明即将降临,黑暗依旧统领一切,白兰花在暗夜发出熠熠微光,此刻与68年前我脱离母体的时辰吻合。
叶间有兰,独放幽香。难道这就是灵魂的转世重生吗?
在我生日的凌晨,母亲变成一朵花来与我相见。我开启眼睛的快门,拍下溢满泪水的全息照片。灵魂的相见的场景是隐秘的,珍藏这一张照片,我无数次点开浓重的黑,只为可以再看到她盛开的姿势,温软如她的手指的花瓣,由此跨越阴阳会见到她的灵魂。
白兰花在梦里摇曳,每一片花瓣都在向我招手。
抵达先慈的路径
(逛艺术书店,走近古籍一角,见到傅山的小楷集,眼睛一亮,一把撸入怀中。我不习字,对书法无甚研究,为什么对傅山书法集情有独钟?)
抵达先慈的精神迷宫,有千万条路径,傅山只是其中一条暗道,通过这个词可以走近已经离开多年的母亲。
母亲口中吐出的每一个词语,根深蒂固长在我少年的记忆中。
一朵花,一个人,一本书;一味药名,一本经典,一位尊师。母亲说过的话被编入我少年的记忆词典。
每一个词语都是一条芬芳的暗道;
每一个词语都是我通向迷宫的地名。
温习母亲的语言词典,是我少年精神的回炉再造。
记忆中鲜活的那部分,一直营养着我的灵魂。
我甚至记得第一次听到傅青主这个名字的场景记忆,中医院的平房屋檐,面北的窗下,母亲在廊下与同事正在讨论中医理论,傅青主这个名字通过这样的语言碎片走入我的记忆。
当年那个痴迷小说的12岁少年,她对中医没有兴趣。
中年的母亲才华横溢,对典籍的研习与临床实践,常常以交谈的方式与隔壁同事在屋檐下展开。
关于中医的词语强行占据了我记忆的大部分,待到我年事渐高,母亲的语言碎片常常在我记忆中凸现。
被这些场景回忆再次唤醒,我沿着这些记忆去寻找母亲。从扁鹊、华佗到李时珍,从张仲景到孙思邈,从傅青主到叶天士,从《黄帝内经》到《经匮要略》,从《灵枢》《素问》《难经》,我牢牢记住了温病学派。
都是零散的语言,风中飘落的词语,每一个词语都是那样亲切,每一个人名都带着母亲的味道。
从妈妈口中吐出的傅青主,也成为追溯的对象,《傅山小楷》成为我的挚爱。
我用读帖的方式行走在这一条暗道,今天,我从傅山这条暗道走近母亲。
梦中的鸽群
梦中的鸽群飞向仄巷之上。
天空依旧被遮蔽。
回到童年场景,我必须穿越铁铺岭。
熟悉的街道被梦改写,恢复为秦代县衙前的古街。
两边都是卖旧货的店铺。
木雕、古老的器物摆在店铺的门外。人影幢幢,来来去去。陈旧的气息,破败的繁华,色调很像旧书的颜色,仿佛一部无声电影的实景演出。
二千多年前的场景复活。
梦境毫无章法地从街道中段开始切入。
我幽灵一样漂浮着走向街尾,街尾的街道陡然变窄。
有很多人,每人都控制着一群鸽子。
多群鸽子同时放飞,在头顶飞来飞去。
我在放鸽人的夹缝中穿过。鸽群噗噗噗地在我头顶飞翔。
唯有鸽群,看不清人脸。
梦中的鸽群飞向仄巷之上的天空。
天空被遮蔽。
穿越铁铺岭,企图抵达我心灵深处的童年温柔之乡。
毫无章法的梦境再次肆无忌惮地修改现实,童年记忆中街尾两边应该是稻田洼地。稻田溪流不见一片汪洋。
灰白色的现代水泥高架桥从巷口直接伸展出去,桥面有及至脚踝的水。我蹚水而行,从铁铺岭到三里桥,梦里的咫尺之地,怎么变得这么难走?
高架的桥面断开,有一处断裂豁口。下断桥走过叽滑的跳石,必须再爬上高架桥。倚着桥墩上的钢铁码钉我攀援而上。上面站着的是我小学的一位校长,她接过我手上的袋子。
梦中的我很有力量,四肢攀援,一下子就攀援上了将近有一层楼高的高架,眼看就要到顶了,这个时候——
我,醒来了。
桥断路断,即使穿越了铁铺岭,我也永远无法抵达三里桥。
梦境戛然而止,只有梦中的鸽群留在我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