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实验小说第一部的意义
谢桃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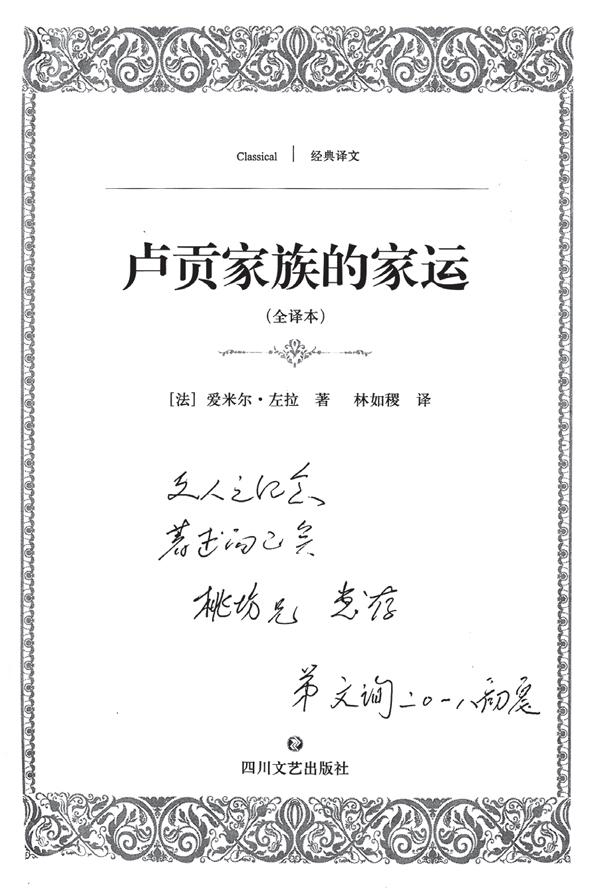

关键词:左拉;林如稷;遗传;帝政;共和;实验小说
法国19世纪文学史上,爱米尔·左拉(Emile Zola)是继巴尔扎克之后的伟大作家。他的《卢贡·马加尔家传》的总题名为《第二帝政时代一个家族之自然史及社会史》,由20部小说组成,共用了25年的时间。它是堪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相媲美的巨著。在这部巨著中实践了左拉提倡的实验小说的理论,其中第一部小说《卢贡家族的家运》尤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它采用遗传学的理论追溯了卢贡·马加尔家族的血统渊源及家族的遗传特点与演变发展,成为理解整部巨著家族遗传的关键;其次它以法国南方一个县城发生的政变,反映了法兰西第二帝政时代的社会现实生活,预示了整部巨著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只有在这部小说中才通过一对年轻人参加反抗义军的悲壮故事表达了作者光辉的共和思想。因此我们若要理解或研究左拉的巨著《卢贡·马加尔家传》,则此《卢贡家族的家运》是一部必读的作品。此著的中译者林如稷先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浅草社和沉钟社的重要作家。他在法国留学时即喜爱左拉的作品,准备翻译《卢贡·马加尔家传》的系列小说。他译的左拉实验小说的第一部《卢贡家族的家运》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今修订本由四川文艺出版社于2018年5月出版,经林如稷先生之哲嗣林文询先生据原稿校理。林如稷先生是小说家、诗人兼文艺理论家。他从法文原版将此著精心译出,文笔流畅优美,特具法文特色,尤能体现左拉的创作风格,因而这是我国经典译文中的精品。
一
左拉(1840—1902)是法国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他主张以科学的实验方法从事文学创作。1880年他发表《实验小说论》阐明了其新的创作理论。19世纪是自然科学辉煌发展的时代,各种自然科学取得巨大的成就;促使人类的智慧在不同的科学领域中得以充分和精湛的表现,体现人类寻求真知而向客观真理的境界前进的崇高精神。然而文学创作是否可以采用科学的实验方法,使它客观、精细、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呢?左拉认为是完全可以的,因而他说:“根据我的理解,对实验小说的含义予以明确阐述,在我看来是十分需要的。”[1]这要求小说家要像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研究非生物那样,要像生物学家研究生物那样,去研究人类的社会现象和人物的性格与情感。作家必须像科学家去揭示自然的秘密那样去反映社会的现象,反对主观想象的虚构杜撰,而且要找出社会中起决定的因素,尽可能地用观察和实验来检验所要表达的作家的先验思想。当作家写一部小说时,应力求达到对真理的完全认识;当计划确定后,思想是自由的,但时时仅接受现象与决定因素相符的客观事实。左拉实施其实验小说计划采取的方法是以研究一个家族,解剖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作为创作对象。他说:
在研究一个家族、一群人时,我认为社会环境同样具有首要的重要性。将来有一天,生理学无疑会给我们解释形成的思想与情感的道理。我们将会明瞭人这架单机器如何运转,他如何思想,如何热爱,怎样从理智发展到激情和疯狂。然而,这些现象生理器官机制的这些事实,是在内部环境影响下发生作用的,决不会孤立地在身体外部和真空中产生。人不是孤立的,他生活在社会中,社会环境中,因而对我们小说家来说,这种社会环境在不断改变上述现象。[2]
这试图说明个人的生理特征及思想情感与家族和社会环境存在着某种关系,每个人物决非孤立的现象。左拉的实验小说理论的产生的契机,是他于1864年读了克莱蒙恩·鲁瓦耶译的达尔文著作,继读了勒图尔诺医生的《情感生理学》,次年读了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导论》,特别是于1868-1869年关于鲁加医师的《自然遗传论》作了许多札记。左拉认真研究了这些著作,于1868年开始创作《卢贡家族的家运》,于1871年出版。法国传记作家阿尔芒·拉努以为在这部小说里,“不仅遗传学为他的小说里人物提供了必要的联系,而且科学也为他提供了崭新的表现手法。是时,在《卢贡·马加尔家族》的创作中,他一直坚持运用这种创作方法。他大胆地将医学理论运用于文学。这样一来,小说家不再是观察家了,而是一个实验家。这些思想的总和构成了他的自然主义理论,而实验小说也随之诞生了。”[3]左拉在这第一部实验小说中是按照他理解的遗传公律来考察卢贡·马加尔家族的。他在序言里表明:“我想解说一个家族——一群人——如何在一个社会里面立身处世,这家族在发展之时,产生了十个、二十个分子,他们在头一眼看来,好像极不相似,但经过分析之后,却指示出他们是彼此深切地关联着的。遗传有它的公律,正如同万有引力有它的公律一样。我一方面解决环境与气质的双重问题,一方面努力寻求和追随从一个人必然通到另一个人的严密线索。”[4]因此由二十部小说组成的《卢贡·马加尔家传》的巨著,虽然各部小说独立完整,它们皆演绎着一个家族的遗传公律,而这公律又受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影响表现为极为复杂的现象和关系。左拉描写这个庞大的家族所受遗传公律的制约与变化,在这部《卢贡家族的家运》中作了探源析流的分析和叙述,成为我们理解整个巨著的家族遗传变化的基本线索,展现了这个家族生理遗传的谱系。
卢贡·马加尔家族兴起于法国南部朴若昂司省区的古城朴拉桑。这个县城有1万左右的居民,形成三个区:贵族区即圣马可区,居住着贵族和官员;老城区居住着工人、商人和贫民,有一个坟场被改造为圣密特广场;新城区居住着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为县公署所在地,有一个索威尔公共广场。在老城区圣密特广场后面有一大片菜地为胡格家族经营。胡格家族在当地是颇为富有的,但只留下了一个女孩阿得拉伊德。她生于1768年,在18岁时,因父亲由疯狂病死去,她遂成为孤女。她身材高大细长,面色青白,眼光总是带着惊惶的神情,其狂乱的精神是受了父亲的遗传。阿得拉伊德虽然有很大一笔财产,但无能力管理,不久她与园丁卢贡结婚了。卢贡是一位憨厚老实的青年农民,粗笨、鲁钝、庸俗。阿得拉伊德本来可以选择社会条件较好的男子结婚,她却选择了卢贡,这在当地人们是难以理解的。婚后12月她生了一个男孩,不久卢贡突然死去。这位年轻寡妇,过了一年,便与情人马加尔同居了。马加尔居住在圣密特广场邻近胡格菜园的破屋内,他的父亲是硝皮厂的工人。他30岁,高大精瘦,有着密杂的胡须,蓬头乱发,棕褐色的眼睛闪闪发光,具有流浪汉的本性。他孤独一人,大多数时间在外贩卖私貨,或者偷猎。阿得拉伊德偏偏热烈地喜爱他,只要他回到圣密特广场边的破屋,她便去与他同居,根本不顾市民们的议论。她与马加尔生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她分娩后经常二三月发作神经病,全身痉挛;只要她的情人回来,便丢下孩子们去了。在她42岁时,马加尔在边界被税关的保安兵用枪打死了。她后来又被儿子夺去了财产,晚年孤独地住在马加尔留给她的破屋里,壁上挂着一支马加尔的重型步枪。

林如稷译《卢贡家族的家运》(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阿得拉伊德与卢贡的合法生的儿子彼得·卢贡,受其父的遗传,中等肥胖的身材,富于理性和计谋,处事谨慎,却又矫伪、懦弱、阴险。他吞没了母亲的全部家产,怀着政治野心,与当地油商的女儿、黑皮肤、小个子而性格刚强的菲丽西德结婚。他们成为小说故事中的重要人物,他们改变了卢贡家族的家运。卢贡家族的遗传,由菲丽西德而改良了。他们生了三子两女。长子雨瑟,遗传了父母的优点,身材肥胖,富有智慧和野心,做事专擅,有几滴贵族的血统,后在巴黎成为律师并角逐权力。次子巴士加,身材高大,性情温和庄严,具有正直的精神,热爱科学,鄙薄财富,是杰出的医师。他好像未受到卢贡家族的遗传,令人怀疑遗传公律出了错误。幼子阿里斯底德,身材瘦小,充满贫欲,渴求财富和享乐,生情懒惰;妻子昂琪儿是软弱的金发女子。卢贡家的大女儿马尔塔在马赛,二女儿西都妮在巴黎。
阿得拉伊德与马加尔的私生子,一男一女。儿子昂多万遗传了父母的缺点,爱好流浪,有酗酒倾向,脾气粗暴,懦弱而又阴险,自私自利,贪图享乐,反复无常,混入共和党而进行政治投机。他与芬娜结婚,有两女一子。长女莉莎为邮务局长婢女,次女薏尔维丝,跛脚,下流,虚弱,嫁与工人;幼子若望勤劳健康,在卢贡家当学徒。阿得拉伊德与马加尔生的女儿玉尔苏有慢性肺痨,嫁与帽商莫瑞,生了一女两子。女儿海伦嫁与雇员;大儿子弗朗奈阿与卢贡的二女玛尔塔结婚,成为卢贡商店的帮手;小儿子西魏尔是工人,成为狂热的共和党人,为其崇高的理想而参加了反抗义军。
《卢贡家族的家运》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851年12月上旬的数日,左拉以追述的方式简略地叙述了卢贡·马加尔家族的形成,而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分析了这个家族登场人物所受之遗传及其在时代与环境作用下所发生的变异,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情况。他在这第一部实验小说中所绘制的卢贡·马加尔家族的谱系在此后的系列小说里分别演绎了这个家族所受生物遗传公律的支配。这主要表现为卢贡一系的人物为政治家、律师、资本家、医生,进入了社会的上层;马加尔一系的人物则为小商、工人、贫民、妓女,沦落为社会的底层。因此这部小说是理解和研究《卢贡·马加尔家传》巨著时必读的,尤其是这部小说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皆是系列小说中最为优秀和杰出的。
当1851年故事发生之时,家族中的阿德拉伊德已经70多岁,人们称她为第德太婆,她是孤苦的老妇人,居住在破屋里,早已被儿女和人们遗忘了。彼得·卢贡已50岁,肚子大得挺出,面孔呆滞灰白,外表颇为得意和庄严,掩藏着他的不得志的愤怒和强烈的贪婪。他等待着社会政治的变化以实现掠夺财富和窃取政权的野心。在这个朴拉桑小城发生的阴谋政变使卢贡·马加尔家族的成员纷纷登场,卢贡家族的家运由此有了转机。
二
法兰西的大革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光辉的一页。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进攻丢伊勒宫,王权中止;9月2日至5日处死大批贵族及反革命分子;9月21日国民大会开幕,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1793年1月21日共和国处死国王路易十六,5月31日巴黎人民包围国民大会,革命派雅各宾党专政。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共和国的社会理想。此后拿破仑建立了第一帝政,1848年又再建共和政制,而政权落到拿破仑一世之侄路易·拿破仑·朋拿巴德亲王之手。1851年12月1日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3万名兵士部署巴黎,宣布戒严,政变者建议由亲王——总统起草新宪法。共和派议员组织反抗力量,巴黎及外省的工业区和红色农业区组成反抗义军。新建立的第二帝政在各省成立特别委员会,逮捕了26000名反对分子,彻底消灭了共和派。自1851年至1870年为法国第二帝政专制的时代。1871年《卢贡家族的家运》出版时,第二帝政刚刚结束,左拉的巨著《卢贡·马加尔家传》实是第二帝政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他对这时代是极为愤恨的:
第二帝国激起了人们的贪欲与野心,贪欲与野心大放纵。渴望享乐,而且享乐得精神与肉体都疲惫不堪。对于肉体来说,是商业的大繁荣,投机倒把的狂热;对精神来说,是思想的高度紧张,与近乎疯狂的行为。疲劳过度,然后是坠毁。[5]
他的巨著即是以第二帝政时代为历史背景。左拉自述创作的意图是:“我把它置于现代的真实性上写种种野心与贪欲的拥挤冲突。我考察一个投身于现代社会的家族的野心与贪欲,它以超人的努力进行奋斗,却由于自己的遗传性与环境的影响,刚接近成功又掉落下来,结果产生出一些真正道德上的怪物(教士、杀人犯、艺术家)。时代是混乱的,我所写的正是时代的混乱。”[6]这部家族史系列小说的第一部正是发生在1851年12月的政变时期。它对南方的朴拉桑小城也有突出的反映,或者我们可以由此见到一个巴黎阴谋政变的缩影。
法国政变时,朴拉桑由自由党人、正统王党、峨尔良旁系王党、朋拿巴德党以及教士的混合而形成强大的反动势力,它们准备着去扑灭共和制。这个反动势力的结合有加拉尔网侯爵、市议员格鲁纳、地主儒第叶、大队长西加多、书店老板魏业为代表的人物。他们时常在彼得·卢贡客厅里聚会,向共和制发出攻击的吠叫。1851年11月酝酿政变。路易·拿破仑称帝的消息于12月3日午后传到了朴拉桑,第5日邻近的反抗义军武装起来了,第7日传来有3000人的義军将到达朴拉桑。“这些大事变成了卢贡家族的家运。他们投身混杂在这个变动的阶段之中,他们在自由的废址上长大了。这些待机而起的强盗所抢劫的便是共和,在别人扼住它咽喉的时候,他们帮助来拦路打劫它。”左拉对小县城政变的描写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情感的,表达了他的憎恨与鄙视,因此我们绝不要以为自然主义的作品是纯客观的照相似的反映现实生活。
反抗义军于晚上暂时驻扎在朴拉桑,这仅是路过,而非目的地,所以次日早上便开发了。义军俘去了市长及一些官员,地方的反动分子都藏匿起来了。义军撤走后,卢贡从母亲阿得拉伊德的破屋里出来,他躲在此处是最安全的。他感到共和党人把朴拉桑给他留下了,等待他来收拾残局。他纠结一群反动势力,串通党徒共40余人聚集在厂棚(藏枪支的地方)进行分工。市政厅尚有留守的20多个共和党人,而政治投机分子——卢贡的同母异父弟弟昂多万正坐在市长的位子上,想当政府的领袖。晚上卢贡作了周密的计划。拂晓时,他带着一群党徒单线行至市政厅。守卫大门的兵士抱着枪坐在门口睡着了,卢贡上前夺下枪并制服了兵士。他们悄悄进入市长办公室。昂多万在与四人起草告示,卢贡等人与他们发生冲突。在争斗的过程中,卢贡手上的长枪机柄滑动,发生一声巨响,子弹飞出去打碎办公室内的一面大镜子;又有三人由儒第叶指挥向天空开枪。昂多万被俘,其余的共和党人逃散,卢贡等人胜利了。镜子的打碎有如荷马史诗式的伟大结局,它迅即被卢贡夸张讲演,于是朴拉桑市民中传说着41个小绅士扫荡了3000反抗军的神话。次日晚上,传说一小群反抗义军将从朴拉桑经过,但天亮了,未见一个反抗军。不久又传说巴黎政变失败,路易·拿破仑亲王被囚,马赛及南方各省均被反抗军占领,反抗军快到朴拉桑来了。全城立即陷入恐惧之中,而卢贡等人更加惊惶失措。卢贡的妻子菲丽西德从邮局获得大儿子雨瑟来自巴黎的密信,告知政变完全成功,巴黎被压服,各省无举动。他还希望父母对局部反抗军的叛乱采取坚决镇压的态度。卢贡夫妇得知消息后,制定了一个阴谋的计划,即让恐怖的气氛更厉害地闹下去,而卢贡保持英雄的姿态,制造一场政变。由菲丽西德去市政厅说服被关押的昂多万,把他放出去,由他组织同伙把市长办公所夺取回来,然后给他1000佛郎逃出国界。次日卢贡独自一人威风凛凛占据着市长办公室,中午去巡视各城门,命令国防军严守。晚上卢贡组织国防军分若干小队秘密到市政厅埋伏,告知共和党人暴乱,熄灭了灯光,准备消灭来犯的共和党人。半夜昂多万与狂热的共和党徒50人,宣称反抗军快到城门,他们先夺取市政厅。这伙人冲进市政厅后被埋伏的国防军包围。一个国防兵被打死,三个共和党人死了,另有一个死在广场,共和党人逃散,教堂警钟轰鸣,城内保安军和国防军奔跑,似乎有数万人在进行着伟大的战争。然而这场枪战的真相却从来没有人知道。官兵到了,市长回来了,联队长也来了,宣布逮捕和处死共和党人。省长接见了卢贡等城市的保卫者。很快雨瑟来信告知,父亲卢贡将被委任为朴拉桑的特别收税员。卢贡家族将飞黄腾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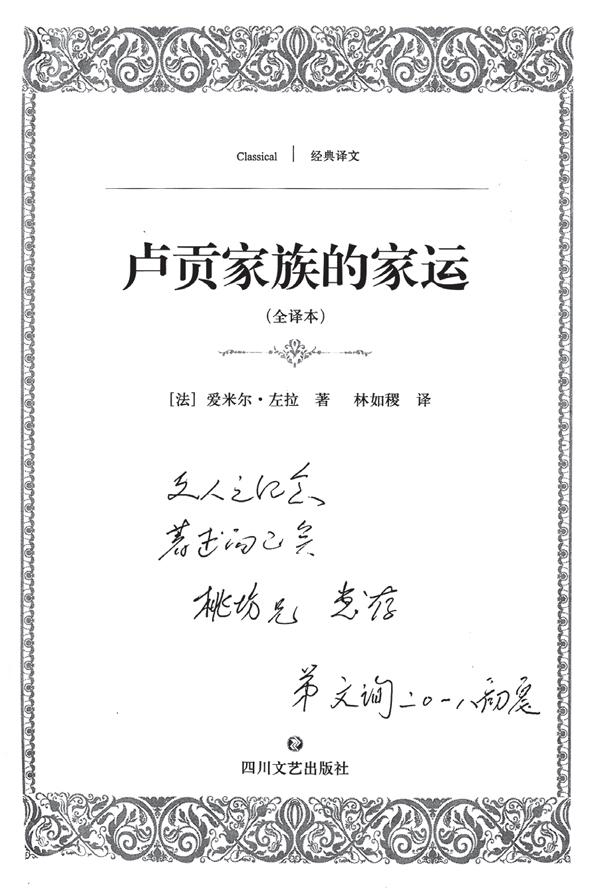
无论巴黎的政变还是朴拉桑的政变,它们有某些共同之处。政变者们对阴谋计划是否能成功,实际并无信心。他们如果失败便立即成为阶下囚,被加以叛国或盗匪的罪名;如侥幸成功,则将卑劣自私的打算变成爱国的大义,阴谋变成义举,他们也成为英雄而彪炳史册了。历史上的政变的成功与否,都具有偶然性,而历史的必然又总是以偶然性出现的。朴拉桑的政变是巴黎政变的局部反映,左拉通过它反映了路易·拿破仑政变的本质。这次政变的成功开始了法国第二帝国的历史,它是卢贡·马加尔家族系列故事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左拉细致而真实地揭露了政变者的自私心理和可耻的阴谋,将一场滑稽丑恶的闹剧的真相细加描绘,体现了批判的深度和艺术的力量。作者不仅在写一个家族在政变中依附反动势力的发家史,更重要的是由此展开“一个充满疯狂和耻辱的奇异时代的画图”。

马奈绘左拉肖像(1868年)
三
法国在第二帝政时期虽然实施专制,但共和反对派仍然通过报刊进行活动。1869年共和派报纸的总数为十万份,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此年在选举之前,共和派制定了著名的《贝尔维尔纲领》,要求个人自由,出版完全自由,真正的普选,集会集社权,義务教育,教会与国家分离,按社会等级纳税等等。[7]左拉是共和的拥护者,他的朋友多为共和党人。1870年8月5日第二帝国覆亡的前夕,左拉发表了一篇《法兰西万岁》的文章,呼吁和平:
在此时刻,在莱因河两岸,集结着反帝国的五万名将士。他们不要战争,不要常备军队,更不要把整个民族的生命和命运交给一个独裁者的可恶政府。[8]
左拉因此被指控为“煽动对政府的不满和仇恨,蛊惑人们违逆法律”。幸好帝国很快倒台,否则左拉会被受到审判的。由此我们可见左拉对共和拥护和对帝国的憎恨。当我们纵观《卢贡·马加尔家传》的系列小说时,显而易见除了最后一部《巴士加医师》而外,没有一个主要人物是正面的,值得肯定的,而都是被否定的被批判的。左拉的共和理想,在第一部实验小说《卢贡家族的家运》中通过一对年轻人——西魏尔和蜜埃特参加反抗义军的英雄的悲壮故事得以唯一的充分表达。它成为整部巨著中最为鲜明的理想之光。
西魏尔是阿得拉伊德与马加尔的私生女玉尔苏的幼子。这孩子6岁时父母死了,由外祖母阿得拉伊德(第德太婆)抚养,在严重的愁郁贫苦中成长;12岁时学习制车技艺,由学徒成为工人。他身上承袭的外祖母的精神昏乱已转变为慢性的狂热,转变为对一切伟大的不可能的事物向往的激情。他有着固执的求知欲望,爱深思,具有雄伟的壮志,努力追求伟大的思想,是极高尚而天真的——共和国的思想自然地激发起来。他17岁时,已是一位健美的青年,面庞瘦而狭长,厚嘴鼻,黑灰色的眼睛,中等的粗壮身材,有着坚强的面相,着绿色绵绒短上衣裤,戴软呢帽。他与附近农庄的女子蜜埃特相爱。蜜埃特的父亲是农民,因一次偷猎而用步枪打死一名保安队兵士,遂囚在监狱做苦工。她9岁时曾跟祖父乞讨生活,后到朴拉桑姑母家庄园做农活。这位南方姑娘发育很快,加上长期的农庄劳动,在13岁时已强壮如同成年的女子,充满热烈的生命活力,有着丰腴的奇异的动人之美。1851年12月7日反抗义军将到朴拉桑时,西魏尔准备参加义军,晚上在圣密特广场与蜜埃特约会。他对蜜埃特说:“反抗义军已经出动了,他们昨晚是在阿波瓦日过夜的。我们要去加在他们一起,这是已经决定的了。”他坚信:“斗争是不能避免的了,不过正义是在我们这边,我们会胜利的。”他将对共和国的爱和对蜜埃特的爱连结在一起,他说:“我把整个的心给了你。我爱共和国,你看,因为是我爱你。”他们的爱情与共和理想都是纯洁的。他们离开广场前去迎接义军。夜10点钟妮司大道的山坡后的大道转弯处,传来共和国歌《马赛曲》,带着复仇的愤怒情绪,歌声激荡,产生可怕的震响。左拉以热烈的情感描述说:“队伍带着一种卓绝的不可抵抗的激情走下来,再没有比这几千人在天地的死寂和冰冻的和平里的出现更非常的伟大了……《马赛曲》充满了天际,如同一些巨大的嘴在吹奏神圣的军号,用钢铁一般的冷酷态度把颤响《马赛曲》向山谷的一切角隅投去。”义军有3000余人,参军的沿途增加,队伍8人一排,浩荡地前进。西魏尔和蜜埃特加入义军。蜜埃特在银色的月光中,身着朱红色外衣,红色的风帽像1793年大革命时共和党人戴的赤色软帽。她从义军中拿过大旗,把旗杆紧紧挨在胸膛,挺起身子,血红的大旗飘飞;这时她有如自由女神一样。在西魏尔看来,她是那样的伟大和神圣!
反抗义军占领了朴拉桑市政厅,西魏尔在争夺保安队兵士昂佳得的马枪时将他的右眼打破。西魏尔到圣密特广场角落的破屋去看望外祖母第德太婆,告诉她打死了一名保安兵士。第德太婆突然眼睛像燃烧的强烈的炬火。她激动地将马加尔的重型步枪从墙上取下给外孙说:“这就是他给我所遗留下的一切了!……你打死了一个保安队兵士。他吗,他却是被一些保安队的兵士打死的啦。”左拉对阿得拉伊德的描叙不多,但是可以透露出她是爱马加尔的,马加尔也未像当地人猜测的是为了巨大的财产,他具有一种反叛的精神。这位孤独抑郁和神经昏乱的老妇人,她厌恶和憎恨儿子们,却特别爱这由她抚养成人的外孙。当她将马加尔留下的枪交给外孙时是带着复仇的心情。她爱外孙即是支持共和,对一切发生的事情似乎是看得清楚的。
次日义军向阿耳竭尔大道前进,在阿耳竭尔城停留了两天,失去了战机。清晨,官军出现在平原边上,义军总指挥带着佩刀,部署包抄官军,首先发起进攻。官军马队很快将平原上的义军扫灭,总指挥逃走,义军溃败。西魏尔和蜜埃特的一队义军正面与官军交战,最后剩下的8个义军,又死去3个。这时:
蜜埃特把旗子是愈高高地举起,她始终握紧了拳头把它向她前面举着,就向一把光明的火炬一样。旗子上面,是早就穿了不少的弹孔……大旗正是从蜜埃特手上折倒了。小女孩两只拳头紧握地放在胸前,脑袋翻向下面的,含着一种剧烈的痛苦神情,正慢慢地转动着。她并没有发出一声喊叫,她向后倒下,躺在大旗的血红的旗面之上。
左拉以痛苦而激烈的情感描写了蜜埃特就义的悲壮的场面,象征着共和的理想的大旗倒下,反动的帝政阴谋得逞了。然而蜜埃特的纯洁的热烈的共和精神将永远鼓舞着热爱共和的人们。
西魏尔悲痛地抱着蜜埃特时,他被俘了。政变的胜利者们在朴拉桑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官军决定枪毙一些重犯俘虏。黄昏时那位右眼被打破的保安队兵士昂佳得认出了西魏尔。他带着复仇的火焰,将西魏尔带到圣密特广场角落——即西魏尔与蜜埃特约会的地方枪决了。这悲惨的一幕恰恰被第德太婆在破屋附近看见。她回到家里精神病发作了,将死时,衣带松开,白发散乱,苍白的脸上泛出红团,痉挛的身躯突然直挺,大声叫道:
我这个不幸的妇人!我只会生了一群豺狼。整一家族,整一窝豺狼。……只有一个可怜的孩子,他们都要把他吃了,各人都咬了一口,他们的嘴唇上还粘满鲜血呢!……啊,这些该死的东西。他们干了抢劫的事,他们杀害了人,然而他们都像阔老爷一般地过活着呢。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东西!
这不是疯话。阿得拉伊德亲历了卢贡·马加尔家族的发展变化,虽然精神昏乱却直觉地感知是非与善恶。这个家族唯一的正直而有崇高共和理想的可爱孩子西魏尔被杀害了,她也悲痛愤怒地死了,留下了一群豺狼。这时卢贡等人正兴高采烈地欢迎新的“帝政”,欢迎狂热的贪欲的时代的降临。
左拉以厌恶的憎恨的鄙视的情感再现了一场阴谋政变的可耻的成功;却以同情和惋惜的情感描写了反抗义军的失败,又热烈地歌颂了伟大的共和精神。作者爱憎的态度在《卢贡家族的家运》中的表现是鲜明的。
四
林如稷自1923年冬赴法国留学,先后在里昂大学和巴黎大学法学院主攻经济学,同时选择了文学院的几门功课,特别喜爱左拉的作品;于1930年秋归国。他是中国第一位翻译和研究左拉作品的学者,1935年受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的委托翻译《左拉集》,于1936年翻译出版了《卢贡家族的家运》;本来计划将《卢贡·马加尔家传》中的其他八种小说译出的,然而未果。1948年至1949年间他翻译了《左拉传》《左拉青年时代的生活》《内战中的文人左拉》,写有《关于左拉的生活》《左拉逝世四十五周年祭》和《左拉与社会主义》等论文。这部《卢贡家族的家运》的译著是非常杰出的经典译文,系林如稷根据两种法文原本译出,最能体现法文的严密细致,亦能忠实地表现左拉的艺术风格;尤其是使用了汉语的优雅流美和纯净的白话文学语言,这在诸种经典译文中是罕有可比拟的。关于这部小说的名称,林如稷据法文原意译为《卢贡家族的家运》,它確切地表明了一个家族的家运发生的转变。此后有译为《卢贡家的发迹》,或译为《卢贡家族的命运》的;但“卢贡家”“发迹”“命运”这些词语显然不符合左拉原意。左拉于1877年再版此部小说时加了《卢贡·马加尔家传总序》,我们试将林如稷和柳鸣九所译此文的一小段作比较:
林译:“卢贡·马加尔家族”,这群人,即我所提出要研究的家庭,它的特征正是过度的贪欲和在我们这个追求享受的时代中的平民阶级的广泛兴起。在生理方面,他们是在一个家庭之内受到第一次的机体伤害之后所造成的神经上与血统上的变态病症的慢性继承者,这些神经上与血统上的变态病症,对于家庭的每个人,又随着环境之不同,决定了各种情感、欲望、情欲,即一切属于自然和本能的人性表露,而这些表现的具体事实,也即是一般所谓的道德和罪恶。
柳译:我所要研究的卢贡·马加尔家族有一个特征。那就是贪欲的放纵,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里向享乐奔腾而去的狂潮。在生理上这个家庭的成员都是神经变态与血型变态的继承者,这种变态来自最初一次器官的损坏,它在整个家族中都有表现,它随着环境的不同,在每一个家族成员身上造成种种不同的感情、愿望、情欲,种种不同的人态,或为自然的,或为本能的,而其后果,人们则以善德或罪恶相称。[9]
这段文字,林译为两句,206字;柳译为三句,180字。显然林译较细致,颇有法文意味,或欧化的文风;而柳译较为简略,具有汉语的明快风格。我以为翻译作品仍以保存其特殊的文风为佳。从林译的一段文字亦可见整部译作的行文特色了。现在《卢贡家族的家运》只有林译。它附有译者对历史、地理、人物、民俗等的注释66条,长者达千余字,可供读者阅读时作参考;还附有左拉的女儿于1927年写的《爱米尔·左拉略传》,这是研究左拉生平与创作的宝贵资料。左拉这部小说乃其实验小说的经典,林如稷的译本更是经典的译文。译者说:“这一卷非但故事本身动人,而且又极完整,可以独立,在结构技巧上面更是谨严不苟。至于书中所描写的许多情节,未尝不可以移过来作为我们现在社会的写照。”此著的真实性、现实性、精密的构思和深刻的意义,使它永远具有旺盛艺术生命。
注释:
[1][2][9]左拉:《实验小说论》,吕永真译,见柳鸣九编《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38页,第750页,第828页。
[3][8][法]阿尔芒·拉努:《左拉》,马中林译,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页,第155-156页。
[4]左拉:《卢贡家族的家运》,林如稷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以下文中引用此部小说原文,不再注出。
[5][6]左拉:《关于家族史小说总体构思的札记》,《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第733页。
[7]参见[法]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1976年),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99页。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