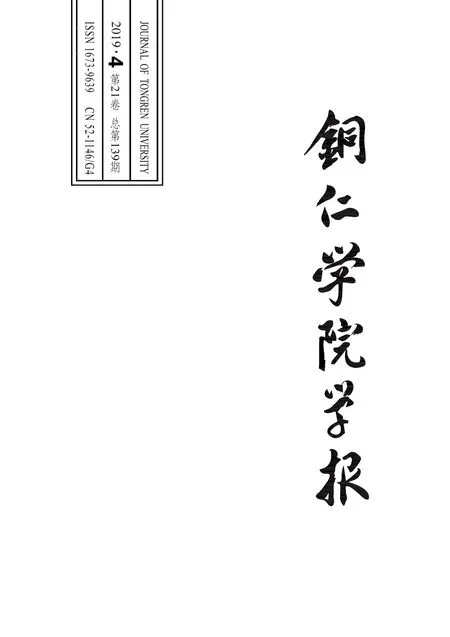论清代汇编体诗法著作的成立
郭星明
(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宝山区 200444 )
本文所拟定“汇编体诗法”此一概念是对“现存大约近千种”[1]清代诗学著述中30 余种诗话汇编类著作①的界定。所谓“汇编体”,是指此类著作的基本文献形态或者说撰著方式是对已有各类诗学资料——多为前人诗论——进行特定方式的汇编。至于其汇编的具体方式或者说材料的取舍标准及安排顺序不影响汇编相对于自撰的独特性质②。所谓“诗法”是指指导诗歌初学者进行创作的广义上的各类诗学著作,这一点在编著者自身有着充分的自觉意识而不仅仅局限于狭义上的诗法——诗歌技法手册[2]。综合上述从文献形态与诗学理论性质两个层面之双重界定,我们拟将后文将要叙录的30 余种诗学著作的基本内涵描述如下:汇编体诗法是指编著者通过广泛汇编他人所撰诗学资料,系统、全面地教授初学者诗歌创作方法的诗学著作。简单来讲,就文献形态和体例言,清代汇编体诗法是清代诗话汇编的一类,是与断代类汇编和地域类汇编并列的清代第三大类诗话汇编——诗法类汇编[3];就诗学理论 性质而言,清代汇编体诗法不是录诗纪事型的传统诗话,也不是评诗论人的评论型诗评著述,而是讨论诗歌创作理念与方法的诗法类著述。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就“汇编”性质而言,其虽然是各类诗话汇编的同类——此处的“诗话”是广义上的诗话[4],包括各类诗论——但已不是对诗学资料的广泛收集或分门胪列,而是编著者精心结撰的产物,具有“寓作于述”[5]的性质。此类著作的成立是中国诗学发生、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固有环节,考察它们和前代相关文献的联系才能说明其在清代成立的具体情况。而对其发生与成立的缘由作社会学意义上的归纳、总结,只能得出“不错”而无用的结论,无益于我们对此类著作之诗学价值认识的深化,也无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诗学精神内核的理解和阐释。
一、内涵阐释
从文献形态与诗学理论性质两个层面之双重界定是准确把握汇编体诗法著作的基本内涵的关键,但此界定只是今人认识整个清代近三百年中数十位此类文献的编著者所编各自著作的一种特定方式,并不能够完全无偏差地还原其历史真相。所以在把握其基本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编著方式颇有出入的各部实际著作,充分阐释此概念各种规定性的丰富含义是更加全面、准确认识清代汇编体诗法成立情况的保障。
(一)材料的广泛性
清代汇编体诗法虽名曰“诗法”,但正如前文提到的,其内涵早已不局限在通常学术意义上的“低级”批评类型[2]如诗格、诗式、诗法之类③,而是“广义的蒙学诗法”[6]。蒋寅先生准确地指出此类著述是“对传统诗学资料……大规模的整理和总结”[6],反观元、明两朝诗法著作则基本不具备这样的编著特征和诗学价值。这种整理和总结的特性,正是有赖于清人在编著过程中广泛采辑相关诗学资料才得以实现的。
材料的广泛性主要体现在时间跨度之大和文献体例丰富两个方面。从中国现存最早的诗论如朱自清所认为的“开山的纲领”——《尚书》中“诗言志”的论断和命题,一直延续到编著者同代人的相关诗论——包括编著者本人实时所加的按语,上下近三千年的诗学文献都是清代汇编体诗法取材的范围。这显然是将历代诗话汇编广泛收集资料的编著方法应用到了诗法创作上,并有意地进行了泛化,其中暗含的是对诗话范畴的拓展。也就是说对于资料时代跨度的延伸和扩展是更多撰著体例不同的诗学资料被泛化的诗话观念所涵容的必然结果。比如宋代前期对诗话纪事性质的普遍认同④就大致界定了同时期诗话汇编的取材性质和范围,所以当时出现的诗话汇编如《唐宋明贤分门诗话》《古今诗话》和《诗总》⑤等都秉持着论诗及事的诗话观念,将唐、宋两朝笔记、小说、杂史等著作中凡是符合此标准的相应文段都尽可能地汇集到了自己的汇编著作中。随着后代诗话观念的泛化,从涵盖诗法、诗评到包容所有的诗学著述⑥,作为诗话的汇编自然也就将历来不同著述体例的所有诗学资料和著作都纳入到了自己的收集视野。如编著于清初的汇编体诗法《雅伦》⑦仅就首卷所辑43 则材料言,就涵盖了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的多种前人著述。具体有:《尚书》《毛诗注疏》《论语》《礼记》《孟子》《吕氏春秋》《史记》《汉书》《宋书》《周书》《诗集传》《文心雕龙》《通志》《困学纪闻》《诗家直说》《古诗纪》《古乐苑》《珊瑚钩诗话》《解颐新语》《诗薮》《册府元龟》《古今诗话》《诗法一指》⑧《释名》《文中子》及崔豹《古今注》、王应麟《诗考》、陆深《玉堂浑笔》⑨、王槚《诗法指南》等。尚有十数处未列出者,是因原文只标作者姓名,不题来源之书名,故未敢轻易认定其所引之具体书目。此处虽然只是一书一卷之示例,但特征之突出可见一斑。如此广泛的材料辑引应当说是前代罕见的,清人似乎尤其热衷于对历来诗学资料的整理和收集,所以成就了汇编体诗法中展示的清代诗学的集大成意义。就此而言,清代诗学与明代诗学可以明显区别开来,前者“具有明显的集成性”[7]。
(二)编排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如果说材料采辑的广泛性是从汇编的角度对清代汇编体诗法学术特征最准确的概括,那么将这些分散的材料结撰成可供初学者学习、研读的诗法指导书,则需要精心的结构意识和理论系统。也正是这一点体现了编著者以述代作的撰述意旨,造就了其诗法的诗学理论特性,而与其他各类诗话汇编从本质上区别开来。
当然,这种诗法讲解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既不是一蹴而就,也非凭空生造,而是对前人不断丰富的诗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总结,所以蒋寅先生说道:“中国古代诗学的理论框架到明代已告完成,清代诗学的贡献主要是在内容的专门化、细节的充实和深描……清代诗论家……努力使之(指诗学思想)成为可以说明的,可以从诗歌史获得验证的定理……清代诗学著述由此而显出浓厚的学术色彩,由传统印象性表达向实证性研究过渡。”[8]具体而言,乾隆元年(1736)刊行的张潜《诗法醒言》就可以印证这样的论断,其书分别从三个不同层面讲论诗 歌具体作法,一是宏观技巧层面:练字、炼句、选辞、用事;二是各种体式的静态层面:基本格式特征和结构方法;三是实际上的操作层面:起法、对法、结法、诗调。这样全面细致的作法指导克服了前代诗法讲解的笼统性和模糊性,所以其被张寅彭先生誉为“集大成之著”[9]。当然,这绝非个例,如篇幅狭小的李畯《诗筏汇说》⑩,也同样有着严密的体系意识。是辑正文四部分,首列标目“说诗体”,先辑田同之《西浦诗说》一则,总体上简单论述历代诗体自《诗经》至近体之流变,后有李氏按语表明首辩诗体之意,其后诗论十数则,分别讲解各体之源流及特色。第二部分标目“说诗人”首引田同之之论,意在推重王士祯“神韵说”并将其作为诗人、诗作成功之标准,后有李氏按语说明理由,认为神韵相较诗歌其他文本可见因素,是唯一能够“道性情”的特质。后文以诗体为纲,每体之内又按时间顺序罗列各体擅长之诗人,意在列举历代各体得神韵之具体诗人。第三部分标目“说诗法”,首辑沈德潜论诗法,强调诗不可无法而不能执着死法,后接李氏按语意在“先从法入去,再从法出来”。后辑11 则诗论,分列各体特征及作法。第四部分标目“说诗式”,首引李攀龙论诗之极致之言,由可学可法之实迹而至最高标准——入神,后加按语说明极致虽虚却可由实法悟入,故列各体前人经典诗作以为初学之范式。分乐府、古体、近体,各体又各列具体格式皆要言不烦。各体名目之后有李氏按语意在说明各具体格式,如乐府有分章、分解两式等,后接前人总论该体之特点。随后则以具体格式为纲,罗列该式之诗例,诗题下有李氏按语,详解该诗之声调特点,诗作正文中亦多加按语以为发明,不厌其详。可见,篇幅的狭小并不意味着诗学体系的残缺,只不过由于其编著意旨主要针对的是科举应试诗,所以省去了很多与具体作法关系较远而又常为其他诗学著作已经讲解过的类目,体现出极强的针对性。
二、分类叙录
清代汇编体诗法在“汇编”与“诗法”界定下的内涵阐释只能说明该类著作的大致著述特征,详细叙录此一概念涵盖的各部著作具体内容则是对其外延的阐释和说明。此两方面的论述合力描述了清代汇编体诗法成立的具体情况。下文叙录的三部著作虽属同类,但又因编著者个人的学术修养和习惯以及作品的针对性而多有差异,所以我们将它们进一步分类叙录,才是对本文核心概念外延的细致性阐释。当然,差异是相对的,整个类的共同特征是绝对的——都是汇编诗学资料用以指导后学,不能因为相互间有限的差异而否定其共性。
(一)资料汇辑式汇编体诗法
此类汇编体诗法更重视诗学资料的广泛收集,能够给后学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料和参考标准。但也因资料的丛杂而影响其讲解过程中的明晰性和层次性,毕竟它不同于其他诗话汇编作为诗话渊薮[10]主要发挥备考备查之功能,而是需要后学从头至尾认真研读的诗学著述。而资料汇辑式汇编体诗法往往篇幅过大,内容庞杂,并不利于广泛地传播和接受。
如佚名《诗林丛说》73 卷⑪首列“引用书目”44 种,诗歌总集占大半,又有文论专著(文)、后人诗话和笔记、明清音韵著作。其后为目录,分73 卷,每卷有标目。第1、2 卷为“统论”,辑前人统论诗歌之文;卷3、4“古歌谣辞”和“琴曲歌辞”,专述古籍所存上古三代之歌谣、曲词,卷首皆列吴讷《文章辨体》于各体之“序说”,后罗列题目,题目下为两行小字之题解;卷5“骚体”,多取胡应麟《诗薮》相关议论;卷6“乐府一·历代乐府始末”,辑前人总论乐府之文;卷7 至13 共7 卷,分论乐府各体,体例同卷3、4;卷14“乐府九·解艳趋和诸释略”辑自《古今乐录》解释乐府相关用语并举例,后附历代乐府总集书目——“附录古今乐府诸选”;卷15“乐府十·诸家论乐府”,辑录前人诗话之细论乐府者;卷16 至29 共14 卷,分论古近体诗,各体之中,采辑诗论皆有次序,往往先总论,后分论,末尾多论杜诗之属于该体者;卷30 至33 共4 卷,论应特殊要求之体者:和韵、联句、拟古、集句;卷34 至39 共6 卷,论杂言、杂体诗,即诗体之有特色者;卷39 至48 共10 卷,为“诸家名论”,辑历代诗论,亦略有次序:总论、辨体、论各代诗、诗法,多为前人诗话;卷49 辑前人于诗题及小序之议论;卷50至60 共11 卷,论古、今音韵,多辑自音韵著作,意在为作诗押韵作工具书用;卷61、62“诗余”,辑前人词论,意其为诗之余脉也,亦仿前例罗列词之各体各题,每体分类,每题说明大致格式;卷63 至73共11 卷为“历代诗人姓氏略”,详列自汉至明文人诗作家生平或评价,惟末2 卷专录福建籍未甚知名之作者。是辑之有特色者首在篇幅浩大,一因喜大段乃至全篇采辑前人诗论,如引《文心雕龙》《文章辨体·序说》中单篇文章等;二因正文中诗体、诸家名论、音韵、历代诗人介绍几个较大板块皆自成体系,作者采辑前人之论也是不厌其详。综论之,全书虽然资料丰富,安排有序,但各板块之间缺乏衔接,对于学诗者而言,缺乏较强的指导意义,且卷帙浩繁尤不利于初学者翻检,故参考意义大于研习价值。
同属此类者,还有费经虞、费密《雅伦》,马上巘《诗法火传左编》⑫等。
(二)入门教材式汇编体诗法
正是惩于上述著作繁冗的弊病,才有了更加简明叙述和讲解的入门教材式汇编体诗法,张潜《诗法醒言·凡例》中说明了其对《雅伦》的删节情况,就是编者自觉的表达。这类著作相较诗学材料的大量汇辑,强调的是书本的可读性和其指导下的可操作性,所以篇幅不大甚至是简洁,与前者形成鲜明对比。
如上文提到的《诗法醒言》⑬10 卷,卷1 分三部分:“本源”与自序对应,辑他人诗论之阐述诗歌发生、发源者;“支派”沿本源而来,辑论诗歌后续发展、衍生之状;“统论”辑他人于诗歌之综论。卷2 分前后两部分,前者辑五古、五律、五排、五绝、七古、七律、七绝各体之说,后者辑作法:练字、炼句、选辞、用事。卷3 辑诗格之论,讲各体之基本格式和各种具体结构方法,分四部分:五律、五绝、七律、七绝。卷4 分辑五、七律具体作法,两体又各分起法、对法、结法、诗调四步骤,并各附唐人名对以为示例。其示人以“诗调”,与诗格相应。卷5 至7 共3 卷论诗品,张氏旨在发扬己论,首列三品、八体而立论,后辑列陈应行《吟窗杂录》之“十一格”、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费经虞《雅伦》之“十八条”,意在参考。三卷之主要部分则为张氏“三品·二十一衡”之讲论,二十一衡归列“神”“雅”“逸”三品,每衡于名目之后先作讲解,少加引述,多为己论,然后罗列前人名作以为诗例,十数首至数十首不等。卷8 前半部分论乐府,卷首辑前人于乐府之综论,末附己论,后罗列乐府各体之诗例若干,不甚全,然各体皆有,意在诗例耳;后半部分辑各类杂体诗,只罗列各体之诗例,未辑他人相关诗论,亦无所发明。卷9 辑他人“论诗及事者”,分时代、盛事、哭志、针砭、剧谈五类,意在展示作诗之具体情形。卷10 分三部分,首论音韵,辑他人论诗之音韵者,后附沈约《韵类》、《礼部韵略》、《洪武正韵》。次论诗题,先辑他人相关议论,后分类罗列诗题,有:古歌曲题、瑟调曲、吴声曲、六朝雅题、唐人雅题、唐人长题,考此分类与目录颇有不同,当是辑者失察处,末辑两则议论;后有“诗叙”部分,只辑前人之诗题、诗叙,当是视其为诗题之一部分。最后一部分罗列历代分人、分代之诗体,末辑略论清代诗体者。是辑仿费经虞《雅伦》而成著,体例与之颇近,所不同者,意在精简,如少列作品、不辑论及辞赋者,故得费氏体例之周严而更整饬。
同属此类者有李畯《诗筏汇说》、蔡钧《诗法指南》⑭、邬启祚《诗学要言》⑮等。
(三)诗学概论式汇编体诗法
相较资料汇辑式汇编体诗法求详求尽的编著理念,诗学概论式的编著思路则明显倾向于简括性地讲解、描述传统诗学的基本问题和整体面貌。前者中的《雅伦》所以被人称作“诗学百科全书”[11],这一点也在前文的叙录中得到了印证,而后者因其对诗学的整体把握,故可命之曰“诗学概论”,当然其指导诗歌作法的学术性质并不因此而淡化,反而 是一种凸显。其实早在宋末成书的《诗人玉屑》就曾被认为初步具有诗学概论的性质[12],但《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以格法分类……颇失简择”,[13]指出了其以诗法汇编为主和资料冗杂的特点。前者降低了诗学概论应有的综合性,后者破坏了其表述上的简洁性。而清代汇编体诗法《小沧浪诗话》[14]则克服了上述缺陷,真正实现了诗学概论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张燮承《小沧浪诗话》将全书分4 卷,各卷又共分19 个子题目。详考此书具体内容和编著思路,当分四个部分:第一卷的“诗教”“性情”“辨体”为第一部分,是关于诗歌的总论。“诗教”主要宣扬儒家思想中的传统诗教观念,“性情”说明诗歌教化作用的实现机制关键在性情,“辨体”讲情感表达的差异造成诗歌体式的丰富,并介绍了各主要诗歌体式的基本情况。第一卷的“古诗”“律诗”“绝句”和第二卷“乐府”“咏物”五目为第二部分,分别讲解诗歌的各种主要体式的详细特征与作法,即诗体论。“古诗”“律诗”“绝句”“乐府”基本沿袭同样的讲解方式,首先介绍其基本特征,随后介绍了各自的源流演变,最后是就此体式特征而总结的作法要求。“咏物”,虽然从分类方式来看,与前面各体式标准不同,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诗歌体式,所以我们仍可以将其归为本书“分体论”的内容。第二卷“论古”为第三部分,评论历代主要诗人及作品,即鉴赏论。本目编著基本以时间为线索,依次品评,但张氏并非简单罗列前人诗评而是在时代和诗人选择上多有侧重,尊唐倾向明显。第三、四卷十目为第四部分,讲诗歌创作。“取法”讲诗歌创作的第一步是要找到自己的学习对象。“用功”讲学习诗歌创作过程中通过不断锻炼来提高技能水平的着手处。“商改”讲诗歌创作中修改的问题,包括修改的必要性、重难点。“章法”未讲具体方法,而重视诗歌结构中的隐藏性因素——脉理、词气、组诗的结构、诗歌结构的预设和创新。“用韵”首先说明不必过于拘泥前人提到的一些十分苛刻的诗歌用韵规则,然后重点提出了一些诗歌唱和中用韵的基本规则,而不主张看重诗歌唱和中的游戏性。“用事”首先介绍诗歌创作中使用典故的基本要求,然后分享了一些前人用事的经典案例和经验,之后分析了读书学习与诗中用典的关系,强调用典是来自平时读书的积累,而不是为了通过诗歌创作中的刻意用典来提升自己创作的文化内涵和水准。最后解析了一些诗歌用典的疑难和避忌。“下字”讲诗歌创作中的练字,即对关键字眼的选取。首先列举一些妄改古人诗作中关键字眼的例子,进而说明诗歌创作中练字的重要性。然后详细讲解练字各方面的要求和避忌:避免痕迹、重视独创、追求平易、同义词的取舍、用字的雅俗、叠字的锻炼。“辞意”分析怎样处理诗歌语言与诗歌思想内容的关系。“指疵”介绍了诗歌创作中的一些避忌。首先简单概括地说明基本避忌,然后重点分析诗歌语言运用上的缺陷。“发微”阐发诗歌创作中的幽微之处,即创作过程无法作出明确规定,只能用语言作象征或比喻式描述。
同属此类者,有张揔《唐风怀诗话》⑯、李其彭《诗述》⑰等。
三、探源与辨析
兼具汇编和诗法性质的著述并非清代独有,前代即有类似诗学著述,可以认为是清代汇编体诗法的前身。如前所述,汇编体诗法的本质性特征一在广泛汇编既有诗学资料,二在全面、系统的诗法指导。如果褪去清代诗学独有的“历代诗评、诗法的集成”[15]色彩,明代颇具时代色彩的汇编性诗法著作多以“汇编尚不广泛、讲解不够全面和系统的”汇编体诗法面世。明代这类著作典型的作法是依托明初以来的宋、元人诗法丛编如付若川编《傅与励诗法》、怀悦刊《诗家一指》、史潜校刊《新编明贤诗法》和杨成编《群公诗法》等,为更加明晰地普及诗歌创作方法,多次变换、重新组合既有诗法成论[16]。这些著作指导诗歌创作的诗法性质自是不言而喻,但仍局限在南朝以来的诗格、诗式、诗法等狭义诗法范畴,与清人将诗法广义地理解为“知吟咏何从而起、性情何由而深,其所以裨益世道者何 在,其所以维持风教者何居”[17]大相径庭。这就凸显出明、清两代学者由对诗法范畴理解的差异所造成的诗法著述内容的时代差异。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差别,我们才能肯定地说汇编体诗法成立于清代,而明代的汇编性诗法著作只能算作它的前身。
不过,这样的区分也不是绝然明晰的,文体的发生与演进总是缓慢而渐进的,呈现着一定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否则脱胎于旧文体的新文体就不能顺畅地为受众所接受和认同。明代初期,面对元代留下的众多诗法著述,学者汇编诗法的主要方式是完整收录其单部文本,然后以丛编的方式加以整理、刊行。如前文提到的几部著作就是这一时期汇编性诗法的典型,它们已经具备了“汇编”和“诗法”的两个基本属性。不过,由于是整部收录,所以即使篇幅很小,其性质也更接近诗法著作的丛书或理解为广义上的“诗话丛书”[18],而不能完全看作一种文体。当然,从出版方式的丛书到著述方式的汇编体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毕竟,这些单部著作是以“卷”的形式归属在一个书名之下,而非以“册”或“部”的形式被冠以丛书之名。所以,这样整本录入的带有丛书特点的诗法汇编并不因后出转精的诗法著作之出现而完全淘汰,市场仍然有着实际的需求而与后出者并行,所以明代中后期还刊行了一些类似的著作,如嘉靖时的王俊民《诗法源流》、黄省曾《名家诗法》、熊逵《清江诗法》等。不过这种简单的收录汇编由自身发展之需求出发,也在不断地改进和突破,目的当是为了讲解的简洁和明晰。所以接着出现了配合编著者自己的诗法讲解系统的对元人诗法之节录,或者说其是主要摘选元人成著重新编排指导他人作诗之理论结构而成之书,完全摆脱了“丛书”的特质。这些新型汇编性诗法的编著者因应读者需求,体现了各自的学术眼光和诗学观念。这一类的著作有宣德时的朱权《西江诗法》、嘉靖时梁桥《冰川诗式》、万历时周履靖《骚坛秘语》、朱之蕃《诗法要标》、胡文焕补订之《诗家集法》、杜浚《杜氏诗谱》、佚名《诗文要式》⑱。这里值得补充的是,从丛编到汇编也有过渡性的著作可供今人参看,它们在延续整本录入的基础上而略有松动,对有些著作的录入作了一定的删节,虽然这样的删节很小,但是的确说明了编著者的能动性和选择意旨。如怀悦在刊行《诗法源流》第四部分时对《诗解》只录6 则,谢天瑞《诗法大成》后5 卷对《冰川诗式》的杂抄,等等。
再回到明代汇编性诗法演进的历程上来,除了对元人诗法的删节,明人逐渐扩大了自己的资料采辑范围,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里来讲解诗法。因为元人诗法本就有相互参考和引录宋人诗法的习惯,所以这也自然提示了明人不该将诗法局限在元人的讲解范围之内。当然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除了已经常被丛编或汇编的《沧浪先生诗法》⑲,明人将宋、元以来融入诗话的对诗歌作法⑳之讨论也加以引录、汇编。最后宋、明以来的诗话、诗评著作也被采辑,诗话汇编与诗法汇编“相混”[19],逐渐呈现出清人汇编体诗法广阔性汇编的特质。这样的著作在明代前期有黄溥《诗学权舆》,中后期尤多,如吴默《翰林诗法》卷1 对宋、明词臣诗论的汇编,《诗法集要》对《中山诗话》的辑录以及李贽《骚坛千金诀》、王述古《诗筌》、王良臣《诗评秘谛》等。这样,从明代的汇编性诗法到清代的汇编体诗法,就又近了一步。不过,由于前述明人狭义的诗法观,使其对于诗歌指导仍停留在诗歌作法的具体操作上,所以未能继续扩展自己的讲解范围,这在前述各著作的篇幅上体现得异常明显,其多为数卷乃至一卷成书,在迎合市场需求的同时也使自己的学术价值受限。
考明代此类著作篇幅超过10 卷而较丰富者,唯有黄溥之《诗学权舆》,共22 卷740 则,然其自11卷后即为录诗并对其注解评析,理论讲解仍局限在前10 卷418 则诗论上。而且前10 卷讲的仍然是诗歌具体作法,整体上与宋末《诗人玉屑》有着几乎相同的结构安排。㉑唯成书于晚明,迟至清初刊行的胡震亨《唐音癸签》,才基本具备了清代汇编体诗法的性质,这主要是就其讲解唐诗的全面性而得出的结论。因为胡著本是一部全面描述唐诗情况、探
讨唐人作诗方法、品评唐诗具体作品的集大成之作。而我们之所以可以将其界定为广义之诗法,那是因为全书虽专论唐诗,但无论是资料的来源采辑还是对象的讨论,都涉及到了历代所有诗论,不拘于唐诗之范围。更重要的是,明代诗学复古派将唐诗几乎等同于诗歌而将宋诗踢出了诗歌的范畴。作为其中一员,胡震亨对唐诗的全面讲解也可以看作是其对诗歌的全部认识,教人作唐诗就是教人作诗,所以今人评价胡著道:“在复古主义的旗帜下,力求从前人创作中为每一种诗体确立一种最高的也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创作规则与审美取向,并以此来规范与指导当时的诗文创作”[20]。这正道出了《唐音癸签》作为汇编体诗法的全面讲解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和诗法意义,因为这之前的汇编性诗法都没有意识到诗法还有如此广泛的延展性。具体到该书之内容,《唐音癸签》卷1 讲诗之体裁变迁及声病,卷2 至4分别讲诗法统论、分体之法和字句偶对用事,卷5至11 汇评唐诗,卷12 至15 谈诗乐关系,卷16 至24 训释唐诗用语,卷25 至29 录唐诗逸闻,卷30 至33 介绍唐诗文献。对照今人对中国传统诗学理论体系的总结,可以说胡著已经很接近清人汇编体诗法对于诗歌作法全面性的讲解特征,唯有缺失的是关于诗歌社会学的讨论㉒。而这也正有待于清人的充实,所以成书于清初顺治年间的《雅伦》和《唐风怀诗话》等汇编体诗法都显示出了比《唐音癸签》更加完善的诗法体系。也正是到了《雅伦》的时代——清初,我们才能肯定地说,作为沟通传统诗学与现代诗学的集成性文学批评之文体——汇编体诗法正式成立了。
注释:
① 清代汇编类诗话著作共计约一百余种,主要包括三大类:地域类汇编、断代类汇编和本文所述之诗法类汇编,另外还包括其他少量不能归入此三类的诗话汇编。
② 自撰与汇编是清代诗学的两种基本著述方式,正在刊行的《清诗话全编》即以此为标准分内、外两编出版。
③ 此三类除可总称“诗法”外,又可命之“技巧批评”而与“理论批评”相对应。
④ 早起诗话作者大多持此观点,如欧阳修在《六一诗话·前言》中所说的“自资闲谈”和司马光在《温公续诗话》所说的“记事一也”等。
⑤ 关于此三种诗话汇编主要内容是论诗及事的诗话,皆见于郭绍虞《宋诗话考》相应章节。
⑥ 晚清学者林昌彝就说到:“凡涉论诗,即诗话体也”;何文焕《历代诗话》及其《续编》等近世影响特大的诗话丛书也将诗话范畴扩展到了诗法、诗评、句图等。
⑦ 费经虞、费密《雅伦》虽被《四库全书》认定为明代著作并为后人普遍接受,但详考原书序言、后记,可知该书的构想与编著时代都已入清代,且编著地点也在满清政府的实际管辖地,而非明亡后的南明遗留政权范围内。所以认定其为清人著述才符合历史事实。现存三种刊本:康熙十年(1671)怡全堂刊本,康熙四十九年(1710)江都于王枨刊本(26 卷),雍正五年(1727)汪玉球重修本(24 卷)。
⑧ 当为元人佚名或题范德机撰《诗家一指》,编者有误。
⑨ 当为《玉堂漫笔》,编者有误。
⑩ 有乾隆二十三年(1758)醉古堂刊本。
⑪ 有上海图书馆藏抄本。
⑫ 有顺治十八年(1661)古香斋刊本,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民国间抄本。
⑬ 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乾隆初年刊本。
⑭ 有乾隆二十三至二十五年间(1758-1760)匠门书屋刊本,上海诗学研究会刊本。
⑮ 有宣统三年(1911)番禺邬氏丛刻本,民国间刊半翻楼丛书本,民国二十年(1931)刊邬家初集本。
⑯ 有顺治十七年(1660)刊本、藏上海图书馆嘉庆元年(1796)雨花草堂刊本。
⑰ 有乾隆四十一年(1776)徐子素戒盈斋刊本。
⑱ 有《诗法统宗》本、《格致丛书》本。
⑲ 即现在流行之严羽《沧浪诗话》,今名始自明中期之正德年间。详见张健《〈沧浪诗话〉非严羽所编》,《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 期,第36 卷,第80 页。
⑳ 蔡镇楚所说“诗话之作虽不无诗律之论,但体大旨宏……漫谈写作技法……熔诗论……于一炉”就是对宋代诗法融入诗话情形的描述。见其《唐人诗格与宋诗话比较》,《中 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3 期,第24 页。
㉑ 《诗人玉屑》结构上和内容上的缺陷可见本文第二部分相关论述。
㉒ 钟仕伦的总结很有代表性,其将传统诗学理论体系分九门:诗本、诗用、诗思、诗式、诗事、诗评、诗史、诗礼、诗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