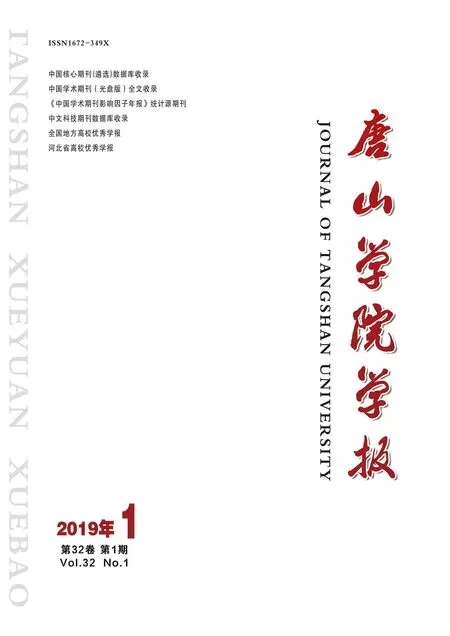论王鹏运《庚子秋词·渔歌子》的“词史”品格
(唐山学院 文法系,河北 唐山 063000)
在近代词史上,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等人的《庚子秋词》以相互唱和的方式,写照了庚子事变中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反映了词人心灵与时代命运的息息相关,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其中,鹜翁(王鹏运)以珍妃命运为主题的《渔歌子·禁花摧》一首,更因其所反映的重要史事而为人所瞩目。此前已有学者特意拈出此词,进行注解、分析,功绩值得肯定[注]陈正平《〈庚子秋词〉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卓清芬《王鹏运等〈庚子秋词〉在“词史”上的意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5月)均对此词作出了解析。。但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未注意到其中某些字句背后隐含的“微言”,《渔歌子》中所包含的重要“词史”价值实际尚未被真正抉发出来。本文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此词进行更进一步的笺释,以揭示其所隐藏的重要史事内涵,以及王鹏运作为词人所具有的“词史”品格,请各位方家指正。
一、《渔歌子》笺释
笺释之前,需对《庚子秋词》的创作意义及版本情况作一说明。首先,关于《庚子秋词》的创作背景,王鹏运《〈庚子秋词〉叙》云:
光绪庚子七月二十一日,大驾西幸,独身陷危城中,于时归安朱古微学士、同县刘伯崇修撰先后移榻就余四印斋。古今之变既极,生死之路皆穷,偶于架上得丛残诗牌百许叶,……乃约夕拈一二调以为程课,……自八月二十六日起,至某月某日止,凡阅若干日,得词若干首,……每夕词成,古微以乌丝阑精书之,伯崇题其端曰《庚子秋词》,盖纪实云。半塘僧鹜记。[1]
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慈禧太后试图藉助义和团的力量对抗外国势力达到专政目的,遂纵容拳民反洋。至五月末,事态激化,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向津、京进犯。七月二十日,北京城破,二十一日黎明,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出京城、奔往西安。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签订后,方于八月二十四日起驾回銮。这一事件,即被称为“庚子事变”或“庚子国变”。
据序文所言,事变发生时,王鹏运“独身陷危城中”,困守斋中;为避乱兵,朱祖谋、刘福姚也先后搬至四印斋与之共居。《庚子秋词》的创作,便是在这样一种“古今之变既极,生死之计皆穷”的氛围中完成的。可知王、朱、刘等于庚子事变中的一系列事件,是以亲历者的身份,以微言写时事,其意义自不同于一般咏史感叹之词。
《庚子秋词》现存版本,主要为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及民国间有正书局石印本[注]按:《庚子秋词》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白纸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黑口,左右单边,单鱼尾,封面题“辛丑冬月古微前辈持赠,萸生记”字样(辛丑,清光绪二十七年。萸生即万萸生,尚书万青藜之子,与王、朱皆友善);卷首题“庚子秋词二卷,春蛰吟附”,有永嘉徐定超叙,半塘僧鹜记,张亨嘉、宋育仁、刘恩黻题辞,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99733。有正书局石印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左右单边,单鱼尾,前有永嘉徐定超叙、半塘僧鹜记、复葊题辞,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86912。另有清末刻本两种,其一有“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钤印,内容、形制与光绪二十七年刻本同,惟前多俞陛云、张仲炘题辞;其二一函四册,形制、内容与光绪二十七年刻本完全一致,惟四张纸一叶,厚度大大增加,故析为四册。此两刻本当为后出。本文所引文字,以光绪二十七年刻本为底本,校以有正书局印本。。内容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起(庚子年)八月二十六日,讫九月尽,凡阅六十五日,拈调七十一,得词二百六十八,附和作三十九,共三百又七首”;下卷“起十月朔,讫十一月尽,凡阅五十九日,拈调六十一,得词三百十三,附原作二,共三百十五首”。《渔歌子》出《庚子秋词》卷下,其词云:
禁花摧,清漏歇,愁生辇道秋明灭。冷燕支,沉碧血,春恨景阳羞说。
翠桐飘,青凤折,银牀影断宫罗韈。涨回澜,晖映月,午夜幽香争发。[注]“秋明灭”,底本作“秋明烕”,据有正书局本改;“韈”,有正书局本作“袜”;“晖”作“辉”;“沉碧血”原作“沈碧血”,径改。
《渔歌子》所咏主题为珍妃之死,在当时已为人所知:清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濒行,太后命崔阉自三所出珍妃,推堕井中。……朱学士祖谋、王给谏鹏运赋《落叶词》纪其事。”[2]68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再谈珍妃之死”条亦云:“以予所知,……王半塘《庚子秋词》乙卷,调寄《渔歌子》,……其中托词寓讽,率指兹事(珍妃之死)。”[3]
(一)“禁花摧,清漏歇,愁生辇道秋明灭”笺释
“禁花摧”,唐王涯《宫词》:“春风摆荡禁花枝,寒食鞦韆满地时。又落深宫石渠里,尽随流水入龙池。”[4]3888五代尹鹗《满宫花》:“风流帝子不归来,满地禁花慵扫。”[5]用“禁花”点明所咏乃后宫妃子。同时朱祖谋亦有《声声慢·落叶词》:“香沟旧题红处,拚禁花、憔悴年年。”[6]203
“清漏歇”,指凌晨时分。唐权德舆《奉和李相公早朝》:“五更锺漏歇,千门扃钥开。”[4]3615清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七月二十日,英军陷京师。翌日,联军继之。两宫黎明仓皇乘民车出德胜门。……濒行,太后命崔阉自三所出珍妃,推堕井中。”[2]68清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亦云:“二十一日,天未明,……珍妃有宠于上,太后恶之,临行推堕井死。”[7]449“禁花摧,清漏歇”二句,言凌晨时分,珍妃遭到摧折,即被害。
“愁生辇道秋明灭”:辇道,指由珍妃被囚之故宫东北角景祺阁后东北三所[注]按: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崔玉贵谈珍妃之死”一节云:“景祺阁北头有一个单独的小院,名东北三所,正门一直关着。……珍妃住北房三间最西头的屋子,屋门由外倒锁着。”据此可知珍妃被囚之所,为故宫宁寿宫东北三所,具体位置位于宁寿宫后区景祺阁北、贞顺门南。宁寿宫后区中路建筑,由南往北依次为乐寿堂、颐和轩、景祺阁、东北三所。今故宫博物院景祺阁区域封闭,故无法得知东北三所之详貌。至颐和轩的甬道。《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辇道纚属。”颜师古注:“辇道,谓阁道可以乘辇而行者也。”[8]“秋明灭”,杜甫《北征》:“旌旗晚明灭。”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此句言珍妃于秋日凌晨明灭黯淡的光线中走上去往颐和轩的甬路,心中忧愁渐生。
何荣儿口述,金易、沈义羚著《宫女谈往录》云:“由东北三所出来,经一段路才能到颐和轩。我(崔玉贵)在前边引路,王德环在后边伺候。我们伺候主子向例不许走甬路中间,一前一后在甬路旁边走。小主一个人走在甬路中间,一张清水脸儿,头上两把头摘去了两边的络子,淡青色的绸子长旗袍,脚底下是普通的墨绿色的缎鞋(不许穿莲花底),这是一幅戴罪的妃嫔的装束。她始终一言不发,大概她也很清楚,等待她的不会是什么幸运的事。”[9]205
“秋明灭”写秋日凌晨光线晦暗不明的样子,同时也暗示人物心情的起伏不定,似乎已预感到自己即将遭到厄运,正可与《宫女谈往录》中所言“她始终一言不发,大概她也很清楚,等待她的不会是什么幸运的事”相参证。
需要指出的是,《宫女谈往录》言珍妃被害之时间乃是七月二十日下午,与恽毓鼎、李希圣之说法有所出入:
七月二十日那天中午,我(崔玉贵)想乘着老太后传膳的机会,传完膳老太后有片刻嗽口吸烟的时间,就在这时候请膳牌子最合适。……就在这时候,老太后吩咐我,说要在未正时刻召见珍妃,让她在颐和轩候驾。[9]203-204
《宫女谈往录》所述珍妃被害事,乃是当事人(推珍妃入井之凶手)崔玉贵亲口所说、宫女何荣儿转述,于情于理,均无伪造掩盖之可能,故当为珍妃被害一事最可信之史料。珍妃被慈禧太后下令推入井身亡,毕竟为宫闱密事,恽、李之记述,或可能得之于宫人之口,或可能得之于递相转述,究非第一手材料,于事件发生时间上有所舛误,情有可原。至于王鹏运词作何以亦出现此时间上之误差,下文还将论及,兹不赘。
(二)“冷燕支,沉碧血,春恨景阳羞说”笺释
“燕支”,即“胭脂”。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景阳井,一名胭脂井,又名辱井,在台城内。陈末后主与张丽华、孔贵嫔投其中,以避隋兵。其井有石栏,多题字。旧传云:栏有石脉,以帛拭之,作胭脂痕。或云石脉色类胭脂。”[10]珍妃井,在颐和轩北、贞顺门内[注]一说现故宫博物院内所标示“珍妃井”并非珍妃遇害之地,其井实在颐和轩内。然据《宫女谈往录》“崔玉贵谈珍妃之死”节所云:“我(崔玉贵)和王德环一起连揪带推,把珍妃推到贞顺门内的井里。”以及“庚子出逃前”节所云:“(慈禧太后)领着人,向后走,绕过颐和轩,路经珍妃井,直奔贞顺门。”可知珍妃井确在贞顺门内,而非颐和轩内。。贞顺门为宁寿宫宫墙北门,北向,门外西行可至神武门。珍妃井即在门内,距门口仅数步之远,周围亦有石栏。由颐和轩出,沿连廊北行,半分钟可至井[注]井旁侧有小门,可通景祺阁及东北三所。由颐和轩至井,走此路当更为快速。但目前小门及景祺阁均处于锁闭状态,无法入内详察。。此句盖以有“燕支”痕之景阳宫井暗指珍妃殒命之宁寿宫井。
“沉碧血”,出《庄子·外物》:“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唐成玄英《疏》:“碧,玉也。……苌弘遭谮,被放归蜀,自恨忠而遭谮,遂刳肠而死。蜀人感之,以匮盛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玉,乃精诚之至也。”[11]此句明确指出:珍妃“忠而遭谮”,一腔碧血沉于井中。
“春恨景阳”,《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隋文帝开皇九年春正月甲申:“陈主……从宫人十余出后堂景阳殿,将自投于井,……乃得入。既而军人窥井,呼之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贵妃、孔贵嫔同束而上。”[12]
《宫女谈往录》云:
珍妃说,我没有应死的罪!
老太后说,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
珍妃说,我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太后说,皇上也救不了你。把她扔到井里头去。来人哪!
就这样,我(崔玉贵)和王德环一起连揪带推,把珍妃推到贞顺门内的井里。珍妃自始至终嚷着要见皇上!最后大声喊,皇上,来世再报恩啦![9]206
此句表明珍妃死于井中,但她不是像陈后主、张丽华那样为避兵而自投其中,而是一腔碧血、被人所害,因而词言“景阳羞说”。“羞说”,即羞于启齿、对某事感到羞耻。唐陆龟蒙《甫里集》卷四《江南秋怀寄华阳山人》:“学徒羞说霸,佳士耻为跉。”[4]7212清金和《秋蟪吟馆诗钞》卷一《题庆子元白门访旧图》:“樽前且呼酒,羞说泪沾衣。”[13]虽是藉陈后主与张丽华投井避兵之事来咏叹珍妃之死,但作者着重指出“羞说”,意即珍妃绝非自投井而死,这是作者希望读者重点关注到的。1916年,甲寅杂志社出版《说元室述闻》,其中“纪珍妃轶事及辨殉国异闻”条末尾云:“近见某氏笔记,乃力辨妃于孝钦出宫后,追随不及,始自行投井者。妄也,附辨于此,读者勿为所惑。”[14]而半塘于庚子事变当时,似已预见到此种诬蔑行径之产生,特以“羞说”二字点明珍妃绝非自杀,其词之信史品格,由此可见。
(三)“翠桐飘,青凤折,银牀影断宫罗韈”笺释
“翠桐飘”,以桐叶飘坠喻珍妃之死。晋王嘉《拾遗记》:“汉武帝思怀往者李夫人,不可复得,……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因赋《落叶哀蝉》之曲。”[15]宋陆游《幽居》:“井桐飘叶觉秋深。”[16]
“青凤折”,唐李贺《天上谣》:“窗前植桐青凤小。”宋吴正子注:“西蜀有桐花鸟,似凤。故杜诗(按:应为苏诗)云:‘桐花集幺凤。’小凤也。”[17]桐叶飘坠,青凤夭折,以形象笔触写珍妃之被害,极为动人。
“银牀”,即井栏。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露井冻银牀。”钱谦益注:“《淮南王篇》:‘后园凿井银作牀,金瓶素绠汲寒浆。’梁简文《双桐生空井》诗:‘银牀系辘轳。’庾肩吾《九日》诗:‘银牀落井桐。’吴曾曰:‘《山海经》:崑仑墟有九井,以玉为槛。银牀者,以银作阑,犹《山海经》所谓以玉为槛耳。’”[18]一说银牀非井栏,乃辘轳架也。
“罗韈”,三国魏曹植《洛神赋》:“陵波微步,罗韈生尘。”[19]“银牀影断宫罗韈”,指井边人影已逝,空留她曾穿过的罗韈。以洛神宓妃射其身份及死于水中。
(四)“涨回澜,晖映月,午夜幽香争发”笺释
“幽香争发”,晋干宝《搜神记》:“初,钩弋夫人有罪,以谴死。既殡,尸不臭,而香闻十余里,因葬云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发冢开视,棺空无尸,惟双履存。”[20]《史记》:“上居甘泉宫,……欲立少子也。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云阳宫。”[21]以钩弋夫人被谴死之古典,喻珍妃被害之今典,其相同点在于二者都是本身并无罪过、而因政治原因遭到杀害。其无罪,一方面指珍妃被害前所言“我没有应死的罪”,另一方面指其平日的品行高洁、素无瑕疵。
“幽香”与“碧血”相互映照,意谓珍妃并无过错,和钩弋夫人一样,是被妄加罪名、无罪而死。她为国为君的节义,终当为人所知。
综上,王鹏运《渔歌子》咏珍妃之死,隐晦地写出了其被害的时间(“清漏歇”)与地点(“景阳(井)”),且其中有两个不可忽视的重点:一、以“羞说”表明珍妃绝非自投井而死,而是被人所害;二、以“碧血”“幽香”表明珍妃生前并无过错,是“忠而遭谮”、无罪而死。这两点的结合,是当时乃至后来的诗词作品所甚少做到的,堪称具有高度“词史”意识的“实录”[注]按:清末咏珍妃之死的作品,多未涉及到其品行,而只是哀悼她的华年遽逝,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势倾颓,故多将其与杨贵妃相比拟(如曾广钧《庚子落叶词》);涉及其品行的,则多数为慈禧太后懿旨所蒙蔽,认为珍妃确有“卖官”行径,品行有瑕(此点后文还将辩及,此处不赘)。少数知其诬枉并写出者,则已多为民国间作品,于时文禁已无、消息流播,自可书写。但处在庚子年事件发生之时就了解这些情况,且敢于在作品中写出者,除王鹏运此词外,未见其他,“实录”之名,庶几无愧。。
二、王鹏运了解珍妃被害真相之途径
那么,王鹏运何以能得知珍妃并非自杀?在当时普遍认为珍妃“卖官”的情况下,他又为何坚持珍妃一腔碧血、并无过错?这实际与他的身份、品行、交游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发生时,王鹏运表面上仍以礼科给事中之身份在官,实际却已形同斥逐、地位尴尬[注]况周颐《礼科掌印给事中王鹏运传》:“试俸期满,援例截取,奉旨以简缺道员用。……故事,京曹截取,皆以繁缺用;以简缺用者,自鹏运始。”又《眉庐丛话》:“向来京曹截取道府,皆以繁缺用,以简缺用者,不用之别名也。”见张正吾等编《王鹏运研究资料》,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4页。。然而即便是此种状况下,当两宫出逃、京内大乱时,他也没有如众多“士大夫之官京朝者”一样“仓皇戎马、奔驰星散”,而是“独闭户如故”,坚持留在京城。这使他能够及时了解到更多的消息与内情。事实上,有关两宫出逃、珍妃之死的消息,很有可能在事变发生后不久即已流传开来了:《宫女谈往录》指出,七月二十日晚,宫中已有出逃迹象,且珍妃被害之消息,此前已为宫人所知:
其实,就在这一天(按:指七月二十日),这个时候,这个地点,老太后赐死了珍妃,她让人把珍妃推到颐和轩后边井里去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晚上便有人偷偷地传说。……[9]200
这天晚上,……又说好多寿膳房的人当了义和拳的都逃走了。我们当然心惊胆战!
正赶上我上夜(值夜班),到丑末寅初(三点四点之间)的时候,突然听到四外殿脊上,远远地像猫叫,尾声很长。……我悄悄地出来,知会外边守夜的人,因为我们心里有鬼。……知道昨天珍妃死在井里,以为她冤魂不散显灵来了。[9]212
清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二十一日,(两宫出逃)……诸宫人皆委之而去,赴水死者数十人,其余走出安定门,遇溃兵被劫,多散失。……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城中火起,一夕数惊。”[7]449随着宫人出逃禁中、四散城内,两宫西狩、珍妃被害的消息,也必然渐渐流播人耳、为人所知。七月二十一日事变发生,至《庚子秋词》开始创作之八月底,王鹏运等留京士大夫于此已有相当了解,实属自然。王鹏运、朱祖谋之友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即对当时的情况有详细记载:
七月二十日,英军陷京师。翌日,联军继之。两宫黎明仓皇乘民车出德胜门。甫出门,白旗遍城上矣。太后御夏衣,挽便髻,上御青绸衫,皇后及大阿哥随行,妃嫔罕从者。濒行,太后命崔阉自三所出珍妃(三所在景运门外),推堕井中。……联军入,日本军护禁城,内庭晏然,乃出妃尸于井,浅葬京西田村。(朱学士祖谋、王给谏鹏运赋《落叶词》纪其事,余亦赋诗云:“金井一叶堕,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2]68
光绪二十六年事变发生之时,据曹允源《原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恽府君墓志铭》,恽氏并未离京:
庚子拳匪之役,八国联军长驱闯京师,车驾仓皇西狩,人心汹惧。府君独偕吏部尚书敬信公单车入使馆,与各国使臣商保卫地方之策,力争主权。创协巡公所,令司坊官莅所判决民事,民遂安堵。会事平,特疏吁请回銮。[22]
两宫出逃之时,恽氏身在京中,又素有探听消息的条件与渠道,故《崇陵传信录》中记载两宫出逃及珍妃之死,与《宫女谈往录》相印证,多有相合之处。惟珍妃被害之时间,误作七月二十一日凌晨。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此事毕竟为宫闱密事,恽氏获知之消息于事件发生时间上有所舛误,也属正常。除恽氏外,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亦云:“二十一日,天未明,……珍妃有宠于上,太后恶之,临行推堕井死。”[7]449成本璞《李先生墓表》言:“未几,有庚子联军入京之变,乱兵大掠,先生仅以身免。”[23]可知李希圣当时亦在京。
恽毓鼎、王鹏运及李希圣在珍妃被害时间上不约而同出现这一错误,恰可证明此消息已流播人耳。三人或从不同渠道听闻此消息,或彼此间有所联系而递相传述,皆有可能。于时流言虽多,谣言则少,故虽时间上有所舛误,然于珍妃生死之大节——被害而绝非自尽,三人皆以史家应有之品格,作出了真实的记录。
三、王鹏运了解珍妃品行之途径
综上,可知王鹏运因在庚子事变发生时选择留在京城,由此得以获知包括珍妃之死在内的宫闱消息,并以“春恨景阳羞说”这样隐晦却优美的微言,对珍妃的节义进行了赞颂。事实上,王鹏运本人也是一位饶有品节的臣子,监察御史的身份与正直敢言的个性,使他与珍妃之兄志锐、珍妃之师文廷式等“帝党”成员立场相似、素有往来,而他对珍妃素行、品格的了解,也正来源于此。
王鹏运《八声甘州·送伯愚都护之任乌里雅苏台》云:
是男儿万里惯长征,临歧漫凄然。只榆关东去,沙虫猿鹤,莽莽烽烟。试问今谁健者?慷慨着先鞭。且袖平戎策,乘传行边。老去惊心鼙鼓,叹无多忧乐,换了华颠。尽雄虺琐琐,呵壁问苍天。认参差、神京乔木,愿锋车、归及中兴年。休回首,算中宵月,犹照居延。[24]8
题目中的“伯愚都护”,即志锐,字伯愚,他塔拉氏,光绪六年进士,瑾、珍二妃之堂兄[注]按:志锐之祖父裕泰有子长善、长敬、长叙,其中长敬为志锐之父,长叙为瑾、珍二妃之父。参《清史稿·志锐传》《裕泰传》及《清史纪事本末》“光绪十五年”条。。光绪二十年,“以其妹瑾珍两妃贬贵人,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释兵柄”。赴任之日,文廷式、盛昱、王鹏运、沈曾植等送之[注]参文廷式《八声甘州·送志伯愚侍郎赴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之任,同盛伯羲祭酒、王幼霞御史、沈子培刑部作》,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11页。。其时二妃遭贬、志锐外放,“帝党”遭到一系列打击,所处政治局势之险恶,人所共知。在此情况下,王鹏运仍送其赴任并赋词为之壮行,可见彼此间乃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同道,而非泛泛之交。
据《半塘定稿》《文廷式集》,王鹏运与志锐、文廷式、安维峻等人的交往,应始于光绪十九年其任江西道监察御史之后,光绪二十、二十一年间,尤为密切。兹简述如下:
光绪十九年七月,王鹏运补江西道监察御史缺。[25]10
光绪二十年七月,王鹏运上《倭夷肇衅,请任亲贤以资戡定折》,坚定站在主战立场。[25]82
九月二十九日,安维峻、王鹏运联衔上疏,请易督办军务大臣李鸿章,并荐户部尚书崇绮及国子监祭酒盛昱,王鹏运疏中言:“今倭夷猖獗,敢肆凭凌,……政府之臣……甚或阳图守御,阴主和议,为苟且目前之计。”[26]84[25]88
十月二十九日,慈禧太后谕旨将瑾、珍二妃贬为贵人。[27]523十一月,志锐被外放为乌里雅苏台参赞,王鹏运以词送之。
十二月,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上疏弹劾李鸿章,并谏慈禧“遇事牵制”(是疏之上,文廷式实主其事),遭革职戍军台,文廷式集银万余,以送其行。[28]1496半塘作《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以送之,有“尚记得、悲歌请剑,更阑相视”之语。[注]按:此处“悲歌请剑,更阑相视”,盖指此前九月二十九日与安维峻联衔参劾李鸿章事。[24]8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王鹏运上《割地讲和万不可行,请旨寝罢以坚战局折》[25]102-104,文廷式《琴风余谭》:“临桂王幼霞御史争割地一疏,有云:‘闻李鸿章奏调随员,有伊子李经方及道员马建忠、罗丰禄诸人。乱臣贼子,狼狈为奸,其可寒心,不啻兵临城下。’自谓警句,为余诵之。时论亦颇谓然。”[28]791
此年春,文廷式作《祝英台近》(翦鲛绡),半塘有和作《祝英台近·次韵道希感春》[28]1410[24]12。《味梨集》中二人唱和之作,前后有十三阕之多。
四月,文廷式乞假(实为避祸)出都,半塘以《木兰花慢·送道希学士乞假南还》送之。[29]此后几年间,二人亦有《鹧鸪天》、《高阳台》等词作往来。
其志同道合,则可由诸奏疏见出: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王鹏运《割地讲和万不可行,请旨寝罢以坚战局折》:“不知图目前一日之苟安,贻后日无穷之远患,实不如一意主战,百折不回,尚有转机之可冀矣。”[25]103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文廷式《和议难成恳速断大计以抒天下之愤折》:“臣愿皇上……永不复言和议。”[28]57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安维峻《请诛李鸿章疏》:“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26]119
光绪二十二年王鹏运《请暂缓园居疏》:“皇太后园廷驻跸,顺时颐养,以迓祥和,诚天下臣民所至愿;若皇上六飞临驻,揣时度势,有不得不稍从缓图者。……伏愿皇上……颐和园驻跸,请暂缓数年。”[25]11-12
光绪二十年六月文廷式《敬陈管见折稿》:“臣愿皇上宏大纲,持坚断,博采古今,详录众论,择其大者、远者,次第行之,则天下幸甚!”[28]5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王鹏运《请行实政以图内治而弭外侮折》:“中国之积弱年复一年,外侮之凭陵日甚一日,……亟望一申乾断,明定国是之归,以大雪积年之耻者也。”[25]136
从以上交游痕迹及奏疏可知,王鹏运与文廷式、志锐、安维峻等政治立场一致,具体表现在:①主战;②促慈禧归政;③寄望于光绪。知此数点,方能对半塘何以能知珍妃品格有所了解。
兹再辨志锐之外放乌里雅苏台因何事而起。《光绪朝上谕档》载: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内阁奉上谕:志锐着赏给副都统衔,作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照例驰驿前往。钦此。[27]539
此前十月二十九日,《光绪朝上谕档》有慈禧皇太后懿旨:
本朝家法严明,凡在宫闱,从不准干预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庭,向称淑慎,是以优加恩眷,洊陟崇封。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皇帝深虑渐不可长,据实面陈。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藉为夤缘蒙弊之阶,患有不可胜防者。瑾妃、珍妃均着降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钦此。[27]523
十一月八日志锐之外放乌里雅苏台参赞,乃十月二十九日瑾、珍二妃遭贬事件之余波。此点人所共知,然于二妃被贬之原因,则甚少注意。《清史稿·志锐传》仅言“以其妹瑾珍两妃贬贵人,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释兵柄”,于二妃何以被贬,则避而不谈;今人有注王鹏运《八声甘州》者,言“中日甲午之战失利后,翁同龢、志锐及珍妃等人支持光绪变法维新,事为慈禧所觉,乃搜光绪宫中,得珍妃西装影片一张,大怒,立杖珍、瑾二妃,并皆降为贵人”云云,变法维新、西装影片者,与此次事件实无关涉,未知何从立论。实则十月二十九日懿旨中已言明二妃降为贵人是因“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清末胡思敬《驴背集》“卖爵西园值几钱”诗注云:
上亲政后,(珍)妃颇干与外事。鲁伯阳进十万金,擢上海道,诏下而军机处不知其名。太后大怒,召妃至颐和园,杖五十,降为贵人,谪其兄志锐于边。[6]95
意即珍妃之遭贬,乃是由于接受鲁伯阳贿赂,为之在光绪帝前有所乞请之事。当时与胡思敬同样为此懿旨所蒙蔽、欺骗者不在少数,皆认为珍妃“卖官”。实则珍妃收受十万金贿赂之事,根本子虚乌有;其“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罪名,乃是慈禧太后对其的诬蔑、冤枉。由珍妃遭贬后第二天慈禧太后谕旨所刻的两块禁牌绝口不言“乞请”一事,即可明白这一点[注]参李松龄《慈禧挟制珍妃的两块禁牌》,《紫禁城》1986年第3期。另,关于珍妃“乞请”罪名之冤,蔡慧《金兆蕃〈宫井篇〉发微》(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已辨之甚详,不赘。。即不由此两块禁牌,从志锐、文廷式等的品行,也可知此事实乃诬蔑。《清史稿》记,志锐“光绪六年成进士,……与黄体芳、盛昱辈相励以风节,数上书言事”;宣统年间赴伊犁之前,“以手书徧告戚友,言以身许国,不作生入玉门想”,最终死于伊犁。而文廷式的品节,亦自不必说。有如此兄长、师傅,珍妃焉能为受贿卖官、乞请干政之事!
慈禧太后何以要诬蔑珍妃以干政乞请之罪名?其原因一方面是挟私报复,因自己为光绪帝所选皇后受到冷落,故诬蔑、惩罚受宠爱之珍妃;另一方面,则是为打击光绪帝及“帝党”。甲午中日战争,“帝党”成员坚定站在主战一方,与慈禧太后等主和派之间矛盾尖锐。志锐之遭外放,事实上与其主战的态度和手里掌握的兵权亦不无关系。《清史稿》:“东事起,(志锐)上疏画战守策,累万言。虑陪都警,自请募勇设防,称旨,命赴热河练兵。未踰月,以其妹瑾珍两妃贬贵人,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释兵柄。”无论是坚持主战的态度,还是有可能被光绪帝一方掌握的一点点兵权,在慈禧太后看来,都是不可原谅的。换言之,无论是对珍妃的诬蔑,还是对志锐的斥逐,其根本目的都是对光绪皇帝和“帝党”的打击。
综上,可知志锐之被谪乌里雅苏台参赞,是因受到瑾、珍二妃被贬的牵连;而二妃之被贬,则是由于慈禧太后为挟私报复、打击光绪及“帝党”,而给珍妃扣上了受贿卖官的罪名。
现在回到本章节开头所引王鹏运《八声甘州·送伯愚都护之任乌里雅苏台》。志锐此行,直接原因是由于受到珍妃“屡有乞请”一事的牵连,而此事,“帝党”人所共知,乃为冤案。文廷式在光绪二十二年所作的《闻尘偶记》中,就已对鲁伯阳得官之途径作过隐约的透露[28]744。而王鹏运其时与志锐、文廷式立场一致、关系密切,于此事焉有不知之理?即便不清楚其中细节,据其平日与志锐、文氏等的相处、交游,亦不至不了解其品行而对此罪名毫无怀疑。明乎此,则王鹏运写下“碧血”“幽香”等微言,是要道出珍妃“忠而遭谮”、无罪而死的事实,为她洁白无瑕的品行留下记录,可以无疑。
综上所述,王鹏运《渔歌子·禁花摧》一词中最关键之微言,在于“羞说”及“碧血”“幽香”六字。前者表明珍妃绝非自投井而死,而是被人所害;后者表明珍妃生前并无过错,是“忠而遭谮”、无罪而死。其所要表达的核心情感,是为珍妃这位贞烈女子之惨死鸣不平,为饱受打击的主战派、自己的友人志锐、文廷式等鸣不平。《渔歌子》,以及整部《庚子秋词》,是在庚子国变这样一种天翻地覆般的巨变中,满含深痛写下的字字血泪的篇章。
庚子之变后有关珍妃的吟咏中,不乏长篇联章者。与之相比,王鹏运《渔歌子》仅以“碧血”“景阳羞说”“幽香争发”等微言隐晦地点出珍妃无罪及被害坠井的两个事实,显得幽微而难解。这自然与清廷尚未覆亡、思想控制仍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仅以这寥寥数语、仅以全词50个字的极小篇幅,却能够揭示旁人需要长篇大论才能表达的内容,王鹏运何以能被冠以“清季四大词人”之称,于此可见一斑。比高超的艺术技巧更重要的是,王鹏运敢于直言上疏、敢于在乱兵中坚留京城,这是他能够得到文廷式等人的友谊、能够知晓珍妃之死的内情、能够写出这篇优秀作品的前提。《渔歌子》的“词史”品格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