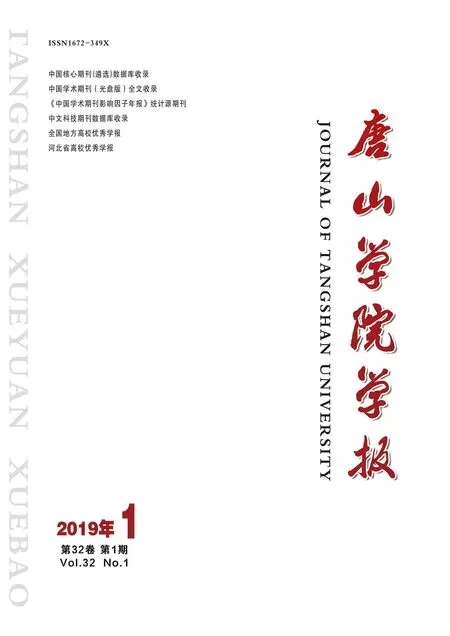论李大钊的中国文化观
(天津商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134)
在李大钊研究中,学界主要集中对李大钊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历史思想与经济理论等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成果也很丰富,对其文化思想的研究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李大钊在旧式私塾中成长,接受的是传统儒家启蒙教育,后留学日本,深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归国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充当了反专制主义的先锋。作为受到传统文化濡染和浸润过欧风美雨的文化人,其思想转折历程无疑是中国近代思想变迁的缩影。在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李大钊对中国文化具有怎样的认知历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作何理解?他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又作何厚望?目前学界尚少人论及,本文拟对此作进一步思考,以纪念这位功绩卓著却又不幸过早牺牲的革命家和思想家。
一
李大钊出生于燕赵之地,少读私塾,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扎根于李大钊的思想血液中,为其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养料。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一度成为李大钊深研政理、评判政治的价值标准。李大钊对孔子儒学的阐述,表现出了儒家文化的内在生命力以及优秀传统继承者的素质。他认为孔子作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经过历史的演变与发展,存在“实在的”“历史的”“世界的”三种形态,应对此加以区别对待。他视“实在的孔子”为圣哲,认为孔子之道“本此真理而成”,符合宇宙间“惟一无二之真理”[1]426。今尚存于世的是经过历史加工过的孔子,这种“历史的孔子”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历史痕迹,是历代统治者用以巩固专制统治的工具。李大钊认为这种被神圣化的孔子只是“君主政治之偶像”,不适应时代需要。同样,孔子作为世界四大圣哲之一代表文化的最高典范,享有至高无上的荣誉。他对现今的世界文化尤其东亚文化依然发挥着影响力,李大钊为此颇感自豪。他呼吁我们应恢复文化自信,发挥自身创造力,塑造出如孔子那般的文化伟人,改变中国文化落后的情态。
仁学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成为孔子儒家最普遍的道德原则。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和“为政以德”,主张仁爱逐步向外扩展,“泛爱众而亲仁”,进而将此推及到自然万物,并被后来的儒者所承扬,李大钊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辛亥革命后,有感于内忧外患的国内环境,他以民主共和为目标,提出振兴“国民教育”和“昌学”以挽“世运”,并号召“好学知耻之士”,应“以讲学明耻为天下倡,崇尚道义,砥砺廉节,播为风气,蒸为习尚”[1]160。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将仁爱与人道主义、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体现了人道主义的胜利,并指出“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会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通法则”。孔子仁学思想体现在行动上则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方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2]480。李大钊自小深受儒家道德主义传统的熏染,对国家民族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深沉的爱国主义和社会责任感。他在民族危难面前振臂高呼,救国救民的爱国精神和积极干预政治的入世态度,以及为革命而选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博大胸怀,便充分体现了孔子儒家经世济民、心忧天下的圣贤情怀。
道家文化对李大钊的影响体现在他利用传统的哲学语言来阐释西方的近现代文化。李大钊十分推崇老子的“第三”之境,认为“老氏之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知宇宙进化之理,由浑而之画,由一而之杂,乃为一定不变之律”[1]420,以此来说明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自然存在,是“宇宙生生之数,人间进步之极”[1]340。还引用庄子的“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如大年”来说明时空的相对性,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他的青春哲学。在李大钊看来,青春存在“青春之进程”与“无尽之青春”之分,个体生命的有限与无限的“宇宙自然之青春”,较好地诠释了宇宙与个体的关系。青春代表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力量,一种觉醒和朝气,是“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1]313。阐述了“有限”与“无限”、“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关系,认为无限是由有限构成展开的无限,有限则是无限青春长河中的有限,阐明个体“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的道理,其目的是使个体能够通过自我的努力,彰显自身存在的价值,不断地张扬个体的本质力量,从而达到“自我无尽”的理想境界。他认为青年的最大使命在于创造“青春之中华”,青年应充分发挥主体性,担起历史的责任。通过对老庄人生哲学的创造性诠释,批判厌世思想,以期唤醒青年的自觉。他认为青春人生是一种特立独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人生,“青年之自觉”在于“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1]317,摆脱历史的重负,不役于物,才能达到青春的大道。
同时,李大钊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重视民心民意和发挥民众力量,他的文章里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疾苦的同情和专制残暴的愤怒。在《民彝与政治》中,他认为专制政治的腐败源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民众在文化传统积习的重压下,没有言论自由,缺乏形成政治民主的传统。唯有改造国民性,充分发挥“民彝”的作用,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他还吸收了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和经世致用学风,对其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在《真理之权威》中,他倡导学术自信的精神,认为真正的学术能够执其所信,深刻影响于社会,即使“直接间接丝毫不为并世之人所用”,却能“默持其所信以终于暗昧之乡”。肯定了李贽反传统专制主义的学术精神,认为李贽“所信表而出之,而今其书固犹流在人间也”[2]149。在《风俗》中,李大钊充分发挥了顾炎武“保天下”的思想,认为风俗的好坏决定着国家的兴亡,即“离于人心则无风俗,离于风俗则无群”,并指出“一群之人心死,则其群必亡”[1]157,以此来强调以教化正人心、厚风俗的重要性。此外,李大钊的世界观也深受中国传统思想中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大化论思想的影响,认为整个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自然存在,是“真实本体”,客观存在着的物质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遵循固有的规律。此种思想可以说是李大钊接受进化论思想、形成朴素的唯物主义,直至最终接受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内在条件或思想基础。
二
五四运动时期,各种西方现代文化思潮涌入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对传统文化激烈批判的风潮。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以理性客观的态度、自尊自信的心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评析。
新文化运动初期,李大钊联系传统思想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传统文化弊端进行观照和反思,揭示出传统思想文化建立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上,以父权为中心的大家族制度为社会基础,具有压抑性、保守性和停滞性。针对袁世凯尊孔复辟帝制和立孔教为国教,他应用进化论和民主主义思想,一方面指出孔子儒学作为专制时代的产物,在“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但孔子儒学作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已成为“残骸枯骨”,而“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孔子与宪法,渺不相涉”[1]423。他认为孔子思想束缚了人们个性与思想的发展,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被禁锢在大家族制中,这便抓住了孔子思想消极面的本质。因此,他提出:“窥吾国思想界之销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而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孔子之束制。”[1]404宣告“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另一方面,李大钊以辩证的态度提出反专制与反孔教存在实质区分,指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1]429。他强调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孔子儒学代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应批判继承其思想的精华,“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1]427。在此基础上,他主张恢复儒学思想文化的本来面目,挖掘传统儒学思想中的积极内涵和优秀精华,按照现实和时代的要求,有选择地加以新的解释,再造适合中国的新体制以及世界的新潮流。他认为“孔孟亦何尝责人以必牺牲其自我之权威,而低首下心甘为其傀儡也哉”[1]274,如他提出要学习孔子的“创造之力”和“日新之旨”,发扬其“固有之精华”,创造“新国民之新历史”。主张以传统思想文化中非主体性思想文化——道家思想文化来弥补儒学思想文化之不足,在肯定老子“在道甚夷,而民好径”的作用时,他还指出:“为治之道不尚振奇幽远之理,但求平易近人,以布帛菽栗之常,与众共由。”主张以平易之境,简朴之生活,使民性顺其自然而发展,从而使个体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显现,才能“易简而得理,无为而成化也”[1]269。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方面,对孔子儒学产生、发展的原因,进行了更为深刻的阐释。他指出“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孔子思想正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上,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等都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大家族制度为社会基础,形成了家国一体化的政治格局。他对建立在大家族制度基础上的儒家伦理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孔子儒学的伦理观表现为:“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损卑下以奉尊长”“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他指出孔子思想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原因在于它是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3]186-187,也是中国大家族制度的表层构造,并非永久不变的真理,必将随着农业经济基础的动摇而崩解。在此基础上,李大钊分析了西方文明的传入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冲击,“中国今日种种思潮运动、解放运动”,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也是“打破孔子主义的运动”,而中国的工人运动,则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必将动摇孔子儒学的经济基础”[3]190。他还批判了“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的“旧史观”,主张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进行“重作”或“改作”,他认为“一切的历史,不但不怕随时改作,并且都要随时改作。改作的历史,比以前的必较近真”[4]524,从而推动古代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同时,李大钊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华也进行了选择性发展。他推崇儒家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人生观,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发展为革命的英雄主义,强调青年要“顺着向未来发展的大自然大实在的方面昂头迈进,变逆退的为顺进的,变静止的为行动的”[4]453。他继承了儒家的道德主义传统,提出用新的道德思想来培育国民,以“爱”为基础的“互助论”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3]22-23。显然,李大钊在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深入,在“进化论”和“互助论”的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内容产生了误解,因而他试图用传统文化中的“互助”“博爱”的观念去弥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道德方面的欠缺。他专门研究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的关系,分析了道德更新的必然趋势,提出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新内容,他认为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的、美化的、实用的、大同的、互助的和创造的道德。李大钊将“孝道”诠释为对老人的敬爱与赡养,在孝道的实践上,作为北大进德会成员,他为人宅心忠厚,对他人讲信修睦,一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矢志奋进于民族解放事业,可谓是儒家道德主义言行一致的实践者。可见,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吸收,成为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内在底色。他以辩证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批判与吸收带有理性的特征,有利于中国文化健康良性的发展。
三
如何处理中西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实现中西两种文化的有机结合,探索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所着力的核心课题。李大钊认为东西两种文化各有缺陷,也各有所长,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的差异,“实为世界进步两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他充分肯定了西方文化先进性、优越性,并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亟待克服的弱点,已经不适应世界发展的新潮流,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造。他说“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并主张“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在具体的方法论上,李大钊在吸收传统文化中调和持中思想的基础上,主张双向吸收、相融调和,再造新文明。李大钊所言的文化调和,讲求持中不偏,折衷和谐,与儒家的中庸之道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他主张两种文化在各自并存的前提下改造与创新,是内在结构的自我调整和内容的自我更新,他强调两种文明“本身各有澈底之觉悟,而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2]311-322。李大钊的文化调和论是他对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思考的积极成果,也是他提出“第三文明”论的理论基础。
李大钊的“第三文明”观是他在对东西文明深刻思考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出路所提出的一种新型构想。“第三”源于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一种理想独立、日新向上的境界,昭示着事物的发展与进步。而“第三文明”正是吸收东西文化、取长补短的结果。李大钊认为文化发展是相互影响和渗透的,正是因为东西文化各自的困境,才使得“第三文明”的产生成为时势必然。李大钊进一步指出,“第三文明”是“灵肉一致”的新文明,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统一的文明。在对东西文明观察和思考的基础上,他提出“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2]311。在李大钊看来,俄国在地理位置上位于欧亚接壤地带,兼有双重文化的特征,而俄罗斯文明作为东西文明融会之交点,有“向上发展之余力”,是新文明的起点,代表新文明发展的方向。李大钊将俄罗斯文明视作世界新文明的开端,“第三文明”实现的契机,并号召青年为创造“第三文明”的新中国而努力。
李大钊的“第三文明”是他寻求民族存亡的解决之道及中国文化之命运的答案,为他深入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并率先由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思想基础,他坚定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推动中国文化走向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新方向。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文化在国内得以广泛传播,李大钊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对此作了阐释,他将儒家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指出两者最终社会理想就是“使人间一切关系都脱去力的关系,而纯为爱的关系,使人间一切生活全不是争的生活,而纯是爱的生活”[3]214。他指出人类进化的轨道就是通向“世界大同”,即“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的“大同景运”。并针对“社会主义是不道德”的指责,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劳动者之间互助相爱,而不是谋怨仇。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组织一个“新联合”组织,开展“大同团结”的运动,从中国不断扩大到全世界,打破国界,组成“人类的联合”,此即是“世界大同”。这些论述拉近了孔子儒家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距离,对孔子儒家的继承和创新提供了新思路,也丰富了共产主义的内涵。
综而论之,李大钊的思想起步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哺育,承继了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和思维精髓,传统文化也成为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养料和素材。在接受了新式教育之后,知识结构和视野日渐开阔,除了努力学习吸收西方现代先进文化和思想观念外,他积极利用传统文化的语言和范畴去诠释和印证西方文化,目的是使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再生。如在对进化论的理解和认知上,他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变易观来论证进化论的合理性,并以此来阐释宇宙永恒变化发展的道路,他说:“大易之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氏之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知宇宙进化之理,由浑而之画,由一而之杂,乃为一定不变之律。”[1]420在阐述政治思想时也吸收和借鉴了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涵,对“民彝”一词的解释和运用就呈现出多方面、多层次的特点,既有总的解释,又有个别的、具体的解释;既有本义的诠训、考释,又有譬喻、引伸和发挥[5]。他大量引用了传统文化典籍来诠释“彝”的本意和引申义:《诗经·大雅·烝民》中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大雅·板章》中的“天之牖民,如壎如箎,如璋如圭,如取如携。携无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无自立辟”,《书·洪范》中的“彝伦攸叙”等,以此打通民彝与政治的关系。在表达统治者要代表民意见解的时候,他说:“子舆氏有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服人且不可,况治国乎?”[1]178而他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同样体现了其独特性思维。他批判传统文化不适应时代的内容,认为代表专制社会的儒家文化“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1]429,应该对之加以批判继承。他指出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融合时代的精神,综合东西文化的先进成果,走自己的道路。
从李大钊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李大钊秉持的是与时俱进的文化心态,他始终坚持文化应该面向世界,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国传统文化应在时代的挑战中批判继承和创新转化。他深受传统文化的熏染,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认知基础,却没有因循守旧,而是以开放的认识视野,以时代精神为前提,使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交融互生中,得到了阐扬和光大。这种与时俱进的心态贯穿李大钊的思想发展始终。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率先预见俄罗斯文明将引领世界新潮流,并在国内公开宣传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在中国知识界普遍没有对十月革命有所回应之时,李大钊最早开始研究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标志着他正式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实践。他认为新文明的产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强调“今”的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只有不断与时俱进,才会迎来民族的复兴与新生。李大钊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与历史根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