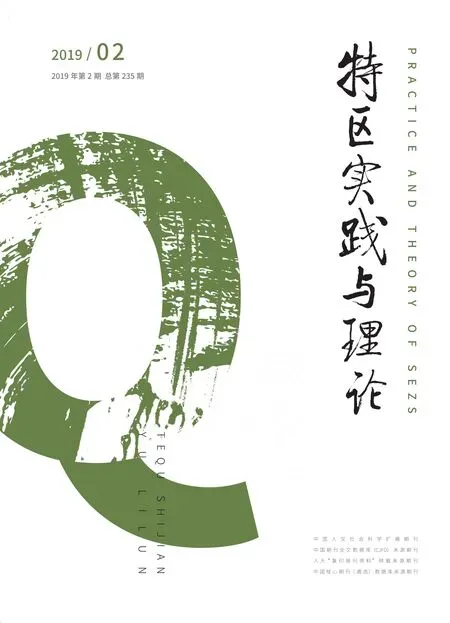城市书写视域
——论吴君深圳系列小说
刘洪霞
一、真实地理坐标下的空间切入
在吴君作品的标题或者作品的内容里,出现了大量深圳真实的地理坐标,例如“天鹅堡”“关外”“百花二路”“深圳西北角”“二区到六区”“十九英里”“樟木头”等等,不可枚举,这显然是作家有意为之。这些深圳人最为熟悉的地名,吴君旗帜鲜明地用真实的地理坐标指示她所虚构的文学空间,作家为何如此乐此不疲地书写?吴君的回答是:“虽然小说中的各种人物生活在深圳不同的地点,经历着各自的故事,但如果从整体上看他们,是有一个暗含的脉络把他们都牵连到了一起。我希望这些小说之间,人物之间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把深圳所有的地方全部涉及是我的一个理想。”①吴君:《舒晋瑜对话吴君:吴君的深圳叙事》,《人民文学》2017年第4期。这为深圳文学提供了一种书写新城市的方法论,那就是对城市空间角度的切入。对于城市书写来说,从时间角度的叙事可能更方便呈现城市的前世今生,人物也可以依据时间的线索来展开活动,文学史上的城市文学往往都采用这种视角。这些城市都有漫长的城市历史,在同一座城市里,可以书写几代人的轮回,犹如史诗般悲壮,例如,《悲惨世界》之于巴黎,《长恨歌》、《繁花》之于上海。对于一个有40年历史的城市,从时间角度的进入并不具备书写的优势,显然很难走进城市的肌理与内在。于是,空间角度的切入自然成为吴君书写深圳城市文学的最佳选择,把人物放在空间中,而不是把人物放在时间中,在空间中凸显人物的特点。吴君敏锐地发现,地理空间之下所隐藏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以及其中存在的社会问题。于是,她在深圳的地理空间中放置了虚构的人物,营造了虚拟的氛围。这些人物在特殊的场域里来去自如,活色生香,并且不同作品之间的人物如作家所愿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吴君的深圳系列小说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文学意义上的版图。
《关外》与《皇后大道》这两部作品中不约而同地都制造了二元对立的空间场景,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价值标准对照的二元结构模式,这种模式成为作家心中的一个稳定结构,根植在作品当中,成为作品的主轴线,也是作品人物展开活动的界限。空间不仅有物理属性,还具有经济属性、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从空间的角度可以更好地讨论作品中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或者文化问题。在她笔下,深圳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铁板一样的空间。完整的空间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化都市,但是却被区分成了各种层次的小空间,这些小空间既交叉,又独立。关键的是,不同空间之间的僭越似乎是个很有难度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问题。所以说,她所标识的空间,是代表着阶级、贫富之间的巨大差别。
吴君对现代的公共空间与狭小的私人空间的比较,不仅是引出了阶级的概念,贫富巨大差异的问题,更进一步地讨论了城市空间与社会公正的深刻问题。真实地理坐标下的空间虚构,呈现出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问题,成为吴君的标识性写作特点。
二、以乡村为他者的城市书写
吴君的深圳系列小说中,除了对深圳这座城市的书写以外,始终有着另一隐含的他者的存在,那就是乡村。它自始至终以陪衬的方式出现在深圳这座城市的书写当中,挥之不去。这里的城市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剪不断,理还乱。邓一光也是深圳城市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但是他的深圳系列小说中,没有任何一部作品涉及乡村,都是很完整意义的城市书写。因此可以说,吴君的城市书写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是因为有乡村的存在,两者在此又构成了二元对立结构模式。在吴君的城市文学的书写中,乡村的描写大量地充斥在她的作品里。她写作的背景,不仅仅是深圳,还有与之相关的乡村。她的作品,如果说城市是书写的近景,那么,乡村就是书写的远景,城市与乡村共同成为书写的大背景。以乡村为他者的城市书写,是吴君的深圳系列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城市与乡村,同样也是地理空间。但不同的是,这两大地理空间已经不是城市内部的地理空间那么单一,它所带出的问题更为复杂和多元。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的主流是“乡土文学”,而不是城市文学。20世纪30年代与80年代的城市化进程都不如90年代的城市化的广度和深度。吴君以乡村为他者的城市书写,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从乡村文学向城市文学的过渡,即以城市来书写乡村,城市对乡村的影响。“她书写的深圳,不是一个现代的、国际的、新兴的大都市,而是一个欲望的对象,一个梦想的载体,一个精神的病源。吴君笔下那些以深圳为背景的人物,几乎全部身处底层,且都有残缺的、病态的心灵。”①孙春旻:《专注于描写底层心灵病相——论吴君小说中的“深圳叙事”》,《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为什么吴君笔下来到深圳寻梦的人物是这样的状态,造成他们病态的心灵的根源是什么?是城市的现代性的无情吗?那么乡村呢?乡村难道就是一片净土吗?城市与乡村,它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塑造了深圳寻梦人的灵魂?雷蒙·威廉斯认为,“现在乡村的一般意象是一个有关过去的意象,而城市的一般意象是有关一个未来的形象,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果我们将这些形象孤立来看,就会发现一个未被定义的现在。关于乡村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以往的方式、人性的方式和自然的方式。关于城市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进步、现代化和发展。现在被体验为一种张力,在此张力中,我们用乡村和城市的对比来证实本能冲动之间的一种无法解释的分裂和冲突,我们或许最好按照这种分裂和冲突的实际情况来面对它。”②[英] 雷蒙·威廉斯:《乡村和城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01页。
除了“深圳叙事”以外,吴君的深圳系列小说也被批评家们命名为“底层叙事”。孟繁华说,“吴君接续了现代文学史上左翼的文学传统,但她发展了这个传统。她的底层不仅是书写的对象,同时也是批判的对象”。①孟繁华:《在都市文明的崛起中寻找皈依之路》,《文艺报》2013年3月23日。吴君所书写的城市底层,他们大都来自于农村,农民进城,给生命带来了新的可能。但同时,也是一种不确定性。在吴君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人们,成了“陷落的底层”。
《出租屋》的写法更为独特,吴君完全把人物活动的场景挪回了乡村,是在乡村中书写城市。留守儿童燕燕只知道爸爸去了深圳,而妈妈则刚从深圳回来,带回了深圳的生活方式。燕燕一边盼望着去深圳找爸爸,一边目睹着妈妈如何在乡村过起了深圳的生活,那就是把家里一间破烂的房子出租给了外人。这件事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村里从来没有发生过房屋可以出租的事情。在这个出租屋里,上演着从城市到乡村的悲欢喜乐。燕燕的妈妈就是在深圳待过的人,她对这座城市又爱又恨,希望有一天身体康复后能够回去,但却没有能力回去了。但是,她真正回来了吗?她已经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故乡,她的心停留在了那座城市。确切地说,是城市改变了她的思维,她的心永远漂在了出租屋里,这就是农民工进城的文化人格的嬗变。
以乡村为陪衬来书写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书写城市的同时观照着乡村,这在城市文学的写作中是非常少见的一种写法。对比的视角增添了作品的丰满性和人物的生动性。吴君不是在真空状态下从事写作的,她20世纪90年代初来到深圳,看到的是这座城市阵痛式的发展与成长,她深刻地体会到,“深圳不仅收取了每个过客最激荡的青春时光,也瓦解甚至掏空了中国农村,对乡村中国的结构改变起了一个最为重要的作用。它的特殊性,以及对当代中国农村文化的影响,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代替”。②吴君:《舒晋瑜对话吴君:吴君的深圳叙事》,《人民文学》2017年第4期。吴君所进行的深圳书写是异常清醒的,她看到了这座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她与她的作品同属于那个时代,吴君的作品是在“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时代大背景之下的产物,是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嘹亮的口号声中应运而生的作品。她的作品,是这个时代赋予的。所以,最珍贵之处,是她的作品有历史的价值。她犹如纪录片一样写实般地记录了时代的面孔、精神的样态,记录了那个时代下的那座城市。这是一种贴着地面的飞行,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近距离的摹写,稍不留心,就可能走向流俗,走向那种只能感受生活的表征层面中的嘈杂,大众化地运用语言,只是简单地讲述一个故事。如何去书写一座城市,吴君的文本提供了这种可能,她发明了足够有特殊的文体与语言,塑造了这座城,它给文学史提供了一个认识这座城市的视角。
三、批判性与生产性的精神探求
如果说,空间角度切入的写作手法以及以乡村为他者的城市书写还只是涉及了吴君深圳系列小说的表层的话,那么,真正批判性与生产性的精神探求才是吴君书写城市的内里与本质。如何书写城市?杨庆祥说:“……沾沾自喜式的胜利者的口吻或者类似于‘农家少年出走都市’的自卑者都显得矫情且平庸,……我特别警惕一种以‘温暖’、‘疗愈’为其美学风格的伪城市写作来弱化和软化我们有力量的、具有批判性和生产性的真正的新城市文学写作。”③杨庆祥:《世纪的“野兽”——由邓一光兼及一种城市文学》,《文学评论》2015年5月。显然吴君的城市书写不是这种疗愈型和温暖型的写作,她对自己笔下的城市爱恨交织,所以她批判性与生产性的表达,仿佛是对灵魂的叩问,非常有力量,掷地有声,有时候甚至觉得她的批判性过于猛烈而显得残酷。
《岗厦》中对于石雨春的用笔是尖刻的,读者几乎能听到石雨春颤抖灵魂的微弱哭泣声和向命运的哀求声,但是作家还是让他扭曲地活着,这种批判性的力度异常强大,同时也是非常残酷的。《樟木头》中的陈娟娟的悲剧性是制度带给予她的。她本是一个优秀的英语系的大学毕业生,她忍辱负重,心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获得深圳户口,身份被确定的重要性超越了一切,包括爱情与尊严。当她终于通过不堪的婚姻获得了户口的时候,更具反讽的是,在她获得深圳户口的21天前,深圳出台了新的政策,大学毕业生可以自行申请户口,而无需任何附加条件。这真是一个让人欲哭无泪的莫泊桑的《项链》的故事。
吴君是一位非常自觉的作家,在她解构的同时,她更能够积极地建构。也就是说,在对城市批判性的同时,更有新生的生产性的建议产生。所以说,她不是一位彻底悲观的作家,她更是一位深情的作家,当她在自己绘制的深圳文学地图上,看着一个个自己创作的人物,被城市的熔炉炙烤的时候,除了哀叹,她并没有束手无策,她不仅仅为自己的笔下的人物悲天悯人。同时,她更愿意出具一剂清醒的良方。
《皇后大道》的批判性可谓深刻,但同时也有建设性。妙龄少女阿慧不过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嫁到香港,到皇后大道去逛一逛,对于一个有梦想的女孩来说,本来也无可非议,但是作者却为她配上一个有残疾的丈夫。不仅如此,她还要以瘦弱的肩膀挑起一家人的重担,因为婚姻而进入了愁苦不堪的生活。但是批判到这里,并不是就结束了,小说有一个饱含寓意的结尾。陈水英的女儿对于妈妈所说的皇后大道,根本不屑,通过后一代人的表现说明,两代人对香港的看法已经完全不同了,随着城市不停的发展和进步,曾经受到伤害的一代人,他们的后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也因此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的未来。
批判性是有力量的,可以鞭挞,可以棒喝。但是,生产性与建设性则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它具备可执行、可操作的可能性。《华强北》的结尾,作家安排了住在华强北商业区、没文化的陈水一家,搬去科技园了,因为那里的文化氛围好,是大学、科研单位的汇聚之地。更有趣的是,有人竟然在保利剧院见到了本来完全不懂艺术的陈水老婆,并且从他们家的窗口,还传出了让人不是很懂的音乐,这音乐在昏黄的灯光下,街上的人和物,也变得温柔了。在吴君一贯的尖刻、批判、冷峻的风格下,突然出现了温暖的色调,这色调的寓意让人报以会意的微笑。吴君的批判,不是完全的一个黑洞,让人找不到出口。她总是不经意地在出口处放置些许的微光,让人寻着这微光,走向豁然开朗。她所建构的城市,已经内在于她的内心,让她爱恨交织,欲罢不能,她只有不停地叩问着这座城市的灵魂,让书写成为可能。
结语
吴君如何书写了深圳这座城市?在真实地理坐标下虚构了文学空间,从这一角度切入,却也把握住了那个时代的脉搏;以乡村作为背景,烘托出城市这一主角,浓墨重彩地渲染,勾连出城市与乡村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她采用什么方式,呈现出这座城市的各个角度,“横看成岭侧成峰”,最后都落脚于城市内在精神气质的叩问,因此而进入了问题的实质。
文学可以荡涤心灵,批判性与生产性的的精神探求,是文学的应有之义。同时,文学安慰着人的心灵,安慰着这座城市中每一颗孤独的心灵。在深圳这座商业化极高的城市,如果没有文学,没有电影,没有音乐,那么,城市就变成了孤岛,孤岛上的人们不知道怎样生活下去。在吴君的深圳系列小说中,很多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找到了共鸣,获得了心理认同。一个城市的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正是无数吴君一样的作家、艺术家一点一滴建构起来的,逐渐强大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