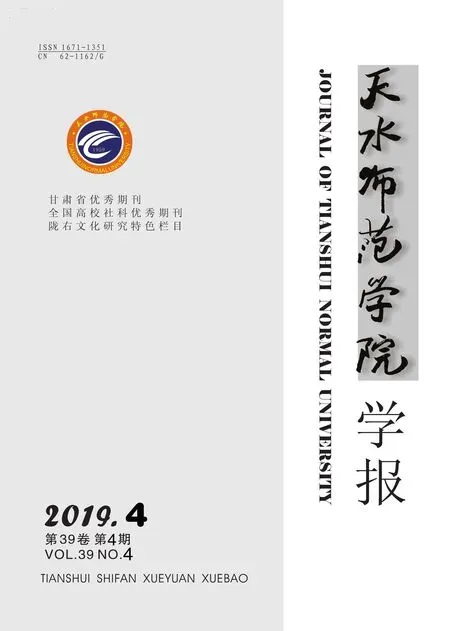近世文人,私所敬慕者,一人而已
——苏轼对陆贽的尊崇与超越
庆振轩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30)
检阅苏轼现存文集,其所著史论、史评多达百余篇,仅就苏轼历史人物史论篇目,一些论者即惊叹苏轼“这类文章数量之多,在中国文学史上仅此一人而已”。[1]然而现通行的文学史,如游国恩、王起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袁行霈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章培恒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孙望、常国武等主编《宋代文学史》,或限于篇幅,或囿于体例,极少给予一定篇幅加以专门论述。自20 世纪90 年代渐多专文探讨,诸如陈晓芬《苏轼史论中的人格思考》、[2]周国林《评苏轼的人物史论》、[1]何玉兰《苏轼史论之特色》、[3]林峥《苏轼史论文的思想与艺术特征》[4]等等,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性诸方面对于苏轼史论进行了探讨。但梳理相关研究论著,我们发现,尽管苏轼历史人物论的研究日益为人重视,但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譬如苏轼史论散文与苏轼咏史怀古诗的综合比较研究、苏轼未列专文评议但对苏轼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研究等。鉴于以上原因,本文拟对苏轼最为尊崇的中唐政论家、政治家陆贽对于苏轼的影响加以探讨,不足之处,望方家指正。
一、东坡尊崇陆贽,源于家学师承而服膺终身
研究苏轼,何以我们特别关注苏轼对于陆贽的接受和尊崇?因为苏轼特别强调“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独陆宣公一人”。[5]6493-6494甚且言“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以还,一人而已。”[5]3566
何以在苏轼史论中未有专论、专评的唐代名相陆贽,竟使苏轼如此尊崇,这激起我们进一步探求的强烈兴趣。据有关史料记载,陆贽乃中唐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政论家。《旧唐书》《新唐书》皆有传。一般介绍略谓:
陆贽,唐苏州嘉兴人。字敬舆。大历六年进士。德宗召为翰林学士;官至中书侍郎、门下平章事。卒谥宣公。所作奏议数十篇。有《陆宣公翰苑集》。指陈时病,论辩明澈。为后世所重。
苏轼自言于近世文人中,独敬慕陆贽一人,但在其浩繁著述之中,论及陆贽之处并不多,以时间先后录载有关篇目于下:
《转对条上三事状》,[5]3195-3199元祐三年(1088)五月一日作于汴京;《六一居士集叙》,[5]977-979元祐三年十二月作于汴京;《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5]3566元祐八年(1093)五月七日作于汴京;《答虔倅俞括一首》,[5]6493-6494绍圣元年(1094)八月作于虔州;《与王庠书》,[5]5306-5307绍圣三年(1096)七月作于惠州;《与刘壮舆六首》(之四),[5]5930建中靖国元年(1101)四月作于南康军。
以上苏轼言及陆贽的六篇文章给我们透露了一个明显的信息,这些文章均作于苏轼人生之后期,参考乃父苏洵、弟弟苏辙,门人黄庭坚及宋人相关评论,可以让我们得出以下推论:
苏轼对于陆贽尊崇服膺终身,与其家学和早年教育密切相关。相关资料可以为证者有三。其一,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叙其兄一生文风之变化曰:
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而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6]71-72
细味文义,则因苏氏家学,东坡早年已谙熟并喜好贾谊、陆贽之书。
言其喜好陆贽之书源于家学,乃父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亦可为证。苏洵在文中极力推崇欧阳修的文章,自以为“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7]327将欧阳修之文与孟子、韩愈之文并列,“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此外,“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得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文,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千年文脉,苏洵所列,欧阳子之外,亦仅孟子、韩愈、李翱、陆贽四人而已。
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作于嘉祐元年(1056),正是苏轼为学有成,随父入京求取功名之时。与之相应的是,元祐三年(1088)十二月在汴京苏轼撰写《六一居士集叙》,亦曰:
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其子棐,乃次而论之曰:“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5]977
两相对照,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苏轼父子尊崇欧阳修的文坛地位、诗文成就,同样于千年道统、文脉仅仅列四人比衬,苏洵所列为孟子、韩愈、李翱、陆贽;苏轼所列为韩愈、陆贽、司马迁、李白,重合者为韩愈、陆贽二人;而于韩愈,老苏所论乃“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灏流转”的文学成就;大苏所论乃韩、欧相承之“论大道似韩愈”的道统承传。唯独对于陆贽,苏氏父子着眼点颇为一致,苏洵谓“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得当,有执事之实”,苏轼谓欧阳修“论事似陆贽”,都聚焦在陆贽之文指陈时病,论辩明澈,“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切近的当的个性特色。所以东坡之尊崇陆贽,家学之外,与其师承欧阳公颇有关联。
讨论苏轼尊崇陆贽乃其家学传统,其《与王庠书》亦可为证,其文曰:
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老病且死,独欲以此教子弟,岂意姻亲中,乃有王郎乎?三复来贶,喜抃不已。[5]5306
要而言之,由苏轼“少好贾谊、陆贽之书”,到嘉祐元年苏洵赞欧阳修之文则言“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得当,有执事之实”,再到元祐三年苏轼《六一居士集叙》称颂欧阳修“论事似陆贽”,直到晚年南迁惠州之《与王庠书》中欲以“贾谊、陆贽之学”“教子弟”的表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轼之接受、尊崇陆贽与其早期教育之家学师承有密切关联且服膺终身。
且寻绎东坡尊崇陆贽的相关文字,我们还发现,东坡喜欢将陆贽与张良、贾谊、诸葛孔明并称,然而陆贽“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张良未有诗文集流传,自不待言;即如贾谊,东坡曾明确指出其“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之缺失;[5]358在《转对条上三事状》中,东坡希望“陛下常以诸葛亮、陆贽之言为法,则天下幸甚”,但在《诸葛亮论》中他也批评孔明之失在于以“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5]378而陆贽则德才兼具,我们看不到东坡批评陆贽的任何文字,由此可见陆贽在东坡心目中的地位。
那么,为什么在东坡心目中陆贽的地位如此重要?我们认为因其家学师承渊源与现实需要,苏轼终身尊崇陆贽,其核心在于实用之学。苏轼对于陆贽的接收、尊崇之核心点在于陆贽“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无当世儒者“多空文而少实用”之病。
东坡一生尊奉实用之学,强调学以致用,其观念源于家学、家法师承而与时迁变。比较对读苏轼与苏洵之作,仅从现存文字即可看到较为明显的“家学”痕迹。苏洵《史论上》劈头一句即曰“史何为而作乎”,[7]229苏轼早期的《思治论》首句即曰:“方今天下何病哉!”[5]389复检苏洵《嘉祐集》,强调针对现实,积极用世,学贵济世的论说随处可见。《权书》《衡论》乃苏洵得意之作,其《权书叙》曰: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使仁义之兵无术自胜也,则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战,“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又何用也?
《权书》,兵书也,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为孙武之徒也。夫孙氏之言兵,为常言也。而我以此书为不得已而言之之书也。故仁义不得已,而后吾《权书》用焉。然则权者,为仁义之穷而作也。[7]26
其《衡论叙》亦曰:
事有可以尽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尽者。尽以告人,其难在告,告人以其端,其难在用。……始吾作《权书》,以为其用可以至于无穷,而亦可以至于无用,于是又作《衡论》十篇。呜呼!从吾说而不见其成,乃今可以罪我焉耳。[7]79
苏洵著述《权书》《衡论》《洪范论》的目的在于“施之于今”,行匡济之志,他在《上韩枢密书》中表述得十分明白:
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7]301
苏氏家学,东坡自幼耳濡目染,自然根植于心。其《凫绎先生诗集叙》曰:
昔吾先君适京师,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以鲁人凫绎先生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曰:“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校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
其后二十余年,先君既没,而其言存。士之为文者,莫不超然出于形器之表,微言高论,既已鄙陋汉、唐,而其反复论难,正言不讳,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贵也。轼是以悲于孔子之言而怀先君之遗训,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复,乃录而藏之。[5]968
“先君既没,而其言存。”东坡求凫绎先生之文“录而藏之”,既藏其文字以醒世,更藏其“有为而作”之创作精神于心,并终身行之。
探讨实用之学为苏氏家法,《颍滨语录》中曾有一段关于苏轼入仕之初向伯父苏涣请教为政之方的记载,可以为证:
颍滨尝语陈天倪云:“亡兄子瞻及第调官,见先伯父,问所以为政之方。伯父曰:‘如汝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子瞻曰:‘文章固某所能,然初未尝学为政也,奈何?’伯父曰:‘汝在场屋,得一论题时,即有处置,方敢下笔,此文遂佳。为政亦然。有事入来,见得未破,不要下手。俟了了而后行,无有错也。’至今以此言为家法。”[8]15
苏涣这一段话作为“家法”,简明扼要地讲明了读书写作与仕宦实用之关系,苏轼、苏辙兄弟终身奉为圭臬。苏辙作于崇宁五年(1106)的《送元老西归》诗曰:“昼锦西归及早秋,十年太学为亲留。……家有吏师遗躅在,当令耆旧识风流。”自注:伯父仕宦四十年,当时号为吏师。[9]404
二、学以致用,学贵实用,苏轼对于陆贽的尊崇体现在仕宦体用和施政惠民的不同方面
翻检东坡诗文中论及陆贽的文字,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5]3566-3567鉴于此文的独特性,在此不惮辞费,稍加分析。
札子开首直陈上札子的缘由:“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圣明天纵,学问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为。”而后以其擅长的以医论事之能,委婉进言:“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敷陈校正陆贽奏议上进之忠心,层层铺设而后进入札子的中心内容:一是对于陆贽的高度评价,“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以还,一人而已”。二是陆贽的忠言谠论远见卓识及不能尽为世用,“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最后落脚到陆贽奏议有益“圣学”足资治道的现实意义,“臣等每退自西阁,即私相告言,以陛下圣明,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覆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
此文元祐八年(1093)五月七日作于开封。前人曾谓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乃“长公最得意识见,亦最得意奏条”,因其“借贽之所苦口于德宗者,感动主上”。[6]978而我们对于此文的特别重视,是因为苏轼的“最得意奏条”蕴含的对于陆贽的高度评价,诸如“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以还,一人而已”,论者多耳熟能详。而苏轼对于陆贽整体认识和现实意义的评说,要综合东坡前后诸文和《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对照阅读会有更为清晰的认知。这些文章应包括《谢除两职守礼部尚书表》之二、[5]2759《申省读汉唐正史状》、[5]3586《朝辞赴定州论事状》、[5]3588《答虔倅俞括》[5]6493一首和《中山松醪赋》。[5]57
综合分析,不难发现,在元祐末期,由于苏轼对于现实的深刻认识凸显了陆贽在其内心的地位。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撰《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三个月之后,东坡又有《申省读汉唐正史状》,同样出于以史为鉴的深心,苏轼诸“讲读官同将汉、唐正史内可以进读事迹钞节成篇,遇读日进呈敷演,庶裨圣治”。而在此前,苏轼诸人已将陆贽奏议校正单独上进,可见陆贽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将东坡相关文章比照研味,可以见出东坡推崇陆贽,重在其“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的实用之学。其《谢除两职守礼部尚书表》之二坦陈:“始臣之学也,以适用为本,而耻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为心,而惭尸禄。乃者屡请治郡,兼乞守边。欲及残年,少施实效。而有志莫遂,负愧何言。”“今乃以文字为官常,语言为职业。下无所见其能否,上无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靦面目。故于拜恩之日,少陈有益之言。”期望“一言可以兴邦”,“一正君而天下定”。
以东坡的丰富人生经历和政治敏感,所谓“八典方州,三入翰林,两忝侍读”,他对于元祐末期朝政之积弊,特别是亲见哲宗已由一孩童成长为有所欲为的青年,长期处于垂帘听政下的压抑、隐忍以及内心的怨望,已然有所察觉。所以针对当下的政治生态和哲宗内心隐藏的“病象”,适时提出警示,其在《谢除两职守礼部尚书表》中说自己和各位讲读之官,“八年之间,指陈文理,何啻千万,虽所论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诚,六曰明。慈者,谓好生恶杀,不喜兵刑。俭者,谓约己省费,不伤民财。勤者,谓躬亲庶政,不迩声色。慎者,谓畏天法祖,不轻人言。诚者,谓推心待下,不用智数。明者,谓专信君子,不杂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陈迹,老生之常谈。言无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饮膳,则为谷米羊豕,虽非异味,而有益于人;璧之药石,则为耆术参苓,虽无近效,而有益于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饮膳,如服药石,则天人自应,福禄难量,而臣等所学先王之道,亦不为无补于世”。
如果把这一大段文字和《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对照,札子言陆贽“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可以推知,苏轼在《谢除两职守礼部尚书表》中特指的“慈”“俭”“勤”“慎”“诚”“明”之“六事”与《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中所指德宗“苛刻”“猜疑”“好兵”“好财”诸过错,均有所指而言。正如曾枣庄先生所说:
开药方就证明有病,开的什么药方就证明有什么病。苏轼要求哲宗慈、俭、勤、慎、诚、明,可见他感到已经成年的哲宗存在不慈、不俭、不勤、不慎、不诚、不明的问题。……他要即将亲政的哲宗,以德宗的“苛刻”“猜疑”“好用兵”“好聚财”为戒。……就可看出苏轼这时对哲宗的政治倾向已有预感。他这些话都是有感而发,并非泛泛而谈。[10]194
让我们颇感兴趣的是,在这一系列文章中,苏轼充分运用了他擅长的以医论政、以医论事、以医明理的论辩方法,显示了臣下之诚、论辩之智。苏轼在《谢除两职守礼部尚书表》中论列“慈、俭、勤、慎、诚、明”要义后,续言:
此六者,皆先王之陈迹,老生之常谈。言无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饮膳,则为谷米羊豕,虽非异味,而有益于人;璧之药石,则为耆术参苓,虽无近效,而有益于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饮膳,如服药石,则天人自应,福禄难量,而臣等所学先王之道,亦不为无补于世。[11]409
其在《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言及上进陆贽奏议之初衷,坦言:
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
其在《朝辞赴定州奏事状》中“冒死进言”:
臣又闻为政如用药方,今天下虽未大治,实无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虽未能尽除小疾,然贤于误服恶药、觊万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祸者远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辄进此说,敢望陛下深信古语,且守中医安稳万全之策,勿为恶药所误,实社稷宗庙之利,天下幸甚。臣不胜忘身忧国之心,冒死进言。[5]3588
在元祐末期的苏轼看来,斯时之朝政是病态的,哲宗皇上是有“心疾”的,而陆贽等前人治世之论不啻苦口良药。东坡诸文皆精心之作,语意轩豁,以医论事,见其措意之深。其所用心,在于感动哲宗。然而当时政局,暗流涌动,哲宗心蓄异志,东坡业已感知。所以系列文章推诚进言之外,东坡心怀忧虑,在《谢除两职守礼部尚书表》中他已预见了他最不愿见到的结果:
若陛下听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闻春禽之声,秋虫之鸣,过耳而已。则臣等虽三尺之喙,日诵五车之书,反不如医卜执技之流,簿书奔走之吏,其为尸素,死有余诛。伏望陛下一览臣言,少留圣意,天下幸甚。
这种担心,苏轼在《答虔倅俞括一首》[5]6493中借医者之语以寓托:
然去岁在都下见一医工,颇艺而穷,慨然谓仆曰:“人所以服药,端为病耳,若欲以适口,则莫如刍豢,何以药为?今孙氏、刘氏皆以药显,孙氏期于治病,不择甘苦,而刘氏专务适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刘氏富倍孙氏,此何理也?”
东坡自谓“始吾南迁,过虔州,与通守承议郎俞君括游”。[5]1231去岁云云,则指元祐八年在京城之时。信中言及“进宣公奏议”,虽文为俞括而发,“使君斯文,恐未必售于世。然售不售,岂吾侪所当挂口哉,聊以发一笑耳。进宣公奏议,有一表,辄录呈,不须示人也。”可以明显看出东坡乃有所激而言。
因是之故,苏轼在国事将变的风雨如磐之际,思考翻云覆雨的政坛风云中的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
始臣之学也,以适用为本,而耻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为心,而惭尸禄。乃者屡请治郡,兼乞守边。欲及残年,少施实效。而有志莫遂,负愧何言。今乃以文字为官常,语言为职业。下无所见其能否,上无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靦面目。故于拜恩之日,少陈有益之言。[5]2759
不幸的是,东坡的一片赤诚对于哲宗而言的确“如闻春禽之声,秋虫之鸣,过耳而已。”而苏轼绍圣被贬,亦在意料之中:
则臣等虽三尺之喙,日诵五车之书,反不如医卜执技之流,簿书奔走之吏,其为尸素,死有余诛。[5]2759
再联系东坡元祐八年(1093)十二月作于定州的《中山松醪赋》,可以见出东坡胸中现实与理想天壤悬隔的痛楚,大材小用甚或学无所用的悲哀。
《苏轼全集校注》62页“集评”录《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二《中山松醪赋》郎晔注引晁补之的一段话,颇有助于我们了解此赋之内涵:
《松醪赋》者,苏公之所作也。公帅定武,饬厨传,断松节以为酒,云:饮之愈风扶衰。松,大厦材也。摧而为薪,则与蓬蒿何异?今虽残,犹可收功于药饵。则世之用才者,虽斫而小之,为可惜矣;倘因其能,转败而为功,犹无不可也。
“大材小用古所叹”,将东坡《中山松醪赋》中“岂千岁之妙质,而死斤斧于鸿毛。效区区之寸明,曾何异于束蒿。烂文章之纠缠,惊节解而流膏。嗟构厦其已远,尚药石之可曹。收薄用于桑榆,制中山之松醪”词句与晁补之所记对照,不难看出东坡在时势迁变中的悲哀,以及在悲思中的一线希冀。
在元祐末期这个时间聚焦点上,我们通过东坡一系列代表作,看到东坡对陆贽的高度评价,看到东坡崇仰陆贽的精神内核是实用之学,看到东坡敏感地由千尺栋梁摧为蓬蒿、化为松醪的悲哀和无奈,看到东坡在时代风云变化之际对自己实用之志破灭的探究,看到东坡对“陆贽不幸”、一己遭逢不幸的深思。然而这一切都和东坡崇尚陆贽忠贞报国,实干兴邦,反对空谈误国的政治理念密切相关。
推而论之,东坡在元祐时期竭忠尽智,杀身图报,在国事将变、潜流涌动之时,依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举措也和陆贽甚为相似。据史载:
德宗在东宫时,素知贽名,乃召为翰林学士,转祠部员外郎。贽性忠荩,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报,故政或有缺,巨细必陈,由是顾待益厚。[12]3791
陆贽由于感德宗重知,思以图报;东坡在元祐朝亦备极恩宠,对于神宗、高太后的眷顾,多次在谢表中表示尽忠报国,虽杀身不顾的勇决。对于君臣之义,东坡所秉持的君上待臣下非常礼,臣下应以特殊之行报之的理念,正如陆贽倾心德宗一脉相承。所以东坡在元祐时期,“文章韩杜无遗恨,草诏陆贽倾诸公。”[6]93对于朝廷要事,知无不言,正如其尊崇的陆贽一样“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至于东坡在地方任上事功建树,在朝廷之献策建言,史皆有载,此不赘言。
需要补充的是,综观苏轼对于陆贽的接受与崇仰,不仅在苏轼政治人格的塑造中,其终身崇尚实用之学;在诗文创作上,致力于“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反对当下儒者“多空文而少实用”,且在日常生活的体用上,也时时可见陆贽的影响。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作于北归途中的《与刘壮舆六首之四》写道:
某启。辱手教,仍以茶簟为贶,契义之重,理无可辞。但北归以来,故人所饷皆辞之。敬受茶一袋以拜意。此陆宣公故事,想不讶也。仍寝来命,幸甚。[5]622
俭以养德,而陆贽之俭德载誉史册。《旧唐书·陆贽传》载:
陆贽……特立不群,颇勤儒学。年十八登进士第,以博学宏词登科,授华州郑县尉。罢秩,东归省母,路由寿州,刺史张镒有时名,贽往谒之。镒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见与语。遂大称赏,请结忘年之契。及辞,遗贽钱百万,曰:“愿备太夫人一日之膳。”贽不纳,唯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12]3791
由陆贽谢却张镒钱百万,唯受新茶一串,到东坡北归以来,“故人所饷皆辞之,敬受茶一袋以拜意”,可以见到,东坡对于陆贽的接受从为政到为人,一切自然而然。东坡风范的最终形成,融合了丰富的精神文化因子,陆贽的影响值得特别关注。也正因如此,东坡在晚年,有意识地要传承陆贽之学。他在《答虔倅俞括一首》中说:
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独陆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议善本,顷侍讲读,尝缮写进御,区区之忠,自谓庶几于孟轲之敬王,且欲推此学于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挟此药,以待世之病者,岂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5]6493
在《与王庠书》中又说:
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老病且死,独欲以此教子弟,岂意姻亲中,乃有王郎乎?三复来贶,喜抃不已。[5]5306
东坡一生,少好贾谊、陆贽之学,入仕之后在地方任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经世济民;身在朝堂,元祐章奏近陆贽。身遭贬放,依然不忘传陆贽之学于后昆。其一生遭际,其一生志向,在社稷,在生民,故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三十四《乞校正奏议札子》引述东坡《答虔倅俞括书》之后,特别强调“此仁人君子至情也”![5]5930
三、尊崇陆贽,效仿陆贽,又超越陆贽,达成东坡风范的完美体现
综上所述,东坡在为政、为文、为人诸多方面接受和崇仰陆贽自不待言,但自苏公之后,论者从不同方面着眼,或言苏公学陆贽而有得,或谓苏公超越陆贽自饶丰采。个人持苏公超越之说,在此试加阐发。
宋人认为苏公学陆贽且为政为人似陆贽者有《陵阳先生集》卷十七《跋三苏帖》,其说谓:
苏氏一翁二季,词旨翰墨,具见于三纸间。敛衽伏读,因有感焉。……然东坡不以患难流落为戚,方且施药葬枯骨,造桥以济病涉,此与陆敬舆在南滨集名方同一意,故颍滨有安遐陋抚恤病苦之语。[13]1255
持此说者还有周必大,其《题苏季真家所藏东坡墨迹》说:
陆宣公为忠州别驾,避谤不著书,又以地多瘴疠,抄集验方五十卷,寓爱人利物之心。文忠苏公,手书药法,亦在琼州别驾时,其用意一也。淳熙戊申三月十七日。[6]552
“苏子瞻氏少而能文,以贾谊、陆贽自命。”[6]1022就具体史实所言,就事论事,应无可议。前人有关论述中,个人喜欢黄震、刘熙载通达之论。黄震认为古今哲人生不同时,前后辉映,各具风采:
(苏轼)杭州上两执政书,扬州上吕相书,论灾伤民事,惋切动人。愚谓古今善言天下事,如贾谊之宏阔,陆宣公之的切,苏子瞻之畅达,皆问世人豪,天佑人之国家而笃生者也。[6]774
刘熙载之说更为通透,他认为苏公之学遍借金针厚积薄发,自成一体:
东坡亦孟子,亦贾长沙、陆敬舆,亦庄子,亦秦、仪。心目窒碍者,可资其博达以自广,而不必概以纯诣律之。[6]1526
更多的论者认为东坡学习效仿陆贽,但超越了陆贽。刘大櫆《古文辞类纂》卷十八就东坡《上皇帝书》加以评说:
虽自宣公奏议来,而笔力雄伟,抒词高朗,宣公不及也。宣公只敷陈,条达明白,足动人主之听,故欧、苏咸效其体。[6]1244
茅坤则将东坡之文与李太白诗、韩信用兵相提并论,认为各达极致:
予少谓苏子瞻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韩信之于兵,天各纵之以神仙轶世之才,而非世间之问学所及者。及详览其所上神宗皇帝及代张方平、滕甫谏兵事等书,又如论徐州、京东盗贼事宜,并西羌鬼章等札子,要之,于汉贾谊、唐陆贽,不知其为如何者。……入哲宗朝,召为两制,及谪岭海以后,殆古之旷达游方之外者已。然其以忠获罪,卒不能安于朝廷之上,岂其才之罪哉![6]976
宋人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谪居中勇于为义》条力倡东坡谪居惠州期间“勇于为义”,超迈绝伦:
陆宣公谪忠州,杜门谢客,惟集药方,盖出而与人交,动作言语之际皆足以招谤,故公谨之。后人得罪迁徙者多以此为法,至东坡则不然,其在惠州也,程正辅为广中提刑,东坡与之中外,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诸军缺营房,散居市井,窘急作过。坡欲令作营屋三百间,又荐都监王约、指使蓝生同干惠州,纳秋米六万三千馀石,漕符乃令五万以上折纳见钱,坡以为岭南钱荒,乞令人户纳钱与米,并从其便。博罗大火,坡以为林令在式假,不当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专牒令,修复公宇仓库,仍约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桥,坡以为吏孱而胥横,必四六分了钱造成一座河楼桥,乞选一健干吏来了此事。又与广帅王敏仲书,荐道士邓守安,令引蒲涧水入城,免一城人饮咸苦水、春夏疾疫之患。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6]671
客观地讲,在各自生活的特定时代,贾谊、陆贽、东坡作为政论家,均为一代之人豪,不必强分高下;东坡在宋,自然会汲取前人政治智慧,济世利民。他少好贾谊、陆贽之书,终身服膺崇仰陆贽,史料所示,自不待言。特别是陆贽、东坡在政坛殊途同归,道大难容,均被贬逐,最终壮志未酬,赍志而殁。因此,陆贽、东坡当年的论政、论军、论学、论事之文,多关切时势,有感而发,有为而发,-达到各自时代的高度。后世论者从不同角度的讨论,也给我们以启示。在这里,我们仅就陆贽、东坡蒐集验方以寓医国之志和被贬之后的为人处世加以比较,以展示东坡效仿陆贽,又不同于陆贽,超越陆贽的独特的东坡风范。
首先就陆贽、东坡在医学上的建树而言,东坡超过了陆贽。据《新唐书》载,陆贽“既放荒远,常阖户,人不识其面。又避谤不著书,地苦瘴疠,只为《今古集验方》五十篇示乡人云”。[14]4932《旧唐书》所载略同。后世论者往往据此以为“陆宣公为忠州别驾,避谤不著书,又以地多瘴疠,抄集验方五十卷,寓爱人利物之心。文忠苏公,手书药法,亦在琼州别驾时,其用意一也”。[6]552
揆诸实际,东坡之爱好医学,虽和陆贽一样“寓爱人利物之心”,但又有极大不同。首先是由于宋代开国之后,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医学,仅《宋大诏令集》所载有宋历代皇帝有关医学的诏书就有百余篇,再加上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范仲淹“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人生宏大志愿的感召,有宋一代文人尚医成为风尚。正是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东坡少年时即阅看接触医书。其《志林·艾人着灸法》载:
端午,日未出,于艾中以意求似其人者,辄撷之以灸,殊有效。幼时见一书中云耳,忘其为何书也。[11]255
由于在医学方面的造诣精深,东坡入仕之后,往往以医论政、以医论军、以医论事、以医明理,至今留下多达三百余篇相关文字,至为珍贵。特别是在地方任职之时,东坡关切民生,重视医政建设。元祐四年(1089),苏轼出知杭州,水涝之后又逢大旱,灾荒与疾疫并作,东坡在公共医疗方面开创了历史:
公又多作饘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公曰:“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私橐,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废。[11]214
正由于东坡长期的地方行政经验,他还关注到一个特殊群体——监狱病囚的医疗情况,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在《乞医疗病囚状》中,东坡请求军巡院及各州司理院应有专人专责,“各选差衙前一名,医人一名;每县各选差曹司一名,医人一名,专掌医疗病囚,不得更充他役,以一周年为界”。并提出赏罚激励之法,治疗病囚,“每十人失一以上为上等,失二为中等,失三为下等,失四以上为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科罪,自杖六十至一百止。”“若医博士、助教有缺,则比较累岁等第最优者补充。如此,则人人用心,若疗治其家人,缘此得活者必众。”[5]2999
但东坡建议,未受重视。元祐七年(1092),东坡《与张嘉父书七首》之三告诫身为狱吏的张嘉父对于病囚深加留意:
君为狱吏,人命至重,愿深加意。大寒大暑,囚人求死不获,及病者多,为吏卒所不视,有非病而致死者。仆为郡守,未尝不躬亲按视。若能留意到此,远到之福也。[5]5864
从书信我们可以得知东坡为疗治狱中病囚所做的努力,他也希望每个狱吏都能尽职尽责。
由于种种原因,陆贽的《陆氏集验方》已佚,而苏轼在医学方面的贡献,赖《苏沈良方》传世,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轼杂著时言医理,于是事亦颇究心。盖方药之事,术家能习其技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儒者能明其理而又往往未经实验。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故宜非他方所能及矣。[6]1279
综合东坡的医学活动和相关著述,可以这样讲,东坡有医国之志,具医国之能,多医国之论,传统医学之医理、药性、辨证施治与其为政、为人、为文已有机融合在一起,成为文化史上的特例,值得特别关注。
至于其身在贬所,也尽一切可能有所作为,利泽一方。前人已具论,前已引述,不再赘言。
再就苏、陆二人个性而言,陆贽“性本畏慎”,《旧唐书》本传载“贽性畏慎,及策免私居,朝谒之外,不通宾客,无所过从”,晚期贬居,“贽在忠州十年,常闭关静处,人不识其面,复避谤不著书。家居瘴乡,人多疠疫,乃抄方书,为《陆氏集验方》行于代”。[12]3817-3818相关资料记载略同。陆贽由于个性原因,谪居之后,“避谤不著书”,使其人生的后十年几成空白,对于今天的陆贽研究,对于我们了解认识特定的时代,皆成憾事。
东坡则不同,初贬黄州,再贬惠州、儋州,多有友朋规劝其谨言慎行以避祸,东坡自己也时时警示自己。但这些只在念想之间。贬居黄州五年,他遨游山水,躬耕东坡,回味追索人生,“石压笋斜出”,贬居生涯成为了东坡人生创作的转变期、爆发期。王水照先生在《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中指出:“元丰黄州和绍圣、元符岭海的长达十多年的谪居时期,是苏轼创作的变化期、丰收期”。[15]17
当然,如果单从字面上搜寻,我们也可以找到东坡闭门幽居以远祸的表达,诸如“幽人无事不出门”,“但当谢客对妻子”,[5]2152“黄当江路,过往不绝,语言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5]5529揆诸情理,一个人政治上遭受打击之后,特别是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丝毫没有忧谗畏讥之心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尤为看重的是,东坡在人生逆境中的浩然之气,其不以一己之祸福而易其忧国爱民之心的政治人格——东坡在黄州《与李公择书》中倡言“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5]5617“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先”,苏轼这几句话掷地有声,振聋发聩。
东坡贬谪岭海之后,亦仅偶发贬谪避祸之叹,其大量的诗文创作、书信往来,载记了东坡晚年对于人生的追索思考;一系列纪实性作品,记载了一代伟人晚年的生活踪迹和复杂丰富的心灵世界,对于后世研究东坡、研究斯时斯地的地域文化,研究认知特定的流寓文化,都是第一手的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陆贽谪居之后,诗文创作几成空白,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令人遗憾的事情。而东坡谪居所作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定的东坡形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东坡的坚毅与执着,在谪居的艰难岁月里,他整理修订《易传》,又撰写了《书传》《论语说》。其《和陶杂诗之九》自述传经之志:
余龄难把玩,妙解寄笔端。长恐抱永叹,不及丘明迁。
……虚名非我有,至味知谁餐。[5]4925
三部书完成于特殊时期,又为东坡心力所系,故作者本人极为看重,北归途中与苏伯固书云:
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喻,其他何足道。[5]6364
东坡一生,黄州惠州儋州,谪居生涯十余年,反复研味,我喜欢东坡自明心迹的诗作,所谓“年来万事足,所欠惟一死”;[5]5026所谓“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5]5292所谓“但使荆棘除,不忧桃李衍。养我岁寒枝,会有解脱年”;[5]4789所谓“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5]5130这些诗作让我们看到了襟怀磊落的东坡,看到了坚毅傲岸执着的东坡。
东坡的晚节风范从不同角度于后来者以启迪,人们也从不同层面探索总结东坡风范的内涵,在此撷其一二,以窥一斑。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言东坡晚年的著述,“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11]85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以为:“阁下谓蜀之锦绮妙绝天下,苏氏蜀人,其于组丽也独得之于天,故其文章如锦绮焉。其说信美矣,然非所以称苏氏也。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惠洪《冷斋夜话》在比较东坡与秦观、黄庭坚谪贬之作后,赞叹:
少游谪雷凄怆,有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鲁直谪宜殊坦夷,作诗云:“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轻纱一幅巾,短簟六尺床。无客白日静,有风终夕凉。”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休歇,故其诗闲暇。至于东坡《南中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唯一死。”则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可畏而仰哉![16]2183
刘克庄也为之感叹:“其浩然不屈之气,非党祸所能佈,烟瘴所能死也。”[13]1361当代学者更从多方面对于东坡晚年处逆如顺的精神内涵进行探讨,并给予高度评价:
《宋史》本传说他谪居惠州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苏轼凭借自己所独具的洞悉苦难的眼光以及开阔的胸襟,处逆如顺,化被动为主动,在痛苦中寻求快乐,在极不自由的现实环境中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由的空间,其人格魅力由此可见一斑。[17]372
所以我们说,东坡一生服膺尊崇陆贽,但细加寻绎,其一生的医学造诣,非陆贽蒐集验方所及;其谪居期间所达到的成就,无论是利人济物之所为,抑或是诗文创作之所获,均远远超越了陆贽。
综上所述,东坡一生服膺、尊崇陆贽,与其家学、师承有密切关系,其对陆贽的评价“近世文人,私所敬慕者,独陆宣公一人”,“三代以还,一人而已”,在其历史人物论中因极为推崇而引人注目;而东坡对于陆贽接受尊崇的核心在于陆贽为政为文“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的“实用之学”,所以其元祐草诏似陆贽,为政为人深受陆贽的影响。但在论者颇为重视的陆贽晚年搜集验方以济世用和如何度过贬谪生涯的生活态度、诗文创作及谪居中不以一己之祸福而易其忧国爱民之心的坚韧刚毅执着方面,有较大差异。所以东坡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师,在于其博采众长,广泛借鉴,不断超越自我,超越先哲,而自成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