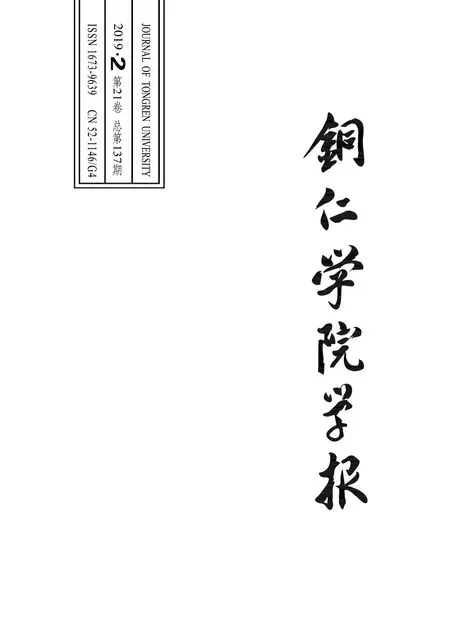《述酒》之谜与诗学文献
范子烨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
在陶渊明创造的诗国中,《述酒》诗是一个特异的存在,其廋辞隐语所造成的晦涩难懂在我国诗史中极为罕见,也与陶诗自然天成、平静恬和的主要文化气质甚不相侔。即使在苏东坡极力推崇陶渊明的时期,《述酒》诗也还是一篇令人困惑的诗作,如黄庭坚就认为“此篇有其义而亡其辞,似是读异书所作,其中多不可解”,隐隐地回应着颜延之对陶公“性好异书”的评说。至两宋之际,韩驹指出:“余反复之见‘山阳归下国’之句,盖用山阳公事,疑是义熙以后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泪抱中叹’、‘平王去旧京’之语。渊明忠义如此。今人或谓渊明所题甲子,不必皆义熙后,此亦岂足论渊明哉!惟其高举远蹈,不受世纷,而至于躬耕乞食,其忠义亦足见矣。”“忠义说”由此而生成。山阳公,即汉献帝刘协。韩氏认为此诗之作是以晋宋易代为历史背景的。在此基础上,赵泉山明确指出:“此晋恭帝元熙二年也,六月十一日,宋王裕迫帝禅位,既而废帝为零陵王。明年九月,潜行弑逆,故靖节诗中引用汉献事。今推子苍意,考其退休后所作诗,类多悼国伤时感讽之语,然不欲显斥,故命篇云《杂诗》,或托以《述酒》《饮酒》《拟古》,惟《述酒》间寓以他语,使漫奥不可指摘。今于名篇姑见其一、二句警要者,余章自可意逆也。如‘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此岂《述酒》语耶?‘三季多此事’,‘慷慨争此场’,‘忽值山河改’,其微旨端有在矣,类之风雅无愧。《诔》称靖节‘道必怀邦’,刘良注:‘怀邦者,不忘于国。’故无为子曰:‘诗家视渊明,犹孔门视伯夷也。’”无为子,即北宋人杨杰。至南宋时代,汤汉确认此诗为“零陵哀诗”:“按晋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 明年,以毒酒一罂授张伟,使酖王。伟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踰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诗辞尽隐语,故观者弗省,独韩子苍以‘山阳下国’一语疑是义熙后有感而赋。予反复详考,而后知决为零陵哀诗也。昔苏子《读述史》九章曰‘去之五百岁,吾犹见其人’也,岂虚言哉!”因此,就政治解读而言,此诗被定性为晋恭帝零陵王哀诗。晚清时代,张谐之著《陶渊明〈述酒〉诗解》一书,后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收入《为己精舍藏书》,此书全面、系统地推进了汤汉的“零陵哀诗”说。1925年,古直撰《〈述酒〉诗笺》一文(章太炎主编《华国》杂志,第2卷第7期,1925年5月),在同一思路上加以拓展;1939年,储皖峰(1896-1942)发表《陶渊明〈述酒〉诗补注》(《辅仁学志》,第8卷第1期,1939年6月),更为全面地揭示了此诗与晋宋鼎革之关系,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指出:“余窃以为渊明作哀时事诗,不以他物为题,而以《述酒》为题者,殊耐人寻味,尝反复推求其故,一则因诗中言酒特多,易于混淆视听。二则晋代兴亡之始末及宋之开国,均有与酒相关之故事。”“渊明既熟闻此等故事,益以亲见禅代之事实,遂发愤而为此诗,故诗中迭纪废兴,诗题犹存《述酒》,题下并注‘杜康造,仪狄润色’二语,观其字面,明为述酒之历史,审其内容,乃述晋宋间之近事也。”“晋祚虽倾覆于刘裕,而玄之篡逆实成刘氏之先驱。”逯钦立在1947年发表《〈述酒〉诗释疑》一文(《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第1卷第3期,1947年9月,后收入《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7-217页),则是对储氏之文的补充和修正。此方面的力作还有邓小军《陶渊明〈述酒〉诗补证——兼论陶渊明的政治态度及其隐居前后两期的不同意义》(《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此文在修订后收入邓小军《诗史释证》,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36页,题为《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态度——陶渊明〈述酒〉诗补证》),而《陶渊明〈述酒〉笺证》(《铜仁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则是邓小军关于《述酒》诗的总结性研究成果。相对而言,对此诗的“自然说”层面的阐释要少很多,也单薄很多,如袁达《陶渊明〈述酒〉新解》(《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田晓菲《清醒的诠释:论陶潜〈述酒〉诗》(赵敏俐、佐藤利行主编:《中国中古文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0-440页)。袁氏的基本观点是“《述酒》是一首气功体验诗”,田氏的宏文主要认为此诗是由追溯“竹林七贤”开始的中古文人饮酒史,“山阳”是以七贤隐居之地代指七贤,而与山阳公无关,故对“忠义说”予以彻底否定。但山阳公刘协在禅位后的14年里,一直住在山阳,山阳公故城至今依然绵延在河南修武的大地上,他的陵墓——禅陵也在修武境内。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也是需要进行田野调查的,否则,“诠释”古典作品,有时就很难做到“清醒”。曹道衡所撰《陶渊明〈述酒〉诗臆解》一文(《古籍研究》,1996年第4期)始于“忠义说”,终于“自然说”,二说适度兼采,表现出客观存疑的学术态度。此外,还有齐益寿《陶渊明〈述酒〉诗旧说质疑兼论该诗的主题》(《新潮》第12卷,1955年9月版);韩明昌《陶渊明〈述酒〉诗考补论证》(《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越南阮氏明红《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谈笑《汤汉前〈述酒〉诗接受情况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顾农《从陶渊明〈述酒〉诗说到他的政治态度》(《文学遗产》2017年第2期),《晋 宋易代与陶渊明》(《中华读书报》2018年1月3日第5版);等等。亦有部分论文虽然不是关于《述酒》诗的专论,但对这篇作品也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如罗根泽《陶渊明诗的人民性和艺术性》(《人民文学》1954年11月号,又见《古典文学研究汇刊》第一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9-48页,罗根泽《中国古典文学论集》,五十年代出版社1955年版,第54-77页)和曹道衡《关于陶渊明思想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增刊》五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53-175页,后收入《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4-183页)。
《述酒》诗的解读史并不复杂,但是,这首诗的内容确实相当复杂。就其内容而言,我们可以视之为东晋王朝的简史,其真正的诗题应该是“《述酒弑》”,因为晋朝最后一位皇帝晋恭帝司马德文(386-421)之被害与酒确有密切关系。元熙二年(420)六月,恭帝禅位于宋,傅亮起草禅位诏书,请恭帝抄写。恭帝欣然操笔,谓左右曰:“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所谓“桓玄”云云,是指晋安帝被桓玄胁迫蒙尘于浔阳的事件,但安帝后来是在桓玄败后被刘裕派人缢杀的,晋恭帝在禅位于刘裕之后,也被其残忍杀害。在谋杀后者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细节都与酒有关:一是刘裕以毒酒一瓮授张伟,令密加鸩毒,这位品行高洁的人在路上自饮而卒;二是永初二年(421)九月,刘裕密令太常褚秀之和侍中褚淡之以兄长约妹谈话的方式调开卫护恭帝甚严的褚妃,兵人借机翻墙而入,进毒酒于零陵王。王不肯饮,说:“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兵人乃以棉被掩杀之。在诗人的笔下,酒代表着罪恶,正如《哈姆雷特》中的毒药一样。储皖峰引清朱乾之语说:“自晋以前,魏之山阳、晋之陈留,犹得善终。虽莽于定安,不敢杀也。自是以后,废主无不杀者,宋启之也。”因此,两位晋帝的惨死乃是晋宋之际的绝大历史事件。明人夏良胜曾经指出:“至如读屈骚,人皆知其屈抑悲愤之志,而莫知大意只在《远游》一篇,当时君闇臣谗,世莫可与,但相与归之冥漠焉尔;读陶诗,人但知其恬淡隐况之高,而不知其大意在《述酒》一篇,盖刘裕以进酒行弑,而莫能正者,则托酒而逃,以慕于仙也。是故作文者,不可不有是也;考文者,不可不知是也。是孔子读诗之遗教也。”(《中庸衍义》卷十六)《远游》是否为屈原最重要的作品,我们姑且不论,但是,《述酒》肯定是陶渊明最重要的作品,因为其悲壮沉痛的历史书写毫不逊色于莎翁的悲剧,它是人类诗史中的永恒经典。
就《述酒》诗的阐释而言,从古至今,“零陵王哀诗说”占据主要地位,我一向遵从之,而今人反对此说者,大都不了解相关的研究史,而流于自说自话。为使人们对《述酒》诗的阐释史有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本期梵净古典学特别推出苏悟森的《陶渊明〈述酒〉诗文献辑校汇评》一文。本栏目之所以给悟森君此篇宏文以“唯我独尊”式的待遇,并非因为她是我的门徒,而是因为此文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述酒》诗的文献问题。悟森君面对的文献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为科学地辑录、整理相关的文献,她首先制定了比较合理的凡例,从而使得全文颇具条贯,囊括包举而丝毫不乱。该文首先校出《述酒》异文13则,其次将《述酒》诗句分为9个片段,并把相应的评论依次骈列其下,复次将47则评论《述酒》全诗、探寻渊明作诗本旨的材料汇 为一编。在行文过程中,随文附以按语,评介重要版本及相关人物的生平,足资研究者参证。这是一份非常非常有价值的陶渊明诗学文献,填补了相关文献学研究的一项空白。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依据丰富的《述酒》诗文献,悟森君指出:“自汤汉之后,注评《述酒》者代不乏人。民国以前,大多数学者仍是顺着汤汉旧路,视之为渊明抒发忠愤之作。《述酒》诗用典密集,词旨隐晦,不类陶诗他篇,虽然陶渊明未必有忠君观念,但其援引史实以论时事的字里行间,确实流露出对世事纷乱、国家兴亡的感叹。而《述酒》诗的历代阐释者又以理学家和遗民居多,忠君理想与亡国之痛,使他们在面对此诗时,往往格外留心《述酒》用典的君臣寓意,实际是借发掘《述酒》本旨之名,行浇自己胸中块垒之实。”她的体悟是深切的,她的观点也比较客观。一位九0后的青年学者能够取得如此创获,实在让为师者欣喜不已。悟森是一个腼腆、含蓄而安静的读书人,但此文却充分反映了她内心所蕴蓄的青春的学术激情。我相信,在她个人学术道路上,这篇由我授意由她自己独立完成的命题作文也必将给她带来永恒的光荣。因为今后无论何人研究陶渊明的《述酒》诗,都离不开她倾心整理的这份诗学文献。
梵净山人
2019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