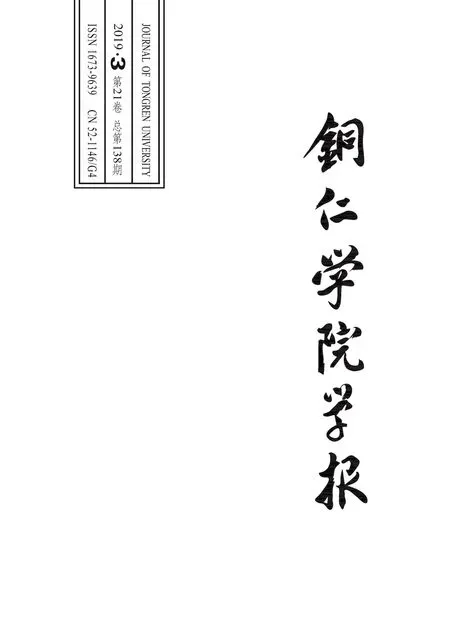《孔子家语》的正名思想及其理辞关系认识
徐东哲
《孔子家语》的正名思想及其理辞关系认识
徐东哲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宁 272067)
《孔子家语》是汉魏时期重要的儒学文献,亦为孔氏家学资料之汇编,书内篇章反映出汉魏学者对先秦儒学的传承与创新。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孔子家语》内有关正名思想的内容,同儒家对“理辞”文学关系的看法有着密切联系。孔子正名思想为儒家“辞以道名,名必循理”的文学理念奠定了思想基础,《孔子家语》充分吸收了孔子正名思想的精髓,在儒家传统文学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正辞淳、简雅质朴的文学审美追求。
《孔子家语》; 儒家; 正名思想; 理辞关系
《孔子家语》渊源久远,早在西汉时期,《汉书•艺文志》已将该书收入“六艺略”之“论语类”中。《孔子家语》传为孔门后学所编,书中辑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但该书在秦代并未为人所见,直至孔子二十二世孙孔猛将古本《家语》献于王肃后,《孔子家语》才以王肃注本的面貌通行于世。但王肃为打击当时风行的“郑学”,私自将此书增删篡改,托古以驳斥郑玄学说,导致此书长久以来被冠以“伪书”之名。直至现代,随着《儒家者言》等汉代早期简牍文献的出土,类似《孔子家语》原型的文献陆续出现,学者又重新对《孔子家语》的真伪问题进行了研究,逐步否定了王肃伪造说。王承略通过对《孔子家语》本文与先秦两汉互见文献材料的比对,认为《家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整理于西汉之时,全书仅有王肃增饰成分,并不是通篇伪造,而是刘向校书时便已有之。李学勤则认为:
“《孔子家语》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禧、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1]
尽管对《孔子家语》渊源尚有许多不明之处,但可以肯定该书保留了大量古老的原始典籍资料,且内容切实可靠,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与汉魏孔氏家学的重要文献材料。现今关于《孔子家语》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但就其文学思想的探讨还有所欠缺,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本文便以《孔子家语》篇目中的正名思想为突破口,着力探究由其思想引申出的文学观念。
一、《春秋》正名思想与其“属辞比事”之教
孔子的正名思想一直以来都是儒家的一个重要学术命题,由先秦至今正名主义之影响犹未消歇。孔子始倡“正名”之论乃缘于其伤于春秋之世周代伦理纲常体系已日趋崩坏,由此而导致了传统道德沦丧。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认为唯有重新捋顺君臣士庶之间的关系,使得上自天子、下自臣民的位置都能各得其所,才能让社会再度稳定。对此,冯友兰尝论曰:
处此情境下,孔子以为苟欲“拨乱世而反之正”,则莫如使天子仍为天子,诸侯仍为诸侯,大夫仍为大夫,陪臣仍为陪臣,庶人仍为庶人。使实皆如其名,此即所谓正名主义也。[2]
此处具体分析了孔子正名主义的概念与实质,实乃君臣本位之义,冯友兰在此处征引《论语》中的材料以为佐证: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3]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3]
这里孔子十分确切地指出定立名分为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名”便是人在伦理关系上的基本位置与属性,长幼尊卑不同,与之相对的人的权利义务也各不相同,倘若长幼失序、尊卑逆位,则国将不国矣。名分理念渊源久远,非仅儒家言之,其如法家、道家等流派都立说以阐明其意,但只有孔子的正名思想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分析其原因,便在于孔子的正名主义充分阐释了名分的伦理学意义,从而将伦理道德对人的感化教育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之后的儒学后继者的相关理论阐发无不是在孔子正名思想的统摄下进行的。至汉代《孔子家语》面世,其书中所传习的依然是传统的儒家正名思想。
自汉武帝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儒学逐渐成为汉代官方学术思想,而汉儒对“名分”的哲学意蕴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吴晓番提出汉儒从两个方面入手对正名思想进行解读:
在汉儒那里,对于“正名”而言,其实存在着两个维度的解释,一个是伦理政治意义上的,一个是明理认知意义上的。[4]
在这两种维度中,《孔子家语》所重视的乃是正名思想的政治伦理作用。较具代表性的例子,如《大婚解第四》阐述为政之道,便是从“正名”之角度切入:
(孔子曰):“人道,政为大。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男女亲、君臣信,三者正,则庶物从之。”[5]
治国理事第一要务乃是正其君,君正则百姓安。而为政之首要任务亦在使夫妇、男女、君臣之关系恰如其分,这与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理想是相一致的。由此而言,《孔子家语》所秉承的正名思想,其核心乃是“正名”的政治伦理意义,这种阐释更为接近孔子思想的原旨。
言及《孔子家语》中正名思想的文学意义,其渊源乃在于其书对《春秋》意旨的推崇,如下面一则材料所论:
“王者有似乎春秋,正其本而万物皆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罪,一动而天下正,其事成矣。(非孔子言,重新确认。)春秋致其时而万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万民皆治,周公载己行化,载亦行矣。言行已以行化,其身正不令而行也,而天下顺之。其诚至矣。”[5]
《孔子家语》将正名思想与《春秋》之义紧密联系,这种看法非其书独有,而是继承自儒家传统思想。《春秋》在“六经”之中自有其独特的作用,《庄子•天下篇》尝云: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6]
《春秋》的主要功用便为正名分以叙大义,《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春秋》正名之功有过评述: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7]
《春秋》虽为史书,但其明纲常,定是非,拨乱反正,是鉴别行为善恶的指导原则,所以被尊奉为经典。《春秋》指正乱名的种种行为,并客观公允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得失,褒贬精切,对后世影响深远。
孔子对《春秋》之义领悟颇为深入,孟子有云: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8]
春秋之世,周代封建体系土崩瓦解,诸侯纷争,乱世伊始。齐桓公、晋文公皆为当时雄踞一方的霸主,“齐桓晋文之事”即为争霸天下之事,此时史官忠实记录了乱世众生善恶之举,称善黜恶以垂教后世。孔子充分吸收了这些史书中的纲常伦理思想,借其义理来阐释自己的正名思想。这一点冯友兰尝论曰:
《春秋》之“耸善抑恶”,“诛乱臣贼子”,“《春秋》以道名分”,孔子完全赞成。不过按之事实,似乎不是孔子因主张正名而作《春秋》,如传所说;似乎是孔子取《春秋》等书之义而主张正名,孟子所说其义则丘“窃取”者是也。[2]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推断孔子甚为重视《春秋》“正名分”之作用,乃至于“窃取”其义,将其为我所用。由此不难发现,《春秋》堪称为儒家阐述正名主义的著作之始,正是以正名思想为依据,汉代学者进一步发掘出《春秋》的教化功用。《孔子家语》援引《礼记•经解》一段文字论述“六经”的教育意义,其中谈到: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5]
《孔子家语》言及《春秋》,主要是就其提升人“属辞比事”的能力来说的,“属辞比事”即为遣词造句、连缀文辞以记事成篇的能力。由此可见,《孔子家语》认为文学能力的训练通过阅读学习《春秋》最为有效。
《春秋》“微言大义”的记事风格早已为大众所熟知,其一字以寓褒贬的文辞特色亦可谓“美质”“尚实”之典范,这与孔子“文质彬彬”的文学主张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孔子家语》认为《春秋》可为“属辞比事”之教,并非仅因为《春秋》辞雅质洁,更深层原因是出于对其文学宗旨的认同。虽然《春秋》文法可为“属辞比事”之教,但其内容却并非十全十美,缺陷就在于“春秋之失乱”。所谓“乱”,并非言《春秋》文辞混乱,而是指《春秋》内容中多记奸佞臣子犯上作乱之实,反映出的现实问题往往沉重而黑暗。司马迁尝言: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7]
这里所说的“失其本”,即为名分混乱所产生的君臣失序、尊卑不分现象,《春秋》的思想主旨正是为矫正乱名之失。《春秋》之文辞虽美,但正名思想之宗旨才是其精髓,同时也是读者难以领会的地方。在学习《春秋》的过程中,如果不能以正确的义理去看待分析史实,只是将其作为文辞学习的材料的话,即便习得高超的写作技巧,立论作说时也无法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去为善恶史实正名,这就是《孔子家语》认为“春秋之失乱”的原因。就理辞关系来看,《孔子家语》显然是认为在属辞比事中,文道义理等实质性内容是外在言辞修饰的基础,文理不正,属辞必乱,如此则会有浮华空洞、矫辞乱名之弊,也就是孔子所谓的“文胜质则史”。“史”之意,梁代皇侃训为:
史,记书史也。史书多虚华无实,妄语欺诈。言人为事多饰少实,则如书、史。[9]
可以推测,在早期史书风格较为浮华不实,大抵因为史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多作溢美之辞,评价他人功过时多没有能做到书法不隐、扬善斥恶。《孔子家语》借孔子之口批判了史书这种文辞风格,其文曰:
夫良史者,记君之过,扬君之善,而此子以润辞为官,不可为良史。[5]
“润辞”即为语辞修饰,过分追求文饰而忽略义理会妨碍大道的阐述,甚至是会被别有用心者拿来文过饰非,将“辞”作为攻讦正理的武器,作辞以害道,可谓本末倒置,是万万不可取的。
二、“辞以道名,名必循理”的文学创作宗旨
《孔子家语》通过分析《春秋》“属辞比事”的教化功能,发现了正名思想对作品思想内容及文辞风格的积极影响。在此基础上,《孔子家语》更为深入地对正名思想的文学意义进行探究,在抽象的理论层面辨析“理”与“辞”这一对文学范畴的关系。由于《孔子家语》并非专门性文学理论著作,故其在内容上没有直接呈现出文学思想方面的内容。但是透过书中许多相关材料,依然能够窥见《孔子家语》对“理辞”文学关系的看法。
《孔子家语》中辑录了许多对孔子弟子评价的材料,如《弟子行》《七十二弟子解》便是专论孔门弟子言行品德的篇目。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孔子弟子的评判中,《孔子家语》将言辞作为了一项重要标准,如其对宰我(宰予)的评判:
澹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胜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辞,而智不充其辩。孔子曰:“以容取人,则失之子羽;以辞取人,则失之宰予。”[5]
宰予,字子我,鲁人,有口才,以言语著名。仕齐为临淄大夫,与田常为乱,夷其三族。孔子耻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5]
宰我在《论语》中列孔门四科“言语”科之首,其言辞水平甚至在子贡之上。孔子虽对其人品颇有微词,可对其文辞还是承认与赞赏的。但在《孔子家语》中,宰我的文辞技巧却受到了孔子强烈的批判,孔子甚至指责其为田常作乱的罪魁祸首。究其原因,是由于宰我违背正理、矫饰文辞的做法与《孔子家语》所秉持的“理辞”观念完全冲突。《孔子家语》对于违背正名宗旨的虚伪言辞持坚决否定态度,《刑政》篇明确地阐明了这一原则:
巧言破律,遁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者,杀;作淫声,造异服,设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行伪而坚,言诈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惑众者,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者,杀。此四诛者不以听。[5]
这段文字杀气充盈,其思想不类儒家观点,而近于法家刑名之说。公允而论,其思想与儒家仁政之说相差甚远,但就出处而言,此段材料源出于《荀子•宥坐》,故在思想宗旨上并未出儒家学说之范畴。《荀子•宥坐》载有孔子诛少正卯一事,其中便言及“大恶者五”:
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10]
荀子以为此五种情形为最恶劣之罪行,其危害远胜于偷窃等犯罪行为。不难发现,荀子痛恨言辞虚伪、文过饰非之徒,认为其人愈是能言善辩、文采斐然,其危害就越大。这段材料后被编纂者收入《孔子家语》的《始诛》篇中,可以说是对荀子求真尚实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孔子家语》中的“四诛”之说,正是在荀子文学观点上的创新。
荀子在《荀子•正名》篇中阐释其正名思想时,曾深入解析了名辩中理辞的问题,并提出了“辞以志义”的文学创作原则:
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10]
荀子认为,作者阐发的义理一定要做到名能指实,即能“正其名”,这是荀子对作品的基本要求。作品必须具有确切的思想主旨,能够揭示事物本质,并以确切的言辞将其指明方称佳篇。荀子这一观念阐述了作品创作“名必符实”的基本原则,即“名足以指实”。这其实是继承了孔子“尚质”的文学理念,认为思想内容决定了作品品质的高低,但荀子论述得更为具体,对何为“实质”做出了解释,将理与名相契合作为作品思想正确性与合理性的一条重要原则。“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名辞是承载“志义”的工具,义理才是作品的灵魂所在。如果能精切简练地将义理论述明白,那么语辞修辞藻饰之工作可退居其次,甚至“舍之”亦可。可知在理与辞的关系上面,荀子是将理放在了第一位的。
“四诛”之说所体现的文学宗旨与荀子是相一致的,二者皆批评借伪辞以饰邪莹众的奸佞小人。但较之于荀子对“伪辞”的看法,“四诛”之说的观点更为深入透彻。荀子谓人“言伪而辩”,认为个体的险恶性情、不端心术是邪辞伪辩产生的根源,而唯有强化个人品德操守,修身养性、端正思想,异端邪说方能止熄。荀子所强调的乃是人内在的主观动机,是一种内发论。而“四诛”之说则有所不同,其将“巧言破律,遁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列为诸恶之首,认为正是巧辞伪辩的盛行,才使得纲纪失常,政治混乱,所以人心沦丧是由扰乱正名的“伪辞”所造成的。《孔子家语》中的“四诛”之说更为注重文辞对人的外化作用,正因如此,才猛烈抨击自作聪明、巧言诡辩以攻讦正名思想的宵小之徒。由此而言之,《孔子家语》乃将正名之理与文辞之道融合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认为辞必当循名理而作,而擅改名理,巧言惑众之辞,即便其文辞高妙,而其文心必然可诛。
《孔子家语》文艺观中循名作辞的创作宗旨,在另一部堪称汉魏“孔氏家学学案”的《孔丛子》中也有较为深刻的体现。《孔丛子》与《孔子家语》之间渊源颇深,两书共列《阙里文献考•艺文志》的子部目录之中。《孔丛子》旧传为秦末孔鲋撰,现今学界则认为《孔丛子》成书过程与《孔子家语》大致相同,是汉魏时期孔子后人合力编撰的一部孔氏家族学术资料汇编,反映出了汉魏孔氏家族的学术思想脉络。由此而言,两书可相互参考,而在思想内容方面亦可互为补充。在《孔丛子》中,亦存有许多辨析名辞关系的材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为《公孙龙》篇,读者由题目便可知此篇与战国名家公孙龙大有关联,通过对其内容进行分析,则能由孔穿与公孙龙的辩论中发现孔氏后学对名实关系的看法及与之相关的文学思想。
后世文献学者通过对《孔丛子•公孙龙》的文本进行分析,确定此篇其实是经由其它文献材料加工而成,其前段又见于《公孙龙子•府迹》篇,二者内容基本相同,学者考据后认为这段材料应当来源于桓谭的《新论》[11],而后段“臧三耳”一段文字则上见于《吕氏春秋•淫词篇》。可以认为,《孔丛子•公孙龙》是孔氏后学对旧有材料整理加工,并重新加入自己观点后的作品,它所反映出的思想内容与原有材料有很大不同,带有魏晋孔氏家学思想的特色。
《孔丛子》此篇关于名实思想的论述没有局限于哲学领域,而是引申至文学思想方面,进一步探讨辞与理之间的关系。在评判公孙龙与孔穿辩术之高下时,有如下论述:
平原君曰:“先生言于理善矣。”因顾谓众宾曰:“公孙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对曰:“辞则有焉,理则否矣。”[12]
撰者借史由之口,指出公孙龙名辩思想的一大特色,即言辞宏博。这一点是孔穿所不及的,所以即便是孔穿在义理上占有绝对优势,依然难以在言辞上与公孙龙相抗衡。《孔丛子•公孙龙》篇中,孔穿在二场论辩中皆落败,孔穿虽被公孙龙驳倒,但其却对结果不以为然,并对公孙龙的观点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中记曰:
明日复见,平原君曰:“畴昔公孙之言,信辨也。先生实以为何如?”(孔穿)答曰:“然,几能臧三耳矣。虽然,实难。仆愿得又问于君,今为臧三耳甚难而实非也,谓臧两耳甚易而实是也,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亦从难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应,明日谓公孙龙曰:“公无复与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胜于辞,公辞胜于理,辞胜于理,终必受诎。”[12]
此处从名实之辩言及理辞关系,就这一问题,此篇做出了如下的概括与论述:
首先,是对公孙龙与孔穿的言辞风格做出了分析与总结。公孙龙论说的一大特点即为文辞胜于义理,其在论辩中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即便是理屈,也往往将对方攻讦到词穷。孔穿则与公孙龙恰恰相反,其言辞风格为理胜于辞,这与孔子所倡“辞达而已矣”的文艺观念一脉相承。孔穿更注重的是言辞所传达的义理,而外化的语言物质载体则并不十分重要,过分矫饰的文辞往往是为搬弄是非、混淆正误,这种“以文害道”的做法是应该被批判的。
孔穿较之于荀子,对公孙龙的评判较为客观公允,他肯定了公孙龙的逻辑思辨能力与言辞技巧。但对公孙龙擅辞乱理的做法,孔穿持批判态度。孔穿认为其违背客观事实立论完全是无稽之谈,之所以在辩说中得胜,无非是搬弄言辞的诡辩而已,“虽难,实然”,技巧再高超,语言再精妙,最终无法掩盖事实与真理。从孔穿的逻辑思想来看,其对于名实关系的态度与荀子乃出同一机杼,皆反对扰乱名实和以言辞害理。
其次,是对理辞关系的评判。孔穿在文中问及平原君“将从易而是者乎?亦从难而非者乎?”事实上就是想探明平原君对辞理何者为第一要务的态度,而孔穿本人的立场无疑是认为理更重于辞。而借平原君之口,撰者评定孔穿要优于公孙龙,同时就理辞关系也作出了评判,即“辞胜于理,终必受诎”,认为理才是言辞之要,唯有掌握真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以言辞乱正理是错误的观念,无论言辞多么焕丽精妙,终究会在辩论中失败。在《资治通鉴•周纪三》中,司马光又以邹衍与平原君对话的形式呈现了这一观点:
邹衍过赵,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邹子曰:“不可。夫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13]
此处申明了论辩的本质不在于展示言辞技巧水平,而在于分析问题的实质。若论辩双方无法申明义理并使真理得以呈现,论辩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辩谈中不能求理,“语佳”便一无所用。一味地矫饰文辞、引譬连喻,会使得言意不明、义理不清,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辨析,反而会妨害大道的阐释,是君子所不为的。
《孔丛子》与《孔子家语》在文学理念上处于同一立场,在辨析辞理关系时都秉持着理优于辞的态度,对擅言辞而乱正理的做法作出了批判。虽然练就高超的名辩技巧本无可厚非,但如公孙龙般专擅文辞的套路却没有得到儒者的广泛认同。究其原因,还是出于人们认为公孙龙立论偏颇,扰乱名实正理,其诡辩的文辞风格也未能为后人所接受。王充《自记篇》认为“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14],并提出“辩论是非,言不得巧”[14]的准则。可见汉代文士已就“文必丽以好,言必辩以巧”[14]的文风作出过批判。梁代的刘勰亦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明确指出:
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15]
是以知,刘勰将“贵能破理”作为立论之基本要求,以理辞相映为尚。《孔子家语》由名实之辩而述及理辞之关系,肯定文辞与名理的统一性,从而确立了“辞以道名,名必循理”的文学理念,这种理辞合一的文学创作宗旨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无可估量。
三、“质有余不受饰”的文学审美观念
经由前文分析可知,《孔子家语》在文艺思想上秉持循名作辞的创作宗旨,尤为重视“理”的重要作用,但这并不表示《孔子家语》就忽略“辞”的重要性。由于辨析名实必然要借助于文辞,所以《孔子家语》在文辞理念的问题上也多有阐述,最具代表性的便为如下一则材料: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贲焉,愀然有不平之状。子张进曰:“师闻卜者得贲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对曰:“以其离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谓之贲,非正色之卦也。夫质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贲,非吾兆也。吾闻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质有余不受饰故也。”[5]
这则材料又见于《吕氏春秋》与《说苑》,可见渊源极早,说明这一看法至秦代便已有之。孔氏后人与王肃将此段材料辑录入《孔子家语》,可见对其文学观念持认同态度。此段所言乃是孔子对于“贲”卦的认识,贲本意为文饰、修饰,所以“贲”卦有饰外扬质之意。《彖》曰:
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6]
“贲”卦言文明以化育天地之象,本意十分美好,孔子却对此卦并不赞赏。究其原因,是孔子认为“贲”卦“非正色之卦也”,即此卦内质杂而不纯,不符合孔子的审美理念。文饰之美,本是人人心向往之的,孔子之所以不持这种审美观点,便是由于孔子追求的乃是中正的内质之美。色彩之中,孔子认为黑白为正为美,虽简单却不失雅洁,这是其它华艳色调所不能比拟的。孔子又特举丹漆白玉二例予以说明,此二物都是生活中的华贵器物,但其色调却简洁纯粹,无需文饰,本质便足以称为人间至美。孔子由丹漆白玉之例引申至文学领域,认为文者以“美质”为上,无需烦以修辞矫饰,即为“质有余不受饰”。
概括而言,“质有余不受饰”可以说是《孔子家语》文艺审美观的核心,虽然目前无确切文献证据表明其观点由孔子本人阐发,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抹杀这一发现的重要价值。《孔子家语》成书自有其特殊性,其书涵盖了孔门后学的诸多学术观点乃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完全能够将“质有余不受饰”的审美理念视为汉魏以来孔氏家学思想的投射。通过对这一观点的分析与解读,可以探究儒家文艺观中“文质”思想的发展脉络。
事实上,儒者对文质关系的探讨由来久矣。早在春秋时期,孔子本人便提出了“文质彬彬”的文学观念: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
“文质彬彬”本身是孔子借以形容君子的道德修养,但后来被文论家引申为孔子的文学观点,指作品文与质的关系,即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孔子认为作为言辞外在修饰的“文”与作品思想内容的“质”应当协调统一,《礼记•表记》对“文质彬彬”的内容作过具体化阐释:
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17]
此段中提及言辞修饰亦为君子之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外在的“文”需要内在的“质”来作支撑,若内质朽坏,则“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质”包含着很多方面的内容,就文学而言,辞令中所承载的义理是最为重要的,若文理虚浮,则语辞空疏;若文理有违正道,那么再华美的语言也是荒谬之谈。正由于“质”决定了作品的取向,所以在“文”“质”二者中,孔子尤为关心的是文辞“质”方面的内容。孔子尝曰:“辞达而已矣”,孔安国将此句阐释为“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孔安国站在了“尚质”之立场解析了孔子的观点,可见其对作品质朴平实风格的欣赏。
战国时期的孟子就“文质”理念也有过评述,其对于作品之“质”的看法,从《孟子•尽心下》的一段材料中可见一斑:
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8]
朱熹训诂此段时有云:
古人视不下于带,则带之上乃目前常见至近之处也。举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18]
孟子在作品风格上更为推重“质”,推崇简约浅近、理旨深刻的文学风格。以直白之语阐释真理,为世人所喜闻乐道,这便是孟子一贯的文艺观念。宋代苏洵曾对孟子评价道:“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可谓是对孟子文风的最好注解。
后至于荀子,其对文质关系的看法已更为明晰。荀子明确地提出言辞的第一要义是“辞足以见极”,即清晰明确地表达出义理之意,这一点与孔子“辞达而已矣”的看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是对孔子文学思想的具体阐发。荀子所追求的言辞风格看似简单,实则难以企及。荀子虽然认为名辞“足以相通则舍之矣”,但能够自然顺畅地表达内心思想却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更何况是要将主旨阐发至极致。要使辞义相贯通需要扎实的语言及文学功底,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荀子从功效的角度描述了言辞到达极致的境界:
故知者之言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10]
这种语辞不仅便于闻之者领会,而且在亲身实践中也便于掌握运用,并能够长久坚持此道而不移。老子尝言:“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可知这种带给人深远持久影响的言辞是非常难得的。荀子所倡“通达”之言辞风格与其“辞以志义”的文学观点相契合,只有在言辞可顺畅阐发义理时,其它高级修辞手法才有使用的意义。这一点清代叶燮在《原诗》中也有过论述:
“推理、事、情三语,无处不然。三者得,则胸中通达无阻,出而敷为辞,则夫子所云‘辞达’。‘达’者,通也,通乎理,通乎事,通乎情之谓。而必泥于法,则反有所不通矣。辞且不通,法更于何有乎?”[19]
叶燮之观点卓有见地,技法的运用需要作者首先具备能够行云流水、自由无碍的书写思想胸臆的能力。无法自然流畅地用言辞展现义理与情感,任何的外在修饰都是徒劳,作品必将走向浮华空洞的风格。
正是在吸收前代儒者文辞思想的基础上,《孔子家语》才确立了“质有余不受饰”的文艺思想,并将其作为统摄全书的核心文艺观念。这一观念在全书许多篇章中都有所体现,如在《致思》一篇中,便有一则例子可为之佐证。
《致思》篇中,孔子让子路、子贡、颜回“各言尔志”,子路言其以勇武匡世,子贡欲以辩术安邦,唯有颜回志在辅佐明君推行礼乐教化,而使“由无所施其勇,而赐无所用其辩”。孔子对颜回之语深表赞许,并给与极高的评价:
孔子曰:“不伤财,不害民,不繁辞,则颜氏之子有矣。”[5]
不伤财害民反映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而“不繁辞”之说特别值得玩味。显然,“不繁辞”并非仅指言辞简约不繁,而是有更深层的含义。追溯本源,“繁辞”之概念来自于《韩非子•有度》:
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20]
韩非子此处言臣子多以夸夸其谈的言辞来欺瞒君上,故应立法度以审赏罚。韩非子所谓“繁辞”,不仅是指文辞的外在修饰,更是就文辞之义而言。在前文中,我们已阐述过以邪辞乱正名,文过饰非的弊端。臣下欲以文辞来欺骗君上,必定会借助于其修辞技巧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其文章辩辞愈为精巧,其观点愈不易辨识,正所谓“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居心叵测的文心孕育出了饰邪莹众的“繁辞”,“繁辞”之风盛行,反映出的问题不止是文风日趋虚浮,还有民众道德素养的衰颓。明代李东阳在《答陆鼎仪诲言》中言曰:“繁辞剧无益,欲制已出口”,便是在谈君子“不繁辞”的修为之难。由此而言,《孔子家语》中“不繁词”之说不仅是文学概念,还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将“美质”的文学追求升华到了伦理道德修养的层次,其内涵已由文质之辩引申至思想义理领域,体现出了儒家文艺审美理论与学术思想的高度统一。
由孔子“文质彬彬”至《孔子家语》“质有余不受饰”的美学观念发展历程,反映出儒家学者对作品文理实质的重视和对朴实文风的追求。老子所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与《孔子家语》中的这一文学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作品的文饰之辞只是外象,内涵之美皆蕴于文质之中,“质”才是作品最为简单纯粹的本真面貌,是文学之美的极致。在尔后千年的文学思想发展史中,虽然“文质之争”始终没有消歇,但儒家“文以载道”的文学宗旨终未改变,而其理正辞淳、简雅质朴的文学审美追求,亦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
[1] 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J].孔子研究,1987(2):60.
[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卷上[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55.
[3] 徐志刚,译注.论语通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58.
[4] 吴晓番.正名思想的历史衍化与哲学意蕴[J].思想与文化,2012(12):38.
[5] 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7:35.
[6] 孙通海,译注.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8:379.
[7]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长沙:岳麓书社,2002:739.
[8]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158.
[9] 皇侃.论语义疏[M].上海:上海古书流通处,1921:47.
[10] 王先谦,译注.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429.
[11] 傅亚庶,张明.再论《孔丛子》的成书与真伪[J].兰州学刊,2013(1):48.
[12] 傅亚庶,译注.孔丛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1:422.
[13] 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9:210.
[14] 张宗祥,译注.论衡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602.
[15] 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2018:218.
[16] 杨天才,译注.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18:126.
[17]王文锦,译注.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6:432.
[18] 朱熹.孟子集注[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782.
[19] 叶燮.原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38.
[20] 王先慎,钟哲,译注.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56.
The Literary Thought of the Correction of Logic Concepts About
XU Dongzhe
( School of Marxism of Shangdong Polytechnic College, Jining 272067, Shangdong, China )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iteratures about Confucianism in the period of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It’s also the compilation of the family of Confucius. This book reflects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scholars in Pre-Qin Confucianism. In the research on this book, we can find the connection of the words and truth affected by the correction of logic concepts. Confucius' thought has prepared the ground for literary theory of Confucianism.has completely absorbed the correction of logic concepts of Confucius and further proposed the literary aesthetic pursuit that seeks conciseness and elegance.
, confucianism, the correction of logic concepts, the connection of the words and truth
2019-04-21
徐东哲(1990-),男,山东济宁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I206.2
A
1673-9639 (2019) 03-0076-10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肖 峰)(英文编辑 田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