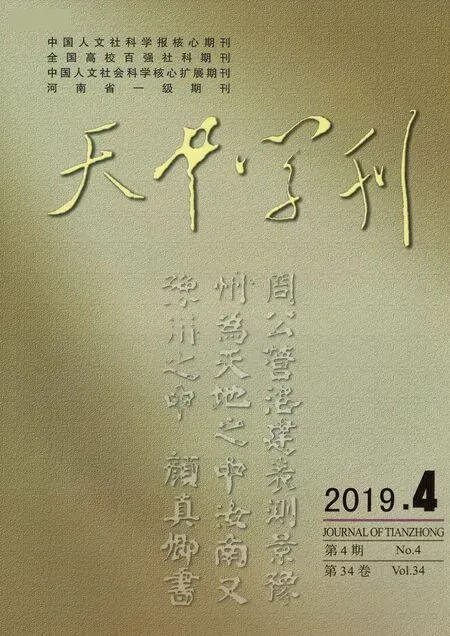再议“五常”
郑 文 宝
(南京工程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211167)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先哲通过对各种道德条目进行筛选、提炼,并经过长期历史演化而最终确定、提倡的核心道德范畴。“仁、义、礼、智、信”五种德目相辅相成,其内容与形式严密契合,是一个论证充分、体系严谨的系统①。
一
“五常”以伦理“体系”形式生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由“自在”走向“自觉”的过程:先秦孕育——无名有实,汉代形成——名副其实。
传统人伦思想是“五常”之道诞生的前提。早在“五帝”时期,传统人伦就已受到重视,“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史记· 五帝本纪》),这实质上规定了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取向和基本态势。先秦儒家在此伦理取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了诸多具体德目:孔子在周“仁民”“亲亲”等伦理思想基础上,强调和提炼出“仁”“忠”“恕”“礼”“义”“孝”“悌”“信”“智”“勇”“直”等具体德目,且在众多德目之中突出“仁”,强调“礼”,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 颜渊》)。孟子继承了孔子“贵仁”思想,提倡“孝”“忠”“信”“智”“耻”“介”。但在诸多德目中,孟子不再强调“礼”,而突出“义”,针对“四心”,将“仁义礼智”四德并举②,而且以“仁”“义”为主体,认为“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此后,管子强调“礼、义、廉、耻”四维,荀子重全德之礼……可见,先秦诸子有五常内容论述者,对“仁”“义”“礼”“智”“信”等单个道德范畴均有详述,甚至更有“五常”二字的提法。“五常”二字在先秦文献中最早见于《尚书· 泰誓下》的“狎侮五常”一语,但这里的“五常”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而不是指“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另外《韩非子· 解老》中也出现“五常”字样:“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显然,此“五常”并非“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字同而意不同。可见,涉及“五常”的论述在先秦颇多,但就是没有儒者将“仁义礼智信”五者作为组合并举,更没有按此顺序将之视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先秦文献中,将“仁义礼智信”并举者,到目前为止,笔者仅发现一例,可惜这人还不是儒者。庄子在发难儒家伦理时指出:“至礼有不人,至义不物,至知不谋,至仁无亲,至信辟金。”(《庄子· 庚桑楚》)庄子此处是在发难儒家伦理条目,并不是有意一一对应而言,五种条目出现并举应属巧合,而且五者次序与“五常”迥异。显然,庄子所说的“五者”绝非“五常”。因此,五常“体系”在先秦一直处于孕育阶段,并未成型。
由上可见,经过讨论、辩争,“五常”之中的“仁、义、礼、智”四者,在先秦时期就以组合形式在诸多道德条目中凸显出来。但是,“五常”的最后一个德目“信”,此时却依然是一泛泛的伦理条目。直至汉代,贾谊在梳理了50 多对道德规范之后,提出“六美”“六行”思想时,才将“信”与“仁、义、礼、智”并举:“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行和则乐兴,乐兴则六,此之谓六行。”(《新书·六术》)。贾谊当时的目的是在阐述“六行”内容,并未强调“五常”,“仁义礼智信”按照“五常”顺序组合在一起,实属偶尔言之,但是却为“五常”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后来董仲舒在进谏汉武帝时强调:“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春秋繁露· 基义》)至此,“五常”第一次带有正式目的和明确规范被使用,而且被明确了具体内容——仁义礼智信。自此以后,经过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广,“五常”便逐渐成为封建社会人们共同拥有和遵守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同时也开始了系统性的政治化历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最为主要的内容之一。后来,西汉末年作为官方文献的《白虎通》再次对“五常”加以整理、加工、提倡。由于《白虎通》处于法典化的特殊地位,“五常”自此之后便被长期固定下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人伦纲常之一。
“仁义礼智信”五种德目的内在逻辑关系在先秦阶段被初步地探索和规定,及汉时被升华为政治伦理,但并没有得到充分论述。儒学经历了魏晋隋唐时期的淡化与衰落,直至最后理学产生以后,“五常”伦理的内部逻辑结构才最终由理学家完成:“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仁,体也;义,宜也;礼,别也;智,知也;信,实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也就是说,“仁、义、礼、智、信”的内部逻辑构成,应以“仁”为核心与根本,“义、礼、智、信”为四支。这就使得“五常”在理论和现实建构方面,“首”“足”并举且层次分明,“仁”“义”“礼”“智”“信”五环相扣,互为支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化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二
长期以来,“纲常”二字已经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统称,所以一提到“五常”,人们便会自然而然地将它与“三纲”“六纪”联系到一起,即所谓“三纲、五常、六纪”。实际上,“五常”与“三纲”“六纪”是不同的,不但含义不同,地位和命运也不同。“五常”与“三纲”“六纪”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三纲”“六纪”是“纲”,属于目的性范畴,因此不一定具有合理性,但一定要处于统领地位;而“五常”是实现“纲”这一计划性目标的有效手段,必须具有合理性,因为只有具有合理性才可让百姓接受,才可能实现目的。
“三纲”“六纪”聚焦于人伦关系,为实现理想的人伦关系而提出具体要求,体现的是目的、期望。按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经济和社会的产物,“三纲”“六纪”诞生于封建社会,调节的自然是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可是现今社会形态、生存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人伦关系自然也会发生变化③,“三纲”“六纪”的“目的性价值”自然会过时。但“人皆怀五常之性”(《白虎通· 三纲六纪》),“五常”是人性,是为了实现“三纲”“六纪”规定的理想人伦关系而要求人们所应具备的基本属性,是抽象的道德精神,在具有“工具理性”的同时还具有永恒的价值。
迄今为止,人类在技术层面的变革日新月异,但是人类的伦理道德格局和价值取向却未曾颠覆,善恶取向、义利态势基本稳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是人性,是人这个感性动物的本身属性,与器物性的物质层面无关,器物一直在变,但人始终是人,人性未变。“五常”不是“三纲”“六纪”的人伦关系,而是以人性为根基,虽然曾经服务于人伦关系,但其体现的是人的基本属性而不是纯粹的人伦关系,所以抛除“仁义礼智信”的时代烙印和阶级外衣,作为“形而上”层面的本质和基本精神意蕴是可以传世的,是具有“普世价值”的④。正因为如此不同,“三纲”“六纪”与“五常”在近代“道德革命”中的命运也不尽相同,“近代的道德革命统称革纲常的‘命’,但在实际进行过程中,绝大多数新学家的批判矛头始终指向三纲,而未正面触及五常。虽然,他们并未明言两者间的差异,但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他们实际上是注意了这种区分”[1]。因此,“三纲应完全废除,六纪也过时了。五常之中,‘信’是最基本的公共生活规则。‘仁义礼智’既包含阶级局限性,也包含合理的内核,都要加以分析”[2]。具体来说,对于“五常”不可简单地加以全盘否定,应该珍视、继承“五常”之中普世伦理的价值取向。
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本文言及“五常”的“恒久价值”,并不是意指“五常”是永恒的、超阶级的、没有历史局限性的。我们必须承认,“仁义礼智信”的具体内涵,在不同的阶级社会里具有些许细节上的差别,带有时代烙印。诸如“礼”,孔子强调恢复周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 八佾》)《白虎通》对于礼的解释为:“所以尊天地,傧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白虎通· 礼乐》)很明显,这都是在强调礼的目的和作用,是在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这对于封建宗法社会而言是有益的,但是对于今天的公民社会则有些不合时宜。因此,文章主张认同“五常”的义理内容,并不是要完全地将传统“仁义礼智信”的具体内容照搬到现代社会中来,我们更需要的是“五常”方法论性质的精神财富和价值取向,而不是具体的条目规范内容。对于这一问题,罗国杰先生早就指出,道德属性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一直有着两种极端的倾向,一是从根本上否认道德的历史局限性,宣扬永恒的、超阶级的所谓‘全人类道德’或‘人的道德’。二是把道德的历史性、阶级性绝对化,否认道德发展中包含和积累着全人类道德的因素。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派内部存在着这两种极端的倾向,便在如何对待遗产问题上形成了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两种极端的态度”[3]。因此,对待“五常”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本文言及的“五常”价值不是具体的人伦关系和处事原则,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精神。这些不带有时代烙印和阶级印记的具有方法论性质的伦理精神,对于当今中国社会而言具有极强的道德优势和伦理教育意义,传承传统伦理合理因子可使当代道德建设内容变得充实而具有实效性,避免了道德建设的苍白、空洞和无力。
三
“五常”曾服务于封建社会,但它确实也体现了一些基本人性,我们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需要肯定、抽取“仁、义、礼、智、信”的合理因子,更需从“五常”整体系统运行机制方面汲取营养。
(一)“五常”内涵的价值合理性
“仁义礼智信”的合理因子便是“仁义礼智信”的基本精神。孔子将“仁”的内涵规定为“爱人”,视“仁”为其他一切德目的出发点和归宿,将“忠、恕”视为实现“仁”的最根本途径,将“仁”细化为“智”“信”“勇”“宽”等具体德目。“义”则是指遇事能自觉地按“仁”的精神和“礼”的原则做出合理的判断并加以实行的品德,“义者,宜也”(《礼记· 中庸》)。作为一个道德规范,“义”并不是偶然处事适宜,而是作为一种择善而行的内在自觉性,其具体内容表现在尊兄敬长等家庭伦理之中,更体现于行仁政反霸道的政论中。由“仁”“义”的内涵来看,二者是“五常”的内在规定,而“礼”则是外在规范,是“仁”和“义”的制度性体现,“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 礼论》),是依“仁”“义”而制定的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礼仪制度。“智”作为道德规范则是指明辨是非、善恶,“信”则是指诚实不欺的道德品质,二者是实现“仁”体现“义”的必要保障,“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 里仁》),“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
“仁义礼智信”的这些基本精神,放置于当今视野中仍有价值合理性。于“仁”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终极目标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市场经济“利”大于“义”的法理型价值取向,使得社会逐利现象日渐明显,而且目前许多人甚至已经开始不以唯利是图为耻,唯利是图的价值观正有逐渐成为通识价值、共识价值的趋势。在这种价值观指引下,物欲横流的人们在社会各个领域急功近利,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渐明显,甚至于在家庭伦理领域内的“父义母慈,正身率下”等家庭教养观也开始异化,新的“礼崩乐坏”现象在当代中国正逐渐蔓延。“五常”之“仁”提倡“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 尽心上》),这种“民胞物与”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如果融入当今经济领域何尝不能有效解决生态、环境等问题?同时,“五常”之“仁”的基本含义为“爱人”,“仁之实,事亲是也”“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颜氏家训· 序致》),如果这种“仁”之要义被经常提起,又何尝不能弥补市场经济下家庭伦理缺失、防止公共冷漠和人情异化?于“义”而言:现代社会是以利益刺激为动力机制的,极易导致极端利己主义出现。“五常”之“义”虽不拒“利”千里之外,但要求“罕言利”,更强调“见利思义”“以义制利”,对于当下混乱的市场行为又何尝不有着不可估量的教育意义?于“礼”而言: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使得一些行业出现竞争、谋利的无序化、混乱化。“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礼记· 曲礼》),作为“仁”“义”外化表现的“礼”使道德精神有“规”可循,有“矩”可依,又何尝不能同“义”一起有效地规范混乱的市场行为?于“智”而言:当前的信息社会使得知识和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被凸现出来,“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白虎通· 情性》),这种传统意义的“五常”之“智”在当今社会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知识、理性、判断,告诫人们应具备“不惑于事”的大智慧,摒弃急功近利的浅识短见。于“信”而言:“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法言义疏· 修身》),这是在教育人们“内诚于心,外信于人”,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人们应该相互信任、言行一致,社会各行各业的良性运转都需要“信”。
但是,由于“五常”的理想目标是要培养“内圣外王”的君子,不得不承认这种价值和思维取向曾经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曾禁锢了人们思想,束缚了人们进取,以至于五四运动以来长久的“道德批判”使得“‘仁’的绝对性与普遍性,‘义’的合理性与适应性,‘礼’的必要性与强制性,‘智’的地位与作用,‘信’的存在与弘扬都受到了人们不同程度的质疑”[4]。今天国家审时度势,要求将传统文化的合理性价值进行有效的当代转换,在当今社会转型、道德文化重构之时,正视“五常”、重新审视“五常”在道德建设中的功能与作用,将“仁、义、礼、智、信”的合理内涵肯定和传承下来,这对于提高道德建设实效性、矫治功利恶果尤有意义——“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不仅在于传统文化本身,更应探寻传统文化所深蕴的道德力量对中国现代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的巨大推动作用”[5]。
(二)“五常”的方法论意义
“五常”体系之所以能够千年传承,一是源于其道德内涵的社会适应性,二是“五常”组合这种系统运行机制的道德哲学优势。“五常”体系的系统运行机制优势在于,“仁义礼智信”五者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却又浑然一体,虽为“道德”内容,但是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出“伦理”的“实体性”,“仁义礼智信”五种德目虽关乎国家社稷,但更直接对应、关联百姓日常“伦理”生活⑤。传统社会从道德教育到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安排,无不充分地体现着这五种要义,这种道德建设方法更值得当今社会借鉴。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价值观念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多元的价值取向,必然会造就更为丰富多彩的社会发展。然而,由此带来的直接的社会负面效应则同样是毋庸置疑的。”[6]当今社会正面临着道德困境,道德建设也正处于尴尬境地:系统的道德教育是在学校中开展的,但是目前学校的首要现实任务却是传授知识和技能。在知识与技能的工具理性咄咄逼人气势下,道德教育显得苍白无力。道德教育是精神建设,属“虚”,但道德教育要取得实效就必须像“五常”那样“实”做。如前所述,“五常”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实体性,虽然是在满足国家需求,实现阶级目的,但却从微观入手,专注于个人的人性伦理建设,与人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将国家“道德”建设赋魅于个人“伦理”生活实际中,化虚为实,使人们在进行个体“伦理”思考时便巩固了国家“道德”建设。当代的道德教育在对比之下,显得“虚”功有余而“实”力不足,在当前的道德建设中,人们只在刻意谈起时才会想起道德,在日常“伦理”活动中不能有效践行“道德”内容,理论与实践不能有效对接,道德建设中缺少涉及基本人性的个体伦理内容。这就需要在方法论层面借鉴“五常”的避虚就实,环环相扣,将道德建设的形式和内容与人们的日常伦理生活紧密结合起来,避免道德建设的乏味和空洞。
另外,不同于器物,民族精神、人们情感是需要有一定基础的,伦理道德教育是讲究传承的,不能断代、凭空建设。即,当前道德建设乏力的原因,一是如上述的务虚不务实,二是多元化社会中缺少一种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支撑。当代社会的确是多元化社会,但多元化社会并不妨碍一种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存在,历史上隋唐五代乱世,佛道盛行,但仍有儒家政治伦理的一以贯之,儒家理念作为多元价值中普遍被认可的文化理念一直固守、承续着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即便是在当代,让中国人普遍认同的文化理所当然是中国的传统伦理文化。可惜的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教育体系现在基本处于被隔绝状态,被工具性教育体系包围、割断,这才导致了国人缺乏文化价值认同。国家现今提倡传统文化现代化转换研究,可能也正是出于此等考虑。“五常”因为承载基本人性,直到今日仍为不同地域所有华人共同认可,可以成为这个共同文化认同的基础,也可以成为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化的突破口。
“五常”作为道德教育典范出现,还有一个更为值得人们关注的合理性价值:道德德目以组合、体系的形式出现。传统社会伦理道德德目过百,但是先哲经过千年梳理,整理出最为重要的五个德目,组合在一起,并且主次分明,这就使得人们清晰地明白在道德领域中何为主何为辅。不但如此,五种德目相互配合、互动成为一个体系,将零散的超百种的道德教育内容整合为“一个”规范化的系统,更利于宣讲、学习和实用。这种以点带面、重点突出德目体系的道德建设方法,经过千年道德实践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道德建设方法。当代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每个层面又由八个字四个词构成,形成一个互动体系,以体系方式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可以说与“五常”的方法论体系建设异曲同工。
总之,无论“五常”的内容精义还是其方法体系,都注定成为今天道德建设理应首选的伦理内容和传承因子。
注释:
①许多人认为中国哲学无体系之说,因为中国哲学以宽泛、零散形式出现。但是,冯友兰却认为“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 页),本文采用此观点。
②《孟子·尽心下》出现过“仁、义、礼、智、圣”的提法:“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体现出孟子受到了“五行”观影响,“五行”强调的是“圣智”,不同于“五常”。因此,孟子虽提“五行”,但整体思想更注重“四德”:“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③早在20世纪80年代,李国鼎、韦政通等台湾学者就针对全球化的信息浪潮,突破传统“五伦”(“五伦”调整的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的熟人圈子)提出了“第六伦”——人与陌生人的“群己”关系。
④学界关于普世价值的认识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从横向上看,普世价值是指是否存在一些价值共识可以超越东西方文化壁垒的限制而成为全球的共识价值;二是从纵向上看,普世价值是指人类历史上存在一些基本价值精神可以穿越历史时空限制而永久使用。本文所言及的普世价值指的是后者。
⑤伦理与道德虽经常被等同使用,但是二者却是不同的:伦理是没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是源自人们日常生活没有经过有意加工自然而然形成的人性观念;道德则是经过国家有意加工而成的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