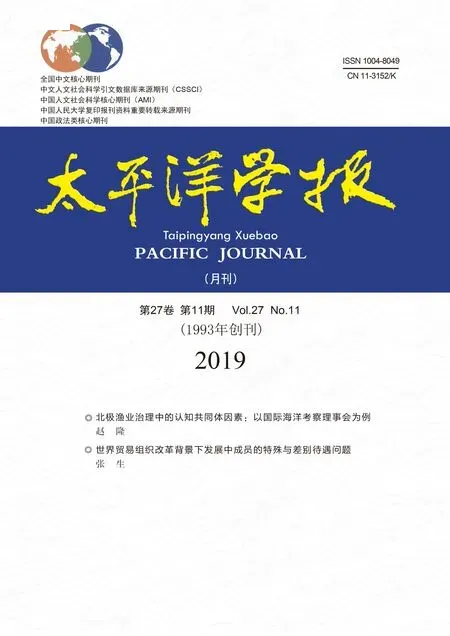断续线与南海总体空间秩序
牟文富
(1.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 成都 610071)
201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裁决出台之后,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指出菲律宾挑起的仲裁行为“不为菲律宾创设任何权利,也不为中国创设任何义务”,“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以仲裁裁决为基础的主张和行动”。(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9、42页。这意味着仲裁裁决之前的法律基础仍然是解决南海争端的出发点,仲裁裁决的法律效果将被忽略。那我们必须严肃地面对这样的问题:南海仲裁之前的南海总体法律秩序究竟如何界定?
本文的思路是根据南海空间秩序的构造过程来理解有关南海的历史事实并分析其法律后果,其中空间分配是一个关键的概念,构成了一种历史与法律的综合范畴。基于此,本文所持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参与南海空间分配的过程到目前为止是一种法律上有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塑造了南海空间秩序,断续线是南海空间秩序的一种标记。长期以来中国主要强调自己对南海诸岛有不可置疑的主权,这固然是中国在南海权益的坚实基础,但南海诸岛的主权与南海断续线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南海空间秩序同等重要。本文把南海断续线视为南海空间秩序中极为关键的一环,并不将它与南海诸岛主权分开考虑,论证的时空背景设定为南海仲裁裁决出台之前。
一、南海空间秩序的总体法律状况:初步描述
南海的法律秩序是一种与当代一般国际法兼容且符合东亚长期历史发展及现实的特殊空间秩序,也符合国际法中特别制度的特征。其核心构成要素包括南海断续线、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中国根据陆地支配海洋原则而享有的相关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长期在南海行使主权而产生的历史性权利。这些要素应作为一种整体性空间秩序的构成部分,而不是各项权利的简单叠加。
南海空间秩序的形成是一种空间分配过程,(2)法国国际法学家勒内·让·杜佩(René-Jean Dupuy)指出二战之后海洋法发展的一个趋势是从传统的航行利用到“由空间分配(apportionment of space)意识所主导的法律制度基础的发展”。René-Jean Dupuy, The Law of the Sea: Current Problems, Ocean Publications Inc., 1974, pp.13-14.整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近代开始、经过十九世纪中叶到1947年中国政府公布南海断续线。这个时期是中国巩固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的时期。这个过程早于南海周边国家。一个关键的法律要点是中国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主张满足了各个时期的国际法要求。该过程属于空间分配概念中陆地占有范畴。第二个时期是1947年公布南海断续线到2009年前后南海争端正式产生时近60年的时间。南海断续线则构成了海洋空间分配的范畴。中国不断强调断续线、周边国家长期的沉默使它构成了南海独特空间秩序的关键要素。总体而言,南海空间秩序的构造进程是一种陆地占有、海洋占有的混合体,是一种部分地独立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特殊空间秩序。
当然,无论空间分配概念对国际法的历史多么具有解释力,它毕竟只是一种供我们理解历史与现实的法律概念框架,本身并不自动为南海空间秩序提供充分的法律基础。既然南海空间秩序的构造过程属于陆地占有和海洋占有的历史范畴,那么就必须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分别考虑这两种要素在南海历史进程中的合法性。下文将主要围绕以南海断续线为标记的南海空间秩序的合法性展开。
二、南海空间秩序的形成
2.1 南海断续线的意义:南海空间秩序的标记
中国在先秦时对南海诸岛就有发现、使用行为,中间经历了唐、宋、元、明、清等若干朝代,一直到当代。无论在十五至十八世纪领土取得形式的发现和象征性兼并,还是十九世纪的有效占领,中国的国家行为都可以满足相关国际法标准。简而言之,国际法中的时际法学说充分支持中国在各个时期的主权主张。相比较而言,周边国家,尤其是越南、菲律宾主张领土主权的证据远不及中国充分。(3)参见赵理海著:《海洋法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贾兵兵著:《国际公法:和平时期的解释与适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9页;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 “The Nine-Dash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istory, Status, and Implic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07, No.1, 2013, pp.110-113。
鉴于越南、菲律宾这两个国家曾经分别沦为法国、美国的殖民地,因此这两个国家独立后的领土来源于对前宗主国的继承。然而,西方殖民国家如法国、西班牙、美国在殖民统治期间没有取得南海岛屿的领土主权。按照“帕尔马斯岛案”中仲裁员胡伯(Max Huber)对先后两种领土所有权(title to territory)之关系的论述,(4)胡伯认为先后两种领土所有权之间的关系中只有一种处于优先地位:“一种初始权源(inchoate title)不可能优于另外一个国家持续、和平宣示的权力(authority);因为这种宣示可能优于另一个国家在先、确定的权源……”。“Island of Palmas Case”,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Vol.II, p.846.这些殖民地国家没有取代中国已经拥有的、在先的领土所有权。就越南而言,其殖民宗主国法国试图在20世纪30年代曾试图侵占西沙群岛,中国一直在抗议,法国从未成功取得西沙群岛的主权。(5)吴士存主编:《南海问题文献汇编》,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7页。显示越南立场最薄弱的一个事实是1956年、1958年对南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的承认,(6)参见:Mark J.Valencia, Shar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Martinus Nijihoff Publishers, 1997, pp.32-33。此时禁止反言原则就会适用。对菲律宾而言,其1946年独立后的领土范围继承于前宗主国西班牙、美国殖民地,而殖民宗主国西班牙、美国的殖民地范围并未包括南沙群岛等。(7)涉及菲律宾领土范围的殖民地割让条约《1898年巴黎条约》、《1900年割让条约》和《1930年边界条约》表明西班牙、美国、英国都没有取得南海相关岛屿的领土主权。参见Lowell B.Bautista,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Legal Basis of the Philippine Treaty Limits”, Asian-Pacific Law & Policy Journal, Vol.10 , No.1, 2008, pp.16-21。所以菲律宾很难依赖前宗主国的行为对南沙群岛主张主权。菲律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屿的主权要求基于对无主地的先占,然而其主张最大的薄弱之处也正是它认为南沙群岛部分岛屿是无主地、被放弃领土这样的立场,而且菲律宾到20世纪70年代才公开其领土主张。(8)1978年6月11日年菲律宾总统第1596号令“宣布某些地区为菲律宾领土之一部分及将之纳入政府管理”。该总统令主要针对所谓的卡拉扬群岛,其陈述的理由为:“虽然有些国家宣称对这些地区拥有部分领土,惟他们的主张因已放弃而失效,无论在法律、历史和衡平上都不能胜过菲律宾。”参见陈鸿瑜编译:《东南亚各国海域法律及条约汇编》,(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1997年版,第67-68页。另参见Mark J.Valencia, Shar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Martinus Nijihoff Publishers, 1997,pp.33-35。
到20世纪初,中国对南海诸岛有一个普遍性的认知——主权属于中国。从1914年开始,各种官方、非官方地图就在南海画了中国领土的范围线。(9)参见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365页。在各种地图中,范围线的位置并不一致。这种情况可以这样解释:第一,地图是一种可以证明主权存在证据,而非领土主权产生的依据,有些地图的线只包括了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南沙群岛不拥有主权;第二,中国利用现代制图技术绘制地图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这些地图能否准确地反映主权状况,还取决于绘图技术水平。因此应综合考虑地图本身及其他证据的证明力。例如,中国古代地图在绘制中国大陆沿海海岸构造时失真度很高,这并不能否认中国对大陆沿岸领土自古以来的行使有效占有、管理的主权权力。最具重要意义的是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方域司印制的《南海诸岛位置图》,在南海诸岛周围画有U形断续线,1948年将该图收入《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公开对外发行。1949年中国新政府成立后也采用了经过调整的1948年南海断续线。
就在二战后海洋法面临巨变的时候,中国绘制了南海断续线作为南海空间秩序的标记。公布南海断续线是一种不为当时国际法所禁止的单方行为,其法律基础也是全新的。类似的《杜鲁门公告》阐述的权利基础是作为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大陆架概念,此后演化成为沿海国对毗邻海域之海床及底土上的自然资源享有主权权利的全新法律基础,而此前的海洋空间则是领海-公海的两分法,对海洋自然资源的权利基于领海主权和公海自由原则。中国在南海断续线内水域的权利基础一方面是“陆地支配海洋”,如果中国不拥有南海诸岛的主权,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有南海断续线。(10)南海断续线的产生主要同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对南海诸岛主权宣示行为有关。参见李金明:“中国南海断续线: 产生的背景及其效用”,《东南亚研究》,2011 年第1 期,第41-44页;贾宇:“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 年第2期,第112-120页。另一方面断续线也超越了该原则。因为根据该原则及当时习惯国际法,陆地领土产生的海洋空间一般为 3~12 海里的领海,而断续线与此不同,依据当时国际法,这种划线意识、方法是全新的,它以不违反国际法、也不为国际法所禁止的单方行为标准标定了一种南海空间的边界,(11)在国际法中,国家的单方行为对国际法的发展有巨大的积极作用。See René-Jean Dupuy and Daniel Vignes, A Handbook on the New Law of the Sea, Vol.I,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1, pp.37-38.确定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空间范围的内-外之分。当然,不管断续线给南海空间秩序带来何种新的影响,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它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
2.2 时际法审视下的南海断续线
(1)时际法与南海断续线的效力
菲律宾在南海仲裁的诉状中引用了18幅绘制有南海断续线的整幅中国地图,(12)Memorial of the Philippines, Vol.II, Annex M1-Annex M18.并指控中国“没有解释九段线内水域及海床的地位”。(13)Memorial of the Philippines, Vol.I, para.4.25.但菲律宾的证据及法律观点并未证明南海断续线没有法律效力,事实上正相反,断续线得到持续地强化,理由如下。南海断续线正式出现在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方域司印制的《南海岛屿位置图》上,按照中国学界一般的理解,当时断续线的功能主要是“确定和公布西沙、南沙群岛的范围和对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14)贾宇:“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 年第2期,第116页。相对于1947年的断续线,1953年的断续线做了小范围内的修正,(15)贾宇:“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 年第2期,第113页。此后60余年中再未有变化。1949年之后,尽管断续线在局部上仍然与南海诸岛联系在一起,但总体趋势是更多地被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这样的整体性地图之中,不再特地将断续线与南海诸岛位置联系在一起——不再以最初的“南海诸岛位置图”这样的名义出现。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地图绘制上的技术处理。合理的解释是,在确信对南海诸岛主权稳固建立之后,中国更倾向于从南海与中国整个领土主权的总体关系中来看待南海。中国长时间不受干扰地主张断续线,到后来断续线已经超越了最初标定岛屿主权归属的功能、从而产生了具有国际法上特别制度地位的南海空间秩序,中国将断续线作为整个南海空间秩序的核心要素之一对待。不过这首先需要在时际法的概念下证明这个过程的合法性。
国内学者已经用国际法中的时际法学说来考察中国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16)参见赵理海著:《海洋法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韩永利、谭卫元:“时际法与南海诸岛主权的历史演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3年第2期,第110-114页;李任远:“时际法视野下的南海诸岛主权归属问题”,《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12期,第24-31页。同样,判断中国公布南海断续线的效力及合法性的恰当方法也应当采用时际法概念,因为周边国家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攻击1947年的南海断续线的效力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除了在“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中胡伯阐述的时际法概念外,时际法的权威性学术表述是1975年国际法学会(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通过的“国际法中的时际问题”决议。已故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赵理海先生对其中的第一、二条翻译为:“一、除另有表示外,任何国际法规则的现实适用范围,应根据任何事实、行为或情势必须按照与之同时的法律规则来判断这项一般法律原则予以确定。二、在适用这项原则时,(a)任何有关单一事实的规则,应适用于该规则有效期间所发生的事实;(b)任何有关实际情势的规则,应适用于该规则有效期间内存在的情势,即使这些情势是先前产生的;(c)任何有关一项法律行为的合法性或非法性的规则,或有关其有效条件的规则应适用于该规则有效期间内所发生的行为。”(17)赵理海著:《海洋法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Intertemporal Problem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Session of Wiesbaden-1975, http://www.justitiaetpace.org/idiE/resolutionsE/1975_wies_01_en.pdf。根据时际法学说,衡量断续线之合法性的相关因素是当时国际法现状、后续发展。
就南海断续线具有分配海洋空间的功能这一点而言,它与美国的《杜鲁门公告》一样,都属于全新的海洋权利主张,那么在二者分别发生的1945年、1947年,它们违反国际法吗?该问题又涉及国家权利的来源:国家的权利是某种既有国际法规则所授予的,还是不能推定对国家的主权行为有天然的限制?从国际法的社会基础来看,更合理的出发点应该是后者,因为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假定主权国家只有明示许可的情形下才有行动的自由是不符合国际关系的现实。(18)参见Christian Tomuschat, “International Law: Ensuring the Survival of Mankind on the Eve of a New Century”, Recueil des Cours 1999,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1, pp.168-172。国家行为合法性主要是看国家行为是否违反主权平等原则、国际法在当时是否对国家行为明确施加了限制、一国行为是否侵害他国的合法权利。
根据时际法学说,南海断续线的产生应当符合它产生时有效的法律,而不是用产生争议时的法律来确定其法律效力。(19)参见贾兵兵著:《国际公法:和平时期的解释与适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5页;赵理海著:《海洋法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Keyuan Zou, “The South China Sea”, in Donald R.Rothwell, et al.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he Se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632。在考察南海断续线产生时有效的国际法时,尤其是应当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洋法律秩序的演化:从美国杜鲁门总统颁布的关于大陆架的宣言开始,各国竞相提出了非常激进的海洋主张,掀起了扩大海洋权益的狂潮。它受对海洋的领土性诱惑所驱使。(20)Bernard H.Oxman, “The Territorial Temptation: A Siren Song At Se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00, No.4, 2009, pp.831-832.这一时期海洋法的发展、尤其是相关习惯法的形成深受一连串的国家单方行为的影响。(21)René-Jean Dupuy and Daniel Vignes, A Handbook on the New Law of the Sea, Vol.1,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1, p.37.一个必须注意的法律现实是二战之后到第一次海洋法大会,国际法一般并不禁止各国单方提出激进的海洋权利主张。如果把当时中国政府公布“南海断续线”的行为放在全球很多国家提出激进的海洋主张的大潮中去看,(22)参见李金明:“21世纪南海主权研究的新动向”,《南洋问题研究》,2001年第1期,第90页;傅崐成著:《海洋管理的法律问题》,文笙书局,2003年版,第511、518页。中国的行为完全符合国际海洋法律秩序形成的现实。尽管中国政府当时的动机可能在于宣示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然而,如果说中国公布南海断续线的实际法律效果也是参与了海洋空间的分配,那此种行为也符合当时国际法。当代海洋法律秩序本质上就是对那之后全球分配海洋所形成的秩序的凝固。
中国有权做出这样的行为。常设国际法院在“莲花号案”中提炼出了这样的国际法原则:“国际法支配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故,约束国家的法律规则来自国家在条约或在被普遍接受为明示法律规则中表现出来的自由意志,这些规则调整着它们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共同的目的。不能推断出对国家的独立是有所限制的。”在缺乏明确的禁止性规范时,“每个国家仍然可以自由地采纳其认为最佳、最适合的原则。”(23)“The Lotus Case”, Publications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Series A.-No.70, 1927, p.19.无论中国的南海断续线还是美国主张大陆架的“杜鲁门公告”的法律效力都应该以此来衡量。
(2)中国公布南海断续线时没有侵害周边各国的海洋权利
当然,国家行为合法性还有第二个层面的内容,即基于自由意志的国家行为不能损害他国的权利。以时际法学说来检验,南海断续线在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没有损害周边国家的权利。南海断续线公布之时,海洋空间秩序中只有领海与公海两部分构成,并无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制度。1949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有一份调查报告,其对海洋法状况的概括就只有领海和公海两部分。(24)Surve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Relation to the Work of Codif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A/CN.4/1/Rev.1), pp.38-44.毗连区制度要到1958年的《领海及毗连区公约》才正式建立起来,专属经济区概念在第三次海洋法大会中才产生,到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才最终确立。中国政府公布南海断续线时海洋法中没有确定的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制度。当时的一般习惯国际法是各国有权拥有3海里宽的领海,(25)1950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弗兰索瓦(J.P.A.Francois)起草的《公海制度》提到普遍的3海里领海宽度。See Rapport de J.P.A.Francois, “Regime of the High Seas”, Document A/CN.4/17, in United Nation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950,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p.46-47。1952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起草领海宽度的条款规定各国可以主张不超过6海里的领海。(26)United Nations,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952,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58, Vol.II, p.26.当然,鉴于50年代联合国启动了海洋法的编纂工作,各国的领海宽度主张有些变化,从3海里到12海里不等。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断续线完全远离周边各国当时根据习惯国际法所拥有的领海的外部界限。
例如,菲律宾在2014年3月30日提交的“南海仲裁”诉状第二卷附图4.1显示,断续线靠近菲律宾的4段线中,从北至南,第一段距离菲律宾为42海里,第二段距离菲律宾为39海里,第三段距离菲律宾为34海里,第四段距离菲律宾为36海里。而菲律宾长期并没有公布领海宽度,而1961年的领海基线法也没有宣布其领海宽度。(27)参见陈鸿瑜编译:《东南亚各国海域法律及条约汇编》,(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1997年版,第69-71页。菲律宾对领海宽度没有固定立场,根据所谓殖民地条约涉及范围的变化而变化,(28)Lowell B.Bautista, “Philippine Territorial Boundaries: Internal Tensions, Colonial Baggage, Ambivalent, Conformity”, JATI-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16, Issue 1, 2011, p.41.甚至主张可以超过12海里,(29)1956年5月4日讨论“公海及领海制度”(Regime of the High Seas and of the Territorial Sea)时菲律宾对第3条“领海宽度”表达了这样的立场。参见United Nation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956, Vol.II, p.23。然而按照国际法一般为3~12海里的规则,菲律宾享有的领海宽度不应该超过12海里。2009年菲律宾通过“菲律宾群岛基线法”(Republic Act No.9522)确定了菲律宾的群岛基线,根据其精神,菲律宾将领海基线、群岛基线统一起来,但没有明确领海宽度。直到2014年12月菲律宾众议院通过了“菲律宾海域法”(Philippines Maritime Zones Act,House Bill 4889),规定领海宽度从群岛基线起12海里,不过该法案还未走完立法程序,到2019年1月为止菲律宾参议院尚未通过。(30)参见该法案的本文:“菲律宾海洋区域法”[An Act to Define the Maritime Zones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S.No.93)],http://www.senate.gov.ph/lisdata/2350620109!.pdf;其立法状态参见菲律宾参议院网站,http://www.senate.gov.ph/lis/bill_res.aspx?congress=17&q=SBN-93,访问时间:2019年1月20日。
同样,断续线靠近越南的第一段距离越南陆地领土为59海里、距离越南最近的岛屿为36海里。此外,断续线距离印度尼西亚、文莱、马来西亚的陆地领土或离岸岛屿的距离都超过至少24海里。(31)美国于2014年12月出台的第143号《海洋界限: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对南海断续线中的若干段到相关国家大陆、最近岛屿的距离做了大致的估计,其中距离马来西亚最近的一段断续线也有24海里。“Limits in the Seas”No.143, “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ct.21, 2016,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34936.pdf。而有关其他南海周边国家的领海宽度的立法情况分别为:文莱于1982年公布领海法,宣布其领海为12海里;印度尼西亚于1960年宣布领海为12海里;马来西亚于1969年公布12海里的领海;越南于1977年公布12海里的领海。(32)参见陈鸿瑜编译:《东南亚各国海域法律及条约汇编》,(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1997年版,第23-25页。
因此,无论是按照较早的3海里还是按照后来的12海里衡量,中国公布南海断续线的当时并没有侵害周边各国的海洋利益。南海周边国家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其保持沉默,合理的解释是断续线同周边国家当时及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海洋权利并不冲突。
2.3 国际社会对南海断续线的沉默、容忍的法律效果
(1)国际社会对南海断续线之容忍、默许的法律效果
虽然周边国家如越南、菲律宾在1970年代主张南海部分岛屿的主权,但并未质疑南海断续线。菲律宾在1978年通过了“菲律宾总统第1599号令设立专属经济区及其他目的”,其中规定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宽度为200海里。(33)同③,第24-25、40-60页。鉴于菲律宾明知中国的南海断续线早就存在,按照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范围计算,它必然与中国的南海断续线冲突,但在2009年之前,菲律宾没有质疑南海断续线。(34)See Memorial of the Philippines, Vol.I, para.3.26-3.30.菲律宾签署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也未见抗议南海断续线。(35)同③,第72页。直到2009年南海争端发生后,周边国家,尤其是菲律宾才质疑它,时间已经过了60余年。
菲律宾在2010年才意识到不对断续线进行抗议将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质疑断续线的合法性。(36)菲律宾首次质疑南海断续线的时间应为2010年12月7日,菲律宾向中国驻马尼拉使团副公使埋怨,中国的九段线侵害了菲律宾的“领土及海洋区域”(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zones)。See Memorial of the Philippines, Vol.I, para.3.41.但质疑整个断续线的效力,则是2012年11月。See Memorial of the Philippines, Vol.I, para.3.56.2010年12月7日,菲律宾这样向中国解释自己抗议断续线的原因:“如果菲律宾对中国主张的九段线不作出正式反应,将受到对中国主张保持沉默的指责。正因为如此,菲律宾和其他国家迫切需要在该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免他们的行为被解释为对九段线构成默许。”(37)Memorial of the Philippines, Vol.IV, Annex 66.然而,过了六十年后才做出反应,时间上太晚了。在“陆地、岛屿和海上边界争端案”(萨尔瓦多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参加诉讼)一案中,针对萨尔瓦多从1916年开始对“梅安格拉岛”(Meanguera)行使主权、而洪都拉斯于1991年才首次进行抗议的事实,国际法院这样认定该事实的法律后果:“分庭考虑到,萨瓦多尔长时间的行使主权之后,洪都拉斯才发起的这次抗议太晚了,无法影响洪都拉斯方面默认的推定。洪都拉斯对早期‘有效占领’的行为显示了对状况的某种形式的默示同意。”(38)Land, Island and Maritime Frontier Dispute (El Salvadow vs.Honduras)Judgment, I.C.J.Report 1992, p.577.南海周边国家的行为与该案中洪都拉斯相同——前者长时间未反对可以构成对南海断续线的默许。(39)邹克渊教授认为南海断续线没有被国际社会,尤其是南海周边国家广泛承认。参见“The South China Sea”, in Donald R.Rothwell,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he Se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635。从明示承认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如此。但是在国际法中,承认可分为明示、默许两种,默许也构成承认。参见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in the Gulf of Maine Area (Canada/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C.J.Report 1984, p.305 (para 130);Jack Wass, “Jurisdiction by Estoppel and Acquiescence in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ume 86, 2016, pp.155-195。长久以来周边国家没有对南海断续线进行抗议可以构成默许。参见贾宇:“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第194-195页;傅崐成著:《海洋管理的法律问题》,文笙书局,2003年版,第518页;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 “The Nine-Dash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istory, Status, and Implic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07, No.1, 2013, p.116。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南海周边国家的前任殖民宗主国家对南海断续线是承认的,至少在其正式出版的地图采纳了中国的主张,(40)参见贾宇:“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第194页。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断续线的普遍接受。
上述事实表明,国际社会长时间内对南海断续线持容忍态度,而这种容忍在国际法上会产生积极的法律效果——南海断续线没有违反国际法,中国因此而享有南海断续线的存在所带来的利益。支持该立场的类似案例是1951年的“渔业案”(英国诉挪威),国际法院在判决中表明国际社会对一项单方行为的长期容忍能够使做出此项行为的国家获益,这对于理解南海断续线是颇有启发意义的。在该案中,挪威的领海基线画法不符合当时国际法,但它存在了近60年,国际法院注意到在此期间没有外国表示反对,包括英国,所以这种领海基线制度应当享有国际社会的容忍所带来的益处。在争端产生之前,挪威的领海基线已经由连续而充分的长期实践所巩固,外国政府面对这种挪威的长期国家实践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它们并不认为挪威的实践与国际法相冲突。最后国际法院认定挪威的国内立法没有违背国际法。(41)Fishery Case (U.K.vs.Norway), Judgment, I.C.J.Report, 1951, pp.138-139, 143.
(2)断续线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历时性与共时性
国际法后续的发展是否仍然能支持断续线的合法性?在南海争端中,比较吸引眼球的是将断续线与周边各国专属经济区主张的外部界限重叠在同一张图上,(42)Memorial of the Philippines, Vol.I, para.2.7的附图2.4、para.2.13的附图2.5。《美国国际法杂志》2013年第1期也附了一张类似的图,将不同期间的所有南海主张共时性地重叠在一张地图上。See Lori Fisler Damrosch and Bernard H.Oxman, “Agora: The South China Sea: Editors’Introduc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07, No.1, 2013, p.96.试图表明断续线属于违法的海洋主张,侵害了周边各国的海洋权益。实际上,公布南海断续线与其他国家建立专属经济区制度属于历时性(diachronic)的主权行为——两类行为在不同的时期先后发生,但这类图解却暗示二者是共时性(synchronic)行为——认为中国的南海主张与周边其他国家的海洋主张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期间同一时期提出的,结果是以公约规定来否认前者的合法性。南海周边一些国家正是以此方式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评估断续线的效力。然而,按照时际法原则,评估断续线合法性应根据公布断续线时的国际法,在本质上这就是一种历时性的方法。如果从历时性的法律视角来考察,断续线并没有因海洋法的发展而丧失合法性,情况正相反。
2012年11月,针对中国在护照中植入南海断续线一事,菲律宾抗议说:“菲律宾强烈抗议在护照中植入覆盖了明显属于菲律宾领土和海域之一部分的九段线。菲律宾不接受违反国际法而过度地主张海洋空间之九段线的有效性。”(43)Memorial of the Philippines, Vol.I, para.3.56.有两个事实需要注意。第一,1948年中国公布南海断续线的时候,菲律宾在南海没有领土主张,其对南沙群岛中某些岛屿的主权要求最早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所以断续线根本没有覆盖任何菲律宾领土。如果把南海断续线视为岛屿归属线,菲律宾在断续线内主张岛礁领土主权是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而非相反。第二,根据习惯国际法,1948年中国公布断续线时菲律宾的海洋空间有3海里,最多不超过12海里,断续线距离菲律宾群岛海岸至少有34~42海里的距离,完全没有覆盖菲律宾的所谓海域,也未与菲律宾的领海有重叠。而且,根据菲律宾总统第1599号令设立专属经济区的时间1978年,这意味着菲律宾产生专属经济区的时间为1978年,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才能说中国南海断续线覆盖了所谓的菲律宾的海域。然而,到1978年,断续线已经存在了30年。此后菲律宾也未提出抗议,又过了30余年后的2010年才明确表示不接受断续线的效力。退一步讲,即使断续线与1978年后产生的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冲突,但从1978年到2010年之间30余年中菲律宾也未抗议。
菲律宾对南海断续线的态度并非特例,是南海周边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印度尼西亚于1980年3月建立专属经济区、马来西亚于1984年建立专属经济区、泰国于1981年建立专属经济区、新加坡于1980年宣布建立专属经济区、越南于1977年宣布建立专属经济区、柬埔寨于1978年建立专属经济区。南海周边一些国家明显知道200海里范围的专属经济区必定与早已存在的断续线冲突,这些国家在当时无一例外地未对断续线提出质疑。就南海断续线而言,这意味着各国公布专属经济区制度之后中国又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坚持行使主权长达近30年时间。这说明,二战后海洋法的发展并未使断续线自动归于无效。
中国在长达近60年的时期内公开、不受干扰地行使主权去主张南海断续线,它已经在南海形成了事物现状的一部分,足以创设一种稳定的、合法的南海空间秩序。
2.4 菲律宾的“条约界线”主张及后来立场的修正、放弃及法律后果
菲律宾较长一段时间内主张一种所谓“菲律宾条约界线”(Philippine Treaty Limits),即1898年美国-西班牙的《巴黎条约》、1900年美国-西班牙的《华盛顿条约》、1930年的美国-英国《菲律宾与北婆罗洲疆界公约》这三个条约所构成的范围。(44)Lowell B.Bautista,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Legal Basis of the Philippine Treaty Limits”, Asian-Pacific Law & Policy Journal, Vol.10 , No.1, 2008, p.25.这是一种与中国南海断续线有竞争关系的主张。1955年菲律宾初次向联合国秘书长笼统地提出各殖民条约“所述的界线内的其他水域,都被视为菲律宾的海上领土水域”。(45)陈鸿瑜编译:《东南亚各国海域法律及条约汇编》,(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1997年版,第38页。1961年菲律宾领海基线法规定“鉴于上述诸条约所规定的疆界内之水域,经常都被视为菲律宾群岛领土之一部分”,“鉴于环绕、介于或连结菲律宾群岛各岛屿之间的所有水域,无论其宽度或大小面积,经常被认为是陆地领土之必要附属部分,构成菲律宾内陆(inland)或内部水域之一部分。”(46)《菲律宾共和国第3046号法案——界定菲律宾领海基线法案》,陈鸿瑜编译:《东南亚各国海域法律及条约汇编》,(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1997年版,第40页。根据菲律宾的主张,“菲律宾条约界线”构成了菲律宾的领土界限,(47)Lowell B.Bautista, “Philippine Territorial Boundaries: Internal Tensions, Colonial Baggage, Ambivalent, Conformity”, JATI-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16, December, 2011, p.7.条约界线以内的水域由领海和内水两部分组成,但菲律宾对内水与群岛水域没有作区分。
菲律宾的海洋主张是其独特的“条约界线”概念与相关海洋法概念的一种混合物,很早就引起一些国家的疑问。1961年菲律宾领海基线法刚一出台,1961年5月18日美国就通过外交照会表示不认同特殊群岛概念以及菲律宾对1898年《巴黎条约》条款的解释。针对1968年9月18日菲律宾修订1961年领海基线法案,美国于1969年3月16日的照会中提出了类似抗议。(48)J.Ashley Roach and Robert W.Smith, United States Responses to 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 Naval War College, 1994, p.134, Footnote No.18, p.139.1982年菲律宾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表示“群岛水域概念是类似于菲律宾宪法所规定的内水概念,连结这些水域与经济区或公海的海峡,外国船只不能以国际航行为理由而享有过境通行权”,(49)同②,第73页。1984年提交条约批准书也表示了相同的意思,对此美国于1986年明确抗议,(50)J.Ashley Roach and Robert W.Smith, United States Responses to 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 Naval War College, 1994, pp.137-138.提出抗议的还有澳大利亚、保加利亚、白俄罗斯、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苏联。(51)Lowell B.Bautista, “Philippine Territorial Boundaries: Internal Tensions, Colonial Baggage, Ambivalent Conformity”, JATI-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16, December, 2011, p.44.菲律宾于1988年声明承诺“菲律宾政府有意调和其国内立法与海洋法公约之规定”。(52)陈鸿瑜编译:《东南亚各国海域法律及条约汇编》,(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1997年版,第75页。直到2009年,菲律宾才通过“菲律宾群岛基线法”(Republic Act No.9522)确定了菲律宾的群岛基线,对1961年的第3026号“领海基线法案”、1968年的第5446号“领海基线法修正法案”进行了修正。(53)An Act to Amend Certain Provisions of Republic Act No.3046, As Amended By Republic Act No.5446, to Define the Archipelagic Baselines of the Philippin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Republic Act No.9522), http://senate.gov.ph/republic_acts/RA%209522.pdf.但该法案并没有明确群岛基线内的水域的法律地位是内水还是群岛水域,也没有明确其领海宽度。菲律宾最高法院在一个有关“菲律宾群岛基线法”案件的判决中提到,菲律宾对群岛基线以内的水域行使主权需受国际法中无害通过、群岛海道通过权的限制。按照菲律宾的解释,这一切使得菲律宾的国内立法要符合海洋法公约。(54)Memorial of the Philippines, Vol.I, para.4.78.正待通过的“菲律宾海域法”第2节“海域”(Maritime Zones)将群岛基线内的水域进一步区分为内水、群岛水域、领海等海域,这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相一致。(55)See “Philippines Maritime Zones Act”, Section 2, http://www.senate.gov.ph/lisdata/2156718334!.pdf.
由此看来,菲律宾对原有立场有所修正、放弃。菲律宾关于领海、专属经济区、群岛水域之立场、其国内法的变化会带来一些国际法上的后果。首先,无论菲律宾“条约界线”概念在法律上有什么可以辩解的余地,(56)同②, pp.42-43, 46.但菲律宾修改国内法、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其海洋权利基础,这意味着彻底放弃了长期以来主张的“条约线”。按照菲律宾政府所认可的其国内最高法院的立场,菲律宾将信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义务,其专属经济区将依托于2009年的群岛基线,也将回归到公约规定的不超过12海里宽度。(57)Memorial of the Philippines, Vol.I, para.3.12.至此,1898年《巴黎条约》第三条涉及的范围再也不能成为菲律宾主张海洋权利的基础。第二,这种变化导致在2009年前菲律宾依托“条约界线”的海洋主张归于无效,至少可以回溯到1955年菲律宾首次提出条约线概念之时。这样菲律宾再也不能以所谓“条约线”来主张中国的南海断续线侵害了菲律宾的海洋权利。第三,菲律宾2009年的“菲律宾群岛基线法”、“菲律宾海域法”统一了菲律宾的群岛基线,其领海、专属经济区的宽度完全依赖该基线,(58)“菲律宾海域法”中关于领海、专属经济区的范围的条款分别为第6节、第8节。该法案第3节明确本法案的基线指2009年的“菲律宾群岛基线法”(Republic Act No.9522)中的群岛基线。这意味着菲律宾主张的领海宽度、专属经济区的外部界限至少到2009年才最后明确。第四,菲律宾的海洋主张前后不一,有些混乱不堪,自它在20个世纪50年代第一次海洋法大会上公开有关领海范围的立场后就引起国际社会的异议,到2014年菲律宾提起南海仲裁时,它自己也断定此前的海洋主张不符合海洋法,(59)Memorial of the Philippines, Vol.I, para.4.76-4.77.因此它不能以此前被放弃的、自己承认不符合国际法的主张来对抗中国的主张。
菲律宾改变自己的立场,以海洋法公约作为自己的海洋权利的基础,这是其行使主权的选择。中国坚持断续线也是合法行使主权的行为。自中国的南海断续线公布之后,中国一直没有以后续海洋法的发展结果作为其断续线的法律基础,相反,中国认为海洋法的发展不能危害中国已经合法享有的在先的权利,至少到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时这类在先的权利已经牢固地建立了。这一立场是自始至终的,从未改变。菲律宾改变自己的立场并非削弱了中国的主张,而是强化了南海断续线长期存在并未侵害周边邻国的海洋权益的事实。
2.5 断续线:赋权性事实产生的南海空间秩序标记
上面已经清楚地表明,1948年中国公布断续线的时候,并无国际法禁止那样做,也没有侵害任何周边国家的合法权利,长期以来也没有来自周边国家的抗议,在此后海洋法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周边国家也对此无动于衷。这些事实不可避免地产生国际法上的合法性效果。简而言之,中国政府在南海断续线方面持续、和平的国家行为构成了中国在南海的“权源”(title)。(60)长期以来“title”被翻译为“所有权”,在中文语境中“所有权”表达的是权利的具体内容,与其“赋权性的事实”的本意有差距。近来清华大学贾兵兵教授翻译为“权源”,本文从之。至于“historic title”,本文遵从惯例,仍用“历史性所有权”来表示,“title to territory”仍用“领土所有权”的惯常用法。权源的法律含义指“赋权性事实”(vestitive facts)、且“法律承认该事实能创设权利”。(61)R.Y.Jennings, The Acquisition of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3, p.4.在普通法法系颇有权威性的教科书《萨尔蒙德论法理学》中这样阐述权源与权利的关系:“每一种权利(用含义更广的词语,包括特权、权力、豁免)都涉及一种权源或权利赖以产生的渊源。‘权源’为事实性前提(the de facto antecedent),权利乃该前提的法律效果(the de jure consequent)。如果法律将一项权利赋予一个人而非另一个人,原因在于某些事实于他为真、于另一人则否,这些事实就是权利的权源(title of the right)。”“无论权利是原生性的(inborn)还是继受性的(acquired),都需要权源作为必要前提。”(62)John W.Salmond, Jurisprudence, 8th edi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Limited, 1930, p.357.“权源”概念在国际法中常常被类比于权利,尤其是领土取得,(63)See H.Lauterpacht, Private Law Sources and Analogies of International Law, Union: Lawbook Exchange, Lit., 2002, p.104.其含义几乎与国内法相同:“从法律上讲,权源这一术语是指所有的事实、行为、或情势,它们构成一项权利的原因或基础。”(64)J.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12.
支持中国可以合法依赖断续线的有效法律框架是历史性所有权(historic title)概念。同权源的要素一样,历史性所有权概念同样由事实性前提、法律效果组成,这里的事实性前提由长期存在的历史事实构成,具体指“有关国家持续和有效地行使政府权力、其他国家的默认”这类历史事实。(65)See Andera Gioia, “Historic Titles”, in R.Wolfrum, ed.,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IV,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822.中国可依赖的历史性所有权的结构表现为:中国长期、持续、和平的主权行为构成了创设权利的事实性前提,即赋权性事实,中国由此而享有的权利乃是这种事实性前提的法律效果。中国在南海可依赖的历史性所有权有两个方面的内容。首要的内容是中国长期对南海诸岛和平、有效地行使主权的行为可以构成中国对南海诸岛的领土所有权(title to territory),历史性所有权提供了补充性支持,中国学者已有充分论述,(66)See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 “The Nine-Dash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istory, Status, and Implic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07, No.1, 2013, p.114.此处不再赘述。第二,同等重要的是,公布、主张和维护南海断续线的持续性国家行为本身也属于赋权性事实、构成了历史性所有权中的事实性前提。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已有先例。在“渔业案”(英国诉挪威)案中,挪威长期单方适用直线基线的行为而英国等国家长期不置可否的态度构成了挪威可依赖的历史性所有权,产生了有利于挪威的权利,这一点获得国际法院的认可。(67)See Fisheries case (United Kingdom v.Norway), I.C.J.Reports 1951, pp.138-139.这一事实性前提对中国产生的积极法律效果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是从空间分配的宏观视角来看,它构成特殊的海洋占有模式,属于空间分配范畴,断续线具有标定空间边界的功能。中国的海洋空间与周边国家的海洋空间之间的边界、范围正是通过断续线来识别的。第二是从具体的权利内容来看,它意味着中国对空间的支配、继而也支配其中的自然资源开发,同时也构成传统捕鱼权、开发生物资源权一类的历史性权利线。历史性权利(historic rights)的本质在于此类权利的权源同样基于某些历史因素形成的赋权性事实。中国在南海断续线内水域享有相关历史性权利,这一点中国政府已经多次强调。(68)中国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明确指出中国在南海享有历史性权利。另参见贾宇:“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第179-203页;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 “The Nine-Dash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istory, Status, and Implic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07, No.1, 2013, p.114。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断续线长期的合法存在本身构成了中国可依赖的历史性所有权,这应当同中国在南海断续线以内享有捕鱼等历史性权利区别开来。
断续线对于南海空间秩序的特殊意义在于,倘若没有它,南海争端就是一般性的领土争端、海洋法下的划界争端。因为断续线长期合法的存在,南海已经形成了在先的且不同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存在法律秩序。下面将说明南海空间秩序是一种虽然与海洋法有相关性,但又不同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特殊制度,为一般国际法所允许。
三、南海空间秩序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南海争端本质上是两种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第一种主要是中国所主张的南海空间秩序,第二种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塑造的海洋秩序。二者之间可能具有这样的关系: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属于一般法,而南海空间秩序属于特别法。南海空间秩序作为一种特别制度,它在下述两个方面都成立。
3.1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外的特别法
南海断续线所标记的空间秩序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非处理同一事项,因此二者是两种空间秩序类型,不是同一法律体系下的一般与特别关系,因为特别法“仅适用于有关具体规定和一般规定均处理同一实质性问题的情况”。(69)Gerald Fitzmaurice,“The Law and Proced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1951-4: Treaty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Treaty Points”,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3,1957,p.237.南海争端的核心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南海诸岛领土主权、与该领土主权密不可分的断续线,二者构成陆地和海洋秩序的统一体。虽然断续线最初的产生与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有关,但之后持续、和平的存在就使它产生了相对独立的法律效果,即成为一种空间秩序的边界标记。南海争端就不是一个简单地依据陆地主权确定海洋权益、在基础上进行海洋划界的问题,因为南海断续线在效果上同样是分配海洋空间,与海洋法公约下的划界不属于同一事项。虽然断续线具有空间分配所产生的边界效果,但它并不是一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海洋划界的直接产物。
3.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内的特别法
即使认为南海断续线所标记的空间秩序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处理同一实质问题,但南海空间秩序也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特别制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并非排斥特殊情况,相反留下了容纳特殊情况的余地。例如,公约第15条关于领海划界就准许特殊情况的存在:“但如因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而有必要按照与上述规定不同的方法划定两国领海的界限,则不适用上述规定。”其中,历史性所有权与其他特殊情况(other special circumstances)并列,二者都属于特殊情况的范畴。该条所准许的特殊情况导致领海范围的确定可以不遵循“等距离线”。公约第298条1(a)(1)还一般性地规定了涉及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所有权的争端可以被排除在争端解决程序之外。这意味着存在某种依赖历史性所有权来确定海洋边界的方法,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种可能性。(70)See Natalie Klein,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49-253.
结合公约第15条、第298条所规定的例外状况,这样解释有关南海的法律状态实更具有合理性:在南海空间秩序构成要素中,南海断续线本身就是一种特殊情况。由马尔蒂·科斯肯涅米定稿的国际法委员会研究组的报告《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认为历史性所有权构成特别法:“基于有效占领(effectivités)的论据,和基于禁止反言规定(如“隆瑞寺案”)以及历史性所有权(如“英国诉挪威渔业案”)的论据一样,都类似于特别法。它们的目的也是力求使法律对特定情况做出回应。通过指出相关事实,它们还建立一种非正式等级关系(informal hierarchies),寻求将特殊情况与其一般性(和正式)的背景区分开来……”。(71)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UN Doc.A/CN.4/L.682, para.107.
中国公布并不断强化的南海断续线、周边国家对此的默认构成了中国可以依赖的历史性所有权,其相关事实的特殊情况在于断续线本身与岛礁一起使得南海的空间秩序迥异于其他海域,所指涉的范围远远超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5条所指的领海划界。具体而言,第298条中的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所有权争端与公约第15条、74条、83条的划界争端放在一起,表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承认历史性所有权争端实际上是可能存在的,这也暗示基于历史性所有权对海洋空间的分配原则可能不同于第15条、74条、83条的划界原则。南海断续线的情况正是如此。
四、结 论
断续线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划界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空间秩序边界标记方式。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一般性海洋空间秩序模式可以描述为:陆地地理状况决定领海基线/群岛基线;应享海洋空间的起讫点是基线;相邻或相向国家可能要通过划界来分配海洋空间。这就是确定海洋空间秩序的一般背景。同这种一般背景相区分的特殊情况是南海断续线本身就具有分配海洋空间的功能。它的特殊之处在于不是以领海基线作为起讫点来确定应享的海洋空间,而且它先于二战之后发展起来并定型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制度而存在。第二,断续线与海洋划界的法律基础各有不同。断续线的法律基础在于中国长期实施的国际法不加禁止的合法主权行为本身,同时禁止反言、默许构成的承认、历史性所有权等国际法原则提供了充分的支持。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海洋划界概念的法律基础在于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概念,其中,大陆架概念又建立在陆地领土自然延伸与邻接概念上,而领海、专属经济区概念则基于纯粹距离概念(分别为12海里、200海里)和邻接概念(从确定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中国当时公布南海断续线并不是基于划定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外部界限这样的考虑,尽管确有隐含的距离因素考虑。
从权利关系来看,断续线所标记的南海空间秩序的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1)中国对南海空间支配权的排它性。在时间顺序上,南海空间秩序的确立先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海洋空间秩序。在权利顺序上,支配空间则支配其中的自然资源开发,基于这一原则,中国支配了南海空间则支配了其中的资源开发和利用。这是断续线赋予中国最大的权益,离开这种基础,南海争端不过就是单纯的岛礁主权之争。(2)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利关系。既然断续线赋予中国对南海空间的排他性支配权,那么可以初步推定其他国家在断续线内海域中并无权利,但这与17世纪持“闭海论”的英国对所谓不列颠海的权利主张不同。当时英国除了主张对渔业享有独占权外,还主张对周边海洋航线的支配与控制,这导致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英国要求在英吉利海峡航行的外国船只行降旗礼,这是英国表达对海洋拥有支配权的象征。(72)See Thomas Wemyss Fulton,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ea, Lawbook Exchange, Ltd., 2010, pp.3, 11.但中国在公布断续线的一开始就没有对南海的航行施加任何限制,也没有试图去规制它,作为通行意义上的航行权完全保留给国际社会。但是这不包括与开发自然资源密切相关的航行活动,因为这种航行仍然要受中国对开发自然资源的权利主张与政策的限制。
中国一直坚持通过谈判解决岛礁主权归属、然后达成海洋划界协定来最终解决南海争端。(73)国新办:《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2016年7月13日,第44页。中国的核心立场是南海各群岛应当作为整体来对待并以此作为解决领土争端和海洋划界的基础。不过,国际法并不强制国家必须解决争端,国家并不负有彻底解决国际争端的结果义务。《联合国宪章》第二条(3)及习惯国际法要求和平解决,但该原则对国家施加的义务性质属于行为义务,而非结果义务,(74)See Bruno Simma, et al, ed.,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 Commentary, 3r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90-191.因此只要确保争端解决的过程是和平的,就符合国际法的要求。在南海争端上,只要不与所承担的国际法义务相冲突,任何一方都可以合法地不寻求争端解决的结果,而是保持现状。中国一直提倡“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是南海区域合作的指导性原则,它有望“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为最终解决争议创造条件”。(75)同①,第4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