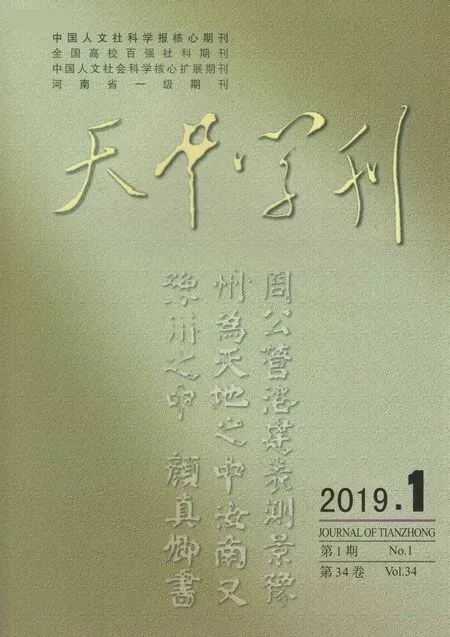金圣叹批评《西厢记》的戏剧文法理论及当代意义
韦强
金圣叹批评《西厢记》的戏剧文法理论及当代意义
韦强
(湖南工业大学 文新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是中国戏曲评点史上的名著,其中提出了多种戏剧写作的文法理论,包括“烘云托月”“移堂就树”“月下回廊”“羯鼓解秽”“一生一扫”“三渐三得”“二近三纵”等作文理法。这些文法虽然使用的是比喻、意象的语汇,但其揭示的戏剧创作原理极具科学性,对于戏剧角色分配、行文节奏、情节设计都具有指导价值,对于当代戏剧创作亦具有借鉴意义。
金圣叹;西厢记;文法理论;当代意义
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是中国戏曲评点史上的名著。金圣叹在其中不仅阐发了大量富有卓见的理论思想与文论观念,同样提出了多种文章与戏剧写作的创作文法理论。针对《西厢记》的角色设置、行文写作、结构布局,金圣叹总结提出了“烘云托月”“移堂就树”“月下回廊”“羯鼓解秽”“一生一扫”“三渐三得”等作文理法。这些总结与分析不仅更为明晰地阐述了《西厢记》的经典所在,对于戏剧创作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烘云托月”之法
金圣叹评点《西厢记》,每折之前都有总评,正是在总评之中,他阐析了诸多文法技巧。在第一折“惊艳”的总评中,金圣叹提出了著名的“烘云托月”之法:
亦尝观于“烘云托月”之法乎?欲画月也,月不可画,因而画云。画云者,意不在于云也;意不在于云者,意固在于月也……然试实究作者之本情,岂非独为月,全不为云?云之与月,正是一副神理,合之固不可得而合,而分之乃决不可得而分乎![1]893
“烘云托月”本是中国水墨画常用的一种方式,指月亮不容易画,所以不画月而画云,把云画的得当之后,月就自然而然地衬托而出。然而金圣叹却将其借鉴到戏剧写作之中,明确提出“烘云托月”的概念。金圣叹评点《西厢记》所指“烘云托月”之法中的“月”指莺莺,“云”指张生:
《西厢》第一折之写张生也是已。《西厢》之作也,专为双文也。然双文国艳也,国艳则非多买胭脂之所而涂泽也。抑双文天人也,天人则非下土蝼蚁工匠之所得而增减雕塑也。将写双文,而写之不得,因置双文勿写而先写张生者,所谓画家“烘云托月”之秘法。[1]894
在金圣叹看来,《西厢记》的主角是莺莺,因此其他人物的创作均是为了衬托莺莺。然而《西厢记》的开篇,却是优先描写张生。金圣叹认为,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莺莺乃是相国小姐,不仅身份高贵,又倾国倾城,直接把才貌俱佳的莺莺描画出来,具有相当高的难度,于是为了更好地刻画莺莺,只可先描写张生,而且要把张生写成才华横溢、谦谦有礼的君子,以衬托出莺莺的美艳动人。所以,《西厢记》第一折重点描绘张生,是为了用张生这个“云”,烘托莺莺这个“月”。
“烘云托月”之法,与现代修辞中的衬托相类,吴士文《修辞讲话》就直接把“烘云托月”“简称‘衬托’”[2]。然而,“烘云托月”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衬托修辞。因为金氏所谓“烘云托月”,其实也涉及一个戏剧主角的问题。《西厢记》是一部多主角的作品,剧中的主角有莺莺、红娘、张生三位。但第一主角是谁,历来众说纷纭,李渔认为张生是第一主角,蒋星煜等现代学者则认为莺莺是第一主角。在金圣叹看来,莺莺是没有疑义的第一主角,所以莺莺是“月”,张生是“云”。但同时,他又强调:“云之与月,正是一副神理,合之固不可得而合,而分之乃决不可得而分乎!”[1]894这实际上指出,虽然戏剧需要明确一个第一主角,但“主角”不是“独角”,第一主角和其他主角乃至配角也要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这就为戏剧写作的角色分配提出了要求:一部戏剧,必须明确一位第一主角,戏剧的故事内容、情节冲突都必须以其为中心,其他角色的设计、发展也必须首先服务于第一主角的角色塑造,如此才能使得一部戏剧不会“群龙无首”,并最终使戏剧作品的第一主角突出。但是,如果一部戏剧仅突出一个主角,那么这部作品无疑容易陷入单调。所以,主角同时也必须兼顾其他角色,尤其是在有多个主角的戏剧中,第一主角在享受其他主角衬托的同时,也要反过来照应其他角色,让其他角色也有血有肉,个性丰满。只有这样,才能给读者留下多个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
二、“移堂就树”“月下回廊”“羯鼓解秽”之法
第五折“寺警”是《西厢记》的高潮之一,写孙飞虎围困普救寺欲要霸抢莺莺,张生此时挺身而出书信解围,老夫人被迫答应将莺莺许配张生。本来莺莺与张生之间的爱情并无可能,经此“寺警”却出现了重大转机。在“寺警”的总评里,金圣叹一共提出了三个文法理论。
第一个是“移堂就树”。金圣叹云:“文章有‘移堂就树’之法。如长夏读书,已得爽垲,而堂后有树,更多嘉荫。今欲弃此树于堂后,诚不如移此树来堂前。”[1]937想要得到树下嘉荫,但因为树是不可移动的,所以只能把堂屋移建于树后,则“诚相厥便宜,而移堂就树,则树固不动而堂已多荫,此真天下之至便也。”[1]937
“移堂就树”与《西厢记》和文学创作有什么关系呢?金圣叹云:
此言莺莺之于张生,前夜酬韵夜,本已默感于心;已又于闹斋日,复又明睹其人……忽然鼓掌应募,驰书破贼,乃正是此人。此时则虽欲矫情箝口,假不在意,其奚可得?……以见此一照眼之妙人,初非两廊下之无数无数人所可得而比。然而一则太君在前,不可得语也;二则僧众实繁,不可得语也;三则贼势方张,不可得语也。夫不可得语而竟不语,彼读书者至此,不将疑莺莺此时其视张生应募,不过一如他人应募,淡淡焉了不系于心乎?[1]937
金圣叹认为,《西厢记》的故事发展中,经过酬韵对诗以及道场相见,莺莺早对张生有了好感,经过张生书信解围,莺莺无疑更加爱慕张生。但由于当时在场人数众多,形势危急,不宜直接表现莺莺对张生的爱慕,于是《西厢记》采用“移堂就树”之法突出张生在莺莺心中的地位:
作者深悟文章旧有移堂就树之法,因特地于未闻警前,先作无限相关心语,写得张生已是莺莺心头之一滴血,喉头之一寸气,并心并胆、并身并命。殆至后文,则只须顺手一点,便将前文无限心语,隐隐都借过来。[1]937
在“寺警”的开篇,《西厢记》并不是直接写孙飞虎围寺之事,而是写莺莺逢春感怀,相思张生。“寺警”本是生死一线、情节紧张的关目,为什么先前要安排一段春思惆怅的舒缓情节?实际上,这个情节就是所谓的“堂”,而张生解围的情节,则是“树”。张生解围是全剧的主体情节,当莺莺与张生的关系陷入僵局时,必须出现这个情节来扭转剧情发展,因此它是“树”,是需要固定在一定时段或方位的,是不可轻易移动的。然而,莺莺思恋张生的情节并非全剧的主体情节,这种情节更多起到的是辅助作用与抒情效果烘托,不必在固定关目中插入,因此具有相对灵活性。如果把莺莺对景相思的情景安排在张生解围之后亦可,那时莺莺再思慕张生也并不为晚,但如果结合普救寺解围的情节来说,其效果远远不如将其安排在解围之前。因为解围之后再写莺莺相思,那么在解围之时,就只能表现张生为莺莺义无反顾,却无法表现莺莺对张生的情感态度。而如果将这个情节安排到解围之前,就更显出张生解围之时,非但自己心仪莺莺,莺莺亦早已心仪张生,故而是两情相悦,而不再是一厢情愿。如此,张生的解围也就更有意义。
加氢裂化装置有大量氢气及烃、非烃类等危险生产介质,泄漏的可燃性、爆炸性物料可能发生火灾和爆炸危险。由于加氢裂化装置反应部分在高压下操作,其爆炸、火灾事故的危害后果尤其严重;同时加氢裂化装置的静设备和动设备及催化剂等造价高,在操作过程中有被损坏的可能,会造成企业资产的严重损失。因此,加氢裂化装置生产过程出现异常时,必须采取可靠的措施,将异常工况控制在可控范围内,甚至停止生产以规避生产异常导致的人员、装备的重大损失。
所以“移堂就树”讨论的是情节走势的安排问题,它启发戏剧作者,情节的推进、铺展、排列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一定逻辑规律的。戏剧创作必须明确主体情节与事件(树),次要情节与事件(堂)需要围绕主体情节的需要来进行安排。如此一来,不仅能够增强主体情节与事件的表现力度,同时也使得次要情节自身更具有存在价值。
第二个是“月下回廊”。金圣叹云:
如仲春夜和,美人无眠,烧香捲帘子,玲珑待月。其时初昏,月始东升……又下度曲栏,然后渐渐度过间阶,然后度至锁窗,而后照美人……然而月之必由廊而栏、而阶、而窗、而后美人者,乃正是未照美人以前之无限如迤如逦,如隐如躍,别样妙境。非此即将极嫌此美人何故突然便在月下,为了无身分也。[1]938
所谓“月下回廊”,就是指行文需要循序渐进,做足铺垫,不可一蹴而就。金圣叹认为,莺莺在酬韵和闹斋之后,已有意于张生,但莺莺毕竟是千金小姐,不可唐突地表现自己的相思之情。因此为表现莺莺乃是并不会轻易爱上他人的矜持闺秀,所以“寺警”开篇的伤春情节,也是对莺莺爱上张生的铺垫。在写莺莺爱上张生的过程中,先写残春伤情,进而写到前夜酬韵之事,从而渐循渐进地表现莺莺对张生的爱慕,最终在寺警解围之后达到高潮。如此一来,不仅莺莺的形象得体,也为二人的恋情发展逻辑提供了合理性。
第三个是“羯鼓解秽”。金圣叹云:
如李三郎三月初三坐花萼楼下……上心至喜,命工作乐。是日恰值太常新制琴操成,名曰《空山无愁》之曲,上命对御奏之。每一段毕……天颜殊悒悒不得畅。既而将入第十一段,上遽跃起,口自传赦曰:“花奴,取羯鼓速来,我快欲解秽。”便自作《渔阳掺挝》,源源之声,一时栏中未开众花,顷刻尽开。[1]938
“羯鼓解秽”这一典故出自《羯鼓录》,记唐玄宗饮酒赏乐之时,感觉乐工所奏之乐索然无味,于是传令拿入羯鼓,自己奏曲,从而心情大好。意指在平淡、舒缓的行文之中,突然加入畅快、激烈的元素,从而加快行文节奏,取得平地起波澜的精彩效果。金圣叹提出“羯鼓解秽”,是针对“寺警”中传递求救书信的情节。因为按照行文常态,张生把书信写好之后,送信这个简单的事件本无太大的波澜可起,只要按部就班地书写某个和尚传书,杜将军来救即可。然而《西厢记》却又刻画了惠明的莽僧形象,使得平淡的行文之中另起波澜。所以,传书之事,就是《空山无愁》之曲,平淡无味;惠明之事,则是《渔阳掺挝》之曲,昂扬振奋,顿起精神,于平淡之中掀起波澜。
“月下回廊”和“羯鼓解秽”,论述的都是行文节奏的缓急问题。在某些情节中,行文需要缓缓渐进才能达到层层渲染、引人入胜的效果。而在有的情节中,行文则需要加快节奏,制造打破平淡、提振精神的效果。行文缓急兼备,才能使戏剧的情节发展富有节奏感,而有节奏感的作品才能使受众感到有滋有味。此于当代戏剧写作,无疑也是具有指导功用的。
三、“一生一扫”“三渐三得”“二近三纵”之法
第十二折“后候”的总评,金圣叹批评了晚明时期所作传奇,“例必用四十折”的风气,指出戏剧不在于固定的长度,而在于如何使结构富有变化、精巧合理、波折丛生。他针对《西厢记》,提出了“一生一扫”“三渐三得”“二近三纵”的行文之法。他首先论及“一生一扫”:
若夫《西厢》之为文一十六篇:有生有扫,生如生叶生花,扫如扫花扫叶……然则如《西厢》,何谓生?何谓扫?最前《惊艳》一篇谓之生,最后《哭宴》一篇谓之扫……此其最大之章法也,而后于其中间,则有此来、彼来。何谓此来?如《借厢》一篇是张生来,谓之此来;何谓彼来?如《酬韵》一篇是莺莺来,谓之彼来。[1]1028
此段文字论述的“一生一扫”,其实就是故事的开始和结束。金圣叹认为,戏剧所写的故事,必须在一定条件之下构成可以成为故事的条件,进而发展下去,不断丰富完善,并在该收尾时收尾,该结束时结束。第一折“惊艳”是写张生巧逢莺莺后一见钟情,是《西厢记》故事的源起,故而谓之“生”;第十五折“哭宴”是张生与莺莺已经确立恋爱关系,进京赶考,生、莺惜别,是《西厢记》故事的结束,故而谓之“扫”。其中,金圣叹又着重论述了“生”,即故事的生成。金圣叹指出,戏剧故事的生成是有逻辑的。若想表现莺、生之恋,首先就必须让男主角张生产生对莺莺的爱慕,于是《西厢记》描写了“借厢”情节,正是因为张生借住普救寺之西厢,才有了见到莺莺的机缘。同时,如果只有张生单恋莺莺,也无法发展二人的爱情,所以也必须设计情节让莺莺对张生产生好感,于是《西厢记》描写了“酬韵”,张生为莺莺吟诗,莺莺被张生的才情所打动。只有两个方面的要素都具备,《西厢记》的故事才能有逻辑地生成。而正是通过“借厢”与“酬韵”,《西厢记》的情节发展从两个方面向故事核心靠拢,构成了一个有序的逻辑推进:借厢→张生对莺莺一见钟情→莺、生恋爱←莺莺对张生产生好感←酬韵。所以,金圣叹所谓的“生”,并非简单地生成故事,而是要求故事的生成必须富有逻辑,符合常理。此外,金圣叹指出,不仅故事生成需有逻辑,故事的发展更需逻辑。于是,他又提出了“三渐三得”:
何谓三渐?《闹斋》第一渐,《寺警》第二渐,今此一篇《后候》第三渐。第一渐者,莺莺始见张生也;第二渐者,莺莺始与张生相关也;第三渐者,莺莺始许张生定情也。此三渐,又谓之三得。何谓三得?自非《闹斋》之一篇,则莺莺不得而见张生也;自非《寺警》之一篇,则莺莺不得而与张生相关也;自非《后候》之一篇,则莺莺不得而许张生定情也。[1]1029
“借厢”中张生对莺莺一见钟情,“酬韵”中莺莺钦慕张生才情,但毕竟只是二人互有好感,远远没有发展到真正相爱的程度。所以《西厢记》又通过“闹斋”“寺警”“后候”三折,层层递进地使二人的关系一步步升级、升温。“酬韵”中,莺莺只是对张生因诗生情,此前也仅仅是佛殿有过一面之缘,其实并未真正留意张生。直到“闹斋”一折,莺莺才算真正注意张生;“寺警”一折,张生为救莺莺挺身而出,二者才算真正发生命运上的关联;“后候”一折,二人私会云雨,终于真正确立爱情。这三折,每一折之间都富有逻辑关系,都是层层推进的:没有“闹斋”,莺、生始终没有真正相见,爱情也就无从源起;没有“寺警”,莺、生命运无法相连,爱情也就无从发展;没有“后候”,莺、生的爱情没有形式上的体现,爱情也就无从确立。所以,“三渐三得”就是指情节推进和故事发展都要富有逻辑地展开。
这三折是张生和莺莺关系逐层递进发展的过程,通过这三折,故事发展才有次序感和层次感,但是仅有次序感很容易流于直线与平淡。所以,圣叹进而提出“二近三纵”:
何谓二近?《请宴》一近,《前候》一近。盖“近”之为言,几几乎如将得之也。几几乎如将得之之为言,终于不得也。终于不得,二又为此几几乎如将得之之言者,文章起倒变动之法也。三纵者,《赖婚》一纵,《赖简》一纵,《拷艳》一纵。盖有近则有纵也,欲纵之故近之,亦欲近之故纵之。“纵”之为言,几几乎如将失之也。几几乎如将失之之为言,终于不失也。终于不失,而又为此几几乎如将失之之言者,文章起倒变动之法既已如彼,则必又如此也。[1]1030
按照普通的情节逻辑,莺、生之恋在经过“闹斋”“寺警”“后候”三折后,已经从相识、相知到相恋,此三折已经可以完成《西厢记》基本故事的叙述。然而,如此故事推进虽然富有逻辑,却使得故事发展过于平淡无奇,显然不具有矛盾性与冲突性,无法成为一部优秀剧作。于是,《西厢记》在“三渐三得”的基础上,又使用了“二近三纵”之法,在戏剧故事层层渐进的基础上,增加冲突和波折,使情节不流于平面和枯燥,达到“起倒变动”的效果。所谓“二近”,是指“请宴”“前候”两折,“三纵”是指“赖婚”“赖简”“拷艳”三折。“请宴”是张生退围之后,老夫人请宴感谢,由于此前老夫人许诺谁退贼兵谁娶莺莺,所以此次请宴本是莺、生喜结连理的第一次机会,然而在“赖婚”一折,老夫人临阵变卦,让二人美梦成空。老夫人变卦后,张生一病不起,于是在“前候”一折,莺莺委托红娘前去慰问。此次乃是莺莺表露心迹之机,张生亦写情简倾诉衷肠,此次本是二人彻底告白对方、确立爱情的又一次机会,最后却在“赖简”一折,莺莺因身份、礼教方面的顾虑最终退缩,二人的爱情进展再次停滞。“请宴”“前候”是写张生无限接近和莺莺结合,“赖婚”“赖简”是写在行将功成之时却最终未能如愿,每当读者或观众被激起二人结合的期待之心时,剧情的发展却又使他们的愿望落空。如此情节起落,无疑成功制造了引受众入剧的矛盾冲突。而在莺、生关系忽远忽近的矛盾中,最大的冲突即是“拷艳”。因为莺、生私会东窗事发,老夫人先拿红娘问罪,按照常理推断,老夫人惩罚红娘之后,必然要拆散莺莺与张生。然而,当剧情朝着莺莺、张生即将离散发展时,却再次出现转折,红娘凭借巧舌利口,劝服老夫人给莺、生一次机会,最终张生与莺莺的爱情又重获生机。所以所谓“二近三纵”,就是指张生和莺莺的爱情经历了“二起三落”:张生两次距离莺莺一步之遥时,都功亏一篑,最后一次以为彻底梦空时,却又生机陡现。正是在如此的波折起伏之中,《西厢记》才使本来平淡无奇的爱情发展变得富有故事性、戏剧性、矛盾性、冲突性。
“一生一扫”“三渐三得”“二近三纵”,指出了戏剧创作在情节铺展与故事开展中的两个基本要素:第一,戏剧情节与故事首先需要富有逻辑性的故事源起、推进与结束。故事的发端要有合理的起因,结局要与发端对应,故事的发展推进要符合逻辑推理与生活常理。第二,在保证基本逻辑的前提下,故事发展与情节推进需要设定若干矛盾、冲突、波折,从而使情节发展具有高潮与起伏。虽然戏剧写作需要波澜起伏的波折是一个剧作常识,但一部作品需要多少波折以及如何制造波折却没有定法。金圣叹提出的“二近三纵”则是一个相对科学的文法理念,它包括三个波折:围绕故事的中心,有两次情节设计把故事进展推向高潮,再有两次情节设计把高潮抑制,最后再设定一个低潮,在故事行将走入低谷时再把剧情重新推向高潮。“二近三纵”呈现的情节推进是:上、下→上、下→下→上。这个情节波折走向无疑是非常符合戏剧创作规律的:先是两个向上指向高潮的情节吊起受众的胃口;然后两次高潮回落让受众提起的兴味被调低,从而吸引他们继续追逐情节的发展;接着,再有一个低潮降低受众期待,最后突然高潮再起,并直接指向故事的终点。先低潮再高潮,既可以使高潮的到来具有突然性与戏剧性,同时也可以凸显高潮的魅力。如果一部剧作仅有一个波折,那么除非是非常简短的短剧,否则这部剧作将缺乏充足的戏剧性。而如果一部剧作有三个以上的波折,又会显得过于凌乱。所以对于戏剧波折设定来说,“二近三纵”是相对科学的设定。这在当代戏剧写作之中,也是可以通用的模式。
中国古代戏曲以歌唱为主体,“大多更加重视歌唱的作用”[3],并且重抒情而轻叙事,因此古代文人研究戏曲也多侧重于音律、辞章等问题,较少戏剧写作方面的理论提出。金圣叹则是一个异类,他对戏曲是个外行,因此以“文章”的视角审视《西厢记》,反而提出了“烘云托月”“移堂就树”“月下回廊”“羯鼓解秽”“一生一扫”这些对于戏剧写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文法理论。这些文法理论在概念表述上富有中国传统的美学特色,并不像西方理论那样具有明确的概念界定和阐释,而是采用比喻、意象、联想的语汇进行表述,其揭示的戏剧创作原理与规律极具科学性,对于戏剧角色分配、行文节奏、情节设计都具有指导价值。金圣叹在批评《西厢记》中提出的戏剧文法理论,不仅在清代影响了李渔等人的戏剧创作观念,对当代戏剧创作也有借鉴意义,可以说“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戏剧美学理论的宝库”[4]。
[1] 金圣叹.金圣叹全集:第2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2] 吴士文.修辞讲话[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150.
[3] 左鹏军.近代传奇杂剧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85.
[4] 邓新华.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观照[M].成都:巴蜀书社,2004:105.
2018-10-17
韦强(1986―),男,河北邯郸人,讲师,博士。
I207.39
A
1006–5261(2019)01–0101–06
〔责任编辑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