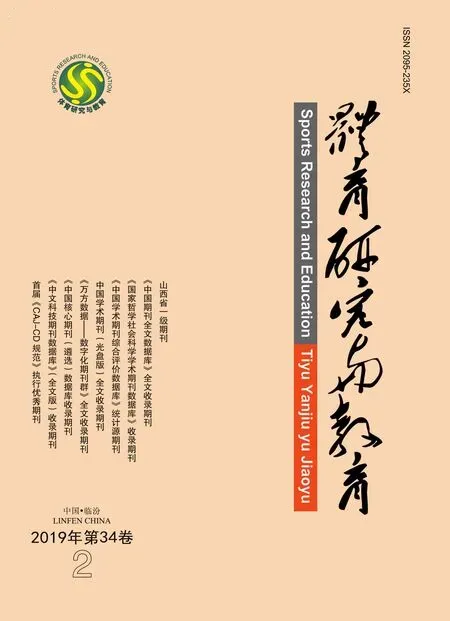客家足球文化的发展及启示
张长城,袁 静
“客家”一词含有“客人”的意思。为了与土著人相区别,居住在广东、福建、江西、四川、台湾及海外等的外来移民自称为“客户”或“客家人”,并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中国汉语八大民系之一的客家民系。梅州是著名的“世界客都”,是客家民系最终形成地、聚居地和繁衍地,也是客家人南迁的最后一个落脚点和衍播四海的出发地之一。梅州也是著名的“足球之乡”,客家足球文化是国家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足球文化给我们建设现代足球文化树立了成功的范例[1],对于中国足球文化建设和改造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和思想启迪价值。
1 客家足球的起源与发展
根据梅州足球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节点,梅州足球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梅州足球肇始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初步发展阶段。1873年巴色差会传教士毕安、边得志在梅州五华长布镇元坑创办中书院,教授足球,梅州足球肇始;1914年瑞士人万宝全担任梅县乐育中学校长,将现代足球规则带入梅州,开启梅州现代足球历程;1929年梅县强民足球队成立,梅州足球开始从学校向社会传播,并迅速传播开来,成为梅州人最喜爱的体育活动[2]。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足球之乡”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1956年梅州被原国家体委命名为“足球之乡”;1964年被原国家体委确定为全国开展足球的10个重点市县之一。第三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后至2010年的“足球之乡”重点发展阶段。1979年梅县被国务院确定为16个足球重点地区之一,并向国家足球队输送了蔡锦标、杨宁、池明华、郭亿军、谢育新、伍文兵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运动员,原国家队主教练曾雪麟也来自梅县;2009年梅州成为全国首批“校园足球”49个城市之一。第四阶段是“足球之乡”振兴发展的新阶段。从2010年梅州市委市政府颁布实施《振兴足球十年规划》开始至今,梅州足球迈入发展的新时代。2013年梅州客家足球文化申遗成功,成为国家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梅州拥有两支中甲球队。
历经百年,梅州足球逐步成为“小、快、灵”典型南派足球风格的典范,走出了一位世界球王——李惠堂,为新中国培养了270多名省市级以上足球队员。其中国家队主教练、国家队队员就有35名之多。足球在梅州人民心中具有非比寻常的特殊地位,已经成为梅州的文化名片。
2 客家足球文化的趣味生成
2.1 客家足球文化取决于参与的主要人群
正如现代足球起源于英格兰痛恨丹麦士兵踢头颅的故事一样,足球往往与战争、种族、宗教、民族主义等等纠缠在一起。足球已经不是单单的足球这么简单,而是取决于参与足球的主要社会阶层,进而成为具有不同特色的地域文化。比如,加泰罗尼亚主义的斗争精神使得西班牙巴塞罗那足球队民族主义特色鲜明,而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则成为推翻政权、引发革命的导火索,格拉斯流浪者与凯尔特人纠缠于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冲突而成为一对冤家……。虽然梅州客家足球文化参与主体多元[2],但是客家人是主要的参与主体。如果说,是西方传教士将足球传入梅州并推动客家足球文化开启了现代化进程,那么,客家人作为主要参与者则是使得客家足球文化成为梅州典型的地域文化的重要因素。梅县强民足球队、世界球王李惠堂与西方列强球队之间的比赛激发了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3,4],在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时代背景下展现了客家足球文化“爱国、进取”的特质,成为客家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2.2 客家足球文化的生成语境——客家人的传统性与西方体育的现代性相结合
体育的主体是人,其本体是人的运动行为,而人的运动构成了体育文化的内涵。西方现代足球文化在客家文化体系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客家文化则丰富了现代足球文化的内涵,赋予了其客家文化特色。两种文化相遇、对话最终形成了客家足球文化。因此,理解梅州足球要将客家文化的传统性与西方足球文化的现代性相结合,特别是要更多地考虑客家人自身的文化语境和思维模式,才能真正把握和解读客家足球文化的思想趣味。客家人在历史迁徙中形成了上层或成功人士影响公众趣味的传统,这从其文化认同中可见一斑。客家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谢重光教授研究相关史料后认为,南宋时期汀州客家移民认同中州(即中原)文化,明清时期赣闽粤客家移民更是倾向于“汉化、儒化、王化”,并进一步指出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同化是必然趋势[5]。又比如,早在西汉时期舞狮舞龙(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就已经出现,其后在全国普及开来,并衍生了许多富有地方性特点的舞狮舞龙。舞狮舞龙最初是皇宫里的娱乐项目,因皇帝的喜爱而在民间广泛开展起来。客家舞龙有纸龙、草龙、板凳龙,客家舞狮则有狮仙、狮王、仔狮和席狮等[6]。客家舞狮舞龙是客家典型的传统民俗体育,往往是同姓族人、一家三代、同胞手足同台演出,是家族传统节庆、婚丧嫁娶、祭祖、寺庙落成、五谷丰登等重要的传统体育项目。由此可知,上层领导(比如皇帝)喜爱是舞狮舞龙发展的主要原因,而根本原因则是“农隙练兵”所追求的休闲娱乐和军事价值。客家足球的发展也离不开“上层”的喜爱和支持,这里的“上层”一是特指两个特殊的群体——华侨华人和巴色差会的传教士,二是国家。因吸收国内外因素华侨文化成为时代先进的文化[7],使得华侨华人在“侨乡”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引领作用。华侨不但以“手信”的方式将足球带入梅州,而且在经济、物质上大力支持梅州足球发展,甚至亲力亲为传授足球技战术[8]。在利用剑和十字架为殖民主义效劳的本性的驱使下,近代西方传教士在粤东客家客观上传播了西方文化和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加强中西交流和了解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9]。西方巴色差会最先在香港成立分会,其后向广东梅州发展。在五华樟村(1858年)和元坑(1866年)成立教堂,并积极向紫金、和平、龙川、兴宁、梅县、蕉岭等地区传教。由于巴色差会不但传教,而且通过创建学校、医院等社会福利事业而为“深受历经艰难困苦”的客家人所接受,并在广东客家人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10]。1873年巴色会传教士毕安、边得志将足球传入梅州五华长布镇元坑中书院(相当于初中),梅州现代足球肇始。其后在各学校相继开展起来。当然,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面临救亡图存、民族生存之重任,强国强种的运动项目成为“先进的”中国人化解民族危机的重要抉择,进而使得传统体育让位于西方体育。具体到客家足球,1926年上海万国足球锦标赛上“世界球王”李惠堂为代表的中华足球队战胜西方列强的足球队,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上战胜日本队,以及强民体育会战胜驻香港英国水兵足球队等等都极大地鼓舞了客家人的反抗帝国主义的热情。
2.3 客家足球文化的生成条件
透过客家文化特性与足球发展联动一百多年的历史,客家足球文化的趣味生成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条件,其中“上层”引领这一条件,前文已经详述,不再赘述。这里主要从客家文化及其审美下的足球技艺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2.3.1客家文化为现代足球在梅州传播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梁启超在其《饮冰诗文集· 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中认为广东人较早接触西方,对西方人也不感到奇怪,“故不恶之,亦不畏之。”客家人在这方面更进一步,不但没有像潮汕人和广府人一样排斥西方传教,而是自发信仰和传播基督教,且善于学习西方文化。美国传教士弗兰克·卫英士(Frank. J.wiens)在其著作《华南客家十五年》中指出:不但客家硕儒认可基督圣灵、客家普通人也自发信仰和传播基督教,而且客家子弟善于习学西方,能够用清晰、标准的英语发音致欢迎词、朗诵、唱歌、对话、唱诗[11]。客家人之所以如此,除了较早接触西方文化外,也许客家人认为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来者为客”,有一种身份认同,在心理上更愿意接受,因为客家人自认为也是“客人”。
客家人生活在艰苦多山的自然环境和多民族长期融合斗争的复杂人文环境下,形成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团结互助等人文性格,同时在与海洋文化、海滨文化的碰撞中又平添了冒险进取、开拓创业的丰富内涵[12]。曾被郭沫若赞誉为“人文由来第一流”的客家传统文化的这种特性与西方现代足球所推崇的团队精神、顽强拼搏、敢于冒险、吃苦耐劳等现代体育精神的契合[3],使得客家文化与西方现代体育文化交流成为可能。
客家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足球文化相遇、对话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跨文化价值冲突不可避免,[13]但由于客家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足球文化相遇、对话,是以教育和民族唤醒为价值追求的着力点,故而不但没有形成必然的所谓“文明冲突”,反而使客家足球文化扎根并发展起来了。19世纪中期,注重学生绅士品质和强调体育运动的英国格拉比公学为教育学生将足球引入学校,并取得积极成效。其他公学也纷纷效仿其体育纳入学校教育内容。1848年来自不同公学的大学生制定的足球的《剑桥规则》则进一步扩大了足球在学校和社会的影响力,也推动了足球的进一步发展。与之相类似,客家人历来就有崇文重教的传统。清末民初梅州教育蓬勃发展,除了官方的学堂外,还有一大批民间、教会的学校。在梅州传教近20年的法国人赖查斯更是认为梅州教育毫不逊色于欧美[14]。足球在梅州通过学校以教育为着力点而得以发端、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在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发端于西方的现代体育发挥着唤起民众的国家政治和民族主义情怀的作用,其中尤以对现代体育产生重要影响的近代德国、法国和瑞典的体操为代表[15]。与此相类似,在被冠以“东亚病夫”触发民族隐痛的时代背景下,足球赛场已超然于足球赛事本身,成为振奋民族精神、塑造国民体质新形象的重要场所。强民体育会、世界球王李惠堂等通过足球比赛振奋民族精神、抗日救国、反抗帝国主义。足球在梅州以民族唤醒为着力点为客家人所接受并进一步发展成为梅州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
2.3.2客家文化审美情趣视域下的足球技艺茅鹏先生认为足球运动的核心在于球艺[16]。足球的先锋性是一种技术创造,是基于传统文化因素的一种审美判断[17]。球艺就是基于传统文化考量的足球的技艺性和技巧性,体现了具有本民族色彩的足球审美情趣。客家足球技艺最杰出的代表就是世界球王李惠堂。李惠堂自小酷爱足球、4岁开始练球,常常练习练习再练习,熬煎千万遍,即茅鹏先生所说的球艺热忱,而这种球艺热忱恰是足球生命力的重要体现之一[18]。李惠堂足球技术精湛,能左右开弓、射门精准、卧射一绝,其盘、传、踢射皆有绝活,素有“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的美誉,而这一赞誉恰恰反映了传统文化的审美情趣和对艺术足球的内在追求。
3 客家足球的文化特性
现代足球促进了客家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而客家足球文化是客家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具体体现。客家足球文化既具有传统性又具有现代性。
3.1 客家足球文化的传统性
民族文化的不同会造成相似却本质不同的足球文化,比如德国的“日耳曼战车”足球文化、英国的“绅士”足球文化、巴西的“桑巴”足球文化等等。而不同国家的足球文化体现了不同民族的传统性。客家足球文化的传统性主要体现为教育性、节庆娱乐性、家国特质以及“德行”思想。客家足球文化的教育性主要体现为足球与学校的紧密联系。据统计,至民国初年,梅州城乡中小学数量相当于同期广州市中小学的数量,有各类中学30多所,小学600多所,而且各学校都开辟了大、小足球场,特别是梅州城区中学各校、各班都有足球队,校际间的足球比赛频繁且热烈[9]。客家足球深得广大群众的喜爱,有许多民间足球组织,也是一般群众晨练、工作之余的重要休闲运动项目,足球比赛成为传统节庆宗亲联谊的重头戏[19]。客家文化具有鲜明的“爱国爱家”的家国特质,足球爱国始终贯穿于客家足球发展历史的始终。 客家足球文化崇尚传统“礼、义”美德,并在足球比赛实践中积极践行之。李惠堂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认为足球“当以道德为本、技术为末,先求其本,后齐其末”,并在比赛中坚守“敬以持躬,恕以待人”传统礼、义之道。即便被故意犯规致左脚胫骨骨折却仍替对方开脱使其免于牢狱之灾[20]。
3.2 客家足球文化的现代性
“现代性就是时代性。”客家足球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外源性”的,一经传入即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客家足球文化现代性首先表现为“脱域”后的国际化发展路径。客家足球文化传入后并没有受到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等地域性限制,而是获得了华侨华人、港澳同胞的技术、物质、资金等方面支持;赴香港、澳大利亚、东南亚、德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足球比赛,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奥运会等国际重大赛事。无论是从外源性的传入、海外支持、海外比赛,还是参与国际重大赛事等,客家足球文化走出了一条国际化的发展路径。
客家足球文化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国家理性。就是通过足球实现强国强种、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增强民族自尊、树立民族自信心,进而展现民族的优越性。
客家足球文化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同一化”以及理性化的契约性的公共体育精神。理性化即“同一化”,对同一化的追求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21]。1914年现代足球规则被西方传教士介绍到梅州,客家足球文化开启了同一化的历程,进而被纳入到现代足球文化的范畴。理性化的契约性的公共体育精神主要体现为自由、平等、契约、竞争等,在李惠堂的足球思想中可窥见一斑。比如,李惠堂把足球当做社交的游戏,而社交则是以友善、平等、公正为出发点;足球队员要有正确的胜负观,要认识到登场比赛不在于输赢,而在于公平;足球能培养勇敢品质、锻炼心理智慧、获得友谊等。以上所有,无不体现出足球队员的主体性。
客家文化与现代足球文化相遇、对话的过程就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相融合的过程。现代足球文化在客家文化土壤里最终成长为中国南派“小、快、灵”足球风格的典型代表——客家足球文化。
4 客家足球文化形成与发展对中国足球改革的启示
4.1 增强传统文化自信,促进新时代足球文化建设
近代以来,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始终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所谓“落后”就是中国的农业文明“落后”于西方的工业文明。在这一惯性思维下,人们把中国足球发展不理想的状况往往归之于这种“落后”。代表性观点有“中国农业文明缺乏对牧业文明的集体记忆是中国足球不发达的原因之一,因为足球属于草原文明”、“古代蹴鞠终日不坠的球技是礼之用和之贵——礼仪文化的产物,而‘和合’礼仪文化造就了中国现代足球文化的落后。”客家足球文化的形成是对这些谬论的无情地强力反击,因为客家文化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足球文化的形成对于增强传统文化自信、加强新时代中国足球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客家足球文化形成的实践表明客家文化并没有一味地固守“山林农耕文化”,而是积极汲取海洋文化、商文化等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营养,积极实现现代化转型。现代足球属于西方文化,客家足球文化则是客家文化现代转型的结果。客家足球文化形成的实践表明只有走传统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并以技术为导向形成自己的足球风格,才能构建新时代的中国足球文化。
之所以出现对中国足球发展的认识谬误,主要原因如下:一是为近现代以来西方体育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所遮蔽,忽视了中国人民发展体育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体育大国、体育强国建设的伟大历史功绩;二是忽视近了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转型发展,已经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三是割裂传统,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中国传统文化贵和尚中,“和合”文化已经是“中国道路”做出的世界性四大总体性贡献之一——文化性贡献[22]。“和合”文化已非中国所独享,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合”体育文化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软实力,成为医治西方竞技体育“异化”的一剂良药[23]。
4.2 中国足球文化现代性重构
4.2.1中国足球文化现代性“不在场”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11号)意味着始于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历经24年的中国足球改革的彻底失败,标志着中国足球文化现代性建设再次重新起航。“他者”是一面镜子,从“他者”的视界可以窥见中国足球文化存在的现代性问题。前国家队外籍教练施拉普纳、米卢蒂诺维奇、阿里汉等这样评价中国球员:缺乏勇敢的拼搏精神、视野狭窄、没有团队精神、害怕丢脸、没有激情、只想着钱、人际关系在团队中处于主导地位等。日本教练冈田武史认为中国球员缺乏自信、自立意识差等。国内一些有识之士更是直指中国足球过去五十年既受到管理体制的制约,又经历无序市场的肆虐[24],由于对足球内在精神的认知不足,随之而来就是制度缺失、文化缺失、道德缺失[25]。现代性在最广义的维度可以分为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中国足球文化现代性可以归纳为球员主体性和自我意识、契约化的理性化的公共体育精神等精神维度上的缺失,以及组织管理落后、监管失察、竞赛秩序混乱等合理的制度缺失。中国足球现代性缺失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的现代性还“不在场”。中国社会依然是经验代替理性,以人情代替契约[26]。当然这种“不在场”主要是指现代性还不是中国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和社会运行机理。足球改革也不是仅仅关于足球本身的现代性问题,而是涉及到国家理性,通过足球改革为社会改革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
4.2.2中国足球文化现代性重构选择客家足球文化的现代性建设为中国足球文化现代性重构增强了民族自信、提供了思路借鉴,但是中国足球文化现代性重构要复杂得多得多。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出台意味着中国足球改革已从行政性上升到政治性高度,为讨论中国足球改革的政治性价值搭建了应有的平台。政治性价值是体育一直以来所追求的最高国家理性之一。一个民族在建国之前往往通过体育强国强种、振奋民族精神。在国家建国以后为展示其政权合法性、民族优越性、体制优越性又往往以此唤起民众情绪、提振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中国在建国之初,足球一直处于世界中下水平,而担当此重任的则是射击、中国女排、女子举重、跳水、乒乓球等中国优势运动项目。今天,尽管中国足球水平相对下降,但是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已经成为中国高层的“审美情趣”。透过《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可以看到足球具有了不同寻常的价值,它关涉到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创建公正公平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以及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规划了中国足球近期、中期、远期的发展目标,显示出这一国家理性重构任重道远。
足球腐败、球场京骂、社会对足球的调侃等等反映了中国足球文化并没有给社会带来正能量,中国足球缺乏一种人性的向善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品质,而争金夺杯、以成绩塑造形象的恶性循环是其根本原因,又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更加恶化。精神的匮乏和危机使中国足球陷入了远离民族精神和游戏精神的“粗鄙化”发展的路径之中,为此中国足球文化精神重构也就成为《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比如要建设球迷文化、城市足球文化、加强运动员文化学习、构建全社会健康足球文化等。重构中国足球文化精神既要立足于足球文化的现代理性,弘扬公正公平、竞争、主体性等公共精神,又要立足于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对足球文化进行创造性诠释。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生活趣味,而“现代性本质上就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世界”[27],因此足球文化只有通过生活体验,才能激发个性化的人性光辉,并在生活体验中展示足球精神。这种足球精神不仅表现为个体化的主体精神和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精神,而且进一步整合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宏大叙事”,进而体现出足球改革与社会改革发展逻辑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将足球改革视为国家现代性治理的前奏。
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完全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竞争是很难想象的,因此既强调竞争,又兼顾中国传统性格的规章制度,才是当下中国足球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也就是在延续现有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渐进待机的方式”逐步实现中国足球的现代化发展。因此,《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继续以新权威主义保证中国足球改革平稳有序进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举国体制”改革,同时在中国足球协会的人员构成、职责、职能、组织性质等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对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重新进行了顶层设计,进一步从股权上对足球俱乐部建设进行了重新定位等等。尽管如此,谭华教授认为,“除了足协与总局脱钩,其他多数措施的落实都有难度……”。
4.3 中国足球球艺应“从娃娃抓起”
李惠堂4岁就开始踢球,技术精湛、球德高尚、崇尚现代足球精神、成绩卓著,并最终成为“世界球王”。这对于发展中国足球具有重要启示——中国足球球艺应“从娃娃抓起”。
从运动训练学角度,足球球艺是以一定的足球天赋为基础,通过长期训练而形成的更好应对足球赛场场景的能力。千变万化的足球实战场景决定了足球球艺是一个复杂系统、且难以具象化,不能像体操动作学习一样获得清晰的“训练途径”。依据生理学原理,儿童学习足球具有低龄起步优势。在同等条件下,不具有低龄起步优势的往往与具有这种优势的形成剪刀差发展结果。世界级球星无不是从小就开始习练足球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然而,“从娃娃抓起”还有更为深层次的涵义。一方面中国足球球艺起于古代蹴鞠,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传承传统文化需从小抓起,并且球艺、技巧的学习领会也是有传统的。另一方面由于现代足球文化本质上是现代人的一种现代性生活世界,“从娃娃抓起”就是通过足球从小培养国民的现代性,缔造新的国民性。从这点上,邓小平所说的“足球要从娃娃抓起”隐含了深邃的哲理性,赋有生活的批判性和重构性,也为“校园足球”指明了方向。
5 结语
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背景下,中国足球改革是一场新型的文化建设活动,是培养国民的现代性、缔造新的国民性的新动力。中国足球改革主要涉及到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以及引入西方足球文化的现代性的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对此各执牛耳。客家足球文化形成与发展在这方面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尽管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所涉及的传统性和现代性问题更加复杂,但其于增强传统文化自信,建设新时代中国足球文化具有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