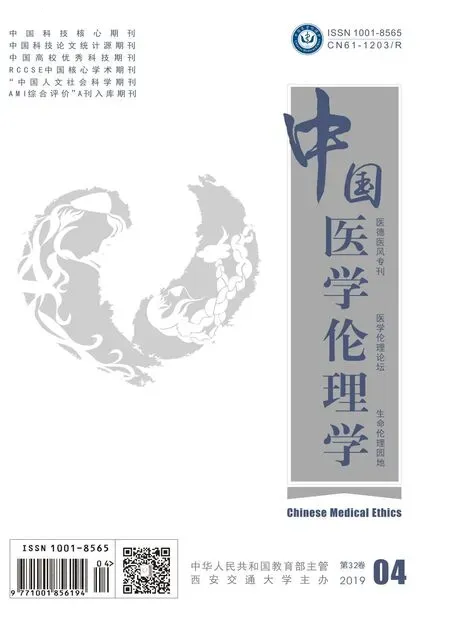对“敬畏生命”新的哲学解读
曾小五
(广东医科大学社科部,广东 湛江 524023,zengxiaowu98@163.com)
1 “敬畏生命”的一般理解
“敬畏生命”,作为一个汉语哲学术语,最初源于施韦泽相关著作的翻译引介,其对应的英文语词为“reverence for life”、德文语词为“Ehrfurcht Vor dem leben”。从语词结构看,它是一个动宾词组。这一词组由两个词项构成:一是reverence(Ehrfurcht)即“敬畏”;二是life (leben)即“生命”。“敬畏”,显然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尊敬(或崇敬)和畏惧(或害怕)。“生命”,其本意当然泛指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体(即一切生命现象)。所以,根据这一语词使用的原初文化背景和它的语词结构,我们不难断言,它的基本内涵是指对所有生命现象(包括所有的动物、植物在内)的既尊敬又畏惧的情感或态度。既如此,按照一般的逻辑,我们可轻而易举地推出建立在“敬畏生命”之上的行为原则或方式,即“在与其他生命体交往的时候, 我们应该像面对一个操控着自己命运的‘大人物’(或神)一样,谦卑为怀、谨小慎微”。
然而,假如把这种逻辑推断与当代人日常生活中培养起来的常识和信念比较,我们会觉得有些不合适:“我们平时是怎样对待昆虫或我们自家豢养的禽畜的呢?我们又是怎样对待路边的小草、园中的蔬菜或山中的树木的?而且,这些生命体有何德何能,值得我们既敬又畏?”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一命题的原初提出者施韦泽,在具体阐释的时候,其理论理解表现出两连跳式的“堕落”。首先,他把“敬畏生命”的实质归结为“对生命意志的敬畏”。他说:“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生命意志。”[1]9又说:“只有我的生命意志敬畏任何其他生命意志才是伦理的。”[1]29其次,当把这种对“生命意志”的“敬畏”落实到作为其表象的“生命现象”时,施韦泽则把它转变为一种建立在“与其他生命共同感受”的同情心基础之上的、对其他生命体的“爱护、怜惜和保护”。他说:“在我们生存的每一瞬间都被意识到的基本事实是:我是要求生存的生命,我在要求生存的生命之中。我的生命意志的神秘在于,我感受到有必要满怀同情地对待生存于我之外的所有生命意志。善的本质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恶的本质是: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1]91-92“从而,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敬畏生命。我给予任何生命的所有善意,归根到底是这样一种帮助,即使它有益于得以保持和促进其他生命的帮助。”[1]92至此,“敬畏生命”一词原本蕴含的“敬”和“畏”的情感几乎丧失殆尽。
显然,在对“敬畏生命”命题的理解上,施韦泽的逻辑并不是一以贯之的。这种现象和本体之间的割裂,多少与植根于施韦泽潜意识之中的西方哲学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影响和限制有关。当然,它也成了施韦泽相关思想在实践中陷入难以克服的自我否定或自相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
或许同样是“敬畏生命”的原初意蕴与现实生活的事实及信念之间的差距与矛盾现象,有的中国学者在理解这一概念时,也赋予了其另外的内涵:从语义上讲,敬畏生命,就是人们对生命的敬重和畏惧。它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敬重生命,二是畏惧死亡,而且人们对死亡的畏惧往往通过对生命的敬重表达出来[2]。把“敬畏生命”理解为“对生的敬和对死的畏”的观点,可能是尚未留意这一语词原初使用的文化背景及其本身的语意结构为前提的。
笔者认为,对“敬畏生命”这一命题的科学理解,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在忠实于其使用的原初文化背景和语词结构基础上理解,即把它理解为“对生命本身的尊敬和畏惧”;二是坚持前后一贯(不割裂本体和现象)的立场,即认为“对生命本身的尊敬和畏惧”同时包括本体(形而上)和现象(形而下)两个层面。只有当我们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这一语词的含义时,才能正确阐释这一哲学命题并彰显其应有的生命哲学价值。
2 “敬畏生命”的生命哲学价值
要阐释“敬畏生命”这一命题的生命哲学价值,首先要阐释的问题当然是:“什么是生命?”但这不是一个多余的话题吗?前面我们不是对“敬畏生命”中“生命”的内涵做出了解读?所谓生命,就是包括人在内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具有生命现象的物体。但这只是常识或现象层面的解读。当我们在哲学层面追问这一问题的答案时,当然是在追问“生命的实质或本质”——那被施韦泽理解为“生命意志”的、生命现象背后的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进一步追问生命的由来或原因。
迄今为止,与人类生活相关的生命,当然主要指地球上存在的生命现象。
从宇宙演进史(或进化论)的视角看,地球上最初本无生命。这里的生命现象,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漫长演化过程的结果。依从这一观点,我们可以简单勾勒出迄今为止地球上生命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综而观之,地球上现有生物(界)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两个密切相连的阶段:原初生命的形成与后继生命的“进化”。
首先是最简单的原初生命的形成。
按一般的科学或逻辑推断,地球上原初生命的形成或出现,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生命物质产生所需要的物理、化学、生物变化的物质和温度条件;二是适宜于原初生命物质生存的、相对稳定的自然环境。对这两个条件进一步解析,可以推出原初生命形成的三要素:一是地球表层存在适量的水分和其他相关的大、小分子(如各种小分子无机物、碳水化合物、蛋白质高分子等)。这是原初生命得以形成的必要物质基础。二是地球外太空稳定的能源提供适当的热能补充。这是地球能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环境的外部条件,也是以光合作用为能量来源的、简单绿色生物能够形成并生存的必要条件。三是地球上空已经形成一个成分构成相对稳定的大气层。这是地球本身能维持相对恒温的内部条件,也是陆地喜氧生物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在这些基本的条件或要素得以保证的条件下,只要给予足够长的时间,地球上的物质之间,便可以通过永不停息的相互作用,因着地球上各个具体部位微环境的多样性,遍地开花,产生出多种多样、特征各异的原初生命物质。
其次是后继生命的“进化”。
原初的生命形成之后,仍然会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生各种变化。当生命体的内在物质基础(DNA)的结构性变化出现时,由于这种变化能通过生殖繁衍而传递并保留,后继生命的“进化”便开始出现。这是地球生物界形成的第二个阶段,达尔文把它叫作“生物进化”。达尔文之后,人们一般用遗传和变异两个词语对之进行概括和描述。
只要稍加分析,我们便可发现,这种生命产生和发展的逻辑,蕴含以下事实:其一,地球上生命的出现以及现有生物界的存在,是地球外环境(即地球外太空)和地球内环境(大气层、地表)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特殊物质运动现象或运动形式;其二,每一种后继生物,作为一个物种,都是地球原初生物进一步演进的结果,是生命体与地球内、外环境相互作用引起的内在可遗传的结构性变化通过漫长的时间积累而形成的;其三,每一生命个体的存在,都既是与自己生活的微环境(个体生存的独特环境)、小环境(生物生存的地区环境)密切相关的,又是与地球的地表层和大气层这个大环境以及地球之外的宇宙空间环境密切相关的。
我们可以顺着“宇宙演进史”推知当今生物界的形成,当然,也可以循着这条来路,逆流而上,设想地球上生命的消失:当适合某个生命体生存的微环境消失时,这个生命体将随之消失;当适合某物种生存的小环境消失时,这类生命体将随之消失;当适合某些物种生存的更大的环境消失时,这些种类的生命体将随之消失;当地球这个大环境或宇宙外界环境不再适宜于生物生存时,当然,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体(包括人在内)将随之消失。
通过这正反两方面的追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事实:地球上的生命现象只不过是整个宇宙(包括地球本身在内)永恒的运动变化在地球上的具体表现与表达。换言之,任何一个生命体,都是整个宇宙的普遍联系和无限运动在一个具体的时空坐标点上的一种表现。
所以,任何一个生命体,就其实质而言,都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一方面,每一个生命体都与它生活其中的环境有一定的区别,因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这种相互区别的条件下,它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生命体,它又与无限的宇宙贯穿一体,是宇宙的普遍联系与永恒运动在一个个具体的、微观的时空坐标点上的具体的表达,因而,具有无限性。只不过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感性生活经验的限制,人们往往只看到生命体有限的一面。正因如此,有的人会不知敬畏,甚至对其他生命体生杀掠夺、为所欲为,而有的人,则会由于某种观念的影响,对其他生命体的这种被主宰的命运表现出同情和怜惜。但假如我们能透过日常生活的限制,看到生命体无限的一面,即看到每个生命体都是与整个宇宙贯穿一体的、是宇宙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的一种具体表达,我们的心情会怎样呢?假如我们知道,我们眼前生物的生灭变化,其实是无限宇宙变化的一种表达,我们不会油然而生畏惧之情吗?假如我们发现,我们本身作为一个生命体或一个生物种类,也同时是包括其他所有生命体在内的整个世界在某种具体时空坐标点的一种表达,其他生命体的存在其实正是我们存在的条件,其他生命体的消失同时也就是我们生存条件的消失,我们不会对其他生命(物种)的存在心怀感恩和崇敬?其实,我们说“生命是一个奇迹”,不能仅仅只意味生命体本身结构与功能的完美与和谐,它应该同时意味着整个宇宙在这个时空坐标点上表现出了自己的完美与和谐!这就是我们应该对“生命”(既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表现出既敬又畏的基本的理由。
所谓敬畏生命,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是人类本应该具有的、一种理所当然的情感!
3 “敬畏生命”的道德意义源头
人和其他生命就其实质而言,同是普遍联系与永恒运动的无限宇宙在一定时空坐标点的表现或表达。虽然,在作为宇宙之表达这一点上,所有的生命体都是完全平等的,但是,其中的任何一种表达都具有自己的个性。人与其他生命表达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是理性动物,它有完整的自我意识,能够在观念层面把自己和环境区分开来,而一般生命体没有这种特性和能力;二是人具有自由意志,能够用观念思维指导自己的行为反作用于环境,即人能按照自己的意图改变环境,而人之外的其他生命体的生存则主要表现为对自己生活环境的适应。正因如此,所有的生命体中,只有人(理性生物)才可能形成敬畏生命的情感和观念,而且这种 “情感和观念”也必然地具有了道德意义。
那么,“敬畏生命”的道德意义源于何处?
第一,道德哲学,作为一种价值哲学,是探讨人类的行为对于其本身生存与发展价值的。所以,探讨行为的道德意义,实质上就是探讨该行为对于相关者生存与发展的价值问题。人作为理性动物,其观念指导的行为应当是有目的的,而这种目的的最终旨归也只能是人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我们无法且无须超越的基本立场。“敬畏生命”的道德意义正应该在其对人类本身的价值中去寻找。
第二,人作为一种生命体,同其他生命体一样,都是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的宇宙在地球这个特殊星球上的一种具体表达。然而,宇宙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既可以生命的方式表达,也可以非生命的方式表达。其在某个时空坐标点到底以怎样一种方式表达出来,是由这一时空坐标点的大小环境决定的。通俗地讲,任何生命体的出现或存在都是有条件的,如具有相对稳定的组成和温度的大气、地表适量的水分等。一旦在这一时空坐标点上,这种条件被破坏或消失,在此,宇宙的运动变化就将无法以生命的形式表达出来。
有了以上两个基本理解,我们便可剥离出“敬畏生命”道德意义之所在。
首先,人类是有限的存在,却同时具有某种意义的自由能力。一般而言,人是相对独立的理性存在。在这个层面上,人的存在具有两方面的规定性:其一是有限性,即作为相对独立的存在者,人是有限的。其二是自由性。因为人是理性存在者,具有完全的自我意识,能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有限的、相对独立的有机体的存在及其活动。这使人具有了意志自由的能力,即人能够根据自己的观点、按照自己的意图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发起主动的行为。既如此,人类当然可以根据对自己有限的体验和理解,从自己的欲望和需要出发,主动发起与环境的相互作用。随着人类行为对环境作用的频次和力量的增大,其对环境的影响也随之增大。当人类的行为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超越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可能促使地球环境本身的现有平衡发生某种转移(包括其大气结构和温度、地表成分等各方面)。这种平衡转移,其结果显然只有两个方面:一是使地球环境越来越不利于宇宙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以生命的形式表达出来;一是地球环境越来越有利于宇宙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以生命的形式表达出来。
其次,人类具有某种意义的无限性,同时又是不自由(或被决定)的。其“无限性”指,人类这种生命形式是与无限的宇宙密切关联的;其“不自由”指,作为无限宇宙普遍联系和无限运动的一种具体表达,人这种相对独立的个体,是被整个宇宙决定的。也就是说,人这种生命表达方式,决定于整个宇宙的状态,是宇宙的整体状态下,地球个体状态的一种现象。既如此,人类这种表达形式能不能成为现实以及其表现状态,归根结底是不以人的意志本身为转移的。当地球环境适宜于人类这种生命表达方式时,它就能生存下去;反之,它也难免消失的命运。
将以上两方面关联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事实:人类相关于其他生命的行为将透过其对环境(生命体是其有机组成部分)的影响反作用于自己。当这种对环境的影响促使平衡转移以至于不利于地球作为一个生命表达场所时,人类这种生命表达方式就会受到不利影响,或者说,人类作为相对独立的有限个体的利益会受到威胁。从伦理学的角度看,这种行为,因为不利于人类本身的生存和发展的,所以是不道德的。反之,当这种对环境的作用促使平衡转移以至于使它更有利于地球作为一个生命表达场所时,人类这种生命表达方式就会得到肯定,或者说,人类作为相对独立的有限个体的利益会得到改善。从伦理学的角度看,这种行为,因为是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所以是道德的。这就是“敬畏生命”道德意义之所在。
4 人类实践活动中“敬畏生命”的表现原则
如前所述,从宇宙演进史的角度看,地球上任何生命的出现,都是太空的宇观环境、地球的宏观环境和生命体本身生存的微观环境相互作用条件下的产物。其中,太空宇观环境是外因,地球自身环境(包括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是内因。两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迄今为止,地球之外的宇观环境是人类自身能力所无法改变的,所以,当考虑人类的行为活动的影响时,地球本身的宏观和微观环境便成为最重要的关联对象。
我们知道,地球上现有生态系统(或生态环境)的形成,是地球亿万年演化的结果,也是地球生命与其环境在亿万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默契”状态——一种相对稳定的、适宜于生命生存的动态平衡。一方面,地球上任何生命都是地球现有大环境条件下某种具体小环境的表现。这种表现包含两个方面,即生物内在生命结构和外在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生活在一定环境之中的生物总是适应使之以生命形式表现出来的环境的。另一方面,一定环境中的任何生命又成为该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生命和非生命物质共同构成生态环境本身。两方面相交相融,密不可分。所以,生态系统,从一种“默契”向另一种“默契”转移,必然以生态系统内生物种类或生命结构(包括内在和外在结构)改变的形式表现出来。生态“默契”的破坏(生态环境的灾难性毁坏),当然也必然是以物种和生命体破坏的形式表现出来。反过来也一样,即任何生命体或生物种类的产生或消失,都会对生态“默契”产生自己的影响,超越一定程度,便会促使这种“默契”的转移,甚至打破“默契”状态。我们之所以要“敬畏生命”,当然基于生命是无限宇宙的一种具体表达,同时也更是基于生命体和生态系统之间这样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
首先,生命作为无限世界的一个具体表达,有限中蕴含着无限,平凡中蕴含着伟大,朴素中蕴含着神奇,并且,它们还与其他生命和非生物环境一起构成了我们生活其中的“默契”状态——良性的生态环境。我们怎能不对其他所有生命心怀怜爱、感恩和敬意?
其次,由于宇宙环境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多层面(从内在结构到外在习性)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使得任何生命体,甚至都同时成为一个启动无限本身(即环境)状态“平移”的一个契机或机关。它们怎能不让我们心生敬畏、谨言慎行?所谓“蝴蝶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正源于此!
再次,任何生命体,作为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变化的一个具体表达,它也同时是人类的意识与无限世界或宇宙沟通的一个窗口,我们的理性之知,可以沿之而走向无限。我们又怎能不对每一个生命体充满崇敬与神往之情?
那么,我们如何才算是在道德层面表达出了自己对生命的敬畏呢?
我们认为,“敬畏生命”,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运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时,表现为三条相辅相成的原则,即“无为”原则、“有为”原则和“中和”原则。
其一,“无为”亦即“顺从”的原则。
所谓“无为”原则,就是要求我们不要以超越自然或僭越的态度对待生命。从外在形式看,它表现为对环境或自然的“顺从”。其基本理由在于,包括人在内的任何生命,都是被环境或无限决定的,是无限的一种具体表达,同时也构成环境或无限中有机的一环。
具体而言,在当今时代,“无为”原则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创造”“不改变”。这是对生命或物种而言的。“不创造”就是不通过人为的方式制造某种自然界没有的“原初生命”或物种;“不改变”就是不要通过人为的方式改变现有生物的基因而改造物种。新的、人为制造的生命或物种,因为不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它的存在便可能给自然环境带来结构性的破坏,从而打破生态平衡,损害甚至毁坏生态“默契”,从而最终损害人类的生存利益。
二是“不破坏”。这是对生态系统或自然环境而言的。这就是不人为地破坏地球生态系统现有的“默契”或平衡。这一规定,要求人类发动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行为时,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量的控制,即不要使我们与自然环境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包括索取与排放)超出现有自然环境承受的限度。很明显,假如超出一定限度,我们的行为就可能引起自然生态平衡的持续转移,最终损坏生态系统的内在“默契”。二是质的控制,即不要人为制造自然界不能“消化”或很难“消化”的物质(这里主要指非生命物质)。因为自然界不能消化或很难消化物质的聚集,将直接对生态环境及其平衡造成挤压与伤害。迄今为止,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这种破坏已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大范围雾霾的形成、温室效应、臭氧空洞的形成等,正是人类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没有注意这种质和量控制的结果。
三是“不违背”。这主要是针对人类自身而言的。它要求我们不要在自身欲望的驱使下追求违背自然赋予的生存或生命状态。任何人的生命状态(包括无形的性情和有形的体貌等),都是外在环境(人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与内在环境(身体内在的结构)相互作用的产物,是这种内外环境相互作用下的一种“和谐共振”状态。所以,小到整容塑形,大到器官移植等,其实都是对这种“和谐共振”状态的某种程度的违背,其负面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在生命科技高度发展且日益被资本的欲望控制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其二是“有为”亦即“适度”的原则。
这一原则之所以成为必要与可能,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这是地球作为一个现实的生态系统的不完美性决定的。如前所说,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在地球这个大环境基础之上的一种特有的表现或表达。虽然,从总体上讲,地球是一个适合生命生存的地方,但就其本身而言,它仍然不是一个不可能再改进或提高其完美的、适合生命生长的系统。地球上仍然有大片的沙漠、荒原。这些地方,生命是很难生存的。而且,它们的扩张,将进一步威胁周边生物的生存环境。其二,这也是生态系统和生物种类之间内在关系的要求。一般来说,越是适宜于生命表达的生态系统,其中的生物种类越多。反过来说,即生物种类越是多样性的生态系统越是适宜于生命表达的系统。这是生态系统和生物种类之间关系的内在逻辑。其三,作为理性动物,人能够认识自然环境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并且能通过工具、按照自己的某种观念改造自然环境。正因为如此,人类可以在自己对自然环境正确的认识和判断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行动促使自然环境朝着更适宜生命生长的状态转化,使自然生态环境更加繁盛、生物种类更加多样,从而在原有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态环境。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有为”。
具体而言,“有为”原则,在人的行为实践活动中表现为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呵护环境。这主要是就对生物的类或生态系统的态度而言。它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地球上生态系的状况及其发展规律,在现有自然环境的基础上,至少要有意识改善、推进与人类的生命活动相关联的自然生态系统,使之更适宜于生命形式的表达,即进一步趋向物种的多样化。具体而言,这种对环境的呵护包括治理、改良那些具有贫瘠、干旱等不适于生物生存特征的土地(如在可能的情况下,在沙漠改建造绿洲、植树造林等);保护湿地;保护海洋的生物资源(如不过度捕捞等);禁止大规模捕杀动物或砍伐树木等;禁止使用对生物物种或生态具有毁灭性的武器或药品;保护濒危物种;不过度开采等。在这方面,迄今为止,人类其实已经是做了很大的努力的,但仍远远不够。二是善待生命。这主要是就对个体意义上生命的态度而言,它要求我们对其他生命体,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怜惜和爱护,具有某种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民胞物与”的情怀。对其他生命体(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的怜惜与爱护,是人天然具有的同情心的一种表现,因而,它实际上也是人内在德性充容的表现。善待生命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停留在生命个体。有子在评论孝的价值时曾这样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正如孝德与社会和谐稳定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样,对一般的动物、植物个体都充满爱心的人,当然更倾向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而要想他大规模毁坏生命或生态环境,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善待生命的“民胞物与”的情怀,作为人的内在同情心的扩展与延伸,同样成为一种具有生命伦理意义的情感。
其三是“中和”亦即“和谐”的原则。
这里的“中和”虽然借自先秦儒家思想,但由于离开了它使用的原初环境,当然具有了不同的含义。在此,“中”,我们取其“执守中道”“无过无不及”的意思,“和”,我们取其“调和”“和谐”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所谓“中和”原则,就是指人类在自己的生活或与自然环境交往的过程中,能一定程度地克制自己的物欲和社会本性(人类的个性)的要求,既不泯灭自己的需要与个性也不过分张扬它们,以便实现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
人虽然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在这一点上,人与其他任何生命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人类终究是一种具有自己独特秉性的生命,如人具有理性、社会性等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很多其他生命不同的特性与需要。正因如此,人类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观点等等,在自然界原有赋予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创造,如发明机械工具(如制造出火车、汽车,发明电脑、电视等)、构造舒适安全的环境(如建造房屋、村庄、城市,发明空调、净化器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忘记了自身的自然秉性而走极端,让自己过多地陷入一种与自然“隔绝”的环境之中或让人为的环境无限制地扩大,而应该在这两种秉性或需要的张力中取得一种协调与平衡,从而,实现人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对内,生物自然秉性与社会秉性相互调和;对外,人化环境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这一原则是相对于人类作为理性动物、社会动物这一独特本性而言的。它同样是人敬畏生命的表现。
总之,敬畏生命,作为一个哲学(伦理学)命题,在人类的生活实践中,它可以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原则,即无为(或顺从)原则、有为(或适度)原则和中和(或和谐)原则。第一方面的原则是要求我们像自然界其他生命一样,遵循并恪守自己自然之子的地位,不僭越、不违背。这是消极意义上的生命之善。第二方面的原则要求我们超越其他的自然之子,在促进环境的改善方面表现出自己作为理性动物的能动性和积极性。这是积极意义上的生命之善。第三方面的原则要求我们全面而非偏执地把握和促进自己生命的实现。这是综合(或关系)层面上的生命之善。三方面的统一,构成完整的人类生命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