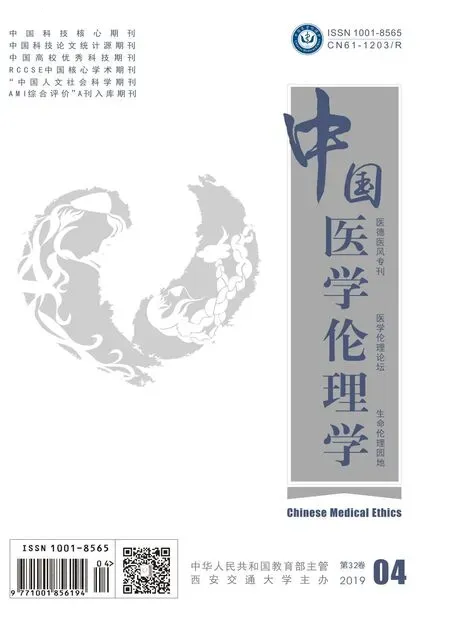国外道德创伤研究的三重视角*
谭 坤,黄 强,肖人铨,李 坤,常运立
(1海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上海 200433,13061714080@163.com;2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四医院药剂科,广西 桂林 541002;3 海军军医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上海 200433;4 山东大学人文医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012)
在现实战争中,战士作为战争中的主体,会面临各种各样来自生理、心理乃至精神上的隐患。这些隐患,表现为没有履行长期坚守的道德观念,违背交战法则或刻意隐瞒。乃至美国战士自“持久自由行动”和“伊拉克自由行动”以来,军事人员的自杀率增加了一倍多[1]。国外不少学者尝试找出一种模型或模式来描述这种现象。Shay等人最早通过文献研究[2],将上述的背叛行为现象称之为道德创伤(moral injury)。随着研究深入,国外学者对道德创伤的内涵不断拓展,泛指战争中具有道德相关的事件造成的创伤,核心是遭到背叛或违背了自己的价值观。同时,道德创伤作为一个新兴的创伤范式,不同领域的学者从自身专业出发,形成不同的认识和解读视角。
1 文化社会学视角
1.1 权威人士的背叛
在《阿喀硫斯在越南》一书中[3],Shay引用了一个老兵的例子,讲述了类似的情况。该老兵原为某远程侦察巡逻队的一名成员,由于情报错误杀害了无辜的平民。退役后老兵说:“让我们彻底困惑的是‘别担心了,一切都没事。’因为这就是你从上级处得到的回答。这该死的上校说,‘别担心了,我们会处理的。’其实‘我们杀了人!我们杀了人!’这想法一直萦绕在你心头。你知道在你的心中这是错的,但你的上司告诉你,没关系。那么,就应该没事,对不对?这是战争的一部分。他们想给我们一个该死的嘉奖,他们真恶心。因为杀了很多人所以颁发来了很多奖章。中尉们得到了奖章,我知道上校也有他的奖章。他们会举行颁奖典礼,而我会像一个混蛋一样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分发杀害平民所得的奖章。”
虽然“权威人士”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牵引点来推动其指令的执行,但“权威人士”并不能理解每个士兵是怎么通过他的指令来引导自己。例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名士兵被命令离开他死去的战友的尸体,或者更糟的是离开一个受伤的战友。虽然“权威人士”所作出的决策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符合需求的,但是在士兵的眼中,可能“权威人士”的考虑是次要的,拯救战友才是主要的。而这种差异就会产生信任危机。一旦产生信任危机,那么很有可能带来道德混乱,进而产生道德创伤。
1.2 非正义之战
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到国内民众的广泛赞同。甚至,美国前国防部长亨利·斯廷森认为: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是为了拯救更多的生命,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带来持久的和平。正如投放原子弹的飞行员Paul Tibbets对于自己投放原子弹的行为也这么说道:“如果我们拥有那件武器,而不使用它,让更多的人死亡,那将是道德上的错误”[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美军老兵们,虽然认为他们在战争中的杀戮行为是不道德的,但少有负罪感。即使产生了道德创伤,也为民众所认同,在社会大众关怀下逐步走向痊愈。但是与之相反,1959-1975年美军所进行的越南战争,因其强烈的政治目的和军事企图,战争后期遭到国内民众的强烈抵制,在美国的大街和大学校园,充斥着对这场战争是否道德的声讨和失败原因的指责。这些反战行为,致使美军越南老兵负有严重的道德压力,部分退伍军人觉得他在越南已经成为一个邪恶的人。“今天我回望过去,我恐惧于我的变化,恐惧于我的所作所为。我看起来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同时,据美军退伍军人事务部统计,越南退伍军人的PTSD的终身患病率超过30%[5]。
Fiala认为非正义的战争很有可能使一些道德敏感的士兵产生道德困惑[6]。此时领导层(决策层)会利用诉诸战争权来使士兵认为这场战争是合理的,以此稳定士兵的道德价值观。但是往往身处和平环境的群众不认可决策层所赋予的战争合理性。军队与民众之间相互矛盾的道德判断会在士兵内心产生一个艰难的调解过程:如果一个人的同胞不认为这场战争在道义上是合理的,那么士兵们将会遭受道德上的伤害,以及对那些显然授权了一场不公平的战争的人的怨恨。这个时候士兵的道德矩阵会倾倒,造成了道德创伤。
这就很好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老兵鲜有遭受道德创伤者,并且对他们的经历感到自豪;而自越南战争以后的战争,美军士兵经过道德上挣扎者越来越多。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看来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而自越南战争以来的美军军事行动都夹杂着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味道,不能被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单个士兵无疑是道德创伤的受害者,毕竟一场战争的开战权从来都不是由战场上的士兵所决定。这需要国家从集体层面为那些遭受道德创伤困扰的士兵们提供帮助,而最根本的则在于努力确保非正义的战争不会发生。
2 临床精神病学和心理学视角
2.1 创伤源
战争的形式多变,使得士兵难以谨慎辨别非战斗人员(或潜在战斗员),从而使得士兵面临道德选择的压力和行为的失误,例如2003年,由于敌人角色的模糊,20%受调查美军士兵和陆战队员支持对非战斗人员的死亡负责。另外,2006年,在伊拉克,对美军士兵和陆战队员的一项现地调查评估显示,45%美军士兵和陆战队员认为应尊重非战斗人员,17%受调查士兵和陆战队员认为应将非战斗人员作为叛乱分子处置(心理健康咨询团队[MHAT-V],2006)。同样,2007年,运用类似的研究方法,31%表示侮辱或诅咒过平民,5%表示虐待过平民,11%表示在非必要的情况下破坏过平民财产([MHAT-V],2008)。Shay和Andrew Fiala等人认为道德创伤的主体是法定的权威人士,而非自我,强调领导人在战争中发挥的道德权威作用极为重要。而Litz等人作为精神病学家,以战争中的创伤源作为切入点,试图用临床的方法来定义道德创伤[7]。
他们发现,士兵以自己的道德准则为衡量标准,对其采取军事行为进行道德评价,从而产生内在的持久的痛苦。道德创伤的创伤源为:犯下、未能阻止、见证或听闻违反道德信念和期望的行为。这种犯罪行为会导致严重的内心冲突,因为这种经历与自身核心伦理道德观念格格不入。道德被定义为个人和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违反这些规则和假设,便会产生道德创伤。
2.2 创伤症状
Harold G. Koenig认为道德创伤是一种可能会伴随着PTSD而来的疾病[8]。并且他认为目前并没有一种可以进行明确诊断的方式。在他之前的两个课题组——军事精神病学家William P. Nash及他的同事以现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为样本所构建的道德创伤事件量表(MIES)和心理学家Joseph M. Currier及其同事所研发的道德创伤问卷(军事版)——都是通过测量士兵的创伤经历的发生情况以及这些事情造成当前症状的严重程度来判定道德创伤[9-10]。这两个量表的做法是由事件和症状相结合,这些措施可能更倾向于诊断,但是对于后续治疗的评估用处不大。Harold G. Koenig认为有效的道德创伤治疗的方法应该是对于道德创伤的症状能够明显的缓解,同时不会改变创伤事件“事实”本身。另外上述的两种量表都没有评估宗教因素对于士兵的影响。为此他提出了道德创伤症状量表-军事版(MISS-M)。
他认为战争上的一些违背正常社会的行为,例如杀戮、极端暴力是个人道德逾矩(Transgress moral code)的表现。而这会导致两个方面的道德创伤,第一种是信仰上的道德创伤,士兵首先会产生信仰上的混乱,认为自己的行为与相信的教条不符,进而丢失了自己的信仰,或是认为自己不再纯洁了。而第二种是心理的道德创伤症状,士兵们对于自己在战场上所做的事情感到羞愧,内疚。若不对两者进行有效干预,将进而引发临床症状,表现为PTSD症状、抑郁、焦虑、药物滥用和人际关系的混乱及心理疾病。
在此理论的基础上,Harold G. Koenig使用了道德创伤症状量表-军事版以及其他对应症状的子量表对他所提出的临床症状进行了测定(The Moral Injury Symptom Scale-Military Version),发现PTSD(r=0.56)、抑郁(r = 0.62)、焦虑(r = 0.59)与道德创伤症状之间具有较为强烈的聚合效应,但是没有能直接检验出收敛效应。
3 精神信仰视角
3.1 Brock与《灵魂修复》
Brock在“Soul Repair”中叙述到[11]:患有道德创伤的退伍士兵的灵魂是痛苦的,而不是一种心理障碍。愧疚感、羞耻感和悔悟曾经被认为是一种触动人的个人价值观的反馈,现在的方法倾向于把它们作为心理神经症。然而,许多拥有信仰的退伍士兵不相信他们的信仰危机是心理治疗能够解决的。相反,他们将自己的感受视为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他们认为这场信仰危机改变了他们自身的“纯洁”,他们不再是原来的“他们”。加上多种多样的任务和不断的破坏自身的“纯洁”。使士兵们认为这违背了自己与信仰中的“神”,自己的“神”已经不再认可自己。
倘若想要治疗或修复,Philip D. Kenneson认为应建立起某种渠道或方法[12]。而那些牺牲的战友,敌对分子,平民百姓,他们虽然失去了美好的“现世”,但是他们会到天堂。以此来弥补患有道德创伤的退伍士兵灵魂缺失的那部分,达到一种灵魂上的升华。
3.2 Brian Powers与《忏悔录》
Brian Powers则将道德创伤放入《忏悔录》中的进行理解,认为患有道德创伤的士兵,他们往往会有一种模糊的内疚感,或是对事物的正确性感到困惑[13]。奥古斯丁认为,我们愿意遵循我们所希望的。问题是我们的欲望是外在的、扭曲的。Brian Powers认为,人类追求扭曲的意愿在人类暴力的成因和战争老兵道德伤害的现象上有着巨大的解释力。正如一些著名的心理学研究表明,进化、社会和文化力量决定了我们作出批判性道德决定的能力。那些研究士兵的道德创伤的学者,已经发现士兵在参与暴力行为时,甚至是那些“道德”的任务时也会产生的深刻的负罪感。Brian Power借用奥古斯丁的观点认为这些外部力量和我们自身道德价值的扭曲性,从而使我们能够在系统的、广泛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的领域患上道德创伤。此外,他还认为士兵缺少对人类意志的可塑性和对外界力量的深刻脆弱性的反思。
4 总结和展望
当士兵处在战场时,看见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每一件物品都可能是凶器。与士兵所处的长期和平环境大不相同,在这种在复杂激烈变化的战场情境下,道德创伤极易产生。如何避免道德创伤的发生?这既是一个军事命题,也是一个医学命题;既需要形而上的精神抚慰,又需要形而下的身心关爱。只有多学科学者共同致力于此,才能深入认知和把握“道德创伤”这一复合性概念,从而寻求有效的预防和康复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