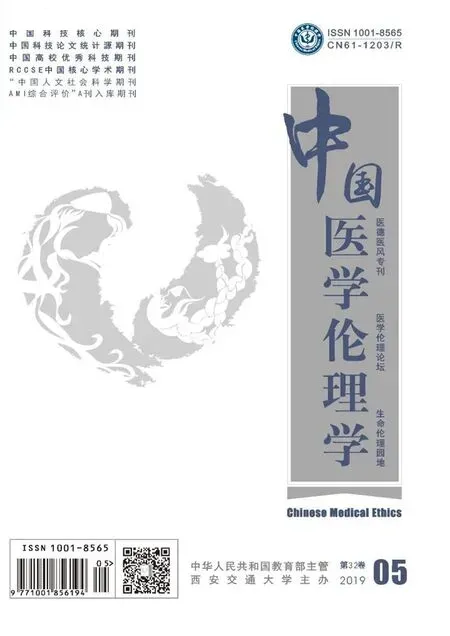伦理原则主义:不同的观点
范瑞平,徐汉辉,蔡 昱,张 颖,边 林,王庆节,孙慕义,丛亚丽,刘俊荣,李瑞全
(1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香港 九龙,safan@cityu.edu.hk;2 南开大学医学院,天津 300071;3云南财经大学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4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香港 九龙;5河北医科大学社会科学部,河北 石家庄 050017;6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香港 新界;7东南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09;8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 100191;9广州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1436;10东方人文研究基金会中国哲学研究中心,台湾 台北)
*范瑞平 整理
范瑞平:诸位好!本刊主编王明旭教授和我就生命伦理学的原则主义理论问题向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丘卓斯(James Childress)教授提出了七个问题,这些问题及丘卓斯教授书面回答的中译文已在本刊上一期发表。这里明旭和我特别邀请诸位对他的回答做一期笔谈讨论,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①丘卓斯教授表明他们的理论属于“共同道德”理论,不同于“具体道德”理论(如儒家或基督教道德理论)。您认为这一区分如何?他同时声称“基于基本文化价值(包括儒家原则和美德)的生命伦理探索不仅在学术上是合理的,而且是非常合适的和有成果的。”这一声称同他的两种理论区分是否协调一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共政策及法律是应当遵循他们的共同道德理论,还是具体道德理论来制定?
②他强调他们的理论超越“基础主义”和“融贯主义”:好像两者皆是,又两者皆不是。这是否说得通?如果像他那样认为“一些得到细化的规范实际上是绝对的”,不允许例外情况,这是否变成了基础主义理论呢?“融贯主义”可以承认这种绝对规则吗?
③他认为更充分的交流无疑能将儒家生命伦理原则和美德与他们的共同道德理论所提供的那些原则和美德相协调一致。您的看法如何?
④他发现在生命伦理学方面最有帮助的工作通常来自那些对一项学科或专业(无论是规范学科、科学学科还是医学专业)有着扎实根基的学者,有建树的生命伦理学家很少是被专门作为“生命伦理学家”而培养成的。这一点对于我们当今的生命伦理学教育和培训有何意义?
当然还有其他重要问题,欢迎大家发表意见,展开争论。
徐汉辉:抛砖引玉,我来就范老师所提的第一个问题谈一些自己的想法。
丘卓斯教授将“共同道德”定义为“所有承诺道德的人所共有的一系列规范。”这使得属于“共同道德”中的规范具有了超越社群的认同性,如“不许滥杀无辜”“不许强奸”等。相比较而言,“具体道德”可以理解为基于某一特定的文化或社群而形成的一系列规范,如儒学中的子女有尽孝的义务。根据丘卓斯教授的定义似乎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即“共同道德”理论中的规范应该也是所有具体道德理论中的规范。这一结论似乎能得到印证:儒家伦理学也反对滥杀无辜和强奸。共同道德理论中的公正原则要求子女感恩回报父母,因为父母含辛茹苦地把子女抚养长大,这似乎与儒家讲的“孝”有一定的相似性。
然而,这种相似性背后却有巨大的理论差异。其中最重要的差异体现在对于规范的重要性排序上。例如,“孝”这一德性在儒家伦理学中排序靠前,无论是“孝出于仁”还是“仁出于孝”,都体现了“孝”的重要位置。丘卓斯教授强调其“四原则”只是具有初始约束力的道德原则,并无重要性排序。这样一来,共同道德体系中感恩父母这一道德规范的位置与儒家体系中“孝”的位置自然差别很大。那么,道德规范重要性排序有无必要?我的回答是,这种排序是有合理性的,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在两种道德规范发生冲突时作出选择。实际上,对不同的道德规范进行重要性排序恰恰是一个具体的道德理论的重要内容。因而,就某个道德规范的具体要求来说(比如子女有义务感恩赡养父母),确实存在“共同道德”;但就某个道德规范的重要性排序来说,似乎很难有所谓的“共同道德”。
如果将“共同道德”理论和“具体道德”理论区别开来,那么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共政策及法律似乎恰恰应该遵循他们的具体道德理论来制定。因为:第一,共同道德理论中的道德规范应该都能在具体道德理论中找到;第二,某一具体道德理论中具有对各种德性、规范的重要性排序,更适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2013年,中国大陆将“常回家看看(父母)”写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其实也是遵循了中国社会重视孝道的传统。很多国家都有赡养法(Filial responsibility law),但要求子女常回家看看的并不多。
蔡昱:汉辉的发言正在消化理解之中,我先来谈一下我对这几个问题的思考。首先,我认为需要区分“形式原则”“实质原则”与“具体道德”这几个不同的概念。
所有的伦理判断和伦理规范都有赖于它的哲学前提和条件(文化就是很重要的差异性条件)。依我的理解,哲学前提主要指对人和人性的假设,文化之间或亚文化之间的最重要差异也是对此哲学前提的不同认定。没有这种认定,道德原则就没有实质性,即成了可以塞进任何东西的空箩筐。因此,如果将“四原则”认定为无哲学前提,那么“四原则”就成了没有实质内容的“形式原则”。相反,儒家或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等具有明确前提认定的原则,才属于“实质原则”。
所谓“具体道德”乃是“实质原则”的落实。这种落实需要反思平衡,即当人们的伦理视野发生变化时,道德判断和道德规范也会发生变化。例如《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2002)(以下简称《准则》)第一次将伦理视野从受试者个体权利拓展到公共卫生,提出研究应针对受试者所在地人群的卫生需求和优先需要;同时,该《准则》还将人体试验看作是有利的,而不仅是风险,第一次提出如要将能从研究中获利的群体排除在外需要有合理性论证。
因此,“形式原则”在没有落实其哲学前提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转化为具体道德的。而如果落实了哲学前提,便已经转化为“实质原则”。这样看来,如果将“四原则”认定为“形式原则”,则“四原则”没有存在的必要,因其应用必须首先转化为“实质原则”。依我的理解,“四原则”是有其隐性哲学前提的,即启蒙理性下的“原子式个人”理念和权力至上的信仰,是一种以权力为中心的伦理传统的延伸。因此,我并不赞同丘卓斯教授的观点,即在充分交流下就可以发现“四原则”和儒家生命伦理学的原则和美德是可以相互协调的。他特别提到的“互惠”,更像是顺着市场主体的思路而设想成“原子式个体”的功利性交换原则,这与儒家所讲的仁爱的关系和谐并不能协调;“有利”也更像是“原子式个体”的功利性计算,其冷漠性与仁爱也不能协调。而冷漠性难道不是当今如此高发的医疗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吗?
张颖:由于现代多元文化既缺乏哲学的形而上学,也缺乏宗教信仰的同一性,因而试图建立基础主义的道德理论或普遍的道德原则会有很大的挑战;同时,情境主义、叙事伦理、美德伦理这些具有相对主义色彩的理论也有其明显的弊端。基础主义不能放弃“事实的普遍化”或者“在永恒的相下”(sub specie aeternitatis)道德判断的审视,正如知识论上的基础主义不能放弃逻辑原子论一样。
由于强调其实践的意义,被称为“原则主义”的生命伦理学“四原则”并非基础主义的道德框架,而是对道德判断的辩护,形成“辩护的融贯性”(coherence account of justification)。基础主义强调形而上学的“不变”(the fixed)或神学上的“所与”(the given),两者都被“四原则”所否定。“四原则”更重视融贯论,强调一个信念的辩护在于它与其他信念的关系。也就是说,信念的证成是要放进整合的系统里,达到适应(fit)的效果。所以,丘卓斯教授虽然提出共同道德作为理论构建基石的重要性,但同时强调反思平衡,希望从中找到其理论的融贯性和灵活性。
其实,所谓“共同”亦是基于人们的道德直觉、价值观判断上的相似性,以及道德价值观在表达形式上的“家族相似性”,而非完全一致的道德原则。比如说“有利原则”的共性,这里的“有利”(beneficence)到底是一种“道德理想”还是“道德要求”呢?前者将之视为“超义务” (supererogatory)行为,而后者则认为它属于一般义务范畴。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不同的解释就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准则。
徐汉辉谈到有关“孝”背后所隐藏的“共同道德”议题。他提到西方国家的“赡养法”隐含“回报父母”的道德规范,这是个有趣的问题。美国有些州政府的确有这个法律,但仔细看这些法规可以发现其主要目的是要在法律上确立谁来负担欠款的问题,即经济考虑大于道德考虑,与儒家传统的“孝道”有很大的差别。再者,用儒家的仁爱伦理或女性主义的关爱伦理取代“自主原则”和“人权”也是令人怀疑的(如以爱的名义在人际交往中实施的各种情感勒索)。不同的道德原则各有各的考虑角度,解决的是不同的道德问题,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取代的关系。
范瑞平:谢谢汉辉、蔡昱首先发言。我同意张颖的看法——丘卓斯教授的原则主义更接近融贯主义而不是基础主义。基础主义不能放弃一些基本的信念,例如无神论者不能相信有神,基督徒不能怀疑耶稣是神的唯一儿子,康德主义者不能允许说谎……这些“基础的”信念是不能为了同其他信念相融贯、相协调而改变的。但丘卓斯教授似乎不接受这一点,大家可以仔细看看他回答的关于“乱伦”问题的说法,他特别强调与其他原则和规则进行平衡。
不同于汉辉,张颖看到中西方在孝道的实质考虑上(不止排序上)的不同,但似乎提示融贯主义(如丘卓斯教授的原则主义)在当今多元化现状下比基础主义(如儒家道德)更可行或更有用。但考虑到原则主义与(例如)儒家道德的不同(在这一点上张颖似乎同意蔡昱的观点:即使在充分交流下也无法使“四原则”与儒家生命伦理学的原则和美德达到相互协调),基础主义是否可以作出合理的回应呢?汉辉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共政策及法律应该遵循他们的具体道德理论来制定,这一点能否得到辩护?
徐汉辉:我同意张老师在文中提到的,“所谓‘共同’基于人们的道德直觉”,而且应该是广泛认同的道德直觉(Widely shared intuition)。不过,我想,“共同道德”理论的支持者会强调,或许不存在完全一致的道德原则,但某个道德原则的伦理基础及其具体要求会有“共同”的可能。仍以“孝”为例,西方伦理学中与之对应的概念是“Filial obligation/Filial duty”,即子女对父母需要承担道德义务。就伦理基础而言,孔子认为子女应该对父母尽孝是因为父母对子女有生养之恩,也就是说,孝源于感恩。同样地,在西方,包括西塞罗和基督教哲学家在内的很多哲学家也都认为,Filial obligation源于对父母的感恩。就具体要求而言,在孔子那里,孝不仅是“能养”(父母),还要“敬”(父母)。在西方,类似的表述也被提及(见Jeffrey Blustein.Parents and Children:The Ethics of the Family)。
其次,一些具体要求的不同也许恰是重要性排序不同的体现。比如,在中国有“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法,这实际上是体现了对父母的义务(孝)比在某些事情上的个人自主选择(远游)更重要。也许正是因为孝在儒家哲学中重要性被不断强化,才使得儒家学者不断给孝赋予新的内涵和解读。比如,朱熹修改了孔子的“孝源于感恩”,认为孝源于天理。
具体到美国的赡养法(Filial responsibility laws),法律条款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伦理价值的体现。西方社会中对于Filial obligation的理解在很多地方与中国社会对于孝的理解有共同之处。美国的赡养法之所以只规定了偿还欠债,而没有像中国法律那样规定常回家看看,可能只是因为,在美国尽管人们也认为子女有道德义务满足父母的精神需求,如陪伴父母(至少Jeffrey Blustein是这么认为的),但并没有重要到需要用法律规定子女常回家看看的程度;或者,尽管子女有道德义务满足父母的精神需求,如陪伴父母,但这会与子女的自主性安排自己的生活发生冲突,而后者可能(在排序上)更加重要。当然,基于儒家伦理学的孝是一种德性,而基于原则主义的“子女应该赡养父母”是一种原则,从这个角度说,儒家的孝和原则主义下子女对父母的义务确实有所不同。但德性伦理学中也有道德原则和规范,这些原则或许可以和其他伦理理论中的某些原则有“共同”的基础。
张颖:美国的《赡养法》来自英国的《济贫法》(poor laws),与经济上的福利制度相关。美国并非所有的州都有赡养法,因为不少美国人反对这种强制的法律。他们的理由是,孩子的出生不是他们的选择,所以对于父母必须有儿童抚养法,而赡养父母则不同。现在美国的赡养法,常常与老人医疗费用的纠纷相关,很多人认为是州政府以此要求“第三方”付欠款的方法。由此这里的“孝”表现为救济行为,所以我认为与儒家的孝道根本不同。其实,美国政府在实施这项法律时非常谨慎,赡养法的前提是,成年孩子必须有一定的(reasonable)经济能力抚养他们自己的后代和家庭,否则不能强制他们赡养父母。有意思的是,美国的赡养法常常和医疗费用的讨论相关,因此赡养法的提出显然与联邦政府的医疗辅助项目(Medicaid)经费不足有关。
徐汉辉:美国大多数州都有《赡养法》,内容规则略有不同,但核心思想是要求子女(也包括其他家庭成员)为年迈的父母提供物质支持。这些支持包括提供食物、衣服、住所等必需品。不过,如张老师所说,这些法律侧重要求子女对父母提供经济资助。另外,新加坡也有类似法律。我还是觉得,不能否认这些政策法律背后的一些共同的道德基础。
王庆节: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就张颖所指出的当代西方主要论证提出反驳。在我看来,父慈子孝,乃天下之公德,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但近代西方以意志自由和个体选择为基础的某些伦理理论却对此提出质疑。例如,曾任美国克林顿政府全国医疗改革计划高级顾问、现任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伦理哲学教授的丹尼尔斯(Norman Daniels)就论证,在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相互道德义务上有着一种“根本的不对称性”,并且这种不对称性有着事实上的根据,即所有的子女来到这个世界都非经其自愿同意,因而他们对于父母并无赡养的道德义务。
对于这种论证至少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我们没有同意或没有自愿选择成为我们父母的子女?这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假问题?当我们说“同意”或者“不同意”“选择”或“不选择”时,我们除了假设这种“同意/不同意”“选择/不选择”不是在强迫的条件下发生之外,我们还必须假设真的存在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基于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丹尼尔斯的问题假设的是一个虚假的前提,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选择是否作为我们父母的子女的可能性,甚至没有选择是否出生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我们既没有选择作为我们的父母的子女的机会,也没有不选择作为我们的父母的子女的机会。如果根本从一开始就没有这种机会,如何谈得上“同意”还是“不同意”“选择”还是“不选择”呢?
第二,我们有必要区分“强同意”与“弱同意”两个概念。“强同意”说的是一个有决定能力的成年人主动地、明确地要求或赞许做某事,“弱同意”既可以指一种被动的准许,例如没有明确反对某人对你做的某事或默许此事的进行,也可以指某一尚未具备完全责任能力的人的主动行为或被动的准许对之进行某种行为。显然,倘若未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有一种“同意”关系的话,这种同意属于“弱同意”。假设有一位年轻人,今年20岁,精神正常。他在邻居家的房子里玩火,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他不仅应当在道德上遭到谴责,而且会在法律上受到追究和惩罚,因为他的行为属于主动同意或“强同意”行为。但如果我们稍稍改变一下条件,假设他不是20岁的年轻人,而是15岁的少年,甚至10岁的孩子,情况会怎样呢?显然,因为这是一种“弱同意”行为,他也许不应当像成年人那样受到严厉的责备和惩罚,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完全没有任何道德责任,完全不应受到责备和惩处。因此应当说,当幼年子女“自然而然”“心安理得”地接受父母的关爱、牺牲与付出时,他们已经对父母-子女关系给出了某种“弱同意”。这种“弱同意”虽然不像“强同意”那样要求子女对日后赡养父母承担“全部”责任,但要求其“部分”地承担责任应当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这种“弱同意”随着时间与子女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强,与此同时,我们作为子女对父母的道德责任也变得越来越强,最终会达到“强同意”的程度。
范瑞平:欢迎庆节加入讨论。记得十多年前在李瑞全教授组织的生命伦理学国际会议上,曾与丹尼尔斯就此问题发生过很不愉快的争论。回头去看,双方可能都带点情绪,不是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瑞全沉默没有参与争论,但有的大陆学者发言支持丹尼尔斯的观点。丹尼尔斯的论证显然是从个人主义、契约主义的道德前提出发的,带有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鲜明特色。但丘卓斯教授声称他们的“四原则”是从“共同道德”(而不是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文化道德)出发的,那么从“四原则”的角度看,他是否会同意丹尼尔斯的观点呢?他在这个问题上将如何解释和平衡自主、有利、公正等要求呢?需要找机会再问他一下。在蔡昱看来,“四原则”似乎也无法超脱现代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价值理念所设定的领域。
王庆节:还没有看到丘卓斯教授在这方面的观点。丹尼尔斯的论断的盲点就在于他把作出同意,承担道德责任的行为主体视为一个非历史的、孤立的、抽象的个体,而非一个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学习、成长着的活生生的人。丹尼尔斯这里也混淆了道德责任主体与法律责任主体的界限。不错,我们并非生来就有同意的能力,就可以承担道德责任,但是,我们也不是一天之内就获得这种能力和承担的。所以,硬性地强调在“成年人”与“非成年人”的道德同意之间作出绝对区别,除了能为某些人对待父母的忘恩负义行为开脱之外,大概什么也说明不了。
张颖:因为探讨共同道德的可能性,汉辉说到了西方的赡养法,引起了我的注意。从庆节的文章我看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以“自主”“选择”“责任”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思维方式的差异。庆节所谓父母“含辛茹苦”的说法(且不谈苦中有乐),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是与自由选择原则相矛盾的,因为即便是苦是累,选择者作为道德主体应为此负责任,而不是把这个责任加之于其他人。从这个角度看,有关“不对称”的论述完全符合自由主义的道德观(是否一定是契约关系,需要另作分析),但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儒家思想。儒家的道德考虑带入了很强的“情”的成分。西方由于基督教的影响,会把“爱”与神的“礼物”相提并论,孩子是爱,是礼物,而不是长线的、需要有回馈的投资或交换形式,但我们中国人好像很难接受这种思想。美国的赡养法和中国的“常回家看看”一样,是政府通过法律建构的一种强制的公共道德,有违自由主义的道德原则。这里我们看到了不同道德原则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所谓共同道德,如果没有相同的宗教或文化传统的支撑,实际上是很脆弱的。
丛亚丽:“共同道德”是值得好好讨论的,但我不赞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需要集中在“孝”这个问题上来说,并以此展开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我个人一直认为大家要一起讨论交流,家庭内部的关系和道德规范是介于个人与社会规范之间的事情,不是伦理学关注的主战场。虽然它很重要,是我们生活中无论幸福还是痛苦的主要来源,是伦理学的一部分,但伦理学更应该关注一个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而非家庭关系)及其规范。现代伦理学主要是对于个人作为独立个体、作为真正自由的人、对于需要社会提供体面生活保障的个人的关切。在这方面的讨论内容中,我更赞成张颖的想法。
丘卓斯教授对于问题1、2、3、4的回答,虽然不说自己是什么固定的主张,但其实就是个人自主至上的理念。但他确实承受不起他人对他的批评,“淡化了美德”的倾向。无论如何,这是他该承受的。为什么不敢呢?或者说他什么都想圆满和平衡,但其实做不到。“四原则”就是帮助生命医学领域的人们去应用和思考甚至解决伦理问题的工具。而真正的生命伦理学的理论思考,还需要进入伦理学视野和领域。
边林:我换一个题目来谈一点看法。丘卓斯教授对于王明旭、范瑞平所提问题的作答,提示中国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界应当重视学科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的研究。从事医学与生命伦理学研究和教学的教师和学者,或许没有人否认学科本身的实践特性,且不说生命伦理学就是为了认识和解决层出不穷的生命伦理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学科。学科意义上的医学伦理学在三个多世纪前形成的时候,甚至可以说中西方古代的传统医学道德思想的产生和进化,直接的目的也都是为了解决医学中的种种职业道德问题。然而,不能因为强调学科的实践特性,就认为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没什么价值。毋庸讳言,当今中国学界确实弥漫着一种反对所谓“放风筝”、主张要用“骑单车”方式开展研究的倾向。如果这种主张是成立的,丘卓斯教授和比彻姆这本专门研究“生命医学伦理原则”的著作,可能就是国际生命医学伦理领域最大的、飞得最高的那个“风筝”。其实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有赖于理论与实践、逻辑与事实结合起来的深入探索,尤其像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这样尚在发展中的学科,理论与实践任何一方面都不可偏废,何况这些学科因为是“伦理学”还带有哲学的基因,非要将二者割裂开来,而不是考虑应该“骑着单车放风筝”或“放着风筝骑单车”,似乎有些不那么“哲学”了。
孙慕义:我接续边林教授的议论,提几点个人意见。诚然,一切现实在某种方式上都是某种精神构筑,医学世界不会存在于人对于它自身的观察和表达之外;被R.J.约翰斯顿强化的理念论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的哲学。它反对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及其对客观证据的强调;又如尤因(Ewing,1934)指出:理念论包含一种信仰,即人对宇宙的认识是由各种精神价值决定的,理念论包含更为广阔的哲学范围。为了发展学科,为救火而挖井取水,为了评价和解释证据,为了不得不使用一些标准,建立原则,就要回归于理念论的核心的研究,就必须确立一致性理论,包括真理的定义、对现实性质的说明和确立医学真理的标准;让我们的说教,真的不是为了只知“按原则”办事而是“一切为了人”去办事!没有思想,我们几乎不能领悟现实。真理是“使真实成为真实的东西”,海德格尔说,真金的真实并不能由它的现实性来保证。事情真理离不开命题真理,我们必须搞清“物与知的符合”,才可回答医学生活中的什么才算“正确性的真理”。
我们的生命伦理学研究水平一直被限制,始终在一个低俗的阶段迂回和循环;除了这支队伍的知识结构和学科晚发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过于纠缠于“问题式争论”;特别是有些过于迁就医学界或具体从业人的喜好,作为其装饰;临床学家的“人文”兴致,对形而上的规范研究有现实主义启发功效,但无益于研究的深度和高度;哲学不是随意可以涉入的,我们不愿意再看到所谓“××医学”这样的闹剧。面对异常复杂的身体与疾病现象,应反对把“医学人文运动”作为一场大众的“游戏”。因此,不能同意丘卓斯教授回答的第四条“有建树的生命伦理学家很少是被专门作为生命伦理学家而培养的”: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长期的哲学训养、没有博大精深的学术修炼、没有艰苦的读书和苦思的过程,如何能成为“生命伦理学家”呢?这就是迄今为止,包括欧美在内的当代世界上,尚没有一个真正称得起为“生命伦理学大家”的原因。当然,如果,抛开“生命哲学”那一派,恩格尔哈特先生可以作为这样的生命伦理学家的榜样,但他并不被丘卓斯教授一派看重。
丛亚丽:孙教授不赞同丘卓斯教授关于生命科学家的作用,那要看具体指向了。我理解丘卓斯教授所说的是经过PhD训练的科学家,不是我们周围那些只会煲点“心灵鸡汤”的科学家,他们似乎很懂人文哲学,但其实只懂一点点皮毛,成了一种“万金油”式的生命伦理学家,讲的很多事情经不起推敲。
边林:从丘卓斯教授的回应可以清楚看出,他们之所以选择使用“生命医学伦理学”而不使用“生命伦理学”这个概念,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两个相互关联但性质并不完全相同的学科领域。我也非常赞同强调学科的实践特性,甚至也认为这种学科的性质属于实践伦理学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认识、探讨和解决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问题,除非认为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尚不构成学科,而只是一种专业领域的活动,是临床实践和生命科学研究中不断提出需要站在伦理立场上认识和解决的新问题,且这些问题是散在的、随机的、突发的和无定律的。事实上,无论从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概念所自带的“学”字本身所标明的,还是从这两个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析,再就是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有关学科的专业设置和专业及公共课、通识课等非专业教育上看,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的学科形态是确凿无疑的。
既然是学科,既然是教育、教学和课程,就需要学理建构、逻辑体系和理论系统,即便是教给学生方法,背后支撑方法的也是理论。单从教育意义上看,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不阐释清楚,无法完成通过教育过程和特定教学方式向教育对象进行精神、理念、理论、方法和知识的传输,也就达不到素养培育和能力培养的目的。基于现实和具体问题的研究,也不可能在逻辑上与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完全脱节,认识上的深入和思想的创新本质上最终都会归结为某种新理论的形成,而这种所谓的新理论至少是现实问题与传统理论两方面结合(甚至是更多要素综合)生成的。关于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其与医学伦理、生命伦理实践的关系问题,需要专门的讨论。在中国学界为实际去解决医学与生命伦理问题的不懈努力中,应当充分地认识到这样两点:一是在这个领域的理论研究还是需要特别强化,这种研究一方面基于实践但不能流于对个案和具体问题的简单分析,另一方面也可以如同《生命医学伦理原则》这部著作和它的作者一样,基于人类伦理认识成就而逻辑地展开对新的生命医学伦理问题的认识和分析,在推进理论创新的同时完成对实践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二是既然基于中国的现实生命医学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就应该在对国际相关研究成果借鉴和吸收的同时,多一些源于中国自身传统伦理文化的新认识,让国际生命医学伦理学领域增加一些中国特色的伦理元素,将引进和输出结合起来。
孙慕义:我同意边林教授的建议:需要学理建构、逻辑体系和理论系统!在我看来,丘卓斯教授他们的理论不属于共同道德的理论,不过是具体的对于方法的指导,只是比基督教道德或儒家伦理少了一定的限域。事实上,任何文化语言的道德理论或由此产生的原则或规范,都具有鲜明的文化特性,但又都含有“共同”的“善与正当”的内核,这取决于各文化框架内的认识论的“共通感”,按康德的意见就是心的统一;共通感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文化差异(异乡人情感)的内涵,始终存在一种分离的倾向,即某一具体道德的个性。共通感也可以作为普遍主义的基础来理解(不是他们所指称的基础主义),它区别于特殊主义的缘由是我们必须寻找隐藏(或蕴涵)在判断或标准中的“共认意识”“共通感”和“部分共认意识”是恩格尔哈特“允许原则”的必要前提。人的判断能力的强弱有赖于是否具有深笃厚实的哲学功力;而作为标准的实践验证和行为的取舍,就比较容易把握。连贯论或融贯论,就是互通-共通-融通,是认可普世价值的前提,也是自由世界主义观念的基础,或作为商谈伦理的条件。
我以为彼彻姆和丘卓斯教授主要还是接受了实用主义的影响,但他们又有别于实用主义伦理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改善主义”(meliorism)。改善主义介于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既体现了这类学者对于未来世界通向光明的信心,又表达了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以及对现实生活问题的正视。这个概念反映了人类对于身体获救和精神救赎双重的祈盼和渴望,表达了詹姆斯心性的最后皈依和对柔性宗教的美好理想。这和我们国人理解的“有用就是真理”、只谈问题不讲“主义”的“单车风筝”论是有差异的,即对现实价值的依赖的同时,不要失去对于身体获救与灵魂救赎的真纯意识和主观生活意义之流的寄托;这里有一个深隐的信仰“动元”和形而上的玄学的思考。“风筝单车”说的提出有一定局限。每个人都同时放飞自己又脚踏实地地生存,作为学人,谁能不迷恋真正的哲学呢?可能有人会觉得哲学是晦涩和深沉的,不屑一顾,但如果没有哲学的承托,哪里有我们的伦理学的合法性!
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和丘卓斯教授等人的几个原则,根源自于古训或圣训;它们都是对“共同道德”的善与“金规则”(爱你的邻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爱的具体行为标准的实践表达,是“思”之必“执”,是对“率性而动”的限制,“散朴则为器”,自在(不证自明)自为的戒律和法条,同时还要避免行动生态主义(事与愿违)的后果,因此在应用这些原则时,我们有必要学会控制与调节,平衡原则应用中的冲突;学会纠错、医生干涉权(父权论)、取舍原则、反省原则、允许原则、宽容原则、拉弗曲线原则等,都是对这些不完善原则的补充与控制。我们至今沿用的、移植过来的这些原则自身存在很大的逻辑破绽,也不尽合理与整全,需要重新审视、清整与梳理。
丛亚丽:赞同孙教授对于丘卓斯教授他们的原则主义理论的看法——“四原则”不属于共同道德的理论,而是具体的方法指导。
刘俊荣:我来对于“共同道德”与“具体道德”发表管见。丘卓斯教授在批判分析功利论、康德的义务论等多种伦理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原则”,并以此构建其生命伦理学理论体系。在他看来,以“四原则”为核心的共同道德理论,不同于儒家、基督教等具体道德理论,是一种超越具体文化局限的普适原则。但问题是,这种共同道德理论的立足点或者说本原性假设是什么?为什么这“四原则”能够作为普遍性原则?我认为舍去康德的三大绝对律令而为“四原则”找到一个共同的原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康德强调:“要只按照你同时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这是道德原则形式上可普遍化的必然要求。依此,一个原则能否成为普遍原则,首先要看原则提出者自己是否愿意按照该原则去行动,是否也愿意适用这一原则。只有当愿意将这一原则用于他人之时也同时希望适用于自身,该原则才能成为普遍原则。如:在扳道员伦理困境中,如果你就是那个站在另一道轨上的人,你是否为了救对面道轨上正在作业的5个人而愿意让扳道员将火车扳向自己所在的道轨?如果在这种情形下,你不愿意让扳道,则当另一道轨上的人不是你自己时而你主张扳道的利他主义,就不具有可普遍性,不能成为普遍性原则。由于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不仅对他人,也希望对自己给予尊重、不伤害、有利、公正,因此这四个原则才能成为普遍性原则即共同道德。
因此,基于康德“绝对律令”的共同道德原则,与基础主义并无截然的不同,仍有其基本的信念即“人是目的”“意志自律”。之所以要坚持“四原则”,是因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目的性存在;之所以“四原则”能够成为普遍性原则,是因为它们符合普遍立法之律令。
在共同道德框架下,“×应该做什么”,主语人称的置换丝毫不会影响宾语的内容,“应该做什么”与主体的文化背景、价值信仰及所处境遇无关。从理论层面来说,“四原则”与具体道德理论不同,具有普遍适用性,能够为不同的文化主体所认同。但当这“四原则”运用于现实活动解决具体问题时,之所以会产生尊重与不伤害等原则间的冲突,正是由文化差异、价值诉求的不同造成的。至于“四原则”中哪一个更为根本、哪一个权益位阶更高、如何排序,也很难有完全一致的道德共识,达成所谓的共同道德。因此,共同道德原则只能停留于抽象的理论层面,不同的利益主体和行动者必然对其有着不同的诠释和解读,就此而言,现实活动中的共同道德需要具体化,无法超越具体道德。
事实上,道德理论的共同性与具体性只是相对而言的,即使儒家伦理中的“孝”也有共同与具体之两重性。“孝”作为儒家伦理的普遍性诉求,不同主体对其也会有不同的解读。如:在急危重症情况下,尊重父母错误的医疗选择是孝、还是违背其意愿而维护其生命健康是孝?忠、孝、仁、义等何者最重?如何解读孝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关系?这些都难以有完全一致的道德共识。
蔡昱:看了各位的发言,很受启发。就像刘老师所说,应用中,不同的主体对“四原则”会有不同的解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四原则”认定是没有哲学前提的“美好标签”,则加入不同的人和人性假设,就会表现为不同的样态。同时,理论上我不认为没有哲学前提的标签性原则可以作为普遍性的原则或普遍性的基础——我们甚至可以将相反的决策放在同一个标签下。对普遍性的研究应该回归生活世界,形式的、抽象的原则不是切入点。
同意丛老师所说,“四原则”是建立在个体自主至上的理念之上的,这和孙老师和刘老师所说的“四原则”和康德哲学的关系是一致的,即个体优先于共同体和集体,权利优先于服从(当然,本质上,现代以来的“大众社会”奉行的和体现的反倒是面对异化的社会力量的“顺从主义”,因为没有真正的人的世界就没有了人的“权力”)。这和儒家对人的假设完全不同。因此,具有完全不同的人的假设的“四原则”和儒家生命伦理学的原则是不能协调的。同意孙老师所说,“共同道德”建立在“共通感”之上。我更愿意将此基础称为“通达性”,而“四原则”和儒家生命伦理学这两者假设的人恰恰是不能通达的,因为原子式的个体的所有活动都是被抛回自身的。同意张老师所说的,现代多元文化下建立普遍的道德原则具有很大挑战性。
同意边老师和孙老师对理论构建的思考。我们需要回到对人的关切,回到对“100%纯金”的思考。再者,医学和生命技术中的反思和批判也需要交给哲学完成。当然,生命伦理学也需要对技术和它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一般了解,这是这个学科困难的地方之一。
张颖:我同意庆节对于丹尼尔斯过于抽象、脱离历史情境的质疑。同样的质疑也适用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他们用的都是一种逻辑上的默认。
但需要强调的是,父慈子孝应是双向的、互动的。子女愿意行孝,父母就会有幸福感;子女自愿行孝而非被要求行孝,子女自己才会有幸福感。但在传统社会里,父不慈子也不能不孝的例子也不少见;当今有些父母以孝道为名,对子女进行“情感勒索”也不是奇怪之事。所以才会出现关于“相互性孝道”与“权威性孝道”的争论。另外,不得不说,在政治生活领域,泛孝主义或权威性孝道(绝对忠诚)真是一件可怕之事。
当“为自己好”与“为父母好”出现孝顺的难题时(当然也有不冲突的时候),比如孩子要学哲学或文学,而父母要求他/她学商科或医科——出于对子女就业的考虑,子女应该如何选择?这里的确有个体意志与父母关系的道德冲突。前一段,我看到一则报道:一位内地通过钢琴8级考试的女生到了美国后,说她患了钢琴恐惧症,现在任何钢琴的乐曲都不要听,原因是她从小被父母逼着学钢琴,所以弹琴只是行孝道,但自己已经失去对音乐的真正喜好。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个极端的例子,但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另外,庆节批评丹尼尔斯混淆道德责任主体与法律责任主体的界限。但像“常回家看看”这样的法律是否也是越界了呢?抑或政府以倡导某种道德为名,制定某种符合那个道德原则的法律规定,是否也是越界的行为?
李瑞全:阅读各位的高论,实非常心切要加入讨论,以就教高明。瑞平提到的台湾会议上的争论,事已太久,我的记忆都有点模糊了。但此中实含有中西文化的一些基本差异性在内,反映了中西方伦理与文化对此论述的不同,可以见出中西方哲学思考的差异和对生命经验的不同了解。
关于道德理论之建立,未能及时响应一些同仁如边林教授的高见,请谅。我认为丘卓斯教授他们书中所采用的一个架构:“道德理论-道德原则-道德规则-道德判断”是一个很好的分析和论证的架构。但在“道德理论”(moral theory)层次,他们的说明其实不足。“共同道德”不是一个道德理论。康德的义务论、穆尔的效益论、儒家的伦理学等,才是一个道德理论。因为,一个道德理论必须说明道德是怎么回事(what is morality?),即道德之为道德的特质是什么。“共同道德”只是指出一些行为规范(norms),这些规范只说如何行动是道德的,如公义原则指出我们要如何行动才是公义的,但没有说明何以这种公义行为是道德的。道德理论才能说明何谓道德。例如效益论可以说明公义原则是道德的,因为,当我们按公义原则而行动时,我们会实现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公义原则是道德的。儒家会认为公义是仁或仁心的同情共感的表现,公义是使每个人都得到公平而合理的对待。仁、义、礼、智、信等都是仁心的表现,都是客观而有合理性在内的行为规范(不少人误解儒家讲“仁爱”变成以“爱”为道德的表现,成为主观的感受的表现,丧失了儒家所强调的道德的客观性、普遍性、恒常性与合理性)。儒家的理论结构可以简化为:仁心/不忍人之心——仁义礼智信忠恕、各尽其性分、参赞天地之化育等道德原则——男女授受不亲、爱人、恭敬等等道德规则——救助快要溺毙的小孩、寡欲、扶贫、捐助等等行动和判断。儒家的伦理学核心观念是“仁”,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亦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不吃嗟来之食、人性善(有内在不可取代的价值)]和每个人的生命价值(行一不义杀一不辜以得天下,不为也)。群体之间以礼相待,和而不同(容许多元价值和多元文化),建立一个让每个人都能够各尽其性分的社会,可以养生送死无憾。
我认为儒家的义理和生命伦理学不但深切于道德的原初经验(不忍其他生命受伤害的道德经验),由此建立的道德的理论、判断和行动,可以容纳个人的自由、自主、自律的道德,生活共同体中共认的道德规范(共同的道德性),由实践仁义而体现为个人的美德或德行(美德论),处事和谐、互敬互爱互助,扩大而视天地万物犹如一身,互相关怀和具有同情共感的感通(关怀伦理),可以具有特殊的宗教或精神的体验(普世伦理),正视每个人都是在重重感情交织的社群中生活。简言之,儒家生命伦理学可以在不同程度和层次中吸纳中、西方各种伦理学理论,以至分析论辩的方法,扩展成为一开放多元而又具有统合性的理论。
张颖:多谢李教授的详尽论述,实为受益,尤其是对儒家道德的整合及辩护:从仁爱到公义;从孟子的道德直觉/原初经验,到张载的同情共感/关怀伦理;从个人的自觉、自主到共同体的互爱、互助;从普遍性到合理性……似乎该有的都有了。如此之完美的、从义理到实践的体系,反而使我起了一点疑心(对不起,我是天生的怀疑论者),这个疑心也是我对共同道德作行为规范之基础在具体实施上的疑问。比如,儒家对个体尊严的陈述问题。我们知道,孔子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豪言,孟子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壮语。但我觉得,这里尊严被看作君子/大丈夫所要追求的气节和风骨,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要求和约束。由于这个道德杠杆抬得很高,“尊严”(human dignity)从基本的保护机制一下子变为人格理想的要求,其结果是尊严成为精英的理念,而非是保证每个人当下的(在“人的地位”意义上的)“受他人尊重”的尊严(尽管儒家也有人人有仁义礼智信的潜质的说法,其似乎预设了每个人的内在尊严)。由此,儒家的人格“尊严”是道德教化的一部分,而不一定是法律保护的一部分(譬如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儒家的“尊严”最多落实在以“仁政”为基础的“民享”(for the people),但不可能是“民治”(of the people)。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儒家体系与西方自由主义体系的不同。儒家道德在其自身的体系中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与西方启蒙思想下的自由主义道德体系具有巨大的鸿沟。起码我不觉得儒家会把人格尊严看成一种个人权利。再有,李教授认为儒家的公义是“使每个人都得到公平而合理的对待”,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透过“共同道德”来解决何谓“公平”、何谓“合理”的判断?
李瑞全:张颖所提的问题和“怀疑”都是我们在伦理学中最深刻和根源性的课题,实难在此作出恰当的一一回应。瑞平提示讨论时限即到,我想对丘卓斯教授的回答作一些一般回应。
首先,丘卓斯教授将共同道德定义为“所有承诺道德的人所共有的一系列规范。”这是从现实所见之社会共同认可的“道德规范”而立言,但这不免是个别特殊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s),这在理论结构上实有不通之处。若共同道德是跨种族文化的,而“四原则”只是其中一些重要的共通的原则,此共同的道德性(common morality)应是更广泛普遍的。若只是由特殊的规范所得出来的,则此“共同道德性”只是某一更普泛的“道德性”所表现在某个文化中的一些日常的规范(或具体行为规范或行为模式),而“四原则”反而是高于这些特殊具体行为规范的普遍原则。
其次,他表示这“四原则”是运用罗尔斯之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的方式得出来的。但从他们的书来看,这一反思平衡的过程似乎是共同道德性之内的“规范”与西方社会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四原则”之类)之间的衡量,由此得出“四原则”,但不代表是共同道德性之内所涵的原则。至于参与进行反思平衡考虑的规范是哪些?恐怕也必是在西方社会文化之下所共同接受的一些特殊的行为规范,这即不可能没有西方文化的特定面相在内。
丘卓斯教授还强调,“我们所达到的结论是:通过考察道德判断和道德信念的融贯性而得出的这四条道德原则处于生命医学伦理学的中心。”虽然丘卓斯教授强调不是个人主义,但所用的反思平衡是以理论与判断之平衡而定(取得最大的公约数)。它们被认受的是在一典型的个人自由主义的美国社会(如罗尔斯所显示的,是一以“公正原则”为根本原则的社会)。所以,原则主义的四个基本原则也必然反映这一特殊取向。这可说是有限度的基础主义与融贯主义的结合。
他说明,“我们从对于一组深思熟虑的判断的反思平衡的过程开始——这组判断,特别是四条原则,不经论证支持就得到我们初始接受为探讨生命医学伦理学的一个框架。”但原则主义所达到的不是个别的判断,而是四大中层原则——此如何由反思平衡达致,实没有被说明,而只是据美国社会的某种共识。如表现在《贝尔蒙报告》(Belmont Report )中的三个(实即四个)基本原则,而视之为经深思熟虑后的“判断”(原则),此实明显有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文化价值的背景在内,而个人自由主义即是其基础。
他指出,“我们并不排除(超出我们的四项原则之外的)其他重要规范也将构成生命伦理探索的一部分中心内容的可能性”。这算是一客观合理的表示,即,“四原则”具有一定的“中心”地位,但其他道德原则也可以同样具有“中心”地位。此如尊重当事人的自主自律固然可说是跨文化种族地被共同接受的,但具体的自律原则却不必限于“个人主义式”的个人自律而已。在中国文化之下家人之亲密性,实不只一般情感上的亲密,更被视为人伦的关系,家属参与患者的决定乃是自然而理所当然的,港台大陆在看病时几乎都与家人一起,不像美国那样只接受患者自己——除非患者同意让家属参与,这即表示个人自律是西方社会的一种特殊规范。按丘卓斯教授此说,则我们主张伦理关系自律(ethical relational autonomy)自是合理而且也是一中心的规范,不是中国文化的偏颇(且不说谁更恰当)。
范瑞平:非常感谢诸位的积极参与和精彩讨论,明旭和我也将把大家的看法摘要转达给丘卓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