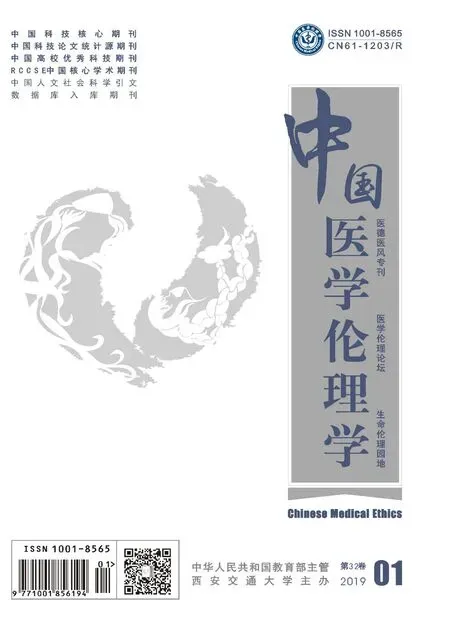“临床伦理抉择”系列讨论之一
——面对不堪忍受的插管之痛,医患双方该怎么办?
张新庆,李瑞全,蒋 辉,张一红,詹心怡,周琬琳
(1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北京 100730 ,zxqclx@qq.com;2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系,台北;3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福建 漳州 363000;4安阳市肿瘤医院,河南 安阳 455000;5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6福建医科大学人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
2018年8月3日,健康报刊登的一篇专栏文章“当活着成为受罪,抢救还有无必要”,引发了热烈讨论,也提出了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为此,本刊特意组织一系列“临床伦理抉择”讨论。参与本次讨论的有一线医护人员、哲学系学生、人文学者。本文立足现实的临床伦理难题,从多视角、跨学科、跨地域的视角开展讨论,由此希望对临床医生、患者及家属、理论工作者有所启发与受益!
【案情介绍】
80多岁的李奶奶已有30年的哮喘史,10年前病情恶化为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并患有糖尿病,因病情加重住进了兰州一家三级医院的呼吸科。在住院的第三天,老人突然呼吸衰竭、昏迷不醒,随即被推进ICU病房抢救。苏醒后的李奶奶发现自己已用上了多功能呼吸机,上腭、牙床被呼吸管硌得生疼。她想拔掉口中管子,无奈手脚都被捆绑在病床上。不仅如此,她身上还插着输液管、导尿管、鼻饲管、血滤管。旁边病床上的几位枯瘦患者,已是奄奄一息。
在ICU熬了10天,李奶奶终于转入了普通病房。面对前来探望的儿子,李奶奶恳求道:“答应我,以后再有事,别再抢救我,别再让我进ICU!”可儿子对她说:“您活着,我们就有妈妈可喊。再说了,治病活命,有痛苦咱忍受一点不行吗?”李奶奶无奈地摇摇头,叹息道:“你哪里体会到我的感受呀。”一周之后,李奶奶的病情再次恶化,痰栓堵塞气道,支气管痉挛引发致死性哮喘。经家属同意,她再次被送进ICU,重新经历了一遍抢救的过程。数日之后,李奶奶苏醒过来,眼角溢出浑浊的老泪。在老人看来,在ICU简直就是活受罪,坚决不要再来这样的抢救,“那活罪实在让人受不了,况且受那么多罪,抢救过来又能多活几天?”这一回,儿子含着眼泪应允了母亲的请求。
一个月后,李奶奶再次被紧急送到ICU。处于肺心病晚期的李奶奶的血氧饱和降至40以下,伴随着严重心衰、呼衰,命悬一线。当主管医生表示要给李奶奶上呼吸机时,儿子冷静地说:“不用了,老人家不愿这样。”大夫一愣,严肃地问:“你确定?”儿子点头,泪光闪现。渐渐地,心电监护仪上的心跳变成直线,老人家双目微合,医生让护士拔掉了所有管线和仪器。“别难过,你的决定是正确的。”主管医生安慰患者的儿子。
1 不堪忍受的患病体验与临床抉择
张新庆:本案中,儿子坚持要希望母亲要接受积极抢救措施的理由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母亲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生命价值,其二,治病活命注定要伴随着需要忍受的痛苦。然而,李奶奶经历了数次ICU抢救后,再也不愿受那份不堪忍受的罪了,况且就是抢救过来自己也无法多活几天。按理说,没有谁比儿子更理解自己的母亲了,但在如此特定是生死抉择过程中,显然儿子并没有真正理解或不愿意接受母亲的真实想法,这反映了患者和家属对患病体验的差异性认知。该不该、能不能忍受救治过程中的疼痛和痛苦,成为患者和家属之间的进一步作出判断和行为的关键点。
一种观点认为,疼痛只不过是患者的主观感受,并不能成为是否继续抢救的主要依据之一;只要有利于危重患者的延长寿命,医护人员和患者家属可以不顾及患者本人的患病体验,这样才符合患者的最佳医疗利益。与此相反的观点是:纵使医护人员和患者家属不能做到半分之百的感同身受,但至少也要同情、理解患者的疼痛体验,尊重患者明确表达的意愿。这也是医者仁心的体现。
詹心怡:我觉得患者的主观患病体验是可变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两年前,我外婆腹主动脉瘤破裂,家人打算转院时,外婆却说不想再折腾了,想回家。可是,真的回到家之后,外婆跟家人说自己其实不想死,很想活下去。由此可见,患者此时的情绪是很不稳定的,做出的决定有时会是一时冲动。比如说,当感受到治疗痛苦时,就想放弃;一旦症状得到有效缓解后,就又有了求生欲。
我不是医学专业,但也知道医学是一门有极高不确定性的学科,没有所谓有百分之百没救了或者百分之百能治好的情况。然而,这个介乎于“0”和“1”的概率会给患者带来希望或折磨。因为,当时两个医院都说我外婆几乎不可能抢救回来了,但是她这两年奇迹般地还可以自己做饭和散步。所以,患者的主观意愿和外在的客观情况都充满不确定性。尊重患者的自主权是一个大的原则,但是具体怎样落实就很困难。因此,我认为尊重患者意愿不能仅凭一面之词,应该要有观察确认真正意愿的机制,确保患者不是因一时苦痛而出现情绪化语言或决定,这样才能避免更多憾事。
蒋辉:我觉得,患病体验与医学原则、医疗利益和价值观相结合,才是明智的医疗决策。当医疗干预会延长患者寿命、提高其生命质量时,医生和患者家属可以帮助患者做出理性认识和选择,暂时忍受疾病的痛苦;若在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下,没有救治成功的希望,投入与收益之间悬殊太大,也可以考虑尊重患者本人意愿,选择放弃有创的救治措施。本案中,久病医治无望的高龄老人希望有尊严地辞世,这种发自内心的诉求最终得到了其子女和医护人员的尊重。
需要注意的是,假如成功救治患者的概率微小,医生也应避免直接建议患者及其家属放弃治疗,因为医生并没有权利评价他人生命的价值,如何衡量和抉择应交由患者及家属共同决定。假如患者个人的意愿与家庭成员意见不一时,是否让患者忍受痛苦,以满足“儿子还有妈妈可喊”的情感需要呢?这时,医生还应帮助和引导患者与家属的有效沟通,让儿子明白如果真的不舍妈妈,应该不要让妈妈再承受这些苦痛,最终得到一个更满意的抉择质量。此外,如何表达对患者意愿的尊重,还应有一套法定的手续和告别仪式。例如,在患者儿子决定放弃抢救时,医生应请他书面签字表示同意;对患者的遗体应及时穿寿衣,表达一系列对逝者、对生命的尊重,寄托其亲友的哀思,告慰生者。
周琬琳:在是否尊重患病体验方面上,我们首先要明确患病体验的主体是患者,还是家属。这个区分往往才是造成临床上医护人员难以让患者及家属参与临床抉择的症结点。与西方社会相比,华人文化社会中时常并不把“患者”视为个体考虑,而是总与其“家属”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以上述案例来看,医师尊重的对象显然不是李奶奶本人,而是她的家属。虽然最后决定不再同意急救的主要决策者看起来好像是儿子,但这个决策实际上是患者(老奶奶)与家属(儿子)所共同制定给出的,并没有产生家庭同意会牺牲或剥夺个人意愿的疑虑。不过,如果患者与其家属的意愿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医护人员又该尊重谁的意愿,是否要充分体会到患者本人的患病体验,这才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临床伦理难题。
李瑞全:对于危重患者而言,临终抉择或许是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生死抉择难题。我们自然应尽量确定患者的意愿,准确判断病情的严重程度,以及其患病期间的生命质量和生活品质。首次进入ICU时,合理的全力抢救李奶奶是应该的,突然的放弃让人难以接受,也会造成家属永久的伤痛与遗憾;但是否动用强烈的入侵性医疗,医护人员必须要作专业的判断。当预测到病人有可能遭受严重的创伤而转成更长期的巨大痛苦(如植物人),且极低的生命素质之下,医护人员应与患者家属作良好沟通,协助家属作出对患者最有利的决定。
先救回来,让李奶奶有机会面对生死问题有第二次的反省和抉择,这也是让家属有同样的机会去深思和互相沟通,希望能达到一种家庭的共识。令人遗憾的是,第一次救回来后的李奶奶和儿子之间似乎没有达成良好的沟通,使其心愿没有办法完成,因而不免受到第二次的生不如死的痛苦。第二次的ICU经验,不但老奶奶受到更严重的痛苦,而家属似乎也由于再次感受到老奶奶的痛苦和真正的意愿,因而在第三次的抢救时作出艰难而合理的决定。这个案例也可以说是相当完满地解决了。
2 尽孝对生死抉择的影响
张新庆:面对处于疾病终末期尤其是濒死状态的老人,是坚持继续抢救,靠各种仪器维持微弱的生命?还是尊重患者的意愿,让其有尊严地离去?对于多数患者家属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艰难的伦理抉择。出于孝心,绝大多数人都会尽全力拯救亲人的生命。“尽孝”这个概念虽然不是华人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由此衍生出来的是“尊重患者的意愿”?还是“尊重患者家属的意愿”?这是华人文化在医疗决策中会遇到的难题。
本案例中的李奶奶在ICU反复遭受了痛苦的体验,实在不愿在病床上苦熬下去了,希望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李奶奶在头脑清醒时,多次明确表达了放弃抢救的意愿。她很有孝心的儿子在陪护母亲的岁月中,逐渐转变生死观念,答应了母亲的请求。主管医生尊重患者及患者儿子的意愿,放弃了进一步的抢救。当然,如果患者家属坚持抢救,医生自然也会全力以赴。总之,我们应该要做的不是让“尽孝”成为临床决策的绊脚石,而是要使家属明白正是因为要“尽孝”,才更应该要尊重母亲的意愿,医生该做的是引导儿子做真的孝顺该做的事。
周琬琳:如何评定临终状态的李奶奶的生命价值呢?这主要靠生命神圣观及生命质量观两种观点来提供解释。前者的含义较接近“好死不如赖活”;后者的含义比较接近“活要活得有尊严”。传统的华人社会,谈“死”是种避讳,更像是一种诅咒,我们总是为即将诞生的新生儿做足准备,却不敢为避免不了的死亡做准备,更遑论直接谈论怎么死?如何好死?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观念的转变,人的生命价值不再局限于“活着”就好,更重视生命的质量问题。因此,在孝道与临终患者的临床决策中,我们应当让患者及家属都能了解生命质量的重要性,只有当患者本人能接受“好死”,家属也确实了解“好死”的意义,家属才能了解真正的孝道应该是尊重长辈想要“好死”的意愿。
李瑞全: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成员之间自然具有很密切的关怀与感通,而子女对父母的态度常以孝顺为词。但孝并不是看他人的评论或死板的形式来行动。在此案例中,在亲和感通之下,孝是一社会人情的合理侍奉父母的方式(事之以礼),但不是盲目或僵化的形式主义。采用合理的医疗救护即是孝的表现。此案例中儿子的初步表现可谓中规中矩的。孝的进一步表现是尊敬父母的意愿与选择(事父母以敬、毋违)。尊重父母意愿这是让父母得到心安,也是得到幸福的最重要因素。也许父母子女之间不无不同的价值取向或实践的方式,但尊重亲长特别是在重大的生死决定上,让父母真能安心无憾,是对彼此都很重要的决定。这是我们达到“养生送死无憾”的基础。
不过,如何真正得知父母之心意,是很不容易的(孔子所谓:色难)。父母的决定常多为子孙而少为自己幸福而来。老人家常有选择不是对治病最好的方案,而是最省钱的医疗;也常有自己活得也长久了,在严重的最后和常伴随极度痛苦和高医疗费用开支中,自然会想以放弃医疗为最佳的选择。所以,如何理解父母在危病中的选择是需要仔细耹听和感通的。我们不必认为,儿子希望母亲生存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应该可以说是一种委婉和合情合理的爱亲表现。此中的拿捏实不轻易!儿子最后可说含泪同意让老母亲安宁地离开,此中应有不少的沟通与感通在内。医师的适时慰勉在此也是很重要的支持和尊重,对家属有很重要的心理和精神的安慰能量。
张一红:在实际临床肿瘤诊疗过程中,类似的案例确实大量存在。不过,因为受到诸多当地风俗习惯的影响,尤其是担心亲友和邻里指责自己不尽孝,而不敢主动选择放弃“积极抢救”。有时,医护人员也不得不为了安慰家属,而做出的象征性抢救措施。因为目前医院的有关规定是:只要家属不放弃,医护人员就不能停止抢救。这个规定对于类似李奶奶这样经历了多次ICU抢救的老人而言确实是活受罪!当然,在当前的医患关系下,医生的判断可能不够精确和人性化,具体的建议也经常采取回避的态度。当务之急,应当加强国人对临终关怀的正确理解与教育工作,不仅有助国人跳脱签署放弃治疗等于不孝的传统观念,对于整体社会医疗资源的有效运用也有帮助。
3 抢救危重患者标准之间的权衡
张新庆:医患双方在做出生死决策之时,需要充分理解生命维持技术的双重效应——延长生命及延长痛苦。多功能呼吸机挽救过无数患者的生命,也延长了许多重症患者的死亡过程。把一根长约30厘米、直径约1厘米的呼吸管插入支气管下端,这给患者带来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虽说生命维持技术能让患者继续活下去,但对备受煎熬的李奶奶而言,每天都要忍受憋气、劳累,治疗不能减少病痛,反而平添了身心痛苦,她选择放弃继续抢救的意愿应该要得到全社会的理解和尊重。面对这种情况,帮助患者减少痛苦,维护患者的尊严,让他们能安然度过最后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当然,并非所有的患者及家属会做出类似李奶奶这样的生死抉择,因为有诸多医学的和非医学的因素影响了是否抢救临终患者的决定。
周琬琳:抢救患者的标准应该要区分两种:一是急诊室不知患者背景的抢救,二是知晓患者背景的抢救。前者毫无疑问,必定要尽全力抢救;后者一般透过是否有传达放弃无效医疗意愿的意向来确定是否抢救。医护人员对于病患的尊重来自于探视病情时的态度及慰问病情的关怀,体现视病犹亲的仁医精神,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的临终临床决策上,给予心灵及情感上的支持与温暖,往往比只是给予透过医疗仪器来延续较低生命质量更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抢救患者不只是延续作为生物性的生命而已,应当要延续的是病患作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
蒋辉:医生在判断是否遵从患方放弃救治的意愿时,不仅要从患者疾病临床诊疗方面做出循证医学的评估,而且要给予人格尊重和人文关怀,还要结合患方的医疗费用支付能力及所享有的医疗保障政策来做经济上的权衡。在类似是否抢救李奶奶的生死抉择上,我有一些额外的担心。因为,“养小不养老”的社会现象背后说明,不尽孝的人可能更多。很多老年人明明有很大希望经过一定痛苦之后救治回来,并且有比较长的预期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但是其家属很可能因为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原因选择了放弃。这个问题也反映出我国医疗体系当中执行尊重自主权指的是谁的自主权的含混。事实上,“养小不养老”观念反映的是在临床医疗决策中,我们所关注的自主权往往都不是患者本人的意愿和最佳利益而是家属的。然而,如何看待死亡,受诊疗技术与经济基础的影响,本身就存在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差异的问题,值得引起各方面的更多关注!
李瑞全:在是否抢救危重患者方面,自然以医疗专业的判定为依据。但在临终患者的可能选取上,患者的意愿仍然是最重要的。我们无理由支持延长的只是一个痛苦的生命,除非患者有更大的未了的心愿而愿意接受更痛苦但不一定能救治的入侵性的医疗方式。老奶奶的选择确是合理的,医护与家属都应支持的。另一方面,我们不希望患者合理的意愿因医疗费用而受到挫折。这自是政府、社会与家属应采用适当的方法去取得共识,作出最有利患者医疗决定。医生、患者及家属三方的会商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4 临床伦理建议
张新庆:本案例给我的一个启发是:医护人员和家属要换位思考,充分体会患病体验,富有同情心;尊重患者真实的医疗需要和愿望,在珍视生命、提升生命质量、维护生命尊严等方面加以权衡,帮助患者本人做出智慧选择。同时,临床生死决策过程还要考虑到患者的家庭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医保状况及其他相关联的社会性因素。
周琬琳:病患与家属的无助通常来自于两方面:即使付出昂贵的经济成本也无法治疗,情感纠结。前者如果付出昂贵的经济成本可以治疗,却因为无力负担,只能选择“等死”,医护人员可以协助病患及其家属寻求政府补助政策或社会公益团的支持。如果已经是做什么都只是“无效医疗”的状况,可以帮助病患及家属真正了解“好死”的意义及价值,了解懂得“放手”才是“真爱”。对患者来说是爱自己,对家属来说是爱患者。医护人员在患者及家属与到情感纠结时,能够为更好的帮助。虽然生命的终结是不能避免的结果,但是“转念”能让情感从悲痛中跳脱出来。
李瑞全:此处所论“无助”是患者极度痛苦而又无法自了的情况。我觉得应在循证医学或精准医学的基础上,支持患者选择离开人世的坚决的决定为主。但是,要推行此医助自杀或他助自杀的行动,不但需要严谨的审核过程,更需要有国家立法才能可行,不过此中利弊不易论断。容许患者放弃治疗,采取临终镇静(Terminal Sedation)可能是一个比较审慎的起手方式。
蒋辉:政府性质的救济渠道大都只能起到“救急不救穷”的作用,很多疾病的救治费用可能是一个无底洞,医保基金毕竟是有限的。在现实中,因对疾病的经济负担能力有限而放弃疾病救治希望的病例,也大有人在。电影《我不是药神》就是在描述这样的问题。对于“穷病”这件事,虽然可以透过网络众筹的方式发挥一些作用,但也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规范和引导。政府应该兜底急救、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发展某些有价值的专项救助基金、引导和规范善良人士的社会互助,建立一个立体的救助网络,尽量减少国人因为经济弱势,明明有药可以医治,却不得不放弃生命的憾事。
张新庆: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要做好患者家属的哀伤教育。有些孝顺的儿女会后悔不能陪老人度过最后的时光,后悔没有时间尽孝,同时也明白自己失去了至亲的亲人,失去了母亲无私的爱,担心亲人在另一个世界是否过得衣食无忧。朝夕相处的亲人突然离世,会让儿女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失去亲人的痛苦,往事历历在目,一切变成了只能珍藏于内心的略带忧伤的回忆;源于无限的思念又会让对逝去的亲人“现在的生活状况”无比牵挂,情感上难以割舍。面对儿女失去亲人的痛苦,医护人员、社区和亲友要学会哀伤教育。昔日的亲情要升华成今日的灵性关怀,一种只有人类才有的跨越时空的大爱。
5 小结
张新庆:临床伦理反思较为理性,不会轻易为特定社会文化中习得的道德观念所左右。但愿有一天当自己没有能力做出艰难抉择时,家人在医护人员的协助下做出正确的生死选择。不过,医生仍要尽自己一切努力去救治患者,要尽可能去理解患者及家属每一个决定的背后的对待生命、尊严的看法,去尽可能帮助他们度过那段艰难的时光,总是能想起“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严谨认真,要去理解并帮助别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
蒋辉:这个严肃而沉重的涉及生死的话题。某些生理上没有疾病的人,因为心理和社会适应方面的问题,认为“活着是受罪”,消极生活,浪费生命,甚至走向“自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遗憾。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探讨,不能仅局限在生理的层面。当对未来充满希望时,人忍受痛苦的能力很强,而一旦心如死灰,沦为行尸走肉,生命又有何意义呢?医护人员要尽力去帮助那些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实现生命的价值升华,让人类社会健康、温暖、积极而富有勃勃生机,是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的人生目标!
李瑞全:临终医疗的决定确是一个不容易但却又是已存在于日常医疗中的道德两难的事实。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和亲长的福祉所必须常加以反省。这也是当前医护界所必须建立规范和政策的临界点。我个人认为,这应当是人文关怀如何进入医疗过程中最重要的建构。医院不只是有高专精的医疗器具或人才即可以解决患者的一切问题,这甚至不是医疗素质的唯一标准。医疗的最高原则应是患者家属如何能达到“养生送死无憾”。把医学人文作为医疗结构的一个不可缺的部分,使医护人员真正理解,是朝向解决各种现有和未来会发生的医疗纠纷和道德两难的起步。
周琬琳:临终医疗决策不仅是医师的难题,同时也是患者及患者家属的难题。医生在见死不救及救死扶伤中两难;患者本人在想要减少痛苦和生存下去之间两难;家属在尽孝及家庭利益之间两难。在一些临终情况中见死不救正是源于医者仁心,医生不忍患者痛苦,同时也是尊重患者意愿的表现。如果是无效医疗还会徒增痛苦,不管是对于自身身体的苦痛或是不愿造成家人的负担的苦痛,患者选择“有尊严的好死”都是出于自我意愿,应当给予尊重。如果患者家属不愿签署放弃急救治疗只是因为想尽孝,那么,通过病情的说明、患者的意愿和澄清孝顺的意义是尊重父母的意愿等沟通,让家属了解,尽量减少痛苦的有尊严的好死才是真正的孝顺。如果是为了家庭利益,并且父母并无意愿放弃急救治疗,那么家属即使签署放弃急救治疗同意书也不是基于患者最佳利益考量的行为,医疗委任代理人应该要以患者身心的最佳利益为考量,医护人员应当要谨慎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