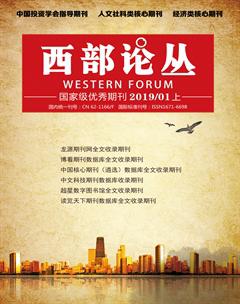《陈君葆日记全集》中的戴望舒
摘 要:《陈君葆日记全集》在展现陈君葆个人生活的同时,也记录了他和当时众多知名人士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其中关于戴望舒的记载,展现了戴望舒在香港时期的活动情形和人物形象,以及他与陈君葆等其他人士的交游事迹。这些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戴望舒屡次遭遇磨难的生活;二是戴望舒从事的有关抗日的文艺工作;三是戴望舒再次受挫的情感经历;四是戴望舒阅读收藏书籍的爱好。这不仅对于有关戴望舒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20世纪学者交往史的研究也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陈君葆日记全集》 陈君葆 戴望舒 香港
陈君葆(1898—1982),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后来跟随父亲移居香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在香港大学任职,历任冯平山图书馆馆长、中文学院教授等职,是香港知名学者、爱国教育家和文学家。陈君葆素来有写日记的习惯,从不间断,从20世纪初起至1982年逝世,共写下了110多本日记。这些日记在2004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名为《陈君葆日记全集》。日记内容十分丰富,留下了历史的宝贵记录,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和极高的文献价值,被香港学者誉为“大时代的证言” 。陈君葆是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与当时到香港的政治界和文化界知名人士,都有广泛的接触和密切的交往。因此,日记中出现了当时中国大多数名人,有数百人之多,几乎涵盖了各个方面。有政坛知名人士,如宋庆龄、周恩来、何香凝、廖承志、柳亚子等;也有文化界知名人士,如郭沫若、陈寅恪、许地山、矛盾、戴望舒等。在涉及到的众多人物中,关于戴望舒的记载有三十一处。这些记载不但展现了陈君葆眼中的戴望舒形象,也记载了戴望舒在香港时期的活动情形以及交游事迹。现从中勾勒出较为重要的记载,进行阐释和说明。
戴望舒在香港的这段日子,可谓是一座灾难的里程碑。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同许多文人一起来到香港,在香港沦陷时,他没有及时离开,以致陷于日本人手中。抗战胜利后,他依然留在香港,家庭的破碎,加上沦陷时期的蒙污经历,又使他遇到更大的挫折。他在香港的这段时期,生活中,屡次遭遇磨难,曾身陷囹圄,又被诬附敌。情感上,婚姻再次挫败,完整的家庭再一次破碎。但苦难的经历,并没有磨灭他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他从事着各种文艺工作,表达着自己内心的热与诚。无论境遇如何,他也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爱好与追求,始终不忘读书。
一、生活:屡次遭遇磨难
戴望舒在香港的这段时期,生活中磨难不断。陷敌期间,他遭遇牢狱之灾,被折磨得身体虚弱,哮喘加深;香港光复后,他又被诬附敌,让刚见到光明的他又再陷深渊。
1942年7月4日,陈君葆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到戴望舒。他写道:“上午到图书馆,不久戴望舒来访,他是被释出来了,但不知所犯何罪”。1942年,在香港沦陷期间,戴望舒在日军大搜捕时被特务逮捕。《陈君葆日记全集》中的这条记载,记载了陈君葆与戴望舒的交往活动的同时,也记录了香港沦陷时期,戴望舒身陷囹圄的苦难经历。自他被捕的牢狱生活,是一场人间地狱似的噩梦。暗黑潮湿的牢房,被血污浸染的铺石,禁锢而冰冷的铁栅,在这生与死就在一线之间的日子里,他甚至见到很多人从此没有回来。但是日寇的残酷折磨不但没有使这位昔日的“雨巷诗人”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爱国之心。在狱中,他写下了《狱中题壁》这首著名的战斗诗篇,字里行间都抒发着他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的强烈情感,寄托着对中华民族必然将会取得胜利、获得解放的坚定信念和誓死不屈的顽强斗志,展现了一位中国文人的不屈铁骨和刚毅灵魂。
1943年8月31日,陈君葆“从东亚研究所出来顺路到大同去走一遭看看望舒,灵凤已出来了,相见之下不胜感慨,他面色灰白,似举步不大健的样子,屈指相隔已三个多月了”。陈君葆前去看望戴望舒的时候,见到了叶灵凤。戴望舒之前因为从事抗日文艺活动而陷入牢狱之灾,在此后,叶灵凤也没能够逃过此难。1943年5月,叶灵凤像戴望舒一样,日本人也认定他为抗日分子,将他关押了三个多月。日记中的这段记载,正揭示了像戴望舒、叶灵凤这样的爱国文人们在香港沦陷时期这一时代背景下的窘迫境地,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1943年11月2日,陈君葆在日记中写道:“岛田谨二,据我看是一个很好名的人,”而“望舒说他是个书呆子,也许是稍慎重其批评而已”。“慎重其批评”,日记中的这条记载,映射出在香港沦陷期间,时局的严峻和敏感。
1946年4月20日,“今日向晚戴望舒来访。他说他们要到上海去”。 在香港沦陷后的几年时间里,戴望舒是在难挨的痛苦中挣扎度过的。他热爱祖国,热爱美好的生活,心中充满向往,但是他不敢去战斗。1946年1月1日,何家槐、黄药眠、陈残云、韩北屏、司马文森等21人又联名写了一封《留港粤文艺作家为检举戴望舒附敌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建议书》。建议书中说戴望舒在香港沦陷这段时间,与敌伪有所来往,附件中还附有三条证据。建议书中不同意由戴望舒主持通讯处,要求重新组织新的文协香港分会。虽然后来进步文艺界纠正了对戴望舒的错误判断,认为“建议书”这一事件,是由于对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的政治、思想和工作情况缺乏全面真切的了解所造成的误解。但是在建议书事件发生后不久,一个新的港粤分会就代替了文协香港会员通讯处,不久戴望舒又丢了《新生日报》的工作。接二连三的遭遇,使戴望舒感到苦闷和彷徨,于是,他便于1946年3月和妻子、女兒一起离开了香港,返回了上海。
二、工作:抗日文艺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望舒意识到自己不能再拘泥于个人的小我情感,而要着眼于整个民族的遭遇。他在香港的这段时间里,投身在各种抗日宣传的实际工作中,推动着抗日文艺运动的进行,抒写着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与忠诚。
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占上海之后,戴望舒和其他许多文人一样,都纷纷逃离上海,辗转千里去了相对较为安全的香港。戴望舒本来没有打算长期留在香港,而是计划安顿好家庭以后,就去参加文艺界的抗敌工作。而在此时,正在筹办的《星岛日报》急需一名副刊主编,机缘巧合之下,戴望舒便担任了《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主编,副刊于1938年8月1日与日报同时诞生。在此后,戴望舒凭借《星座》这片阵地与香港岛这一特殊环境,编写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星座》由此成为了香港进步文艺活动的重要阵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日产生了尖锐的利益冲突。港英当局为了维持英日关系,避免刺激日本方面,设立了特别的检查机构,对宣传抗日的言行实行防范和管制。这段时间里,《星座》又办得极好,自然成为了被主审的目标。戴望舒就只好尽量不使用敏感的文字,采用比较含蓄的手法从侧面进行讽刺,不得已时甚至直接用空白版面应对,以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声抗议。1942年12月,日军攻陷了香港,当时滞留在香港的各界知名华人几乎都被逮捕审问,戴望舒也不例外。他因为主编《星座》宣传抗日而被捕,《星座》也由此停刊。陈君葆在日记中初次提到戴望舒时写道:“他是被释出来了,但不知所犯何罪”,这也正是戴望舒被捕入狱的原因。1948年8月3日,日记中又写道:“金应禧到图书馆来访;随着薛汕亦来,并拟在《星岛》开个《民风》双周刊。关于主持者我又想到望舒来了”。而陈君葆想到戴望舒,正是因为戴望舒曾经担任过《星岛》副刊《星座》的
主编。
1945年6月2日,“水云楼随笔写了《杂感一束》约一千字,因为前已答应了望舒,而且这次他们送《文艺周刊》稿来时又故意留起地位”。戴望舒被保释出狱后,内心始终保持着爱国的坚贞,但在严峻而又残酷的形势下,他身为一个柔弱的知识分子所能做的又是有限的。他与黄鲁、万扬一起合资开了一个名为“怀旧斋”的旧书店,但是因为经营不善,不久之后就关闭了。后来,又与叶灵凤一起负责编辑了《华侨日报·文艺周刊》、《香港日报·香港文艺》、《香岛日报·日曜文艺》,他还负责编辑了《香岛日报·新译世界短片杰作选》专栏等。日记这里所提到的《文艺周刊》,就是1994年戴望舒与叶灵凤负责编辑的《华侨日报》的副刊。这个副刊的出现,正像许多文艺爱好者所呼喊的一样,两年以来,南国的文艺园地实在是太荒芜了。在香港沦陷的三年多时间里,戴望舒书写着各种文字,在香港的报刊上发表,力求在这些文字中保存着自己灵魂的最后一片净土。但在沦陷期间,这些报刊为日军所控制,不得已时戴望舒就采用“开天窗”的形式,“故意留起地位”,无声地表达对日军的抗议。
1945年11月18日,陈君葆“下午回来,望舒家里的茶话会几乎忘却;赶到那里已四点半了,桂黄等均在,如此抗战文协会员到的满七人了,因此也不妨开分支会了,免堕广州的恶劣环境”。抗战文协,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8年3月27日成立于武汉,并在成立后立即在各地筹建分会,征集会员,戴望舒在此年参加了文协。这一时期,香港云集了众多的政治、文化界人士,香港迅速成为了抗战初期政治、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1938年底楼适夷到香港主持文协香港分会的筹备建立工作,戴望舒由总会函聘参加筹建工作。在这前后几年时间里,戴望舒一直活跃其中,为这个协会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日记中的这条记载,记述了戴望舒以及以他为代表的爱国文人们,在严峻、恶劣的时代环境下进行的文艺界的爱国救亡运动。
三、情感:婚姻再次受挫
在香港的这段时间里,戴望舒除了在生活上屡次遭遇磨难、身体上饱受病痛折磨,又再次遭遇了婚姻的挫败,家庭的支离破碎。多重的打击与压力,让他决意离开香港,远离困扰。
1949年1月29日,“傍晚叶灵凤、林焕平夫妇与他们的小孩子们连同马文山等来拜年,满满地坐满一屋子。由灵凤处知到(道)望舒又离了婚。他现在和他两个女儿住在灵凤家里”。1942年5月,戴望舒与杨静结合,从此,他的家庭生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赠内》这首诗,可以看出他新婚后的心境,他欣赏妻子“明媚的朱颜”,受着妻子“光彩的熏沐”,这首诗处处都传达出他温馨而亲切的爱和不想遮掩的幸福之感。包括在《偶成》这首诗中,对于“生命的春天”、“灿烂的微笑”、“一切好东西”、“象花一样重开”等美好景象的歌唱,这是在戴望舒笔下难得一见的。可是,由于两人年龄与性格的差异,再加上两人婚前缺少深入的沟通与了解,结婚后不久便产生了各种矛盾。1948年末,杨静就移情他人,提出了离婚。戴望舒虽然竭尽全力却也无法挽回,最终同意了离婚,孤独地领着两个孩子寄居在叶灵凤家中。并且这时候戴望舒的哮喘病已经很深,这也是他没有一同前去拜年的原因。婚姻的挫败、生活的磨难,再加上病痛的折磨,戴望舒的精神与肉体承受着双重的负担,让他“不想在香港住下去,决定要到北方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可见其中包含了多少的心酸。1949年3月12日,“戴望舒走了,与卞之琳同行。灵凤请晚饭,本是为送望舒,但他船期定了来不及”。卞之琳从英国回国,经过香港,戴望舒便和他结伴一起去了北平,离开了香港,结束了多年的灾难岁月。
四、爱好:收藏阅读书籍
虽说文人们都爱好读书,而戴望舒则是更甚。他不但热爱阅读书籍,也热爱收藏。他在香港巨变这一时期,也不忘记读书,经常前去冯平山图书馆阅读书籍。
1942年8月4日,陈君葆在日记中记载道:“上午叶灵凤与望舒到馆来访,望舒念念不忘念书,他真有点书呆子的性格。说他思想左倾,那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戴望舒在法国巴黎留学的时候,最喜欢流连于塞纳河畔沿岸的书摊。虽然自己独自一人身处他乡,手中又没有钱,甚至衣食都没有着落,对于书籍不能大量购买,也不能高价罗致,只能是偶然发现,携归珍藏。但是经过日积月累,还是收集了不少。当时身为穷学生的他,要是只花费几法郎就从一个不起眼的小书摊上买到一本意想不到的珍贵的书,便会欣喜若狂。《陈君葆日记全集》中的这条记录,展现了戴望舒在陈君葆眼中的形象,也正是戴望舒的性格和爱好的展现。戴望舒平时话语不多,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写文章,戴望舒的第一任妻子穆丽娟曾抱怨说过“望舒的第一生命是书,妻子女儿则放在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戴望舒对穆丽娟缺乏应有的关爱与体贴,久而久之,造成夫妻关系的疏远、冷淡乃至对立。此外,甚至在香港沦陷之时,众多文化界人士都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安全撤离了香港,到达了后方,而戴望舒却没有走。至于他没有走的原因,在抗战胜利后,他在同杜宣谈话时解释说当时不走是因为“他舍不得这一屋子多年收集起来的好书,他怕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后,在1943年1月26日,陈君葆“午后访灵凤,望舒也在,大家似均感精神食粮缺乏而希望图书馆能早日开放”。香港沦陷后,在1942年1月的时候,日军突然大肆搜查香港大学,并封闭了由陈君葆所管理的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而戴望舒、陈君葆、叶灵凤这些热爱读书的文人们都希望图书馆能够尽快恢复开放,以满足精神所需。从以上这些记录中,都可以看出戴望舒对书籍的
热爱。
除上述内容外,《陈君葆日记全集》中还有多处关于戴望舒的记载。这些记载,均详细真切地再现了戴望舒在滞留香港这段时期,与各方人士的交往活动与交游事迹。
结语:
《陈君葆日记全集》是陈君葆生活经历的直接记录,因此,与有关戴望舒的其他研究相比,日记中关于戴望舒的记载,更加具有一种当事人的“在场性”,也能更加清晰地还原发生的历史场景。无论是戴望舒在香港的重大活动经历,还是日常交往活动,日记中皆有述及。其中,戴望舒在香港时期的重大活动经历,在有关戴望舒的其他研究中,已有很多相关内容,日记可起到印证的作用。而戴望舒在香港时期与陈君葆及其他人士的日常交往活动,在有关戴望舒的其他研究中,很少有如此详尽的记载,在此,日记可裨补相关研究的缺漏。
从《陈君葆日记全集》中梳理出有关戴望舒的记载,并参照其他材料相佐证,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这些内容反映出了戴望舒在香港时期的活动情形。展现了他生活遭遇的苦难,情感遭遇的挫败,也展现了他在抗日文艺运动方面产生的积极作用。其次,这些内容表现出了戴望舒的性格特点及其兴趣爱好。他热爱阅读和收藏各种书籍,即使环境艰难,也不曾间断,展现了他嗜书如命的生动形象。再次,这些内容详细、丰富地记载了戴望舒与陈君葆等其他人士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这段时间里,“国内有许多文化界人士聚居香港,当时陈君葆与他们一道,共同进行了文化交流活动,这也为香港原有的殖民主义文化增添了中华民族的色彩”。这是当时文化界人士交往的一个缩影,这不但对于关于戴望舒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20世纪学者交往史的研究也具有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王海燕:《文坛双杰戴望舒与叶灵凤》,《文史春秋》2009年第2期。
[2] 卢玮銮:《戴望舒在香港的著作译作目录》,《香港文学》1985年第2期。
[3] 冯亦代:《戴望舒在香港》,《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4] 叶灵凤:《忆望舒》,《华侨日报·文艺周刊》1950年第127期。
[5] 卢玮銮、郑树森:《沦陷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香港:天地圖书有限公司2013年版。
[6] 陈君葆:《陈君葆日记全集》,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
[7] 施建伟、应宇力、汪义生:《香港文学简史》,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 王彬:《戴望舒 穆丽娟》,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
[9] 陈丙莹:《戴望舒评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10] 陈君葆:《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二),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V页。本文所引《陈君葆日记全集》均为此版,就不再一一标注。
作者简介:潘思婕(1995.8-),女,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