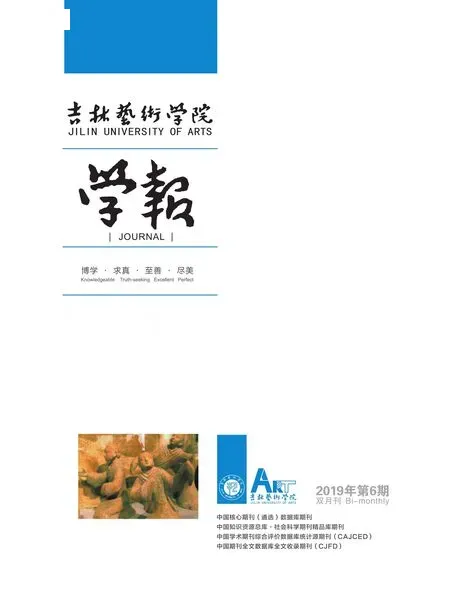谈中国山水画的皴法美
何延喆 樊晓婷
(天津美术学院,天津,300141;吉林艺术学院,吉林 长春,130021)
表现自然美的山水画一直是以山、石作为主体物象进行观察和描绘的。这一画科的命名也将“山”放在首位,山水画的取材若离开了山川岗阜、奇石巧岩,便不成其为山水画。正如贺天健先生所讲:“中国画艺传统的山水画,是以山石皴斮美和皴法美为主要‘艺能’,去除这个表现,便不是山水画,而是一种风景画……然而一有山石,就必须兼有山石皴斮美和皴法美。”[1]168
“皴法”是山水画中极富表现力的形式构成要素,既有鲜明的特征,又有抽象符号之属性;既是真实存在的物象,又合乎形式法则规律;既是视觉中的自然形态,又是主体心象结构的反映。其中,具有异常丰富的审美内涵,给人以诸多感觉经验的启示,其审美特征、审美法则贯穿其中。从事山水画的创作者、研究学者应对山水画皴法的诸多美学问题进行思考和梳理。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山水画大家都有其独特的风格面目:五代到宋元明清诸家,至近现代的黄宾虹、傅抱石、陈少梅、孙天牧等。这些画家都是兼收并览、广益博考,之后自成一家。皴法是画家审美表达的重要标志,画家对山石皴法的创作体会为后辈画家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经验,因此有必要研究山水皴法、深入理解皴法的美学表达,才能够精准把握艺术语言,发挥中国画艺术表现的无限可能。
一、山水皴法的产生、演变与发展
按照“六书”的解释,“皴”为“形声”字,“皮细起也,从皮夋声。”[2]61皴,原是形容皮肤表面的干裂状态,后用“皴”字形容山水画中石头及树木表面的纹理与褶皱。皴法是表现山石﹑树皮纹理的一种方法或手段。
山石质地结构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而不同,画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创造出了各种笔触表现不同的山石、树木的结构与纹理(肌理)。但在早期的山水画中是没有这种笔触的。
由于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使画家心性变得更加自由,贴近自然,从而影响了中国山水画创作的发展,山水画由早期作为人物画的背景转向独立的山水画科目提供了条件。随着山水画的逐渐成熟与发展,单是勾勒填色的方法已不能充分表现山石树木的纹理、结构、阴阳向背等凹凸感,于是皴擦的笔法应运而生。
从早期山水画的“空勾无皴”到五代和两宋皴法相对完备的高峰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演变过程。期间发展出很多皴法,例如荆浩的钉头皴,董源的披麻皴,范宽的雨点皴,郭熙的鬼面皴,李唐的斧劈皴、马牙皴,马远和夏圭的大斧劈皴等。到了元代又出现王蒙的解索皴、牛毛皴,倪瓒的折带皴等。之后明清两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创造。近代山水画家傅抱石在传统“乱柴皴”“乱云皴”的基础上融合了自己的笔法创造出“抱石皴”,以及陈少梅、孙天牧先生“北骨南风”的独特面貌等。
皴法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山水画真正走向成熟。锤炼和升华山水画皴法的表现性,是探求山水画审美真谛的必由之路。
二、皴法表现的技法美
“皴法美”的第一次提出是在贺天健先生的《学画山水过程自述》一书中。他认为中国山水画中皴法美的来源,是自然山石皴斮美的艺术加工,皴斮美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由此可见,要研究山石的皴法,首先要深入大自然中寻找,创造者必是真理的搜寻者。
黄宾虹有山水画“得之于壮游”之说。“缣素临摹,有不敌舟车浏览者矣”。黄宾虹先生外出游览写生,足迹遍布黄山、九华、南京、镇江、江苏、杭州、太湖,以及两广、四川诸省等。每到一处都会勾画速写,他以实际行动来告诉画家们要向真山水学习。可以说天下的名山胜境都是画家眼中活的画稿,它们的形状、质地等各具地域特色,更有奇岩巧石、耸崖危峰、天坑地缝等各样的奇景。天下美景就像一个大宝藏,奇绝神秀,欲夺其造化,则必须饱游饫看,历历罗列于胸中。之后才能以笔墨之自然写天地之自然。
清朝书画家笪重光所著《画荃》有记:“从来笔墨之探奇,必系真山水之写照。”正是出于对自然界的观察,才产生了不同的皴法。今天的山水画创作,如果想突破古人的藩篱更进一层,那么像郭熙那样饱游饫看,像黄宾虹先生那样“行万里路”,师自然,师造化,如此才可能认识山水的真面目。
在画自然景物时,如果看到什么就画什么,就和照相一样,虽真实但缺乏艺术性和主观加工的色彩。这就需要兼有笔法墨法的皴法美,经过这样的艺术加工,才具有艺术美。中国山水画皴法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表现方式的独一无二,在笔墨表现上,皴法的排列、湿燥、虚实、浓淡要运用适宜,才能产生美感,给人形式上的视觉冲击。比如笔墨的交叠、皴与轮廓是否浑然一体,皴与染的结合,在不同程度体现出皴法的意境和美感。
1. 笔墨交叠,同形而异色
皴法笔触中普遍存在一种重复的共性特征。重复是美的基本要素之一。有一个基本的单元形作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重复排列叠加。过程中可做方向、位置变化,具有很强的形式美感。
歌德说:“重复就是力量。”重复出现能产生很强烈的感染力,使主题加以强化。皴法中用重复的笔触去塑造山石的体积和质感,一笔一笔皴下去,追求统一中的丰富和微妙。每一单元的笔触形状相似,而大小与墨色上有所变动,是单纯里面的丰富、单纯里面的微妙、单纯里面的复杂。重复叠加下来气势壮观,墨色时浓时淡,可谓同形而异色,笔触虚实相生,变化莫测,极其丰富,乱而有序,看似一团乱麻,实则有理有法。皴笔的重复是有规律性的构成形式,画面感很强,给观赏者带来细腻的视觉美感。
2. 自然天成的肌理感
清代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中云:“依石纹理而为之,谓之皴。”[3]885由此可知,皴法的笔触可以把山石的肌理美直观地表现出来,按照一定规律组合起来,就具有了审美意义。米芾、米友仁父子以横点子的排比、叠错之法皴山石,达成“点滴笔墨草草成”的朦胧迹象之美。“石如飞白木如籀”,赵孟頫以‘飞白’之笔法作石,表现石头的肌理。李唐、马远之“大斧劈皴”,行笔硬直粗阔,呈条缕状笔触肌理,有刚健雄奇之美等。山石的皴法种类繁多,但人创造出的只是皴法。山石是自然天成的,每一种皴法的出现,都以自然中真山石作为依据,并非率意杜撰,皴法在表现真山石中,切不可失去真山石的肌理美、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
“写石欲超脱画派,要游览真石,胸有真谱,乃有真画。兴到时以奇别之笔,弗计是皴是廓,横推侧出,以肖天生纹理,若非人事所能成者,乃臻奇妙。”[4]962-963肌理是一种非规律的构成形式,自然天成,方得妙处。
3. 皴与轮廓,浑然一体
清代画家郑绩在《梦幻居画学简明》中云:“皴要与轮廓浑融相接,像天生自然纹理,方入化机。若轮廓自轮廓,皴自皴,一味呆叠呆擦,便是匠手。”[4]950因此,皴笔不可与轮廓相左,轮廓不处理好,皴法将无处付之,或先廓后皴,或先皴后廓,亦或是边廓边皴,无论用哪种皴法,必先胸有成竹,然后落笔。皴法根据轮廓的起伏,笔触叠错交搭有秩,阴阳向背,适具体情况而变化。皴法与轮廓的关系如此紧密,水墨交融一体,生动自然,且无呆板刻意之感,彰显浑然天成之美。
4. 皴与染的结合,拖泥带水
拖泥带水皴是劈皴的一个重要变种,又称“带水斧劈皴”,为南宋画家夏圭所首创。方法是浓墨湿笔迅疾皴拂挥洒,然后趁湿用淡墨水扫开,极淡处用干净的水笔再接再扫,勾皴结合,一次完成。在这一过程中,水与墨相互渗透、交织在一起,从无层次到有层次、从不透明到半透明、从有肌理到无肌理、从浓淡有无的过渡中,在皴与染的巧妙结合中变化多端。水墨淋漓体现在画面上,即使画面干了之后还是润润的,饱满又不失骨力,湿笔有骨,枯笔能润,润燥在笔端,元气淋漓障犹湿;在气韵上,氤氲的状态非常高妙。产生了自身独特的美感,温和的变化在不经意间似有浪漫的情怀。
三、皴法表现的艺术美
1. 皴法的意境美
意境美是一种情景状态,是心与物相融相契的审美状态,可以理解为一种抽象之美,属形而上的范畴,需要感知和领悟,语解言诠常常难以切中谛要。其间不乏朦胧虚幻、惟恍惟惚的成分。《易·系辞上》说:“圣人立象以尽意。”即是指取法万物之形象以表意。圣人用卦象的符号传达思想情感,山水画家则用中国绘画特有的符号传达思想情感、主观审美意象,并借助于皴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皴法不仅仅是描摹自然物象的一种手法,更是画家传达内在审美意象的媒介。
人之读画无异于读书,其精神内涵或引发思考,或引人入境,或震撼人心。凡画至此,皆入妙品。这样的妙品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呢?皴法在其中又起到怎样的作用?
前文讲述要去真山水中饱游饫看,这是师造化的过程,外师造化后才能中得心源,之后才能像庄周梦蝶一样,物我两忘,万物合一,才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此之谓“物化”①的过程。“物化”之后方可在绘画创作中达到形而上的高度,从而完成了审美意向的外化。整个过程中“皴法”就是审美意向外化的一种具体表现手法,也是组织画面的必要技法,最后“以画为媒”传达给观者想传达的内容,表达深远的意境,感动自己的同时也感染了赏画之人。
苏东坡就这样评论王维的诗画:“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如此诗中有了画的意境,画中也有了诗的意境。所谓见景生情、因物起兴,看到自然景物便引出了思想情感,客观形象与主观的思想情感结合,形成了思想情感的象征,描绘出来,便成了画;歌唱出来,便成了诗。如此诗画融合便有了意境。
石涛要“搜尽奇峰打草稿”,正是这奇峰让他“起兴”,给予他作画时的灵感和精神上的愉悦,然后笔下产生了画境。在这个过程中,皴法就是他抒发情感和表达意境的最直观具体可见的语言,具有中国山水画的独特意味和审美境界,而这些意味早已反映在我国千余年来的山水诗画里。
在古代题画诗中有很多描述和赞美皴法的句子,如元代书家王逢撰《梧溪集》中“悬崖怪石鬼呈面”,赞叹了唐棣笔下石皴的奇异突兀之美;明代学者汪珂玉《珊瑚网》撰记“螭虬资质风云变”,描绘了曹云西山石皴纹斑驳的肌理之美;元人方回《桐江续集》语录“铁干皴涩撑霜皮”,形容了郭熙所绘老树主干的粗涩浑朴之美,让诗意的描述进入大自然的微观结构和笔墨形式的单元形态。
除了这种诗化的意境,季节、朝暮四时、阴晴变幻也有其独特的意境美。比如郭熙的《早春图》通过季节表现意境,画中运用形似卷云的笔触扫出大概的结构,再用淡墨渲染,整个画面像是笼罩了一层薄薄的雾气,当你看到这幅画就像处于真山里边,感受到空气比较湿润且有一丝的凉意,春天的感觉扑面而来。看画的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可谓意境深远,不禁感叹中国的绘画艺术境界之高。在《林泉高致》中更是有这样的描述,“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看此画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画之景外意也”。[5]26
2. 力量的美感体现
皴法的力度美在北宗山水的画法中有很好的体现,因为北宗山水多表现筋骨外露的山石,其皴法都属斧劈系,如大斧劈、小斧劈、刮铁皴、雨淋墙头皴、拖泥带水皴等。这些基本都属于“面”一类的皴法。北宗山水画大家孙天牧先生讲:“面,在北宗山水画中多为皴法,尽管有时笔上水分很多,但亦须沉着有力。”[6]4
掌握好斧劈皴的画法,注意用笔的力量和速度是关键所在。此皴法命名为“斧劈”,顾名思义,如斧劈木,肯定不会是钝刀子锯木头,而是用锋利的斧刃一劈到底,这股力量可想而知。反映在绘画上就是以笔代斧,一气呵成。如孙天牧先生所讲的:“干、湿、浓、淡在笔行过后,一次显示出来,笔与笔相接之处,水墨交融而有阴阳向背之感。”[6]4如李唐、马远擅长此法,他们的皴法中透出一种硬朗、坚凝的力度美。
3. 浑厚华滋
“峰峦浑厚,草木华滋”是元人张雨对黄公望画境的评价。黄公望的代表作品《富春山居图》是大众比较熟悉的,画中山石以披麻皴为主要表现手法。运用积墨法,柔美的披麻线条一遍又一遍地叠加塑造理想的画面效果,给人以浑厚之感,山上丰富或短线或点状形态的植被,使得画面更加丰富饱满,可谓“浑厚华兹”。董其昌用“川原浑厚,草木华滋”来评价董源、黄公望等南宗墨法的精妙。王原祁评黄公望,言其平淡天真,高华流丽,“达其浑厚之意、华滋之气也”,自有一种“天机活泼隐现出没于其间”。[7]1
北宋范宽的作品《溪山行旅图》给观者的第一印象是雄厚壮美,中锋顶立的构图,画面中间高耸的山体,大片形似雨点状的小笔触皴点紧密有序地罗列、重叠。一层层的积墨后产生既浑厚又苍苍莽莽、大气磅礴的美感,后人多用此法描绘高耸雄壮的北国风光。
四、结语
皴法是中国山水画重要的表现语言,它承载着主体的精神气质、生命状态、人格修养,体现着视觉形迹和思维感知的独特规律,使实践者在既精微具体又恣性随机的过程中拓展想象、调动灵机、驾驭规律、变通法则,在惟恍惟惚的审美愉悦状态下把握结构总体的复杂微妙关系,并发挥媒材物质属性的视感魅力,吸引着我们与受众共享其美妙的意蕴。
老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皴法便存在于这“天地大美”之中。天地万物之美皆从直觉关照中产生,不假言诠语解即可自然显现。一切美的事物都需要有人去发现、去感受、去表达,绘画只是其中的一种反映方式。而皴法作为传统绘画中的重要表现元素,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丰富完善,为艺术家提供了创意与想象、模拟与再造、静观与神驰的无限空间。这恰如古代画论所云:“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其画所以称独绝也。”
注释
①此处为道家文化学者陈鼓应先生在《庄子今注今译》的注言:消解物我界限,融化万物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