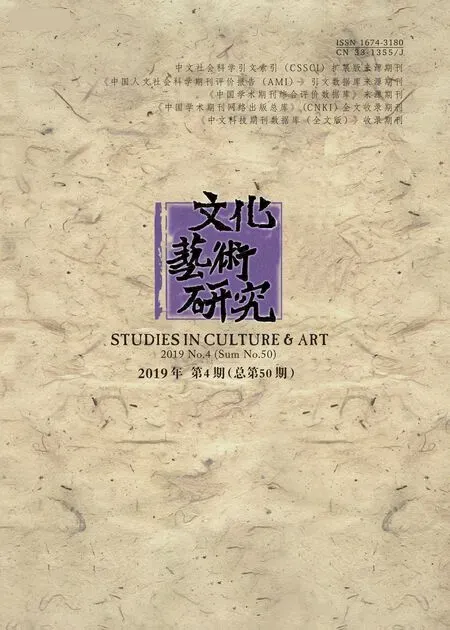衰世文人的性别越界想象
——从晚清笔记的狎伶书写看士伶交往的话语建构
王雪松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 230601)
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戏曲蹀躞至晚清,其最重要之变革,乃是将其生命系在了一个个伶人身上。然而这场变革却使伶人们深深地堕入了一个二律背反的话语陷阱中:一方面,伶人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受人瞩目,因此精进技艺,附庸风雅;而另一方面,这份奉人清赏之心却进一步使得“优伶,贱业也”[1]1643的理念根深蒂固。尤其是一些旦角伶人,“男身女相”的表演形式使得他们既需要承担伶人身份之“贱”,又需要背负女子身份之“轻”,这在晚清文人笔记狎伶的相关记载中体现得特别明显。文人们对待这些乾旦,有感叹其“歌苦识稀,曲高和寡”[2]683,称赞其“歌伶虽贱技,而品格不同”[2]595者,亦有批评其“弄权纳贿,怙恶纵淫”[1]5136,鄙夷其“侑觞媚寝”[3]15者,但这些汝南月旦却无一不带着一种“雅俗之间相去乃真不可以道里计”[2]297的文士心理。
有清一代,文士狎伶之风极盛,而又以晚清为最盛,据王书奴《中国娼妓史》考,此风顺治时已是“荡靡之习”,“延及康雍……仍而未辍,至乾隆朝而极盛。迄于光绪末叶,男色风靡一世”。[4]319—320究其原因,学者一般认为,是清初一系列严禁士绅狎妓的禁令以及戏曲艺术的勃兴,使得这种由明代延续来的少数人习癖在清代蔚然成风。a如施晔《清季北京相公及士优男风文化》(《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综合版)》2008年第1期)、程宇昂《明清文人与男旦交往述论》(《戏曲艺术》2010年第2期)、岳立松《晚清狭邪书写与京沪性别文化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林星群《清代法律视野下的男风现象》(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等均持此论。然而,这种说法却不能解释此种狎伶之风为何延续至晚清方才大盛,却至民国初戛然而止。笔者以为,相较于关注这些社会文化,晚清文士性别越界b性别越界是晚近性别研究中的重要论题。对文本中性别越界的解读,可以为探索文本的话语策略和思考方式提供依据。晚清伶人“男身女相”的反串表演以及文士与男伶的狎亵关系,便是性别越界的一种表现。正如张逸凡《〈九层云霄〉里的性别政治与性别表演》(《中外文学》1996年第4期)所说,这种性别表演形式暴露的是社会文化中性别建构的矛盾,显现出的是父权(男权)社会对性别认同的压迫。张小虹则在《性别越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评论》中进一步为我们指出,实际上这些性别越界的结果,并未动摇固有的权力话语,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原本的主流体制和权力结构。参加张小虹:《性别越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评论》,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的扭曲心理更值得注意。
从晚清笔记c笔记至清而大盛,张舜徽先生称其平生所寓目者,便有“三百余家”(《清代笔记条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本文目光所限之晚清笔记,主要为梨园掌故笔记、品鉴优伶花谱及纪闻、游记、稗史中的相关记载。中文士狎伶之“温柔富贵乡”的描述来看,这种性别越界往往与衰世文人的扭曲价值观有关联:看似现实主义的梨园记录,却往往在尝试规避国势崩颓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努力建构一个情真意美的审美乌托邦。因此,有学者认为,晚清文人的这些创作正是显现了“清季文人承受传统体制下的压抑影响,及其面对现代进程里的潜在焦虑”[5]271,而在这些“压抑”和“焦虑”中所展开的文士话语建构,却也是“伶人们为什么会深深地烙上‘卑贱者’和‘色情者’的社会性别角色”[6]31的重要原因。于是,以此视角切入晚清文人笔记中狎伶的情色书写,分析文人独特话语下的“言说自觉”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男身女相:伶人身体的书写
“梨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往与相狎”[2]886,梨园旦色最重色艺,而尤以色为先,“色稍次者即场上无分”[2]91。所谓“爱娼家以色,爱相工亦以色”[7],许多文人士绅甚至是“重色而轻艺,于戏文全不讲究,脚色高低,也不懂得,唯取其有姿色者,视若至宝”[8]184。艺兰生《侧帽余谭》里也解释了这种“重色不重艺”的风气形成之原因:“大约生旦之曲,宜于浅斟低唱。雏伶喉气未充,仅能随箫管依约附和。而观此等剧者,亦以色不以声也。”[2]602
综观晚清文人笔记,文人对伶人“色”的偏爱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神貌,二是身形,而这两个方面也基本成为文人笔记对优伶“姿色”描写的主要内容。
文人笔记对伶人神貌的描写多包含以下几个关键词:
首先是“妖”“媚”“艳”,此为最多,如施兴儿“明艳妖娆,颇饶风趣”[2]30,王庆官“抹粉登场,浪荡妖淫”[2]31,小添喜“妩媚飘逸,翛然尘表”[2]395,沈宝玲“风流放诞,媚态横生”[2]421,金林“妖韶婉娈,楚楚可怜”[2]586,等等。《莺花小谱》甚至直列文艳、婉艳、柔艳、丰艳、秾艳、娇艳、妍艳、稚艳、酣艳、纤艳、芳艳、浮艳、冶艳等十三种品级来对伶人分类。[2]219—221
其次是“娇”“憨”,如罗霞林“娇憨习态,谑浪成风”[2]203,史章官“弱骨多娇,似柳态三眠”[2]28,张发官“弱不胜娇,雅韵闲情”[2]40,翠琴“是真娇艳,一顾倾城”[2]392,翠玉“侍儿扶起,娇态怜侬”[2]393,等等。
再次是“静”“婉”,如薛四儿“风姿婉娈,面似芙蕖”[2]27,陈桂林“性情温婉,举止安闲”[2]65,朱延喜“以清婉之品,驾而上之”[2]397,汤金兰“静婉有度”“憨态横生”[2]397,等等。
除此之外,描述伶人神貌尚有“秀”“丽”“俊”等关键词,不一而足。李渔《闲情偶寄》单列“声容部”,以品析女性之美,其中选姿上的“态度”一方面,便特重“媚态”[9]225,而晚明类书《事物绀珠》卷十“姿容部”中,亦将“艳丽”“婵娟”“妖冶”“妍媚”等均归在“女美姿类”和“女嘉容类”。[10]通过这些关键词的比照,不难看出,晚清笔记中对乾旦神貌的描写,多半用描写女性神貌的词语。
笔记中对乾旦身形的描写,主要集中在“肌肤”和“身材”上。
肌肤方面,《闲情偶寄》云:“妇人本质,惟白最难……白难而色易也。”[9]212而晚清文人品旦色之肌肤亦特重“白”“雪”“玉”。正所谓“雪肤花貌不参差,绝似人间好女儿”[2]506,文人对乾旦们皮肤之白皙的喜爱到了一种偏执的状态,那些被文士欣赏的名伶,几乎均属于皮肤白皙的类型,如“雪肤兰质”[2]34的四喜官,“肌肤似雪”[2]204的王桂林,“玉肌莹洁”[2]205的飞来凤,“白皙清癯”[2]1031的张发林,又如“雪肤玉肌,冠绝流辈”的袁双喜[2]587等。因此,许多皮肤黝黑的伶人便往往被人讥诮,如被称为“状元夫人”的道光名伶陈长春,“面目黧黑,有‘墨牡丹’之诮”[2]365,“肌肤不甚白皙,当时轻薄者有煤炭捏成一联”[2]298,在京师人称“煤黑子”[2]365。故《侧帽余谭》所谓“相君之面,虽不能尽似六郎,然白皙翩翩,鲜见黝黑”[2]624,信也。
文人笔记对伶人身段的描写,虽无特殊关键词,但可以见出的是晚清文人所爱者多系“腰肢丰约得宜,身材修短合度”[2]88者,如“癯不露骨,丰不余肉”[2]312的陈玉琴,或如“面目丰腴润泽”[2]298的庆龄,而其他“丰肌露靥”[2]26(于永亭)、“体干丰肥”[2]84(玉林)、“体貌丰腴”[2]101(春林)者,均需要有其独特的魅力方可赢得士夫的欣赏。所以,为了弥补,许多身材不足的伶人也尝试了很多方法,如双喜官“弱冠后,颀长堪憎”,于是他在演《玉环醉酒》时“多作折腰步”以藏拙[2]36,而梅巧玲更是利用其丰腴的身材专演《雁门关》《盘丝洞》等剧,并因此获得“胖巧玲”的美誉。
从这些文人笔记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不论伶人的神貌还是身形,都旨在追求一种柔媚的女性之美,柔在弱柳扶风,媚在娇艳动人。结合《闲情偶寄·声容部》来看,这种追求与其说是清代知识分子对女性的一种憧憬和追求,不如说是一种规定和要求。而值得注意的是,优伶们对这种文士追求并未反抗,而是妥协并主动参与这种话语建构。这种妥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作为文人士夫性爱的对象,伶人在一定程度上要代替妓女,需要接受“女性化”的培训,在“成童”之前,学语、学视、学步,一步步女性化,这是性别特征的妥协。《清稗类钞》载:
同光间,京师曲部每畜幼伶十余……其眉目美好,皮色洁白,则别有术焉……择五官端正者,令其学语、学视、学步。晨兴,以淡肉汁盥面,饮以蛋清汤,肴馔亦极醲粹;夜则敷药遍体,惟留手足不涂,云泄火毒。三四月后,婉娈如好女,回眸一顾,百媚横生。[1]5102
艺兰生《侧帽余谭》中所记更详:
凡新进一伶,静闭密室,令恒饥,旋以粗粝和草头相饷,不设油盐,格难下咽。如是半月,黝黑渐退,转而黄,旋用鹅油香胰勤加洗擦。又如是月余,面首转白,且加润焉。此法梨园子弟都以之……粉郎一至,正如荀奉倩熏衣入坐,满室皆香。盖丽质出于天生者少,不得不从事容饰。芳泽勤施,久而久之,则肌肤自香;更佩以麝兰,熏以沉速,宜无之而不香矣……窄窄蛮靴,小步花砖面上,亦殊可观。[2]624
这里,粉饰和熏香的表面修饰尚不足提,小脚蛮靴的体貌改造却让人深思,据《金台残泪记》云:“京伶装小脚,巧绝天下。谱云始于魏三,至今日尤盛也”。[2]244“谱”即《燕兰小谱》,叙及京旦装小脚时云:
友人云:京旦之装小脚者,昔时不过数出,举止每多瑟缩。自魏三擅名之后,无不以小脚登场,足挑目动,在在关情。且闻其媚人之状,若晋侯之梦与楚子抟焉。余曰:“闻昔保和部有苏伶沈富官,容仪娇好,缠足如女子,但未知横陈否耶?若偶渔婢,当有可观。”相与大噱,诗以解嘲。[2]46
伶人如女子一般缠足以娱士人,士人却“相与大噱,诗以解嘲”,此中辛苦怕只有伶人自知。
其次,作为文人士夫亵玩的对象,伶人多以一种娇弱的姿态在文献记载中出现,弱柳扶风的样子才能赢得士夫们的垂怜,这是人格形象的妥协。所谓“儿女英雄自可人,娇憨无力总风神”[2]241,“娇憨无力”才是文士大夫们最喜爱把玩的状态,也正是为了迎合这种喜好,“乐部登场,必有扑跌一出”[2]241。作为戏曲舞蹈动作的一种,“扑跌”除了用在武打场面,还经常用于展现女性娇弱失闪的样子,以此来表现女性的娇柔。
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文士与优伶实际深深陷入的是一种“看”与“被看”,“欣赏”与“被欣赏”的权力话语体系之中。“戏园客座,分楼上、楼下。楼上最近临戏台者,左右各以屏风隔为三四间,曰‘官座’,豪客所集也。官座以下场门第二座为最贵,以其搴帘将入时便于掷心卖眼。”[2]353“狎旦色者,曰‘斗’,争坐下场门。……二‘斗’每据一几,虚其位,待旦色入座问安,立于仆竖之间。”[2]249“掷心卖眼”之谓,系指伶人的“站台”,是伶人招徕顾客的一种方式,多由貌美的雏伶来进行,“自挂籍乐部后,日日进园,立于戏台之东西房,谓之‘站台’”[2]602。其实质是一种色相的展示,即用美貌和身段的展示来吸引老斗们的目光,引起注意并相与狎亵。《梨园竹枝词》中有“站台”一首云,“隐约帘栊半面窥,亭亭玉立雁行随。秋波最是传情处,一笑瓠犀微露时”[2]514。“似曾相识者通眉语”[2]602,站台的雏伶通过眼神与台下的老斗搭讪,往往带有“挑逗”的意味,“绣幕微开,璧人宛在,不觉目为之注,然犹仙树有花难问种也。郎即搴帘凝视,竟日不移,浅笑微颦,目挑眉语”[2]187。
这种看/被看、欣赏/被欣赏的话语建构,实际上暴露出的是伶人身份中悲剧的实质。厉震林在谈及中国古代伶人“性别的话语权力与编排”时认为,正是知识分子拥有话语权的优势地位,所以他们试图建构的权力制度和价值体系才试图将伶人“从常规的社会性别角色体系中驱逐出来,成为一种异类,失却了‘正人君子’和‘良家妇女’的正常社会性别角色”[6]38。从这些文人笔记的记载来看,乾旦们也确实是这样一群被社会“孤立”与“放逐”的人群:为博取文士的关注提升色艺,却依然是文士“讥嘲”和“戏谑”的对象。因此,与其说乾旦的女性化具备“社会性别的‘女性’气质,故而是‘卑贱者’的社会角色”[6]35,不如说,正是伶人“卑贱者”的社会角色以及女性地位的卑微,男性伶人以女性的“身份”进入男权的社会视野进行话语编排时才更显悲剧。
二、文士品格:伶人才艺的书写
《金壶七墨》记载,“京师宴集,非优伶不欢,而甚鄙妓女。士有出入妓馆者,众皆讪之;结纳雏伶,征歌侑酒,则扬扬得意,自鸣于人”。[11]40—50又《春明梦录》云:“京官挟优挟妓,例所不许;然挟优尚可通融,而挟妓则人不齿之。”[12]139这两则记载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京城士绅狎伶的原因,一是“例所不许”,二是狎妓“人不齿之”。一种口径被封死,总需要借另一种口径加以疏解,清初的一系列严禁狎妓的禁令确实使得士夫群体向优伶倾斜,但一定意义上将士夫们几乎完全推向优伶的是那种以狎妓为耻的文士价值观。嘉道时,妓馆青楼所处的金鱼池一带,因多系贩夫走卒的聚集地,文人士大夫多避免与下流为伍,往往投以鄙夷之视,至光绪丁酉、戊戌间“娼寮颇卑劣,视韩家潭之伶馆不如远甚”,[1]51—53因此士夫们更对妓馆避而远之。《燕京杂记》云:“京师娼妓虽多……豪商富官多蛊惑于优童,鲜有暇及者……过而狎者,尤为下流无耻。”[13]129
晚清狎亵小说《九尾龟》一百五十三回中,秋谷与姚观察一番对话颇能解释晚清士人狎伶的状态:
秋谷道:“……那班相公,究竟是个男人,应酬狠是圆融,谈吐又狠漂亮,而且猜拳行令,样样事情都来得,既没有一些儿扭捏的神情,又没有一些儿蝶狎的姿态,大大方方的,陪着吃几杯酒,说说话儿,偎肩携手,促膝联襟,觉得别有一种飞燕依人的情味。不比那些窑子里头的妓女,一味的老着脸皮,丑态百出,大庭广众之地,他也不顾一些儿廉耻……偏偏的一个个都是生得个牛头马面、蠢笨非常,竟没有一个好的。……却又觉得不叫一个陪酒的人,席上又十分寂寞,提不起兴趣来,所以每逢宴会,一定要叫个相公陪酒,这就是大家都叫相公不叫妓女的原因了。”姚观察听了道:“……做妓女的究竟是个女子,比不得当相公的是个男人……这班当大老的人……在席上露了些马脚出来,体统攸关,不是顽的,倒不如叫个相公,大大方方的,没有什么奇形怪状的丑态发现出来。”[14]971—972
如果说秋谷所云道出的是士人狎伶的客观事实,那么姚观察则着实道出了士人狎伶的内在原因——“体统攸关”。一定程度上而言,晚清文士与伶人相交与嘉庆以前相比的确少了一些“形而上的诗意”,“明显地形而下起来”,趋向于理性化。[15]242这重“理性化”体现在文人对世俗眼光的关注以及对阶级身份的体认上。优伶清赏过人,“学士文人皆乐与之游,不仅以顾曲为赏音也。然此皆闲曹年少时为之,若官跻卿贰,年逾耆艾,则仍屏绝征逐,以避物议”[12]140。最具代表意义的是潘祖荫与朱莲芬的交往。《怀芳记》记载,“(朱莲芬)稚齿喜作字,后乃益工,得者珍如珠玉。度曲亦极精,亭亭物表,独步一时,无与抗者。潘侍郎极赏之。莲芬遂谢却梨园,闭门种花临帖”,“水芝已杜门数年,忽失潘侍郎意,不能自存,复上歌场,风情不减”[2]588。又《春明梦录》云:“尝闻潘文勤平时最喜一善唱昆曲、兼工绘事之朱莲芬,及任侍郎,便不与之相近。而莲芬年节前往叩贺,文勤必袖廿金银券,出而亲授之,一见而别,至老不衰,都下传为韵事。”[12]140
不过,从晚清笔记中的相关记载看,文士与梨园的交流多呈现为一种主动和自觉,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梨园秩序与伶人品格的建构,梨园花谱的传写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从这些以文人笔记的形式流行的花谱中,我们可以看到,文人通过建立花榜、品题月旦的形式将文士世界中的金榜移植入梨园界的同时倾注了文士阶层的许多权力话语a“权力话语”是米歇尔·福柯思想的重要关键词。在福柯那里,“话语通常指陈诉的总体”,它往往与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参与制度和规则的建构,某一时代或某一群体特有的话语秩序“具有规范和规则的功能,它利用组织现实的机制,并生产知识、战略和实践”。而福柯的“权力”就在这些机制的关系之中存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行使权力”,总有一方占据着“关系的要点”。[16]40—41,121—123,也正是这些话语建构起了晚清文人的独特品质,伶人的文士化就是其中很重要的方面。
从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看,晚清的许多伶人均有文士习性,如“人前小坐抱幽怨,酒半清谈解名理”[2]238的昆曲名伶杨法龄,“聪颖特达,文而又儒”[2]291的吴金凤,“笔墨超脱”[2]306—307的俞小霞,“风流自赏,拈毫弄翰,怡然自得”[2]319的张纫仙,“学弄墨,作小楷,画兰蕙,并有可观”[2]339的胡韫香,“耽诗史,尤工楷法”[2]463的乔蕙兰,“工书法,笔意似赵王孙”[2]464的钱桂蟾,“工画兰,有板桥道人风致”[2]671,“儒气且益,深言动雅”[2]676的梅凌云,“酷嗜书画,每见必论及之”[2]678的顾玉仙,“性喜文墨,暇辄染翰”[2]1100的姜妙香等,不一而足。b有文章如何志宏《男色兴盛与明清的社会文化》(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从《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整理出“有‘文士风’的优伶”共55人之多。这些伶人中亦有不少技艺不凡,令文士叹服,如师名伶范小桐擅长画兰,士夫“有不能致小桐手迹者,自惭为不登大雅之堂,自惭为不韵”[2]304;沪上名伶周凤林“能摹写钟鼎古文,悬针折钗,盎然古趣。寸缣片纸,人皆宝之”[17]173;“状元夫人”朱莲芬“师法襄阳,又参以诚悬体,劲挺有姿,其擘窠大字书,尤有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之概。吴县潘文勤公时命其代笔,名噪都下……未得倩朱伶一书屏联,殊为憾事”[2]830—831。
从晚清笔记的记载来看,伶人亦多以文士自处,以文化人自居,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儒雅化,培蓄文士的修养;一是侠义化,追求文士的品格。
首先,所谓伶人的儒雅化,指伶人学习文士的行为法则和处事方式,修身养德。从笔记中看,无论才艺展示还是生活起居,伶人无不向文士倾斜。京师文士们钦服的名伶吴桐仙,除绘技非凡外,在倚声填词、修文断句方面也十分精通。许多文士“往往以门生畜之”,其研学精益,“举人且逊其勤苦”[2]291—292,而且每有伶人尚雅,文人常以吴桐仙作比。有的伶人甚至有诗集付梓刊行,《日下看花记》中便有刘朗玉“著有《红药新唫》,乞序于味闲居士表其方韵”[2]57和王锦泉有“《兰秋小咏》,壶天大隐序而梓行”[2]64的记载。前述擅长画兰的范小桐“所居曲房小室,张自画兰蕙小幅……绿窗人静,空谷生香”[2]304,而芷香的春华堂也是同样,“窗明几净,壁上皆名人书画,案头设绿萼梅一盆,清芬扑人,无纤毫尘俗气”[2]569,如处士一般。有的伶人境界高远,追求孔颜之乐,如林韵香,“室无纤尘,名书法画外,古琴一,洞箫一,自鸣钟一而已”[2]251。林韵香气质“渊然静穆”,文人多对其敬佩有加,认为他“无烟火气,无尘土味”,如藐姑射之山上的神人一般。[2]283不仅学习文士行为,吟诗作画,同时亦将文士情怀渗入在日常起居,伶人的儒雅化,可见一斑。
其次,伶人不沉迷名利和欲望,“品格高绝”“不趋时好”“任性豪侠”,便往往会得到文士们的极力赞扬。如文人笔下广为传颂的名伶梅巧玲轶事,《明僮续录》云:“蕙与某公善,居久之,某公得监司,贫无以治装,蕙贷以资,且不责劵。某公强予之。囊橐既具,未成行而某公殁。会吊日,甫辨色,蕙遽至,人谓为索逋来也,相愕眙。蕙入帏哭且拜,探怀出劵就烛焚之,大恸去。”[2]426又如张梅生,“时所知有官闽中者,寄百金为催妆资,乃书达而金不至,无从责寄书邮,几不能归。梅生竭旬日力,遍告知好,醵二百金以壮其行”[18]555。此外,笔记中屡有记载伶人接济落魄书生的义举,如《梦厂杂著》中载有李玉儿接济李重华事。李玉儿资助落魄书生李重华,一直至“登进士,入翰苑”,二人“交情不替如一日”,李重华死后,李玉儿并能“经纪其丧,抚其幼子”。[2]894—895伶人的这种信义之举、侠义之风,往往让文人感叹古风,“今之古人哉,乃于伶也一遇之”[2]426——这是文人对衰世世风的感叹,又是对其自身的自警和自效。
值得注意的是,文人们对于这些“不趋时好作妖媚之状”[2]21的伶人颇有好感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品格清奇。如姚妙珊“性简默,若不屑角逐歌场,尤为町畦独辟”[2]571;张菱仙“气度闲雅,静穆自好,不屑俯仰侧媚取贵人欢”[2]538;陈秦云“巾影衫痕,风流自赏,其风度正当在魏晋之间也”[2]668;李德华“神情蕴藉,襟带闲殊,有晋人风概”[2]537;王玉笙不齿为淫邪之戏,不与世俗同污,“亭亭自好,专以色艺见长”,“有识者嘉其志,亦遂以青眼相加”[18]568。
文人“品藻群芳,不尽以古代著名美女相比拟,而屡形容为名士高士,却正好显示了他们评价的标准”[19]209,正如《怀芳记》所云:
歌伶虽贱技,而品格不同。其为贤士大夫所亲近者,必皆能自爱好,不作谄容,不出亵语,其令人服媚,殆无形迹之可指。爱身如玉,尤如白鹤朱霞,不可即也。别有一派,但以容貌为工,谑浪媟女卖,无所不至。且如柳种章台,任人攀折。此则我辈所恶,而流俗所深喜者。[2]595
可见,文人喜与伶人交往,多半是由于伶人身上的所谓“性情”与“品格”,而这些均是文士话语的产物。
三、我辈情结:衰世文人的话语陷阱
通过对晚清笔记中乾旦身形与才艺书写的分析,我们时时可以见到的,是文士价值观对伶人的要求、规定,甚至改造。在面对乾旦这一特殊群体时,文人们无不具有一种文士阶层特有的优越感,而所有对伶人阶层的关注与关怀亦是以此为前提。
“花谱虽强调士优之间的平等关系与情感交流,但仍主要将演员作为其品赏的客体,以及有别于自身阶层的‘他者’来看待,因而在花谱中缺乏演员自身的声音,而是文人将心目中的各种性别理想特质,投射在演员的形塑描写之中”[20]47。正如福柯所说,“知识分子本身是权力制度的一部分。”[21]206而这里,文士阶层实际上借助着一种性别越界的文体想象,实现了对伶人外在和内在的双重建构:一是接受看/被看的话语体系,对伶人外在身体进行了改造;二是在欣赏/被欣赏的依赖关系中,实现对伶人内在人格的建构。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福柯的“主体与权力”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控制和依赖而屈从于(subject to)别人”,二是“通过良知和自我认知受制于(tied to)自我的身份”[22],因此,某种意义上,伶人们看似主动进行的“改造”,以及文人对自身阶层身份的维护,均系来自社会和文化的建构。
在文人对优伶的记录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一种看似美妙,实际却是社会和文化建构起来的话语陷阱,这从笔记中时常推崇的“状元夫人”故事,以及文人品花、惜花的题赠中可以窥得一斑。
(一)“状元夫人”故事的话语陷阱
道光之后,文人笔记中“状元夫人”的故事广受称赞,也记载颇多。“状元夫人”指乾隆朝尚书毕秋帆与男旦李桂官之间的风流韵事。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记载,“毕秋帆尚书沅、李郎之事,举世艳称之。袁大令、赵观察俱有《李郎曲》……溧阳相公呼李郎为状元夫人,真风流佳话也”[23]50。杨懋建《辛壬癸甲录》所录较详,“乾隆初,毕秋帆先生春试报罢,留京师,李桂官一见倾倒,固要主其家。起居饮馔,供给精腆。昕夕追陪,激厉督课,如严师畏友。庚辰,秋帆尚书以第一人及第。时溧阳史文靖公重宴琼林,来京师,笑谓诸君曰:‘闻有状元夫人者,老夫愿得一见。’一时佳话流传至今”[2]296。嘉道之后,凡伶人与士夫官绅公开交往,人多以“状元夫人”目之,如《啸亭杂录》中所载龙汝言最善的檀兰卿,《金台残泪记》中所载查友圻所悦的何郎,《辛壬癸甲录》中朱朵山所眷的陈长春,以及《梨园旧话》中潘祖荫所赏的朱莲芬,均被人称为“状元夫人”。[24]这些状元夫人的记载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伶人与文士相倾相赏,“起居饮馔,供给精腆。昕夕追陪,激厉督课,如严师畏友”[2]296,常被认为是晚清文士大夫与伶人相处的最高境界。杨懋建所记自己和名伶俞小霞的故事便是如此。杨懋建春闱落地,“小霞每以为戒曰:‘以子才华,如日在东。奈何效唐子畏、杨升庵、康对山诸公失意所为?窃恐文人无福,不幸言而中也’”[2]307。后杨懋建因科场案牵连入狱,“小霞职纳橐饣亶,拜为上下营救”,二人常以诗文知己相称,小霞“尝手抄掌生诗词成帙”,并多有诗歌唱和。[18]565
值得注意的是,文人笔记中关于“状元夫人”这些记载,一直隐藏着一种“发迹变泰”的线索,可以大体整理为“文人落难—伶人接济—文人发迹—伶人追随”的情节模式(前文所引《梦厂杂著》,伶人李玉儿对李重华的接济与相守亦是一例),而且这种模式均以互不离弃作为结局。这与古代戏曲、小说中的“发迹变泰”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a关于古代戏曲、小说中的“发迹变泰”故事,可参考潘承玉:《论宋元明小说、戏曲发迹变泰题材的流变及其文化意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张健秋:《古老而常新的模式化叙述——论“发迹变泰”故事的叙事艺术》,《北方论丛》2005年第5期;王伟:《元杂剧发迹变泰情节模式化浅论》,《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等等。从中可见的是,文人们一直试图将文士与伶人的同性关系努力整合到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以换取合法身份的自觉。一定程度上来讲,这正是王德威在谈论晚清小说时所说的,晚清文人在“将男伶写成才女,将伎男及嫖客写成恪守孔孟之道的禁欲主义者,以及将颓废堕落写成三贞九烈”时,所暴露出的“急于调和伦理规则和情欲诱惑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局限。[25]77
(二)“品花”题赠的话语陷阱
文人笔记中多记文士对伶人的月旦品评,美其名曰“品花”。“我辈素有雅癖,苟于若辈中得一知己,亦可以无憾”[2]571,这是《凤城品花记》中香溪渔隐的感叹,而某种意义上也是所有品花文人品藻群芳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文人在会试之年同时为伶人开花榜,据艺兰生《侧帽余谭》记载,“逢会试年,新进士胪唱后,品题群英,定为及第花三枝。填写花榜,鼓吹送至其堂,一时传为佳话”[2]604。可见为伶人开设花榜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戏仿,而是将伶人“引为同调、视同侪类 ”[19]214。
“天涯落落,知己难逢”[2]573,晚清文人笔记中的“品花”记录,均有一种“我辈”之叹与“知己”之思。“常将肝胆酬知己,小占温柔即美人”[2]307,在这些乾旦身上寄托着文士们对“知己”和“美人”双重意象的追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士们将伶人视为另类的“红粉知己”,很大的原因来自伶人“风尘沦落”的身份。这些撰写花谱的文人,有很大一部分是科场失意的典型,“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红粉”[2]279,“长安羁滞,短剑飘零,一名未成,万里空涉”[2]386,其撰写花谱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抒发自己的不遇感怀。因此当他们发现许多清雅的伶人“非俗眼所能赏,故座客终稀”[2]585时,便往往引而感伤。
“世多怪事,仆本恨人。沦落既同,悲歌何极”[2]389,晚清风云变幻,世事莫测,令文人们担忧,这在《金台残泪记》自叙中表露得特别明显:
孔子泣获麟后,天下有二泪焉。汉贾生之哭时事也,晋阮籍之哭穷途也。余居都门三载,深观当世之故,颇能言其利而捄其弊。无荐之者,既不敢献策,复不敢著书,辄恸哭。遭家多难,顾影自悲,又恸哭。故人怜之,恐其伤生,每为征乐部少年,清歌侑酒,以相嬉娱。[2]225
“遭家多难,顾影自悲”,这是国与家、时与世的深沉忧思,鲜花易逝,文人们怜花便是怜己。因此,文人对于伶人身世浮沉的感怀并非真正去怜悯伶人世界中那份悲苦的不平等,而只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自身的情感投射,一种自我忧思纾解的途径。这在文人对“黑相公”的态度上便可以见出。“群趋其艳者,曰‘红相公’;反是,曰‘黑相公’。”[2]246作为相公行业底层的一种,黑相公因为色艺平庸少有客人光顾,鲜有收入,往往被师傅责打,因此境遇凄惨,甚至会沦落成为“男妓”。[26]74—75文人们对于这些低贱的黑相公往往鄙夷之,常常作诗嘲之,所谓“万古寒碜气,都归黑相公。打围宵寂寂,下馆昼匆匆。飞眼无专斗,翻身即软篷”[2]562。文人根本无心怜悯伶人们悲惨的境遇,更关注的只是自身情感的定向投射。
文士狎伶虽是时态,但实际上文人对其狎伶总三缄其口,笔记中往往因“或隐讳于家庭,或嫌疑于风影”而“泯其事迹,隐厥姓名”,甚至“其下伎之名字,亦羞污于简编”。[2]706这些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文人们通过“性别越界”的方式对优伶赏析的尝试,但这些尝试却最终堕入了传统的教化理想之中,那份看似由情欲而起的狎亵和品评最终被替换成了“色而不淫”的道德律绳。
虽有学者在经过考论清代梨园私寓的伶人生活和演剧之后,郑重解释“晚明以来流行的男风与狎优,有重合的部分,但狎优不等于男风”[26]17,但这些文人笔记所载却着实记录了晚清文人在衰世中历经沧桑的性别越界想象,这些越界想象对伶人身体和心灵上的改造,实际上书写着的是文士们的人生哀苦与家国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