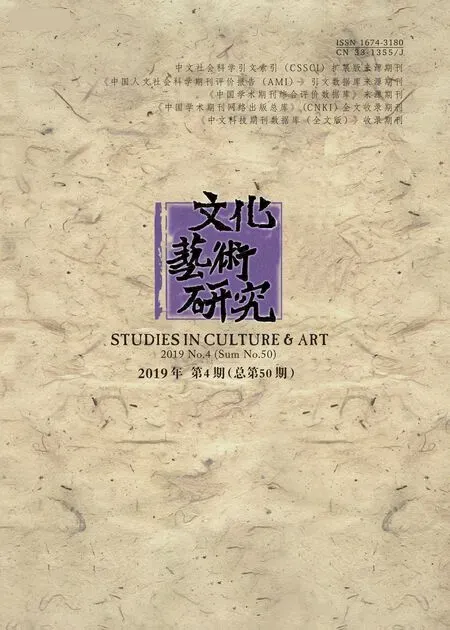符号学视域下《地球最后的夜晚》的电影诗学建构
金 明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作为中国新锐“艺术电影”创作者,毕赣的电影新作《地球最后的夜晚》(下文简称《地球》)延续了《路边野餐》“作者电影”的诗意风格,试图在新时期中国电影版图中书写自己的边疆。在《地球》中,毕赣将故乡凯里凝滞成了爱情的最后幻域,并以电影镜像重新开启自己对于个体生命意义的思考。作为贵州籍导演,毕赣在文化身份上的复杂性,使其电影影像给观众提供了观察全球化视野,兼具审视后现代消费时代脉络下“移民电影”的多重认同特征,同时也形成了带有地域性旨趣的美学风格。《地球》完美的沉浸式视觉效果与作曲家林强、许志远的华丽乐谱相得益彰。这部电影提名第七十一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大奖”,同时收获了第五十五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包括最佳剧情长片、最佳导演奖在内的五项提名,并且最终斩获最佳摄影、最佳音效与最佳原创配乐三项电影大奖,这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该影片在电影美学上的探索与创新。本文以记忆论、影像诗学解析《地球》中的电影符码,试图展现影片独特的美学建构。
一、符号学视域的“记忆呈现”
电影叙事可以理解为记忆的再现。在《地球》中,“记忆”成为毕赣翻转、重译时间的感性材料,契合着罗纮武对万绮雯执拗的追寻过程,透过镜像语言呈现了电影独特的拓扑空间结构。《地球》在2D部分主要讲述了罗纮武现实世界的个人生命经验,在作为朋友、儿子、丈夫、情人、父亲的角色全部失败之后,他走进电影院,用梦境给自己建构了一个乌托邦。3D部分主要呈现罗纮武基于过去与现实的“伤痕记忆”,用梦境不断叙述疗愈创伤的过程,补偿性叙事安排让罗纮武最终得偿所愿。《地球》中时间与空间的表达,呈现出多层性、破碎性、渐变性、去中心化的特点,拼贴式的记忆影像叙事使影片形成弥散性结构,成为日趋多元、充满离散絮语的现实语境的镜像缩影。毫无疑问,《地球》中关于罗纮武“记忆”呈现的片段式叙事是基于其非连续性的生命经验的串联,各种意象不是以时间先后剪接编排,而是通过电影镜像“象征/隐喻”的诗意组合,使得电影梦呓般感官体验与含混暧昧的记忆独白达成和谐的互文与共振。
雅克·拉康认为基于父权社会理性思维建立的城市文明,建构了现代文明社会的“符号域”。《地球》中毕赣则试图通过电影镜像来呈现这个“符号域”试图遮蔽的“真实域”。罗纮武家庭关系的支离破碎、情人关系的相互利用及帮派利益的暴力与死亡,都是父权社会制造的最真实且无法回避的创伤。“符号域”的失真在《地球》中往往经由空间美学的建构与解构表现“真实域”的衰落、灾变与蔓延,通过现实与梦境的失衡暗喻“符号域陷落”的危机。
露西·伊里格瑞发现了尼采哲学中刻意规避的“水”元素,在她的著作《尼采的海上情人》中,以“水”意象开启了对尼采生命哲学的颠覆与重建。在《地球》中,“水”作为一种最为柔性的叙事元素,充斥在影片的房屋、通道中,漫布在自然的、社会的一切场域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最为原始的、具有冲击性的“创伤性内核”。导演塑造了一个欲望蔓延的暧昧空间,这样的情绪也在电影的2D部分中不断蔓延。作为符号秩序失真的重要“能指”,渗漏的水在电影里频频出现,隐喻了“真实域”无法控制的危机与灾变。漏水的隧道以及房间等现代空间暗示着固有伦理的崩坏,连同凯里城市空间的阴雨连绵与河流意象,均隐喻了“现代文明”与“原始环境”的双重危机,从而形成了自然的无力感和文明现代性衰落的宿命感。雨水的连绵不断终于造成了泥石流的危机预警,形成了更为严重的创伤性焦虑的可能。伴随着罗纮武与万绮雯的“偷情”,河流中的“水”意象,作为流动景框的“空镜叙事”,成为情欲原罪的“能指”,暗示着父系情欲法则的崩坏。“水”制造的自然危机感与欲望的失衡感使得固态符号的城市、建筑指涉的“符号域”受到了危机与重创,将要拆迁重建的破败舞厅的门上印有的身体意象,放大了消费社会对于身体的想象,同时也是罗纮武窥探另外一个空间的通道,“洞”造成了原有完整空间的破碎,从而瓦解了原有空间秩序的层次分明,使得人作为文明的“大他者”呈现出生命意义的荒芜。
《地球》中无论是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的破败不堪,都显示出“符号域”内在秩序的脱节以及“真实域”中永远存在的裂隙。泥石流的到来预示着现实的符号秩序所面临的必然冲击,它来自作为“真实域”中多变而无法控制的自然界,代表了现代性符号都市不得不承受来自难以阻挡的“真实域”的侵蚀。这个背景也成为罗纮武的主体欲望(情欲和暴力)无法宣泄的前提,持续累积的压抑与焦虑,迫使其开启了主动的寻梦过程。
《地球》中的凯里并未包含浓烈的城市消费主义符号,如高楼大厦、繁华街市、忙碌交通、琳琅商品等意象,但霓虹夜市、废弃工厂、拆迁影院、破败通道等消费空间以及手表、手枪等充盈着个人生命经验的意象,反映了导演对于社会转型期边缘文化地位的个人意绪与经验。这些“反现代”的电影意象仍然代表了符号化的都市中象征秩序的空洞性与无意义,从而吊诡地呈现出父系文明下“真实域”的鬼魅。
在视觉呈现上,《地球》不断将人物置放到场景中,并且使用多种运镜,使景观作为一种叙事手段,代替了传统的身体叙事,形成了“场景式叙事”。镜头在2D部分不断摇移,人物不再是被呈现的主体,取而代之的是场景——空旷的垃圾场、漏水的空房间、即将拆迁的电影院,运镜呈现出布莱希特式的疏离美学效果。“场景式叙事”充盈在电影的现实记忆部分,一方面延展了电影叙事空间感,使场景代替事件,使得凯里形成了地域性的叙事符号;另一方面,这种策略也制造了电影叙事的留白,通过在身体叙事中不断制造叙事节点的断裂,凸显《地球》暧昧又独特的审美旨趣:伴随叙事与空间的错位,观者从连续的时间轴中跳脱出来,直面“真实域”中种种破败与不堪。
二、延宕式“长镜头”的慢速造梦
《地球》以明晰的两段展现记忆、现实与梦境,现实与记忆是片段式的、断裂的、悬置的,而在梦境中,则用了一镜到底的长镜头去塑造完整的梦境,“导演对于梦境的呈现则是完整的、浓情的和轻盈的”[1]。梦境成为罗纮武在电影院“观看自我”的一种方式。电影的叙事时间被切割成两部分,在现实情境中他不断与亲人、朋友、爱人分离,在梦境中他达成所愿,与想见的人不断“重逢”,“实”与“虚”的电影镜像,使电影中的叙事元素不断编译在莫比乌斯环上,实现了现实与梦境的亲密耦合。
毕赣在《地球》中给观众带来了一种延宕式的“慢”感官体验,其呈现方式就是一镜到底的长镜头运用。长镜头是电影的诗意写真。长镜头因其持续不中断的镜头方式,在电影中制造了一种真实。雅克·拉康在精神分析学中对“真实域”的意涵分析是基于亨利·柏格森和吉尔·德勒兹对 “真实”概念讨论的延续,在其“真实域”中,“真实”是符号化的“现实”所面临的空洞深渊的严肃讨论。《地球》中不断展现被“击碎/整合”的现代秩序,连同人类伦理与原欲的呈现,将父权文明下的现代秩序的断裂褶皱映刻于电影肌理间,以电影之思建构了一个反讽式的道德寓言,而这些质疑印证了拉康认为的“真实域的陷落”。
《地球》通过长镜头这种强烈风格化的电影语言表现罗纮武的圆梦过程。人物的“运动”伴随着长镜头形成了一种迟滞的观影体验,这无疑是导演在蓄意考验观众的忍耐力和专注度。导演以长镜头展现罗纮武在“寻找/逃离”的路径变化,同时也试图呈现他面对生命中难以忍受的时间性压抑的勇气。可以说,毕赣把长镜头和平移镜头运用到极致,呈现出“作者化的运镜”,摄影机及其代表的视点与角度制造观影体验的静止感,以及导演放弃距离感的主观视角的连续跟拍,在《地球》中运用得细腻、隐忍且克制,从而凸显出罗纮武强制性自律的“规训快感”。
父亲留下的汽车是罗纮武继承的唯一遗产,汽车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是现代速度的象征。汽车隐喻现代性,它的速度也是一种快感。电影中,汽车、摩托车所承载的速度明显放慢,这也是电影对于现代性的一种拒绝。这些交通工具作为加速运动的方式,同时作为视觉机器也为观众感知电影时间带来新的可能。它们代表的是一种帮助、自主与治愈,搭载着罗纮武离开一个又一个空间,同时也帮助他开启寻找万绮雯之旅。电影中这些交通工具承载了像摄像机一样的视觉机器的功能,搭建出流动景框,不仅表现速度,同时也重新检视视觉。这一手法串联起现代社会寂寞的边缘,交通工具衍生出承载人物运动的空间,从而帮助电影产生新的空间与景观,体现出导演建构与思考着的速度。
电影中的慢同时也是一种情绪化的呈现,是一种祛除身体叙事的途径。电影通过身体以及身体仪式(行为)在不同空间中穿梭,使得主体的身体无法被符号化,从而呈现出被彻底同一化的创伤性状态。在这个叙事路径中,身体的行动和意义的能指变得虚化空洞,场景中其他要素比相对迟滞的身体更加凸显出叙事作用,隐喻了现代符号秩序的熵运动,它的无序性、含混性暴露出现代社会中所特有的症候。在梦境中,罗纮武从矿山中寻找童年伙伴白猫,经过他的指引,通过缆车慢慢下降到贵州村庄,在台球馆相识凯珍并且帮其解决了纠纷,与凯珍飞到戏台,与“母亲”重逢,并且用手枪迫使养蜂人带走“母亲”,再次与凯珍相会,一起进入空房间,念起绿皮书中的咒语,身体旋转飘移。这个梦境是连续的,也是多个空间交接堆砌的。在这个过程中,身体被不断输送到场景中,“时间/运动”“速度/感知”同步,身体伴随着影像中的轨道(摩托车、汽车、索道)呈现出相对的静止性,但是影像中的其他场景元素则呈现出强烈的律动感。毕赣以承载着身体的慢速影像凸显出与“被加速的时间性”为特质的现代符号秩序,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性别视域下的家庭权力建构
《地球》以电影镜像弥合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三重时间维度的“伤痕记忆”,记忆成为《地球》撕裂观众与封闭银幕空间的路径;同时,记忆作为影片的元叙事也不断交织缝合了电影的叙事剧情。在电影这个宏大暧昧的场域中,叙事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折射社会中“真实”的中性文本,同时为了映刻出在电影中所展现的叙事历史里镌刻着社会秩序、权谋关系与性别话语等共生性力量。电影以空间化的视觉记忆凝滞了离散者的个体生命经验,同时也暗含了其性别主体的文化身份认同。“空间中隐藏着社会权力关系,其中的‘所属’与‘话语关系’都和性别权力关系相关联。”[2]《地球》中的女性形象一直处于失踪、失联的状态,从而制造了一种神秘化,但她们依旧承载着男性的凝视,体现了一种由男性主导的视觉想象与视觉快感。但是伴随着电影叙事,男性的话语权不断遭到冲击与拆解,万绮雯、凯珍、母亲的反叛与出逃逾越出困住她们的父权牢笼,她们逃离焦虑与规训的“密不透风的铁屋子”,在各自的生命历程中重拾主体情欲,从而实现多重主体的自我命名。
当身体嵌入电影镜像呈现的场景中,便形成了新的表意“场域/空间”:符号化后的空间场域。在这个表意系统中,身体与空间形成了紧密的表意联系,身体遭受的伤害、破陨与土地所承受的消费主义的入侵相互联结。《地球》中,万绮雯一直处于被凝视的位置上,她一直都是“被发现/被寻找的”,即欲望的原因——对象。她的存在是罗纮武直接面对“真实域”的起点。她个人的情欲展演复刻出父权社会女性“情欲本我”的面貌。最初,她不得不顺应父权社会的欲望法则,肉身在消费社会与父权制度的合谋下逐渐成为失去能动性的主体,身体成为了欲望胁迫下空洞的躯壳。万绮雯无论在黑暗悠长的隧道里行走还是在断裂的墙壁上移动都可以理解成漫无目的的行为。她居无定所,行无所终,身份暧昧模糊,当她成为欲望对象接受检视时,一切围绕她形成的“真实域”的关系都濒临破灭,如临深渊。
家庭空间是父权文明建构的最稳固的、权谋关系最明晰的伦理场域。家是个体生命的最初起点,是原始恒久的栖居与依恋。但是在《地球》中家庭对于女性却成了不可逃离的围城。罗纮武的母亲、凯珍都因为难以忍受家庭禁锢而被迫逃离。她们如同本雅明描述的巴黎漫游者,寻求现代生活的诗意栖居,躲避一切的规训辖制,拥有鲜明的个人立场。罗纮武的情欲渴望源于其家庭的破碎生命经验,如同《俄狄浦斯王》的“父母子”情欲三角关系的重译:父亲的“在场式的缺席”与“幽灵般的存在”使之成为家庭权谋关系的奇点,母亲的身体是父与子之间争夺的情欲飞地,儿子主体性的焦虑与压抑一方面源于父亲的缺失,另外一方面来自对母亲欲望的误判,但母亲欲望深渊的焦点依旧指向父亲。不同于俄狄浦斯,罗纮武在梦境中拿枪逼走了自己的母亲,拒绝对母亲的情欲依恋,因为主体认同与情欲关系的被迫分离,他在现实中开始了对欲望的独立探索。他遵循着父亲一直凝视的坏了的钟表,在里面寻找和母亲有关的线索。坏了的钟表指涉停留的时间,这与照片的隐喻不谋而合。而照片是记忆的载体,罗纮武依旧沿着记忆去寻找和母亲拥有相同容貌的万绮雯,他们之间的爱情变成了不可解的魔魅。电影中呈现的爱恋模式,依旧带有原罪模式的“恋母情结”。情欲戏仿策略的运用,再次质疑了父权社会的欲望法则,《地球》试图将那些游离于边缘的爱恋关系以影像写入正典。
四、电影镜像“阴性书写”的诗意表达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个人“情欲”的哲学解释建立在以男性身体作为完整的身体原型的基础上,以其理论模型为特点的“阳性书写”注重逻辑与理性。而露西·伊里格瑞则以“窥镜政治学”颠覆了弗洛伊德的身体观点,她认为女性不应该以男性的身体结构去建构自身的完整性与主体性,而应该在基于自身生理差异的基础上考虑自身的完整,因而女性的书写应该与自身的性别气质与身体奥秘贴合,拒绝男性崇尚的理性位阶的起承转合的线性书写,试图展现女性性别气质与多元逻辑。因而“阴性书写”则充满了暧昧、混沌与梦呓癫狂,成为如柏拉图所言的“子宫般”的玄牝空间。诗性元素的加入拓展了“阴性书写”的可能,从而使得“阴性书写”展现出变幻莫测、灵活多变的美学风格。电影的“阴性书写”则借助镜像场域,透过电影感官化的表达方式,呈现非线性、多意化、片段式的电影意象,从而制造与延宕出新的意义,电影镜像在这样的表达中渐生的诗性特质,在《地球》中有影像、空间、身体三个方面的表现。
(一)影像
《地球》中常通过破碎的镜子、切割的玻璃表现人物,暗喻了人物多重主体性的存在。电影运镜不断游移在被拍摄人物周围,当人物停止运动,镜头便开始了游移。镜像留白的使用使得人物嵌入场景,不再是电影叙事的主体,而是通过空间叙事来代替身体叙事。电影镜像对于个人生命意义的重新思考同时还体现在对于分裂的呈现,“众多人物身份错位漂移后留下的回溯式记忆体验和弥漫其中的对于情感对象近乎顽固的追寻意图”[3],如同对于弗洛伊德所言的“文明以及对文明不满”的矛盾逻辑的镜像释意。这种分裂展现了影像的分裂:伴随着罗纮武的追寻,开启了他反思生活的契机,如德勒兹所言的“意义的逃逸线”,“它是开放的、多样性的,无主体的、无中心的,充满着差异的、多元的、非地域化的,是边界和障碍的打破,无拘无束,自由奔放”[4]。“逃逸线”不断将主体送离当前所处阶段,同时又帮助主体进入全新未知的新旅程。它承载着现代秩序的释义,同时也预示着个体生命在现代生活中的多种可能性。电影中多次将罗纮武呈现为“脱轨分子”,他不断离开原来的既定路线,“出轨/调轨”“迷失/导正”,这不仅包含着对宿命论的反抗,同时也承载着对未知生命历程创造性的感知与探索,为个体生命经验的开展带来了新的可能。电影中女性角色在现实与梦境中拥有不同的身份,演员汤唯分饰万绮雯和凯珍,演员张艾嘉分饰理发店老板(白猫的母亲)和红头发疯女人(罗纮武的母亲),这些女性角色虽然都与贫穷、底层、异质的边缘生命经验相连,但她们总是敢于开启自身生命的“逃逸线”,践行“庶民的发声”与多重话语权的争取,实现个体生命意义的抗争。
(二)空间
《地球》中,公共空间的繁华映衬着私人空间的衰败,资本积累导致的空间扩张进一步加深了公共空间的人物焦虑。电影中,人物栖居的房间,或是暗居于地下,或是破败不堪,这是资本与现代性秩序对于个体生命空间吞噬的焦虑表现。梦境中的城市中心是电影院地下的洞穴,白猫的家被凝滞在废弃的矿穴之中,成为黑暗幽闭的场所。这些空间意象反映了消费社会带来的资本在城市无节制的扩张造成的空间紧张,体现了消费社会带给个体生命情感上以及潜意识层面的压抑与抵抗。在电影中,梦境使语言、文字具象化、肉身化,罗纮武与凯珍伴随旋转的乒乓球拍飞翔,他们念着绿色封皮书里的“咒语”自由旋转,电影中“语言/身体”呈现出的反复粘连与抵抗,电影空间得到了极大的延展。《地球》中电影意绪的表达取代了叙事的意义,镜像空间通过“阴性书写”衍生出创造性的审美想象,电影意象承载的能指变得丰富且多义,这是被压抑的无意识获得宣泄的方式,从而为导演的感性想象提供了某种契机。《地球》通过对运动的呈现形成了一种电影式的知觉阐述,在这种表达中,时间不断拆解着知觉,时间与知觉的瞬时性被强制中断,同时时间也不断重组知觉,进而形成一种复调式审美体验,达成了与时共生的美学碰撞。
(三)身体
《地球》中,罗纮武的身体不断穿梭于隧道、通道、街市、废墟等公共空间,休憩于地下洞穴、漏水的房间、破败的宾馆等私人空间,这些幽深空间映照出人物虚无荒凉的精神世界。伴随罗纮武寻觅万绮雯路途上的层层受阻,他也未能放下为白猫复仇的执念。随着电影镜头的缓慢推进,身体不断在空间中置换,罗纮武呈现出身体的焦虑疲惫,影片中的空间与身体互相“进入—浸入”,意义叠加渗透,形成了意义的能指链。
《地球》中身体还呈现出一种极端的处境——暴力。暴力,在电影诞生伊始就成为重要的原始命题,它以征服与终结人的肉身为目的,同时兼具极端的权力指向。《地球》中,女性的身体不断承受着男性的暴力:万绮雯受到左宏元的殴打,凯珍受到两个不良少年的骚扰;男性则不断与死亡的生命经验相连接,白猫、左宏元相继被谋杀。伴随电影中暴力情节的展现,身体处于极端的规训处境中,通过身体的受难、创伤,一方面以视觉图谱的形式记载着身体的记忆;另一方面,暴力作为一种视觉奇观,本身就具有拯救、受训、复仇的感官快感。电影中展现的两场谋杀,充斥着人性的罪恶与欲望的污垢。毕赣试图通过包裹着性别要素的身体呈现来体现现代秩序中性别权谋的博弈:父系身体的无力、焦虑与创伤对应着现实世界的“真实域”;而女性身体的丰腴、鲜活与激情则复刻着现实世界的“符号域”。两个场域意象的巨大反差映射了“真实域”的倾颓。万绮雯的身体成为欲望的机器后,身体不断与外部欲望勾连,伴随着丰沛的欲望流动,女性身体在欲望的支配下不断充盈,开始了对父系伦理的反抗。女性以自身生命经验的身体逻辑,演化成性别反驯化的原动力,进而建构了充满性别愉悦的身体诗学。
结 语
《地球》中有音乐、梦想和魔幻现实主义的爱情,也有暴力、血腥和死亡的严酷现实。这部作品平衡地呈现了梦想、噩梦和现实。《地球》不仅是一部黑暗悬疑电影,而且是一部反讽式道德政治片。就像《路边野餐》,毕赣试图以一种打破地域隔离的艺术情怀使电影拥有共生式的美学体验,它既是爱情故事,也是写给老电影和旧式观看方式的情书。《地球》通过对罗纮武破碎生命经验的书写,梦境乌托邦的呈现,揭示“真实域”的内在匮乏。电影通过镜像的解构与建构,杂糅出现实记忆与虚构梦境的开放性文本,创造了一种女性主义表达方式,逃逸出传统男性叙事的权威,对女性的身份、主体性、身体进行了想象性的建构,使其变奏出独特的美学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