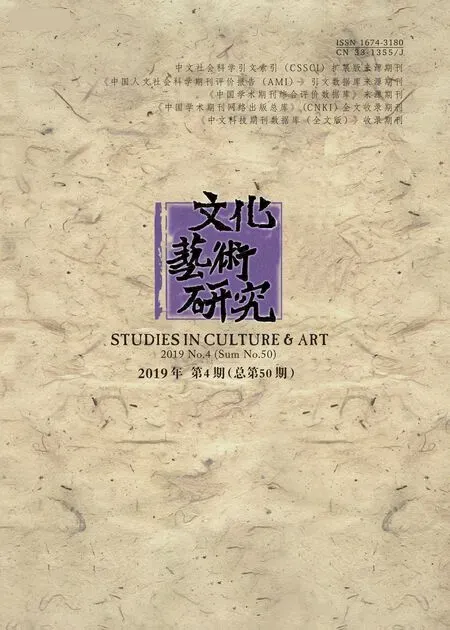《江湖儿女》与贾樟柯的电影江湖
田 野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贾樟柯是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从影数年,斩获多项电影艺术奖。从《小武》到《站台》《任逍遥》《三峡好人》《江湖儿女》,贾樟柯逐步建立起他的电影江湖。《江湖儿女》于2018年9月21日在中国大陆上映,关键词“江湖”引人注目。贾樟柯成长在武侠小说走红,香港武侠、黑道电影在国内盛行的20世纪80年代,这孕育了他少年时代的“江湖”梦想,也使他在电影创作中一直致力于表现“江湖”:小武“是一个江湖人士”[1]86;《三峡好人》“整个框架模型就是武侠片的”[1]86;《天注定》亦是“借鉴武侠片的方法”创作的“当代故事”[2]140。“江湖”是贾樟柯年少时的情怀和电影创作的核心理念,其创作历程也是理想“江湖”的实践和沉淀。
《江湖儿女》是贾樟柯“江湖”创作的总结和超越。从电影技巧讲,《江湖儿女》用不同的媒介呈现了贾樟柯“个人影像生活的记忆”,开头片段是贾樟柯于2001年用他的第一台DV拍摄的一段原始素材,画幅比例只有4︰3,影片从DV到HDV到胶片再到最新款数码设备,贾樟柯在创作《江湖儿女》时用了“六种摄影器材来呈现时代的变化”[3]。从叙述时间看,《江湖儿女》故事时间从2001年到2018年,相当于贾樟柯电影创作的时间长度。影片中2001、2006、2018三个时间节点,正好对应《小武》《三峡好人》《江湖儿女》。贾樟柯在节目访谈中也曾提及这种有意的对照,可见其对《江湖儿女》寄予的厚望。此外,从情节、人物塑造到景致、音乐、服装饰物等,《江湖儿女》都流露出贾樟柯往昔电影的痕迹。比如,其主人公与《任逍遥》的人物重名。多处影片段落与往昔电影重合。或从昔日电影里截取片段直接运用,或是同样场景的再现,如《站台》中的集体演奏,《任逍遥》中通往公路的小桥,《三峡好人》中的三峡场景等。人物服饰方面也有意重合,巧巧开襟黑丝短褂内搭玫红绸的蝴蝶套装与《任逍遥》中的巧巧相同;巧巧着米黄衬衣、淡灰西裤,与《三峡好人》中的沈红相同。
总之,《江湖儿女》是贾樟柯电影创作历程的浓缩,也是贾樟柯情感的积淀。“写下江湖儿女四个字时,我好像潜到了自己的感情深处。”[4]因此,可以说《江湖儿女》是贾樟柯电影江湖最全面的体现。从“江湖出发”,在时空变动中可以把握贾樟柯的电影精神和美学理想。
一、地域·人缘·文化
先从“江湖”说起。从词源意义讲,“江湖”本指三江五湖,后泛指江河湖海、四方各地。“江湖”最早出现于《庄子·大宗师》:“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5]指各自生活的一方天地。春秋时期范蠡携西施“乘扁舟浮于江湖”,江湖成为自由空间的表征。及至北宋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中,江湖便带有了政治隐喻色彩,蕴含民间与权力中心的对立。再至《水浒传》中,江湖有了秩序和规则,增添了批判精神和反权威色彩。到《笑傲江湖》中的“恩怨江湖”又有了人情世故的人缘联系。而在香港的黑道电影中,江湖又有了新的含义,成为“游民社会”(王学泰),是社会黑暗力量的汇集地。“江湖”一词在不断发展中,意义越来越丰富多元。贾樟柯的“江湖”既有传统江湖含义,延续边缘身份和情义的表达;也有现代江湖的承袭。关于现代江湖的传承,其来源较为多元,如秉承现实主义对个体生存的关注,侯孝贤和小津安二郎表现日常生活的美学传统,山西地域文化的耳濡目染等。贾樟柯的“江湖”是地域、文化、人缘多重视域交织下的空间概念,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
首先,江湖是地理空间。地理概念的江湖是与山西相对的外界,闯江湖就是去故乡以外的地域。小武从村庄走向县城,沈红从山西走到重庆,张晋生从上海去往澳大利亚,外出寻找、漂泊谋生、对大城市的憧憬等驱使他们在地域江湖中漂泊闯荡。《江湖儿女》赋予了地域江湖更深刻的意义:在他乡中审视故乡,在游走中发现自我,寻找存在的诗意和自我的价值。贾樟柯的电影人物在地域江湖游走、闯荡,“江湖”既是他乡亦是故乡,是梦想和远方亦是回忆和乡愁,以上均是电影叙事的地域依托。
地域江湖还是与中心相对的边缘,与权力相对的民间,它“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感世界”[6]271。表述民间是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的山西传统,贾樟柯因袭了山西文化的表现传统,并结合自身经历,塑造了农民工小山,县城小偷小武,流浪艺人,矿工韩三明,混迹社会的斌斌、阿飞、小济等一系列边缘人物。同时,贾樟柯的民间呈现还具有批判和反抗意味。不仅是对同代之间的个体批判,还有代际之中横冲直撞的反抗。《站台》中崔明亮穿着广州时新的裤子嘲笑他的母亲不懂潮流;《任逍遥》中小济对父亲的行为不屑一顾;《江湖儿女》中曾经风光的江湖大哥被街头青年小混混群殴:这些象征着新一代的崛起和老一代的末路,代际冲突在暴力中深化,曾经意气风发而今壮士暮年,其中也蕴含了江湖反思的黑色幽默,体察了边缘小人物的命运莫测及社会更替中的浮沉变幻。值得一提的是,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不同,贾樟柯表现的民间存在于现代都市中,“在现代都市中,与国家权力中心相对应的是个人”[6]306。因此,贾樟柯在地缘江湖上构建了人缘江湖,在关心底层人群的基础上进而关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联系。
其次,江湖是社会空间,是各种关系的总和。人缘江湖的建立和生成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交织。情感的联系是必然性发生的基础,“情”和“义”是人缘关系的联结纽带,“义”多体现于兄弟之中,“情”包括亲情、友情和爱情等,其中爱情存在于两性之间。贾樟柯的江湖之“义”从小武开始,且在《江湖儿女》中最为丰富,从单向显现转为辩证思考。这具体体现为电影中关于“关二爷”含义的转变——从“义”的化身转为“财”的象征。《江湖儿女》中,老贾在关二爷面前因为“义”的信仰说出了实话,也在关二爷面前奚落晚年的斌哥,“你又不能带兄弟发家致富,算什么大哥”。“义”的联系变成了“财”的联系,反观电影前半部分国标舞演员在昔日大哥葬礼上的舞蹈也像极了一曲江湖义气的挽歌。“财”不仅使“义”丧失,也使爱情不再纯粹,《小武》中梅梅结识了大款便抛弃了小武,《山河故人》中涛儿选择和开小汽车的张晋生结婚而非一无所有的梁子。可见,人缘江湖的联系是变幻莫测的。也有坚守着江湖情义的,如巧巧对待斌斌从“情”而生“义”。总之,“情”“义”“财”的交织联系是复杂多变的,因此也造就了人缘江湖的复杂性。必然性之外的偶然性联系,加深了人缘江湖的多重性和深刻性。在偶然的关联中丰富个体自身的经历,与他人和世界的不期而遇也为个体经验和生命历程提供了丰富的可能。其中或许险恶艰难,善恶难分:饭前要祷告的同船女子却是小偷,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酒店客人却背叛家庭婚外偷情。无论如何,“让一个人置身变幻无穷的环境中,让他与数不尽或远或近的人物错身而过,让他与整个世界发生关系”,是贾樟柯人缘江湖的表现,“也是电影的意义”[7]。
动荡多变的人缘江湖和漂泊游移的地域江湖都不具有稳定性,而文化江湖是相对稳定的存在。如果仅从地域和人缘看,贾樟柯的“江湖”过于浅表,在地域和人缘背后的山西情怀和故乡认同才是贾樟柯的精神来源,贾樟柯的江湖也在故乡文化的浸染中更加鲜活和独特。
江湖也是一个文化空间。文化江湖在贾樟柯这里是山西根基与故乡情怀。“故里”是贾樟柯电影创作中“最根本的”观念,也是贾樟柯影片的“母题”。[8]山西、山西人是贾樟柯电影创作的对象,而山西文化内化在贾樟柯电影中的多个方面,从语言、服饰、习俗到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此外,山西方言是贾樟柯对故乡最深切的情感认同。这些都是贾樟柯确立自身电影特色的方式,也使贾樟柯的电影质朴而踏实,这种踏实源于对故乡的归属感。人之于故乡的归属感是与生俱来的,“出生地和居住地很大程度上对应着个人的归属感”[9],这种归属感从深层讲属于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产生在“共同的起源或共享的特点的认知基础之上”[10],是个人身份的唯一认同。基于这样的根基性情感和文化背景,再实实在在地去感受中国人的生存处境和变化,电影中内蕴的感情和思考才最为真切。
总之,贾樟柯的江湖离不开地域、文化和人缘,这也是他构建电影“江湖”的基础。以此表现小人物的江湖、山西的江湖、中国社会的江湖;多重性与复杂性也在地域、文化、人缘的交织游移间徐徐展露。
二、时与空:“江湖”变更
贾樟柯的江湖是在时空变更中呈现的。变化是贾樟柯思考世界的方式和途径,在时空变化中发现日常生活的哲理和历史的诗意,时空变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复杂性”[8]。
时空变更浸透着日常生活的哲理和历史的诗意,贾樟柯的影片蕴含着“理性思考”和“富于哲理性的诗意”[11]。他擅长在电影中通过光影的自然流动和长镜头的记录展现时间的变化,日常生活的哲思在明与暗、静与动、偶然和瞬间中显得韵味深长。巧巧站在江边看向远方时,时间在光影明暗的交替中变化,时间的自然流动让空间变得寂静沉默,伴随着欢快明朗的乐曲戛然而止,动静、明暗之间形成空间的留白,人物置身于沉默之中,这种沉默是“意识到自己在大时代中的无足轻重与无能为力,把一种茫然若失的心理哲理化,变成无可奈何的宿命感”[12],以及悲凉感和无助感。而自然界由黑夜到白天的转变同时也蕴含着黑暗总会过去光明总会到来的朴素哲理。生活化的场景常若有似无地暗含着对生命的思考,意味深长。
贾樟柯的电影始终蕴含着历史的诗意,在艺术的陈列和重复中展现。贾樟柯将许多复杂的东西并置于同一时空中,“不做深层评述、不做来龙去脉的交代”,“然后在种种影响起起落落之间呈现出现实的质感和纹理”,让我们从中“感到电影本身的能力和深邃”[8]。起起落落之间是人生境遇的无常感、个人内心深处的孤独感、背井离乡的漂泊感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的诗意。《江湖儿女》将贾樟柯的电影过往放在了同一空间中呈现,有意强调在同样的地域上不同人的不同选择和相同命运,电影与《站台》有同样的场景,人物“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却“同是天涯沦落人”。巧巧远赴奉节寻找斌斌,像多年前去找丈夫的沈红,贾樟柯以艺术的重复展现生活本就如此。空间场景在《江湖儿女》中多次再现,同样的街角,年少的斌斌和巧巧开着豪车在这里打架,中年的斌斌和巧巧落寞地坐着破旧的三轮车从这里经过,而“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历史的诗意也在个人与时代的浮沉中显得韵味深厚。
时空变更的过程是人发现自我的过程,人物在地域、人缘、文化江湖之间交织游移并发现认同。巧巧从山西到重庆再回山西,经历街头争霸、情人变心和上当受骗,在出走—寻找—回归的模式中成长、发现和确立自我。确立自我的过程是曲折的,其一是他者与自我的凝望与审视。巧巧去重庆是为了找回曾经的爱情,“但到头来,找到的东西也在变质”,斌斌变心了,“找到”本身就成了自我否定,或者说,“找”就是自我否定的方式。[13]594在他乡的游走与审视也是巧巧凝视外界和发现自我的过程,在否定中确立自我。巧巧在遇骗与行骗的经历中看清了自己仍然是为爱义无反顾、勇敢和有情有义的人,转而回到故乡。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找到自我,不少影评都说斌斌是个负心汉、失败者,贾樟柯却坚持说:“廖凡演的不是一个失败者,而是一个迷失者。”[14]的确,斌斌是一个迷失者,在对金钱和成功的渴望中迷失了江湖信仰、情义和初心。《江湖儿女》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巧巧在演唱会上将歌词“是否还有勇气去爱”改唱为“是否还愿意去爱”,这也预示着巧巧心里的情义永不会变,凝望审视的过程让她更加坚定与无畏。
其二是身份认同的游移和转换。从饰物到语言的内外变化可以窥见巧巧自我身份定位的转变与认同。从外在的饰物说,“衣着和饰物是将身体社会化并赋予其意义与身份的一种手段”[15],饰品是身份的标记和象征,巧巧的饰品随着电影的叙述一直在变化。影片开头巧巧手上的戒指与结尾相互呼应。监狱中的巧巧身上没有任何饰物,巧巧失去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身份。在三峡的游轮上,巧巧腕上的手表是对监狱经历与底层身份的掩饰,正好巧巧去奉节要见香港毕业的大学生,因此手表有了伪装知识分子的意味。在去武汉的火车上,巧巧的饰品变成了玉,玉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对应巧巧在奉节通过敲诈获得的一笔横财。影片最后饰物又变回戒指,可能它只是一个廉价的装饰,但却象征着故我与故乡,玉和戒指对应外面的繁华世界和朴实故乡,玉到戒指的转变也隐含着对故我及故乡的认同。从语言来说,一方面,语言是观念的表现。巧巧反复追问斌斌“我到底是不是你女朋友”以及对“我是江湖人”的重复强调,暗含着巧巧对身份的重视。另一方面,语言是身份的内在表征。巧巧的语言经历了山西方言、普通话、重庆方言再到山西方言的转变。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最终认识到山西才是她真正意义上的江湖,而这个江湖也正是文化视域下的江湖。
贾樟柯的电影创作历程同样是他凝视自己的过程。戴锦华曾经指出第六代导演的致命伤在于“尚无法在创痛中呈现尽洗矫揉造作的青春痛楚,尚无法扼制一种深切的青春自怜”[16]。的确,小武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少年,“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湿的泪,我的天空为何总是灰着脸”的故作忧伤,是对自由的向往和青春的叛逆,环绕着“现实的焦灼”。[17]26《站台》是困惑和迷茫的,也是温暖和期待的,站台“是起点也是终点,我们总是不断地期待、寻找,迈向一个什么地方”[17]73,外面的世界是美好的,未来也如此。《三峡好人》中的整体情感是失落和失望的,环绕着这个时代中“好人”的悲凉与天助。《任逍遥》展现的是穷途末路的困境,“狂欢是因为彻底的绝望”,“暴力是他们最后的浪漫”[17]113,在绝望中走向无谓的挣扎与反抗。贾樟柯拍完《天注定》后戏谑地说自己的电影连起来是一部《悲惨世界》,并意识到“如果困难变成了景观,讲述误以为诉苦,我应当停下来,离自己和作品远些”[17]162。《山河故人》变成反抗后的凝望和自救,指向了家和故乡,《江湖儿女》是对故乡和情义的确立与认同。故乡的意义也在贾樟柯电影创作中逐渐深入,在小武眼中,故乡是“经历变革的内陆小城”,汾阳是“中国所有待发展、待开放的城市的缩影”[2]204;《山河故人》中汾阳代表着“深刻的乡愁”[2]205;《江湖儿女》中故乡山西是文化的确认和身份的认同。
从少年心性到中年情怀,贾樟柯的创作之路是一条逐渐深入且日渐开阔的思考之路,从焦灼犹豫、面对现实再到冷静凝视。《江湖儿女》正是他年少时的梦沉淀后的审视。少年时也许拍不出江湖,拍不好江湖,总是充斥着拉帮结派、寻仇、报恩的年少热血。如今再看《江湖儿女》,已不是少年江湖的味道。“少年时代不畏天命的勇气丧失殆尽,不由自主地萌生一种宿命的感觉。”[18]这种宿命感源于历史沉淀后对生命与存在的深刻思考,如《江湖儿女》的开头和结尾,影片开头公交车上黄色衣服的小女孩睁开眼睛向上看;影片的结尾,巧巧靠着墙壁低头往下看。从对世界的好奇到对生命的沉思,正是每个人半生的缩影。
时空变化中,“江湖”更迭。时代和社会日新月异,人际关系变幻莫测,然而“伴随着这个变化的主题或不确定性的主题的,就是对于不变或确定性的追寻”[13]594。《江湖儿女》的英文片名是“Ash Is Purest White”,意为“灰烬是最纯的白色”,“纯”可以说是江湖精神,也可以说是贾樟柯的电影理想。时空的变化不可避免,可总有些东西不变,这种“不变”是时空和历史沧桑中精神的底蕴,是贾樟柯的江湖精神和美学理想。
三、江湖精神与存在美学
对贾樟柯的评价除了积极的肯定,一直以来存在着一种批判的声音,认为他将中国边缘化、苦难化、符号化以献媚于欧美,具有文化殖民的色彩;并且只呈现中国边缘苦难景观,缺乏思想深度的内蕴,只有力度而无深度。其实不然,贾樟柯电影是有精神内蕴的,江湖精神就是他的电影精神和美学理想,江湖情怀本身就有“中国风”的韵味,而贾樟柯努力呈现一个不断变化的当代江湖,致力于联系传统与当代,依托传统文化与山西底蕴,并随时代的变迁不断增添新的要义,这使得他的“江湖”始终鲜活。出于对中国、对中国现实的专注,对传统与山西的认同,对当代性的追求,贾樟柯的江湖精神体现在“情义”、东方品格和人道主义关怀三个方面。
“情义”是江湖精神的底色,“情”是基础,“义”是承诺和责任。贾樟柯的“情”和“义”是分而论之的,“义”是“情”沉淀后的升华,且在亲情和爱情之外,还有对友情的感悟。贾樟柯的情义传统来源于山西文化的熏陶,源于山西关公文化精神。事实上,关羽文化中还有“忠”,“忠”暗含在对情义的坚守和信仰中,关羽精神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财”相联,但贾樟柯仍不放弃对最初含义的坚持。情义不仅是传统的承袭,也关乎时代的需要,“基于民间出身的底层经验,情义传统一直是贾樟柯接受物质现代的前提和对应体制现代的基础”[19]。情义变成了一种信仰,以精神信仰对抗现代化的创伤。
东方品格首先是农耕文明下乡土中国的价值伦理的承袭。山西“在近现代是属于疆域变化较少、受近代文明冲击较轻、社会变化也较缓慢的省份之一”[20],地理环境的特殊使山西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乡土中国的风貌和传统价值伦理。“记得‘奶妈’一直对我说:为人要讲义气,待人要厚道,对父母要孝顺,遇事要勇敢。”[17]47勤劳勇敢正义善良的传统价值伦理是东方品格的第一重含义。贾樟柯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像《甲申文化宣言》的东方品格那样“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那种人格是完美的东方品格,不能涵盖所有现实大众的模样。贾樟柯是写实的,他以现实技法表现真切的人和生活,所以他笔下的中国形象是真实鲜活的,也许爱占小便宜有点懦弱、有点自私,但他们同样热爱生活且富有生命力,这正是东方品格的第二重含义,是在苦难生活中的生存美学。当电影导演维尔纳·斯洛德问及福柯的生活方式时,福柯用四个字概括“足智多谋”。[21]345这也正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存技巧。也许从道德层面讲,巧巧在他乡的偷盗是非合法、非道德的,但这却是小人物的生存智慧,“不断地在压抑和灵活应变中‘继续活着’”。在苦难中努力活着是对生命的热爱,渗透着“乐观的”“行动的哲学”。[22]31贾樟柯电影中的集体景象都是闹的、笑的、嘈杂的、淳朴的,人们操着山西方言一起看戏、拉家常,这就是东方生命力。东方品格的第三重含义是当代精神的融入,是独立而自由的当代品格,体现在贾樟柯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所以在影片中贾樟柯让梅梅“走了”,钟萍“走了”,却让小玉和巧巧留下来了。尤其是巧巧,她的成长历程是东方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缩影,她在维护斌哥时的魄力和勇敢,在面对危难时的从容和胆识,都是传统美德与当代精神结合后的当代女性品格。
对情义的坚守和对完美东方品格的认同,使他的创作始终蕴含着人道主义精神。贾樟柯的人道主义关怀首先是对自我存在的认知,“他是自己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他愿意成为的那样”[22]8。贾樟柯电影中的主角都是为自己而活的小人物,追求时髦或追逐财富,浑浑噩噩或拼搏奋斗,都是对自我主体性的张扬。贾樟柯的电影没有英雄,每个小人物都可以成为英雄,这是对第五代电影导演的英雄主义的消解,也是第六代导演对个体自我存在的集体关注。其次是文化尊严,一方面是贾樟柯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尊严,这是他人道主义关怀的主要来源,也是他艺术创作的精神支撑。对知识分子职责的坚守,让他始终不放弃对个体生命的思考。另一方面是贾樟柯塑造的小人物的文化尊严,贾樟柯曾经说:“我觉得我在奶妈身上看到了比那种所谓的知识分子身上更多的文化的尊严。”[17]47这是个体生存的尊严,也是一种“对待自身、对待他人以及对待世界的态度”[21]403。贾樟柯的电影不是解构的,而是重塑的,在变迁的时代和社会中,“建立一个价值模式的人的王国”[22]21。不是理想的而是真实的,寓普遍性于特殊性之中,“你除掉你的生活之外,更无别的”[22]19,正如西西弗斯不断地将石头推向高处,在反复中不断斗争,迈向高处的挣扎足够填充一个人的心灵,人们应当想象西西弗斯是快乐的。人类一代又一代的繁衍斗争,在反复中走向永恒,这便是存在的意义,贾樟柯的电影中始终存在着这种乐观的生存美学。而“在电影虚拟的时空中我们可以看见别人的生活、命运。从电影中我们可以寻找另一种人生,另一种更可能,得到某种解答”[23],这也是贾樟柯对观众的关怀。
总的来说,《江湖儿女》是贾樟柯对旧梦的重拾,对往昔创作的回顾,亦是对自我的总结与超越。“江湖”是能潜到贾樟柯创作深处的途径,也是贾樟柯观察世界的方式,更是贾樟柯对中国电影构建自身特色当代模式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