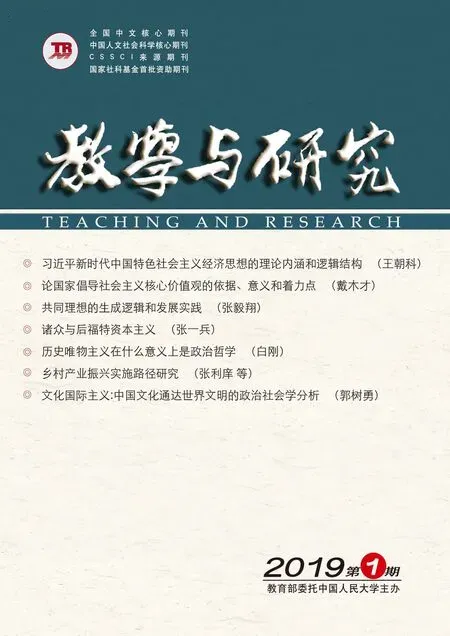中国百年哲学通识教育的回顾与评析
——以哲学概论类教材为例
,
现代社会日益精细化的分工和与此互为表征的学术专业细化、窄化与锁闭,使得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成为紧要的事情。201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并首次提出在高等教育阶段实行“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鉴于哲学在人类精神文化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哲学通识教育在整个通识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甚至核心作用。哲学通识教育有“内通”与“外通”之分,所谓“内通”是指哲学内部不同哲学传统、分支、门类之间的“通”;所谓“外通”是指非哲学专业的不同学科之间的“通”。21世纪以来,国内大多数高校逐渐将哲学通识教育作为人文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入门、哲学导论、哲学概论、哲学通论等课程不断涌现,往往成为热门课程。事实上,中国哲学通识教育断断续续走过了一百多年历史,通过对相关教材(本文统称为哲学概论类教材)的梳理与分析,回顾我国哲学通识教育的曲折历史,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哲学通识教育的发展和完善。
一、1949年前:西学东渐背景下的发生
哲学(philosophy)作为现世的智慧,是各民族所固有的,是各民族、文明活的灵魂,但是作为一门严格的学问,则产生于西方,于中国而言是地道的舶来品。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一本《天主实义》将西方哲学带入中国,影响了黄宗羲、戴震等明清思想家。同时,利玛窦还将中国文化典籍译介到西方,力图将中国传统儒家哲学思想同西方哲学思想相融合,可谓首开西学东渐、打通东西哲学的先河。直到鸦片战争,诸多传教士和中国学者的类似努力都进展甚少,影响甚微。鸦片战争之后,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包括哲学)逐渐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寻救国自强之路的重要途径。诚如容闳所说:“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注]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62页。一时间形成译介西学(包括哲学)的热潮。甲午战败之后,日本学者所译的西洋著作更为国人重视。1896年,由日本学者西周翻译的“哲学”一说正式通过黄遵宪引入中国。然而,由张之洞等主持的开启中国现代教育的《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1904年颁布),贯彻“端正趋向、造就通才”的宗旨,因袭西方学制却在科目设置上删去了哲学一科。曾为张之洞幕僚的王国维揣测,张之洞这么做的理由有三:“必以哲学为有害之学”“必以哲学为无用之学”“必以外国之哲学与中国古来之学术不相容”。同时,王国维也分析到,“此恐独尚书一人之意见为然,吾国士大夫之大半,当无不怀此疑虑者也。”[注]《王国维文集》,下部,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38-40页。可见,哲学进入中国教育体系殊为不易。
蔡元培1923年写下《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认为此前“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可分为西洋哲学的介绍和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注]《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51页。甲午战争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通过学习日本而学习西方哲学时,由应用而学理,往往以中国古书予以印证,这事实上开启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整理,而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可谓肇始,1919年由胡适完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著作。1914年,北京大学设“中国哲学门”(北大哲学系前身),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或专业终于置身于中国大学体系之中,也标志着中国拥有了职业的哲学研究人员。1915年,北京大学哲学门下设印度哲学。于是,无论是译介域外哲学,还是对中国哲学自身的反思性建构,基本形成了关于三大哲学传统即西方哲学传统、中国哲学传统、印度哲学传统的研究格局。这些都为民国时期的哲学通识教育奠定了基础。
根据北京图书馆1991年编纂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哲学·心理学卷)显示,民国38年间,出版各类哲学书籍3 085部,哲学总论性质的有214部,其中“哲学概论”类就有47本。[注]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哲学·心理学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最早的一本是1903年由蔡元培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哲学要领》,其实是根据日本下田次郎以日文笔述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德国学者科培尔(Kobell)讲稿译成,其时尚在清代。1914年,出现了3本师范学校使用的哲学概论教材,一是谢无量(署名“谢蒙”)编写,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制)《哲学大要》;一是夏锡祺编写,由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出版的《新哲学》;再有是侯书勋编写,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哲学发凡》。其中,谢无量的《哲学大要》最早(1914年5月),堪称中国最早的自编哲学概论类教科书;而且,他还同时配套推出了(新制)《哲学大要参考书》,根据《哲学大要》一书的各章次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可见,当时哲学教育甫一登场,就考虑得十分周到。就目前可考,1949年以前最后一本哲学概论类书籍是1948年3月由北京明德学园出版、常守义著的《哲学概论》。
通观1949年前的哲学概论类著作,既有以大众为对象的普及类哲学书籍,如1929年张东荪于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哲学ABC》、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哲学阶梯》(刘强编),都是尽量以初浅语言简论、泛论哲学;又有教材或教材、学术著作兼顾的著述。总体上,后者是主流。我们可以从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来了解这些著述。
从形式看,1949年以前的哲学概论类著作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直接译介西方学者的著作,这既是最早的形式,也是一直贯穿于民国时期的形式。除上述最早蔡元培译德国科培尔著、日本下田次郎述的《哲学要领》外,日本稻毛诅风的《哲学入门》、日本纪平正美的《哲学概论》、英国拉波普特(A.S.Rappoprt)的《哲学初桄》、美国布赖特曼(E.S.Brightman)的《哲学导论》、日本金子马治的《哲学概论》、日本松本悟郎的《哲学问答》、美国霍金(W.Hooking)的《哲学大纲》、美国杜伦(W.Durant)的《哲学概论》、法国克勒梭(A.Cresson)的《哲学系统》、英国罗素(B.Russell)的《哲学大纲》、日本佐藤庆二的《哲学新讲》、美国塞尔萨谟(H.Selsam)的《简明新哲学教程》相继出版,晚至1946年。在这其中,以译介日本学者著作或讲义最多,可见日本对我国早期哲学及其教育的深刻影响。
二是以西方某部或多部著作,甚至是某个哲学家的观点为主体,进行改装编著。除翻译《哲学要领》外,蔡元培还分别于1915年、1924年编著了《哲学大纲》和《简易哲学纲要》。他明确指认,前者是“以德意志哲学家厉希脱尔氏之《哲学导言》”为本,而兼采包尔生、冯德之《哲学入门》;[注]《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45页。后者(被列为现代师范教科书)则“多取材于德国文得而班(今译文德尔班——引者注)的《哲学入门》”。[注]《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90页。刘以钟1920年所著《哲学概论》被作序者指出是“以德儒帕尔生之哲学为本而参以己意立论”。[注]刘以钟:《哲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序言。罗鸿诏在1934年出版的《哲学导论》“自序”中,坦承自己的材料来源于日本桑木巌翼讲义和德国文德班《哲学导论》;[注]罗鸿诏:《哲学导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自序第1页。邹谦则认为康德为哲学划出了新时代,康德之后“无能超出其思想之范围者”,所以他1935年出版的《哲学概论》“即汲其(即康德——引者注)思想之末流,为一贯之中心者也。”[注]邹谦:《哲学概论》,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自序第2页。
三就是按照自己的研究、理解进行撰写或编著。这直接反映了中国学人在消化、吸收西方哲学后的一种综合性重述和自我理解,真正代表着当时中国人自己有关哲学总体理解的水平。
从内容看,就中国学人自己编撰的著作与教材而言,渐次呈现出三个重要特点:
首先是偏重于介绍西方哲学。谢无量在(新制)《哲学大要》中介绍了哲学(其实是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及各种派别,分知之哲学、实在体哲学两编;陈大齐在1918年《哲学概论》中分形而上学、认识论对西方哲学知识进行介绍;范锜在《哲学概论》课程教本中更加系统地展现了西方哲学,从哲学概念的解释到哲学研究的方法,再到西方哲学中典型问题——认识论、实在论;而在邹谦的《哲学概论》中,中国学者已经能够全方位介绍西方哲学,在实在论、认识论、价值论三大方面展现西方哲学的独特魅力,并从时间维度介绍西方哲学的变迁,从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再到近代哲学及德国哲学,达到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
其次是就打通中西甚至是中西印哲学作了很好的探索。中国学者在译介、编著西方哲学思想时,逐渐注意到本土性的回应,尤其是在反思性建构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汇通中西哲学成为一种自觉不自觉的追求。蔡元培认为,美国哲学家杜威1920年在北京大学演讲中提出了媒合东西文化的问题,把这个问题明确提了出来。他本人在编著《简易哲学纲要》时,并非完全照搬文德尔班的《哲学入门》,而是时时用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进行印证。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是这方面最早的系统性努力,尤其是将其他著作很少涉及的印度哲学含摄其中,一体论述,堪称经典。周辅成的《哲学概论》将哲学史上各派的意见融合在内,特别将中国哲学也置入其中。1947年李相显著《哲学概论》时,学界对中西方哲学的介绍已然接近成熟,概述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发展历史,在论述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人的同时,也并未遗忘中国的孟子、墨子、庄子与朱子,而且专门讨论了“中西哲学的会通”。唐嗣尧为之作序时说,该书首要特点就是“中西合也”。“旧日之著哲学概论者,类多编译西洋之书,而不知中国亦应有哲学概论也,更不知中西可以合而为一也。”更认为“世界综合之哲学概论可得而成立矣。”[注]李相显:《哲学概论》,世界科学社,1947年,序言第1页。
再次是不少概论类书籍已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其中。自1899年上海《万国公报》首现对马克思进行介绍,包括哲学在内的马克思思想在中国逐渐成为重要热点。早期主要是经由日本的译介,十月革命后,更多来自苏俄。1918年,李大钊开始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讲授“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式进入中国教育体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著名的通俗读物和教材。一些哲学概论类教材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重要内容。例如,范寿康的《哲学通论》中专门设立章节介绍费尔巴哈哲学、辩证的唯物论等内容;吴大琨的《新哲学概论》中更加不吝惜笔墨,介绍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的唯物辩证法,辩证法唯物论的斗争,关于自然以及人类智慧的辩证法,关于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在大多数著作的序言中,都表达了这类书籍之必要性,大抵强调两方面:
一是突出哲学的特性,强调需要总括、简易的导引。范錡指出,哲学“范围之广,探究之宏,实为各科冠;加以见解悬殊,持论互异,益使学者罔知所从。”“愿编述哲理者,每滞于义,而艰于辞,或译笔过泥,或撮义不精,辄使读者搔首攒眉莫解其所以;即以哲学概论言,不失诸过约,即失诸太繁,欲求一明简而易晓者,良不可多得。”[注]范錡:《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序言第1页。罗鸿诏在《自序》中写到:“哲学之书,专论易而通论难。专则其范围狭,而论究易精;通则其问题多,而体要难问。今导论之为书也,于现代哲学上各种问题,皆不能不加论列,而尤须有一贯之思想为其中心,然后能折中众说,归于一是。”[注]⑤ 罗鸿诏:《哲学导论》,自序第1、3页。
二是基于中国当时对哲学理解的现实,强调要正本清源。作为第一本哲学概论性质著作《哲学大要》的译者,蔡元培这样告诉我们他因何为之:“初学者不得正宗之说以导之,将言惟物而诋纯正哲学之蹈空,言惟心而嗤物质文明之为幻,言有神而遂局古代宗教之范围,言无神而又以一切家政为仇敌。门径既误,成见自封,知之进步,于焉窒矣。”[注]《蔡元培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176页。生动说明了当时国人对哲学的理解之误,表明进行哲学通识教育之必要。面对当时有人食洋不化,试图“原汁原味”、照搬照抄的现象,罗鸿诏则明确强调要尊重教育规律和中国学子实际:“学问之道必由迩以至远,由浅以及深,不可飞跃而躐等也。今日中国之学子能知哲学问题之所在者尚鲜”。⑤
总体上看,1949年前哲学通识教育是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伴随着中国现代教育的兴起,哲学传入中国以及哲学教育在中国的兴起而进行的。由译介西方教材到以西方哲学教材或某一哲学思想为主进行编著,再到中国哲学学者的独立著述;从完全以西方哲学为内容,到以中国哲学进行引证,再到中西哲学乃至中西印、中西马开始汇通。整个过程显得自然而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逐渐走向成熟,也使得哲学概论的“概”逐渐具有了中国情境的独特意味。那就是,不仅只是对哲学内容(主要是西方式划定)的概论,而且还指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乃至印度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上的概论。这对当年青年学子扩展视野、提高思维水平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二、1949年后: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再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照搬了前苏联的专业教育模式,由于历史原因,哲学在知识思想中的地位一度达到极高的位置,不时兴起人人争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但当时自上而下理解的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是源自前苏联《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的“钦定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居于国家哲学地位,事实上长期充当了哲学原理、一般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就充当了哲学概论类的教材。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甚至一度仅仅被作为批判的对象、材料加以介绍。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直接地是一场哲学大讨论,事实上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正是在改革开放中,人们开始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及其整个哲学教育进行反思。也正是在这种反思和关于哲学教育改革的探索中,从1949年开始断裂的哲学通识教育及哲学概论类的教材、课程在中国重新发生。
1994年底,当时的国家教委决定并批准在一些高校设立“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并组织编写了全国“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这些改革举措对哲学通识教育的再发生起到了很好的催化作用。可以说,哲学通识教育的再发生是改革开放的结果,直接地是哲学教育改革的结果。发展至今,大陆学者已出版30多部“哲学入门”“哲学导论”“哲学概论”“哲学通论”等著作或教材,几乎所有重要的大学都开设了类似的课程。
这个“再发生”的过程总体上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可以称为拓荒和奠基阶段。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由建国以来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初的哲学热逐渐消退,而现代化建设又急需具有哲学素质的人才。基于这样的判断不少哲学工作者认识到哲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并展开了自己的探索。1993年童世骏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开设“哲学概论”课,这是1949年后国内最早开设的哲学概论类课程。1994年底,孙正聿在吉林大学哲学系开设“哲学通论”课,1995年他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如何建设具有当代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哲学教育改革,必然呼唤“哲学通论”的出场。同时,他指出,开设“哲学通论”更大的期待在于“使之逐步地成为高等学校各专业的重要的人文教养课”。[注]孙正聿:《关于开设“哲学通论”课的思考》,《光明日报》1995年9月21日。1996年,王德峰在复旦大学开设“哲学导论”课程。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世纪之交也开始开设“哲学导论”课,最初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青年教师负责,后由张世英、叶秀山、余敦康等名家主讲。这些开拓者的讲义大多陆续得以出版,成为标志性的教材。例如张天飞、童世骏主编的《哲学导论》(1997)、孙正聿的《哲学通论》(1998)、王德峰的《哲学导论》(2000)、张世英的《哲学导论》(2002)、叶秀山的《哲学要义》(2006)和余敦康的《哲学导论讲记》(2018)。[注]余敦康的北大讲义早有网络版流行,2018年1月方正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其中,张天飞、童世骏主编的《哲学概论》是多人集体编写,但正如其封底所示,是“建国后国内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论析哲学本身而非某一种哲学的著作”;[注]张天飞、童世骏主编:《哲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孙正聿所著50万字的《哲学通论》则是1949年后我国学者第一部哲学概论类的专著性教材,而且孙正聿对哲学通识教育用功最专、最持续,影响也最大,还出版有《哲学导论》(2000)和《简明哲学通论》(2000)等书。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阶段的学者较少参考国外和国内1949年以前的哲学概论类资料,彼此之间也基本没有沟通,属于各自探索、很少借鉴的阶段。从无到有的开拓可谓筚路蓝缕,但十年左右就已奠定了当今中国哲学概论的基本范式,使之成为哲学教育及其通识教育的最基础内容。张法曾评论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哲学的一个重大的标志,就是哲学原理的出现。”[注]张法:《从四本哲学原理著作看中国当代哲学原理的演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第二个阶段是指最近十来年。在这个阶段,一方面,众多高校的哲学专业都陆续开设了哲学概论的课程,即所谓进行了哲学通识教育的“内通”;另一方面,很多高校已经在全校设立跨院系、专业的哲学通识公共选修课。随着哲学通识教育成为共识,哲学通识课教师、教材的需要量也大幅增加,这不仅从供给侧的角度提出了更多的需求,而且促使更多的高校教师、哲学工作者研究这类课程,编著自己的讲义、教材。于是,几乎所有国内知名大学都有自己的教材,可以说是逐渐实现了一校一本——有些学校甚至出现好几本。从教材来看,这是一个有所参照、个性理解、百花齐放的阶段。所谓有所参照,既指有了第一个阶段的拓荒和奠基因而可以吸收借鉴,还指一批西方和港台的哲学概论类书籍乃至1949年前的相关书籍的挖掘整理、相继出版而可资借鉴;所谓个性理解,既指每位学者基于自己的学养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内容体系,还指更加注重结合当代大学生的新情况甚至是不同类型学校的大学生情况采取更加差异化的形式。到目前为止,这个阶段有代表性的个人专著类教材主要有庞学铨的《哲学导论》(2005)、沈湘平的《哲学导论》(2008)、杨国荣的《哲学引论》(2015)、潘德荣的《哲学导论》(2016)等;集体编著有代表性的教材有李德顺主编的《哲学概论》(2010)、阎孟伟主编的《哲学概论》(2014)和程广云主编的《哲学导论》(2018)。
早期的哲学概论类课程与教材具有强烈的针对性,那就是针对传统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般哲学原理的做法,所谓哲学教育改革其实就是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改革。张天飞、童世骏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担负了‘哲学概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的双重任务”,从学科分类上看显然是不科学的,“《哲学概论》所论述的是哲学一般,这一般涉及古今中外各种哲学及其分支学科,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它是“学习哲学的一门先行入门课程”。[注]张天飞、童世骏主编:《哲学概论》,序言第5、6页。高清海在为孙正聿《哲学通论》作的序中认为,怎样看待哲学,哲学究竟属于怎样一种学问?这是哲学观,研究各种哲学观的理论可以叫做“哲学学”,而“哲学通论”从其实质内容来说,也就是承担了“哲学学”的任务。孙正聿进一步指出,这些问题原来只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绪论”中被简单提及;“哲学通论”的开设,“不仅可以讲述哲学原理的‘绪论’部分,从而使哲学原理课可集中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本身,而且还可以促使哲学原理课以学生已有的哲学背景为前提,在全部的课程内容中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革命变革,集中地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新问题,从而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所具有的理论说服力。”[注]孙正聿:《关于开设“哲学通论”课的思考》,《光明日报》1995年9月21日。一句话,这类课程其实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的。事实上,孙正聿明确指出自己的《哲学通论》是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特别注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来提出和回答问题”,“是建国以来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所撰写的《哲学通论》”。[注]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89页。这也使得孙正聿的《哲学通论》等书成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撰写教材的典型代表和成就最高者。
从事哲学概论类课程教授、教材编写的学者,除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背景外,更多的是西方哲学背景的学者,也为其理解的一般哲学打上深深烙印。王德峰的《哲学导论》首开先河,在内容上偏重西方哲学传统,除了介绍哲学的一般规定和哲学的诞生外,其余篇幅就是哲学的问题域:本体论、形而上学、认识论、先验哲学和历史哲学,虽偶有论及中国哲学,但总体上是西方哲学,可谓典型的西方“哲学导论”。正如王德峰自己认为的,“东西方哲学的对话和会通,是当代哲学的最大任务……多元的智慧,比单一的智慧要好。中西哲学的会通,不是中西哲学的同一化,而是异中见同,同中见异,以求互相启发。哲学的生命本来就在对话的辩证法中……但说老实话,这在目前只是良好的愿望而已。中国学人自20世纪初以来大抵是以西方哲学的学术规范、标准和框架来分析、描述和理解中国哲学的。”“中国思想史早已证明仅在自身传统内部是开不出新路来的。”因此,“照西方哲学的基本原貌来介绍哲学,是目前所能取的最恰当的方法。”[注]王德峰:《哲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6、67、68、前言6页。叶秀山《哲学要义》源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讲授“哲学导论”讲义,全书没有一个注释,简略、深刻而通达。不过,正如叶秀山自己所坦诚的,这是“以论带史”的、以西方哲学专业为背景的“导论”。[注]叶秀山:《哲学要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前言第1页。
更多的学者试图不囿于某一国别、派别、部门的哲学,以尽量公正的态度面对和探究人类的哲学智慧,即被讥讽为所谓“打通中西马”的努力。事实上,这方面公认的力作还没有出现。但在打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方面已经有了高水平著作。张世英对接、统揽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从真善美等多个角度阐述万物一体的境界领悟,其基本哲学思想和观点围绕中西哲学的发展历程而展开。杨国荣以哲学作为智慧之思,也着意沟通中西哲学。余敦康可谓接着梁漱溟讲,“从梳理中西印三种哲学同异出发,来探索哲学原理应当怎样展开,这是一条更为宽广也更为艰难之路,但也是中国自现代以来被公认的哲学之路。”[注]张法:《从四本哲学原理著作看中国当代哲学原理的演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关于为什么要开设哲学概论性质的课程,大家的意见差别不太,但对于如何从教育实际的角度定位此类课程则有所不同。张天飞、童世骏明确要在这门哲学的先行课程中讲“哲学ABC”的内容,而王德峰则申明自己“不注重对哲学知识的一般介绍”,而是集中于问题本身的深入讨论,“这种执拗,是决心不放弃哲学思辨的水准,不打算将哲学学说简化为通俗的观点”。[注]王德峰:《哲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6、67、68、前言6页。孙正聿认同个性化写作,也不认为这些写法之间是彼此矛盾的,他还最早对“哲学导论”“哲学概论”“哲学通论”的不同侧重作了思考和分析。他指出,“导”,侧重于“引导”“导引”,着重于深入哲学研究之前的知识性、思想性准备,即梳理和分析有关哲学自身的若干重要问题;“概”,侧重于“概括”“概述”,着重于概略叙述哲学相关领域,即概括和归纳哲学主要学科和分支的理论内容;“通”,侧重于“疏通”“通达”,着重于对哲学自身的追问,即在学理上探讨“哲学究竟是什么。”[注]孙正聿:《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4-245页。沈湘平则认为,“概论”“通论”都有居于各门具体哲学课程之上的意思,而“导论”则有居于各门具体哲学课程之前的意思,它的假定前提就是学生或读者对哲学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因此“哲学导论”的定位应该是使学生对哲学完成“从宫墙外望到初识门庭”的任务。[注]沈湘平:《哲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无论是内容结构还是呈现方式、语言风格,当今中国哲学通识课程、教材都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多元的时代,这不仅体现为学者自身强烈的自我意识,使中国的哲学及其教育从“无我”时代进入到“有我”时代,而且还在于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背景下能让更多作为“他者”的哲学概论类著述纷纷呈现出来。这其中又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当代西方学者的相关著作被译介过来。主要有布莱恩·麦基的《哲学的故事》(2002)、罗伯特·所罗门的《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2004)、罗伯特·保罗·沃尔夫的《哲学概论》(2005)、庞思奋的《哲学之树》(2005)、布鲁克·诺埃尔·穆尔、肯尼思·布鲁德的《思想的力量——哲学导论》(2009)、克里斯·霍奈尔、埃莫里斯·韦斯科特的《哲学是什么》(2010)、弗罗洛夫主编的《哲学导论》(2011)和道格拉斯·索希奥的《哲学导论——智慧的典范》(2014),往往成为国内哲学通识课的指定参考书。其中,所罗门的《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影响最大,有不少教师直接将之作为教科书进行讲授。西方哲学通识教材往往以设置不同的主题为框架,显得别具一格,以《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为例,自我、自由、美……以常见的问题引发思考开头,进而鼓励读者表达自身看法,强调“哲学主要不是研究其他人的观点,而是努力用尽可能有说服力、尽可能使人感兴趣的语言清楚地表述你自己的观点,这才是做哲学。”[注]罗伯特·所罗门:《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西方哲学通识教材的一些特点也在改变着中国哲学通识教材和教法。
二是1949年前的一些哲学概论类名家教材被重印出来。例如,蔡元培的《简易哲学纲要》(2015)、范寿康的《哲学通论》(2013)等。不过,怀旧、致敬或作为研究资料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用于通识教育方面的作用。
三是台港地区一些相关教材在内地出版。例如,沈清松主编的《哲学概论》(2004)、唐君毅的《哲学导论》(2005)、邬昆如主编的《哲学概论》(2005)、傅佩荣的《哲学与人生》(2005)和《哲学入门》(2011)等。由于有别于内地的独特历史经历,港台地区较早开设哲学通识教育课程,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和完善,哲学通识教育体系相对成熟。除上述在大陆地区出版的著作外,赵雅博(1975)、吴康和周世辅(1978)、李雄挥(1989)、陈俊辉(1991)、劳思光(2001)等先后出版哲学概论类著作。与一般的大陆教材不同,他们往往能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乃至印度哲学比肩而谈、试图融会贯通。正因为如此,台港地区的相关教材不像纯粹的西方同类教材见“西”不见“中”,内地读来很亲切,也往往是将之作为立足中华文化进行融通的先行者来予以学习、借鉴。
总的来看,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的重新发生的哲学通识教育,已经改变了国人对哲学的认识,改变了中国哲学教育的版图,以一种多元、自由的方式实现了与世界的接轨,同时又存有或生发了哲学的中国特色,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与维度,对于当代青年扩展人文视野、提高人文素养、促进思维训练乃至领悟人生智慧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哲学通识教育历史与现实的启示
通过对哲学概论类教材的分析,我们可以管窥,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教育及其通识教育的曲折历程事实上是中国融入世界、走向现代化,从追随、模仿到自主自信建构的曲折历史的缩影。今天,中国已经全方位地与世界保持同步,乃至,由于走进“强起来”的新时代,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不得不发挥着积极引领作用,从哲学的角度则是为人类问题的解决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这对我们的哲学通识教育反过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思百年历程、瞻望未来,有几点认识特别需要洞明。
一是哲学通识教育大势所趋,必须更加重视。一方面,就哲学自身而言,受现代学科分化的影响,当今哲学的学术研究日益呈现出窄域化、知识化、技术化、精微化、碎片化倾向,各专业“目无全牛”,缺乏对时代大问题的真正总体性思考,日益丧失整体性的智慧,背离哲学自身的规定性。哲学内部各专业“小国寡民”、彼此隔阂、自我陌生。哲学通识教育首先就体现为哲学内部的通识教育,正如百年哲学教育历史所示,哲学内部通识教育的诉求正是哲学概论类教材产生的首要动因。不过,在今天,我们在谈哲学内部的通识教育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注意,那就是全球化不仅使不同民族、国家的生产、交往方式趋同,而且使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危机、困境,作为一种反映,哲学必然要具有世界性的维度。马克思早就着眼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这也是哲学必然、必须走向内部通识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不仅是哲学自身,而且是所有的学科都急遽分化,“道术将为天下裂”,“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庄子》),不同学科对自身的前提性追问和前瞻性探索都需要哲学的襄助。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冯友兰指出的,各门具体科学完成的主要是使人成为某种人,而哲学功能在于使人作为人成为人,这是每个人的必修功课,成为人比成为某种人更重要、更根本,这是所谓通识教育中人文教育的根本所在。人人需要哲学乃是因为哲学本就不外在于每个人,哲学通识教育不过是从教育的角度去落实这样的本真。
二是中国特色的“概论”方式恰恰是中国哲学研究及中国哲学教育的优势所在。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在世界之林的地位日益取决于其文化软实力,而哲学正是文化活的灵魂。毋庸置疑,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发源于西方,这也就意味着在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去谈哲学就有一种“原罪”,不仅在于冒着“两种语言在根本上不可翻译”(奎因)的艰难、风险去理解本是“他者”的哲学,反思构建自己民族的哲学,而且在于无论怎么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都只能是一种努力,而不可能彻底。如此,从学术的角度看,中西方学者之于哲学并非公平的竞争。对于西方学者而言,可以从自己的语言、文化轻松进入堂奥,在内容上完全不管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也未尝不可。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不了解西方哲学而谈论哲学就让人怀疑其合法性。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反而获得了一种“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老子》)的优势。在1949年前,中国学者就对中、西、马乃至印度哲学有所融通。改革开放后的再发生,哲学概论类的工作一直受到“打通中西马,吹破古今牛”的揶揄和讽刺。就其水平而言,毕竟“通”的时间太短,确实不乏可批评之处;但就其努力方向而言,这恰恰是当代中国人对哲学理解不同于甚至优越于西方的地方。西方由于他们的“优越”而不必要去“打通中西马”,而中国却因为历史的原因走上了这样一条可以彼此参照、印证、补充的融合之路,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各种片面性。这既是中国的哲学自我理解的自觉,也是中国的哲学教育的自觉,对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哲学教育以及中国人的哲学素养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我们也相信,这种“打通”后的中国哲学智慧不仅会重构中华民族的“哲学自我”,为中华民族面临的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法论启示,为中华文明永葆活的灵魂,而且在人类面临主要是由西方文化带来的困境时,提供更多优越于西方的中国方案。
三是要保证哲学通识课程、教材的公共性讨论。哲学通识类课程、教材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再生以来,走过20多年,经过拓荒和奠基,已经进入百花齐放的多元化阶段。不仅有大陆学者自己撰写或主编的教材,还有译介西方的教材和台港编著的教材,哲学通识类、哲学概论类书籍也成为图书出版的一大类型,哲学概论类的通识课也成为各校的热门课程。当然,在生机勃勃的另一面也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于是,希望以一种教材作为范本甚至试图将哲学概论类教材定于一尊的想法和努力就出现了,但到目前的结果还是无能为力,所谓的范本最终也不过是作为众多“本”中之一。哲学概论类教材的多样性并非中国如此,西方也如此,而且是古来如此,说到底,这是由哲学的本质属性所导致的。正如黑格尔指出的,“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于它的本质,对于它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页。每一本哲学概论类教材都写出了作者心中的哲学,也都是带领别人进入哲学的一条路径,但并非完全就是哲学自身,也非唯一的路径。的确,“哲学犹如一个公共世界,问题不在于我们能否获得一致看法,而在于我们能否始终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同一个它。当我们只从一个角度去看,或者只允许它从一个角度展现自己时,哲学就走到了尽头。”[注]沈湘平:《哲学导论》,第297页。这正是不同的“哲学导论”“哲学概论”“哲学通论”得以确立的合法性根据。当然,目前的哲学概论类教材各自为战、彼此少有沟通的状况也是有必要超越的。至少,应该成立相应的组织,定期开展哲学通识教育的学术研讨、研修,以哲学的方式即反思批判的方式进行平等的公共性讨论,在互动中促进整个哲学通识教育水平的整体进步。
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地位及其自我认同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前已及,改革开放中再生的哲学通识课程和教材最初针对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绪论”部分的“独立门户”。事实上,哲学概论类课程、教材的迭出,内蕴着一种一般哲学的诉求,正在或已经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原理、一般哲学的地位。在很多哲学概论类课程和教材中,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西方哲学中的一种,甚至干脆不予提及,或者以批判、讽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着讲来获得自己课程教材的合理性、合法性。如今,随着中国传统哲学作为国学的核心被激活,中国哲学逐渐获得了一种时代的合法性。由于早年中国哲学本身就是在西学东渐之后反思性建构起来的,其当代化与西方哲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加之新儒家特别是海外新儒家的阐释,看似对立的“中”“西”在全球化时代恰恰直接构成纠缠、互动的“对子”,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诸哲学的平等对话显得顺理成章,中西汇通也成了很多学人的自觉追求。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壮大起来的西方哲学,已经从西方哲学在中国,走向了与西方的哲学研究联为一体。当中西哲学直接互动、汇通的时候,中心与边缘、主角和配角的位置发生了反转,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其尴尬地发现,在这场必将影响中国未来哲学格局甚至是文化走向的“对话”中,自己在很大程度处于失语、缺场状态或是沦为配角。面对中、西哲学的夹击和哲学概论类课程教材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改革发展问题变得十分的急迫。